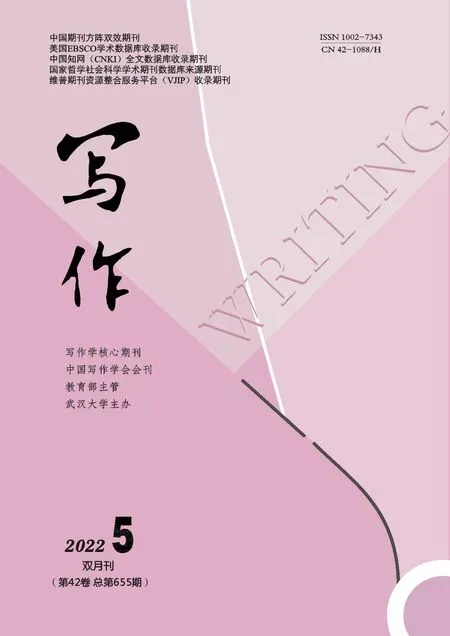幻想的越界與限制
——《貓頭鷹恩仇錄》“凱爾特神話”的閾限寫作機制與功能
吳翔宇 任超
在20世紀的復興運動中,凱爾特文化的復魅與英國幻想兒童文學的興盛具有同步性。從啟蒙主義運動到工業革命初期,由于清教主義者和資產階級保守黨的共同倡導,“幻想”長期被視為理性與道德的另一面而加以限制。“新時代運動”的尋根潮流發掘了潛藏在主流意識形態之下的凱爾特文明,并試圖將其抬升到足以同西方文明兩大源頭相提并論的高度①葉舒憲:《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0頁。,在文學上的標志之一是重拾因鼓吹理性與科技而招致否棄的幻想力。這一時期,英國幻想兒童文學以重寫神話的形式復現凱爾特所推崇的“靈性世界觀”,柴郡作家艾倫·加納(Alan Garner)的長篇幻想小說《貓頭鷹恩仇錄》(The Owl Service,1967)可被視為典型。加納將威爾士神話融于幻想文學,利用神話與現實的動態關系表現兒童文學“為兒童”與“為文學”的邏輯本體。在處理神話與幻想小說的關系時,加納并非將神話簡單圖解和改編,而是充分利用了“閾限寫作”的機制與功能。神話與儀式構成了“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因此,“閾限”理論介入幻想小說,為洞悉幻想兒童文學的深層結構及審美意蘊提供了新的方法與路徑。
一、凱爾特復魅中的幻想:從“教訓”到“神話”
在文化復魅熱潮中,“反傳統”的凱爾特文化與兒童文學產生了交匯,促進了幻想的流變。自兒童被“發現”以來,兒童文學的發展在兒童觀的牽引中一度伴隨著“為教育”還是“為娛樂”的爭議。1750—1860年間,作為一種“協商”①Colins Manlove.From Alice to Harry Potter:Children’s Fantasy in England.Christchurch:Cybereditions Corporation,2003,p.18.手段,幻想通常被用于平衡兒童文學的“教育性”與“娛樂性”。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推行下,英倫三島一度迷失在科學與技術的陷阱中,完全將理性至上視為圭臬,造成幻想的受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將此運動稱為“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科技的進步不僅促進了人類的理智化過程,同時楔入了西方文化中持續千年的除魅運動②[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6-17頁。。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基督教新教試圖減除神話與巫術的成分來建構理性的絕對權威。為了穩固發展,精英階層把文學中所有的魔法手段“都當作迷信和罪惡加以擯棄”③[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丁曉軍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79頁。,倡導對兒童居高臨下進行教導的“嚴肅文學”“勸善文學”“教化小說”和科普類圖書④舒偉:《從工業革命到兒童文學革命——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6-67頁。。幻想小說與童話被視為禁忌,伴隨而來的是,“教育性”在與“娛樂性”博弈中的勝出。然而,“唯理派”實則陷入了邏輯與現實的雙重困境,這一定程度上給幻想提供了發展的空間。一者,對“理性”的絕對崇拜在宣揚“去魅”的同時也締造了“理性”無所不能的“神話”。工業文明的超速推進將英國帶入不具有任何目的的“物化世界”,引發了維多利亞人的“信仰困境”。幻想從道德的傳聲筒中脫離出來,開始以貼合現實的潛隱狀態在童話與小說中懷念過去,在裂隙中給予人們精神的撫慰。二者,兩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在現實層面給盲目的理性崇拜敲響了警鐘,戰亂帶來的生存危機使人們看清了科技的另一面。為了緩解恐懼,人們轉而走向了私人性質的幻想領地,以此反抗人性的異化,呼喚人與自然共生的生態觀念。究其本質,理智化是神圣性的反面,它是祛魅或驅除神圣化之道具,它所帶來的必然是信念倫理和價值理性的解體,是一個實質理性不斷萎縮、工具理性不斷擴展、責任倫理成為主旋律的演變過程⑤王澤應:《祛魅的意義與危機——馬克斯·韋伯祛魅觀及其影響探論》,《湖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因此,當理性至上的空想泡沫破碎時,隨之傳來的便是讓文學“復魅”的呼喊。
由文學的“復魅”引發的文化變遷突出表現在對“魔法與劍”等幻想元素的召喚,這與“新時代運動”的尋根思潮產生了交匯。新一代的信仰者開始追逐“二希”文化之外的“異教思想與知識體系”,其中包括巫術、女神及自然崇拜、中世紀史詩、神話傳說等為代表的原始信仰,“反傳統”性質的凱爾特文明在此時受到了人們的大力推崇。作為英國三島文化的一脈,凱爾特文明一直潛隱在傳統“二希”文明——即古希臘文明與古希伯來文明的遮蔽之下。工業革命期間,雖然英倫三島均是全球經濟流通與資源掠奪的受益方,但是三島內部的文化沖突始終如影相隨,主要表現為南部的英格蘭人與北部的蘇格蘭人、西北的愛爾蘭人之間的離心張力⑥葉舒憲:《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頁。。隨著復魅思潮的興起,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因與工業化進程聯系緊密、宣揚人類中心主義而破壞自然、滅絕生物等原因遭到了普遍質疑。同時,凱爾特文化則以其“推崇巫術與魔法”“恢復人與自然的原始親緣關系”等觀念獲得了人們的支持,并在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生根開花。20世紀初,第一個把獨木舟推下水的人是內斯比特(Edith Nesbit),其《砂妖精》(Five Childre and It,1902)開辟了書寫“日常巫術”(everyday magic)幻想小說的新形式⑦彭懿:《西方現代幻想文學論》,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頁。。到了20世紀中期,凱爾特元素與兒童文學有了更為深入的對接,幻想為其提供了有利的“位置”,打開了解決最頑固的失敗和恐懼的可能性⑧T.E.Apter.Fantasy Literature:An Approach to Reality.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p.6.。以艾倫·加納、蘇珊·庫伯(Susan Coo-per)為代表,他們將凱爾特神話與幻想小說嫁接,企圖通過歷史的回聲來塑造一種“新傳統”。蘇珊·庫伯的《大海之上,巨石之下》(Over Sea,Under Stone,1965)與艾倫·加納的《貓頭鷹恩仇錄》分別是對凱爾特神話“亞瑟王傳說”(The Legend of King Arthur)與《馬比諾吉昂》(The Mabinogion)的現代書寫,他們接續了J.R.R.托爾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C.S.劉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等人對“第二世界”的構建,在神話傳說的“歷史回溯性”中充實幻想兒童文學的表現形式。
C.S.劉易斯、J.R.R.托爾金等人在20世紀初期創作的“納尼亞傳奇”系列(The Chronicles of Narnia)與“魔戒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開啟了英國兒童文學書寫本土神話的風潮。艾倫·加納、蘇珊·庫伯等人均在前者的基礎上對神話傳說開展了更新的嘗試。其中,艾倫·加納的作品被路易莎·史密斯(Louisa Smith)認為是對神話“最微妙和最復雜的使用”①Louisa Smith,Peter Hunt,ed.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2004,p.452.。幻想在加納作品中呈現出“反傳統”的“越界”傾向,這與傳統宗教所規制的“魔法不能涉入現實”的教義相違背。反觀“納尼亞傳奇”系列,三個孩子通過衣櫥進入了充滿魔力的第二世界,衣櫥象征著連接幻想與現實的紐帶;“魔戒三部曲”以及《霍比特人》(The Hobbit,1937)等作品則徹底擱置了現實世界,主人公雖然有矮人、精靈、巫師等具有歷史文化氣息的非人角色,但是故事均發生在與現實世界相區隔的“第二世界”。也就是說,幻想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有著明確的界限。與C.S.劉易斯和J.R.R.托爾金不同,艾倫·加納的幻想小說更加注重歷史材料和古老神話之間的融合,他通常讓兒童主人公在了解神話背景的同時進入神話,親自參與到相關時空的冒險之中。作為柴郡的本土作家,加納自幼受到威爾士與盎格魯·撒克遜兩種文化的交互影響。經歷過高等教育之后,艾倫·加納逐漸對“去魅”的理性派失去信心,成為了復興凱爾特文化陣營的一員。隨著《寶石少女》(The Weirdstone of Brisingamen,1956)、《蘇珊的月亮手鐲》(The Moon of Gomrath,1963)等作品的發表,艾倫·加納有意淡化了現實與幻想無法相融的傳統教義,并且將凱爾特神話作為故事背景,利用神話去“試圖解釋一些事情”②Alan Garner.“Coming to Terms”.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1.2(1970):16.。一方面,這類兒童小說以威爾士山村為背景,故事中的人物、語言、環境均帶有威爾士的民族色彩,以兒童視角展現了民族性與現代化的張力。另一方面,幻想的“越界”構筑了幻想與現實的新型關系,現實世界與原始神話產生了時空的交互與重疊,幻想世界甚至主動“入侵”現實世界。在融通幻想與現實的同時,作家開始關注兒童的內心世界,借助神話的“閾限性”展現兒童成長中復雜的心理變化。
當然,幻想的“越界”并不意味著幻想兒童文學可以脫逸出兒童文學元概念的“本體”意涵,從而造成幻想的“失控”。如齊普斯(Jack Zipes)所言,具有實驗性質的童話具有顛覆性的潛力,但這種“顛覆”的程度必須有限③Jack Zipes.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London:Routledge,2011,p.105.。也就是說,作家在兒童文學中表現幻想的同時仍需考慮“幻想的限度”,此處的限度就是要以現實為依托。兒童文學是倚靠“兒童的”與“文學的”雙層邏輯的文學,幻想兒童文學借用神話資源自然也需要符合兒童文學的生產機制。具體而論,在轉化神話和傳說故事時,一味地迎合兒童的喜好容易造成“文學性”的流失,削弱文本的現實性。對此,佩里·諾德曼(Perry Nodelman)提出“彌補”式的改編策略,在引進異文化時,讓它們變得更加熟悉、更容易接近④[加]佩里·諾德曼、梅維絲·雷默:《兒童文學的樂趣》,陳中美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頁。。因此,在為兒童創作幻想文學時,作家仍需處理好“幻想”與“現實”的關系問題。
艾倫·加納認為,將神話引入兒童文學不是源于神話的敘事性,而是反映現實的隱喻性:“神話不是逃避,也不是娛樂,而是一種接受現實的嘗試”①Alan Garner.“Coming to Terms”.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1.2(1970):17.。在《貓頭鷹恩仇錄》中,加納始終以克制的筆法表現幻想與現實的交融,他巧妙地將凱爾特神話《馬比諾吉昂》中的三角關系嫁接到三個孩子身上,有意安排主人公談論魔法入侵現實的現狀。其中,神話人物的悲劇與三個孩子的結構性關系超越了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言的“模糊的極限”②[英]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徐文博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頁。而呈現出真實性。換言之,從神話傳說中汲取思想性的兒童文學借助幻想的形式揭示兒童的主體需求,通過兒童視角反思傳統與現代的復雜關系,表現出對更深層次的現實與永恒真理的普遍追求。不同的是,這種“兒童的視角”區別于對童心的“真空”崇拜,而是植根于現實的。這即是說,幻想不可能獨立于看起來令人沮喪的“真實”世界,而是存在于一種與現實的寄生或者共生關系中③Rosemary Jackson.Fantasy:The Literature of Subversion.London:Routledge,1981,p.12.。幻想兒童文學的“反傳統”仍需要立足“本體”框架,源于現實而又不完全依附于現實,才能真切地還原童年的精神力量。
二、解讀神話:作為幻想兒童文學方法的“閾限”
作為一種民族資源,復魅時代的凱爾特神話形構了英國幻想兒童文學的新傳統。然而,神話傳說自帶的瑰麗“想象”與兒童文學中的“幻想”并不完全等同。現代兒童文學在借用或重述神話資源時需要對該種想象進行轉化與加工。因此,解讀幻想小說不得不重新認識“幻想”與“想象”之間的轉化機制,不得不解讀神話在幻想小說中的具體表現形式。在《貓頭鷹恩仇錄》中,加納并非將神話簡單地圖解或改編,而是借助過渡儀式的“閾限書寫”來表現真實與幻象、自我與他者、神話與現實的融通。通過從想象到幻想的“過渡”,幻想兒童文學將讀者帶入那原始或神圣的時間里,給予個體一種“根”的感覺④[美]杰克·齊普斯:《作為神話的童話作為童話的神話》,趙霞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因之,某種程度上,神話與儀式構成了“思想”與“形式”的關系。立足“何以能”的問題,由“過渡禮儀”引申的“閾限”理論作為解讀幻想兒童文學的方法具有一種普適性。
儀式研究興起于19世紀。在儀式的界定中,它不僅被當作具有重復性質的象征活動,也被視為幫助處理混亂的人類經驗,將之整理成為有序框架的一種分析類型⑤[美]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頁。。其中,范·熱內普(Arnold van Gennep)提出的“過渡禮儀”(rite of passage)理論影響深遠,他將儀式視為包含“分隔—邊緣—聚合”的動態過程⑥[法]阿諾爾德·范熱內普:《過渡禮儀》,張舉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0頁。。作為后來者,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推進了“閾限時期”(liminal period)的相關研究,在前者的基礎上生發了對“閾限性”(liminality)的思考。不同的是,范·熱內普提出的“邊緣”概念“對應的是‘中心’或‘主流’”⑦張舉文:《重認“過渡禮儀”模式中的“邊緣禮儀”》,《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3期。,意在突出邊緣的“對立”屬性;而后者使用的“閾限”則強調一種“反結構性”的文化狀態。但是從兩者的共性來看,他們都承認個體在成長的不同階段會經歷各種“過渡”,即包含著“對結構和交融及狀態和轉換的交替性體驗”⑧[英]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頁。。對于少年期的兒童來說,順利度過青春期的“閾限階段”是其成長的必經之路。幻想兒童文學在表現少年兒童的“過渡”時,不僅要考慮兒童在生理層面的過渡——身體從幼年成長為成年,也要關注兒童向成人轉變過程中的心理層面的渴望與猶疑。同時,兒童步入成年亦是從個體走向群體的社會化過程。借助儀式的過渡,個體經驗會與社會公共秩序互動⑨Roy A.Rappaport.Ecology,Meaning and Religion,Richmond:North Atlantic Books,1979,p.188.,并受到社會力量的形塑。
閾限實指過渡的關鍵階段,閾限時期被視作“位于結構之間的”人類之本性的本土概念①[美]維克多·特納:《象征之林》,趙玉燕、歐陽敏、徐洪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93頁。。受到范·熱內普的影響,特納將儀式結構化為“閾限前”“閾限”“閾限后”三部分。具體而論,“閾限前”是儀式的“分隔”階段,個人或團體離開了先前在社會結構中的固定位置,脫離原有生命狀態從而進入分隔后的“過渡狀態”之中;閾限階段是新舊交替、半明半晦的過渡狀態,充滿不定性與危機感。閾限期間存在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儀式行為,代表舊體的個性轉變與地位更替。這也是儀式主體面臨考驗與接受教誨的時期;融合階段即新生的個體正式作為社會整體中的一員,回歸世俗生活,以新的社會角色建立新的人際關系與生活習慣,擔負成年的職責。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將過渡儀式視為向上的通道:“正是這種通道使從一種生命模式向另一種模式、從一種存在狀況向另一種存在狀況的轉變成為可能。”②[羅馬尼亞]米爾恰·伊利亞德:《神圣與世俗》,王建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頁。然而,將閾限理論作為視角或方法時,需要深入文本的多維性中審視“古典式想象”與“現代式幻想”在小說中的聯結與融通,在神話與現實的表述裂隙中探究幻想兒童文學的本體蘊含。據此,可以延展出如下兩種形態與秩序:
(一)聯結與融通: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動態關系
在《為兒童及青少年的幻想文學》(Fantasy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2003)一書中,帕梅拉·蓋茨(Pamela S.Gates)等人指出,同神話傳說一致,幻想文學源自人們“對善與惡的斗爭的需要”③Pamela S.Gates,Susan B.Steffel,Francis J.Molson.Fantasy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Lanham,Maryland,and Oxford:Scarecrow Press,2003,p.2.。幻想兒童文學通過幻想的“可視化”(making visible)④Pamela S.Gates,Susan B.Steffel,Francis J.Molson.Fantasy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Lanham,Maryland,and Oxford:Scarecrow Press,2003,pp.1-2.追求深刻的現實性和真理的普遍性,同時滿足讀者的審美需要。幻想文學在以豐富想象力探索生活的奧秘時,可以不受時空的限制。一般而論,為了區分現實并凸顯幻想的特殊性,幻想兒童文學通常構建了兩個相區隔的空間。首先,存在一個依托于現實世界的現實空間,它與我們日常的生活世界沒有什么不同。除此之外的“第二世界”或“另一世界”,是包含“魔法與劍”的幻想空間,亦是兒童“內心世界”的代理。為了制造兩個世界的連接點,表現兩種空間的轉換,儀式書寫是幻想小說家常用的方法與策略。儀式在幻想小說中具有“從現實世界到作為對現實生活的觀照和激情的藝術”⑤[英]簡·哈倫·哈里森:《古代藝術與儀式》,劉宗迪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82頁。的過渡作用。因此,在“閾限”理論的視域下審視兩種空間的動態轉換,有利于厘清幻想兒童文學在表現外部世界與內心世界的復雜關系。
然而,從兒童文學的生成機制來看,幻想兒童文學并沒有脫離成人為兒童書寫的“代際”關系,幻想仍要遵守成人制定的規則,受到成人意志的控制。正如彼得·亨特(Peter Hunt)所言,許多幻想世界根本不能迎合一個正在發展的心靈⑥Peter Hunt,Millicent Len.Alternative Worlds in Fantasy Fiction.London:New York Continuum,2003,p.4.。一旦成人話語遮蔽了兒童的主體性,則易造成“童年—成年”整體性的斷裂。例如,《彼得·潘》(Peter Pan and Wendy,1911)即是一部“反成長”小說。對于現實世界而言,永無島是完全“懸置”或“孤立”的,彼得來到現實世界的唯一動因是迎接下一個“溫蒂”來滿足自己“天真的家庭夢”。無論是彼得永無島的現實冒險,還是其精神層面的幻想運動,其身體和精神都沒有成長,都停歇于“現實與幻想的延長線及深處”⑦吳翔宇:《代際話語與性別話語的混雜及融通——〈彼得·潘〉的性別政治兼論兒童文學“不可能性”的理論難題》,《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9期。。從本質上看,空間的區隔實則為“一些特定的、無法破除的對立所統治”⑧包亞明主編:《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頁。。“不想長大”的彼得代表了美化純真與童年的成人意志,這與兒童渴望成長的主體性相違背。
20世紀的社會經歷巨大變革,思想的解禁推動了幻想的越界。現實空間與幻想空間在兒童文學中也由完全分立逐漸轉向了接壤、碰撞甚至融合的關系,并以神話與禮儀的形式“自由地進行統管”。換言之,幻想與現實兩個世界的結構化傾向得到解放,開始發展為一種新的關系,即特納所謂的“空想的交融”①[英]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頁。。從思想上看,現代兒童觀逐漸生成,成人作家開始關注和重視兒童的特殊性,進而著力構建幻想空間來反映兒童的內心世界。從形式上看,“魔法與劍”不再是幻想世界的專屬,也成為現實世界的常客,現實與幻想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可以說,二者在空間形式上的交融體現了閾限階段的特征。具體而論,若要探析兩種空間的動態關系,尤其要對象征心理世界的內部空間進行形象學分析。其中,作為兒童文學表現“內宇宙”的常用意象,家庭空間起到了庇護幻想的功能。家宅是“回憶與無法憶起之物的結合”,它既是身體又是靈魂,是人類最早的世界②[法]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張逸婧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頁。。在《貓頭鷹恩仇錄》中,艾莉森臥室頂部的閣樓與整棟房子實為一體,但從掉落的灰塵來看,閣樓的空間是在很久之前與外界分隔的。因此,葛文所推開的門雖然有別于普通住宅的立式大門,卻也可以看作連接現實世界與密閉空間的儀式通道。這與《納尼亞傳奇》中的衣櫥、《湯姆的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1958)中的花園功能類似,通往魔法世界的機關被設置在家庭的某個角落。不同的是,在《貓頭鷹恩仇錄》中,艾倫·加納模糊了開啟魔法世界的標志,葛文進入閣門后感知的魔法與原有的現實世界產生了重疊。
在敘述兩種空間的交融時,艾倫·加納利用語言制造神話與現實相融的“威脅氣氛”③Andrew Taylor.“Polishing Up the Pattern:The Ending of The Owl Service”.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3.2(1992):94.,看似簡單的句子卻包含了豐富信息量。例如,加納在描寫葛文進入閣樓的狀態時暗示了處于空間交融階段的主體感受:“當我抓起疊在最上面的盤子時,一陣奇怪的感覺貫穿全身。握著盤子的手上有一種刺痛感,隨后一切都變得模糊不清……只有當我回過神,又能看得清真切時,情況才有所不同。反正有些東西已經變了。”④“When I picked up the top plate,I came over all queer.A sort of tingling in my hands,and everything went muzzy…only when I could see straight agagin,it was different somehow.Something had changed.”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10.為了凸顯故事的真實性,加納有意弱化了魔法的視覺呈現,而是通過兒童身體和心理的感知來表現兩重世界的動態關系。
(二)過渡期的復雜性:“游走者”的審美悖論
在分析高年齡段兒童的閱讀心理時,班馬曾提出“兒童反兒童化”的理論命題:“從兒童心理視角出發,所達到的反兒童化,是為兒童自身的心理狀態及其傾向。兒童自身的反兒童化傾向,其精神在于擺脫自身的兒童狀態之動因。”⑤班馬:《前藝術思想:中國當代少年文學藝術論》,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1996年版,第518頁。此處涉及的“兒童美學悖論”,班馬將其概括為兒童對“無主題形態”與“主題形態”兩種游戲精神的追求。在“無主題形態”中,兒童展現出對原始性與生命力的追求與釋放,體現了兒童的某種“投射性本能”,即對布魯克斯(Peter Brooks)所述“至善”(ultimate good)⑥[美]彼得·布魯克斯:《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欲望對象》,朱生堅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頁。身體的渴望。處于“主題形態”游戲中的兒童,則試圖擺脫成人對其身份定位的強勢介入,通過勞動和游戲來扮演成人的角色與模擬社會“實踐”活動⑦[蘇]瓦·亞·蘇霍姆林斯基:《學生的精神世界》,吳春蔭、林程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5頁。。
毋庸置疑,閾限理論概括的模糊特性較好地解釋了過渡期間“兒童反兒童化”的審美悖論。特納指出,閾限前后表征為“狀態”的改變。在閾限階段,儀式主體“很少帶有或者不帶有任何過去的或即將到來的狀態的特性”①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86.,而處于“模棱兩可”或“似是而非”②[英]維克多·特納:《象征之林》,趙玉燕、歐陽敏、徐洪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93-94頁。的中間狀態。落實到幻想文學中處于過渡儀式的兒童,其閾限階段可以引申為兩個層面的內涵。其一,兒童想要脫離原初的兒童狀態,過渡為“理想的他者”。其二,兒童仍然對成為“他者”的不確定性感到猶豫甚至恐懼,有退回“原初自我”的傾向。換言之,在將青少年兒童作為主人公的作品中,作家往往通過幻想的形式表現主人公在兩種“狀態”之間的游移。兒童以“游走者”的身份徘徊于兩個空間之間,這既是成長面臨的現實困境,亦是成人作家試圖傳遞給兒童讀者的精神指引。
在文本中,當葛文在雞舍發現艾莉森拓剪貓頭鷹紙片時,艾莉森“忙個不停,專心極了”。隨后葛文試圖阻止,艾莉森采用了“掙扎—放聲大哭—哀求”的方法,終于剪完了最后一只貓頭鷹。然而,隨后她的身體卻發抖得厲害,對著葛文哭訴:“我好怕。你幫幫我吧。太可怕了,你不明白。”③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83.艾莉森在雞舍拓印的過程,正是處于過渡儀式的“邊緣”階段。運用閾限理論分析艾莉森的行為,此刻的艾莉森正是一名“游走者”,她進入了“明日”,“并且連‘昨日’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在此處的“昨日”“今日”“明日”,即是“分隔”“邊緣”“聚合”三個儀式過程的表現。一方面,布勞狄薇的附身,激發了艾莉森對魔法的好奇與控制欲,她不由自主地想要通過拓印來獲得山谷的力量。另一方面,當神秘力量真的降臨時,艾莉森又產生了對未知的恐懼與焦慮。在完成貓頭鷹拓印的同時,艾莉森感知到了這股力量背后的宿命邏輯。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加納致力于通過儀式書寫表現兒童對于“身份問題”④Sarah Beach.“Breaking the Pattern:Alan Garner’s The Owl Service and the Mabinogion”.Mythlore 20,1(1994):11.的思考,艾莉森的“游走者”形象不僅體現在她對于魔法力量的游移,還深層次地表現在面對葛文的感情與母親的控制時的曖昧態度。可以說,在提取布勞狄薇力量的同時,艾莉森即感知到了女主人的堅韌意志,也意識到了其命運的不公。艾莉森對“湖中倒影”的身份猜想暗示了她對布勞狄薇的肯定,“但我看得出來那就是我——頭發的顏色,臉……反正那就是我”“窗玻璃上一定是我的倒影”⑤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126.。在內心深處,布勞狄薇是艾莉森“理想的自我”,艾莉森試圖與葛文相愛以效仿這種“反叛”。然而,葛文的“理性”卻一再否定了其對“自我”的想象,“所以從你所在位置的角度怎么也不可能看見自己的倒影。那并不是你的倒影。不可能是的”⑥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125.。這無疑加深了艾莉森對“自我”的懷疑。最終,艾莉森徘徊在葛文的消極態度與母親“退出合唱團與解約網球俱樂部”的警告之中,呈現介于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游走”狀態。事實上,“游走者”形象并非僅出現于幻想兒童文學之中,在以兒童主體與兒童成長為主題的作品中也并不鮮見。在閾限理論的視域中觀照“游走者”,有利于從整體層面把握童年向成年過渡的復雜性。
作為“方法”,閾限理論介入幻想兒童文學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幻想與現實的勾連需要借助閾限的區隔及融通,并以此匯聚為成長議題的動態觀照。《貓頭鷹恩仇錄》以解讀神話的方式展示幻想兒童文學的內在結構、機理,從而表征了作家加納的思想意涵。與此同時,閾限理論的運用也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源自幻想兒童文學“元概念”的多歧性上。尤其是當其中雜糅著現實與幻想、成長與反成長、越界與鎖閉等多元范疇,這種張力與限制容易造成閾限理論邏輯不自洽的問題。由是,在時段的切割、主體性的標尺、觀照點的確立等方面容易造成理論偏誤,這是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究的理論問題。
三、反傳統的張力:閾限的內在機理、表征及省思
閾限理論的適用性是需要條件的,文本的語言與思想都要切合理論的學理邏輯。同時,討論幻想兒童文學的相關理論問題,需要返歸“兒童是什么”及“兒童文學是什么”的本體。語言既是形式工具又是思想本體,文學語言的本體性集中體現了“道”與“器”的合一①吳翔宇:《中國兒童文學語言本體論:問題、畛域與路徑》,《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4期。。這種特性對《貓頭鷹恩仇錄》文學思想的生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艾倫·加納采用“簡單語”的策略,以簡單的語詞傳達更為清晰、豐富、美妙的含義。另一方面,艾倫·加納運用“第三種語言”凸顯威爾士方言的民族性,并借助威爾士語與標準英語的融合介入民族性與現代化的基座,建立一種“互為他者”的視野。其次,在反思清教思想與理性主義遏制幻想的基礎上,艾倫·加納摒棄了舊式兒童觀的保守與成人化局限,將幻想延伸至更為廣闊的神話空間,拓寬了幻想兒童文學的表現領域。基于對“實體童年”而非“觀念童年”的現實觀照,艾倫·加納并未忽視兒童的“內宇宙”與外部環境的關系,著力描繪兒童“個體性”與社會“群體性”的互涉,在民族文化情志的映襯中重構童年的精神價值。此外,艾倫·加納對神話資源的使用不局限于素材層面,神話作為一種“經過提煉的真理”②Alan Garner.“Book Review the Death of Myth”.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1.3(1970):69.被應用于《貓頭鷹恩仇錄》的敘事思維之中,在結構性的“立與破”之中最終指向了“反傳統”的思想層面。總之,在閾限視域下對《貓頭鷹恩仇錄》進行個案分析,作品在“語言”“內宇宙”“思維”三個維面均體現出艾倫·加納“反傳統”的思想觀念。
(一)“反傳統”的語言:介入民族性與現代化的基座
出生于柴郡工人階級的工匠家庭,艾倫·加納自小接觸的即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語言文化。受益于1944年英國頒布的《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Act),艾倫·加納先后進入曼徹斯特文法學校和牛津大學接受精英教育,在語言研究方面頗有成就。兒童文學創作需要考慮兒童的語言能力與閱讀水平,因此使用適合兒童的敘事語言是作品成功的關鍵。從《寶石少女》《蘇珊的月亮手鐲》《貓頭鷹恩仇錄》來看,艾倫·加納的主要讀者群體是處于青春期的青年兒童,但是作家仍然將“簡單語”作為其兒童文學創作的語言策略。他表示“文本內容的豐富程度與語言的復雜性成反比。我寫得越簡單,我能說得就越多”③Alan Garner.“Achilles in Altjira”.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8.4(1983):7.。換言之,艾倫·加納利用“簡單語”排除了混淆和隱含的意義,削弱了兒童理解文本的難度。同時,清晰的文字卻提供了更加開放的“可闡釋空間”,讀者更易擺脫作家敘述的主觀性。《貓頭鷹恩仇錄》對結尾的處理體現出“簡單語”的魅力:“Oh yes they are flowers!And you know it!Flowers,Ali.Quietly,now.Flowers.Flowers.Flowers.Gentle.Flowers—”④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214.通過羅杰的呼喊,正處于儀式的閾限階段的艾莉森度過了由貓頭鷹向花的蛻變。羅杰對“Flowers”一詞的重復營造了戲劇式的緊張感,讀者既能體會到羅杰對艾莉森的關切,也能構想出艾莉森處于羽毛和花瓣紛飛的儀式場景。
此外,《貓頭鷹恩仇錄》的語言并非通篇采用“標準英語”,艾倫·加納將威爾士方言融于故事的對話當中,試圖以介于威爾士語與標準英語之間的“第三種語言”來權衡民族性與現代化之間的矛盾。加納說過:“我所有的寫作都是用一種真實的北方的聲音與文學流暢的語言相結合。因為如果我想跨越我的故事,我需要這兩種語言。”①Alan Garner.“Achilles in Altjira”.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8.4(1983):8.為了將民族語與標準英語有效地結合,必須對方言的詞匯及語法進行精妙部署。例如,《貓頭鷹恩仇錄》中的方言與威爾士神話形成了一種創造性的呼應:“他冷靜地殺了葛榮,不帶一絲憤怒、愛或憐憫……她是被領主創造而成的。沒有人問過她是否想要嫁給葛榮。被迫和自己不太喜歡的人在一起是痛苦的。我想她一定時常想起以前在山上的日子,那時的她是美麗的花朵,而現在她變得殘忍,就像玫瑰身上長出了刺。”②“He is killing Gronw without anger,without love,without mercy……She was made of her lord.Nobody is asking her if she wants him.It is bitter twisting to be shut up with a person you are not liking very much.I think she is often longing for the time when she was flowers on the mountain,and it is making her cruel,as the rose is growing thorns.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67.休在向羅杰敘述《馬比諾吉昂》的傳說時,都采用了動詞的進行時態,即動詞的“威爾士”形式,在這種時態中,“很自然地加強了在山谷中重新被喚醒的神話的永恒”③Michael Lockwood.“‘A Sense of the Spoken’:Language in The Owl Service”.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3,2(1992):88.。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曾言:“語言就其內在聯系方面而言,只不過是民族語言意識的產物。”④[德]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7頁。可以說,該神話在威爾士語的講述中被賦予了新的意義,這不復是新舊現象的衍伸,而是在現代視角下演化出了一種積極的自身生命力和活動力⑤[德]恩斯特·卡西爾:《語言與神話》,于曉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39頁。。
從結局來看,葛文無疑是個失敗者,無論是他繼承的威爾士語,還是他習得的英語,都不能向他提供合適的聲音和身份⑥Michael Lockwood.“‘A Sense of the Spoken’:Language in The Owl Service”.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3.2(1992):91.。葛文對待民族母語的疏離態度,反映了現代化社會對民族文化傳統的沖擊。而身為威爾士人,葛文也不愿意在公開的場合使用方言,試圖學習英語改變自己的口音。當羅杰與葛文發生口角時,羅杰就以正音教材中的入門課程諷刺葛文的口音及出身。由于羅杰的階級優越感中,葛文與之決裂,語言成為摧毀葛文心理建設的關鍵一環。因此,葛文在兩種語言之間的徘徊既源自城市現代化對鄉村民族文化的同化與吞噬,也產生于威爾士民族自身的落后觀念以及個人的自卑心理。無論是“簡單語”還是“威爾士語”,艾倫·加納都在“反傳統”的框架中構建作品與讀者、傳統與現代的交互關系。
(二)“反傳統”的“內宇宙”:“自我感”與“群體感”的互涉
在《阿喀琉斯在阿爾特吉拉》(Achilles in Altjira,1983)一文中,加納將兒童文學創作歸納為“故事是什么”“用什么語言講述”兩個問題,其中“語言”部分前文已經作了相關闡釋,而故事被其解釋為“解讀現實的媒介”⑦Alan Garner.“Achilles in Altjira”.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8.4(1983):5.。總體上看,艾倫·加納創作的幻想兒童故事沒有受困于西方舊式兒童文學觀的制導,涉及了神話與現實、倫理與自由、民族與階級等多個“反傳統”的悖論。除了加深幻想與現實的動態聯系,加納不斷擴展幻想兒童文學的表現領域,進一步提升兒童文學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他認為兒童文學應該廣泛地表現兒童的閱讀需求,不應該讓步于傳統觀念對題材或主題的限制:“我開始寫作是因為我覺得孩子可能是我唯一能交流的人。我們可以在這里觸及性、審查制度和有關神的主題,但是我認為,那些說孩子不應該接觸這些事情的人實際上沒有意識到童年的本質。”⑧Alan Garner.“Coming to terms”.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1.2(1970):21.在表現兒童主體與意識形態客體的互動時,加納設計了一種“反傳統”關系。這種關系擺脫了傳統兒童觀的限制,深入青年兒童成長期的內心變化,以童年的獨特視角呈現兒童的“自我感”與歷史、傳統、倫理的“群體感”之間的深層聯系。
事實上,在展現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互涉關系時,作家必須要深入民族文化的內核,利用“浸透文化重量的書寫”①方衛平:《童年寫作的厚度與重量——當代兒童文學的文化問題》,《文藝爭鳴》2012年第10期。彰顯文化場域中的童年力量。以神話《馬比諾吉昂》為原型,加納的《貓頭鷹恩仇錄》巧妙地將神話人物的宿命悲劇復刻于現實世界的三個兒童身上。加納將神話意識作為表現“同一感和生命感”②[德]恩斯特·卡西爾:《神話思維》,黃龍保、周振選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196頁。的工具,借助儀式書寫設計了兒童個體與群體意識的互涉關系。面對身份問題時,葛文的內心一度在“自我感”與“群體感”之間搖擺。作為保姆的兒子,葛文與艾莉森之間的曖昧關系使其回避甚至厭惡自己是一名威爾士人。存錢買唱片機學習正音教材,上夜校進修,都是葛文向往城市生活、擺脫鄉下人身份所做出的努力。此時,葛文的自我意識與威爾士族群存在裂隙,他并未找到自己所認可的集體與歸宿。然而,在得知身世的特殊性之后,葛文貪戀山谷的魔法與權力,即刻將自己視為威爾士人的一員。當艾莉森處于生死邊緣,休與羅杰共同求助于他時,葛文卻忽視了昔日的情誼,將艾莉森、羅杰視作與山谷無關的異鄉人而冷眼漠視:“我留下來是為了幫你和這座山谷,決不是為了他們。”“我不會為他們做任何事。我跟他們沒有瓜葛了。”③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210.個體性若完全寄宿于群體性之中,則容易造成自我的迷失。過度沉溺于繼承者的角色,葛文游移在怨恨與郁結之中,最終被陳舊腐朽的思想吞噬,失卻了“本真的自我”。正如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所言,神話塑造的超自我形象,是兒童效仿的對象,只有兒童主體放棄對“伊底”④[美]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童話的魅力:童話的心理意義與價值》,舒偉、丁素萍、樊高月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76-77頁。和“超自我”⑤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67.的盲目順從,認識到人性的弱點時,他才獲得了完整的人性⑥[美]布魯諾·貝特爾海姆:《童話的魅力:童話的心理意義與價值》,舒偉、丁素萍、樊高月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76-77頁。。通過神話和儀式,加納還原了童年向社會群體接近時的真實底色。
(三)“反傳統”的思維:對傳統與現代的雙向批判
從某種意義上說,神話不僅能以獨立的文學性成為幻想兒童文學的組成部分,也可以作為一種思想資源推動兒童文學的現代化⑦吳翔宇:《作為“方法”的神話——論中國兒童文學對神話資源的化用與限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5期。。神話本身即是一種意識形態,神話對思維的傳遞通過“對虔誠化‘范型’之刻意模仿”⑧[俄]葉·莫·梅列金斯基:《神話的詩學》,魏慶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78頁。來完成。換言之,神話具有的某種普遍性思維需要經過獨特的結構形式進行展現。為了凸顯神話的內在生命,作家在化用神話資源的同時往往會著力書寫由此類“范型”具象化的儀式。因此,儀式因其具有的結構性特征成為理解神話思維的方法。在《貓頭鷹恩仇錄》中,艾倫·加納效仿了威爾士神話《馬比諾吉昂》基于“永恒三角形”(an eternal triangle)⑨Carolyn Gillies.“Possession and structure in the novels of Alan Garner”.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6.3(1975):113.的底層結構。傳統神話的敘事通過主人公的自主發現以及休的指引逐漸清晰,布勞狄薇對自由戀愛的追求觸犯了封建倫理的禁忌,怨恨的黑色力量始終留在山谷,化為縈繞千年的悲劇之源。布勞狄薇—葛榮—里奧克勞的三角結構以儀式性的輪回復現于艾莉森—葛文—羅杰三人身上。
從休與葛文、羅杰的對話中可知,三角結構的輪回儀式已在威爾士山村里延續了上百年。但是不論是神話中的魔法師,還是休的祖父輩,都深陷于傳統倫理觀的框架,不能真正尊重和包容布勞狄薇對愛的追求。休是第一個站在布勞狄薇的立場對傳統進行反思的人,他認為這并不是一次“背叛”,“因為她是一件為領主訂做的禮物,沒有人問過她愿不愿意嫁給這個男人”①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67、p.213.。羅杰率先認識到,拘泥于三角關系的傳統結構中只會造成同樣的悲劇。由神話暗示的結構模式并不會因為仇恨消除,只能依靠下一代的新生力量去重塑。
布勞狄薇所代表的這股力量,在休以及其叔叔、祖父看來形同洪水猛獸,是災難和厄運的象征。他們只會徒勞地“把她封進壁畫,封進餐盤里”②彭懿:《這本書講述一個什么故事》,艾倫·加納:《貓頭鷹恩仇錄》,蔡宜容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197頁。,從未真正地反思厄運一再輪回的原因。然而,在羅杰眼中消解山谷的魔力“就這么簡單”,他寬恕了葛文,他的內心也感知到了“痛苦消失的平靜”③Alan Garner.The Owl Service.London: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2017,p.67、p.213.。羅杰持續的堅持,用溫柔的聲音改變了力的形狀,化解了艾莉森的自我郁結。附身于艾莉森的魔力因為理解而釋懷,它從剝奪人生命的恐怖能量轉變成了由金雀花、繡線菊、橡樹之華組成的淡淡清香。艾莉森身上紅色抓痕的消失預示著聚合階段的完結,布勞狄薇由貓頭鷹變回了花朵,縈繞村莊近千年的輪回儀式在此刻終被打破。看似圓滿的結局實則暗含了“反傳統”的線索:拯救者是羅杰而非讀者期待的葛文。葛文最終的命運會如何?三人的友誼將走向何處?艾倫·加納對結局的從簡處理體現了一種反常規的創作思想:沒有設置帶有說教意味的“唯一解”,而是給文本提供了更多思考和質疑的空間,引導“兒童自己進行研究,自己去推理”④Herbert.Education:Intellectual,Moral,and Physical.London:William&Norgate,1911,p.124.。
從整體來看,《貓頭鷹恩仇錄》的結構源自神話,卻又打破了神話。艾倫·加納將人情的溫暖與冷漠楔入于《馬比諾吉昂》的元結構,通過顛覆讀者的期望重申神話對人性的洞察力⑤Andrew Taylor.“Polishing Up the Pattern:The Ending of The Owl Service”.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3.2(1992):99.。在結構立與破的背后,實則隱含了作者對傳統與現代的審思。面對威爾士神話的悲劇,艾倫·加納沒有依循舊倫理觀的軌轍,而是以現代兒童的視角承認了布勞狄薇追求自由之愛的合理性。布勞狄薇對自由之愛的向往是一種源自底層的樸素情感,最初便存在于神話的原始思維之中。然而,在現代化社會發展的背后,人們的真實需求一再讓步于理性與效率,現代性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往往束縛了人們的真實自我。“貓頭鷹”的復魅與新生,對當下文明依然具有警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