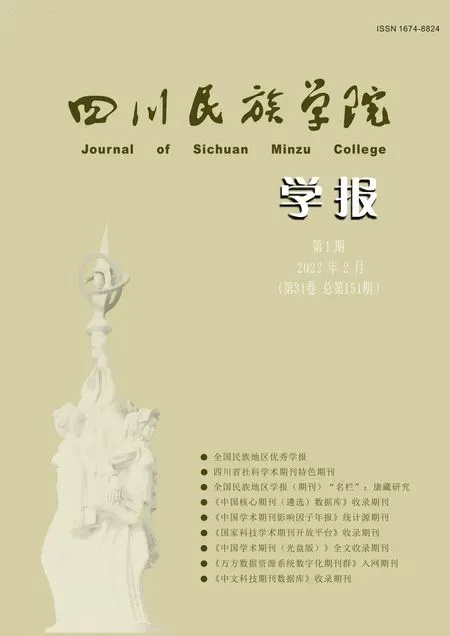成都地區五代十國音樂圖像研究綜述及反思
蘇 俊
(成都師范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
縱觀五代十國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唐末北方戰亂導致經濟和文化重心歷史性向南轉移。距離長安(今西安)數百公里外的成都以政治安定、獨具特色的文化魅力吸引晚唐文人雅士和樂工舞伎入蜀,促使唐風樂舞和巴蜀本土音樂文化在該時期的高度融合,成都成為南方絲綢之路音樂文化北進中原與南、北絲綢之路多元音樂文化交融、發展的重要樞紐。此時的成都不僅保存唐代音樂文化的精髓,更為宋代音樂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在中國音樂文化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成都現已發掘五代十國前蜀、后蜀大量手持樂器的陶俑、石棺刻畫的樂舞圖、石窟中雕刻的演奏者。因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前蜀高祖王建墓石棺上二十四張音樂圖像,其他較為稀少,故本文對該區域五代十國墓葬、石窟音樂圖像研究成果統一梳理并探討。
一、音樂圖像樂器考辨研究
1939 年秋,寶天鐵路工程隊在成都市區西門建防空洞時發現一處古墓。1941 年春,四川省人民政府聯合四川大學成立四川博物館,遺址發掘工作正式啟動。1943 年 9 月,在中央研究院和國立中央博物院的協助下發掘工作全部結束。修筑在中室的棺床背面雕大朵蓮花,其余三面均為浮雕女伎樂。其中東、西面各有十尊伎樂,正面兩尊樂女和兩尊舞女,每副石雕音樂圖像高度約25厘米,因石雕共有樂者22人、樂器23 件、舞者2 人[1],學界也稱“二十四伎樂”,現公開展示在成都市永陵博物館內。王建墓石棺上的音樂圖像研究主要集中在石棺樂器考辨:1955年,考古發掘者之一的楊有潤在《王建墓石刻》中圖文并茂地對石棺中每件樂器批注名稱[2];1956年,楊有潤參與日本召開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公布該組音樂圖像照片,日本東亞音樂研究學者岸邊成雄根據照片予以一一定名, 1979年,翻譯《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寄王建墓管理所。1988年,樊一譯《王建墓棺床石刻二十四樂妓》在國內公開發表,并認為樂器編排非常接近唐、宋宮廷燕(宴)樂樂隊編制[3];1957年,本次考古發掘的主持者馮漢驥在《前蜀王建墓內石刻伎樂考》指出“這部器樂浮雕屬于唐代燕樂(宴樂)系統,歸屬龜茲樂和清樂樂器”,根據音樂史料相關論述對圖像中的樂器種類及名稱定名[4];1982年,俞松云《永陵樂舞石刻》認為王建墓石刻中的音樂圖像描繪的是唐五代宮廷中的“燕樂”形態,也對每幅音樂圖像闡述了樂器定名原由[5];1992年,李成渝《王建墓浮雕——樂器研究》首次對前面學者關于王建墓音樂圖像中的樂器定名諸說整理性研究,并提出自己對樂器名稱的觀點[6];2012年,鄭以墨《往生凈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與十二半身像研究》,依據敦煌中的伎樂圖像和圖像學研究方法對馮漢驥,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前期樂器定名深度剖析,同時提出自己命名及原由[7];2019 年,永陵博物館王建墓研究院劉仕毅《永陵棺床鼓類石刻樂器芻議》針對鼓類分歧較大的樂器命名重點闡釋,并對永陵博物館展覽區樂器標注說明[8]。從上可見,王建墓從挖掘者、音樂學者、考古專家、博物館研究者等相繼對石棺上音樂圖像樂器種類提出自己的觀點,但均未達成共識,主要分歧代表如下(見表1)。

表1 王建墓石棺音樂圖像樂器分歧代表性觀點
1957年,四川省博物館對成都市彭山觀音鄉后蜀宋琳墓進行挖掘。1958年,四川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任錫光為代表的考古隊發布《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簡報》,其中提及棺座正前方有三個樂舞伎[9],暫無該音樂圖像的研究成果;2011 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隊對成都市東門十陵鎮五代十國后蜀宋王趙廷隱墓進行挖掘,考古報告沒對外公布。后續彩繪樂俑研究成果閆佳楠在《趙廷隱墓出土樂舞伎俑音樂文化研究》一文從樂器命名、舞蹈種類等方面詳細介紹出土樂俑分男女樂俑,男樂俑 2 件,女樂俑 20 件,其中一女樂俑的樂器遺失無考,男樂俑所奏樂器皆為笛。女樂俑所奏樂器有方響 1 件、排簫 2 件、笙2 件、笛 2 件、篳篥2 件、四弦曲項琵琶 1 件、拍板 1 件、都曇鼓 2 件、正鼓 2 件、答臘鼓 1 件、雞婁鼓并鞉牢鼓 1 件、細腰鼓 1 件、大鼓 1 件,共計 22 件、14 類樂器。[10]該文的樂器命名和數量與成都博物館展覽廳的趙廷隱彩陶伎樂俑批注有少量出入,因考古報告沒有公布,無法考證; 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樂至縣文物管理所發布《四川樂至縣報國寺摩崖造像踏查記 》考古報告圖文并茂描述該摩崖石刻一共8窟,其中有2個石窟有豐富的音樂圖像,對窟1的十二種樂器做了詳細的說明,窟5僅手繪圖闡釋第二層左右各五名伎樂,其下有兩名樂者、頂部有多個樂器,[11]并沒有文字性說明該石窟不同區域樂器的具體名稱及數量;2019年,林戈爾在《 當代古蜀樂樂隊建制構想》以樂至縣報國寺石窟樂俑為歷史來源點構想建立古蜀樂樂隊數據庫[12],但該研究中的十七件樂器數量與考古報告并不一致。
二、承唐啟宋音樂歷史研究
五代十國時期,成都地區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藝術氛圍吸引了大批文人雅士入蜀,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唐五代成都藝術文化圈,為中古歌舞伎樂向近古戲曲音樂轉型提供了有利條件。1984年,何昌林《唐五代西川音樂之一瞥》列舉唐五代時期四川的各種音樂形式,說明當時四川音樂的繁榮景象源于盛唐遺風[13];1986年,楊偉立、胡文《前后蜀宮廷中的音樂歌舞初探》對前后蜀教坊機構、歌舞種類進行研究,粗略地勾畫了前后蜀宮廷音樂歌舞的基本輪廓[14];1988年,秦方瑜在《五代南方藝苑的奇葩——王建墓石刻伎樂與南唐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的比較研究》一文中對王建墓和《韓熙載夜宴圖》中石雕樂舞的音樂歷史價值和美術史意義分別予以闡述[15];1992年,趙為民在《試論蜀地音樂對宋初教坊樂之影響》從《宋史》關于教坊記載中樂工來源和數量闡述五代十國時期后蜀在音樂上對宋教坊的重要影響[16];1994年,秦方瑜、朱舟在《試論王建墓樂舞石刻的藝術史價值》一文中從王建墓石刻史闡述唐代樂舞的流布軌跡和藝術史學價值[17];2009年,包德述在《唐五代時期南北朝絲綢之路多元音樂文化在成都的傳播與交融》中以《南詔奉圣樂》在成都完成過程史料記錄與王建墓樂舞石刻遺物來說明成都在五代十國時期擔負南北絲綢之路音樂文化傳播與交融的重要樞紐作用[18];2010年,羅天全《前后蜀是唐宋音樂傳承的紐帶》從宋初教坊樂工來源考、宋初教坊體制來源考、蜀派教坊樂工技藝記載說明該時期宮廷音樂編制和樂工在宋初宮廷傳承中的重要作用[19];2014年,謝艾伶在《后唐宮廷音樂興衰之緣由考》一文中過,以盛唐遺風和民族風俗文化兩個方面闡述五代十國時期成都音樂的風格特征來源和現存遺物的歷史價值[20],該類研究主要通過考古中出土的音樂圖像佐證和豐富史料記載。
還有少量關于舞蹈名稱研究,如秦方瑜先后在《王建墓石刻伎樂與霓裳羽衣舞》,《王建墓石刻樂舞伎演示內容初探》認為王建墓中的其中兩舞伎所跳正是唐代流行的霓裳羽衣舞,樂隊反映了唐代宮廷坐部伎演奏燕(宴)樂的風貌和編配形式[21-22];2017年,閆琰《后蜀趙廷隱墓出土花冠舞俑與柘枝舞》一文闡述其中舞伎的姿勢是唐五代時期最流行的柘枝舞,柘枝舞與胡旋舞、胡騰舞并稱為“西域三大樂舞”,后蜀樂舞形式與唐代宮廷配置形式一脈相承[23]。該類研究主要是圖像學常用的“看圖說話”,通過外在舞蹈姿態和裝扮對該時期樂舞形態的初步猜測。
綜上所述,成都地區已出土的五代十國前蜀高祖王建墓、后蜀宋琳墓、后蜀宋王趙廷隱墓及后蜀樂至縣報國寺石窟均有較豐富音樂圖像。不同學科專家從不同視角對音樂圖像進行研究,極大的推動了成都地區五代十國這段歷史的研究價值。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單一考古地址中音樂圖像的個案性研究,并無對該區域音樂圖像整體性研究。研究方向集中在音樂圖像樂器考辨和音樂史學價值研究兩大板塊。如:五代十國前蜀高祖王建墓石棺音樂圖像中的樂器命名占據了10篇論文/專著,多運用目前世界通用演奏性功能樂器分類法命名,其中分歧最集中在鼓類樂器,表1已列出具有代表性爭議觀點。其次研究數量較多的是從出土相關音樂圖像結合史書記載闡釋唐五代時期成都在承唐啟宋的歷史地位和音樂史學價值,該類研究多運用考古學中常用的“二重證據法”,即史料記載和地下出土文物互相佐證;后蜀宋王趙廷隱墓沒有公開考古報告, 三篇論文分別從樂器命名、舞伎的舞種和衣著頭冠與道教文化交融上猜測,其中《趙廷隱墓出土樂舞伎俑音樂文化研究》該文的樂器命名和數量與成都博物館展覽廳的趙廷隱彩陶伎樂俑批注有少量出入,因考古報告沒有公布,無從考證;后蜀樂至縣報國寺石窟的音樂圖像研究僅考古報告,一篇古蜀樂樂隊建設構想的論文提及該石窟伎樂,但樂器種類和數量同樣沒有達成共識。總之,成都區域王建墓、趙廷隱墓及報國寺石窟研究成果爭議問題都涉及音樂圖像的樂器考辨。
三、研究反思
筆者認為,研究結果沒有達成共識的主要原因是參與發掘的一線考古工作者、文物管理人員及少量藝術學研究者僅對單個墓葬中的陶俑、石磚浮雕、地面遺存石窟雕塑樂器命名或分類等個案性研究,缺乏對該區域音樂圖像整體性研究。例如:從王建墓浮雕中爭議最大的鼓類來看,墓室石棺雕刻中的“鼓”不僅是對當時某種音樂場景的模仿,也是一種美術創作加工后的“鼓”,更是喪葬儀式中墓室文化的“鼓”。王建墓25厘米高的石棺浮雕作品中的“鼓”從形態上已經與實物有了新的創新,音樂圖像呈現的形態和現實中的樂器必然存在一定差異,僅個案性研究是不能滿足音樂圖像發生規律,唯以區域性音樂歷史研究為中心,建設五代十國考古發掘和地面遺存的音樂圖像數據庫為基石方可緩解研究過程中的這些爭議問題。通過選擇一定區域相關的事物的共性,獲得普遍性歷史發展規律,并把有著相似形態特征的音樂圖像組合在一個音樂文化時空之中,最終找出成都地區在唐宋銜接關鍵時期音樂文化變遷和發展動力中的本體文化與外來文化交融變異動態走勢圖。從整體的數據庫走向個案性多學科研究,并以科學懷疑精神圖文互佐,弱化音樂圖像研究中的二度創作帶來的考辨問題。這也是本文以成都地區五代十國音樂圖像研究整體綜述的出發點。比如:王建墓音樂圖像中的十五種樂器與唐代史書記載龜茲樂比較,沒有五弦、侯提鼓、檐鼓,但又新增加了羯鼓、鞍牢鼓、拍板、葉等新的樂器種類,這到底是唐樂在五代十國時期成都地區新發展還是美術工匠筆下的偶然事件。又如:王建墓石棺上的簫顯示十管,唐史書記載多是十六管或二十三管[24]。王建墓中的簫到底是漢代十管簫在成都區域的樂器形態遺存,還是工匠在尺寸限制下美術作品的二度創作?音樂圖像個案研究還不足以真實反映音樂景象,唯獨建立區域性數據資料庫方可弱化工匠二度創造性,最終為研究唐宋時期音樂的承傳轉變及五代十國社會生活、喪葬禮儀、文化思想等提供更為準確的參照依據。
縱觀西方圖像學研究發展史,藝術史學家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藝術史學家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美國德裔猶太學者,著名藝術史家。在圖像學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影響廣泛。其中《圖像學研究》(1939)和《視覺藝術的含義》(1955),它們對圖像學這一藝術史領域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是較早探討美術作品中的圖像,他把音樂圖像研究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依照常識辨認音樂場景中的對象和基本形態;第二層是參考史料記載發現與音樂形象相關的文化或習俗含義;第三層是通過視覺中的圖像去研究形成這種音樂圖像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個體心理特征,最終探索音樂圖像背后的深層意義。羅斯基爾(2)羅斯基爾:美國抽象派畫家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男,1903年生于俄國,抽象派畫家,抽象派運動早期領袖之一。在著作《圖畫的闡釋》中也指出音樂圖像的闡釋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叫“圖說”;第二個層次是“詮釋”;第三個層次是“估測”。按照以上圖像學經典理論來看,目前針對成都地區五代十國王建墓或趙廷隱墓中的音樂圖像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第一層“圖說”,即依照常識辨認音樂場景中的對象并進行分類。對音樂圖像中樂器名稱的考辨、舞蹈名稱猜測占了相當大的數量。作者認為,中國的音樂圖像是古代雕塑家或者美術家通過作品創作讓音樂景象參與到社會生活中,體現的是文化中的音樂,此刻的音樂景象主旨是喪葬文化、禮樂文化、民俗文化等直接表現手段,不同于影像資料記錄音樂表演場景或者拍攝具有演奏功能的樂器。中國的音樂圖像從誕生之初就以音樂景象展現音樂文化為目的,反映該區域生命形態的精神面貌,展現歷史中區域文化的基本社會特征。從古文獻所載“河圖”“洛書”(3)“河圖”“洛書”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兩幅神秘圖案,蘊含了深奧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譽為“宇宙魔方”,是中華文化、陰陽五行術數之源。“河圖”“洛書”在現存文獻中最早收錄于《尚書》,其次在《易傳》以及諸子百家亦有收錄。到戰國“按其圖以想其生”(4)出自《韓非子·解老》:“人希見生象也, 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乃至宋代形成并傳承至今的“金石學”(5)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偏重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中國音樂圖像自古都展示的是一個廣泛的文化綜合體,體現區域群體共同認知、審美和哲學思想,與西方美術作品中的圖像學研究有完全不一樣的文化起源和社會結構,這恰是中國音樂圖像研究價值所在和特殊性質。由此可見,中國音樂圖像研究不僅需要從區域性數據統計分析結果弱化美術工匠者的二度創作,更要打破西方圖像學常規研究中的三層次順序關系,從中國歷史文化出發,多學科、多視角中準確解讀音樂圖像后的深層文化含義,建立符合中國氣派的音樂圖像學研究體系和方法。
四、結語
成都區域相繼出土的五代十國音樂圖像在音樂史上的意義及其對宋文化的影響均有很高的研究價值。1942年,成都市一環路出土的前蜀皇帝王建陵墓石棺上二十四幅音樂圖像完美地呈現出前蜀宮廷樂舞的盛大規模及壯闊場景;1957年,四川省博物館對成都市彭山城北觀音鄉后蜀宋琳墓進行發掘,棺座正前方有三副石刻樂舞圖;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龍泉驛區發現后蜀宋王趙廷隱墓共計二十余件彩繪樂俑;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樂至縣文物管理所對四川樂至縣報國寺摩崖造像公開發布考古報告,其中2窟有大量音樂圖像遺存。成都地區不斷涌現的五代十國考古成果讓我們更加清楚意識到該區域音樂文化歷史價值,但大多墓葬和石窟中的音樂圖像“后發掘”并不充分,研究成果較少,這無疑是對整個五代十國音樂文化研究的重大缺憾。2020 年 12 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一文,對如何做好我國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做了重要指示: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是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25]。本文意在梳理成都地區五代十國音樂圖像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前期研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反思和探討,相信通過諸多學者不斷努力,必將有更加完善的中國氣派音樂考古圖像研究體系和更豐富的圖像研究成果誕生,在傳承、保護與創新音樂圖像所體現的中華文明基礎上找到文化研究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