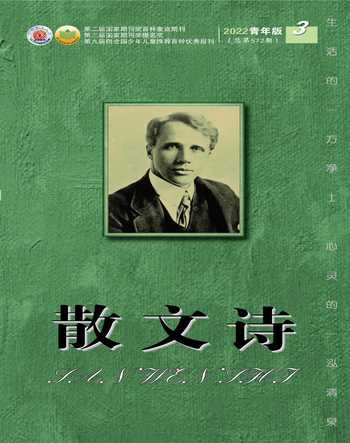叫做穆恩的人
杜輝
題記:此時,打谷場上正在落日……
獻 辭
尖頂谷囤,站在自己逐漸伸長的陰影里。斑駁枝干,零散懸掛著麻雀的舊禮服。光,時松時緊,夜的容器不急于被裝滿。忙碌了一年的作物停止思考,天空松弛的眼瞼垂向池塘,所有牲畜都被藏進黑暗,只有夢中的眼和翅膀還掛在樹巔。叫做穆恩的人,在通靈者的暗示里跋涉。過去、現在與未來似乎匯聚于一點。
黑 鐵
人們自導自演古裝劇。
秸稈、竹竿、木棍充當寶劍,沾滿污跡的道袍、鎧甲、王冠、笏板,還有一匹不存在的瘦馬。許多人輪流著成為朋友、仇敵、親人,以及陌路,源源不斷的喜怒哀樂在磚頭城堡里上演。稻草垛山嶺容易攀爬,矮土墻城池難于攻陷,樹枝畫出的江河永遠無法跨越。庭院里,田壟間,池水旁,冰面上,不時傳來身體和器物的碰撞聲、嬉笑聲和咒罵聲。然而,他們更想擁有的是一把真正的寶劍。在圖片和露天電影里,那些通體雪亮的寶劍,在白衣劍客手中上下翻動,巧舌如簧,神氣十足。
直到有一天,人們偶遇一把真實而具體的劍,一把漆黑的、拙嘴笨舌的劍,確切地說,那是一塊沉重且并不鋒利的鐵。彼時,月亮似乎還是干將、莫邪時的月亮,卻沒有山,沒有松生石上,沒有眉間尺……有的只是井水冰涼刺骨,貓頭鷹的圓眼睛掛在堤壩下的影子里,石磨盤泛著安靜的青光,矮土墻上貝殼在星斗間隱秘旅行,谷物還在麻袋里孕育。黑暗中,叫做穆恩的人取出那塊鐵,就像扛著一把衰老的農具,毫無敬畏。他說,那是一把看家護院的家什,他爺爺以及他爸爸守夜時用過,甚至,冬日里還用來扒爐灰……這時,他們才發現,鐵的一端有些彎曲,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與之相反,多年后的某次參觀,燈火通明,陣仗隆重,氣氛莊嚴:同樣其貌不揚的鐵,躺在寬敞舒適的玻璃柜里,泰然自若。大多數朝拜者都若有所思,嘖嘖稱奇,有人竊竊私語,仿佛一切都感同身受。但如果真正的親歷者能夠在場,他一定選擇沉默。因為,他揮舞過的器物不計其數,而這塊鐵過于具體,以至于它并不那么“真實”。
回想那塊更加親切的鐵,它的粗野、傲慢和滿不在乎,卻更加鮮活,它極有可能是一個人一生中觸摸到的、最初的、毫不修飾的真實。
涂 鴉
學校對面的馬路邊有一間店鋪,它開著極小的窗,旁邊的紅磚墻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這些用滑石寫的字停留在那里,已有許多年。
他們喜歡在墻上隨意涂寫:五顏六色、毫無主題的曲線,鳥類簡筆畫,課本上學來的詞語,判斷句,沒來由的愛戀,無厘頭的挑釁,甚至是對某人完全無害的嘲諷。這些文字和線條就像永不謝幕的木偶戲,有趣的是,操縱者除了能在幕后操作,更能走到前臺欣賞自己的“杰作”,品頭論足之后,若無其事地走開,自然是,有人義憤填膺,有人心懷竊喜。店主是一位肥胖而安詳的老人,她從來沒有責備過那些涂鴉者,因為,她也有一個差不多年齡的孫女,她就是涂鴉者中的一員。她有著圓圓的、稚嫩的臉,細細的語聲,她的名字叫月亮兒。
夜晚,叫做穆恩的人來到雪后的圓形池塘上。起初,先是月亮在枯樹下涂鴉:多刺的王冠、瘦骨嶙峋的墨梅、野獸派的狂舞、忙碌的工業管道……他觀察了一陣,就從坡上緩緩下降到冰凍的池塘表面:隨著身體移動,腳步制造的每一次擠壓都富有節奏,那些松散的雪在腳下發出咯吱咯吱聲。雪并不很厚,影子在一長串腳印的指引下,來到池塘的中心,它更像是整個大地和時間的中心,他仰望夜空。此時,冰下的魚還在黑暗中摸索?植物的根系也保持著攀爬的姿勢?空氣清冽,一種神圣而純粹的力量,在他體內向各個方向生長。
后來,叫做月亮兒的胖女孩,帶著甜甜的笑容從池塘的另一邊走來。她也在雪的平面上涂鴉,兩串腳印在圓周中心交匯,如時針和分針……
機 械
在那部夢寐以求的破舊機械面前,叫做穆恩的人反復確認自身,確認踏板、曲柄、鏈條,以及車輪。確認所有這一切的真實性,然后,他飛奔著,來到一小段偏僻的土坡,讓自己和機械不斷滑行、磨合,心甘情愿地摔倒,再爬起……日復一日,直至身體可以與機械熟練地對話。
駕駛最初的機械,沿著狹窄而彎曲的道路,去繁華渡口。作物整齊的腳印從高處梳理下來,收割后的原野芬芳四溢,草蟲低聲吟唱,土壤沉穩有力。路邊粗壯的排水管道從廢棄的水泥泵房里鉆出,銹跡斑斑的鐵被炙烤得滾燙,景物讓人昏昏欲睡。只有水泥槽中偶爾投出的反光,刺得人眼睛酸痛。溜過最后一段斜坡,渡口的紅房子、白房子好像伸手可及,卻又像在云端,無法親近。回望來時的路,它隱約起伏,像一條蟒蛇臥在堤壩和田野之間。
駕駛最初的機械,來到水邊,河流巨大的畫面撲面而來。空氣足夠鮮活,腥膻里像是裹挾著無數條跳躍的小魚,初來者不由自主地大口呼吸,想要把一切都裝進身體。緊接著,聽覺也活躍起來,馬達聲,輕微流水聲,嘈雜人聲,在正午的陽光里攪拌、波動、跳躍、升高,不知疲倦。這是一種狂歡的氛圍,它逐漸包裹住每一個人。巨型輪渡把大河打斷的車流和人潮,一遍又一遍地連通。叫做穆恩的人踩在人字形紋理的鋼鐵甲板上,感受船底水波的流淌,那些隱藏在身體里的波浪也隨之律動。
駕駛最初的機械,從顛簸土路趕來。此時,落日正棲息在打谷場上。拓坯人用木頭模具制造出泥塊,再排列成規則矩陣,毛茸茸的草地上,許多平滑表面泛起金色光芒。這些等待成熟的糕點,正在構建希波丹姆的整齊街市。場院邊緣,燕子在電線上降落又起飛,這些正在演奏的五線譜,余音越來越弱。最后,暮色掩蓋了大平原上的一切,萬物都躺倒,只有那部破舊機械還屹立在夢中……
四 兒
不知什么時候,廣場上的兩根水泥柱之間升起了微微泛黃的幕布。夏日夜晚降臨了。
有人交頭接耳,也有人毫不掩飾地大聲說笑,賣冰棍的小販馱著白色木箱在人群四周不停叫賣,不知是誰在角落里燃起了蒲草用以驅蚊。巨大燈光突然亮起,幕布出奇地醒目。不斷移動著的圖斑,像許多奇怪的昆蟲時而緩慢時而迅速地爬行,電影放映機運轉的聲音是那么光滑。孩子們在幕布上做出各種手影,有的干脆把整個身體映上去,追逐的笑鬧聲不絕于耳。直至人群有些疲倦,四周漸漸安靜下來,蒲草細細的白煙升起。第一幀圖像突然跳出來,緊接著,懸掛在高處的擴音器里發出沉悶對話聲,所有人都被陌生而巨大的情景吸引了。
放映機在人群的中后部,放電影的是一個紅鼻子、小眼睛的矮胖男人。膠片轉動的整個過程盡在他的掌控之中,有時,他還要故意拖慢換膠片的節奏,給原本起伏的劇情平添了一點波折,如饑似渴的人群也被吊足了胃口。人們都說,他短而粗的手指能流淌出離奇的故事。真實故事卻更加離奇,相貌平庸的他沒有老婆,卻有四個漂亮女兒,最小的那個叫做四兒,她天生一副好嗓子。
放映場的微弱光線里,人們專注于幕布上的悲歡離合,只有穿著花襯衫的四兒對劇情熟視無睹,她稍側過臉,似乎正向穆恩輕輕哼唱:“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中狀元著紅袍,帽插宮花好啊……”那一年的那一刻,她雙頰燦爛如花。
小 站
從一處平交道口爬上鐵路路肩,然后沿著一側寬度不足一米的碎石小路前行。這是去往火車站的捷徑。
叫做穆恩的人跳到軌道上面。他有節奏地踏著枕木,像木偶那樣制造雷同步伐,一會兒工夫,就像是經過了許多年——這種重復步伐更容易讓人產生疲憊和幻覺。再一次眺望,視覺盡處的鐵軌閃著白亮的光,它們指向不可知的遠方。途中有一處小橋,站在上面,可以透過石板縫隙看腳下安靜的河水。揀起一小塊石頭投入河水,聽水流發出笨重的簡狀回響,隨后,河流繼續平緩前行,楊樹、田野和其他的石子也都平靜如初。陽光更加耀眼。這時,如果正好有火車經過,他會躲進橋上的“避難所”。那是橋梁向外側突出的像耳朵一樣的場所,它是專門為橋上的行人躲避火車設計的。站在狹小的平臺上,叫做穆恩的人感受滾地而來的鋼鐵巨獸從身邊怒吼著經過,手里緊握的鐵欄桿在跳動,腳下的石板在跳動,眼前的石子在跳動,心也在猛烈跳動。
終于到達站臺了。那是一處鋪著紅白石子的狹長平臺。它一面朝向小鎮最熱鬧的街道,一面朝向荒蠻的曠野,四根光亮的鐵軌分割這一切。當蒸汽機車巨大的紅色曲柄緩慢往復,大股水蒸汽不知從哪里涌出,不一會就淹沒了人群,遮蔽了景物。雷霆般的汽笛聲響起,火車就要啟動了。人們懷著些許驚懼,目光投向那移動中的龐然大物。叫做穆恩的人竟忘記了自己身為何物,是目送一個背影離去,還是居于眺望中的那個背影……
地平線上,列車和汽笛聲完全消散,眼前只剩熟悉的事物,離愁重新滋生。
芳 塵
傍晚時分,操場上的夾竹桃累了,沙子沉甸甸的,風把一切都放回原處。那個高年級的白皙高個子女生,在人群里,緩慢且虛幻。“凌波不過橫塘路”,仿佛許多年,叫做穆恩的人都坐在矮墻上的黃昏里,目送芳塵。
狩 獵
沿著冬天瘦削的脊梁,叫做穆恩的人不斷尋找獵物。昏黃背景里,北風堅硬,原野疲憊。大多數時候,他都一無所獲,空手而歸。
終于,他的目光止于視野盡處,那是一叢被季節遺忘的蘆葦。沿著人跡,他緩緩下降到水塘,那結了冰的表面……一會兒工夫,蘆葦叢已整齊躺在腳邊,它們飽滿的葉、莖和穗子仍閃著野性的光芒。他把它們捆成幾捆,那些原本松散的身體,瞬間被束緊了腰身。只有風中的葦絮不聽召喚,它們俏皮地牽著他的衣襟。土地沉睡如鉛,糧食在谷倉里繼續成熟,黃牛瞇起眼反芻,鳥雀的跳躍零散,陽光掠過東廂房外的榆樹枝頭。
從清晨的獵獲里起身,他翻過埡口,身體是大平原上唯一的移動。筆直的堤壩平面,幾只臃腫的鳥,在黑色電桿上凝固,電線在它腳下默默延長。壩里,那間米勒的小屋,雜亂器具中,冷靜地站立著一把犁。它的三角形犁鏵與眾不同,那是一塊磨得發亮的熟鐵,刃口仍向土地微微傾斜,鋒芒無法隱瞞。
他卸下蘆葦,那些將在春天修葺屋頂的蘆葦,被臨時安置在窗下,那里花崗巖和青磚已被陽光打磨得蒼白。門軸轉動,少量倫勃朗暗調被開啟,光止于陰影中的犁鏵:那順滑的榆木犁柄被握住且提起,像是一條剛被捕獲的梭魚。冰冷的鏵,它仍貼近地面,只是被偏移了一個角度,像是在壟間地頭的某次折返。
叫做穆恩的人勉強擠進門,將噼啪作響的蘆葦移植進屋子,如同獵人把新鮮的獵物從肩頭卸下,或許它們還有為數不多的心跳,但時間終將拿走這一切。蘆葦失去了最后的野性。他稍稍直起佝僂的身軀,門軸再一次轉動,隨意一瞥,停靠于墻角的犁鏵仍在閃光。重新匿于黑暗的刀鋒,蟄伏草莽的好漢,農耕時代的最后剃度者,以無邊寂寞為食。
期待再一次試刃:撣去滿身灰塵,重溫干燥原野。那思慮良久的熟鐵,將以雄性手勢,獵獲更多春天。
還 鄉
真實犬吠響起:樓群裂隙里,四根平行電線分割天空。月亮突然掛在建筑一角,就像某次交談中,不經意間流露出的一句鄉愁。叫做穆恩的人,從鏡湖沙數之上認出拱橋邊垂釣的老者。干枯柳枝上的風箏,還是幾十年前那只?可是,它已消瘦得只剩骨頭。
困倦時,萬物失效。蜂群逆光,嗡鳴聲不斷毀壞林陰,旅行者無法捕捉溝畔野花的芬芳。云彩以下,景物清透得瘆人,牧羊人能聞到自己的心跳。夕陽,把最后幾個孩子領向分岔小徑,叫做穆恩的人,借來道具:搖晃的井水,拍不響的鼓,舊面具,稻草人和幾顆星子。
通向村莊的道路是一條曲折的藤蔓,它在時光里不斷伸展。遠處,無限灰以上,目力所及的房屋是藤蔓的一片片葉子。炊煙向星座攀爬,露水打濕所有光滑的植物,蟋蟀不知在哪里喝醉后睡下了。此時,蟲聲與果實一同成熟,野貓試探著移動藍寶石。水銀燈晃動,叫做穆恩的人走出灰頂小屋,瞬間,蒼老的身體被無限拉長。
蘋 果
集鎮邊緣,有一片果園,這里偏僻而幽深,在幽深的更深處有一間茅草屋,那里住著沉默寡言的老者,沒人叫得上他的名字。
屋外有一條黃狗,它清瘦、衰老、倦怠,幾乎遺忘了叫喊。大多數時候,四周清澈,仿佛這是另一個平行世界。秋天,樹葉閃著革制的光,風把無數打擊樂器交替奏響,爬山虎連接土地和天空,蟲子低唱,鳥兒們有錯落的口哨聲和凌亂的飛翔,破碎的一切試圖編織更大的穹窿。后來,果園成熟的蘋果整齊地碼放在學校門口,仿佛最精致的藝術品。
老者表情專注而虔誠,一切更像是一種等候。只有果實在晨曦里閃著快樂的光,空氣里盈滿了香味。偏僻的紅色、黃色和綠色在熱鬧人群旁邊無法掩飾。那輛人力板車,木板腐朽得如同蜂窩,板車后面的他滿頭白發,一身褪色的藍布衣裳,沒有人聽到過他的叫賣聲。
白皙的高個子女生,聲音輕盈如蘋果的芬芳。那個黃昏,經過木板車時,她正輕輕哼唱:“你看,你看,月亮的臉偷偷地在改變……”一個陌生而蒼老的笑容打斷了她,又大又紅的蘋果遞到了她遲疑的手里。
那一刻,他的臉,閃著年輕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