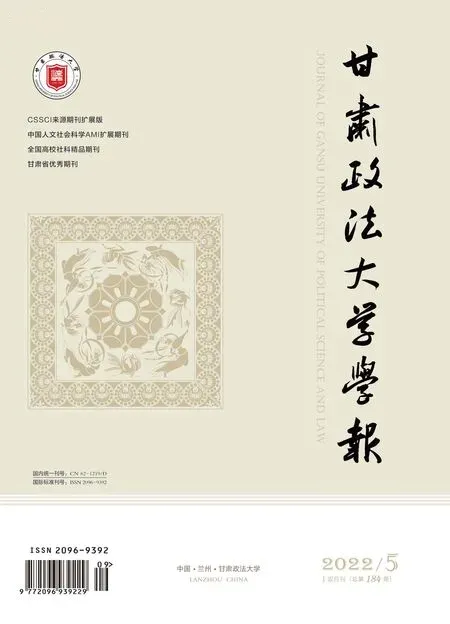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邊界
——以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否擴張至債務人配偶為中心
趙大偉
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是指在執行程序中,由執行部門依據當事人的申請,將執行力及于當事人以外第三人。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包括向債權人的擴張和向債務人的擴張兩種基本類型,向債務人的擴張主要為執行程序通過追加被執行人的方式,使第三人成為被執行人,一般認為,“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與“執行程序追加當事人”為一個含義。(1)參見陳計男:《強制執行法釋論》,臺灣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48-56頁;肖建國主編:《民事執行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譚秋桂:《民事執行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148頁。實際上,在我國強制執行制度背景下,“直接執行”也是一種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方式,該方式不需要執行程序追加,可直接執行第三人,其法律效果與追加為被執行人一致,即第三人以其財產對債務承擔給付責任。
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關系執行權與審判權的界分。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第三人,實質是執行權擴張,將本應通過訴訟程序解決的部分實體爭議轉歸執行程序處理,只是這種擴張需要充分且正當的理由。而執行力過度擴張,是在無正當理由的前提下,應由審判機構處理的部分實質爭議,卻被執行部門處理,屬于執行權濫用,這會異化審執關系,剝奪第三人的程序權利。我國當前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執行力隨意擴張至第三人的現象,加劇了執行亂象。(2)參見常廷彬:《試論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載《法治論壇》2010年第1期。對于此種亂象的治理,需從源頭上進行遏制,確定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邊界。厘定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邊界,需要界定影響擴張的各類因素,明確限制擴張的依據。既有研究主要考察影響擴張的因素以及保障機制,但未能厘清擴張的邊界,且對于直接執行這一擴張形式缺乏關注。(3)參見肖建國、劉文勇:《論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及其正當性基礎》,載《法學論壇》2016年第4期;張海燕:《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配偶追加問題研究》,載《當代法學》2019年第1期;趙志超:《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保障機制——再論可否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19年秋季卷等。在當前《民事強制執行法》被納入立法規劃的背景下,從理論上厘清決定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依據,明確追加被執行人和直接執行這兩種擴張形式的適用條件,對《民事強制執行法》的科學制定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否擴張至債務人配偶,是當前激烈爭論的一個問題,也是考察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邊界的一個典型事例。當前強制執行立法如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變更、追加當事人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執行變更追加規定》)未確認法院有權追加被執行人配偶(4)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33條規定個人債務不得向債務人配偶主張權利,似也隱含執行程序不能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但司法實踐中仍時有債權人申請追加(5)參見劉某平與萬某飛、周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興慶區人民法院(2021)寧0104執異432號執行裁定書;孔某、王某鳳民間借貸糾紛一案,遼寧省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遼03執復47號執行裁定書;李某富、艾某萍承攬合同糾紛執行審查一案,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贛執復118號執行裁定書;孫某莉與孫某強其他案由執行一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蘇執復161號執行裁定書。,許多學者也支持執行程序追加債務人配偶。(6)參見肖建國、劉文勇:《論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及其正當性基礎》,載《法學論壇》2016年第4期;張海燕:《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配偶追加問題研究》,載《當代法學》2019年第1期;趙志超:《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保障機制——再論可否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19年秋季卷等。還有學者如黃忠順認為執行機構可參照督促程序向被執行人配偶發出支付令的追加裁定,若債務人配偶提出異議該裁定自始不發生執行力,參見黃忠順:《變更追加連帶責任主體為被執行人的類型化分析》,載《法治研究》2020年第3期。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夫妻債務司法解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采取了限縮共同債務的進路(7)參見劉征峰:《夫妻債務規范的層次互動體系——以連帶債務方案為中心》,載《法學》2019年第6期。,“個債推定”取代了“共債推定”。(8)參見李貝:《夫妻共同債務的立法困局與出路 ——以“新解釋”為考察對象》,載《東方法學》2019年第1期。由此觀之,對于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否擴張主債務人配偶,各方依舊莫衷一是,新規則下探討該問題極具必要性和現實意義。本文希冀通過對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邊界以及能否擴張至債務人配偶的研究,推動學界對執行力擴張理論和審執關系的關注,以便更好指導和規范執行權的行使。
一、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從執行程序的運行來看,執行力擴張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包括實體正當性與程序正當性,執行程序運行中出現的當事人變更等應由執行程序處理,這也有利于保障債權。
(一)擴張的正當性
對于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學界主流觀點認為能否擴張,需要從實體正當性和程序正當性兩方面考量,即應考量程序效率、糾紛解決與程序保障等程序性因素,也需要結合實體法規定考察實體利益歸屬的一致性和實體權利存在是否具有高度蓋然性。(9)有代表性的論述如肖建國、劉文勇認為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需要考慮執行債權實現的迅速經濟、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的依存性和實體利益歸屬的一致性、第三人的程序保障、權利人對特定債務人享有權利的高度蓋然性;臺灣學者許士宦認為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省略債權人取得新執行名義,實體上之正當性在于權利人對于第三人之權利存在相當可能性,程序上之正當性在于賦予第三人一定之程序保障及訴訟經濟;譚秋桂認為執行力擴張的理論依據包括及時有效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既判力延伸的結果、實體法賦予第三人的義務以及節約權利保護的成本;常廷彬認為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包括實體和程序兩方面的正當性,即執行公平、效率和實體權利義務關系的存在、轉移。參見肖建國、劉文勇:《論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及其正當性基礎》,載《法學論壇》2016年第4期;許士宦:《執行力客觀范圍擴張論之生成》,載《臺灣法學雜志》2017年第329期;譚秋桂:《論民事執行當事人變化的程序構建》,載《法學家》2011年第2期;常廷彬:《試論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載《法治論壇》2010年第1期。考察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否擴張至債務人配偶,需結合實體和程序兩種視角。
第一,從執行程序的角度來看,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是因其能夠促進執行效率,平衡程序保障與糾紛解決的關系。首先,從執行效率考慮,基于審執分離原則和執行形式化原則,強制執行的范圍原則上依生效裁判文書確定,不應擴張至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若執行程序出現當事人去世、組織合并分立等特殊情況,便需要通過訴訟程序確認,這會嚴重影響執行程序的效率性。允許執行程序追加債務人配偶等第三人,通過“先追加后救濟”的方式,將救濟程序后置,能夠最大程度保障執行效率。其次,能夠平衡程序保障與糾紛解決的關系。一方面,執行程序追加或直接執行較為簡便,無需經過訴訟程序確認,能更快地解決爭議;另一方面,部分當事人對執行裁定有異議的,也可通過異議之訴等訴訟程序解決,以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最后,這是當前切實解決“執行難”的特殊國情決定的。有學者認為減少訴累、克制不誠信行為是追加被執行人的主要原因。(10)參見譚華霖、徐春成、賈建鵬:《民事執行中追加被執行人問題探析》,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雖然當前“執行難”已基本解決,但切實解決“執行難”仍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尤其當前信用社會尚未建成,司法實踐中轉移財產、規避執行的情形多有發生,若此類情況皆要求通過訴訟程序解決,將可能影響執行權的強制性與權威性。發揮執行權的能動性,合理擴張執行力主觀范圍,是解決惡意逃債等執行難問題的一種對策。(11)參見劉書星:《我國執行力擴張制度研究》,載《法學雜志》2015年第7期。
第二,從民事實體法的角度,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具有實體法基礎。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建立在程序法與實體法規范協調的基礎上,需要實體法上對第三人的實體利益歸屬具有一致性、實體權利存在高度蓋然性。如實體法上規定投資人需對其個人獨資企業的債務承擔責任,若個人獨資企業對外負債不能清償,債權人主張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該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因該擴張具有實體法依據,執行力主觀范圍可擴張至投資人,即使投資人提出異議,該異議也將會被駁回。將不存在實體法關聯或實體權利存在可能性的案外人納入執行力的擴張范圍,將使得程序效率、權利保障等程序目標難以實現,加劇執行亂象,影響擴張的正當性。如若實體法規定投資人無需對個人獨資企業承擔債務,即使執行立法明確執行力主觀范圍可擴張至投資人,若投資人對執行程序追加其為被執行人的裁定提出異議,依據民事實體法該追加裁定將會被撤銷,造成司法資源浪費,也加重當事人訴累。如何判斷程序法與實體法規范是否協調,不僅需要結合實體法的規定,也應考察實踐中該實體權利的具體運行情況。
總之,當前我國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具有現實必要性,一定范圍內的執行力擴張能夠實現程序法與實體法的統一,平衡執行效率與程序保障,具備正當性,應正視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
(二)擴張的必要性
其一,執行程序的當事人變更等特殊事項難以通過訴訟程序解決。在審執分離原則下,審判程序與執行程序分離,若要求執行程序出現特殊事項皆要求訴訟程序解決,審判權會侵蝕執行權,將威脅執行程序的獨立性。如在執行程序中出現申請執行人去世,要求已去世申請執行人的繼承人通過訴訟程序確認其為債權人后,再啟動執行程序,將使訴訟程序不堪重負,加重當事人訴累。執行程序應對執行程序運行中的執行主體變更具有決定權,執行力主觀范圍可依法擴張至相應第三人,以維護執行程序的獨立性和效率性。
其二,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有利債權保障。強制執行程序為債權實現程序,奉行“債權人中心主義”執行程序觀,在價值上堅持效率至上。(12)參見肖建國:《中國民事強制執行法專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頁。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應在債權優先的理念下,為債權人實現權利提供便利,將相應第三人納入執行力主觀范圍之內。有部分學者對“債權人中心主義”理念進行了批評,認為強制執行法應當向案外人提供足夠及時且正當的救濟權利,不能因強制執行限制案外人的救濟權利。(13)參見江必新主編:《比較強制執行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頁。筆者認為應區分一般案外人和與債務人具有特定財產關系的案外人,以確定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否擴張至該案外人。一般案外人與債務人沒有特殊關系,執行程序不應隨意限制其權利,典型代表是債務人合同糾紛的相對人,執行力主觀范圍原則上不能擴張這類案外人,若債權人主張第三人承擔責任的應通過訴訟程序解決;與債務人具有特定財產關系的案外人,執行程序應堅持債權保障優先,將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該第三人,執行法院可要求財產繼承人在繼承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責任。
二、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形式及限度
執行力主觀范圍向債務人擴張不僅包括追加被執行人,不追加、直接執行也是一種擴張的形式。(14)我國實際還有一種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形式,即“通知+直接執行”方式,典型情況是對第三人債權的執行,債務人對第三人享有債權的,法院可依申請向第三人發出債務履行通知,若第三人未提出異議,法院可直接強制執行第三人。但一方面,這一方式在我國立法中僅有第三人債權執行這一情形適用,且其正當性在學界備受質疑;另一方面,這一執行方式可視為直接執行方式的特殊形式,與直接執行方式不同的是多了通知程序和第三人的異議權,所以本文未特殊涉及這一執行方式。執行力過度擴張會影響執行權的正常運行,從強制執行理論和比較法上看,應限制執行力主觀范圍過度擴張,將執行權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厘清執行權與審判權的運行邊界,遏制執行亂象,維護相關案外人的合法權利。
(一)擴張的形式
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包括執行程序變更、追加當事人和無需追加直接執行兩種形式,超出執行力擴張邊界的應通過訴訟程序解決。執行程序變更、追加當事人是執行法院通過執行裁定方式變更、追加當事人,執行裁定生效后相應案外人成為執行程序當事人。直接執行形式是指在債務人不能履行義務后,執行法院無需經過變更、追加程序,直接執行相應案外人的財產。當前學界研究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主要關注執行程序追加當事人形式,對直接執行形式關注不夠。實際上不經過追加程序,直接執行相關責任主體,是我國執行程序中一種重要的執行方式。我國當前立法規定了數種不需追加直接執行的情形,典型的如執行擔保人(1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擔保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暫緩執行期限屆滿后被執行人仍不履行義務,或者暫緩執行期間擔保人有轉移、隱藏、變賣、毀損擔保財產等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請執行人的申請恢復執行,并直接裁定執行擔保財產或者保證人的財產,不得將擔保人變更、追加為被執行人。 ”和執行個體工商戶經營者、個人獨資企業、法人分支機構。(1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變更、追加當事人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3條:“ 作為被執行人的個人獨資企業,不能清償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債務,申請執行人申請變更、追加其投資人為被執行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作為被執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執行該個人獨資企業的財產。個體工商戶的字號為被執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執行該字號經營者的財產。”第15條:“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分支機構,不能清償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債務,申請執行人申請變更、追加該法人為被執行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法人直接管理的責任財產仍不能清償債務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執行該法人其他分支機構的財產。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直接管理的責任財產不能清償生效法律文書確定債務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執行該法人分支機構的財產。”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被直接執行的第三人,根據立法規定,不需經過追加程序,法院即可直接采取強制執行措施。與另行訴訟、執行程序追加相比,直接執行方式雖能體現執行效率,有利于債權實現,但對第三人的程序保障不足,易造成執行權濫用,需要嚴格限制其適用范圍。
債權人申請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債務人配偶的,執行程序可通過追加被執行人或直接執行方式實現擴張。在夫妻債務執行領域,相對于追加被執行人,直接執行債務人配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國當前采取的法定財產制為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取得的財產原則上為夫妻共同財產,物權公示原則難以作為界定夫妻財產的標準。(17)參見趙大偉:《夫妻個人債務執行標的實體權屬界定標準重塑》,載《西部法學評論》2022年第3期。執行夫妻財產,需結合共同財產制界定財產權屬,對于夫妻一方為債務人的,因執行程序對夫妻債務的不同認定,直接執行有兩種形式:執行程序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可直接執行債務人及其配偶的所有財產;認定為夫妻個人債務的,可直接執行債務人在夫妻財產中的相應份額,夫妻個人債務直接執行財產份額不屬于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
有學者認為夫妻債務領域的直接執行,與執行程序中其他直接執行方式具有本質區別,夫妻債務領域的直接執行債務人配偶需要進行實體審查,而其他直接執行僅需形式審查即可。(18)參見張海燕:《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配偶追加問題研究》,載《當代法學》2019年第1期。筆者認為從執行理論上來看,共同債務推定的直接執行方式與其他直接執行方式不存在本質區別,同樣需對實體問題進行審查,都屬于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一種方式。在夫妻債務領域,執行法院需審查實體法上該債務性質為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其他直接執行方式,同樣面臨實體審查,以直接執行擔保人為例,直接執行擔保人之前,執行法院需要在實體上判斷擔保人是否需要承擔擔保責任以及責任范圍。在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下,執行法院的審查權未超出執行權形式審查的范圍,法院只需確認債務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即可從形式上確定該債務系共同債務,直接執行債務人配偶個人財產。
(二)擴張的限度
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包括向債權人的擴張和向債務人的擴張兩種類型。司法實踐中向債權人的擴張不具有現實的迫切性,并非理論和實踐亟須解決的問題。(19)參見肖建國主編:《民事執行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而向債務人擴張是化解“執行難”的一種有效措施,對于債權實現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實踐中存在隨意擴張、執行第三人財產的現象,無論是從擴張的程度還是從過度擴張的危害來看,都亟須限制向債務人的擴張,故本文主要以執行力主觀范圍向債務人擴張來探討擴張的限度。
現行法上執行當事人適格的范圍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已遠遠超過了傳統既判力主觀范圍的擴張,需合理規制,確定邊界。(20)參見肖建國:《強制執行形式化原則的制度效應》,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執行變更追加規定》不僅將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到既判力所及之人,而且還特別擴張到與執行當事人具有特定實體權利關系的第三人,大大超越了傳統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射程范圍。然而,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是一把雙刃劍,合理擴張雖能提升執行效率,減輕當事人訴累,但若過度擴張可能引發執行混亂,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21)參見郭士輝:《第一屆法院執行理論與實務研討會綜述》,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辦公室編:《強制執行指導與參考》2005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頁。
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實質是執行權的擴張,確定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邊界,應限制執行權的過度擴張。一般認為強制執行權包括執行實施權與執行裁決權,執行裁決權又包括變更和追加被執行人、執行異議、執行復議、中止執行和終結執行等裁決事項。(22)參見于泓:《關于我國民事強制執行機構設置的構想》,載沈德詠主編:《強制執行法起草與論證(一)》,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300頁。有學者認為在司法體制改革中宜將執行裁決權從執行權中剝離出來,成為審判權的組成部分。(23)參見肖建國:《民事審判權與執行權的分離研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6年第2期。筆者認為執行裁決權雖然與審判權具有相似性,屬于廣義審判權的組成部分,但執行裁決權與審判權具有內在差異,不可將二者混淆。理由是:其一,執行裁決權雖可能對實體問題進行審查,但仍以形式審查為原則,與審判權的實質審查有本質區別。其二,部分執行裁決權與執行程序的正常運行具有密切關聯,難以強制分割,機械地將其劃歸審判權,將嚴重拖累執行效率。如中止執行、終結執行等程序事項,雖涉及當事人的重大實體利益,但更關涉執行程序的運行和終結,將其劃歸審判權影響執行權的正常行使。其三,執行實施權中實際也涉及對實體權利的判斷和識別,若將執行程序存在的所有實體判斷事項都由審判程序處理,執行權將難以行使。如法院在查封被執行人財產時,需要先確定該財產屬于“被執行人”后才能執行,這一確定財產權屬的過程實際也涉及實體判斷,判斷性權力和實施性權力在理論上不可能徹底分離。(24)參見肖建國、黃忠順:《論司法職權配置中的分離與協作原則——以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為中心》,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6期。其四,若所有執行裁決權都成為審判權,追加執行人也將成為審判權的組成部分,將混淆執行權和審判權的界限。可見,執行裁決權屬于執行權的內在組成部分,追加被執行人或直接執行是執行權的擴張,需要處理好執行權與審判權的關系。執行力擴張至第三人,在執行程序解決第三人責任承擔問題,能減少另行訴訟的訴累。執行力的主觀范圍若過度擴張,許多本應由訴訟程序處理的事項轉歸執行程序解決,執行權會侵蝕審判權,影響審判權的正常行使,也給執行程序造成巨大的負擔。以不當追加債務人配偶為例,法院在執行程序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配偶對追加行為提出執行異議,由執行異議程序審查夫妻債務性質,一方面超出了執行權的權限范圍,另一方面也使執行程序的效率受到影響。
從比較法上來看,在大部分大陸法系國家,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是有限度的。在德國、日本等采取執行文制度的大陸法系國家,只有審判機構出具“執行正本”后,才能啟動強制執行程序,執行當事人的范圍在出具執行文時即確定,即由審判機構確定,執行機關無權擴張執行力主觀范圍。(25)參見《德國民事訴訟法》第724條規定:“強制執行,根據附有執行條款的判決正本(有執行力的正本)實施。有執行力的正本由第一審法院的書記科發給,如訴訟案件系屬于上級法院時,由該法院的書記科發給。”詳見《德國民事訴訟法》,丁啟明譯,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頁;《日本民事執行法》第25-26條規定:“強制執行的實施,應根據付與執行簽證的債務名義正本。……對于執行證書以外的債務名義,根據申請,由存有案件筆錄的法院書記官付與執行簽證;對于執行證書,由保存其原本的公證人付與。”詳見《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白綠鉉編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頁。大陸法系的其他國家,如瑞士、法國、意大利、秘魯、瑞典、芬蘭采取了更為寬松的執行力擴張制度,除瑞士外主要采用擴大執行依據的方式來擴張當事人的范圍。如意大利法律規定某些特殊類型的債權文書,如票據、倉單、提單、訴訟外和解文書等文書,不需要經過訴訟程序,債權人可以申請執行。(26)參見《意大利民事訴訟法》第474條規定:“強制執行時,應具備為確定、可計算和可求償的權利而制作的執行文書。執行文書包括:1.判決、決定和其他法律文書明確賦予執行效力的文書;2.內容與金錢債務相關的經認證的私證書、票據和其他法律明確賦予相同效力的信用票據;3.公證員或其他公共事務官員依法提供的文書。”詳見《意大利民事訴訟法典》,白綸、李一嫻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頁。瑞士在所有大陸法系國家中,執行力主觀范圍的射程最遠,這主要是因為瑞士執行程序不受既有執行依據的制約,即便沒有任何執行依據也可直接啟動執行程序,其執行力的擴張沒有實質性限制。這種不必經訴訟或其他程序取得執行依據,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制度設計,對于瑞士這種信用機制高度發達、債務案件數量不高的國家具有極強的實用價值,但對于包括我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是無法復制的。(27)參見肖建國:《執行當事人及其變更和追加》,載江必新、賀榮主編:《強制執行法的起草與論證(三)》,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頁。
三、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邊界的確定依據
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聚焦于實體法秩序的調和,落腳在執行債權的迅速與經濟。(28)參見陳克:《148號指導案例引發的執行力與既判力問題(上)——兼論涉公司類變更追加執行糾紛》,載微信公眾號“法語峰言”,2021年7月26日。臺灣學者許士宦認為與既判力擴張較重視程序因素不同,執行力擴張必須重視實體法秩序調和,原則上以能推論債權人對于繼受人請求權存在之情形為限,始可擴張執行力。(29)參見許士宦:《訴訟系屬后之繼受人與執行力之擴張》,載許士宦:《執行力擴張與不動產執行》(第二版),臺灣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3頁。在影響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眾多因素中,程序性事由難以決定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射程,實體利益歸屬的一致性在當前我國也難以作為依據,界定擴張的邊界應協調程序法與實體法規范,可通過考察實體權利存在的高度蓋然性確定。
(一)程序性因素的局限性
雖然在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時,執行效率、程序保障以及糾紛解決等程序性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程序因素不能單獨決定執行力擴張的邊界。這主要是因為執行力擴張雖發生在執行程序,但程序性規定屬于強行性規定,對所有類型的擴張都適用,不能用于區分該擴張是否具有正當性。執行效率、程序保障以及糾紛解決等程序性目標能否實現,需要結合實體法確定。追加前的審查和追加后的救濟程序,雖有助于保障第三人的程序權利,但所有類型的第三人皆可適用該審查和救濟程序,第三人的異議能否得到支持,主要通過實體法審查其權利能否成立。執行程序追加的效率性,主要體現在追加被執行人能夠免去債權人另行訴訟的訴累,不論追加該第三人是否具有實體法基礎,執行追加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會節省司法資源。
程序性因素產生作用的基礎在與實體法相一致,缺乏實體法基礎的效率、程序保障、糾紛解決等程序性追求將是水中花、井中月。若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太過,在沒有實體法依據的情況下追加第三人為被執行人,執行效率、糾紛解決、程序保障都難以得到保障。如在沒有實體法依據時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債務人配偶對此提出異議,能否追加只能等待執行救濟程序審查結果,執行效率無法得到保障,糾紛難以得到及時解決,債務人配偶的合法權利受到損害。可見,程序性事由無法單獨作為決定擴張范圍的依據,程序法價值的發揮有賴于與實體法規范的協調。
(二)實體利益歸屬一致性的滯后性
部分學者認為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需要考慮實體利益歸屬的一致性,關于如何理解“實體利益歸屬的一致性”,有學者認為“實體利益歸屬的一致性”指第三人與執行當事人實體利益歸屬上是一致的,第三人的權利義務是從前執行當事人處承繼、轉移而來,應受到執行力的拘束。(30)參見肖建國、劉文勇:《論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及其正當性基礎》,載《法學論壇》2016年第4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擴大解釋,認為實體利益歸屬的一致性包括前后執行當事人之間存在權利義務關系的依存性、前后執行當事人具有實體法上責任主體的一致性、前執行當事人責任財產因第三人而不當減少(或減少的危險)以及第三人自愿代償的場合。(31)參見趙志超:《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保障機制——再論可否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19年秋季卷。筆者認為不能任意擴大解釋此概念,因同一實體法律關系所產生的實體利益承繼、轉移,如因債務人死亡、法人名稱變更所導致的,此時可以認為該實體義務關系具有依存性、實體利益歸屬具有一致性。而對于基于另一實體法律關系所產生的權利義務轉移,涉及對實體爭議的判斷,原則上應由訴訟程序解決,不能以執行權代替審判權處理。典型的如債務人與第三人之間存在經濟糾紛,該經濟糾紛雖可能影響債權實現,但債務人與第三人之間的糾紛屬于實質爭議,應當由審判機構審理確定。考察實體利益歸屬一致性足以確定擴張的邊界,這類情形也是我國當前執行程序中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中最常見的情形。
原則總有例外,由于債務人串通第三人轉移財產、逃避執行行為的多發,以及為追求執行效率和徹底解決“執行難”的需要,我國已將部分基于另一實體法律關系而產生的變動納入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中,單純考察實體利益歸屬一致性難以確定擴張邊界。(32)參見劉學在、王炳乾:《執行當事人之變更、追加的類型化分析》,載《政法學刊》2018年第2期。《執行變更追加規定》第14條第2款、第17條至第21條規定存在基于另一實體法律關系而擴張執行力主觀范圍,當股東出現未足額繳納出資、抽逃出資等情形時,債權人可申請追加股東為被執行人。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第5章規定對基于另一實體法律關系所發生的擴張,債權人可直接提起許可執行之訴,即認為基于另一實體法律關系產生的擴張不屬于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需要由訴訟程序先行確認后才能執行。肖建國教授認為這種許可執行之訴先行模式,屬于古典理論下的產物,確保正當性有余,執行效率不足。(33)參見肖建國:《強制執行形式化原則的制度效應》,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筆者認為從執行效率和保障債權人合法權益、打擊惡意逃債的角度,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另一實體法律關系具有現實必要性。以執行程序追加債務人配偶為例,相對于金錢債務關系,夫妻債務性質認定屬于另一實體法律關系,原則上應通過訴訟程序解決。若嚴守執行力主觀范圍不能擴張至另一實體法律關系,配偶追加問題沒有討論的必要。有學者認為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另一實體法律關系屬于政策性擴張,基于各種考慮,各國執行立法中有部分政策性擴張,如《英國最高法院規則執行程序》第45號令第5條中規定執行效力可及于法人團體的高級管理人員。(34)參見劉書星:《我國執行力擴張制度研究》,載《法學雜志》2015年第7期。目前,我國基于另一實體法律關系所產生的擴張是一種特殊政策考慮,仍然具有存在的價值,“實體利益歸屬的一致性”難以作為決定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邊界,需要探索新的確定標準。
(三)實體權利存在具有高度蓋然性的決定性
那么在理論上如何界定債權人對第三人的實體權利具有“高度蓋然性”?高度蓋然性原系大陸法系證據法中的概念,指依據日常經驗可能達到的,疑問即告排除,產生近似確然性的可能。(35)參見畢若謙:《試論民事訴訟證明上的蓋然性規則》,載《法學評論》2000年第4期。此處高度蓋然性指由于實體法規定和證明責任分配等原因,使得在事實上能夠基本確定第三人應對債權人承擔給付責任。以因刺破公司面紗引發的追加被執行人為例,由于《公司法》第63條的特殊規定,一人公司的面紗刺破率高達100%,對一人公司股東的實體請求權具有高度蓋然性,而其他類型公司適用《公司法》刺破公司面紗的一般規則,債權人的實體權利即不具有高度蓋然性。(36)參見黃忠順:《變更追加連帶責任主體為被執行人的類型化分析》,載《法治研究》2020年第3期。為提高執行效率和及時實現債權,執行力擴張至一人公司股東具有正當性,擴張至一般公司股東屬于典型的“以執代審”。此處的高度蓋然性不需要100%確定,只要在實體法規范下,債權人對第三人的權利請求原則上能夠成立,即可認定請求具有高度蓋然性,執行立法應明確執行力主觀范圍能擴張至此。
債權人對第三人的實體權利具有高度蓋然性,應成為界定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依據。這主要是因為高度蓋然性標準能夠將實體正當性與程序正當性統一,平衡執行權與審判權的關系。第一,在程序上,債權人對第三人的實體請求具有高度蓋然性,執行程序通過略式程序形式審查即能夠判斷。第三人對追加為被執行人一般也不會提出異議,第三人的程序權利能夠得到保障,執行效率得到提升,糾紛也能夠得到及時解決。第二,在實體上,實體權利存在的高度蓋然性基本能夠涵蓋我國當前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情形,實體利益歸屬一致性的請求一般具有高度蓋然性。如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去世,需要追加其繼承人在被繼承遺產范圍內承擔給付責任,此時債權人對請求被繼承人在繼承遺產范圍內責任的實體權利請求權具有高度蓋然性。第三,在執行權與審判權的關系上,以實體權利高度蓋然性作為執行力擴張的邊界,審判權和執行權的界限較為明確,不具有高度蓋然性的實體權利請求由審判部門審理,具有高度蓋然性的由執行程序處理。這要求執行立法機構在界定執行力擴張的范圍時,需要結合實體法的規定,厘清執行程序處理與訴訟程序解決的邊界。債權人對第三人的實體請求不具有高度蓋然性,即使執行立法強行規定該事由屬于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在執行程序追加為被執行人后,第三人一般會提出異議,需要經過執行救濟程序審查,才能最終確定能否追加,第三人的程序權利與執行效率難以得到保障,糾紛難以及時得到解決。以執行程序能否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為例,若在實體法上債權人對債務人配偶的實體權利存在具有高度蓋然性,債權人申請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執行程序經過形式審查即能夠確認,即使債務人配偶提出異議,該異議將會被駁回;反之,若實體法上債權人的實體權利歸屬不再具有高度蓋然性,執行立法強行規定執行程序可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若債務人配偶提出異議,追加裁定將會被推翻,追加程序空轉,影響執行效率。
四、執行力主觀范圍難以擴張至債務人配偶
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需要實體法基礎,實體法的變化可能影響執行力的擴張,使得原本具備正當性的擴張不再具備正當性。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確立了共同債務推定規則(37)《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又稱為“時間”推定規則(38)參見孫若軍:《論夫妻共同債務“時間”推定規則》,載《法學家》2017年第1期。,即將婚姻存續期間所產生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由雙方共同清償。顯然《婚姻法解釋(二)》采取的是“債權人優位”的價值取向,以共同債務推定的方式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39)參見薛寧蘭:《中國民法典夫妻債務制度研究》,載《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3期。,但這種推定規則遭到了學者們的批評,在社會上也遇到了巨大的反彈。(40)參見王春霞:《修法保護夫妻共同債務中的婦女權益》,載《中國婦女報》2016年3月14日,第A1版;馬賢興:《夫妻債務司法認定及實案評析》,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19—232頁。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又發布了《夫妻債務司法解釋》,改變了先前夫妻債務認定規則,《民法典》繼承了《夫妻債務司法解釋》的規定。對訴訟程序來說,新規則改變了夫妻共同債務證明規則,《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需要由債務人與其配偶證明該債務屬于夫妻個人債務,否則該債務將被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在《民法典》第1064條下債權人有證明該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的義務。這一變化對執行程序的影響更大,在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下,對于夫妻一方為債務人的,執行程序可將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的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具備正當性;新規則下,執行程序難以依據實體法對夫妻共同債務進行推定,在訴訟程序未確認的情況下,執行程序將其推定為夫妻個人債務更為妥當,追加被執行人或直接執行不再具有合理性,債權人申請擴張的應通過另行訴訟解決。
夫妻個人債務執行一半夫妻共同財產,不是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債務人配偶,而是由于共同財產制下債務人的責任財產可能在配偶名下,法院執行的實質是債務人的責任財產。有實體法學者將《民法典》第1064條確立的債務認定規則稱為“夫妻個人債務推定”(41)參見李貝:《夫妻共同債務的立法困局與出路——以“新解釋”為考察對象》,載《東方法學》2019年第1期。,筆者認為對于夫妻一方為債務人的強制執行程序來說,將這一實體法變革理解為由“夫妻共同債務推定”到“夫妻個人債務推定”的轉變,可能較為妥當。
(一)追加被執行人喪失正當性
在2016年《執行變更追加規定》出臺前,雖然司法解釋未明確規定可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42)2005年10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執行中變更和追加當事人的規定征求意見稿》第3、4條曾明確執行法院可追加債務人配偶或家庭成員為被執行人。參見田玉璽、丁亮華:《在超越與限制之間——民事執行中變更和追加執行當事人制度研究》,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辦公室編:《強制執行指導與參考》2005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但許多地方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意見支持法院通過追加配偶方式解決債務人配偶責任承擔問題。(43)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夫妻個人債務及共同債務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解答》(滬高法執〔2005〕9號)第2條規定:“執行依據中沒有對債務性質作出明確認定,申請執行人主張按被執行人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并申請追加被執行人配偶為被執行人的,執行機構應當進行聽證審查,并根據下列情形分別作出處理:……(三)除應當認定為個人債務和執行中不直接判斷債務性質的情形外,可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裁定追加被執行人配偶為被執行人。”2013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疑難若干問題的解答》第7條規定:“是否必須先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然后才能采取執行措施?答:原則上應先追加被執行人的配偶(或原配偶)為被執行人,再執行其名下的財產,但緊急情況下,為了防止其轉移財產,可以在追加的同時采取控制性執行措施。”2014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程序中追加、變更被執行人的裁判指引》第1條規定:“執行程序終結前,申請人以下列事由提出追加、變更被執行人申請的,執行法院應當受理:……(11)因債務人個人財產不足清償債務,申請追加其家庭成員、原配偶為被執行人的。”在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下,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具有實體正當性和程序正當性。債權人對債務人配偶的請求權具有高度蓋然性,追加配偶是“先追加后救濟”(44)參見闕梓冰:《執行程序中變更、追加當事人制度的價值理念與具體適用》,載《人民法院報》2019年8月1日,第05版。或“后發式救濟程序”(45)參見肖建國:《強制執行形式化原則的制度效應》,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能夠兼顧配偶的實體權利保障與執行效率,且能夠保障配偶的程序救濟權。在《民法典》下,隨著夫妻債務認定規則的修改,執行程序追加被執行人不再具備正當性。實體上,債權人對債務人配偶的實體權利不再具有高度蓋然性,認定共同債務屬于獨立的法律關系;程序上,由執行程序追加配偶不能體現執行效率,難以保障配偶的程序利益。
1.失去實體正當性
執行程序追加當事人的合理性在于程序性規范與實體規范的一致,實體法的修改使得追加當事人不再具有正當性。
首先,債務是否成立與該債務是否為共同債務,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以民間借貸為例,債權人對債務人的民間借貸和對債務人配偶的共同債務認定需要考量不同的要件,二者具有不同的訴訟標的。對借貸關系,法院主要通過合同編關于民間借貸的相關規定考察借貸關系是否成立;認定夫妻共同債務,主要依據婚姻家庭編的相關規定。在夫妻共同債務推定時期,夫妻債務認定附屬于債務成立,只要該債務發生在婚姻存續期間即可推定為共同債務,法院幾乎沒有裁量空間。在當前債務認定規則下,共同債務能否成立需要債權人提供證據證明,具有獨立性。當然,目前我國基于不同法律關系也可能引起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這是基于執行效率以及我國目前“執行難”的現狀等因素作出的便宜性規定。債務人配偶能否被追加,應結合其他因素進行考察。
其次,新規則下,債權人對債務人配偶的權利不再具有高度蓋然性。允許債權人申請通過略式程序追加第三人為被執行人,最主要原因是債權人對實體權利的存在具有高度蓋然性,略式程序能基本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權利,部分有異議的可通過執行救濟程序解決。在《民法典》第1064條下,需要由債權人證明夫妻共同第三人債務。債權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該債務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但由于夫妻生活的私密性,債權人事實上很難進行證明。據統計,江蘇省法院系統在共同債務推定時期的2017年,審結涉及夫妻共同債務的民間糾紛案件7735件,二審判決書有1016份,其中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判決940份,占比92.5%。改變夫妻債務推定規則后,2018年1月18日至3月31日,江蘇法院共審理涉及夫妻共同債務的民間借貸案件660件,抽取其中300份樣本去除非判決書部分剩余272件,認定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共計90份,占比35%。(46)參見陳愛武:《夫妻共同債務的類型化及其法律適用》,載《人民司法》2018年第8期。可見,因實體法規則的改變,債權人對債務人配偶享有的權利不再具有高度蓋然性,執行程序難以直接將夫妻債務確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并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
最后,執行法院具有實體判斷權,并不等于執行程序能夠認定夫妻共同債務。執行權包括執行實施權和執行裁決權,一般認為追加被執行人涉及對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認定,屬于執行裁決權,執行法院有權對實體問題進行審查判斷。(47)參見肖建國:《執行標的實體權屬的判斷標準——以案外人異議的審查為中心的研究》,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5期。尤其當前我國采取執行異議前置的方式,對當事人的實體爭議,執行程序有權作出執行異議裁定書,對裁定不服的可提起異議之訴。但執行裁決權與民事審判權對實體問題的認定仍具有本質區別。其一,執行程序對實體問題的判斷是初步判斷(48)參見[日]三月章:《民事執行法》,弘文堂1981年版。轉引自肖建國:《執行標的實體權屬的判斷標準——以案外人異議的審查為中心的研究》,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5期。、程序判斷、外觀判斷,不具有既判力,可能在之后的執行救濟程序中被推翻,而審判程序作出的實體判斷是實質判斷,具有既判力。其二,執行裁決權審查與強制執行有關的執行爭議,對于與本案執行無關的其他實體爭議,當事人應通過另行訴訟解決。在夫妻個人債務推定規則下認定夫妻共同債務,不屬于執行裁決權的審查范圍,應通過另行訴訟解決。其三,執行權與審判權具有本質區別,執行權主要是強制權,以效率為首要價值追求,通過略式程序行使形式判斷權,而審判權是判斷權,以公正為目標,保障雙方當事人的程序權利,處理當事人之間的實質爭議。執行裁決權雖分享部分判斷權,但仍屬于強制執行權的范疇,不能代替審判權對實質爭議行使判斷權。
2.缺乏程序正當性
隨著實體法規則的變革,追加被執行人的程序正當性可能也將喪失。此時追加被執行人可能影響執行效率,難以保障當事人的程序利益,糾紛也難以及時得到解決。
首先,從程序效率的角度來說,新規則下追加債務人配偶可能難以提升執行效率,甚至可能造成執行拖延。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落腳點是執行債權的迅速和經濟,正因為追加第三人能夠節省司法資源,減輕當事人訴累,才允許追加未取得執行依據的第三人為被執行人。然而當前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可能并不能保障執行效率。第一,在當前債務認定規則下,債權人對債務人配偶享有的權利不再具有高度蓋然性,即可能只有少數配偶追加申請能夠得到支持,大部分將被駁回,若允許此類請求啟動追加程序,將會造成追加程序的濫用,影響執行效率。第二,即使執行立法強行規定執行程序可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追加債務人配偶后,債務人配偶對追加裁定提出異議,缺乏實體法依據的追加裁定在執行救濟程序時將被推翻。有學者選取了2421份全國各級法院生效執行裁定書,共有309份涉及追加債務人配偶,在這309份涉及追加配偶裁定書中,在債權人向法院提出追加申請后,其中債務人配偶提出異議的有244份,約占80%。(49)參見韓紅俊、趙培:《論民事執行中被執行人配偶的追加》,載張衛平主編:《民事程序法研究》第16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116頁。
其次,從保障當事人程序利益的角度來看,執行救濟程序并不足以保障債務人配偶的程序利益。有學者認為在追加前進行實質審查,在追加后配偶可提出執行異議和案外人異議之訴,能夠為追加配偶提供程序正當性。(50)參見張海燕:《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配偶追加問題研究》,載《當代法學》2019年第1期。筆者認為這種程序設置只能部分保障債務人配偶的程序利益。然而,在當前債務認定規則下,寄希望通過執行救濟程序解決債務性質認定問題,可能會增加訴累,無法充分保障配偶的程序利益。執行異議與異議之訴主要解決執行行為合法性以及異議人實體權益能否排除強制執行,共同債務性質問題在執行救濟程序只能附帶涉及,無法對是否構成夫妻共同債務獨立進行審理。而共同債務認定在當前的夫妻債務認定規則下較為復雜,具有獨立的訴訟標的,執行救濟程序難以解決共同債務性質認定問題,應通過另訴解決。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423號執行裁定書認為執行異議之訴的實體權利判斷僅限于對執行標的提出的權利主張,申請人要求確認該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并非針對執行標的提出的爭議,不屬于執行異議之訴受案范圍。(51)參見河南省萬里建設發展有限公司、趙某汎申請執行人異議之訴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423號執行裁定書。
有學者認為若債權人主張由于夫妻雙方共同合意或基于家事代理權而形成夫妻共同債務,執行程序可進行夫妻共同債務推定,對于由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產生的債務,需由訴訟程序確認。(52)參見趙志超:《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保障機制——再論可否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19年秋季卷。筆者認為無論是夫妻合意之債還是家庭日常生活之債,執行程序都難以直接進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首先,對于合意之債來說,一方面,在夫妻雙方“共債共簽”的情況下,債務人夫妻雙方以其獨立意思表示對債權人承擔責任,在債權人起訴夫妻一方且生效裁判僅確認一方為債務人的情況下,在執行程序再主張夫妻另一方承擔責任,這一請求屬于獨立訴訟標的,應通過訴訟程序審查;另一方面,對夫妻雙方“合意”的認定也具有復雜性,如默示同意或在場是否視為達成合意,這都需要訴訟程序確認。其次,對于日常家庭生活之債,雖立法者認為家事之債為當然的夫妻共同債務,但這并不等于執行程序能夠直接進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民法典》第1060條規定夫妻一方基于家庭日常生活而實施的行為由夫妻雙方負責,《民法典》權威釋義書認為家事之債的范圍可根據夫妻共同生活的狀態和當地一般社會習慣來認定;(53)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987頁。最高人民法院也認為對于因家庭日常生活所負的債務,債權人無須證明,由配偶證明該債務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54)參見《妥善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 依法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答記者問》,載《人民法院報》 2018年01月18日,第03版。然而,執行程序仍難以直接進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應由訴訟程序處理家事之債的債務性質問題。一方面,“日常家庭生活”屬于典型的不確定概念,司法實踐中很難界定(55)參見冉克平:《論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引起的夫妻共同債務》,載《江漢論壇》2018年第7期。,其范圍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因人因事變化,在外部很難判斷。(56)參見馬憶南:《家庭日常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認為夫妻共同債務》,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頁。理論和實踐中對于分居能否中止家事代理權,以及贍養父母是否屬于家事代理權的范圍等問題尚未達成一致意見。(57)參見肖暉、訾培玉:《夫妻共同債務認定問題探析——基于對法釋〔2018〕2號實踐狀況的考察》,載《學術探索》2020年第1期。有學者認為日常家事代理以家庭主婦婚姻模式為基礎,有違當代雙薪夫妻共同管理家務之現狀,在實踐中已淪為債權人的“便車”,對婚姻有歧視之虞,主張廢除當前的家事代理制度。(58)參見王戰濤:《日常家事代理之批判》,載《法學家》2019年第3期。另一方面,雖家事之債為夫妻共同債務,但仍然需要債權人提供證據證明債務成立以及該債務為家事之債。(59)參見賀劍:《〈民法典〉第1060條(日常家事代理)評注》,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若債權人只要主張該債務為家事之債,執行法院即進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這會嚴重損害債務人配偶的合法權利。事實上是否實際發生交易、民事法律行為是否真實、債務的產生是否基于債務人家庭生活需要,都需要債權人提供證據證明,只有在債權人證明該債務確實為家庭日常生活所負后,才能確定該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可見,在當前日常家庭生活之債內涵和外延未明確、債權人需要承擔家事之債證成責任的情況下,執行程序難以進行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貿然規定執行程序有權認定日常家庭生活之債,可能導致濫用,產生另一種形式的夫妻共同債務推定。
總之,無論從程序法還是實體法上來看,在當前夫妻債務規范下,債權人對債務人配偶的實體權利請求缺乏高度蓋然性,追加債務人配偶為被執行人缺乏實體正當性和程序正當性,執行力主觀范圍難以通過追加被執行人方式擴張至債務人配偶。
(二)直接執行債務人配偶的財產不具可行性
將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直接執行債務人配偶財產曾被廣泛接受,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執行局局長劉貴祥在2016年1月9日“全國法院執行工作經驗交流座談會上的總結講話”中認為夫妻一方為被執行人的,執行程序可推定為共同債務,并可直接執行配偶(包括已離婚的原配偶)的個人財產以及夫妻共同財產。(60)劉貴祥專委認為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與夫妻財產的執行要分為兩種情況,對于執行依據明確債務為夫妻一方個人債務的,可直接執行債務人的個人財產和一半份額的夫妻共同財產;對于執行依據未明確債務為夫妻一方個人債務的,若該債務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配偶不能證明為非共同債務的,法院可以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并可以直接執行配偶(包括已離婚的原配偶)的個人財產以及夫妻共同財產。詳見國家法官學院案例開發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7年度案例:執行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頁。《執行疑難問題問答(二)》對于“夫妻一方為被執行人的案件,能否執行夫妻共同財產或者配偶的個人財產?”問題的解答和劉貴祥專委是一致的(61)“對此應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執行依據明確債務為夫妻一方個人債務的,除能執行債務人的個人財產外,可以執行夫妻共同財產中的一半份額。配偶對于執行共同財產有異議的,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的規定進行救濟。第二種情況,執行依據未明確債務為夫妻一方個人債務的,如果債務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配偶不能證明非夫妻共同債務的,可以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并可以直接執行夫妻共同財產、配偶(包括已離婚的原配偶)的個人財產。配偶有異議的,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27條的規定進行救濟。”參見高執研:《執行疑難問題問答(二)》,載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編:《執行工作指導》第46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部分省高級人民法院亦曾出臺類似規則。(62)參見2014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夫妻一方為債務人案件的相關法律問題解答》第3條規定:“三、債務性質經判斷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執行程序應當如何進行? 答:執行機構可直接作出裁定查封、扣押、凍結、變價夫妻共同財產或者非被執行人的夫妻另一方名下的財產,而無需裁定追加夫妻另一方為被執行人。執行裁定書主文部分應當寫明執行的具體財產。”在《執行變更追加規定》出臺后,追加配偶喪失合法性,將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直接執行,成為法院執行配偶財產的兩種主要方式之一。(63)參見張海燕:《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配偶追加問題研究》,載《當代法學》2019年第1期。在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下,直接執行方式雖面臨正當性追問,但能夠在司法實踐中廣泛適用,有其制度背景。首先,直接執行符合民事實體法的規定。執行程序能夠進行共同債務推定是由于執行機構擁有債務性質判斷權,共同債務推定僅需形式審查即可確定,這一切的前提是《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確立的共同債務推定規則。其次,直接執行方式有利于債權的實現,減少當事人訴累,提升執行效率。
隨著《夫妻債務司法解釋》以及《民法典》對夫妻債務認定規則的修改,在實體法上廢除了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直接執行全部夫妻財產不再具有可行性。更重要的是,直接執行方式作為新規定的執行方式,相關配套規則不健全,操作上存有困難,如債務人配偶的程序定位如何界定,債務人配偶是不是“被執行人”,通過何種程序將其變為“被執行人”,執行查控系統如何查控配偶的財產等。(64)參見金殿軍:《執行當事人變更制度研析——以執行依據、既判力和執行力的辨析為基礎》,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辦公室編:《強制執行指導與參考》2005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頁。夫妻個人債務可直接執行一半夫妻共同財產,但執行一半夫妻共同財產不同于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
1.通過直接執行擴張喪失可行性
基于自負其責理念,債務人僅以其個人所有財產對其債務負責,執行法院原則上不能直接執行案外人財產。夫妻一方為被執行人的案件,執行程序直接執行債務人配偶名下所有財產的邏輯前提是能夠進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只有在民事實體法允許強制執行程序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情況下,執行法院才能在夫妻一方為被執行人時審查該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若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即要求債務人配偶承擔給付責任,法院直接查封、扣押、凍結債務人配偶財產。夫妻共同債務推定的正當性源于《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認為婚姻存續期間一方負債的,即使裁判文書僅確認夫妻一方為被執行人,該債務性質依據實體法規范也應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法院可直接執行被執行人配偶名下的個人財產和共同財產。(65)參見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變更和追加被執行主體問題研究》,載《法律適用》2008年第10期。在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下,執行程序將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并直接執行配偶財產,具有實體法依據。隨著民事實體法中夫妻債務認定規則的修改,對于執行依據僅明確夫妻一方為債務人、未明確債務性質的執行案件,將其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喪失正當性。《民法典》夫妻債務規則下,將夫妻一方為債務人的案件推定為夫妻個人債務,可能更符合實體法規范和程序法規范的要求,在實體法上債權人未能證明該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程序法上生效裁判僅確認夫妻一方為債務人。(66)參見趙大偉:《共同財產制下夫妻個人債務執行程序的規則建構》,載《交大法學》2022年第2期。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的做法雖然較為混亂,但對于夫妻一方為被執行人的案件,在債權人未申請追加或未另行訴訟前,總體上仍推定為夫妻個人債務進行執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67)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其制定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夫妻個人債務及共同債務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解答》(滬高法執〔2005〕9號)第2條規定:“執行依據中沒有對債務性質作出明確認定,申請執行人未申請追加被執行人配偶(包括原配偶)為被執行人的,按被執行人個人債務處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68)《北京市法院執行工作規范》第539條第1款:“執行依據確定的債務人為夫妻一方的,根據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不得裁定追加被執行人的配偶為被執行人。申請執行人主張執行依據確定的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申請追加被執行人的配偶為被執行人的,告知其通過其他程序另行主張。”有類似規定。
2.直接執行一半共同財產不同于執行力擴張
對于夫妻個人債務,我國當前執行實踐普遍采取直接執行一半夫妻共同財產的方式(69)參加趙大偉、張興美:《民事執行視域下夫妻個人債務清償規則重塑》,載《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國家法官學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等編的四冊《中國法院年度案例:執行案例》(70)參見國家法官學院案例開發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7年度案例:執行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頁;國家法官學院案例開發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8年度案例:執行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146頁;國家法官學院案例開發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9年度案例:執行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頁;國家法官學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編:《中國法院2020年度案例:執行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26頁。中也貫徹這一理念。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執行疑難問題問答(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夫妻一方為債務人案件的相關法律問題解答》(浙高法〔2014〕38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疑難問題的解答》(蘇高法〔2018〕86號)有類似規定。
夫妻個人債務直接執行一半夫妻共同財產,但此處的“直接執行”與直接執行擔保人、共同債務執行債務人配偶、執行個體工商戶經營者等的“直接執行”具有本質區別。“直接執行”擔保人是指執行力擴張至擔保人處,不需要經過追加程序即可直接執行,本質上是擔保人的給付責任。夫妻個人債務直接執行一半夫妻共同財產的根本原因是夫妻財產制,夫妻個人債務的責任財產限額是假設債務人沒有結婚,她(他)應當取得的個人財產,在執行過程中,為了便于計算以共同財產的一半為限進行清償。(71)參見繆宇:《美國夫妻共同債務制度研究》,載《法學家》2018年第2期。夫妻個人債務“直接執行”債務人配偶不是因為執行力已擴張至配偶,是由于在共同財產制下,債務人的責任財產可能在配偶名下,執行配偶名下的財產,執行的不是配偶的個人財產,而是屬于債務人的財產份額,是財產的責任而不是人的責任(實質執行的是債務人的責任財產,在外觀上看執行的可能是配偶)。
(三)另行訴訟的合理性
超出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邊界的,若債權人主張執行第三人,應告知債權人另行訴訟解決。2010年《北京市法院執行工作規范》第539條第1款規定債權人要求債務人配偶承擔責任的,應通過其他程序另行主張。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及夫妻債務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法〔2017〕48號)第2條明確規定“未經審判程序,不得要求未舉債的夫妻一方承擔民事責任”后,從司法解釋層面堵死了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路徑,債權人只能通過另行訴訟解決配偶承擔責任問題。以此方式解決配偶責任承擔問題,能夠保障配偶的程序權利,符合審執分離的要求。但在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下,夫妻共同債務與個人債務的界限較為明確,不需要經過訴訟程序,可較為容易地區分債務性質,強制要求通過訴訟程序解決夫妻債務性質認定問題可能造成程序空轉、給予配偶轉移財產的機會(72)參見趙志超:《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正當性保障機制——再論可否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19年秋季卷。,而過于注重程序保障,會拖累執行效率,加重雙方訴累,也會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民法典》新規則下,在裁判文書僅確認夫妻一方為債務人的執行案件中,債權人若主張該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要求配偶承擔責任,執行法院無權對債務性質進行認定,應告知債權人通過另行訴訟解決。這是因為從實體法上來看,在夫妻個人債務推定規則下,共同債務認定具有獨立性和復雜性,執行程序難以處理該實體問題;在程序法上,執行程序處理復雜實體問題將嚴重影響執行效率,另行訴訟能為當事人提供充足的程序保障。
理論上,債權人可提起的訴訟主要有兩種。一是提起確認之訴,要求法院確認為夫妻共同債務。告知債權人提起確認共同債務訴訟,在訴訟程序確認債務性質后再執行,這也是當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債權人另行訴訟的主要方式。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執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夫妻一方為債務人案件的相關法律問題解答》(浙高法〔2014〕38號)明確申請執行人提起的訴訟為共同債務確認訴訟。二是提起許可執行之訴,申請法院允許執行債務人配偶。一般認為許可執行之訴屬于對債權人的事后救濟機制,在債權人提起追加被執行人被駁回后,可提起許可執行之訴。(73)參見譚秋桂:《論民事執行當事人變化的程序構建》,載《法學家》2011年第2期。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執行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8〕13號)第21條規定申請人可“請求對執行標的許可執行”,2019年《民事強制執行法草案》(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許可執行之訴,值得注意的是該方案采取區分追加被執行人和許可執行之訴兩種方式,許可執行之訴的提起不需要以駁回債權人的追加申請為前提,債權人可直接提起訴訟。筆者認為能否對第三人執行屬于實體爭議,執行權不能代替審判權,該爭議雖與執行程序有關,但屬于獨立的訴訟標的,不應以執行程序駁回追加申請為前提,應允許債權人直接提起許可執行之訴來解決當事人資格問題。
結 語
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否擴張至第三人,關系執行權的運行以及與審判權的界分,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具有必要性和正當性,執行力主觀范圍一定范圍內的擴張既能夠保障執行程序的效率,也不會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權益。但若執行力主觀范圍過度擴張,執行權侵入審判權的領域,將部分應由訴訟程序解決的爭議納入執行程序處理,執行程序的效率將受到威脅,部分案外人的權利會受到執行權侵害,影響執行權的順利運行。執行力主觀范圍向債務人擴張主要有執行程序追加被執行人和直接執行兩種方式,直接執行是我國一種重要的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形式,立法需明確適用范圍和程序,完善救濟機制,以更好地規范這一擴張形式。為平衡執行效率和案外人權利保障的關系,應將執行力主觀范圍的擴張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并對追加被執行人和直接執行兩種擴張方式予以規制。在影響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眾多因素中,債權人對第三人的實體權利請求具有高度蓋然性,能夠平衡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間的張力,可決定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邊界。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否擴張至債務人配偶,一直是我國執行程序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其中夾雜著婚姻家庭規范的夫妻債務問題以及夫妻共同財產制,使問題更復雜化。婚姻家庭規范的相關規定對于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否擴張至配偶具有重要影響,有時甚至起決定作用。在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下,執行力主觀范圍能夠擴張至配偶,執行程序追加配偶為被執行人可能是較為妥當的選擇;在夫妻個人債務推定規則下,債權人對認定共同債務、由配偶承擔給付責任的實體權利請求不再具有高度蓋然性,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至配偶缺乏正當性,債權人申請擴張的,執行法院可告知其另行訴訟解決。
民事程序法雖具有獨立的程序價值,但發揮其程序價值需要與民事實體法規范相一致。夫妻債務推定規則的變化,使得原本具備正當性的執行程序追加配偶不再具備正當性,執行力主觀范圍難以擴張至債務人配偶。在程序法的制定和修改過程中,應關注民事實體法的規定和修改對程序法的影響,全面評估實體法規則的法律后果。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與“夫妻個人債務推定”雖是不甚精確的概念,如夫妻共同債務實際包括多種類別,以及司法實踐中絕大部分債權人僅起訴債務人且并未要求配偶承擔責任,不涉及夫妻債務認定問題,但這兩個概念能夠大體上概括強制執行視域下我國夫妻債務實體法的立法變遷。筆者只是從執行權與審判權的關系、執行力擴張與實體法的聯系出發,探討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問題,并嘗試建構執行力主觀范圍擴張的邊界,對于執行力擴張的程序問題暫未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