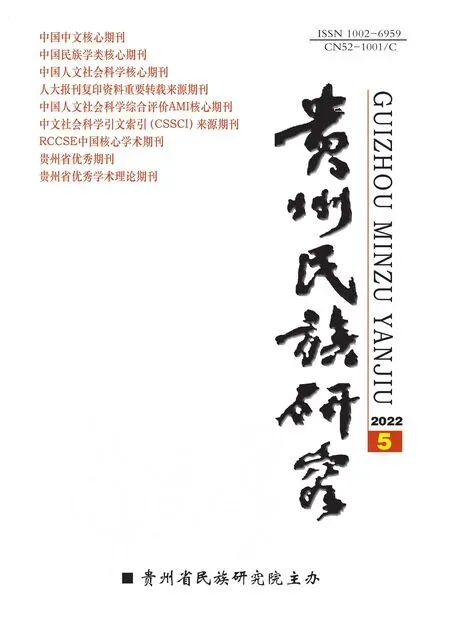海南省人口遷移、空間互嵌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論略
趙羅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一、引言
在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實現(xiàn)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歷史上人口流動對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yè)化、城市化、市場化的興起,我國進入了各民族跨區(qū)域大流動的活躍期。根據最新的“七普”數據統(tǒng)計,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已高達3.76億,占全國人口的26.6%[2]。據《中國流動人口發(fā)展報告2018》數據顯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規(guī)模1982年為31萬人,2015年增至1936 萬人[3](P5)。我國人口的大流動帶來了各民族居住空間的融合,為深化各民族交往提供了新機遇。
民族學、人類學界早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關注人口遷移對民族關系的影響,圍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特征、社會文化適應與融入、對當地民族關系的影響、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互嵌式社區(qū)建設等方面開展了諸多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成果。綜觀文獻,許多研究聚焦于當前的現(xiàn)實狀況,對歷史上民族人口遷移與民族關系互動的影響關注較少,實際上歷史上各民族人口遷移流動對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奠定了當下中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礎。本文通過對海南省三個不同時期人口遷移、聚居空間分布結構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變遷經驗進行歷時性的綜合考察,分析概括人口遷移、空間互嵌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
海南省成立于1988年,作為中國最南端的島嶼,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根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海南省共有少數民族48個,少數民族戶籍人口158.3萬人,占全省戶籍總人口的15.70%。少數民族中黎族人口最多,占少數民族人口比例的90.67%[4]。歷史上海南島的開發(fā)發(fā)展與移民緊密相關,自從漢代以來,海南島經歷數次人口遷移浪潮,因此也被稱為“移民島”。進入新世紀,伴隨著海南建經濟特區(qū)、國際旅游島的開發(fā)建設及2018年中央宣布推進海南島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海南省的人口遷移流動再次急劇增加。人口的多次遷移流動促進了海南省各民族在空間、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互嵌,其在全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二、不同時期海南省的人口遷移、民族聚居空間分布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一) 多元與匯聚:黎族進島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中國各民族間的遷移在歷史上從未停止[5],海南島在歷史上不同的王朝時代經歷過多次人口流動。黎族是最早大規(guī)模開發(fā)海南島的民族。據《海南省志》記載,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時期,就有以百越文化為主體的黎族先民,從廣東、廣西以及越南北部地區(qū)先后到達海南島。南北朝至隋朝初期,在冼夫人的帶領下,廣東和廣西一帶大規(guī)模“俚人”遷移至海南島。之后“俚人”稱為“黎”[6](P23)。漢族遷移入島始于秦漢時期,據《海南省志》 記載,秦始皇曾派遣50萬人戍守嶺南,后隨著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 郡治行政建制的確立,全國各地的移民開始進入海南島,且多為盲流難民、官吏、官兵、戰(zhàn)俘及少量商人和手工業(yè)者。漢末到五代時期,移民則以中原避亂之人為主。宋朝至明清時期,來自兩廣、福建的客家人與閩南人移入海南,成為海南漢族移民的主流[6](P22)。苗族則主要由官府征兵和民間遷移人口構成。明嘉靖、萬歷年間,從廣西調了一批苗族士兵來海南島戍邊,撤防后很多官兵在當地定居,還有一部分苗族因不滿民族階級壓迫,從云南、貴州、福建等地遷移到海南島謀生[6](P400)。回族先民主要由于經商、躲避天災人禍、從軍等原因遷移至海南。
從遷移人口的來源及數量來看,唐宋之前遷入海南島的人口主要來自全國,但整體數量較少。唐宋以后,來自廣東、福建的移民開始大規(guī)模進入海南島,這也基本上奠定了后來海南的人口構成趨勢。據日本人1939年占領海南期間的調查:“從福建省移居過來的移民有150萬人,占當時全島人口235.1萬人的63.9%,中原漢人近40萬,占17%,客家人和黎人分別有20萬,各占8.5%,苗人約5萬,占2.1%,回民1千人,占0.1%”[7](P16)。
隨著各民族人口的遷移流動,各民族在生存競爭、對抗、調適過程中,聚居空間不斷地進行轉換更替與再分布。由于漢族和黎族人口最多,因此該時期的民族人口聚居分布主要以漢黎為主,經歷了從“漢北黎南”到“外漢內黎”,再到“大圈層、鑲嵌雜糅”的民族聚居分布格局變遷[8]。
史前時期海南島黎族先人主要集中居住在沿海地區(qū),最初是“穴居”,后出了山洞改為“巢居”。隨著嶺南地區(qū)被秦始皇統(tǒng)一,移居海南島的漢族開始增多,特別是漢武帝以后,中央政權按照島內河流的布局進行行政部署,設置了儋耳、珠崖二郡和16縣,漢人依托這些行政據點遷居到島的北部、沿海、平原等地區(qū),遷入數量不斷增加,黎族從沿海地區(qū)遷至南部,“漢北黎南”格局逐漸明朗。隋唐時期,海南島的行政建制由北向南、東、西沿岸地帶逐步擴大,環(huán)島布局完成[9]。根據郡縣建置,漢族移民進入海南島四周沿海,黎族向中部地區(qū)遷徙,漢族和黎族人口分布形成“漢在外,黎在內”的聚居分布。宋代之后,行政設置基本承襲唐制,從沿海至五指山腹地的島內山區(qū),人口密度逐次減少,并沿海南島形成圈層分布[8]。明清時期全島建置更為深入,海南島圈層聚落格局進一步強化,同時此時期島內內部人口流動加大,各民族呈相互鑲嵌聚居趨勢。近現(xiàn)代以來,隨著交通的便利,島內各地區(qū)流動范圍更廣,但大圈層的民族居住結構沒有改變。隨著黎族和漢族之間的流動增多,漢黎村落的錯雜居住現(xiàn)象也逐漸增多。
伴隨著聚居空間結構變遷,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在曲折中不斷發(fā)展,盡管在相處過程中,不同民族間有摩擦沖突,但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未停止,并最終形成了“多元融匯”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傳統(tǒng)。首先,經濟上互通有無,相互依賴。秦漢至隋時期,黎族傳統(tǒng)生產方式仍為“刀耕火種”,生產效率比較低,漢族的遷入帶來了新的農業(yè)耕作方式,加快了黎族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宋元時期依賴港口的海港交易和墟市興起,明清時期商貿興盛,墟市活躍,黎漢之間互市貿易廣泛開展。其次,生活方式上相互交流學習。建筑居住方面,在漢黎雜處的中部山區(qū),一些黎族向漢族學習,開始采用和吸收漢族的居住建筑和聚居方式。在語言方面,海南方言由于移民的多源性,呈現(xiàn)出明顯的繁雜性和鑲嵌性。例如,海南島的漢語方言就有五大類,而三亞則有七種方言,屬于典型的多語言地區(qū)。通婚與身份認同方面,一些進入黎族居住區(qū)的漢族人口與黎族人民友好相處,互相影響,有的相互通婚,還互相更改民族成分。再者,文化上交融匯聚。黎族文化作為島上最初始的文化,其原始樸素隱忍的文化內涵奠定了海南島最早的文化基因。漢人遷入海南島后,特別是隋唐時期,大批官吏被貶到海南,廣傳儒學、道教,中原文化傳入海南島,海南社會進入文化交融階段,漢族中原文化與黎族原生文化開始相互影響不斷產生共性[8]。宋代閩南和潮汕的客家、廣西人、廣府人等又帶著自己的地域文化因子進入海南島,成為海南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海島文化。
(二) 計劃與集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88 年海南建省期間
歷史上海南各民族間的關系總體是和諧的。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仍存在著封建統(tǒng)治制度對少數民族的一些不平等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從根本上廢除了民族壓迫和歧視制度,解放了海南黎族、苗族等各族人民,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在民族地區(qū)實施,1955年建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國家為加快推進海南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從全國調撥資源,在物力、財力、人才等方面給予海南島大力支持,促進了人口向海南的遷移流動。
此時期海南的人口遷移主要由農墾移民、對口支援干部和少量自發(fā)流動的移民構成。(1) 農墾移民。1950年5月海南解放后,發(fā)展橡膠業(yè)成為海南建設事業(yè)的重要任務之一。從1952年起,有相當數量的轉業(yè)復員軍人及其家屬、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全國各地和海南內部的漢族群眾到少數民族聚居區(qū)建設墾殖基地,發(fā)展橡膠和熱帶作物。據統(tǒng)計,1952至1979年,進入五指山地區(qū)的農墾人員約有33萬人[6](P732)。(2) 對口支援干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建立后,國家對海南投入了大量干部人才支持。據統(tǒng)計,至1987年底,各級組織派遣了成千上萬的漢族黨政干部、醫(yī)務人員、文化教育工作者、財務人員、各類科技人員和工人,到自治州參加社會主義建設。(3) 自發(fā)流動移民。這部分移民主要是因工作分配、讀書、經商等原因自發(fā)流動到海南,數量相對較少。
從空間分布來看,該時期遷入海南的漢族流動人口響應國家經濟建設需要,深入海南中部少數民族聚居區(qū)進行農墾開發(fā)與援建。而海南內部黎、苗、回等少數民族群眾因生活、工作、讀書、經商等原因也開始在各市縣內流動,從中部的山區(qū)逐漸向南、北部漢族聚居區(qū)遷移。根據1990年全國四普數據顯示,該時期黎族主要聚居于海南的南部,少數散居于北部的萬寧縣、屯昌縣、儋縣、澄邁縣等[6](P37),回族則遍布在全省19個市(縣),不過仍以南部的三亞市較為集中[6](P515),苗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陸續(xù)搬下山來定居,分布在島中部和南部,少數分布于北部各縣[6](P407)。總之,該時期全國大量漢族同胞遷入海南中部少數民族聚居區(qū),而中部地區(qū)部分少數民族則向海南的南部、北部漢族聚居區(qū)流動,這種雙向的民族人口遷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海南傳統(tǒng)的圈層空間分布結構,各民族聚居分布開始呈“大雜居、小聚居”的趨勢。
伴隨著這種雙向民族人口流動,各民族在同一集聚空間內接觸互動的頻率也不斷增加,逐步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一是各民族間互助合作開發(fā)經濟。海南農墾創(chuàng)建之始,黎族、苗族同胞支持國家建設需要,與農墾職工互幫互助,把農墾職工當作親人朋友,為農墾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與此同時,農墾移民幫助當地少數民族群眾修渠開路,拉電打井,發(fā)展生產。據不完全統(tǒng)計,1981至1989年,海南農墾投入扶持海南民族地區(qū)從事開發(fā)性生產的資金達803.4萬元,發(fā)展種植業(yè)、養(yǎng)殖業(yè)和加工業(yè)項目65個,在海南民族地區(qū)建立科技扶貧點237個,無償投入資金882.5萬元[6](P569),使一批鄉(xiāng)鎮(zhèn)擺脫貧困,走上了致富之路。二是處理黎族和苗族矛盾,增進各民族團結。在1954年的民主改革中,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區(qū)區(qū)委、區(qū)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正確處理了嚴重影響各民族和各族內部團結的土地糾紛及典當關系達27000多宗,使各族人民消除了隔閡,增進了團結[6](P552)。尤其是為了幫助世代在高山密林中生活的苗族同胞搬到平地定居,國家撥出專項資金,組成移民工作組,幫助苗族同胞進行遷移前后妥善照顧與安置。在苗族同胞移居過程中,黎族同胞則積極為苗族同胞蓋新房備料,定居之后,黎族同胞又手把手地教苗族同胞農業(yè)耕作技術。三是漢族移民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人是文化的載體,來自全國各個地區(qū)各種職業(yè)的軍人、支援干部、知識青年、工人等長期扎根海南,在與少數民族群眾的共同生活和勞作中,帶來并傳播了各地區(qū)、各民族、各行業(yè)不同的文化,促進了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不同行業(yè)的生活風俗和社會文化的互相融合。
(三) 發(fā)展與變遷:1988年建省至今
1988 年中央決定在海南撤州獨立建省辦經濟特區(qū),海南島的開發(fā)建設進入快速增長期。2009年,海南提出了國際旅游島建設和全域旅游。2018 年,黨中央在海南建設經濟特區(qū)30周年之際,從國家戰(zhàn)略角度提出在海南建設首個中國特色自貿港試點,海南不斷迎來新的對外開放和發(fā)展契機。海南近30多年的快速發(fā)展再次帶動了人口的急劇流動,尤其在當前旅游已成為我國族際人口流遷的重要背景下,海南旅游業(yè)的勃興無疑使旅游旅居人口激增,也使得海南省人口遷移的數量、廣度、頻度達到歷史新高。
該時期海南省的人口遷移主要由經商務工群體、旅游旅居群體、優(yōu)秀人才引進和歸僑僑眷構成。(1) 經商務工群體。海南設經濟特區(qū)后,經濟發(fā)展迅速,房地產、旅游開發(fā)和通商貿易等產業(yè)勃興,20世紀90年代大批外省人來海南經商投資或務工。進入新世紀后,伴隨國際旅游島的開發(fā)建設,外地來瓊務工群體更是大規(guī)模涌入,他們主要從事建筑、酒店、餐飲、養(yǎng)殖、批發(fā)零售等職業(yè)。(2) 旅游旅居群體。伴隨海南省旅游業(yè)的發(fā)展,尤其是鄉(xiāng)村旅游與生態(tài)旅游越來越成為民眾的主要偏好,每年到海南旅游的人數不斷攀升,除了短期逗留旅客外,由于海南氣候條件適宜,度假養(yǎng)生資源豐富,還出現(xiàn)了大量候鳥遷移人口,他們每年10月份至次年4月份,因休閑、游覽、觀光、度假、探親訪友、康療等活動來海南度假養(yǎng)老。根據2019年海南文旅部門的旅居旅游發(fā)展報告,2019年來瓊旅居的游客達115.03萬人次。(3) 引進優(yōu)秀人才。自2018年習近平宣布確立海南自由貿易港的戰(zhàn)略地位以來,為加快人才建設,海南省發(f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吸引優(yōu)秀人才、高校畢業(yè)生等落戶建設海南。以三亞市為例,根據三亞市人力資源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自2018年5月至2020年9月,三亞市共辦理落戶達26107人(含隨遷人員)。(4) 歸僑僑眷。海南是我國重點僑鄉(xiāng),僑務資源十分豐富。根據海南省僑聯(lián)的統(tǒng)計,瓊屬華僑華人有390多萬人,分布在以東南亞為主的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此外還有近30萬的港澳臺同胞。近些年,隨著海南的開發(fā)建設,歸僑僑眷不斷增多,截至2020年,海南省共有歸僑僑眷近130萬人,其中歸僑16萬多人,僑眷110萬余人。
在空間分布上,該時期遷移至海南的人口群體來自全國各地,他們如“插花”般分布在海南全省各縣市。以旅游旅居人口的分布為例,根據2019 年海南文旅部門的報告,海南的旅游旅居人口來自全國30個省市區(qū),其中北方地區(qū)人口居多,東北三省(排名前三的分別是遼寧省、黑龍江省、吉林省) 占比最高,占比26.74%。從海南旅居地游客數占全省旅居游客總數的比例來看,排名前五的分別是三亞(22.3%)、海口(13.3%)、澄邁(9.4%)、儋州(7.4%)、東方(7.0%)。分東、中、西區(qū)域來看的話,東部市縣旅居游客為66.67萬人次,占全省58%,西部市縣旅居游客為38.36萬人次,占全省33.3%,中部市縣為12.71 萬人次,占全省11%。總之,人口大流動帶來各民族大融居,隨著全國各地乃至全球外來人口流入海南各地,海南省各民族人口居住空間也由局部互嵌向全域互嵌轉變,呈現(xiàn)出“大散居、小聚居、交錯雜居”的分布態(tài)勢。
伴隨著流動人口的急劇增加和工業(yè)化、市場化、城鎮(zhèn)化的興起,海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廣度、頻度和深度也不斷增強。一是經濟上各民族間實現(xiàn)合作共贏。首先,旅游業(yè)帶來了國內旅游旅居群體的不斷增加,刺激了海南省各市縣的消費市場。海南的旅游旅居群體一般屬于中高等收入群體,經濟實力較強,消費需求突出。據海南文旅部門統(tǒng)計,2019年,海南旅居群體帶來旅游消費約132.71 億元,占海南旅游總消費的十分之一。其次,華僑歸僑作為連接國內和國外的橋梁紐帶,華僑投資成立企業(yè)帶來新的經營理念,創(chuàng)造了較高的經濟效益,帶動了當地相關企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當地民眾包括少數民族群眾的就業(yè)。再者,十三五期間,海南省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qū)實施脫貧攻堅戰(zhàn)略,約有65.9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xiàn)脫貧[10]。尤其近些年海南通過發(fā)展民族文化旅游,打造特色民族村寨和旅游景點,有效地帶動了當地少數民族的就業(yè)和增收。二是建立了融洽和諧的社會交往關系。旅游作為和諧、融洽的民間交往形式,將不同階層、不同生活閱歷和文化背景的游客與本地人聯(lián)結在一起,反映了各族群眾自發(fā)交往的意愿,非常有利于促進民族間友好往來。海南省的候鳥群體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較高,具有強大的社會文化資本[11]。近些年海南省各市縣積極建立候鳥人才工作站,在教育、衛(wèi)生、文藝、科技等領域對候鳥人才和當地社會之間進行有效的供需對接,有效彌補了當地之所短和所需,促進了海南省科教文衛(wèi)社會事業(yè)的發(fā)展[12]。同時,民族通婚也是反映民族關系的重要指標。在海南,黎族、苗族文化醇厚,包容性強,他們并不排斥與外族結婚。根據國家2000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各民族間通婚率最高的民族中,黎族(12.78%) 和苗族(0.29%) 分別排在第1位和第2位[13](P294)。近10年來,隨著海南島的開發(fā)建設,大批黎族和苗族男女青年來到縣、市務工謀生,他們與外界通婚的比例仍在不斷增長。三是多元文化交融發(fā)展。一方面,華僑僑眷帶來了具有南洋和西方風格的建筑、飲食風俗和歌舞藝術等,華僑闖南洋的歷史、僑鄉(xiāng)文化和南洋騎樓文化等已成為海南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候鳥群體也帶來了各地的文化資源,他們通過成立興趣團體和公益組織,舉辦文娛活動等,豐富了海南當地群眾的文體活動。此外,旅游作為一項跨文化交流活動,在推動文化的傳承、保護和開發(fā)的同時,也弘揚民族文化和發(fā)展新興文化。海南建設國際旅游島以來,海南省政府積極挖掘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資源,通過節(jié)慶宣傳活動、旅游景點歌舞展演、少數民族特色村寨文化體驗等環(huán)節(jié),架起了海南各民族間友好往來的橋梁及相互聯(lián)系的紐帶。
三、人口遷移、空間互嵌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機制
空間作為社會關系和人類活動的容器,人口遷移通過改變民族人口居住空間分布格局,客觀上增進了民族間的交往。人口流動打破了地理居住空間的局限,縮短了民族交往的距離,使得不同民族群體在同一空間內交往的對象和范圍大大擴大。早期海南島僅有黎族先民居住,后隨著中央政權在海南設置行政建制,漢族、苗族和回族等各民族移民人口開始陸續(xù)進入島嶼,海南島的民族人口構成由單一民族向多個民族轉變。在從不穩(wěn)定逐步尋找基本穩(wěn)定的居住點的過程中,不同民族群體在海南島內的空間分布格局不斷經歷調適,直接促進了各民族間的交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海南建省時期,由全國支援海南地區(qū)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帶來的漢族人口遷移,直接改變了海南傳統(tǒng)的民族人口圈層空間分布結構,各民族聚居分布開始呈“大雜居、小聚居”的趨勢,這不但使各民族群體間接觸互動的機會大大增加,而且交往的對象來自全國各地各行各業(yè),交往范圍大大拓寬。海南建省以來,伴隨旅游業(yè)的勃興和海南島的開發(fā)建設,大批來自全國乃至全世界各行各業(yè)的移民如“插花般”地分布在海南省各縣市,使得海南省民族人口居住空間分布格局由局部的鑲嵌雜糅向全面互嵌轉變,各民族交往的頻率和范圍進一步擴大,且個體與個體間的接觸交往取代過去的群體交往成為主流態(tài)勢,交往方式和內容更加多元豐富。
另一方面,盡管人口流動帶來了各民族人口居住空間的調整,增加了各民族交往的機會,但是各民族群體接觸增多并不必然會帶來和諧的民族關系,也可能在競爭中產生更多的矛盾、沖突與摩擦。那如何在同一空間交往的過程中產生和諧的群體關系呢?芝加哥人類生態(tài)學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帕克認為,人們在“競爭性合作”中產生共生關系,即人們在相互競爭中,勞動分工或者生活的功能分化處于相互依存與合作的關系,彼此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這種既競爭又共生的關系造成自然界的平衡和秩序[14](P59)。霍利也強調相互依賴,即異質性的互補性共生關系(如功能不同的群體之間的互相補充的關系) 是社會成員適應環(huán)境的關鍵[14](P68)。人口流動在改變民族人口空間分布格局的同時,使得各民族個體與群體在同一空間內適應環(huán)境的過程中,由于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的相異而相互補充,產生互補共生關系,這種互補共生關系成為各民族遷移人口在同一空間內和諧共處、交融發(fā)展的核心動力。生產方式上,海南各民族間在競爭中互相合作,生計方式上互相學習,互利共贏。早期黎族通過向漢族學習種植和養(yǎng)殖技術,提升了社會生產力,漢族向黎族學習紡織技術并進行改造創(chuàng)新,促進了漢族地區(qū)紡織業(yè)的發(fā)展。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全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體化,經濟上各民族群體在產業(yè)鏈條與職業(yè)結構中的分工與合作更加緊密,經濟相互依賴性不斷增強。生活方式方面,黎族和漢族在建筑、語言、飲食、服飾等方面互相欣賞、接納認同并交流互鑒。精神文化上,早期中原文化與黎族文化相互影響,共同促進,形成多元匯聚的海島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海南建省時期,來自不同背景的支援干部、知識青年、轉業(yè)軍人、農墾移民帶來并傳播了各地區(qū)、各民族、各行業(yè)不同的文化,促進了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不同行業(yè)的生活風俗和社會文化的互相融合。海南建省以來,外來人口帶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各種文化,使黎苗文化、南洋文化、移民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海南匯聚、共存、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