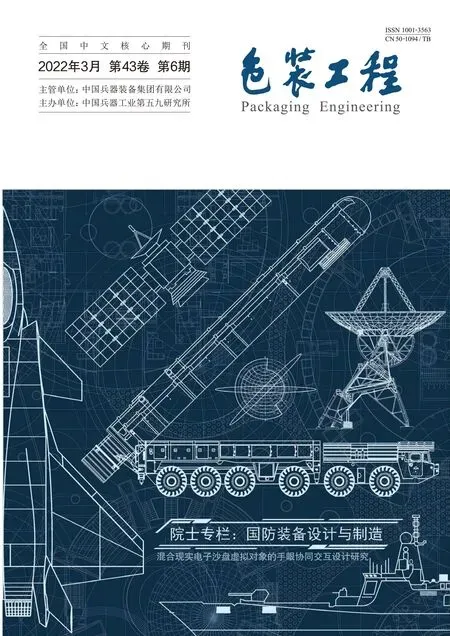當(dāng)代文創(chuàng)設(shè)計中的中國器物精神繼承與再造
蔣鵬,付業(yè)君,李樹
當(dāng)代文創(chuàng)設(shè)計中的中國器物精神繼承與再造
蔣鵬,付業(yè)君,李樹
(西南民族大學(xué),成都 610041)
中國經(jīng)典文化呈現(xiàn)出顯著的獨特性,在古代文人與工匠的合力下,已經(jīng)物化進古代中國器物的造型、紋樣、材質(zhì)之中,這些古代器物包含中國的哲學(xué)認知與倫理規(guī)范;研究并重新認識“中國器物精神”,在現(xiàn)代器物中營造當(dāng)代價值,將中國文化植入現(xiàn)代文創(chuàng)產(chǎn)品之中,能助力當(dāng)下在國際化語境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文脈,踐行文化自信。以優(yōu)秀典型案例分析為途徑,在古代器物文化中完成文化挖掘、做好文化分類、舍棄文化糟粕、弘揚優(yōu)良文化精髓,通過闡釋、比較等質(zhì)化研究方法,植入現(xiàn)代設(shè)計方法與技術(shù),形成新的中國當(dāng)代文創(chuàng)設(shè)計邏輯理論。現(xiàn)代制造業(yè)進入新的“智能、個性”化階段,給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帶來了更多的機遇與挑戰(zhàn)。文創(chuàng)設(shè)計教育只有面向本土文化挖掘與整理,加強設(shè)計人才人文素養(yǎng)和深層次中國工藝美術(shù)的知識建構(gòu),才能完成新時期的中國器物精神繼承與再造。
文創(chuàng);器物精神;再造
器物是經(jīng)過人類加工,并在使用、流傳和解釋過程中獲得文化價值[1]。中華民族在數(shù)千年的生存過程中,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這種文化經(jīng)過傳承,大部分內(nèi)化于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器物之中,由此形成了中華民族強大的器物文化;因為其擁有強大的造物能力,所以在絕大部分時期,古代中國成為世界上強大的文明存在;在精神層面上,中華民族的形成與延續(xù),是基于種族對中國文化數(shù)千年的集體認同。在物質(zhì)與精神的契合中,中華文明特有的“造物”文化萌芽、壯大、繁衍,內(nèi)化于中國人的世界觀中,這就是獨特的“中國器物精神”。從秦漢時期開始,器物交換造就了“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明交流走廊;唐宋的瓷器、日用工藝品、船舶等器物制造技術(shù)的傳播,促成了東亞儒家文化圈;明清時期,以絲綢、瓷器、茶文化為核心形成的器物體系,對世界人民生活水平進步和造物技術(shù)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歷史上中國長期引領(lǐng)世界器物制造業(yè),形成了輝煌的器物文化和權(quán)威的器物話語體系,也創(chuàng)造了《考工記》《格古要論》《宣和博古圖》等器物文化典籍。
1 中國古代器物精神的判別
將器物作為傳播載體,在其上傳遞精神性,是人類共有的認知,“器物審美”的對象是人工之物,而非天工之物[2]。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上的魚紋,敘述著半坡先民對魚的圖騰崇拜;古希臘黑繪陶瓶“阿喀琉斯與埃阿斯”上,描繪著《荷馬史詩》里他們的偉大英雄阿喀琉斯與埃阿斯在征戰(zhàn)途中,偷閑玩骰子的故事。古希臘“幾何紋高足陶罐”上滿是戰(zhàn)車與武士,記載著他們的輝煌武功;戰(zhàn)國“水陸攻戰(zhàn)銅紋壺”上,除宴樂桑獵的場景外,在壺最下方的紋樣中,還描繪著水戰(zhàn)與攻城的場景。各種文明都不約而同地將器物當(dāng)作載體,用不同的方法“描繪”各自迥異的精神與物質(zhì)世界,見圖1。

圖1 各種文明不同的器物
1.1 中國古代語境中“器物精神”的重要性
中國文字“書畫同源”,字形乃應(yīng)物象形,以形表意,可以從中回溯文字原初的意義。《說文解字》中是這樣解釋“器”字的: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專門用犬守護的財產(chǎn),必然寶貴;而《說文》解釋“物”為: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dāng)?shù)起于牽牛,故從牛。牛作為古代的重要生產(chǎn)工具,是不可濫殺的,古代帝王祭祀的貢品用“太牢”,諸侯祭祀用“少牢”,“太牢”與“少牢”的區(qū)別就在于前者多了牛,可見“物”字所指的尊貴。
現(xiàn)代文化研究將文化形態(tài)分為3類:器物文化、行為文化、觀念文化。中國古人用含義重大的“器”“物”二字稱謂器物,可見器物文化在古代中國的重要性。器物文化集中反映出人和人所改造自然的關(guān)系,是人在利用、改造自然對象過程中,取得的文化成果,中國古代器物文化是同時期行為文化、觀念文化的載體,是兩種文化的物理存在方式,是中國古代文明獨特性的物化表達。鑒于篇幅原因,文中僅從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念、宜人性、功能極致的務(wù)實主義及物以載道幾個方面論述中國古代器物文化的獨特性。
1.2 中國器物精神中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念
與同時期的其他國家相比,古代中國面積巨大,在絕大部分時期內(nèi)國家統(tǒng)一,生產(chǎn)資料流轉(zhuǎn)暢通并成本較低,但中國古代器物文化并沒有因為物產(chǎn)豐富而奢靡,一直保持著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念,踐行著當(dāng)今所推崇的“環(huán)保”理念。
瓷器長期是中國古代器物的代名詞,相較于其他材料,源于泥、成于火的瓷,是優(yōu)良的低成本器物。如果說低成本高嶺土是大自然對古代中國的偶然“饋贈”,瓷還不足以體現(xiàn)古代中國主動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觀,那金繕工藝則完全體現(xiàn)了節(jié)儉、環(huán)保的價值追求。
金繕(又稱漆繕),是用髹漆并局部貼金的工藝,修補瓷等器物。即使易碎的瓷器破損,仍不丟棄,將修補后的器物化殘為美,在踐行節(jié)儉的同時,體現(xiàn)了中國古人在面對物質(zhì)與精神的缺陷時,坦然接受不完美,在不完美中追求完美,反而超越原有美,從而達到更高精神境界的審美邏輯。
另一個體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念的代表器物是“省油燈”。古代百姓用陶瓷碟盛放燈油,燈芯燃燒時產(chǎn)生的高溫,會大大加劇燈油的揮發(fā)速度。唐宋時期四川老百姓創(chuàng)造出一種內(nèi)有中空夾層碟壁的油燈,碟壁側(cè)面有一個圓口,從這里可以注入清水;當(dāng)上部燈油燃燒時,夾層中的清水起到降低油溫的作用,從而減少油的揮發(fā),使“省油燈”節(jié)約油。宋代詩人陸游這樣描述“省油燈”:“書燈勿用銅盞,惟瓷盞最省油。蜀中有夾瓷盞,注水于盞唇竅中,可省油之半。”可見這種科學(xué)的設(shè)計,可以省下一半的燈油。
1.3 中國器物精神中的宜人性
宜人性,即“以人為本”“物人合一”,尋求人對器物的良好體驗,是現(xiàn)代設(shè)計學(xué)中“人機學(xué)”研究的一部分,這種“人機意識”早已融入中國古代器物的設(shè)計之中。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的青銅制“長信宮燈”就是典型案例。長信宮燈通體鎏金,表面的黃金為青銅材質(zhì)隔絕了空氣,避免了青銅的氧化,起到了保護作用,這也是時至今日宮燈表面依然金碧輝煌的原因。宮燈采用仿生設(shè)計的方法,整體造型是一個雙手執(zhí)燈的跪坐侍者,左手托燈座,右手提燈罩。侍者的頭、身、右臂、燈座、燈盤和燈罩等六部分中空,右臂與燈的煙道相通,當(dāng)燈盤中的油脂或蠟燭燃燒時,產(chǎn)生的煙會順著侍者袖管進入侍者體內(nèi),煙灰溫度降低后得以沉降,被收集在宮燈內(nèi)的底部(即侍者跪坐的腿部內(nèi)),不會四處飄散而污染環(huán)境,保持室內(nèi)的清潔。燈光的出口可開合旋轉(zhuǎn),燈光的亮度由此可控,見圖2。

圖2 長信宮燈原理
1.4 中國器物精神中的務(wù)實主義
除了如乾隆等少數(shù)個別統(tǒng)治者的繁復(fù)奢華審美需求外,絕大部分的中國古代器物將功能至上列為首要因素,那時的“中國制造”意味著質(zhì)量上乘、樣式精美,極致追求器物質(zhì)樸耐用的用戶體驗。
科舉考試是古代文人求取功名的重要途徑,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道路中,必須經(jīng)歷十年寒窗苦,冬季書房中的便攜火爐成為必需品。這類火爐,放在手中的小型爐叫手爐,放在腳邊取暖的叫暖爐,明代晚期的張鳴岐,是制作此類銅爐的著名工匠之一,被稱為“張爐”,慢慢成為當(dāng)時的馳名品牌。“張爐”為銅制,造型古樸簡約,頂部散熱部位或仿竹條編花,或紋樣鏤空,去除多余紋飾,以務(wù)實精神追求功能。“張爐”有兩大特點:第一為放紅炭暖而不燙(說明爐控溫做得好,炭火能長時間均勻燃燒,透過厚厚的銅爐壁,散發(fā)出的熱量剛好取暖,卻不燙人);第二個特點是踹而不癟(腳邊的暖爐常在使用中被誤踢誤踹,爐不變形,說明用料扎實,材料強度高,經(jīng)久耐用)。這種簡樣式、重功能的思想根源來自于務(wù)實主義,也是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念的另一種體現(xiàn)——產(chǎn)品耐用是生產(chǎn)資料最好的節(jié)約方式。
滲瀝液一期O池的結(jié)構(gòu)跨度較小,密封蓋板采用有機玻璃鋼弧形蓋板,二期O池的結(jié)構(gòu)跨度較大,故采用有機玻璃鋼W型蓋板,為方便日常設(shè)備檢修、維護,工程施工中在相應(yīng)的位置預(yù)留了檢修門窗。
1.5 中國器物精神中的“物以載道”觀念
作為亞熱帶地區(qū)普遍存在的竹子,生長迅速,質(zhì)地堅韌,是世界上生長最快的植物,各地區(qū)人民普遍將其作為建筑材料,但賦予它特殊精神意義,將竹作為優(yōu)良精致器物制造材料的,唯有中國。《禮記》中論述了通過“藏禮于器”來達到“器以載道”的目的,通過器物達到道德教化的作用[3],其根本實現(xiàn)方式是通過特定的設(shè)計,將教化內(nèi)容以“禮”規(guī)則內(nèi)化在具體器物之中,借此實現(xiàn)特殊的教化目的。文房竹制器物是這種思想的典型代表。
中國古代藝術(shù)、文化的核心締造者是文人群體,雖然頂級器物審美往往由出資人——帝王或富豪權(quán)貴——決定,但這種藝術(shù)評定標(biāo)準(zhǔn)依然源于文人營造的文化語境。唐代劉禹錫詩云:“高人必愛竹,寄興良有以,峻節(jié)可臨戎,虛心宜待士”,竹的挺拔、修長、中空,又廉價、普遍,還四季青翠,這些特征都被中國文人引申為他們推崇的堅韌、苦修、虛心、恒定,將竹子化為中國文人集體的品格象征,將竹擬人化,對它進行頌揚:與梅、蘭、菊并稱為“四君子”,與梅、松并稱為“歲寒三友”,最終將竹塑造成中國文人的文化標(biāo)志。竹成為筆、筆筒等文房用具的主要制作材料,創(chuàng)造出各種文房器物精品。古代中國文人衣著長袖,書畫時容易沾染墨汁,故用中間剖開、一分為二的半邊竹筒,置于腕紙之間,作墊手之用,稱為臂擱,類似歐洲藝術(shù)家支腕杖的功用。但與木桿式歐洲支腕杖不同的是,臂擱上雕刻各種內(nèi)涵文人精神的圖文,或象征清廉的荷花,或代表苦中高潔的臘梅,或在真竹制成的臂擱上再刻竹圖案,或銘刻文人榜樣的隱居高士,或是自省的詩句……李約瑟也注意到:“沒有哪一種植物像竹一樣在中國歷代藝術(shù)和技術(shù)中占據(jù)如此重要的地位。”
文人在造物的過程中,在功能之上講究內(nèi)涵,這是文人造物與匠人造物的區(qū)別[4]。不僅是臂擱,中國文人擅于將各類器物的材質(zhì)、功能提升到哲學(xué)高度,在器物之上建構(gòu)出某種文化特質(zhì),正如學(xué)者李硯祖所說,“傳統(tǒng)器物……是民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是‘國學(xué)’的一部分[5]”,包括傳統(tǒng)工藝、對材質(zhì)的哲學(xué)認知在內(nèi)的各種觀念與方法一起構(gòu)成了中華器物精神。竹的案例中,與竹關(guān)聯(lián)的各種因素一齊將竹制文房器物從廉價的日用器,升華為具有“以天合天”意味的觀念器,在器物實用功能性之外擴展出觀念功能,價值觀傳播成為其存在的重要意義,樸素的文房器物成為古代文人精神的輿論場。
1.6 中國古代器物精神的判別與繼承
歷史文化成因的復(fù)雜,導(dǎo)致器物文化的復(fù)雜,其中亦有糟粕,需要判別區(qū)分,例如來自纏足風(fēng)俗的“三寸金蓮”鞋。北宋時期,出于對舞女舞姿的欣賞,纏足只求足部纖直,而后卻漸漸成為一種審美情趣,在摻雜著審美、禮教等復(fù)雜因素之后,轉(zhuǎn)化成為一種畸形病態(tài)的社會認同[6]。在纏足初始階段,追求的是腳型平直,尚屬視覺美;到了“弓鞋”階段,腳的塑形追求走向反自然的一面;再到“三寸金蓮”鞋的標(biāo)準(zhǔn),女性必須裹腳至破壞天生骨架,徹底成為畸形審美,小腳是在男權(quán)“注視”下的女人帶有“性趣味”的著裝[7]。到了清代,官方禁止纏足行為,“三寸金蓮”成了被統(tǒng)治群體對統(tǒng)治群體的無力反抗,反而鼎盛。無論當(dāng)初流行的初衷是什么,今天來看,這種器物內(nèi)涵的“精神”,體現(xiàn)了禮教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推崇柔弱的審美觀[8],是對女性的摧殘,是文化沉淀后的殘渣,絕對不值得弘揚繼承,只能成為歷史過往中的器物文獻樣本。
除了前文中的“宜人性”,產(chǎn)品還必須具備“宜產(chǎn)性”,包括可持續(xù)發(fā)展、綠色、低碳、環(huán)保之意,而物質(zhì)的匱乏與豐富,是隨歷史時代變化的。商周時期,大象與犀牛遍布中國大部分地區(qū),以牙(象牙)、角(犀角)等材質(zhì)制作器物,符合宜產(chǎn)性原則;到了稍后的千年,使用此類材料制作器物,純粹是為了追求“物以稀為貴”的奢侈心態(tài);在當(dāng)今社會動物保護的語境與現(xiàn)實下,再提象牙、犀角的器物用料,必然有違常理,不能成為當(dāng)代“中國器物精神”。
由此可見,今天值得繼承的中國古代器物精神,應(yīng)當(dāng)同時具備符合現(xiàn)代社會的“宜人性”與“宜產(chǎn)性”,必須內(nèi)含健康、積極的中國哲學(xué)思想,對當(dāng)下的人類生活產(chǎn)生良性的影響。
2 中國器物精神的當(dāng)代意義與再造案例
包括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在內(nèi),當(dāng)今的器物絕大部分是現(xiàn)代工業(yè)化的產(chǎn)物,工業(yè)化過程中的技術(shù)共享,也往往意味著文化趨同、本土文化消失——源于西方的工業(yè)化挾裹著西方文化一同影響著中國文化。在當(dāng)下“文化自信”的自覺中,包括經(jīng)典器物精神在內(nèi)的中國文化研究得到重視,中國當(dāng)代器物設(shè)計制造重現(xiàn)“中國美”成為踐行的熱點,但必須認識到,中國當(dāng)代器物對經(jīng)典器物精神的繼承與踐行,必須進行當(dāng)代化改良,即對器物材料、結(jié)構(gòu)、性能進行優(yōu)化,才能符合當(dāng)代社會生活的效率要求,否則進入不到當(dāng)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如前文所述,基于傳統(tǒng)器物精神的當(dāng)代產(chǎn)品設(shè)計,必須有選擇地重構(gòu)器物精神,否則盲目挪用只會產(chǎn)生牛頭不對馬嘴的文化怪物,中國器物精神必須完成當(dāng)代“再造”,這種“再造”,不是簡單“復(fù)刻”,而是在現(xiàn)代設(shè)計、制作手段下的文化內(nèi)核延續(xù)與創(chuàng)新。
在當(dāng)代“文化自信”的中國文化自覺中,有很多優(yōu)秀的踐行案例值得學(xué)界研究,下文集中研究LKK洛可可設(shè)計“新文創(chuàng)”理念下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案例,探討這些器物背后的設(shè)計思維與文化傳承。所謂“新文創(chuàng)”理念,即用現(xiàn)代技術(shù)手段,內(nèi)涵中國器物精神,設(shè)計制造符合當(dāng)代審美標(biāo)準(zhǔn)與生活方式的新型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這種“新”,是現(xiàn)代簡約抽象審美與中國文化內(nèi)核的融合,已經(jīng)成為一種特有的設(shè)計方法,普遍應(yīng)用于LKK洛可可的文創(chuàng)設(shè)計之中。
2.1 東方意境美與現(xiàn)代設(shè)計表達的融合
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觀認為,對自然萬物的簡單仿生(即寫生),其美學(xué)層級低于采用抽象式的藝術(shù)意念化表達(即寫意),意境美是古代中國器物的最高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但因技術(shù)原因,落實到具體表現(xiàn)方法時,依然是具象式的,例如筆筒上淺浮雕的松下高士,或筆架的山石造型,依然離不開對具體現(xiàn)實事物的描摹,依然是寫生的方法。熏香,作為華夏民族共同生活行為特征,除了驅(qū)蟲醒神,亦有營造意境之意。洛可可設(shè)計的文創(chuàng)代表作品“高山流水香臺”,用抽象設(shè)計語言,將熏香場景演繹為當(dāng)代化的中國意境美。
“高山流水”出自中國著名的知音典故:先秦時,琴師俞伯牙在荒野中彈琴,悠揚的琴聲吸引了樵夫鐘子期,由此兩人成為知音好友。子期去世后,伯牙悲痛知音已去,摔琴絕弦,終生不再彈琴,而傳說中俞伯牙創(chuàng)作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也成為中國代表性古曲之一。
LKK洛可可設(shè)計取古琴曲之名,演繹為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高山流水香臺”。香臺通體黑色,在粗糙的底座上,有三枚頂面凹陷、互相重疊的光滑“黑石”(陶瓷制成),頂部的“黑石”最小,有一上下貫穿的孔,孔中正好可放入一枚錐型塔香。塔香內(nèi)部掏空,呈倒U狀結(jié)構(gòu),當(dāng)頂端被點燃時,倒U狀結(jié)構(gòu)內(nèi)的煙只好向下流動,遇到溫度較低的陶瓷表面,煙的溫度下降并下沉,繼續(xù)像水一樣向下流動,仿佛變慢的白色溪水一樣。在第二層“黑石”上,還可以放置一枚小小的橢圓“黑石”,隨著煙的流動,“黑石”會從第二層滑到第三層,再從第三層滑落在粗糙的底座上,叮咚的聲音,仿佛石子落入溪水一般。
LKK洛可可的“高山流水香臺”,黑石間白煙緩慢流動,如云海瀑布,讓人聯(lián)想到古代傳說中仙人居住的蓬萊仙山;而黑色橢圓造型,又與無定型的白煙一起,象征著山川河流的天地之美,構(gòu)成濃重的禪宗意味。不知何時會跌落下來的“黑石”,又增添了一個期待與驚奇。這款香臺文創(chuàng)擺脫了具象造型的束縛,用極簡的抽象形態(tài)傳遞中國審美韻味,成為一款優(yōu)秀的當(dāng)代中國文創(chuàng)精品。
在LKK洛可可后續(xù)的“香臺”系列文創(chuàng)中,這種抽象化的雅致恬靜,如同中國文人寫意畫般的意境,繼續(xù)在煙與石、山與水中放大。“觀魚香臺”,金銀兩色的魚循煙而上,仿佛在晨霧中游弋;“獨釣香臺”則還原柳宗元“獨釣寒江雪”的視角,傳達出古代文人追求的孤寂之美;“江南荷塘月色禪意香臺”,煙云中,月光下,荷花已盡,唯剩蓮蓬。即使不用塔香原理的“南京牛首山禮物”,也用倒懸煙香中的牛首山與地標(biāo)塔樓,營造出極雅的中國意境,見圖3。

圖3 “香臺”系列文創(chuàng)
不僅是“香臺”系列產(chǎn)品,LKK洛可可的文創(chuàng)設(shè)計中,始終回避簡單自然主義寫生的設(shè)計傾向,把設(shè)計語言控制在寫意之中,將中國雋永禪意與抽象極簡結(jié)合,再造出干凈利落的中國當(dāng)代器物。去繁求簡,將產(chǎn)品使用過程中的動態(tài)場景,營造成符合中國文化的意境,是當(dāng)代文創(chuàng)器物的一種設(shè)計新思路。
2.2 基于中國“喜文化”共識的宜人性設(shè)計
在文創(chuàng)設(shè)計過程中,主要從語義學(xué)的角度來探究,運用符號學(xué)理論與方法來進行創(chuàng)意表達[9]。器物具有象征性是社會科學(xué)物質(zhì)文化研究的共識,在組織場域內(nèi),某一人工器物被大多組織認可為符號的時候便具有了合法性,并影響新組織對符號的選擇和意義的建構(gòu)[10]。“喜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中國人將子嗣繁衍寓意的圖案視為吉祥,至今依然如此。古代器物中使用具象紋樣或造型表達這類“喜文化”,例如蝙蝠寓意“福”,石榴象征“多子”,葫蘆象征“福祿”。LKK洛可可擺脫了具體形象的描繪,用抽象符號勾起中國人的文化共識,傳遞吉祥期盼。
由4件套盤組合而成的“大耳有福”文化禮品,極簡的外形,卻能讓中國人會心一笑,這是因為盤的外形,讓人聯(lián)想起布袋和尚。五代時寧波地區(qū)有體胖腹大、袒胸露腹、笑口常開的僧人,常手提永遠裝不滿的布袋,民間稱為“布袋和尚”,認為他是彌勒佛化身,象征量大福大,有提醒世人包容、和氣生財之寓意。“大耳有福”盤兩側(cè)凸出“耳”的造型又似古代漆器“耳杯”,在使用中便于拿取,造型的吉祥寓意為餐食過程帶來愉悅,“美食必然要配美器”[11],最終達成宜人性的目的。
基于強大IP符號的文創(chuàng)設(shè)計,反過來會限制其發(fā)展,人人皆知的文物原始形態(tài),讓后續(xù)設(shè)計被原始形態(tài)“綁架”,顯得束手束腳,故宮博物院文創(chuàng)產(chǎn)品也面臨這種境遇。現(xiàn)存故宮文華殿的“孩兒枕”,是北宋定窯瓷枕的典型器物,一個素面光潔的孩兒伏臥床榻,兩臂環(huán)抱,墊起臉部,撒嬌蹬腿。LKK洛可可根據(jù)這件古代瓷器珍品,創(chuàng)造了“故宮百子”系列日用瓷器,巧妙地對母題進行解構(gòu)——將白瓷材質(zhì)與孩兒造型分離開來,用白瓷作為香具、茶具的構(gòu)造材質(zhì),借用如白玉一般的材料質(zhì)感勾起中國人崇玉的文化情懷;造型借鑒中國古代器物中的缽(佛教常用器)、葫蘆(道教常用器)、提梁壺,完成吉祥造型的寓意轉(zhuǎn)換;將孩兒枕形態(tài)用現(xiàn)代設(shè)計手法,抽象簡化為美國波普藝術(shù)家哈林(Keith Haring)式的極簡風(fēng)格——金色孩兒標(biāo)志,在產(chǎn)品中重復(fù)出現(xiàn),成功地用當(dāng)代化設(shè)計語言完成了對中國古代器物解構(gòu)后的當(dāng)代重構(gòu),見圖4。正如有的學(xué)者指出,傳統(tǒng)器物元素在現(xiàn)代性轉(zhuǎn)化過程中,是將這些有形和無形的元素進行解構(gòu)和重組,用現(xiàn)代手段進行再造與構(gòu)建,以適應(yīng)現(xiàn)代人的使用需求和審美觀念[12]。
上述2個白瓷產(chǎn)品案例,不僅巧妙回避了古代器物制作中對文化樣本的簡單寫生、復(fù)制,而且對關(guān)鍵文化符號進行抽象提煉,用寫意的方法完成“意念仿生”,創(chuàng)造了極富現(xiàn)代感的當(dāng)代中國器物產(chǎn)品。將中國傳統(tǒng)器物文化中的圖像符號解構(gòu)重組,轉(zhuǎn)具象造型為抽象符號,結(jié)合新材料、新工藝的使用,是當(dāng)代文創(chuàng)器物的一種設(shè)計新方法。

圖4 大耳有福文化禮品、北宋定窯孩兒枕和故宮百子系列文創(chuàng)
2.3 “由意而生”的環(huán)保型旅游文創(chuàng)產(chǎn)品
建于唐初的樂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彌勒佛坐像,千年以來,大佛一直被表面雜草災(zāi)害所困,這些雜草不僅有礙觀瞻,而且草根深入“佛體”,造成巖體分裂、表層剝落,堵塞排水管道后進一步加重佛像的水害。
文化認同是民族群體共同的精神紐帶,“喜”文化是一種精神信仰和心理暗示,人們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通過表意符號系統(tǒng)轉(zhuǎn)化為樂觀的態(tài)度和積極的祝愿[13]。LKK洛可可在“樂山大佛彌勒瑞草”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設(shè)計時,憑借當(dāng)代藝術(shù)中“理念重構(gòu)”的技巧,用“由意而生”的概念構(gòu)建法,將大佛表面的雜草制成各種符紙、書簽、賀卡等紙制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從“佛性”改造“廢物”,充分利用人們的吉祥訴求,將旅游IP形成吉祥概念,促使人們心中吉祥向往的產(chǎn)生。“樂山大佛彌勒瑞草”利用人們希望借助某些事物或神靈幫助他們消災(zāi)滅害,保佑他們平安順利的執(zhí)念[14],用前文中竹的概念轉(zhuǎn)移邏輯,將“佛身上的雜草”轉(zhuǎn)化為“與佛相關(guān)的靈草”,即將無用“雜草”轉(zhuǎn)化為吉祥的“喜”符號,完成從“雜草”到“瑞草”的概念轉(zhuǎn)換,順利地創(chuàng)造了一款材料環(huán)保“宜產(chǎn)”的爆款文創(chuàng)。挪用當(dāng)代藝術(shù)中的“觀念性”概念營造手法,對“宜產(chǎn)”材料植入某種“宜人”觀念,使該材料制造的產(chǎn)品具有符合中國文化的特殊積極的精神意義,是當(dāng)代文創(chuàng)器物的一種設(shè)計新手段。
3 結(jié)語
中國古代器物展示了中國美學(xué)成就中最具魅力的一面,直接反映了中國審美文化所達到的高度[15]。中國數(shù)千年形成的器物文化蘊藏著中華文明的文化密碼,針對中國器物文化進行研究,并在之基礎(chǔ)上完成當(dāng)代文創(chuàng)產(chǎn)品開發(fā),不僅是市場與經(jīng)濟問題,更是文化傳承命題,諸如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與非遺原生地手工業(yè)保護、少數(shù)民族器物精神傳承等問題,還需要各界一同研究、實踐,LKK洛可可文創(chuàng)設(shè)計只是邁出了卓有成效的第一步。在提升“中國制造”與“文化自信”的當(dāng)下,產(chǎn)品創(chuàng)新與文化內(nèi)涵聯(lián)動,可以“以器載道”“以物載道”,創(chuàng)造當(dāng)代中國器物二次崛起,完成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必須看到,在當(dāng)代中國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創(chuàng)造與研究過程中,依然還有諸多問題需要面對、解決。如只在傳統(tǒng)器物上進行裝飾,以表面材質(zhì)的華美體現(xiàn)工藝技術(shù)的精湛,造型未能創(chuàng)新;向雕塑方向轉(zhuǎn)變,失去器物造型的根本屬性;高校理論教材表面看是器物造型設(shè)計,實際是成形工藝或傳統(tǒng)器物造型的形式規(guī)律分析,極少涉及從創(chuàng)新觀念到創(chuàng)意表達的系統(tǒng)論述[16]。
中國器物精神的當(dāng)代再造,不是簡單照搬中國古代器物的文化復(fù)古主義,而是梳理中華器物文化體系中的優(yōu)良精神共性內(nèi)涵,進行當(dāng)代產(chǎn)品創(chuàng)新實踐,用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基因支撐起當(dāng)代中國設(shè)計。“文化自信”始于了解,在高校設(shè)計學(xué)科教學(xué)中,完成中華民族器物精神理論研究和實踐還有較大空間,畢竟當(dāng)代學(xué)子們是吃著洋快餐、看著西方動畫片、唱著HIP-HOP長大的一代,他們接觸到的是物化的西方思想,在文化上,或多或少認同西方的頹廢文化、街頭文化、死亡文化;年輕一代文化產(chǎn)品創(chuàng)造者知識體系狹窄化,對中國文化理解膚淺化,從中國文化安全而言,這無疑是危險的。唯有對新一代文化產(chǎn)品創(chuàng)造者完成中國文化綜合素養(yǎng)知識架構(gòu)的建構(gòu),使之學(xué)會器物精神背后的文化挖掘方法,才能培養(yǎng)他們繼承、創(chuàng)造中國文化新產(chǎn)品的能力,用優(yōu)良產(chǎn)品完成市場引導(dǎo),進而完成同齡人的價值觀認同引導(dǎo),達到弘揚中華文明的目的。在文創(chuàng)設(shè)計實踐中完成中華文明傳承,在專業(yè)課程中完成課程思政,亦需要高校同仁的不懈共同努力。
[1] 朱大可. 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器物文化遺產(chǎn)的遺忘、拯救與復(fù)興[J]. 河南社會科學(xué), 2010, 18(5): 54-59.
ZHU Da-ke. Utensils Narration in Shanghai Exposition—The Mislaying, Saving and Reviving of Utensil Cultural Heritage[J].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0, 18(5): 54-59.
[2] 李社教, 邱紫華. 論器物審美的特性[J]. 中國文學(xué)批評, 2018(3): 67-73.
LI She-jiao, QIU Zi-hua.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esthetics of Utensils[J]. Chinese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2018(3): 67-73.
[3] 李委委. 《禮記》造物思想的文化生態(tài)論[J]. 美術(shù)大觀, 2017(9): 54-55.
LI Wei-wei.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creation thought in The Book of Rites [J]. Art Panorama, 2017(9): 54-55.
[4] 陳原川. 明式家具設(shè)計與審美理念的精神影響研究[J]. 包裝工程, 2018, 39(22): 194-199.
CHEN Yuan-chuan. Spiritual Influence of Ming Style Furniture Design and Aesthetic Idea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22): 194-199.
[5] 李硯祖. 物化的國學(xué)[N]. 人民日報, 2016-10-02(8).
LI Yan-zu. Materialized Chinese Studies[N].People's Daily, 2016-10-02(8).
[6] 盧堯選. 人工器物與制度——組織社會學(xué)器物研究述評[J]. 社會發(fā)展研究, 2017, 4(1): 208-227.
LU Yao-xuan. Study 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Artifacts and Institution: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Artifacts in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J].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17, 4(1): 208-227.
[7] 尹志紅, 陶輝. 論男性視閾下的女性的審美價值取向——以三寸金蓮和高跟鞋為例[J]. 藝術(shù)百家, 2012, 28(S2): 248-249.
YIN Zhi-hong, TAO Hui. Female Aesthetic Orientation in the Male Threshold: Taking Women's Bound Feet and High-Heeled Shoes as Examples[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2, 28(S2): 248-249.
[8] 許仲林, 李穩(wěn), 鄔紅芳. 論我國明清時期弓鞋所折射的文化象征寓意[J]. 吉林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 2017(3): 71- 77.
XU Zhong-lin, LI Wen, WU Hong-fang. On the Cultural Symbolic Meaning of Bow Sho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 Journal of Jilin University of Arts, 2017(3): 71-77.
[9] 汪天雄, 周美玉. 基于用戶感性需求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設(shè)計范式構(gòu)建[J]. 包裝工程, 2020, 41(20): 14-18.
WANG Tian-xiong, ZHOU Mei-yu.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Paradigm Based on User Kansei Need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20): 14-18.
[10] 張競瓊, 李洵, 張蕾. 從纏足風(fēng)俗解析弓鞋裝飾設(shè)計的形制流變[J]. 藝術(shù)百家, 2013, 29(6): 177-181.
ZHANG Jing-qiong, LIN Xun, ZHANG Lei. Form Transformation of Bow Sho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et Binding[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3, 29(6): 177-181
[11] 王偉. 漢代漆制食器設(shè)計美學(xué)研究[J]. 北京印刷學(xué)院學(xué)報, 2018, 26(1): 45-47.
WANG Wei. Aesthetics Research on Lacquer Tableware Design in Han Dynasty[J].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2018, 26(1): 45-47.
[12] 姜陳. 傳統(tǒng)器物元素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化與應(yīng)用[J]. 包裝工程, 2018, 39(16): 228-232.
JIANG Chen. Functional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ifact Element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16): 228-232.
[13] 莫軍華, 劉蓓蓓. 傳統(tǒng)“喜”文化在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設(shè)計中的應(yīng)用[J]. 包裝工程, 2019, 40(22): 247-252.
MO Jun-hua, LIU Bei-bei.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Happiness" Culture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22): 247- 252.
[14] 鄧焱. 中國傳統(tǒng)吉祥圖案在現(xiàn)代設(shè)計中的應(yīng)用[J]. 包裝工程, 2019, 40(20): 223-225.
DENG Yan.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in Modern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20): 223-225.
[15] 趙元昊. 話語場中的民間藝術(shù):作為商品的泥泥狗在不同語境中的社會生命[J]. 民族藝術(shù), 2019(6): 59-70.
ZHAO Yuan-hao. Folk Art in the Discourse Field: The Social Life of the Mud Dog as a Commodity in Different Context[J]. National Arts, 2019(6): 59-70.
[16] 王立德. 基于中國美學(xué)精神的當(dāng)代器物造型研究[J]. 包裝工程, 2015, 36(16): 1-4.
WANG Li-de. Contemporary Utensil Styling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Aesthetic Spirit[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5, 36(16): 1-4.
The Spirit Inheri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Utensil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JIANG Peng, FU Ye-jun, LI Shu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Under the joint effort of ancient literati and craftsmen, the great uniqueness of Chinese classical culture has been materialized into the shapes, patterns and materials of ancient Chinese artifacts, which contain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gnition and ethical norms. Studying and re-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spirit of classical utensils", creating contemporary values in modern artifacts, and embedd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an help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spread Chinese context, and practice cultural confid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xcellent typical cases, we should complete the cultural excavation in ancient artifacts culture, do a good job in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discard the dross of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fine cultural essence.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ison, we should implant modern design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and form a new logic the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creation design.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intelligence and individuality", bringing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education should be oriented to the local culture, strengthen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design talents and the deep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so as to complete the reengineering of Chinese utensils spirit in the new era.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utensils spirit; reengineering
TB472
A
1001-3563(2022)06-0252-07
10.19554/j.cnki.1001-3563.2022.06.033
2021-11-12
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xué)重點研究基地工業(yè)設(shè)計產(chǎn)業(yè)研究中心開放課題資助(GYSJ2019-010)
蔣鵬(1976—),男,碩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工業(yè)設(shè)計。
付業(yè)君(1976—),女,碩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藝術(shù)設(shè)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