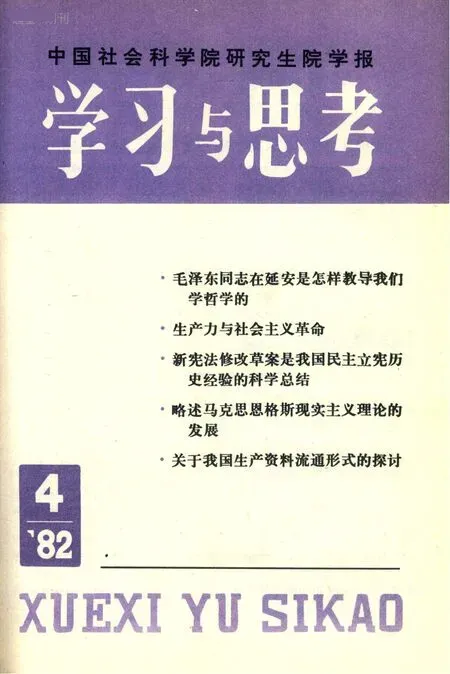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形成和發展的三重維度*
黃先祿
提 要:實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最大黨性”,是貫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的“活的靈魂”。百年來,實事求是逐步形成和發展成為黨的思想路線,成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思想武器。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不僅是一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奮斗史,而且也是一部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史、發展史。因此,從理論、實踐和價值三個維度條分縷析地剖析實事求是,探尋其從哲學層面提升到思想層面、從品性層面提升到黨性層面、從道德層面提升到宗旨層面的邏輯路徑,初步探究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形成和發展的邏輯機理,從而深化理解延安精神孕育、形成和發展的歷程,進而提升用延安精神深化新時代黨性教育的科學化水平。
引言
實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最大黨性”,是貫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的“活的靈魂”。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實事求是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而且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敢不敢堅持實事求是,能不能堅持實事求是,始終“考驗著我們的政治立場”,始終“考驗著我們的道德品質”,始終是我們“黨性純不純、強不強的一個重要體現”。歷史證明,黨自成立以來,實事求是就成為價值追求,逐步形成、發展成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武器,我們黨著力從哲學層面提升到思想層面、從品性層面提升到黨性層面、從道德層面提升到價值層面,使之發展成為黨的思想路線。可以說,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不僅是一部黨的革命史和奮斗史,而且也是一部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史和發展史。今天,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面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關鍵時期,重溫和演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形成和發展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價值邏輯,對于堅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用延安精神“滋養初心、淬煉靈魂”,從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黨性的差距、校準前進的方向”,進而“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意義十分重大。
一、實事求是從哲學層面提升到思想層面的理論維度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就是“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直接用過“實事求是”這個詞,但他們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突出強調的就是實事求是,并且始終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作為一條重要原則來加以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層面來看,其最偉大之處就在于其將實踐引入認識論,這是與其他一切舊哲學的根本區別所在。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雖然費爾巴哈是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走向了唯物主義,但在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上,費爾巴哈與黑格爾的“邏輯范疇的預先存在”即“邏輯范疇先于自然界而存在”的觀點卻是完全相反的、割裂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表達的,思維方式決不是人們頭腦中固有的,而是實踐活動的結果,是實踐活動邏輯的“內化”,且永遠“不能從自身中,而只能從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發。否則,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就會被顛倒、被分裂,即“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而否定唯心主義的認識論的同時,也相應地肯定了堅持物質決定意識立場觀點的“費爾巴哈體系”和被稱之為“倒立著的唯物主義”的“黑格爾體系”。也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世界里,一方面,人們的一切認識都要以客觀物質世界為前提和出發點,“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即在強調物質的決定作用的同時,也強調意識的能動作用;另一方面,“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即人的思維不僅不能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且還必須反映并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不僅要來自于人的實踐活動,而且還要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加以檢驗。顯然,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兩大問題的回答是:物質是第一性的,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本源;意識是第二性的,是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反映。正是在這樣的哲學框架下,實事求是才一直貫穿其中并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核心和思想精髓。
(一)實事求是思想中的“實事”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實事”的相似性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寫道:唯物主義歷史觀“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顯然,在這里,與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的是,唯物主義歷史觀所講的“物質”是指客觀存在,即客觀“世界的真正的同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質性”。即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實事求是”中的“實事”具有相似性,也就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格物致知”和“即物窮理”中的“物”。然而,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中國古代的先賢們更多的是從唯心主義或者機械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實事求是”中的“實事”,如:王船山說過:“不相信純粹的理,而關心固有的社會關系”。即強調社會存在的客觀性,但忽視“純粹的理”或者說是“實事求是”中的“是”的能動作用;而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則是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兩個視角來詮釋“實事求是”中的“實事”。其所謂物質決定意識,就是指“實事求是”中的“實事”決定“是”,并通過“實事”來求“是”。而其所謂意識反作用于物質,就是指“實事求是”中的“實事”與“是”存在著內在的、辯證的邏輯關系,即“求”來的“是”不是無所作為的,而是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所講的“物質”,不僅僅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實事求是”中所講的“實事”那么簡單,而是還包含著整個歷史和社會中真實發生的事實。即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闡述,不僅僅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雙重維度展開的,而且其所謂的“實事”在他們那里還包含了世界中的客觀存在和已經發生的歷史史實以及當下的社會現實,其對“實事”的內涵的理解比中國古代的先賢們要更有深度和廣度。其深度體現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實事”是能夠通過“求”來與“是”相結合的“物”,是全面的、具體的,而不是片面的、抽象的。也就是說,相當于把朱熹這一代表著宋代儒家學派中的“即物窮理”的“物”和顧炎武這一代表著清朝乾嘉學派中的“經世致用”的“用”“結合”起來。但這種“結合”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那里才得到了提倡,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中得到了踐行。其廣度體現在“實事求是”中的“實事”,不僅包括世界中的客觀存在物,不僅包括當下發生的社會現實,而且還包括過去已經發生的歷史史實,“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堅持實事求是,最基礎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實事’,就是了解實際、掌握實情”。
(二)“實事求是”思想中的“求”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論中的“求”的相似性
《神圣家族》是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批判哲學”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觀點的同時,也闡明了他們自己不同于“‘自我意識’哲學”的“歷史運動離不開人的物質生活”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觀點。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這里講的“人的活動”,即是“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在這里,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的不只是認為歷史的活動是人的實踐活動,而且還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古典哲學的區別。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充分地認識到了實踐的作用,而且還表明了其對世界的研究并沒有只停留在認識與解釋層面。為此,馬克思在“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還進一步強調,“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在馬克思看來,實踐不只是改造主觀世界的主要方式,而且更是改造世界的主要方式。顯然,馬克思主義實踐論中所講的“求”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實事求是”中所講的“求”具有相似性,比如:“格物致知”中的“格”和“致”的作用,與“實事求是”之中的“求”的作用。盡管如此,甚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關于認識與實踐的辯證統一關系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具有相通之處,但中國古代的先賢們對“實事求是”思想中的“求”的研究也就僅限于此,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眼中的“實踐活動”在具體的研究和應用中,要遠比中國古代先賢哲們的“經世致用”更加細致、更加深入。其細致之處就在于,馬克思主義詮釋“實事求是”中的“求”,不僅強調其實踐的重要性,認為人不是一種被動的、動物式的適應,而人的實踐則“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一部分”,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全部活動、只有作為歷史的結果才有可能”,“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而且還強調其“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在馬克思看來,人不但屬于自然人,同時更是社會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其本質在于通過實踐活動實現自我完善。人的實踐活動,不僅是構成人的認識活動的基礎與條件,而且也是理解人的實踐活動本身的前提和條件的。為此,他基于實踐的作用而定義于人類的內涵,指出:“人類并非是簡單的生物個人,人類的形成縱貫著各種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才能唯物主義地分析實踐問題,并在此基礎上真正地解決理論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才鄭重地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只有這樣,才能使“感性的人”的實踐主體變成“理性的人”的實踐主體,使抽象的、形而上學的、片面的“哲學的實踐”轉向“實踐的哲學”,從而使我們從“感性的人的活動”角度去理解“主體實踐”,進而真正實現“對這個實踐的理解”,真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為什么“把他們所創立的辯證的、歷史的唯物主義簡稱為‘實踐的唯物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的根本的標志”為什么是“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去提出和回答‘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并“把‘實踐’作為回答全部哲學問題的邏輯起點和核心范疇”的道理。其深入之處就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中的“實事求是”中的“求”,不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而且也強調認識的重要性,特別是強調實踐與認識之間辯證關系的重要性。雖然“意識在任何時候只能是被意識到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但是,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文中所說的那樣,馬克思首先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同時又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馬克思的“理論”,都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都源于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理論回答。
(三)“實事求是”思想中的“是”與馬克思主義規律論中的“是”的相似性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還是馬克思主義的規律論,都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都認為規律是存在的,具有客觀性。對此,在《反杜林論》一文中,恩格斯指出,“有一種客觀地存在于事物和過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這是一種實際的力量”。這里所提到的“實際的力量”,即同規律或者真理一樣,是真實存在的。雖然“是”既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實際的力量”的實際作用卻既可以被真切地感受到,也可以被真實地感知到。而在《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恩格斯所論述的規律或真理的客觀性以及與實踐的關系一樣,也是真實存在的。因此,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哲學體系中所探尋的規律乃至于真理,與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實事求是”中所講的“是”具有相似性,但他們所探尋的真理和中國古代先賢們在“格物致知”和“即物窮理”中所探尋的“知”和“理”是有著不同的內涵,并比其更加深刻,即中國古代先賢們所探尋“知”和“理”的內涵一般都只是停留在最初的、現象的、片面的認識層面上,并沒有像馬克思、恩格斯所探尋的規律或真理那樣,通過實踐檢驗而被認為是正確的并已經上升到真理層面上。其深刻性就表現在:一方面,要認識到“實事求是”之中的“是”,即是說,相對于“實踐”而言,“認識”也不是或缺的。雖然“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但正如馬克思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所說的那樣,“哲學的實踐本身是理論的”。因而,“自我意識”業已成為馬克思早期實踐主體思想的重要原則。特別是在對待理論與實踐、物質力量與理論力量之間關系時,馬克思在闡述“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之時,也強調“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這就表明馬克思在此已經鄭重地強調了理論具有對實踐的指導功能。另一方面,要認識到“實事求是”之中“是”是否正確還必須在實踐中進行檢驗。“求”之不易,“是”得之亦不易。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也正如列寧所說的,“人的實踐經過千百萬次的重復,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來。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萬次的重復才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即是說,人之所以能夠認識客觀真理,是因為人通過不斷的實踐活動,將外在的客觀邏輯轉化為包含著這種客觀邏輯的、以人的主觀意識呈現出來的真理或真理觀,將這種隱藏在世界之中的客觀邏輯逐漸掌握起來,并在人的意識中確定下來,在人的認識上再現出來。
二、實事求是從品性層面提升到黨性層面的實踐維度
列寧曾經指出:“實踐比世界上所有理論爭論都更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也更加鮮明地指出:“我們黨是靠實事求是起家和興旺發展起來的。”那么,“實事求是”何以能行?據研究,其初始文本最早來源于《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傳》中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有注釋云:“‘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謂根據實證,求索真理。”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實事求是”的涵義遂逐步由初始代表著嚴謹、務實的治學品性,向“即物窮理”乃至“知行合一”的“修齊治平”方向演譯,并最終由經史考據論向社會實踐論的立場轉化。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在……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的”。可見,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一樣,并沒有用“實事求是”的思想去專門研究自然界的問題。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是一致的,并在此前提下,將中國共產黨人對“實事求是”理論層面的深刻理解應用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深度實踐層面,將中國古代先賢們對“實事求是”品性層面修煉提升到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層面修養。
(一)實事求是思想在確立之前的探索與實踐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新希望。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下,毛澤東堅持“古者為學,重在行事”的理念,堅持“閉門求學,其學無用”的觀點,堅持“引入實際研究事實和真理”的思想,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為上,他都自稱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爾后,他還深刻地認識到:“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從上觀之,可以說是青年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最初萌芽,并在這些思想與觀點的引導下,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己任,贊同以“俄式”道路推進對中國道路的改造。如:早在1919 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就寫道:“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從1925 年開始,毛澤東在撰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系列文章之后,又針對那些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等問題,在1927 年起草的《關于土地問題的七項決議草案》一文中給予了辯駁,并且指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此前,針對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性質和前途等一系列問題,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并初步提出了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敗之后,針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的問題,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強調,“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黨“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就是毛澤東提出的“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這句話后來被總結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此后,針對“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問題,毛澤東親自撰寫《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等系列文章,對不符客觀實際的“城市中心論”的錯誤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提出了將革命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向農村轉移的戰略決策,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并在井岡山地區創建了第一個紅色革命根據地。針對黨內存在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問題,毛澤東又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出“思想路線”的概念和馬克思主義“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等重要命題,作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而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即是“在實際經驗中”產生的,并批判了脫離中國具體實踐的教條主義錯誤,強調調查研究在革命斗爭中的重要地位。這篇文章,雖沒有明確談及“實事求是”,但通篇的闡述都體現了“實事求是”思想及其在實踐中的運用,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實事求是思想在確立之中的探索與實踐
遵義會議的召開,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運用“實事求是”思想獨立解決中國革命實踐問題的開始。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有目的地批判王明等人的“左”傾教條主義。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并吞東北”“吞并整個華北”、而且正準備“吞并全中國”并企圖“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之際,剛剛在陜北落腳不久的黨中央不失時機地組織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會上,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不僅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而且還提醒全黨記取歷史上發生過的實行統一戰線政策中的右傾錯誤的教訓。1937 年7—8 月,基于認識論、實踐論和規律論,毛澤東撰寫了著名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揭露了黨內錯誤的思想路線,批判了那些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條化等“左”、右傾錯誤思想,認為那些“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1938 年10 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報告并正式使用“實事求是”的概念,要求共產黨員“做實事求是的模范”。1940 年2 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第一次使用“實事求是”,指出對待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并提出中國的革命工作者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民族矛盾和革命問題。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在1941 年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中系統闡述了“實事求是”的基本內涵,并將其界定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從而概括得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的科學結論。接著他又分析指出黨內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還存在著兩種迥異的態度:一種是主觀主義的態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即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種態度,既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作風,也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他看來,“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的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而那種“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至此,毛澤東不僅把“實事求是”同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聯系了起來,而且還多次把“實事求是”提到是否具有黨性的高度來認識,認為“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如:毛澤東在《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一文中指出:“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毛澤東還歷數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提出“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必須反對空談馬克思主義”,“必須聯系中國的革命實際來研究馬克思主義”。隨著整風運動的不斷開展和深化,最終完成了以“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革命任務,從而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進而使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正式得到確立。至此,“實事求是”精神不再是單純的延安時期的精神。往前追溯,它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賡續著中國共產黨特有的紅色血脈和紅色基因,是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的繼承和發展;而往后展示,它以抗大精神、延安整風精神、南泥灣精神、張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和勞模精神等為原生形態,永放著光芒,不斷地煥發著恒久生命力,并持續體現在延安時期之后發展的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改革開放精神等諸多精神之中,其時代價值巨大而深遠。
(三)實事求是思想在確立之后的主要實踐
就中國革命而言,實事求思想路線的確立,使得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不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而且還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解放戰爭時期,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同“以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的大決戰時期,而且也是在中國究竟是“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還是使中國“繼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大決戰時期。在這一時期,鑒于兩種力量的角逐、兩種前途和兩種命運的抉擇,毛澤東不僅注意敵我軍隊在性質上的根本區別,而且十分注意敵我軍隊在數量方面上的懸殊對比,并在數量分析的基礎上,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制定出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并領導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僅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宣告了國民黨統治的覆滅,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其進展之快、影響之大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夠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
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而言,實事求思想路線的堅持,使得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瀕臨凋敝的國民經濟“起死回生”、迅速得到恢復,并且提升了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新中國成立以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就把中國革命勝利后所建立的社會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又指出了我國生產力落后的現實,并提出將“現代性的工業占10%左右”作為我國最基本的國情,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新中國初期,為反對急于求成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過渡時期”的經典理論,并結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在1952 年提出“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指導方針,在1953 年提出“總路線”的基本內容。顯然,這個“總路線”,在當時反映了中國由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行性,是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總路線,是“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總路線”。其實質,就是要使得“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使得中國這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使得馬克思、恩格斯在有生之年并沒有看到的“跨越卡夫丁峽谷”在中國轉變為現實。1956 年,由于蘇共二十大暴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又促使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最重要的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實行“第二次結合”,“找出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隨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又指出:“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然而,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最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遭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十年內亂”時期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
就中國改革開放而言,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使得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978 年12 月,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勝利召開。會上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樹立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權威,破除了“左”傾教條主義,并作出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世界謀大同”的革命初心,牢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時代使命,從“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出發,緊緊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的變革,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蘊含的實事求是思想,體現于新時代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生動實踐中,體現于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體現于新時代中國偉大的社會變革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這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
三、實事求是從道德層面提升到宗旨層面的價值維度
班固在《漢書》中所講的“實事求是”這句話為何能夠“一直流傳到現在”。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河間獻王劉德具有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據史料記載,劉德官位雖然不高,但他那種“實事求是”治學的態度、治學的方法和治學的精神,在當時還是得到了儒家學者的一致認同,故而“山東諸儒(多)從而游”。其詔策應對被認為是“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當朝大臣稱他為“明知深察”,朝廷譽其為“聰明睿知”。班固更稱他是“夫唯大雅,卓爾不群”。其影響之大,“深為學者所重”。顯然,在中國古代的先賢們那里,不僅把“實事求是”的精神發揚光大了,而且還遠遠超越了“實事求是”的初始內涵。既在哲學層面已經發展成為比較系統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又在道德層面業經發展成為儒家崇尚的“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既能“格物致知”,又能“經世致用”。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始形態,實事求是不僅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偉大結合,而且也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偉大結合。在這兩個“偉大結合”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將“實事求是”從哲學層面提升到思想層面而融入為黨的思想路線,從品性層面提升到黨性層面而融入為黨的政治路線,而且還將“實事求是”從道德層面提升到宗旨層面而融入為黨的群眾路線。這就充分地說明了“實事求是”不僅凸顯了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民本思想,而且也凸顯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本思想,凸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立場、價值主張和價值取向。因此,從價值維度來分析,“實事求是”不僅是實踐哲學,而且也是價值哲學。作為科學的價值觀,“實事求是”具有豐富的價值論內涵,也具有鮮明的價值取向,其過程就是實現價值的實踐過程。所謂“實事”,其所要解決的就是為誰“實事求是”的問題;所謂“求”,其所要代表的就是如何“求”的問題;而所謂“是”,其要所闡釋的就是“求”什么的問題。
(一)“實事求是”中的“實事”在價值層面體現著價值取向
從道德層面來看,南宋時期,湖湘學派張栻在《岳麓書院記》中強調,“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主張“知行并發”“知行并重”和“經世致用”等。明末清初時期,湖湘學派的另一位大家王夫子則注重把“天”“道”“心”和“性”奠定于“氣”“物”和“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礎上,發展出“天下惟器”“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的唯物自然觀,強調“言必征實、義必切理”,提出“即事窮理”的命題,創立了一個“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的思想體系,閃耀了實事求是精神的光輝。從哲學層面來看,相對于中國古代先賢們的“實事求是”,“實事”不僅是獨立于行為主體的客觀存在,而且也是具備行為主體對象性意義的客觀存在,并包含在與人的關系之中,即包含在與行為主體的認識、與行為主體的實踐和與行為主體的需要都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中。從實踐層面來看,“實事”——這一客觀存在并不是純客體的、純感性的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實際上是與人密切相關的,是實踐的客觀存在,都烙上了人的痕跡。即包含著客體的存在、主體的存在及以實踐為中介和基礎的主體與客體統一的客觀存在。因而對“實事”的理解,應該從行為主體的角度出發,從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出發,從人與“實事”的關系出發去理解。而不能把“實事”理解為與行為主體無關的、純客觀存在的客觀存在。也就是說,“實事”并不是遠離行為主體的實踐活動,或者是認識目的純粹客觀的事物,而是內藏著行為主體的對象性的客觀存在。由于“實事”固有的客觀復雜性,不論從個體的行為主體,或是群體的行為主體都無法對“實事”進行客觀而全面的認知與分析,只有將“實事”框定于一定范疇內,才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因此,從宗旨層面來看,所謂價值維度中的“實事”,就是與中國共產黨這一實踐的行為主體的需求或利益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實事”需要通過認識活動或實踐活動明晰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并以此探索“實事”中的“是”的所在。因為我們黨自創立之日起,就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始終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一邊。即只謀求“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勞苦大眾的利益”,而不謀求“自己的私利”,其唯一的任務就是“團結全體人民,奮不顧身地向前戰斗,推翻民族敵人,為民族與人民謀利益”。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關于“實事求是”的“實事”是中國人民的“實事”,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和幸福的“實事”,而不是個人的“私事”“家事”。因而,他們堅持以“人民群眾利益”為先、以“個人私利”為后的人民立場,以“人民的根本立場”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根本前提,堅持以“為人民謀解放”“為人民謀利益”和“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目的,堅持以“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并以“為人民服務”為歸宿,認同“實事求是”的活動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活動,認同“實事求是”的過程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
(二)“實事求是”中的“求”在價值層面體現著價值取向
從道德層面來看,“求”,就是指從事研究的活動,其中“從事研究”的行為主體,指的就是“實事求是”的行為主體,也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為主體。即是說,要做到“實事求是”,就是要增強行為主體“求”的自覺性,從敢于“求”轉變為善于“求”,從善于“求”轉變為工于“求”,以尋找自身道德品格的完善。顯然,“實事求是”的行為主體,不應當是抽象的人,而應該是具體的人,是處于各種復雜社會關系中的“現實的人”。就是說,一方面,“實事求是”中的“求”既表現為一個認識過程,是一個“現實的人”對客觀事物由“認識”到“再認識”的全部認識過程。因而,其行為主體要以其自身對于客觀事物的諸多價值標準、諸多價值觀念為依據,進而更加充分地蘊涵著其自身具有的價值意蘊。就中國共產黨而言,這個實踐的行為主體指的就是廣大的無產階級,就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其“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即要做好“求”,就需要以“實事”為基礎,勇于探索,勇于創新。而另一方面,“實事求是”中的“求”又表現為一個實踐過程,是一個“現實的人”對客觀事物由“實踐”到“再實踐”的全部實踐過程。即在這一全部的認識過程與實踐過程中,不是對客觀世界簡單地加以認識和了解、對客觀事物直觀地加以認識和觀察,而是要在全部認識過程與全部實踐過程的基礎上達到“認識”和“實踐”、“再認識”和“再實踐”的有機統一。那么究竟如何“求”呢?這不僅體現著“實事求是”價值追求的取向性問題,而且還體現著如何“求”的價值衡量的標準性問題。因此,從宗旨層面來看,所謂價值維度中的“求”,既不是盲目地、片面地甚至無意識地“求”,也不是形而上學式地甚至“走馬觀花”式地“求”,而是體現著價值追求,體現著價值標準。盡管在對不同“實事”進行“求”時可能會存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狀況,甚至在對同一“實事”或者同一“實事”的某一方面進行“求”的過程時可能會存在著只能看到那些感興趣的、具有利害關系的而不顧其余方面的狀況,但在對于不同的對象抑或是對于同一對象的不同方面所蘊含的規定性,即在確定先觀察哪個角度、后觀察哪個方面的選擇上,也會與各人的目的和需要等方面密切地聯系著。這就是在“求”的過程中所實現的“認識”和“實踐”、“再認識”和“再實踐”的有機統一。只有這樣,才能使“實事求是”的“求”在“求”的過程中離“是”更近。而且,也只有這種“求”,才會實現“實事求是”行為主體在價值層面上所追求的價值取向。
(三)“實事求是”中的“是”在價值層面體現著價值取向
研究表明,相對于“實事”與“求”來說,對于“是”的探索與研究則顯得比較單一。而真正取得突破性研究的則是毛澤東。在毛澤東那里,“是”,是在“實事”的基礎上“求”來的。也就是說,“實事”這一客觀存在是“求是”的最為基本的前提,而從“實事”出發,則是“求是”的最基本的要求。從道德層面來看,“實事”是與人相關的現實的、具體的客觀存在。所謂“是”,既是指事物客觀存在的、本質的、內在的、必然的聯系,也是指對客觀事物內部聯系的正確把握、正確的認識,即指規律或真理,但這一規律或真理,則不是人們先天帶來的,而是后天“求”到的。雖然人們對于“是”的追求是在其符合“實事”的基礎上對“實事”的正確認識與把握,但是實踐層面中的“是”卻并非僅僅是“實事”的運動、發展和變化的規律,而且還包括社會歷史發展規律。這種規律是“實事”行為主體在實踐過程中以客體運動規律為基礎的行為主體的實踐活動規律。在這一實踐活動過程中,人在客觀規律面前并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人們在實踐中,通過大量的外部現象,可以認識或發現客觀規律,并用這種認識指導實踐。在此,這就涉及到究竟“求”什么樣的“是”以及怎樣去“求”“是”的問題,進而明顯地涉及到“現實的人”“實際的力量”“社會關系的總和”等問題。因此,從宗旨層面來看,所謂價值維度中的“是”,是指在實踐活動中的“實際的人”的愿望、意志、需求等相關地蘊含著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即如何運用客觀規律或真理來指導和改造自然,指導和改造社會,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所體現在“實事”中的規律或真理,既是一個“實踐論”的問題,也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要解決“規律論”或“真理論”的問題,即“是”不會無緣無故或者說是自由自在地甚至先驗式地存在于人的頭腦之中,而是需要“實際的人”這一行為主體通過實踐活動并借助于“實際的力量”對感性認識進行升華,對理性認識進行檢驗,最終將感性認識轉化為理性認識,將理性認識轉化為真理認識或者規律認識,因而才有可能透過現象探索本質,從而實現對“是”的真理性把握與科學性認識。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通常將科學的“規律”稱之為“真理”的“是”,那就是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這就是說,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黨所代表的利益就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并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充分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客觀真理不僅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需要是一致的,而且還與黨所追求的價值尺度是一致的;而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所“求”的“是”并不是一般事物之間的一般發展規律,而是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發展過程中所“求”的特殊發展規律,即中國共產黨人不同于以往任何非無產階級政黨較為特殊的價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