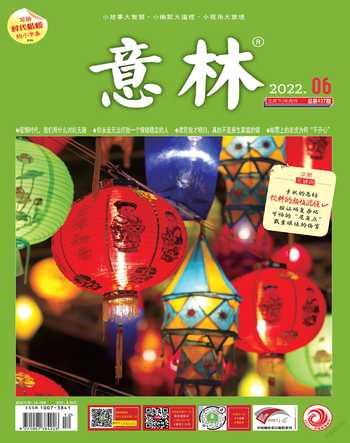趁著年輕,我偏要勉強(節選)
詹青云
辯論這件事,我曾一直以為只是我許多課余愛好中的一個, 卻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如果不是因為辯論,我不會對政治學產生興趣,以至于去讀博;我不會被隊友激勵,說我一定擅長挑別人邏輯漏洞的法學院考試,以至于做了律師;我不會認識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會參加《奇葩說》,以至于有機會寫了這本書。
這是不是說明,有些“無用”的愛好,堅持下去,也許就會改變人生呢?
我媽是個“文藝女中年”,做班主任,參加合唱比賽、校運動會、班會活動,甚至辦黑板報,樣樣都認真做,樣樣都爭第一。學校教職工歌唱比賽,我媽勇奪第一。我想,我媽一定很希望我承其風采,是個文藝細胞發達的孩子,可惜我截然相反。就連小學六一文藝會演集體舞蹈,這種以“大家都能參與”為導向的活動,在四十個孩子里選三十六個,我都能因為“動作實在不協調”而落選。長大以后,我媽跟我聊:“那么簡單的舞蹈動作,怎么就學不會呢?”我說:“那時候我連跳繩都學不會,何況跳舞?”不過我媽并不放棄,正視我的優缺點,開發了其他冷門些的文藝項目,比如說相聲、詩朗誦,組織智力競賽、話劇表演一類的班會活動。只要我表示有興趣,我媽一定鼎力支持,把我家客廳借給大伙排練,買好多純音樂光碟幫我們挑選詩朗誦的配樂,我們家甚至有一本關于出黑板報的書。我媽是這樣的人,積極參與生活,參與了就要認認真真、有模有樣,無論大事小事,理論先行,熱情實踐。大概我確實有些語言天賦,也因為其他有文藝細胞的同學都不怎么在這個領域競爭,我竟然另辟蹊徑,一直穩定地做著班上的文娛委員。

我媽也很喜歡辯論,應該是因為那兩年沉迷于風靡一時的國際大專辯論賽,覺得唇舌之間揮斥方遒,風流瀟灑,有為青年正該如此。她帶的高中班,進了學校辯論賽的決賽,她很是開心。我那時候才上三四年級,作為教師子女,被悄悄帶到禮堂去看。臺上一名辯手是我表姐,另一個是她的緋聞男友,我似懂非懂,笑吟吟地盯著他們看,也不大明白其他人說了些什么。那題目是關于學習方法的,突然,對方一位辯手問我表姐:“你說什么什么方法有用,那請問你是你們班學習最好的人嗎?”
我大吃一驚,只見我表姐站起來冷冷地說:“這個問題與本場辯論無關,我有權不回答你。”一時掌聲如雷。這句話我記憶至今,當時心中一定滿是艷羨,心想,如果有一天我參加了辯論賽,也在場上抓住機會,大氣磅礴地說出這句話來,一定帥氣極了!想不到,過去十年打了那么多場辯論賽,我還沒能找到機會說出這句話。
這大概是我對辯論的第一印象,最重要的是姿態,要凜然又冷硬。在我當時的認知里,最好的辯手是藺相如和諸葛亮,最好的辯詞是唐雎對威脅要殺了他的秦王說“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好像我的確永遠也走不出那種對英雄氣概無限向往,有時候會被批評為用力過猛的辯論風格。
小時候我媽買了不少國際大專辯論賽的光碟,她自己比我看得起勁。后來我進了大學辯論隊,好多隊友都因為家里人反對他們浪費時間在辯論上、耽誤學習而和爸媽冷戰。我就不同了,我穿上黑西裝站到辯論場上的那一刻,想必我媽會想起她那些年看過的光碟,老淚縱橫,沒想到別人家的孩子就在身邊。我媽(以及我爸)傾力支持我參加辯論。每次外出比賽,他們跨山跨海到現場來給我們加油。有一年回貴陽比賽,電視臺采訪他們,我媽百感交集,說不出話來,倒是我爸侃侃而談。
我外公有一次看新聞,正好看到我們在香港奪冠的報道,全家人高興了好一陣子。我外公更是得意非凡,說幸虧他堅持看新聞頻道,比我外婆整天看電視劇高明太多。每次贏了獎杯、獎牌,我都直接送給前去觀戰的爸媽,很像小時候我爸參加工廠的游泳比賽,我組織同學去給他加油,他拿到八十塊錢獎金,立刻送給我們去吃火鍋了,皆大歡喜。后來回家,發現我一個“最佳辯手”的獎杯,被我媽用來代替她的小錘子,敲核桃吃。雖然感覺怪怪的,但我媽連說“這獎杯不錯,重量正好”,就覺得也算終于送了我媽一樣實在禮物,挺開心的。
辯論給我這樣平凡的少年帶來恍惚英雄夢的瞬間,何況還是衣錦還鄉、舉家歡慶,獨樂樂后眾樂樂,實在是夫復何求。雖然我媽傾力支持我搞過的活動還有許多,但大多草草收場,只有這條路我一直走了下來,是因為我在這個愛好里感受過實在的快樂,也滿足過小小的虛榮心。
可是當眾辯論,屬于“正面硬剛”,是需要些勇氣的。我第一次辯論是在初中歷史課上,學到了安史之亂,老師讓辯論“楊貴妃是不是該為唐朝走向衰落負責”。我到現在還有些無法相信這題目真是這樣問的,而在我之前發言的大部分同學都覺得“該”。我那時候頭腦中沒有什么理論武裝,想法樸素而簡單,只覺得一股怒火在腦海中爆裂開來,一句話如鯁在喉,竟然是“小女子何德何能”。一個為君王寵幸的女子,在那樣的時代,講兵制變革不會有她,講以胡制胡不會有她,講民族關系不會有她,講兼并、講貿易、講科舉、講王侯將相和百代功業,講那個時代重要的一切,樣樣都沒有她,一講到盛世衰頹、大廈將傾了,歷史突然就化作“紅顏禍水”這么簡單的四個字了。她被當作背鍋的棋子賜死,千百年了,對方辯友還要她背這鍋,氣死我了。
那是打辯論時最真誠的一種狀態,一種原始的不服和不甘,一種想要吶喊的樸素欲望。后來的辯論被這樣的憤怒點燃的次數并不多,它們也都不是我發揮得最好的比賽。被持續加班磨平了的時候,我懷念那種感覺,那是在表達樸實的快樂。 (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