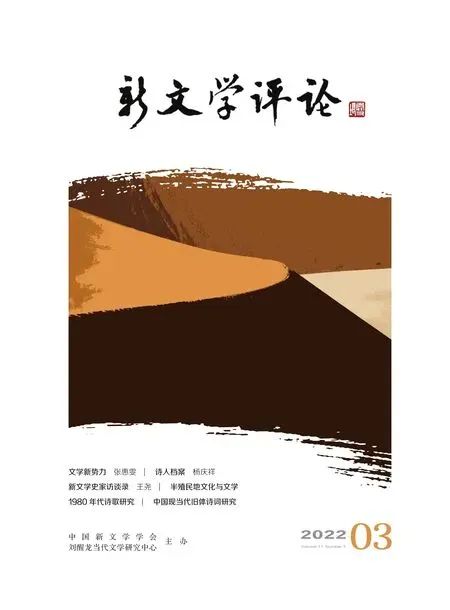20世紀80年代詩壇的喧嘩與騷動
□ 呂周聚
20世紀80年代可謂詩的年代,先是以北島、舒婷、顧城等為代表的朦朧詩人浮出地表,從地下登上公開的文壇,引發了一場長達數年的關于“懂”與“不懂”的論爭;后是以韓東、周倫佑、尚仲敏、于堅等為代表的第三代詩人以群體的方式登上文壇,上百個詩歌團體在《深圳青年報》和安徽《詩歌報》上公開亮相①,以陌生的面孔和另類的聲音引起文壇的關注。這兩個詩潮規模龐大,它們于1986年疊合一起,如同兩個巨浪相撞在一起,頓時浪花四濺,濤聲震天,形成了20世紀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非常獨特的詩歌事件。20世紀80年代已成為遙遠的過去,站在今天的角度來回望當年頗為壯觀的詩壇,曾經那么多的詩歌團體和詩人在經歷了時間大浪的淘洗之后,留下了哪幾個具有生命活力的詩歌團體?還剩下多少仍在堅持自己詩歌觀念的詩人?他們創作出了哪些作品?他們給后人留下了哪些有價值的東西?如果從這個角度考察20世紀80年代詩壇,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失望,大部分的詩歌團體不見了蹤影,大部分的詩人中途失散,真正能夠堅持下來的屈指可數,而堪稱經典的詩人和作品則更是寥若晨星。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輕視20世紀80年代的詩壇,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的詩壇給文壇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喧嘩與騷動。
在許多人看來,喧嘩與騷動是一種混亂與無序,何以會成為一種文化遺產?因為表面上的混亂與無序蘊藏著無限可能,“嘈雜的、無序的、喧囂的、閃色的、帶虎紋的、有條紋的、雜色的繁多,五色繽紛,斑駁陸離,它就是可能性。它是一組可能的事物,也可以是一切可能的事物的總體”②。塞爾認為混亂是積極的,斯賓諾莎則認為確定性即否定,不確定性即肯定,“混雜沒有被排除,被擯棄,而是成為客體,進入認識領域,進入認識的演變過程。可是相反的,只有分類是否定的,從否定方面運作的是編碼,這就是一般的概念,這就是確定性,也就是否定”③。混亂意味著不確定性、開放性和可能性,它充滿了生命活力,給人以無限的遐想與期待,詩人們不再靠誰的指導來進行創作,他們自己播種,自己收獲,可能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也可能播種的是跳蚤,卻意外收獲了一兩個龍種。這是一種真正的詩歌精神,有了這種精神,詩人們便陷入了迷狂狀態,整個文壇都沉浸在這種氛圍之中,詩歌、詩人受到應有的尊重,詩人們獲得了創作自由,這與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精神是相一致的。
一
20世紀80年代詩壇的喧嘩與騷動的實質是一種反叛精神。無論是朦朧詩人,還是第三代詩人,都以反叛為旨歸,當然,他們反叛的對象有所不同。朦朧詩人反叛其前輩的詩歌傳統,而第三代詩人反叛的則是朦朧詩人。由此觀之,20世紀80年代的詩壇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反叛精神,這些反叛的聲音匯集在一起,形成一種集體的喧嘩與騷動。
朦朧詩剛出現在文壇時,被譽為新的崛起,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很好地概括出了朦朧詩與傳統詩歌之間的差異。實際上今天來看,朦朧詩人所反叛的傳統主要是其前輩們所熱衷的空洞泛濫的政治抒情詩,帶有深刻的時代痕跡。1972年舒婷以獨生子女的身份回城,沒有被安排工作,產生一種擱淺的感覺,不被社會接受,不被人們理解,處于冷窖之中。她在感到“沉淪的痛苦”的同時,也感覺“覺醒的歡欣”,這種覺醒,“是對傳統觀念產生懷疑和挑戰心理。要求生活恢復本來面目。不要告訴我這樣做,而讓我想想為什么和我要怎樣做。讓我們能選擇,能感覺到自己也在為歷史、為民族負責任”④。北島的《回答》中塑造了一個反叛者的形象:“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被判決了的聲音://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這不是北島一個人的聲音,而是一代人反叛的聲音。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一代人》),同樣表現出一代人的反叛精神。可以說,反叛成為朦朧詩人的精神特質,成為朦朧詩的一個重要思想主題。
第三代詩剛登上文壇,便打出了反叛朦朧詩的旗號。1984年底到1985年初,以尚仲敏為代表的大學生詩派在重慶成立,他們宣布:“當朦朧詩以咄咄逼人之勢覆蓋中國詩壇的時候,搗碎這一切!——這便是它動用的全部手段。它的目的也不過如此:搗碎!打破!砸爛!它絕不負責收拾破裂后的局面。”⑤1985年3月7日,《他們》第一輯印出來,相對于當時的主流詩壇而言,“他者”是一個異己,表現出一種異質特征(思想、藝術),隨后韓東發表的《致大海》《有關大雁塔》,便是對舒婷的《致大海》和楊煉的《大雁塔》的仿寫。從這種帶有反諷意味的仿寫之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已背離朦朧詩傳統,越走越遠。以周倫佑為代表的非非主義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反叛意識,他們反叛的不僅僅是朦朧詩,而是整個的傳統文化。1983年秋周倫佑、廖亦武、黎正光在“四川省青年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對正統文學觀念公開挑戰,他們提倡“狼性文學”,即“原始的,本能的,沒有被馴化的生命意識的自由表達”⑥。以周倫佑為首的四川詩人提倡“非非主義”,創辦《非非》刊物。“非非”是何意思?周倫佑認為:“如果仔細追溯起來,即隱含于我在這篇文章中首次寫下的‘非崇高’‘非理性’中的兩‘非’字。”⑦對于第三代詩人來說,反叛既是一種詩學觀念,又是一種詩歌策略。
盡管朦朧詩人和第三代詩人反叛的傳統不盡相同,但他們對傳統的反叛導致詩壇出現了混亂和無序:傳統的詩歌觀念被顛覆,不同的詩歌團體提出自己的詩歌理論主張,詩壇呈現出空前的喧嘩與騷動。我們應如何看待這種混亂和無序?這種混亂與無序意味著詩歌的新生與繁榮,“我們應當把混亂的概念引進哲學范疇,直到目前這個概念還如同神話一樣,受到理性的蔑視,現在只有說到妄言妄語時才使用這個概念”⑧。依靠混亂與無序,詩人們打破了封閉已久的詩歌系統,“混亂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系統,它半開著。為了編碼,必須閉合起來;為了分類,必須加以確定,或是劃定界限。混亂是不容置疑的,它不是一種系統,而是繁多性。它是繁多的,出乎意料的”⑨。不同的詩歌團體各有自己的詩歌主張和詩學宣言,詩人們破壞已有的詩歌分類標準,試圖建構新的分類標準。他們拒絕按照已有的概念、標準對詩歌進行分門別類,不接受已有的所謂詩歌界限和秩序,他們將混亂、差異感性作為自己的創作追求,以此對禁錮的理性進行沖擊與毀壞。
20世紀80年代詩壇的這種反叛精神對后來者產生了重要影響,已經作為一種傳統或詩歌遺產傳承下來。進入21世紀之后,以沈浩波為代表的70后詩人以更加激進的態度反對傳統:他們不僅反對以唐詩宋詞為代表的中國詩歌傳統,而且反對以葉芝、艾略特、里爾克、瓦雷里、帕斯捷爾納克等為代表的西方詩歌傳統;他們反對詩意,反對抒情,反對思想,反對大師,反對經典,反對“上半身寫作”,提倡“下半身寫作”。他們的這種主張及姿態,對21世紀初的詩壇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
在詩壇大一統的時代,由獲得權力的人們給詩歌設置嚴格的標準、秩序和界限,這無形中給那些想走上詩壇之路的人們設置了重重障礙:“嚴明的編輯、選拔,嚴明的單一發表標準,大詩人小詩人名詩人關系詩人……什么中央省市地縣刊物等級云云雜雜,把藝術平等競爭的圣殿搞得森森有秩、固若金湯。”⑩在這種限制之下,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登上詩歌的殿堂,這些詩人由此而獲得一種特殊的榮耀與權力,并因此而具有了崇高與神圣之感。單一化的詩歌觀念和標準在無形中扼殺了詩人的創新能力,偌大的詩壇只有一種聲音、一種顏色。朦朧詩和第三代詩反叛傳統,詩壇趨于開放,詩人們呼朋喚友,形成一個個詩歌圈子,自己創辦民間刊物,自己給自己當編輯,自己給自己制定多樣化的標準,甚至自己給自己頒獎。這賦予每個人都可以當詩人的權力,從而降低了詩歌入門的標準,詩歌呈現出一種多元化、世俗化的傾向。
詩歌世俗化,表現為一些在正統眼里根本不具備當詩人資格的凡人開始成為詩人。朦朧詩人大多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寫詩,當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下鄉知青,身處一種失重的狀態,與主流文壇處于脫節狀態。他們以身處的鄉村為據點,形成了一個個詩歌團體,且這些團體并非封閉的,而是敞開的,是互相流動的,其中最有名的是白洋淀詩歌群。當年白洋淀聚集了一批來自北京的下鄉知青,每個村的知青基本上是以在北京中學學校為單位的組合,他們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經常聚在一起交流學習體會、書籍、詩稿,切磋詩歌理論和寫作技巧。除了白洋淀的知青之外,還有許多外地的同學朋友到白洋淀來進行詩歌交流,他們從遠處帶來自己手抄的詩稿,還帶來了一些內部出版的書籍。圍繞白洋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詩人群體,其中包括林莽、江河、栗世征、方含、根子、芒克、北島等人。他們大多都有流浪的經歷,而這些經歷給他們的詩歌創作帶來了豐富的經驗與題材。他們的詩歌寫作、交流處于地下狀態,他們寫作的詩歌不符合當時主流文壇的標準,根本無法公開發表,且隨時可能引來意外之禍。后來這些人逐漸返回北京,回京后經常在一起聚會交流詩歌,他們醞釀辦一個刊物,北島、芒克、劉禹、張鵬志等七人組成編輯部,大家每人給刊物起一個名字,芒克提議的“今天”得到大家的認可。1978年12月《今天》第一期出刊,被譽為1949年以來第一家民辦刊物。刊物印出后,北島、芒克等騎著自行車到西單、天安門、王府井、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化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張貼,將裝訂好的第一期1000冊散發出去,后來又加印了1500冊。到第二期出刊時便開始征求訂戶,這說明《今天》已經在社會上產生了影響,有了自己的讀者群,這在當時的年代堪稱奇跡。圍繞《今天》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詩人群體。到1980年9月《今天》停刊,共出了9期。盡管《今天》存在的時間有限,但它開啟了詩人創辦民間刊物的先河,為后來的詩人們開拓出了一條新的詩路。
與朦朧詩人不同,第三代詩人大多是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在校大學生。他們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在校園里組織詩歌團體,創辦刊物,于是在當時的大學校園里,詩歌團體、詩歌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如尚仲敏等人的《大學生詩報》、韓東等人的《他們》等。這些人以詩會友,居住一地的詩人們經常聚會,朗讀詩歌作品,交流詩歌寫作經驗;他們也通過郵寄自己創辦的刊物與異地的詩友進行詩歌交流;除此之外,他們還通過串聯的方式,走親訪友。據小海記述,他當年在南京大學讀書時,西安的島子,上海的孟浪、郁郁、冰釋之,北京的唐曉渡、老木、馬高明,四川的雨田等先后造訪南京的韓東、小海等人;韓東、小海、賀奕等到西安、九寨溝、成都、重慶等地游歷,在成都他們見到了楊黎、萬夏、馬松、石光華、宋氏兄弟等。在寬敞的教室里,在昏暗的茶館里,在嘈雜的飯館里,到處都能見到詩人們的身影——他們手里拿著油印的小冊子,如打了雞血般在狂熱地討論詩歌問題,聲情并茂地朗讀自己的作品。盡管他們在物質上并不富裕,有的詩人甚至要靠賣血籌錢來印刷自己的作品,但他們在精神上是富足的。在那個年代,整個詩壇處于狂歡狀態,寫作詩歌,當個詩人,是一件令人非常羨慕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以北島為代表的朦朧詩人身上刻下了時代的印記,盡管他們的作品中帶有英雄情結,表現出一種崇高化的審美風格,但他們的作品中已經露出了世俗化的端倪,北島宣稱,“我并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北島:《宣告——獻給遇羅克》);舒婷宣示,“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舒婷:《神女峰》)。到了第三代詩人這兒,這種世俗化的傾向更加強烈,他們以“反崇高”“反英雄”“反文化”為追求,詩歌觀念和詩歌風格發生了巨變。徐敬亞認為,朦朧詩把詩寫得充滿人文美,這非常了不起,因此要使它成為起點就很難辦:“把極端的事物推向極端的辦法就是從另一個角度反對它。崇高和莊嚴必須用非崇高和非莊嚴來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為后崛起詩群的兩大標志。”“‘反英雄化’是對包括英雄(人造上帝)在內的上帝體系的反動,是現代人自尊自重平民意識的上升,是把興奮矛頭最后指向人本身的一種必然結果。”這與20世紀80年代的“反神化”運動相一致,“反神化”脫去了神圣的外衣,恢復了人的本來面目。
如果說朦朧詩人開始走下神壇步入民間,那么第三代詩人則徹底地流入民間,其結果是詩歌日常生活化,或者說日常生活成了詩歌。第三代詩人的詩歌觀念趨于開放狀態,誰都可以是詩人,什么都可以入詩,什么都可以是詩,詩人們不再是頭上發光的圣徒,而是有著七情六欲的世俗凡人,詩人成了“腰間掛著詩篇的豪豬”(李亞偉)。他們以口語入詩,抒寫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甚至個人的隱私,詩歌成了一種波普藝術。生活即詩歌,這隱含著另一個結論,即人人都是詩人,或者說人人都是潛在的詩人。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一批沒有詩歌才能的人成了詩人,人們喪失了對詩歌藝術的判斷力與辨別力,好的詩歌與拙劣的詩歌的界限沒有了。“作為當代中國前衛藝術的傾心者和介入者,有相當數量年輕的詩作者,因其心智上的不成熟不夠強健,因其藝術素質的貧弱和藝術精神的匱乏,暴露了詩學上的嚴重缺陷(甚至無知),其作品令人難以在藝術上給予必要的肯定。”這是詩歌世俗化、狂歡化必然會帶來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詩歌的世俗化傾向,在后來的詩歌尤其是網絡詩歌中得到了繼承與發展。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詩人們申請創辦詩歌網站,圍繞著這些詩歌網站聚集著成千上萬的詩人,他們在虛擬世界里狂歡,一個人扮演著詩人、編輯、主編、讀者、評論家的多重角色,真正實現了“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下半身寫作”成了他們展示的風景,甚至有人提倡“垃圾派”寫作,詩歌成了俗不可耐的東西。
三
詩壇的喧嘩與騷動形成一種怪異的氛圍,詩人在這種氛圍中容易進入一種迷狂狀態。這時詩人往往會摘掉其理性的面具,暴露出其本真的面目,其主體意識和個性意識得到彰顯,而個性意識與創新意識又密切相關,這也就意味著詩歌的喧嘩與騷動與創新意識發生了關聯。
20世紀80年代,朦朧詩人和第三代詩人以異端的姿態登上文壇,在許多正統的眼里,他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怪異性,“‘怪異性’不是傳統想象中的‘奇異力量’或者是奇事怪物,而是一個空洞的空間、一個間隙式的空地、一個狹小的距離”。怪異性本身具有特殊意義,它是以分類的形式對分類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質疑和解構。類與類之間的差異取決于其某一方面的不同,由此觀之,怪異性既是朦朧詩與第三代詩的共同特點,又是它們之間的差異性特點。
朦朧詩人與其前輩詩人的重要區別,在于他們的自我意識覺醒了。北島聲稱:“詩人應該通過作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這是一個真誠而獨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義和人性的世界。”顧城認為,我們過去的文藝、詩,一直在宣傳一種非我的“我”,即自我取消、自我毀滅的“我”,現代味的新詩之所以新,是因為它出現了“自我”,出現了具有現代青年特點的“自我”,新的“自我”,“他打碎了迫使他異化的模殼,在并沒有多少花香的風中伸展著自己的軀體。他相信自己的傷疤,相信自己的大腦和神經,相信自己應作自己的主人走來走去。”由此出發,他們有意識地張揚自我,標新立異,即便是聲稱要尊重傳統的楊煉,也強調“詩歌傳統的秩序應該在充分具有創新意義的作品有機加入后獲得調整”。“詩人的一生,應當是自我更新的一生,既不怕打破舊有的平衡,又不斷追求在更高水平上的新的平衡。‘批判精神’是汲取的前提,‘自我更新’是創造的必然。不斷更替的充實和空虛,蘊藏著詩人成長的全部奧秘!”這種清醒的自我意識使朦朧詩形成一些群體特點,同時又賦予朦朧詩人以個性差異。
第三代詩人身上表現出一種弒父情結,他們以群體的形式對以北島等人為代表的朦朧詩進行反叛與顛覆。由于第三代詩是以詩歌團體的形式出現在讀者面前的,因此許多人認為第三代詩人的共性大于個性,實際上并非如此。我們應該看到,在第三代詩人那里,存在著相似性與差異性的矛盾。我們必須承認,第三代詩人的創作的確存在著一種同質化現象,為何會出現這一現象?李德武認為:“這其中的問題很多,但根本問題是詩人缺乏對自我氣質的辨認(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我是誰’的問題。‘我是誰’辨認的是主體在和不在,而氣質辨認的是如何獨立存在)。表面上看,詩人都是獨立的,實際上,無論作為社會群體,還是作為閱讀影響下的人,詩人都帶有無法擺脫的共性特征。”因此,他認為當代詩歌緊迫的問題是解決語言生長的問題。與朦朧詩人強調自我意識的差異不同,第三代詩人從語言的角度切入來探討詩人的個性差異。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詩人與詩人之間的距離就是語言和書面的距離,這種距離便是不同詩歌團體乃至同一詩歌團體內部詩人之間的個性差異。《他們》第五期的封二上刊發了韓東的刊首語《為〈他們〉而寫作》,“排除了其他目的以后,詩歌可以成為一個目的嗎?如果可以,也是包含在產生它的方式之中的……《他們》不是一個文學流派,僅是一種寫作可能。《他們》即是一個象征。在目前的中國,它是唯一的、純粹的,被吸引的只是那些對寫詩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這就涉及個體與群體(團體)的關系,“其實,像‘他們’的這個‘他’包含了一個藝術上‘他者’的意味,‘們’并不意味著簡單的歸類和抽象。他們中每個人都代表了他們,是在承認個體差異基礎上個體可以自我實現的團體,‘他們’的共同性和彼此之間可以印證的趣味,并不代表同一和彼此的混淆,‘他們’成員之間有不同個人氣質、趣味的差異,也會時常發生一些爭執、交鋒和撞擊,即使偶爾詩人脾氣發作時的彼此攻訐和意氣使然的謾罵,也是藝術理想、風格追求和個人氣質的迥異帶來的磨合與不適造成的,其實原因也很簡單。‘他們’這個團體的集體性只在每個個人中得到體現,但團體絕不取消個體,團體精神在其中只體現在藝術的無限可能性中,即是烏托邦意義上的。這個‘他者’和個體的‘我’區別性地共存著,就因為這個‘們’代表的是自由和無限。‘他們’這個群體也是在暴戾之氣盛行的特定歷史大背景中逐漸成長起來的,這是藝術的大環境決定了個體成員要承受得起這份‘磨礪’”。這是“他們”詩歌團體的特點,也是其他第三代詩歌團體的共同特點。
20世紀80年代的詩壇,圍繞著朦朧詩展開了長達數年的論爭,在一夜之間冒出了上百個詩歌團體,這是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它打破了長期以來一花獨放的局面,符合文學創作的發展規律。這種混亂與無序就是不確定性和可能性,意味著個性與創新,意味著詩歌可以有無數條路可以走,詩壇因此而獲得了無限多樣性。這種喧嘩與騷動對后來的詩人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網絡詩歌又加劇了這種混亂與無序。20世紀末乃至21世紀的詩歌基本上還在按照“現代詩群體大展”所開拓的混亂路子往前走,中間曾試圖有人來給詩壇以界限和秩序,如20世紀90年代的盤峰論戰,但并沒有產生實際的作用,詩壇基本依然處于無序狀態。混亂與無序是詩歌創新與發展的必要條件,或者說混亂與無序是一種新的“秩序”狀態:“這里的無序,我指的是,大量可能的秩序的片段都在不規則事物(l’hétéroclite)之毫無規律的和不具幾何學的維度中閃爍。”實際上,詩歌發展本身就是混亂和無序的,所謂的秩序都是后人賦予它的,“秩序只是暫時的、變動的和局部的,在科學的意義上,也不存在不變、同一、永久和全部的秩序”。這就是詩歌發展的“常”與“變”,“詩這東西的長處就在它有無限度的彈性,變得出無窮的花樣,裝得進無限的內容,只有固執與狹隘才是詩的致命傷,縱沒有時代的威脅,它也難立足”。
混亂與無序會給詩人提供一種巨大的能量,賦予詩人一種開放的、無止境的探索精神。它是一種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20世紀80年代詩壇出現的喧嘩與騷動與當時的改革開放精神是相一致的,改革就是打破原來的穩定性、確定性、封閉性、單一性系統,使之趨向動態性、不確定性、開放性和多元性,“變革的影響就是繁多的影響”,“繁多性到處都引起事物的變化”。繁多就是多元化,就是混亂,就是開放。“繁多在傳播中飄忽不定,如同結構在網絡中非常廣闊一樣,即在無數的起伏波動上有很長跨度的結構。這個純粹的繁多就是秩序的基礎,但是,我認為它也是秩序的起始,或者至少是它的潛在性意義上的力量。可能只有在推動、移動的力量之下,通過繁多的起伏不定,才有真正的影響。這是處于等待中的許多情況,它們在虛無中消失,或者是在把它們遺忘的秩序中消失。”
20世紀80年代詩壇的喧嘩與騷動已經沉靜下來,已經成為歷史,將作為一種壯觀的詩歌現象載入史冊。在這場喧嘩與騷動中,詩人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聲音或高或低,或長或短,或響亮或嘶啞,或高亢或低沉,每個聲音都迥然不同,每一個聲音都有自己的特殊內涵,彰顯出每個詩人的個性特質;詩人們的狂歡流浪行為呈現出其躁動不安的內心世界,表現出詩人對詩歌的滿腔熱情。喧嘩與騷動是每個詩人的本能,也是每個詩人的使命。喧嘩與騷動打破了封閉一統的詩壇局面,詩壇從此趨于開放,從“一”走向“繁多”,蘊藏著無限可能與生機。
注釋:
①由徐敬亞等編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第一、二編收入68個詩群,第三編收入西北區詩人8人,華北區詩人11人,華東區詩人19人,東北區詩人5人,西南區詩人12人,中南區詩人13人。
②米歇爾·塞爾著,蔡鴻濱譯:《萬物本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頁。
③米歇爾·塞爾著,蔡鴻濱譯:《萬物本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頁。
④舒婷:《生活、書籍與詩——兼答讀者來信》,老木編:《青年詩人談詩》,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1985年刊印,第9頁。
⑤《大學生詩派宣言》,徐敬亞等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頁。
⑥周倫佑:《異端之美的呈現》,周倫佑選編:《打開肉體之門——非非主義:從理論到作品》,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⑦周倫佑:《異端之美的呈現》,周倫佑選編:《打開肉體之門——非非主義:從理論到作品》,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⑧米歇爾·塞爾著,蔡鴻濱譯:《萬物本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頁。
⑨米歇爾·塞爾著,蔡鴻濱譯:《萬物本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頁。
⑩徐敬亞:《歷史將收割一切》,徐敬亞等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