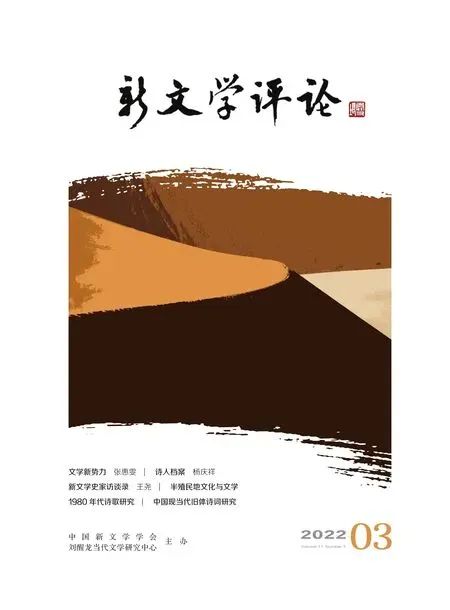半殖民文化語境下的服飾、性別與民族
——旗袍與1930年代留日女學生的身份政治
□ 張惠娟
至1920年代末期,在有關留日學生的文學書寫中,知識分子作為弱國子民的身份“焦慮感、悲怯感和不確定性”①明顯減弱,文化立場和民族身份認同向本民族回歸,他們通常以一種平視的姿態去觀賞和體驗東洋文明。與此同時,日本侵華帶來的民族危機又讓身處戰爭策源地的留日學生,在精神上、心理上遭受著殖民文化的侵襲與裹挾,身份體驗更為敏感、復雜和深刻,留日學生的形象塑造、文化身份建構和民族情感表達呈現出新的樣態。相比于清末和1920年代,1930年代的留日學生生活書寫和形象塑造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在國族敘事和殖民敘事之間嵌入了性別因素,給予留日女學生獨特的觀照。
只關注清末和1920年代留日男學生的生活書寫和形象塑造,難以觸摸不同歷史語境中留日學生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現實,概覽現代留日學生群體的全貌。在這個意義上,留日女學生的生活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在現代中國作家筆下,留日男學生和留日女學生的著裝表現出明顯的區分:留日男學生的著裝以日本的學生裝和洋裝為主,著重呈現的是日本衣服與中國身體之間的緊張關系;留日女學生的著裝以旗袍和洋裝為主。這些都決定了留日女學生文化身份建構的路徑、方法與留日男學生迥異,服飾的敘事功能也必然有所區別。日本的女學生裝就是西式的洋裝。在留日女學生身上,洋裝不再是帶來文化沖突的主要因素,文化身份問題的復雜性主要由旗袍來完成。1930年代流行于中國的旗袍是中國女性大眾與國民政府建構民族國家中心意識相互協商的產物。隨著留日女學生的身體“越境”進入日本的文化空間,旗袍牽動的是中國衣服、中國身體與日本文化空間之間的對抗。旗袍和洋裝不僅表現了留日女學生對自我民族身份的體認,還參與調配了男留學生的民族文化認同、民族情感和審美心理。另外,留日女學生生活的書寫和形象塑造與男留學生構成了對照與互補,提供了性別視野中的留學生形象。考察這一特殊現象,能夠讓我們窺探到現代知識分子留日生活的堂奧,觸摸到1930年代中日戰爭語境中知識分子民族身份的特殊形態。
服飾是“人的第二皮膚”②,不同種族之間,民族身份首先是以膚色來區分,在同一膚色的不同種族之間,服飾是區分我族與他族的視覺“符碼”。旗袍是1930年代留日女學生區別于日本女學生的重要標志。但在歷史現實和文學書寫中中日女學生的服裝并非是那么涇渭分明的,留日女學生也有穿洋裝的習慣,加上男性審美視角的參與,留日女學生的身份問題在旗袍與洋裝之間也變得更加曖昧。旗袍與洋裝都是時尚虛擬鏈條上不同的幾何形狀,二者在中國女留學生身上的互換和分布(個體選擇偏好的差異),“指向一種力量的匯集、沖突與布置”,這種力量是性別之力、速度之力、戰爭之力、殖民之力、都會之力、摩登之力等復數力量③。
一、承認的政治:旗袍的時尚衍化與“旗袍—中國”話語象征的形成
民國時期流行的旗袍脫胎于清朝的“旗裝女衣”④,與男性的直筒長衫、五四時期的“文明”新裝、20世紀20年代的西式長裙有著密切的關聯,聯系著民國初年的社會生態和女性的身體、精神世界。民國時期女性穿旗袍不同于清兵入關時“男降女不降”的文化現象,是清朝覆滅、民國建立這一社會生態的結構性變動背景下中國女性的集體文化選擇,體現著推翻帝制,締造共和的政治變革給予民國女性實際生活的意義。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對一切舊制做了徹底清掃,旗袍在辛亥革命以后幾乎銷聲匿跡。1920年前后,在“文明”新裝高調宣揚文明、進步、民主、自由之時,旗袍卻在上海女性身上悄然復活,由老大帝國的遺物搖身變為滬上女子的新寵⑤。旗袍在俏女、徐娘身上重新綻放時,也招來了維新與復辟的聲討。但是從隱匿到現身,旗袍引發的喧嘩與騷動不止于歷史線條上的反常,它的突現也帶來了文化身份上的結構性變化。西化的穿著搭配、從妓女到婦女大眾的流行路徑,以及與男式長袍相似的視覺觀感等都將旗袍嵌入了新的表達方式與配置關系之中,使旗袍具有了新與舊、中與西、男與女、良家與妓女等二元混合的文化特征。朱鴛雛寫作的小調《旗袍》⑥可謂是對這種變化最為敏銳的觀察,首當其沖的就是性別的“出線”:“玉顏大腳其仙乎?拖了袍兒掩了襦。婆婆年老眼模糊,笑姑姑一半兒男一半兒女。”放了腳的女子穿著前拖后掩的一截式旗袍,形象酷似青年男子,造成了女著男裝的視覺混淆。在一個穿長袍是男子的專屬形象的社會里,女子對旗袍熱衷的意義就越過了出風頭的內心沖動,演變為一種由分化走向統合的性別政治。時裝“也是女性表達自我的方式之一”⑦。旗袍被突然翻牌,一反常態地風靡開來,其實是女性在利用旗袍直筒一截的形式特征,回應和對抗流行的“文明”新裝,以尋求改善上下兩截的穿衣傳統,從而獲得與男性共享一截穿衣的權力。可以說,“性別革命的質變”⑧是滿人旗女之裝向民國旗袍演進替嬗的核心動力。女子選擇一截式旗袍,與剪發、放腳有著同等的價值追求,首先是“泯滅性的區別”⑨,便于爭得與男子共享教育、參政的權力。
與一截穿衣的視覺訴求相應的是,女子旗袍在款式、形制上也呈現出去滿族化和民國化,或者說是去封建和現代化兩個方向。首先是去除帶有滿族印記的繁鑲闊滾、雕花刺繡,下擺由寬變窄,顏色以碎花、純色、格子取代華麗艷彩,面料不僅限于細綢錦緞,土布、棉布也可制作,穿著者無年齡、身份之別,花季俏女、半老徐娘同穿旗袍上街。這些具體而微的細節變化讓旗袍徹底改頭換面,也打破了皇權時代森嚴固化的社會身份等級區別。其次,當旗袍成為一種時尚,與其他審美活動一樣,可以被看為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具有想象性地解決難以解決的社會矛盾的功能”⑩。1920年代,除了表達男女平權的訴求,旗袍也是女性身體與現代建國理想等國族政治交鋒的舞臺。旗袍的民國化可以說是兩個“民族”之間的轉換,是一種去舊布新、舊貌換新顏的文化翻新,意味著祛除前清印記之后的再次民族化。初興的民國旗袍雖然符合了現代化國族論述中去繁從簡的需求,但依舊保持著寬大、方正、嚴肅的流行趨勢,強化著中性化的審美和生活實踐,和“文明”新裝一樣,仍然不能體現民國女性服裝的現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女性新形象。也就是說,只有明確了旗袍在中華民國的現代國家體制之中如何完成從封建落后向現代文明的形象躍升,如何成為中華民國新的國民身份的象征,才可以理解女性在現代共和制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角色。
旗袍的流行實質上是婦女解放的思想現代性與時尚現代性的一場接力。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后,思想解放、女性獨立、男女平權的啟蒙呼聲不再是女性服飾變革的主要動能,時裝的潮流更仰賴于女性時尚意識的增強。比起報紙雜志的思想說教,婦女大眾更愿意沉浸在大眾傳媒制造的幻想中,她們對新聞、廣告和攝影照片呈現的穿旗袍的生活方式趨之若鶩,在模仿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種無意識的身份認同。就像張愛玲所說:“中國的時裝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設計靈感皆出自不謀而合的“公眾的幻想”,進而“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洪流……裁縫只有追隨的份兒”。旗袍在民國的流變也是對女性氣質不斷的重新定義。經過十多年的蟬蛻,旗袍就像一個經過磋磨、淘洗,再重新上釉的花瓶,中性化(男性化)色彩徹底脫落,煥然而成專屬于女性的新時裝,已“無真正與男裝相等之旗袍者”。至1930年代,旗袍的款式和造型基本固定,呈現凹凸有致、寬窄有距的立體流線型,“烘云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曲勾出”。在此期間,婦女解放思想、西化摩登的時尚潮流、簡潔自由的現代審美黏合在一起,捏成了一個完整的身份,重塑了現代女性的身體和形象。
1929年4月,國民政府頒布的《服制條例》對女子的服制做出了規定,女子常禮服在原來上衣下裙樣式的基礎上,還增加了一種“長至膝與踝之中點”的袍式。即使服制中沒有明確說明甲種袍式禮服就是旗袍,但齊領、右掩的前襟、衣長、袖長等特征的描述,以及當時旗袍的流行普及程度,都足以說明服制中的袍式禮服就是彼時的流行女裝——旗袍。至此,旗袍作為民國女性的身份標識從政令上被確定下來。同時,作為女公務員的制服,旗袍也具有了公共性的社會意義。1930年代中期,國貨運動和新生活運動的集結帶來了國家權力意志對旗袍顏色、面料的統一規范,進一步強化了旗袍的文化合法性,使之成為全民族“廣泛團結和群體認同”的標志,具有了國族符號象征的政治意義。
身份是群體在個體構成中的沉淀堆積,是個體的明確表達中改變特性的結構呈現。民族身份在個體的自我表達中蘊含著向內和向外兩個維度:在民族內部,民族身份需要被承認、被接納;在異族環境中,民族身份需要被發現、被認可。服裝是支持身份認同的“物質的和象征的資源”,是身份認同的標識條件之一。旗袍作為國族符號的象征,同時也是一種“承認的政治”,經由“旗袍”這一符號,表現出女性與中華民國政體之間承認的關系。在中華民族內部,女性與政體的承認關系被納入更大的國族論述范疇,旗袍所起的中介作用會被弱化。如:張若谷在《戰爭·飲食·男女》中對“一·二八事變”之后摩登時尚服膺于抗戰動員情形的描述,就體現了旗袍在承認關系中的弱化傾向。“一·二八事變”的炮火,讓上海的摩登女郎和女學生們“回憶到那有聲影片《璇宮艷史》中的婚典禮炮……他們于是都感興而起”。“許多城里的小姐,她們都脫卸五顏六色的長旗袍,短大衣,和高跟皮鞋,不再搽脂搽粉,穿了黑短褲、白襯衫,在公共體育場,和男學生們同受軍事訓練。”脫下旗袍,換上戎裝或醫護服的摩登小姐將會成為與男性比肩同齊的“摩登花木蘭”。在戰爭動員的催化之下,圍繞女性的性別論述從屬于國族論述,不僅承認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可以共同構成強大的抗敵力量,也承認穿旗袍的摩登女郎和女學生有著愛國抗敵的激情和勇氣。在這套承認的關系之中,旗袍不僅不具有象征意義,而且成了障礙,只有脫下旗袍,這套關系才能真正實現并發揮作用。也應該注意到,戰爭刺激下摩登女郎改頭換面的自覺意識和行為選擇充滿了羅曼蒂克式的浪漫幻想,是不牢靠的,難以成為殘酷戰爭中強大的精神支撐。建立在幻想和摩登時尚基礎上的承認關系也是單向的,摩登女郎這個群體還沒有形成“抗戰救國”的認同感。
當有異族文化觀念、文化立場參與其中,或者走進異質的文化空間時,這種承認的關系發揮的效用會更為顯著,旗袍的象征性會明顯增強。進入異質的文化空間之后,附著于旗袍上的性別基因就淡化了,旗袍獲得了與中國女性民族身份同義替換的價值功能。女性與國家政體之間的承認關系由旗袍來完成,并轉換為旗袍和中華民族、中華民國政體、中華民國國民之間的親密關系。主要體現在旗袍與異族服飾在同一主體身上的互換和對峙,進一步來說就是旗袍與洋裝的交鋒。洋裝在中國和日本具有混淆、改換和重塑民族身份的功能。男留學生通過學生裝和洋裝使得民族身份模糊于中國和日本之間,洋裝和旗袍也同樣可以讓留日女學生在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隨意切換。換裝的故意為之有時也是為了維護本民族的國族尊嚴,有著正向、積極的意義。廬隱1930年寓居日本期間,為了近距離觀察娼妓生活,去柳島時特意脫下中國服裝,換上西裝。在日本,只有“不守婦女清規”的摩登女子會在娼妓聚集的胡同漫游,她們都是身著西裝、長筒絲襪、皮鞋搭配起來的洋化裝束。廬隱正是通過換裝的方式,以日本摩登女子的身份進入娼妓生活圈,有意識地維護了中國的國族尊嚴。更為普遍的是,留日女學生會通過穿旗袍的方式表達“華夷之辨”的排外心理,對異邦文化、異邦民族的劣勢加以指摘。在留日學生的民族身份敘事中,不僅旗袍的民族性得到強化,還產生了排他性。“中國”與“旗袍”的拓撲聯結更加穩定,“中國”成為“旗袍”的限定語,形成了“中國旗袍”的偏正結構。在留日學生中間,“中國旗袍”不止于表達上的自覺,在精神心理層面也是一個敏感的信號,厘定著本民族與異族之間的界限。
二、旗袍的表意功能與逆寫文明優劣的反殖民話語
在留日女學生的民族身份建構中,旗袍的敘事功能,是在與人物的性格氣質、傳統的審美標準以及留學生面對日本的文化心態等緊密串聯來實現的。大革命之后,中國殖民話語由“矮化中國轉向‘逆寫帝國’”,留日知識分子通過強調和突顯中國文化的優越感,以中國傳統審美觀念區分中日女學生之美等策略,來逆寫文明優劣,構設反殖民話語。
首先,旗袍具有標識中國人身份的表意功能,是中國留日女學生能夠引發身份認同的“共享的特點”。集中講述旗袍與留日女學生民族身份故事的是崔萬秋的《新路》。小說中馮景山在火車上與林婉華初次相遇時,洋裝干擾了馮景山對林婉華民族身份的判斷,當林婉華開口說話時,她的民族身份才得以明確。而旗袍就像一個自動發聲器,它的標識性打破了留日女學生民族身份的神秘感,免去了猜測和打量的解密過程。這樣一來,留日女學生穿上旗袍,就等于出聲宣告自己是個中國人。林婉華與柳慶荇在東京街頭也都因身穿中國旗袍而引起對方的注意。林婉華“一看見中國旗袍知道是中國女留學生”,她“辨出那穿中國旗袍的是柳慶荇。柳慶荇見有穿中國旗袍的女子,也特別留心看”。這種表意功能還體現在旗袍與洋裝在同一主體身上的選擇和替換。林婉華、金秀蘭、梅如玉三位留日女學生對旗袍和洋裝的選擇有著不同的偏好。旗袍是林婉華的主要社交服飾,洋裝只是居家的常服。在公共場合,她通常“借旗袍表示中國女子的驕傲,她不惟訪友出游要穿旗袍,就是早稻田大學上課,也穿旗袍”。舞場、晚宴之類的地方更不消說,就算是和房主的女兒一同去逛公園,她也要脫下洋服,特意換上一件海藍色方格子夾旗袍。金秀蘭只有在家這個屬己的空間時才穿旗袍,“出門時從來不穿旗袍”,惟恐往來的人“生出奇異之感”。在外出游玩、參加聚會或者去學校上課的時候,她總要換上“頸項胸脯都可露出來的檸檬黃色的上下一體的洋服”,唯一一次穿旗袍出游還是在與男留學生馮景山在公園約會的時候。而梅如玉自從來到日本,再也沒有穿過旗袍,無論在家還在外出均是各色洋裝相搭配。應該注意的是,留日女學生服飾選擇上的偏好與民族身份意識之間并不能完全對應。盡管林婉華樂于享受旗袍帶給她的高貴的、積極的身份體驗,但也不忘在東洋尋找故國的熟悉感和舒適感。東京街道平坦光滑,街路樹排列兩側,“好像上海霞飛路一帶的樣子”,甚至路況比上海還好,汽車從這馬路上走,不惟速度甚高,而且沒有顛簸得難過之憂。洋房前貼滿商業廣告的松坂屋讓她“不由得聯想到上海的永安公司”。她寄宿的公寓也有上海法租界福熙路一帶西洋住宅的風味。東京的道路和住房讓她的內心涌動著他鄉亦故國的歸屬感。
旗袍不僅具有標識留日女學生文化身份的功能,還具有表現留日學生文化心態、民族情感的功能,二者構成了一個鏡像結構。當女留學生的著裝意愿與留日女學生的民族身份意識不一致時,敘事者的文化立場就顯得尤為重要。林婉華積極的身份體驗是日本文化空間和中國服飾兩種因素聯合帶來的。在描寫馮景山的歡迎宴這一情節時,崔萬秋借助中日青年混雜的舞場空間來鋪陳意境,對林婉華的出場進行了影像化的慢鏡頭式的描寫。“旗袍姿的中國美人林婉華出現在這舞場時,正是一支華爾茲的曲子剛完,電燈恢復了亮度的時節,全場的視線,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舞曲結束,狂躁的舞場回歸平靜,燈光恢復正常亮度,人的意識如夢方醒,一個旗袍姿的中國美人緩緩步入,吸引了眾人的目光,占據了被觀賞的中心地帶。敘述者通過對時間的把控,來精心布置場景,為林婉華的出場渲染了一種嚴肅而隆重的氛圍,也襯托出她的漂亮和高貴。這一切都在提醒和強調林婉華的身份非同一般,而“旗袍姿”和“中國美人”就是她最核心的形象修辭。當在場的日本舞女被這位中國小姐的美深深吸引,并議論不斷時,敘事者的目的似乎達到了,即立足民族本位,通過在異質的日本空間樹立中國女留學生的中心位置,表達自我民族身份的優越感。在這個過程中,旗袍在其中起著結構性的作用。事實上,這也正是1930年代留日學生民族身份敘事的重要特征。
身份是“通過差異與區別”建構的,“只有通過與另一方的關系、與非它的關系、與它正好所欠缺的方面的關系以及與被稱為它的外界構成的關系”。留日學生的民族身份的認同是在與日本國族形象的相互建構中完成的。留日學生在定位和找尋自我的同時,也在發現和塑造著日本。他們通常把中國和西方提到同等的位置,以現代人和文明者的眼光來打量日本,發現了一個既傳統又現代、既文明又專制、既先進又落后的矛盾重重的日本。崔萬秋的《新路》是通過發現落后于中國的“日本時尚”來表達民族身份優越感的。馮景山在去往東京的途中,兩次發現與中國同步的“日本時尚”。第一次是火車到三宮站,他洗漱完回到座位上時,對面來了一位短發的女性,他聯想到中國的“披發鬼”,“原來‘披發鬼’不是中國專利,在日本的火車中也可以發見得出來”。第二次是在火車經停御殿場時,車上上來一群女學生,她們“穿著衫裙連在一起的制服”,坐定之后與周圍的男學生大膽打鬧,他驚訝地發現“原來中國和東洋是一樣的”。林婉華也發現東京的夜生活不如上海熱鬧,最豪華的舞場停業時間竟早于上海,還未盡興就要打烊。“她想,若是在上海十一點半鐘,正是熱鬧的開端,一直可以跳到明天四點,東京真是太鄉下氣了。”而旗袍作為中國女性的常服,是中國社會時尚現代性的重要標志。當它跟隨留日女學生進入日本時,在其流行中留日女學生也發現了落后于西方和中國的“日本時尚”。日本摩登女郎鈴木信子對中國女留學生穿旗袍的美態艷羨不已,她邀請金秀蘭去舞場時,建議金秀蘭穿上旗袍:“我希望你今晚穿那身華爾紗的旗袍去,一定可以把全舞場的羨望吸集在你一個人身上。”但金秀蘭不愿惹人注意,羞于穿旗袍,還是選擇了乳白色的洋裝和茜色的領帶。當鈴木信子驚異于金秀蘭不穿襪子時,金秀蘭“對這位半熟的日本摩登女子感到一點輕蔑之意,她心里想不穿襪子在巴黎和上海早就流行了,而這自以為很摩登的信子女士竟引以為異,實在好笑”。謝冰瑩1930年代留學日本時,在電車里發現了一個文明、有序、勵志的日本,同時也發現了一個男尊女卑、大男子主義風氣盛行的落后帝國。“如果你是一個女性的話,走進電車里,不平之氣就會整個地占滿了你的腦海。舒舒服服坐著的大半都是男人,攀著圈子隨著電車的搖擺的,不是老態龍鐘的老太婆,便是背上馱著孩子,手里抱著大包袱的少婦。”中國知識分子歐化程度較高,在電車上男子會主動給女子讓座;而在日本的電車上,日本的男子只會偶爾給小孩和六十歲以上的老太婆讓座。在男女平等的現代文明秩序里,中國是優于日本的。謝冰瑩相信,日本女人要是看到中國電車上的情形,一定會心生羨慕,“而嘆息自己太可憐了”!“每遇到中國女人自由地和男子挽著手一同在大街上走,或者坐在車上很自由地笑著談著……她們的表情是含著無限的羨慕和感慨的。”蕭昔生的《留日漫記》則是通過借日本之勢,貶低矮化異族留學生形象,在日本下女和菲律賓留學生的身上尋找自我民族的優越感。他在《留日漫記》中講述自己下課回到住所,看到日本下女富季桑“穿著一件中國式藻皮紅色的中國旗袍”,既驚訝又好奇。“我真不知道她何以忽然要穿著一件中國衣服!又不知道她是由何處尋來了一件中國衣服穿的。”雖然他對旗袍的來歷百思不得其解,但認定這件旗袍一定來自中國留學生之手。很快他就將這份驚詫和疑問遷移到中國男留學生的人格品性,并以菲律賓留學生作為參照。“凡中國留學生的男子,據說都是對于日本女子特別殷勤,特別表示親切與有禮,尤其中國男子,普通都是堂堂儀表,決無如菲律賓人之粗暴野蠻鼻突臉陷滿面青須者可比。故超達如富季桑者,于無意之中,對中國男子特別愛慕,因而打破國家觀念,喜好中國式衣服而求取好于人亦未可知。”蕭昔生將菲律賓留學生塑造為面相兇惡,品行低劣,蠻橫粗暴的野蠻人,來凸顯中國男留學生的高潔、端正的人格品質。故而,日本的兩位下女對中、菲兩國留學生會產生異樣的感情,“均似對于中國人有一種特別的感情,而對于菲律賓人多加歧視”。
旗袍同樣也是留日男學生彰顯民族主義文化立場,向本土文明和民族傳統尋找文化認同根基的觸媒。《新路》中,馮景山的文化立場和敘述者是一致的,他的文化身份可以定位為“理想的民族主義者”。他企圖通過林婉華和金秀蘭兩位留日女學生的服飾與身體在她們身上尋找民族印記,辨識中華文化的特征,達到民族身份認同的內在與外在的完全融合。馮景山在火車上初遇林婉華時,他的審美觀念隨著林婉華國族身份的明確而產生變化:生出日本健康美和中國陰柔美的雙重標準。當時,林婉華穿著藏青嗶嘰學生裙、白襯衣和藍底紅花上衣,衣領上打著茜色領帶,手中提著西式小包,是一個短發洋裝的日本女學生形象。勻稱的身姿、豐潤的肌肉、嫩紅的面頰和水汪汪的大眼睛,體現出一種健康美。確定林婉華是中國人之后,敘述者的審美修辭立馬轉向中國文化內部:“她的眼睛和嘴唇最是動人。中國舊話上有句‘脈脈含情’,馮君以為這四個字正可形容她的眼睛了。至于她的嘴唇是怎樣的美,馮君覺得現下名傳天下的中國女明星胡蝶的唇,長得和這位林婉華很相像”,并在體形相貌上刻意與日本女子做出區分:“她的腿,不像日本女子那樣粗,她的腳,不像日本女子那樣大,長筒絲襪,黑色皮鞋,與她上身的洋裝非常相配。”當林婉華脫下洋裝換上旗袍,帶給馮景山的是欲望化的吸引。在歡迎宴上,身穿黑色旗袍的林婉華甚是驚艷,身段體態嬌而不媚,氣色可人,馮景山立刻被打動。在櫻花跳舞大會上,兩人在孤燈下對坐暢談,林婉華因旗袍加持由內而外透露出來的優雅氣質,令他感佩。旗袍塑造出來的身體豐姿更是“給他以誘惑”。旗袍的美麗同樣在金秀蘭身上也風韻難掩。和金秀蘭同游井之頭公園時,看到金秀蘭的旗袍豐姿,馮景山再次心神蕩漾。他從側面看去,旗袍包裹下的身材楚楚可人,“她的細長的臉龐,是那樣紅潤,兩個乳房輕輕的鼓出一點來,藏在鈴蘭花樣的輕羅之下。兩支肩膀的曲線,又是那樣豐滿優美”。把公園內所有的日本女子都捆在一起,也趕不上她的可愛。等到站起來,“長身玉立的她,步法非常婀娜,鈴蘭花的旗袍直垂到腳跟,一陣風過,衣裾飄動,好像仙女的仙翼。從后身看她的兩肩的勻整,背脊的挺直,以及腰身的纖細,都是異常輕靈灑脫,一點兒笨重處也沒有,至于面部,則更充滿了青春的光明”。即使是穿洋裝的時候她的臉龐、身段、姿態,也“是代表的中國傳統美人;尤其是傳統的蘇州美人,與日本的女子迥然不同”。同樣是穿旗袍的中國女留學生,在感性層面,她們對馮景山的誘惑力難分伯仲,但在理性層面,他仍然以中國傳統的審美標準來作出區分,并在她們身上尋找中國的地域文化基因,以此來給她們進行文化身份定位。來自長沙的“林婉華是現代美人”,有著蜀湘女子的執拗、強韌、聰慧、熱情、爽快,在她身上甚至可以看到湖南女作家丁玲、白薇、謝冰瑩的影子,她們都“是‘楚國情調’的產兒”。來自蘇州的“金秀蘭是中國傳統的美人”,有著江浙女子的才氣、精巧、溫婉、含蓄、內斂、綿軟。就連她們戀愛的方式也是大異其趣:“江浙的女子對于戀愛的態度,是欲擒先縱;蜀湘的女子對于戀愛的態度,是一往情深。”而“馮景山喜歡古典的”,喜歡金秀蘭“蘊藏乎中的”才氣和她的溫柔、順從、純潔。留日男學生定位異性同胞也是在表達自我。以中國傳統的文化基因作為參照對留日女學生做出民族化的文化身份定位,隱含著男性視角下的民族主義文化立場。他們通過給本國女學生服飾和身體的傳統賦意,實現了對自我民族身份意識的表達。
三、作為他者的旗袍:國族論述里的殖民糾葛
“作為身體的延伸、卻又并非身體一部分的服飾,就不僅連接了身體和社會,更清晰地區分了它們,成為‘我’與‘非我’的邊界。”旗袍作為國族符號的象征,劃定的是“我族”與“他族”的界限。半殖民地文化語境中,當服裝的社會批判功能指向日本的殖民策略時,就產生了殖民性的社會話語作用,具體表現為被殖民和自我殖民化的表意功能。1930年代,“旗袍—中國”的話語象征也屢屢被日本殖民者所征用,實行文化殖民策略。為了制造中日親善的幻象,日本社會提倡讓本國婦女著旗袍。如:1930年代“在銀座常可見到穿旗袍的日本女人,中日戰后這種打扮即告滅跡”。又如:1934年長崎國際產業觀光博覽會和1937年日本東京博覽會都為偽滿洲國設專館,并讓日本的女招待穿上中國旗袍,雙手拿著日本國旗和偽滿洲國的旗子,以表示中日之“友好”。當身體“跨境”時,服飾引發的國族論述張力,不僅包含不同民族的服飾在同一主體身上的“文化互換”,還包含同一民族服飾在不同主體身上的“文化易界”。在后者的視野中,殖民話語對“旗袍—中國”隱喻結構的征用,還體現在旗袍作為相對于另一種服飾的他者而存在。
進入一個國家,就是進入一種文化。1930年代,旅居中國的日本僑民同樣也需要用中國服裝來掩蓋自己的民族身份。小說《娟子太太》中,旅居上海的娟子太太為了生存需要,只有通過換裝頻繁改變民族身份,呈現了殖民時代的民族身份矛盾。娟子青年時期,與中國留學生相戀,跟隨戀人來到上海。在戀人死后,為了保障日常生活,她不得不穿上中國旗袍,將自己偽裝成中國人。只有到了深夜,她才能穿上和服和木屐,享受做日本人的短暫時光。兩套服裝,兩種身份,娟子太太的民族身份由白天和黑夜來操控。白天她是面容白皙,穿灰色旗袍的中國教員,晚上她是“穿和服拖木屐的日本婦人”。日軍占領上海后,她被聘為日本憲兵隊的翻譯官和治安維持會的顧問,脫掉了灰色的旗袍,做回真正的日本人。當戰火熄滅,日本撤兵,她又重新過上了晝夜分裂的生活。此時的她就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在回不去的祖國和扎不了根的異國之間漂浮、游蕩。縱使旗袍會給她帶來生活的便利,讓她受到中國民眾的認同,但她難以在情感上認可自己穿上旗袍的中國人身份。旗袍在她的精神世界始終難以跨越“我”與“非我”的民族邊界,一直是相對于和服和木屐而言的他者。換裝給娟子太太帶來的身份之累既是主動選擇,也是被動接受的結果,隱含著殖民時代的歷史創痛。不知“到什么時候,用什么法子,才能夠將那可怕的火的記憶忘掉,將那尖銳的仇恨的狠刺拔去呢”?
圍繞旗袍展開的國族論述和殖民糾葛,在崔萬秋的《新路》中,通過“九一八”國難敘事、日本殖民敘事和留學生民族身份敘事的含混表達來實現。來自東北殖民地的留日女學生梅如玉是主要敘事焦點。剛到日本時,她還是一個“半城半鄉的姑娘”,“勢利眼的女孩子”,“身上穿的也是一件樸素的旗袍”。在日本不到三個月,就完全換了副模樣,她變得“有些像美國女明星葛萊泰嘉寶那樣的女性。她的臉上浮現著一種近代的銳敏,鼻梁筆直,眼睛大而有光。乳白色的皮膚,紅莓似的嘴唇,頭發漆黑”。樸素的旗袍被形形色色的洋裝所取代,變成了她生活世界中的“他者”。與她的舊裝束一起被遺棄的還有資助她的愛人和民族身份。中國同她的愛人方潛亭一樣,“只是多余的贅瘤,已不是可戀慕的對象”。文化認同和身份體驗的錯亂是日本在東北進行殖民教化的直接后果。她從小接受日本的殖民教育,日本文化深刻進她生命的底色,習文斷字都是日本式的。長時段的殖民教育截斷了原生民族文化對梅如玉的浸潤和供養,擾亂了她的根源認同和價值認同,帶來文化認同和民族身份的錯位。“她自幼受的是日本教育,她心目中本沒有中國”,也“從來沒有意識到她自己是中國人”,甚至對中國的認知也是久遠的,且充滿了殖民色彩。她的意識里,“沒有中國,只有一個腐敗的支那,這支那是人人吃雅片,各個女子都纏小腳,各個男子都拖著長辮,讀書人都是彎腰駝背的老迂腐”。與本民族文化的隔膜,和對日本文化的熟悉,為她脫下旗袍換上洋裝,獲取新的身份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意味著自我殖民化。她的身上充滿了悖論,在厭棄、漠視本民族身份的同時,又利用本民族身份之便從留日同胞周星庵、劉維廉等身上獲取生活資本,還同時給深愛著自己的方潛亭寫信敷衍,表達虛假愛意,騙取生活費。寄生于男留學生時,她又對威脅、擠壓自己生存資源的中國女留學生充滿了敵視和嫉妒,甚至以耍弄男留學生作為報復手段。事實上,對梅如玉來說,與情感危機、生存危機相伴而生的還有懸置于本民族和異族之間的身份危機。在她與男留學生的寄生關系中,在滿足男留學生情欲需求的同時,梅如玉也遭到了他們的排擠、蔑視和嘲諷,被稱為“爛熟的妖星”。小說著意淡化甚至抹除梅如玉對日本殖民統治的體驗和記憶,反之以深刻的受殖體驗剖析她的文化根源,在揭示日本殖民策略的徹底性和破壞性的同時,為旗袍的缺席找到了合理的根由。
《新路》中,九一八事變激發了留日學生休戚與共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事變發生之后,日本當局加強了對留日學生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控制。留日學生界為日本的殖民野心和侵略行徑而憤慨,他們因為“九一八這樣的國恥,而在日本身受種種刺激”。清脆急切的號外聲就像一個個魔爪,將他們從狂歡的夢境拖回冷酷的現實。文化根源的改變必然帶來民族情感的疏離。當留學生界熱火朝天地召開會議,籌劃運動時,很晚得知消息的梅如玉“既不憤慨,也不激怒”,唯一詫異的是“她沒想到竟發生得這樣快”。看到沈陽淪陷的報道,她首先想到的是“她們一縣的學生就又擴大了做事的地盤,于她有益無損”,所以她對此事并不感甚大的痛苦。在日本資本主義享樂原則和金錢誘惑之下,梅如玉慷然接受了殖民勢力的收買,答應日本政客向他們提供留學生內部的情報,以賺取優渥的生活資源。這種神秘的工作性質,讓她精神振奮,甚至認為自己接受了一項莊嚴神圣的任務,與好萊塢電影中嘉寶飾演的國際間諜有著同樣偉大而高尚的意義。一個人民族身份的根源一旦改變,文化認同一旦缺失,殘酷的殖民現實就失去了感召力,更無休戚與共的民族情感和國家觀念可言,直至與殖民勢力聯合,走向漢奸的歧路。當她激怒方潛亭而被殺害的時候,也意味著她對同胞和自我民族的叛離受到審判和裁決。
結 語
“近代的半殖民境遇使得中國臣服于歐美對‘文明’‘現代’‘進步’的定義,中國固有的文化價值系統和文學觀念被‘西方中心主義’拆解,中國在模仿(或對抗)殖民帝國的現代化的過程中陷入了‘自我迷失與重拾’的怪圈。”旗袍在民國的時尚衍化以及“旗袍—中國”隱喻結構的形成,凝聚著大眾審美、民族國家觀念、政權意志的力量,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模仿(對抗)西方殖民帝國現代的過程中重拾自我的表現。在留日學生的民族身份敘事中,旗袍是留日女學生和留日男學生表達民族身份認同的共有媒介。隨著留日女學生的身體“跨境”,旗袍的表意功能超出了本民族的社會文化范疇,更多受制于日本的文化空氣。中國普遍流行的旗袍在日本成了一種張揚的個性表征,標志摩登、歐化的洋裝反而是一種內斂、保守的選擇。在民族外部,旗袍是留日女學生的身份標識;在民族內部,旗袍塑造的女性身體又對男性同胞構成了情欲引誘,也是進一步定位留日女學生文化身份的重要參照。
也需要注意到,經“旗袍—中國”的隱喻結構建立起來的民族認同邏輯,有一定的限度。留日女學生的身份意識是在追求物質現代性的快感和刺激中逐漸感知的,功利性的誘惑是主要動力。當身著旗袍的留日女學生進入日本的舞廳、公園、街道等公共空間時,她們的身體也并沒有實現由個體到民族國家的文化轉換。作為中國民族身份象征的旗袍無法換來日本民眾對中國國族本身的認同和尊重。以旗袍作為國族象征,重建民族自信的愿望只能在日本的普通民眾和部分中國留學生那里有效。因此,崔萬秋《新路》結尾大致可以作出這樣的理解:林婉華加入馮景山等男留學生的反帝宣傳運動,并一起被遣返回國,既宣告了留日女學生難以承擔起現代知識分子身份重建的任務,也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民族身份的建構和反帝、反殖民的抗爭也需要在國內的戰斗實踐中來實現。
注釋:
①李永東:《身份焦慮、民族認同與洋裝政治——以創造社作家為例》,《文藝研究》2018年第3期。
②瑪麗琳·霍恩著,樂竟泓、楊治良等譯,卜文校:《服飾:人的第二皮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③張小虹:《時尚與現代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第221頁。
④漱石:《京劇物類名稱表·衣履類》,《繁華雜志》1914年第1期。
⑤根據當時報載的記錄,旗袍在1920年前后開始流行,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光緒帝逃難,宮中的細毛皮貨、書畫珍寶流散宮外。辛亥革命之后,散入上海的競賣市場,旗袍被衣裝商人收買,受到戲子和妓女的青睞,上海婦女求新趨異,以為穿旗袍為出風頭之事,旗袍在老少之間流行開來。參見一動:《新聞拾遺 新年新裝束之怪現狀》,《申報·自由談》1920年2月20日;獨鶴《閑話·大衣與旗袍》,《天津益世報》1921年1月17日;病鶴畫并注:《旗袍的來歷和時髦》,《解放畫報》1921年第7期。
⑥鳳兮(朱鴛雛):《旗袍·調寄一半兒》,《禮拜六》1921年第101期。
⑦伊麗莎白·威爾遜著,孟雅、劉銳、唐浩然譯:《夢想的裝扮:時尚與現代性》,重慶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頁。
⑧張小虹:《時尚現代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第230頁。
⑨許地山:《女子底服飾》,《新社會》(北京)1920年第8號。
⑩Jameson, Fredric(1981),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asSociallySymbolicAct, London: Methuen, p.79.轉引自伊麗莎白·威爾遜著,孟雅、劉銳、唐浩然譯:《夢想的裝扮:時尚與現代性》,重慶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