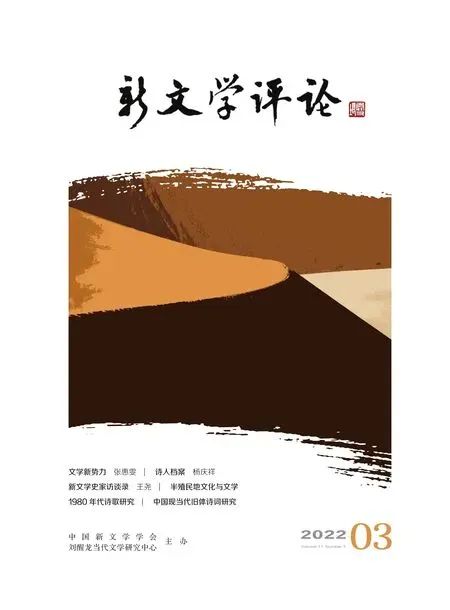敞開和激活文學史研究的空間
——王堯先生訪談錄
□ 王 堯 房 偉
房偉:當代文學史是一個迷霧重重、矛盾重重、充滿話語沖突的研究場域,您多年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且成績斐然。您能否概括一下文學史研究的心得?
王堯:謝謝房偉。我們借這個機會來討論和交流一些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問題。當代文學史研究,這些年來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的成果,作為學科的中國當代文學也因此逐漸成熟。但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問題與方法需要拓展、深化和激活。就我個人而言,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國當代散文史》算起,三十余年我的主要精力是在做當代文學史研究,兼及文學批評。我導師范培松專治中國現當代散文,對我影響很大。越深度進入文學史和相關學術史,越會發現自己作為文學史研究者的局限。“文學史家”這個概念需要謹慎地使用,一個學者出版了學術性的文學史著作,或者主編了文學史教科書式,不等于自然而然獲得了“文學史家”的身份。我們今天稱為文學史家的學者,如現代文學史家王瑤先生、唐弢先生等,他們對文學史研究和寫作范式的建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他一些學者,嚴家炎先生、范伯群先生、樊駿先生等,在文學史研究范式轉型或在文學史研究的問題與方法上也各有建樹。按照我說的這條線索梳理,陳平原、陳思和、洪子誠、丁帆、於可訓等先生都有重要的建樹。程光煒關于20世紀80年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歷史化的研究,張福貴關于民國文學的研究,陳曉明關于當代文學與現代性的研究,等等,都拓展和深化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還有不少我沒有提及的一些學者的文學史研究。這才有了現在這樣的文學史研究格局。在學者的身份表述中,沒有必要把“文學史家”置頂。
從文學史口述史研究開始,這些年來,我除了關注文學史研究的復雜性、關聯性外,我比較側重探索文學史論述的形式。我們已經習慣于文學史教科書這種形式,但文學史著作同樣有一個文體問題。這是我在閱讀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美國文學史譯叢”、《俄羅斯文學史》和《英格蘭文學》等著作時想到的問題。當年,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曾經給文學研究者啟發,謝冕先生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就選取一個時間點來寫作文學史。文學史著作的論述方式,其實就是文學史著作的文體問題。用什么樣的形式論述文學史,不僅是形式問題,與治史者的史觀密切相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內容的呈現。我想完成的是“三體”當代文學史,口述體完成了,現在做的是敘事體和論述體文學史。在《文藝爭鳴》連載敘事體文學史時,我寫了這樣一段“前記”:我一直想用敘述的方式寫中國當代文學史。試圖將場景、事件、思潮、人文、作家、文本及其他相關要素融合敘述。這種“敘事的歷史”并不排斥“分析的歷史”,敘述本身已經是分析之后的選擇,但包含了分析的“敘事的歷史”顯然會呈現出與“分析的歷史”并不完全相同的景觀與肌理。這是我近幾年研究和寫作文學史的計劃。
房偉:您一直強調,要用“關聯性”觀念理解當代文學的復雜面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文學史過渡狀態”“擴大的解放區”等關鍵詞。具體文學史實踐之中,對關聯性的關注,在增強對文學現象復雜性認知的同時,是否會因為對不同觀念的調和,降低當代文學史書寫的權威性?如何使關聯性研究,真正推動當代文學經典化進程?
王堯:“關聯性”研究、“文學史的過渡狀態”、“擴大的解放區”和“無作者文本”等,是我在文學史具體問題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觀點和方法。在研究“文革”時期的文學與思想文化時,我意識到了方法的重要,問題是與方法想聯系的。所謂“關聯性”研究,重視的是文學史的結構關系,在各種因素之間尋找歷史和邏輯的聯系,不僅是呈現文學史的復雜性,還試圖分析文學史的內部矛盾運動,而不只是呈現結果。無論是在文學史內部還是外部,各種因素糾纏、碰撞、融合,單一的因素分析不足以呈現文學史的復雜進程。所謂“矛盾運動”,不全是對立的沖突,有融合,才構成文學史的主線,有并列,才有文學的多樣性。我們需要剪裁的枝蔓是那些不能入史也沒有對文學史進程產生影響的因素。“關聯性”研究,將有助于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和經典化,在各種關系中認識文本的意義、討論文本的內部構成,會避免線性分析的偏頗。“關聯性”研究還涉及學術共同體問題,在相同的問題域,需要比較中國學界和海外漢學界的研究成果,在這方面,我的同事季進做得很好。
我講文學史的“過渡狀態”,是“關聯性”研究的一個結果。文學史不同的階段之間,既有斷裂也有聯系,還有其他特征,這是需要研究的,不能簡單化。如果我們要建構具有總體性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框架,需要解決“過渡狀態”的問題,否則不能形成文學史階段之間的聯系。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最直接的背景是解放區文學,在1956年之前,文學制度的設計也基本按照解放區文學的模式進行,這個階段可以稱為“擴大的解放區文學”。1956年之后,對社會主義文學的認識深化了,當代文學的制度設計也發生了重大轉換。在研究“文革”時期文學時,我提出了“無作者文本”這一概念。這些文本有些是集體創作,但更多的是個人署名,這些文本的共同特征是沒有“個人”,基本內容都是對主流話語的轉述,而不是個人的見解。我在這個意義上討論這一現象,“無作者”不是“作者已死”的概念。
房偉:您的當代文學史研究,非常強調思想史研究的路徑。請問如何將思想史研究結合入文學史研究?是否存在喧賓奪主的情況?文學史研究如何利用思想史研究豐富自身,又不失其研究主體性?
王堯:我年輕時候寫過一本書《鄉關何處——20世紀中國散文的文化精神》,我想從文化精神角度進入散文研究,還提出了“散文是知識分子精神與情感的存在方式”這一命題。90年代中期,我開始轉向“文革”時期的文學與思想文化研究,在寫作博士學位論文時我體會到離開思想史,很難研究這個時期的文學與思想文化。此后我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都保持了對思想史的興趣。文學史當然是文學的歷史,但文學歷史的生成過程中,政治、思想、哲學、倫理、經濟、法律、軍事等對文學和文學的歷史產生了影響。不必說作家的生平道路創作,研究者的文學史觀、世界觀與方法論等,都不是單一的文學因素養成的。我們研究五四新文學,研究當代文學史中的思潮論爭運動,都離不開思想史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如果考察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我們會發現,你說的思想史研究路徑一直存在著。90年代以后,確實出現了“文學研究的思想史轉向”這一現象。比如汪暉、王曉明等,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側重思想史研究。一些學者比如蔡翔、賀桂梅、羅崗等,他們的文學研究有著顯著的思想史研究的問題與方法特征。我熟悉的另一批學者,丁帆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包括他談俄羅斯文學的一組文章;張福貴關于新文化運動和魯迅的研究;孫郁關于魯迅和民國作家的研究;陳曉明關于百年中國文學與思想文化的研究;王彬彬關于魯迅和現代史的研究;李建軍關于俄羅斯文學與思想的研究等等,都介于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之間。當然這些研究者進入思想史的價值判斷是不一樣的。這一現象的興起,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跨學科研究的方法問題,學科邊界的問題。但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講,思想史研究路徑的介入,首先是文學史研究的內在需要。剛剛我也說到這點。文學史的研究應該有不同路徑,思想史研究是一種路徑。我說的關聯性研究就包括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關聯。這些年來,何謂文學和文學史,分歧很多,唯一的共識可能就是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如果不把文學史視為思想史研究的素材,這樣的研究仍然是文學史研究。
房偉:您的《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曾獲魯迅文學獎,廣受學界贊譽。您認為目前汪曾祺研究存在什么問題?對汪曾祺的推崇,是一種對逝去的文人品格的懷念,還是汪曾祺本人的藝術成就使然?對汪曾祺的文學史地位,應有一個怎樣理性而準確的判斷?
王堯:我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關注汪曾祺創作,9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當代散文史》列了專章談汪曾祺的散文。現在看,這本書當然很不成熟,但當年對當代散文史的基本判斷是能夠成立的。我沒有寫過很多關于汪曾祺的研究文章,但對汪曾祺和汪曾祺現象一直有所思考。能不能在文學史的脈絡里討論汪曾祺的意義,是我想做的事。這篇論文是在旅途中寫的,我帶了很多書想在旅途和學術會議間隙完成這篇文章。如果不是張濤不停催促,也許還不能完成。我對汪曾祺先生的創作和文學史意義評價很高,也在文學史和文化現實的結構關系中討論了汪曾祺何以成為汪曾祺。這篇文章也簡要提到了汪曾祺創作的局限,包括他晚年作品的一些問題。在當代作家中汪曾祺先生是少數幾位差不多被經典化的作家。《汪曾祺全集》《汪曾祺別集》的出版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都將離開我們二十余年的這位先生建構成傳說一般的人物。一位當代作家大半生處于寂寞,因《受戒》《大淖記事》和重寫的《異秉》而聲譽鵲起,辭世后影響力在相當范圍內持續不減,這本身就是值得關注的現象。這個現象與汪曾祺先生鮮明的個人特色有關,但其中研究者的審美趣味、當代作家的文化素養以及仍然處于轉型時期的文化結構都催生了我說的這種現象。因為文化斷裂,汪曾祺先生的意義凸顯,他銜接了傳統,恢復了語言的文化屬性,話語的個人特質鮮明,而這些都是當代文學史在一段時間里缺失的。我無法預測以后的文學史會如何論述汪曾祺,但在當代文學史的整體結構中,汪曾祺當有一席之地;同樣,我也認為,過往汪曾祺研究中的水分或許也會收縮。我在2020年第12期《文藝爭鳴》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關于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的札記》,談到這些問題。我在文章中說:汪曾祺研究存在過度解讀的問題,突出表現為從個人偏好出發過度闡釋汪曾祺的文學史意義,在文本之過分把玩汪曾祺個人生活的趣味,對汪曾祺士大夫式生活方式的過度渲染有可能將汪曾祺先生的性情與作品變成一種文化消費。如果汪曾祺先生健在,他也可能對這些善意的夸大與過度解讀不以為然。汪曾祺先生本人的文論,對自己作品的解讀其實是非常謹慎的,特別是意識到自己這種寫作方式的局限。我們當然不必完全以作家的夫子自道論長短,但我以為汪曾祺先生自己是清醒的。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之際,在表達敬意和緬懷的同時,我坦率說出我的憂慮和異議。這是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觀點。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大家,但遜色于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
房偉:您在郁達夫文學獎評審會議上,提出新“小說革命”命題。您認為,當下小說洞察歷史、回應現實的能力在衰退,小說藝術發展滯緩。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是時代變化引發的結構性問題,還是當下文壇生產機制問題?柄谷行人曾大談“日本近代文學終結”,他認為,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方式的文學,是現代的發明,也有特定的政治有效性范疇;今天“以小說為中心”的現代精英文學模式,必然會走向衰落,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如果說,今天的中國小說,還有著“小說革命”的可能性與沖擊力,那么,它將在哪些實踐層面展開?
王堯:前年在郁達夫小說獎初評會議上,我提出了新“小說革命”的話題。這個想法并不是一時興起。我們在一起交流也比較多,會談到小說的問題和新的可能性。這幾年,閻連科提到21世紀小說的概念,他覺得小說應該在19、20世紀的小說基礎上往前走。我和連科也經常討論這個話題。以這個思路來看,我們對當下的小說創作不是很滿意。《文學報》的傅小平報道之后,“小說革命”的話題引起關注,他又約我寫成文章,這就是《新“小說革命”的必要與可能》。《文學報》在發表這篇文章時組織了專題討論,鐘求是主編的《江南》雜志又請楊慶祥、張莉二位組織了一批小說家批評家和編輯討論這個話題。我這里不重復我的基本觀點。但想強調,不僅是小說,文學在整體上陷入了困境。丁帆老師在他的演講和文章中,都痛陳過當下的問題。現在說百年未有之變局,其實百年前也出現了百年未有之變局,曾經的變局和現在的變局疊加在一起了,我們不能孤立地看現在的變局。百年前現代知識分子包括文學知識分子介入中國和世界的方式仍然值得我們重視。我們不能把今天的困境和小說的停滯不前歸咎于文化現實,文學知識分子從來不應該被文化現實裹挾。我們在思想上藝術上缺乏應對變局的能力。
文學在發展過程中,不時有人斷言文學的命運,小說會死亡的說法也不曾停歇過。新文化運動以后,現代小說成了文學秩序的中心。以小說為中心的精英文學模式會不會衰退,我無法做出判斷。文學的演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某一個階段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可能只是文學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細節。我關注的重點不是衰退,而是在文化結構,特別是數字技術迅速發展的情形下,文學如何來應對這種變化,而精英文學的模式肯定也會發生變化。最近我讀到柄谷行人的一篇文章《我為什么不搞文學了》,這題目是譯者戲擬的,這篇漢譯出自《柄谷行人講演集成1995—2015:思想的地震》。柄谷行人說,盡管不想反思自己,但是仍然反思了過去的工作,僅僅是反思了一下《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這一本書,就能看出許多東西了。柄谷行人對文學有點悲觀,說他已經沒有積極地思考文學的心情了,連今天這種半死不活的心情都沒有。他說《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這本書,雖然是對文學的批判,但是在文學具有特別價值的時代里寫出來的。如今怎樣批判都沒有意義了,文學已經變得沒有價值了。我不知道這個翻譯是不是準確,柄谷行人說文學的身價一落千丈,這沒有錯,但我不認為文學沒有價值。價值是獨立的,文學賣多少的身價是受市場和讀者影響的。我注意到,柄谷行人還說:“政治對于文學而言也是重負。毋庸置疑,從屬于政治的文學根本不是文學。但是完全喪失了政治向度的文學,就變成了娛樂。而在1990時代之后,文學已經從一切重擔下‘解放’了。但是與此同時文學也終結了。當然,作為娛樂的文學還殘存著,毋寧說還很興盛,但是卻喪失了連接理性和感性的想象力。”柄谷行人這里說的“終結”了的“文學”是特指的,他說的這種文學的困境在90年代以后的中國也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是,柄谷行人提出了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文學/想象力和理性的關系這一問題。閻連科早些年出版的《發現小說》和近年在香港科技大學關于外國小說研究的講稿,對文學/想象力和理性的關系有許多新的思考和見地。
房偉:您曾在一篇文章談到對當代文學史料的看法。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是當代文學研究熱點之一。如果說,加強史料研究,可以回到古典文學成規,推進當代文學經典化,那么,目前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存在哪些問題?它是否能達到某些學者的預計效果?如果沒有達到,問題出在何處?我們是否要讓當代文學研究在“淡化批評、走向學術”的過程中,保持史料研究的“有效性”?
王堯:重視文學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其實是中國學術的傳統。我讀大學時,有專門的文學文獻課程,我另外還選了文獻檢索,這是一門選修課。給我們講授中國當代文學史課程的卜仲康教授長期參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的編寫出版工作,我和卜老師交往密切,他參與的這一工作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80年代初、中期,明清詩文研究室和現代文學教研室,和我們的教室以及我后來的辦公室靠在一起。錢先生在主持清詩紀事編纂工作,范先生在主持通俗文學史料的編選工作,會感受到“故紙堆”的氛圍。后來,我自己做過些史料的編纂,如“‘文革’文學大系”“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等,現在寫作的敘事體文學史,需要非常充分的史料準備。
近幾年,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研究興起,尤其是史料整理一時蔚然成風。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固然是當前文學史料整理熱潮產生的原因之一,更多的則與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科意識的深化和學術研究的成熟有關,一些整理者和研究者個人的特質和學術興趣也促進了史料整理與研究工作。但史料意識和學科意識的強化,并不等于當代文學史研究學術分量的增加,并不意味著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思想淡化具有合理性,同樣也不助長史料的整理遠比當代文學史論述更有學術生命力這樣的偏見。
在談到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時,我個人的習慣表述是“整理”與“研究”。我目前不太贊成“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這樣的提法,現在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古代文學史料學有自己的體系,當代文學因其當代性,其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文學。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如果整理不是堆砌和復制,那么整理無疑帶有研究的性質。事實上,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一種學術研究。盡管文學史料學也可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我覺得史料學還是服務于文學史研究的,沒有孤立的史料整理與研究,史料整理和研究是和文學史研究相關聯的。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史料整理與研究是文學史研究的一部分。換言之,我們存在如何整理文學史料的問題,但在整理之后如何研究,同樣是一個需要討論的重要學術問題。如果把史料的整理簡化為文獻的匯編或者以新的分類重編文獻,而忽視對現有文獻是否具有史料價值的判斷,忽視對史料的再挖掘、拓展和考訂,那么這樣的史料整理可能會為一般的研究者提供查閱資料的方便,但就學術價值而言只是平面上的重復,通俗地說就是“炒冷飯”。現在需要用學術思想對應和激活當代文學史料。
在文學史料學的分類中,文學批評是史料之一種。對當代文學批評學術性的質疑從來沒有間斷過,我們不必因此委屈。無論是文學史研究論著,還是文學批評,都需要經過學術史的檢驗。如果沒有及時性的文學批評,其實就沒有后來的文學史論述,或者說文學史論述是建立在文學批評的基礎之上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之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意義正說明了這一點。
房偉:您曾出版《“新時期文學”口述史》,湯普遜稱口述史為“過去的聲音”,口述史能否算做傳記式史料?當代文學學科引進口述史方法,與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相比,有著怎樣的自身特色?目前,當代文學口述史研究推進的難點和突破點在哪里?
王堯:在史料學的分類中,口述史料是文學史料的一種。如果用口述體的方式編纂文學史,那么口述史又是建構文學史的一種文體,它的意義應該大于史料。口述史料中有一部分是傳記式的,但不全是。我差不多在二十年前開始文學口述史的工作,除了做口述的史料準備外,我關注和思考文學口述史的理論和方法,以及我自己做口述體文學史的路徑、方法和結構。前者,是思考和研究口述史方法的文學化。口述史在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領域比較成熟,也形成了各個領域自身的特點。我十多年前寫過一篇《文學口述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初探》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作家的訪談錄,可以說是一般意義上的口述史,但和用口述史方法建構文學史是不同的。我自己在設計和操作口述史的文學方法時,著眼于文學生產的全過程,除了作家外,文學組織者、活動家、編輯家和批評家等都是口述者,口述活動的這一過程,就是文學史建構的過程。這也是文學口述史的特色。當代文學有鮮明的當代性,因為參與者的在場,這才有編纂口述體文學史的可能性。所以,現在需要搶救口述史料。專題的或者作家的文學口述史應該可以側重去做,時空遼闊的文學口述史已經很難做了,許多親歷者過世了。根據不同的口述對象確定口述史的方式、做好口述史料的鑒別和注釋、設計出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結構,這是口述史的難點。
房偉:您是一個優秀的批評家,當下文學批評呈現出多元化態勢,但批評影響力并沒有增強,反而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學院派批評受到多方制囿,活力逐漸萎縮,豆瓣、知乎等網絡媒介為載體的“新大眾文學批評”對“傳統文學批評”形成質疑,而批評粗暴化和批評贊歌化,幾乎同時出現在當下批評場域,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王堯:我已經不是一線批評家,對文學批評現場的關注比以往少了。現在的文化現實就是各種話語并存和沖突,這是常態,而且會越來越喧嘩。我們在前面談到,文化現實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文學批評的影響力一方面由于自身問題的局限,一方面受到各種話語的擠壓。文學批評有自身的邏輯,它無法和所有的話語去較量,但在傳播文學、思想、審美和人文價值方面是不可替代的。我偶爾也看看豆瓣和知乎等網站,這些網站也有學院批評的聲音。媒體只是載體,可以有大眾的聲音,也可以有精英的聲音,學院批評也需要借助媒體。我們都曾經想過,學院批評應該去影響什么,現在看來思路需要改變。新文學以來,批評粗暴化、批評歌頌化等現象從來沒有停歇過。歷史在積淀過程中會留下的是那些發自內心的聲音。
房偉:我注意到您非常關注“語言”的問題,例如,您認為,汪曾祺的小說語言,是接續了舊傳統與新傳統的獨特語言,您也曾談到文章學傳統的語言訴求在當下文本之中的缺失。請問,您如何將語言問題放置于文學史研究視野之中?對語言問題的思考,是否也影響到了您的小說和散文創作?
王堯:大學期間,我非常喜歡現代漢語和修辭學,但風生水起的80年代一直蠱惑我參與現實,因此選擇了現當代文學研究。最初對現代散文的研究,對我自己的語言修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青年時期寫的那些文章,現在看當然很幼稚,但從那時開始我似乎就注意自己的語言表達方式。讀現代批評家的文字,包括當代批評家如謝冕先生的文字,我確認這樣一種觀點,文學批評也應當有自己的文體特點。語言的問題,是文學的基本問題。汪曾祺先生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本身即是目的。汪曾祺先生說,這是他的老師聞一多先生說的。汪先生在《寫小說就是寫語言》中進一步說,語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樣,可以剝下來,扔掉。世界上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小說的語言是浸透了內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汪先生的這些觀點特別重要。我想補充的是,語言浸透了內容和思想,也浸透了作者的性情,個人的語言才會產生。汪曾祺先生的小說是當文章寫的,這就有了小說散文化的特點。短篇小說可以當文章寫,長篇小說則很困難。進一步說,寫散文、寫詩歌,也是寫語言。所以,將語言問題置于文學史研究視野之中是必要的。這方面我也做得不好。在研究汪曾祺先生時,我比較多談了語言的問題。我們需要重視作家對現代漢語的貢獻,重視文本如何因語言而成為經典。
房偉:您的學術研究工作,呈現出一種有別于一般學者的闊大面貌,可以說“小說研究與散文研究并重”,“文學史探索、史料建設與文學批評并進”。這種多維度研究視野,是否影響到了您在散文與小說領域的創作?有人認為,您是“學者作家”代表,您在小說領域的創作,是否可稱為“批評家小說”?或者說,是從更深廣的思想領域出發的小說實踐?
王堯:自古說術業有專攻。其實,我自己的領域并不廣闊,是因為人為的學術體制將研究領域和方向劃分得太細了,我只是在這樣的邊界里移動了幾步。新文化的傳統便是跨界研究、跨文體寫作,這個傳統后來式微了。這是我們今天都開始意識到的問題。我寫作散文的歷史,早于學術研究,這影響到我后來的文學批評文體。在某種意義上說,散文是現代學者基本的存在方式。你自己也是跨界的,既學術也創作。以我的理解,寫作者的學養、思想、文化都會對散文和小說產生影響。散文自不必說,學術寫作者的學養和思想同樣十分重要。我在《民謠》的后記里談到這個問題:小說寫作需要思想、學養和多方面的文化積累。我們不是把思想、學養和文化積累附加在小說中,而是說思想、學養和文化積累影響了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和把我握,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小說的故事、語言、結構和意義。換一種表述是,思想、學養和文化積累影響著我們對歷史、現實和人的理解。就此而言,批評家或學者寫作小說,如果他能夠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審美方式,他所有的資源將會提升他的寫作境界。
小說的寫作者可能有身份側重,這種身份會影響到小說的特質。但我認為小說就是小說,沒有“批評家小說”“學者小說”這樣的概念。
房偉:您的長篇小說《民謠》,出版后產生廣泛影響,尤其是激活了小說重新介入歷史與現實的能力。它既有非常先鋒化的形式探索,也有深刻又含蓄的內涵。您能否介紹一下寫作這部小說的初衷?今后您是否還會繼續小說創作?下一步有何打算?
王堯:對一個小說寫作的新手來說,這些鼓勵很重要。但我自己知道《民謠》的不足。我和所有的文學青年一樣,有小說家的夢想,即便到了這個年紀,我還有這樣的夢想和沖動。我一直想嘗試用多種問題表達我對一段歷史的理解,學術的,散文的,都嘗試過了,終于完成了小說。我在學術上的思路你是了解的,我想在另一個方向上展開,這就是虛構的方式。我在《民謠》的后記、《我夢想成為漢語之子》等創作談和一些訪談中,我都說了自己的想法,現在感覺說多了,太“批評家”了。我想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系,這個重建幾乎是我中年以來在各種文體的寫作中不間斷的工作。我在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和一段時間以來的散文寫作中,一直在詢問這個問題,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尋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這個過程中時隱時現。除了故事、細節、意象外,對語言和結構的摸索是我的重點。我曾經很長時間研究中國現代散文,也較長時間寫作散文,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寫作小說的語言。除了文學的淵源外,寫作者個人的心理、氣質和趣味影響了語言。寫小說和抽煙一樣,會上癮。現在寫作中的長篇小說試圖一步把故事、思想、語言、結構等融為一體,能夠完成到什么程度,自己沒有把握。我已經從碼頭上離開,我在另外一個時空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