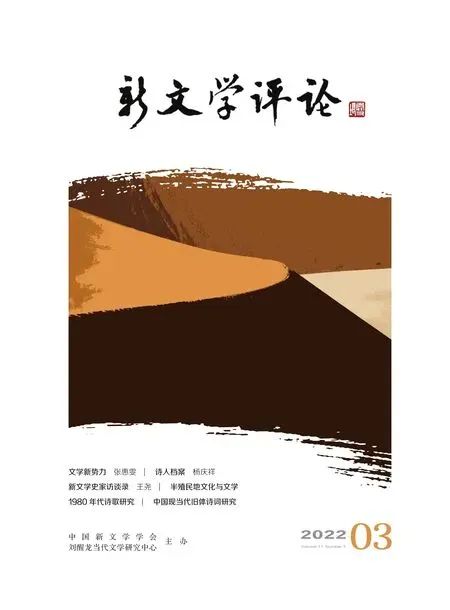如何克服“語言的腐敗”?
□ 楊慶祥
人類最早的語言是什么形態(tài)?始于何時?在何處誕生?直到目前這依然是無法準確回答的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人類最早的語言是舌語,曾經(jīng)在非洲的坦桑尼亞和納米比亞的一些原始族群中使用;還有一種更有意思的觀點是哨音,人類通過模仿動物尤其是鳥類的聲音而獲得一種信號語言,這種語言至今依然在西班牙加納利群島中戈梅拉島一帶留存。嚴謹?shù)恼Z言學者或許對這些“野觀點”不以為然,在更嚴格科學的譜系中,人類的語言當然是經(jīng)過長期的發(fā)展和訓練,是舌頭、咽喉、肺以及大腦共同進化協(xié)同合作的成果;但是神秘主義者也許另有他見,他們或許更愿意信奉那個人的判斷:“要有語言,于是有了語言。”
無論語言的起源和誕生如何的模糊不清——就像人類的歷史一樣,誰知道在那幽深的過去到底發(fā)生了一些什么!但是有一點確定無疑,人類使用語言,是為了更好地交流、表達和創(chuàng)造。口語與文字的結合被視為人類文明史的重要時刻,《淮南子·本經(jīng)訓》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套用維柯的話來說就是,屬鬼神的時代結束,屬人的時代來臨。
現(xiàn)代語言學的奠基者索緒爾認為語言的一大特征在于“約定俗成”,也就是“符號”和“意義”之間的聯(lián)系并非唯一,而是帶有某種任意性。這是古典語言學與現(xiàn)代語言學之間的本質(zhì)性區(qū)別。古典時代有一種單純的信仰,語言與意義之間的關系是神圣的、唯一的、不可隨意改變和扭曲,好的語言就是為了表達出那種唯一的神圣意義。因此在古典的譜系中,對語言的泛濫化、工具化有著高度的警覺。老子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辯若訥”。佛教的基本原則有“八正道”,其中之一是“正語”,所謂“正語”者,即遠離一切虛妄不實之語言。《馬太福音》的告誡則是:“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于那惡者。”
不過遺憾的是,人類從來就沒有按照智者們的要求來使用語言。就像價值與使用價值相符的商品只存在于理想狀態(tài)一樣,語言在人類的歷史上也幾乎是以一種現(xiàn)實貨幣的狀態(tài)出現(xiàn):膨脹,溢出,曲解,拜物。在語言的使用中,人類固然展示了其理智、洞見和創(chuàng)造的一面,但也有很多時候淪于盲目、愚蠢和譫妄。這種譫妄癥至現(xiàn)代而達其高峰,而其高峰之高峰則有二。一是將語言視作意識形態(tài)的載體,并將其徹底工具化為一種洗腦術,納粹德國在這一點上堪稱表率。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克萊普勒用詞匯表的形式深入分析了納粹是如何偷換概念和重塑意義,將語言改造為一種貧瘠、夸張、假大空的口號和標語。比如英雄,它“原本是一個促進人類事業(yè)的行動的實施者”,但是第三帝國的宣傳語言卻將其濫用于所有參與殘忍侵略戰(zhàn)爭的人,并為此頒發(fā)眾多的獎章。對此克萊普勒痛心疾首地批判說:“當英雄主義越是沉靜,越少面對公眾,越少有裝飾性的時候,才越是純潔,越具有意義。……對于正義的、真實的英雄主義,納粹主義從來就沒有公開地提及過。由此,它篡改了整個概念,并毀壞了其名聲。”出于對這一語言控制術的抵抗,后結構主義者們強調(diào)語言自身的革命,并以游戲的方式來解構一切確定的價值和意義,其經(jīng)典表達類似于蒙特·羅賽特在《結構主義者的早晨》中的戲仿——“當我說愛你的時候,事實上我本不應該這么說,對不起,我將把這句話收回,我將從頭開始;我又說了一句我愛你,但是經(jīng)過再三考慮,我似乎也不應該這么表達。”不過可見的歷史事實是,后結構主義者的這種“革命”并無顯著的政治實效,它倒是在大眾文化的層面收獲了層出不窮的“跳蚤”:廣告語、辯論賽、傳銷方案、深夜電臺、綜藝節(jié)目以及脫口秀……
我們似乎沒有辦法逃離語言通貨膨脹的困境,語言的暴力和控制傾向借助發(fā)達的現(xiàn)代傳媒擴大了它的領地,通過無限的增殖、賦值和單一性野蠻繁衍,如帕斯所言的“語言的腐敗”已然構成我們這個時代最頑固同時卻被視而不見的事實。憂心忡忡的哲人們將改變的可能寄望于詩人,海德格爾流傳甚廣的一句話是:“語言是存在的家,詩人是這個家的看門人。”阿蘭·巴丟則認為:“詩歌是一個終止點,它使語言停留在自身之內(nèi)。反對令人生厭的無所不見和無所不言——就是說,炫耀,放松和評論一切。”當無法找到那個“恰當?shù)恼Z言”來表達和言說的時候,詩人和哲人寧可選擇沉默。一個經(jīng)典的案例是,1966年7月24日,德語世界最重要的詩人保羅·策蘭與現(xiàn)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海德格爾在弗萊堡大學相遇,這一天,策蘭受邀在大學進行了一場詩歌朗誦會,而海德格爾是聽眾。第二天,策蘭前往黑森林中心參觀海德格爾的著名小屋——《存在與時間》即完成于此。據(jù)記載,兩個人隨后在小屋附近的沼澤地散步,但僅僅走了一半,就像“兩枝互不相干的蘭花”分道揚鑣。這次相遇是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關鍵性時刻,其蘊含的問題和意義值得反復探究——與本文主題相關之處在于,無論是策蘭還是海德格爾,都可能意識到了通用性的語言無法表達自己。于是,在這次相遇中,詩人選擇了詩歌,而哲人,干脆選擇了“不說”。或者更進一步,如果考慮到海德格爾對語言作為一種本源性存在的敏感性,他的選擇也許不僅僅是出于怯懦或者逃避,而是主動讓渡自己言說的權利,讓詩人“去說”,因為詩人的語言,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是現(xiàn)代社會存在的唯一“圣言”:
給這個本子寫下
那行關于
一個希望的字,希望
一個思想家今天
把心里的
話
說出來
這是策蘭在相遇后寫的一首詩,思想家并沒有說出來,詩人其實也難以說出來,在重重“偽語言”的包圍中,改變和轉(zhuǎn)化已經(jīng)變得異常困難。在策蘭另外一首詩歌《圖賓根,一月》中,詩人想到了也許可以采用另外一種方式:
要是
要是有一個人
要是有一個人在今天,來到這個世界上,
留著族長們的
光之胡須:他只能,
如果他談論這個
時代,他
只能
反反復復地
咿咿
呀呀
這另外的一種方式就是“咿咿呀呀”——初生嬰兒式的語言,帶有某種原始性的語言,拒絕將語言作為宣傳、表演、嘩眾取寵的工具的語言。它可能是舌語、眼語、唇語或者哨音,也可能是一種“贖回”(redeem)、“覺醒”(awaken)和“轉(zhuǎn)化”(transfer)。借助這一神秘的“咿咿呀呀”,詩人不負所望地給我們提供了啟示。
如是我聞,在最理想的語言狀態(tài)中,我們不是需要說得更多,而是需要說得少一些,更少一些。這樣,我們才能夠從現(xiàn)代社會泛濫成災的語言洪水以及被這洪水裹挾的立場、價值判斷、集體癔癥以及精神控制中抽身出來。并非每個人都是思想家或者詩人,但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well-saying”的權力和能力,我們所要謹記的無非是兩條戒律:
第一,“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wǎng)子里”。
第二,“當初連個名字都沒有的時刻,我們肯定聽到了一切,也說出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