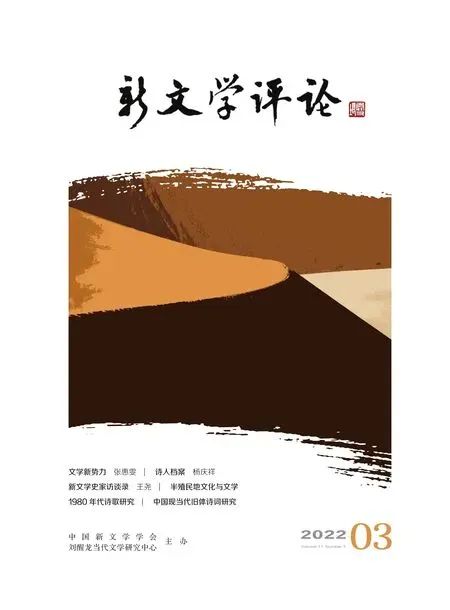主持人語
□ 張清華 王士強
作為詩人的楊慶祥與作為學者的楊慶祥確有很大不同,學者楊慶祥是理性、深刻、淵博的,而詩人楊慶祥則是感性、隨性甚至虛無的,兩者之間或有社會性與個人性、入世與出世之間的區別側重。應該看到,楊慶祥首先是一位詩人,其后才成為一位學者;詩人的一面于楊慶祥而言是更為基底、原生的部分,包含了進入其精神世界深處的秘徑和密碼。學者的楊慶祥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80后學者的代表性人物;而詩人的楊慶祥一定程度上是被遮蔽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楊慶祥為詩長于感受,他敏感、細膩、頹唐,不確定大于確定,猶疑大于確信,詩中呈現更多的不是強大的主體性,而是有限的主體性或者審視與懷疑的主體性(當然,這背后仍然包含了主體性的強大和自信,不過無論如何,其中的主體已然不是單向度、單極化的主體,而有著更復雜的內蘊)。一定程度上,楊慶祥詩歌表達的是一種“充分現代”的狀況,它與“前現代”、與“初級的現代”均有不同,而與平面、消解、游戲的“后現代”也有不同,這是一個包含了自省、自否而又拒絕自我消解的充分現代的主體在面對今日中國的獨特生存狀況所進行的書寫,是深具當代性的寫作。楊慶祥對于當今世界、當代生活有著深廣的關切和深入的思考,思想性和知識性也素為其所長;但在詩歌中,他更多的是回到了生活本身,回到了個我與本心,呈現了自我與生活、與世界、與他者、與本我的遭逢。他詩中呈現的不是簡單的愛或恨、契合或齟齬,而是更為復雜混沌的臨界與復合狀態,這是最具可能性,也最具詩意的狀態。楊慶祥的詩是感性的,具體、直接而又豐饒、含蓄,包含了真誠與反諷。它不是觀念性的,而包含了觀念;它不是知識性的,而包含了知識;它不是反映論的,而包含了反映;它不是深度模式的,而包含了深度……這種“感性的復合性”成為楊慶祥詩歌顯著的特征之一,難于被定義,而又充滿詩意的魅惑。
楊慶祥的詩是向內的、幽深的,他直面內心的深淵,并不試圖拯救或抗爭,而首在表達自己真實的感知、感受、所思所想,傳達個我與私我的真實處境。與學術研究中的理性自我、公共性自我相比,詩歌中的楊慶祥放飛了自我,將自我深度呈現出來(當然這個自我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角色性、戲劇化、虛擬性的成分)。他的詩重在表現“一個人的世界”,自然,如前所述,他的創作同樣具有外向性和現實關切,這時所表現的則是“一個人與世界”。而無論“一個人的世界”還是“一個人與世界”,其重點都在“一個人”,都在獨特的、這一個的“我”。楊慶祥的詩歌語言獨具個人特色,生動、自然、精煉而充滿彈性,沒有匠氣和經院氣,他以一種“曖昧、反諷、哀告”的語言反對著這個時代的話語暴力和思想宰制,是對于日益板結、僵硬、蠻橫的現代漢語的突破和打開,探尋著現代漢語新的路徑與可能性。
在新近出版的詩集《世界等于零》中,楊慶祥認為所有的詩歌寫作都可以說是“從零到零”:“從零開始,意思是指詩歌的起源不可確定,到零結束,意思是指詩歌的意義永遠無法窮盡。真正的詩歌就在這兩個零之間劃出一道無法測量的曲線,這個曲線的長度與詩歌的生命力成正比。”楊慶祥的詩正是這樣一道“無法測量的曲線”,它面對“零”、面對空無、面對存在、面對語言,寫下屬于我們時代的詩歌的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