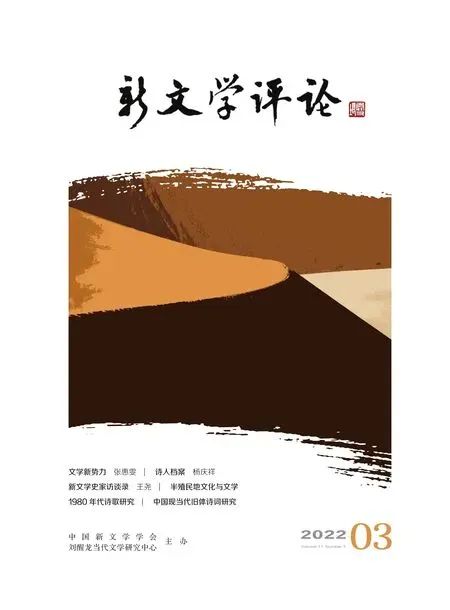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故事
□ 張惠雯
我在某本雜志上讀到一首翻譯詩,描述在一場大雨中,“她”駕駛,而“我”在一旁注視著她……它在我腦海里立即轉化成一幅可見的畫面。詩人描述說車子穿過暴風雨如同穿越河流,我覺得這里面有某種令人震顫的美感。后來,它成了我的小說《暴風雨之后》里的一個場景。我有很多類似的經歷,我覺得它說明讓小說在作者心中萌芽的可以是任何東西:詩里的某句話、一首歌的旋律、一個你在街頭看到的陌生人的影子、一則傳聞的一鱗半爪……
作者在寫作中當然也會經常動用自己的記憶和經驗庫存。譬如,在我最近出版的小說集《飛鳥和池魚》里,對故鄉的描述中,我肯定動用了相當多的記憶和經驗。但構成其中每個故事的骨架的東西,多半來自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故事。當我寫《在南方》里面的移民故事時,他人的故事就更為重要了,因為我自己在美國的生活就是美國人所說的家庭主婦的生活,大部分的活動空間就是家——我很難基于自身的經歷、故事來寫作。本雅明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拉丁文中,“文本”也是“編織”的意思。寫小說的確就像做編織,你要把從外面獲得的見聞,那些相互并無關聯的人事片段,用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的絲線全部連綴起來,讓細節得以填充,使整體致密而流暢。
下面,我就以《雪從南方來》和《玫瑰,玫瑰》的創作談來闡釋這兩個寫作問題:第一,找到那粒能生發、成長出小說的種子;第二,把他人的故事轉化為自己的小說。
一粒種子——《雪從南方來》創作談
我們此處不談什么創作手法,而是談談“燃起”這篇小說的一星火花。
我想起亨利·詹姆斯在他最好的長篇小說《使節》的自序里有關“微小的暗示”的那段話:
其靈感來自微小的暗示,而這么一點點暗示的種子又落入土中,發芽生長,變得枝繁葉茂,然而它依然可作為一個獨立的微粒,隱藏在龐大的整體之中。
讀到這句話時,我忍不住用圓珠筆畫一條波浪線,做了個標記,因為它讓我如此心領神會。一點微小的、暗示的種子落入土中,長成一棵樹,這就是我那些小說產生的過程。我去年出版了一個小說集《在南方》,里面將近一半的小說產生所依賴的“微小的暗示”都來自同一位朋友講述的故事。作為一位批評家,陳瑞琳對故事有很好的敏感度,同時她又活躍于休斯敦的華人移民社交圈。有時候她一個電話打來:“惠雯,我要給你講幾個故事。”然后,她講我聽。有一次我們約在咖啡館講故事,我帶了一個筆記本,她一口氣講了六個故事。這些故事繁雜、耀眼、情節曲折,而我的任務是在其中發現那個具有意義的“微小的暗示”。同樣,《雪從南方來》也來自這么一個暗示。
2021年10月的某天,一位聲稱喜歡我的小說的人從另一個城市來到波士頓。我一般不愿見陌生讀者——那種會面的尷尬可想而知。但由于此人是一位朋友的朋友,她特地囑托,我似乎推辭不了。
我和那位先生約定在我家附近的咖啡館碰面。這是一次平淡無奇而且匆忙的會面,主要是他在談喜歡讀哪些小說,中間插入了有關自己生活狀況的簡單介紹,說到自己以前有過兩次婚姻(目前是單身),和第一位妻子有個女兒,女兒年幼時他就一個人帶她來到美國。他坦承第一次離婚是因為和妻子完全合不來,而當他想要說起第二個妻子時,停了一下。我誘導他說下去:“那么第二個妻子是來美國后遇見的?”“對,”他說,“第二個妻子我喜歡,但我女兒不喜歡,她們處不來,只能分了……”從他不自然的神情看,我覺得我們不該再談這個話題了。我們又扯到別的他喜歡的作者,然后匆匆喝完一杯咖啡告別了。但他關于第二個妻子的那句話留在我的腦海里,成為這次會面的意義所在。
我覺得這個“舍棄”的故事里蘊含著強大的中國式家庭倫理,這倫理本身存在著頗有悲劇性的荒謬:一個成年人的感情生活竟然很大程度上被他們未成年的子女所支配,而成年人卻要承擔其后果。例如,小說中的父親失去了真愛,在女兒長大離家后注定孤獨終老……但同時,我也想到,身處那樣一個處境,究竟有幾個中國父親會做出和他不同的選擇呢?對西方人來說,這幾乎不是什么問題,因為他們的自我意識很強,覺得照顧好孩子是責任,但選擇伴侶是自己的事兒,二者涇渭分明;但對慣于為子女犧牲、奉獻一切包括自我的中國父母來說,這簡直是個哈姆雷特式的難題。從邏輯上說,這也不是問題;從情感和主人公的倫理考量來說,卻是大問題……但小說恰恰不愛講明白的道理和邏輯,它偏愛的是矛盾、困境和偶然性。此外,它也恰好是我近年來喜歡的主題:婚姻、情感、家庭關系。確實,我這些小說不大可能受到太年輕的讀者的喜愛,它更適合成年人尤其是已經結婚的中年人來讀。
我沒有立即去寫,但我在腦海里做了標記。直到兩三個月后,接近農歷歲末的冬寒時節,我覺得可以動筆了。還有什么比“虛構”更讓人激動的工作嗎?基于一句話而構造出與之相關聯的整個世界!合適的場景是波士頓,這樣我就能用周圍熟悉的環境畫出不失真的布景;既然是寫一個即將孤獨終老的人,那么把季節選在冬季似乎更有些象征意味兒,況且也是我身處的季節,景色和感覺都直接而新鮮;最后,我回想起波士頓的第一場雪,那也是整個東岸的第一場雪。那天下午,下雪的消息先從紐約傳來,然后是康涅狄格州在下雪,然后是羅德島,最北邊的波士頓反而雪來得最遲。而在東岸下第一場雪之前,南方的休斯敦(也是我住了將近八年的城市)已經降過一場罕見大雪。所以,我那時在朋友圈寫了一句話:今年的雪好像從南方來。至此,我給我的小說找到了題目——雪從南方來……我看著我的種子落入土中、發芽生長。
現在,人們喜歡感慨說:現實比小說更精彩。這個“精彩”往往指曲折離奇、炫目刺激的效果。不過,真把現實中的各種精彩事件和高明段子搬進小說里去,那小說倒未必好看。小說的精彩和現實的精彩是不同的。有時,精彩紛呈、光怪陸離的現實也許會令作者迷失其中,而一個“微小的暗示”,宛如人性中一點兒微暗的火,反倒可能照亮藝術的想象力。小說當然可以選擇龐雜地呈現,也可以選擇往深處、細微處行走。我選擇的方向是后者。作為一個寫短篇小說的人,我知道我尋找的只是一粒有生機的種子,而不是一棵大樹。
他人的故事——《玫瑰,玫瑰》創作談
我總是需要別人的故事,因為我自己的生活平淡安適,毫無戲劇性可言。這對我來說倒是件幸事,我并不愿意為了小說題材而讓自己的人生充滿波蕩起伏。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藝術家的人生應該充滿悲歡離合、大起大落的傳奇,或者其本人至少有諸多異于常人的品行。如果這樣的話,我活得很不夠藝術。那么退而求其次吧,與其活得藝術,我更希望寫得藝術。何況,還有那么多別人的故事可寫。我相信,脫離了作者自我中心式的展示欲和傾訴欲,小說依然能很好地寫下去。
我不是那種閉門靜修、格調高冷的作者。我喜歡與人交往,喜歡聽人們講各種各樣的生活上的事、分享八卦。有朋友批評我愛聽沒有嚴肅意義的閑話,我想那是因為他并不真正了解小說的精神里的某一方面,其實包含著八卦精神的精髓——對別人的故事、別人的狀況,以及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豐富性的發自內心的興趣。在此,談論八卦的目的不是像長舌婦們那樣傳播謠言,評判、中傷他人,而是為了發掘出某種隱藏在這些事件背后的東西。因此,我們不會像娛記們那樣僅僅關注事件的行動層面,而是會深入這些行動的動機層面。我很難想象簡·奧斯汀會拒絕傾聽或談論八卦,事實上,她和她姐姐的書信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談論社交圈、鄰里鄉親們的八卦。我也無法想象沒有足量巴黎社交圈軼聞(“八卦”較為文雅的稱呼)的支撐,普魯斯特如何寫他的“追憶”。如果我們用稍微幽默一點兒的視角(而非嚴肅苛責的目光)去看,我們就會明白,八卦和廢話一樣,是生活中較少的有趣的事物之一,是可供小說家觀賞、琢磨的社會風俗畫。
如我的很多小說一樣,《玫瑰,玫瑰》也是“別人的故事”化為了“我的小說”,它基于我的一點兒觀察和一個聽聞,二者之間沒有關聯。
一點兒觀察來自我在朋友圈看到的幾組照片。幾年前,有位朋友去探訪老友,賺了錢的老友夫婦在海邊買了座山。在朋友發到朋友圈的圖片里,除了海邊風光和豪宅外,我也注意到她拍的室內景觀:中式家具、繡花坐墊、餐桌上鋪著藍印花布……第二天,她在朋友圈展示了早餐:茶葉蛋、豆漿、八寶粥、咸菜。第三天,她的朋友圈更具有戲劇性:她被朋友夫婦熱情地帶去海邊搭建的一個棚子里打太極拳……從我朋友的年齡,我推斷這對夫妻也不過五十來歲,但他們倆樣子都很顯老,顯然過著一種注重養生的、退休老人般的生活。而這棟房子的外景和內景、其所在的大環境和人的生活方式構成了一種怪異的對比,這給我留下了印象。
一則聽聞則是我從另一位朋友那兒聽到的小故事。她提到的那位女性的遭遇有點兒接近《玫瑰,玫瑰》里那位女主人公:嫁人多年,丈夫一直有性功能障礙疾病。但因為種種外人不可知的原因,這對夫妻并沒有離婚,保持著一種相安無事又相互疏離的關系。這些外人不可知的原因,這種關系對于兩個人尤其是女人身心的影響,難道不會比每日政治新聞更值得人去思考、去理解嗎?
在我的意識里,那些有點兒喜劇感的朋友圈圖片和這對夫妻有些悲劇性的關系之間慢慢產生了關聯,似乎它們具有某種相似的東西,這種相似性、關聯性不一定是邏輯上的,而可能僅僅是它給予人的感覺,譬如那種疏離、隔絕的氣質。讓不相關的人與事與景物的各種碎片之間產生聯系,并且嚴密地黏合在一起,使其看起來仿佛本來就是個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這大概也是小說家必須掌握的技能之一。于是,當我想要寫這么一個多少有點兒怪異的小說時,我選擇了那個仿佛與世隔絕的海邊豪宅作背景。至于題目,它先于正文出現,成為一種象征。那些干燥的玫瑰花的意象,統攝了這篇小說的氛圍:美麗、怪異、枯竭、孤絕,散發著一絲命運的殘忍氣息。我選擇了外人視角來描述這個故事,以便它具有印象的模糊和多義性,從而保持小說本身應有的一點兒神秘感。小說里的作家“我”只是個外來的觀察者,讀者通過“我”的眼睛去觀看那對夫妻、那種生活狀況,同時也觀察了“我”,但“我”卻不可能給予讀者任何答案。
這也是我一貫的做法——我不想在小說里販賣什么離奇故事,更不想指明什么道理。那種離奇故事,你在小報的社會新聞版或是網絡頭條可以一口氣讀十個。至于道理,難道微信圈各種有關人生道理的雞湯還少嗎?雖然我的小說常常拿別人的故事的一鱗半爪做材料,但我恰恰不希望讀者在讀過后只是感到津津有味地聽了個別人的故事。我想給讀者的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閱讀過程,我希望讀者在此過程中感受到一些東西,無論是關于審美的,還是關于生活與人性的,無論如何,那都是一種自我發現。
最后,應該提到美麗的新英格蘭地區。它指的是美國東北部毗鄰加拿大的六州,包括我所居住的馬薩諸塞州以及我在小說中寫到的以風光著稱的緬因州。我去過美國的很多地區,感到我最喜歡的是這里。它的風景并不是大峽谷式的壯麗、奇詭,而是秀拔、優美、雋永,這一地區到處是森林、湖泊、溪流、綿延的綠野,這種美更具有一種生活氣息,令人如同置身于童話世界。關于這種美,我在小說中也有描述。以前住在得克薩斯的時候,我很少到戶外活動,這固然和大部分時間天氣炎熱有關,但也因為確實沒那么多去處。但現在周遭到處是幽靜所在,仿佛林中生活,我就喜歡上了散步,喜歡觀察植物的變化、動物的活動,對自然界也更為敏感。踩著厚厚的松針穿過林中小徑給人一種心靈的滌蕩,這和美國南方那種潮濕、悶燥的感覺完全不同。這一地區盛產思想家、詩人和自然主義者,應該并非偶然。以我自己的感受來說,南方文化仿佛是神秘地交織糾纏的熱帶灌木和藤類,北方氣質則像挺拔的參天松杉。美麗的新英格蘭好像打開了我的心胸,令我從一個盆栽植物愛好者變成了森林的愛好者。
常有人問起身居國外是什么感受,我覺得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詩句很貼切地描述了它:
身居國外是美妙的,有一種冷淡的快樂。
黃色燈光點亮塞納河岸邊的窗戶
(那里有真實的神秘:他人的生活)
這種異鄉人的感覺和寫作者的身份有某種相通之處。寫作者無論生活在哪里,其實多多少少都像個“身居國外”的人——他既有異鄉人的好奇心,同時也保持著一定程度的陌生感和疏離,習慣于旁觀、揣摩、沉思。我一直認為,作家不能和所處的時代、身邊的人事貼得太近,否則你就無法跳脫出來,無法具有看清某些東西所需要的距離感。這種興趣、好奇心與陌生疏離感結合起來,也許就恰好產生了詩人所說的“冷淡的快樂”和“真實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