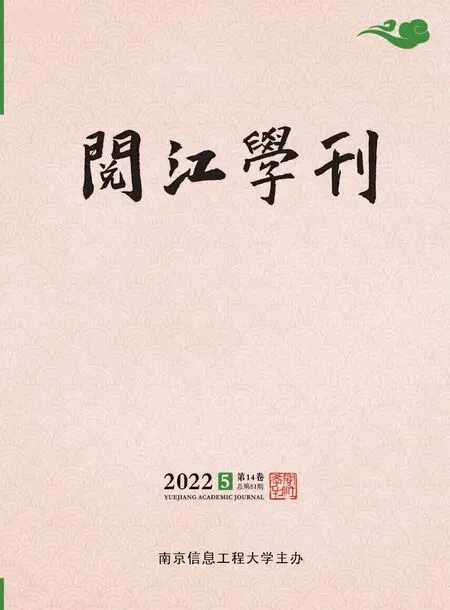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管理研究新議題
戚聿東
當下,以ABCD(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底層數字技術驅動的數字經濟正在全球蓬勃興起。2021年,全球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為38.1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為45%,其中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為27.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為55.7%。中國2021年的數字經濟增加值為45.5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為39.8%,規模同比名義增長16.2%,在疫情沖擊和全球經濟下行疊加影響下,中國數字經濟依然保持高增長,為穩增長和穩就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數字經濟的崛起,對人類生產、生活和生態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1)習近平:《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求是》,2022年第2期。在數字技術的驅動下,平臺經濟、共享經濟、數字貨幣與數字金融、“四眾”模式(眾創、眾包、眾扶、眾籌)、三R產業(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混合現實)與元宇宙、產業互聯網等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層出不窮、日新月異。伴隨著數字產業化的發展與繁榮,產業數字化的發展也方興未艾,使得經濟社會呈現出“三新”特征,即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和新經濟結構。與工業經濟相比,數字經濟在眾多屬性上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新屬性、新特征。
一、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的屬性差異
從企業形態來看,工業時代的企業都是典型的單邊市場,即單一企業作為產品和服務供給方的市場形態。數字時代下的企業是典型的雙邊或多邊市場,數字平臺鏈接買賣雙方及其他市場主體,圍繞平臺組成了一個雙邊或多邊市場,構成一個生態圈。在這種情況下,數字企業不同于傳統企業單一的技工貿或購產銷功能,而是積極拓展受眾,精準供需匹配,提供工具和服務,制定規則和標準。
從基礎經濟規律看,工業時代驅動企業的經濟規律是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正如經濟史學家錢德勒所說,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在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的經濟規律讓位于梅特卡夫定律和交叉網絡外部性。所謂梅特卡夫定律,是指網絡的價值在于網絡節點數的平方。如果網絡中有n個節點,則每個節點都可以與其他n-1個節點發生作用,總共獲得n×(n-1)個單位的價值。因此,該網絡的總價值為n×(n-1)。當n很大時,n-1近似于n,網絡的總價值可以表示為n的平方。由于價值來自連接而非節點,任何兩個節點只能算為一個連接,因此網絡價值的正確表達式應為n×(n-1)/2。當世界上只有一部電話時,這部電話的價值為0;當世界上有2部電話時,有1個連接存在,網絡的價值為1;有3部電話時,有3個連接存在,網絡總價值為3;有4部電話時,網絡總價值為6。梅特卡夫定律認為,每個新入網的用戶都因為別人的入網而獲得了更多的信息交流機會。對數字企業而言,首要的任務就是利用各種營銷手段(如免費、補貼),迅速吸引大量用戶加入網絡,建立足夠大的用戶安裝基礎,隨著使用人數的增加,不論是老用戶還是新用戶,效用價值都會呈爆發式、指數級增長,取得先動優勢。這就要求平臺企業首先要做大用戶群,突破關鍵臨界點,形成正反饋效應。所謂交叉網絡外部性(cross-side network effects),是指平臺市場一邊的使用者越多,平臺對市場另一邊使用者的價值越大,反之也成立。比如,在購物平臺中,買家數量越多,平臺對賣家的價值就越大;同樣,賣家數量越多,平臺對買家的價值也越大。這種情況就是所謂“雞生蛋、蛋生雞”的“雞蛋難題”(chicken-and-egg problem)。
從關鍵要素看,工業時代典型的生產要素是“薩伊三要素”即勞動力、土地和資本。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除了薩伊三要素以外,管理、信息、科技相繼被看作生產要素。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被看作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既然是生產要素,就會被納入生產函數,參與價值創造過程,按照生產貢獻參與分配。
從收益成本習性看,工業時代的企業成本習性是典型的邊際成本遞增和邊際報酬遞減。在數字時代,企業的成本習性演變為邊際成本遞減甚至為零,同時邊際報酬遞增。這是因為,工業企業一般都存在巨額的固定成本和原材料、零部件等變動成本,其中變動成本一般與產銷量正相關,而數字企業則不同,雖然存在巨額研發成本,但拷貝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就使得邊際成本呈現遞減趨勢,進而邊際收益呈現遞增狀態。
從盈利模式看,工業企業的盈利模式可以概括為“羊毛出在羊身上”,買賣雙方采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交換模式。數字企業的盈利模式則表現為“羊毛出在狗身上,豬買單”,是一種被免費模式掩蓋的間接盈利方式。例如,騰訊公司的微信是免費使用的,憑借產品不斷迭代和免費機制,微信及WeChat的月活躍用戶數目前已經達到12.9億。如此巨大的用戶基礎和流量吸引著大量廣告,因此廣告收入成為騰訊公司的重要利潤來源。同時,微信的海量用戶也便于為其他業務(如微信支付)“引流”,進而通過微信支付的商家端獲取巨額利潤。
從成長路徑看,在工業時代,企業的成長路徑是線性的,即從小微企業、中型企業、大型企業再到巨型跨國公司,整個成長過程非常漫長,可能需要經歷上百年的原始積累。但是,在數字時代,這一歷程被顯著地加快了,數字企業呈現爆發式、指數級的成長,從初創企業到中型獨角獸、大型獨角獸,再到巨型超級平臺,多則一二十年,少則兩三年,這就極大地縮短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歷程。
從競爭屬性看,傳統的市場競爭一直強調產品和服務的競爭,不管是“人無我有”還是“人有我廉”,競爭的關鍵一直強調資源基礎上的核心優勢,即所謂“沒有金剛鉆,就別攬瓷器活”。在數字時代,數字企業更強調流量為王,數據制勝,突出強調用戶安裝基礎上的動態能力。從工業時代的核心優勢觀轉向數字時代的動態能力觀,這是傳統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時面臨的最大挑戰和考驗。如果不能順利實現這一轉變,即便是百年名企,也可能說倒閉就倒閉,企業甚至可能到死都沒弄明白為什么會如此。這意味著隨著工業化時代向數字化時代的轉變,賽道變了,規則變了,打法變了,企業只有與時俱進地轉型升級,做好各方面各環節的適應性轉變,才會贏得“數字競爭”,如果缺乏動態能力,就會招致“贏了天下輸了時代”的后果。
二、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管理研究新議題
數字時代的來臨和數字企業的誕生,在戰略、目標、產權、治理、研發、生產、商業模式、組織結構、企業競爭、戰略競爭、供應鏈、物流、產品開發、定價、渠道、促銷等各個方面都給傳統的企業管理帶來了新挑戰。無論從理論價值還是現實意義來看,這些新議題都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第一,在戰略層面。隨著數字時代的來臨,傳統企業面臨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這已經成為擺在企業面前的不二選擇和最大戰略,也是當下企業要做的最“正確的事”。企業如果無法貫徹執行這一戰略,那么過去的成功可能會孕育今天的失敗,過去的經驗會釀成今天的教訓,過去的優質資產會成為劣質資產乃至負資產。這里需要特別強調,轉型不是轉行,因為數字技術作為一種通用目的技術(GPTs),適合于各行各業,適合于所有企業。但轉型的模式和路徑存在差異,如何從此岸通往彼岸,是擺在企業面前頭等重要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第二,在目標層面。隨著數字企業的崛起,企業目標成為一個重要話題:到底是賺錢還是值錢?從長遠來講,賺錢和值錢是統一的,但是我們在現實當中可以看到,處于發展階段的企業特別是數字企業非常值錢,但并不賺錢,甚至是虧損的。與之相反,如金融、房地產等行業的企業非常賺錢,但是不怎么值錢。如何看待企業賺錢和值錢脫節的現象,讓值錢建立在賺錢的基礎之上,最大化地實現二者統一,需要數字企業和傳統企業共同思考,因為這個總目標會決定一系列次級目標和后續眾多環節的安排。從價值創造流程的角度看,企業價值最大化比利潤最大化的層次更高,是一個更為根本的目標,但是從長期來看,值錢也要建立在賺錢的基礎上,否則,單純追求值錢就有可能演化為泡沫甚至危機。
第三,在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層面。傳統企業在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方面都遵循股權平等、所有權與控制權對稱的原則,即同股同權同利。但是數字企業中流行雙重股權結構和有限合伙制。也就是說,在數字企業中,將普通股分為優級股和一般股,優級股的投票權往往是一般股的n倍,少則十倍,多則數百倍。這就形成了創始股東相對于大股東擁有超級控制權,進而出現了同股不同權、不同利現象。這種情況使得工業化時代的“誰出資、誰所有、誰控制、誰受益”面臨極大的挑戰。在未來的數字化時代,很可能更強調“誰創造、誰所有、誰控制、誰受益”。
除了雙重股權結構和有限合伙制引發的股東間關系變化之外,數字企業的各類利益相關者都在深度參與數字企業的內部治理,高管股東化、用戶員工化、員工創客化等現象已經屢見不鮮。這表明,除創始股東以外,其他利益相關者也正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深度參與公司治理結構。比如,很多數字企業將用戶員工化,海爾、滴滴、小米等都把一些忠誠的優秀用戶發展為公司員工,這樣就輕易地打破了企業與市場的嚴格界限。高管股東化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傳統“委托-代理”關系下企業所面臨的“激勵不相容”問題,員工創客化很大程度上貫通了企業與市場的邊界。
第四,在競爭層面。數字經濟的崛起意味著顛覆性創新、替代式競爭,傳統行業之間的邊界因此變得模糊。行業、企業、產品等眾多概念都將被重新定義。數字企業都在精心構筑自己的生態圈,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正在演變為生態圈之間的競爭,后者也成為平臺企業競爭的一種最高形態。頭部企業更加強調競合關系,競合關系正在成為企業在競爭層面追求的一種最高境界。
第五,在企業內部管理方面。網絡化、扁平化的組織結構正鮮活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海爾集團通過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使整個集團變成了數千家小微聯合體。正如張瑞敏所說,“人人都是CEO”,海爾的“人單合一”模式使得整個組織的結構呈現扁平化、網絡化特征。也如華為公司總裁任正非所說,“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去指揮戰斗”,這說明組織結構扁平化、網絡化正在大踏步地變成現實。組織模式的變化倒逼營銷模式的精細化、精準化,數字營銷正在成為一種時尚。通過大數據對用戶進行多維度的精細畫像,可以實現對消費者的精準營銷,產品、價格、渠道、促銷都可以訴諸個性化表達。營銷模式的精細化精準化倒逼產品設計的版本化、迭代化。以數字產品的設計為例。沿著數字產品的屬性以及時間和空間維度,數字產品的設計創意是無限的。企業可以先設計出一個最復雜版本的數字產品,然后不斷精簡屬性,因為邊際成本為零,所以可以形成眾多的數字產品版本,在此基礎上不斷迭代。迭代過程更強調沒有完美的產品,完美的產品永遠在路上,完成勝于完美。如果等到產品完美時再推向市場,那么這個市場早已被競爭對手“鎖定了”,這就是數字產品市場競爭的特點。產品版本化迭代化倒逼生產模式的模塊化、柔性化。基于工業互聯網的智能制造方興未艾,在數字時代,產品的制造流程沒有改變,但是各個流程的實現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進行生產。”(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4頁。所以,傳統的線性生產模式正在通向基于工業互聯網的智能制造模式,從以企業為中心真正走向以市場為中心,從福特制的大規模生產、豐田制的大規模定制,最終走向海爾制的個性化定制,這是生產模式最本質的變化。生產模式倒逼研發模式的開源化、開放化,進一步倒逼用工模式的多元化、彈性化,等等。總之,數字經濟給傳統企業帶來了全方位、各環節、全周期的變化,企業轉型升級不是某一方面的轉型升級,而是全面深刻的系統化變革,這就要求秉承“系統決定成敗”的理念,把戰略和執行有機結合起來,對模式選擇與路徑進階進行優化設計。
三、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管理研究新愿景
隨著數字技術的日益成熟,所有行業和業務都要用數字化重新做一遍。從企業角度看,數字化的滲透與賦能是全方位、全流程和全生命周期的;從產業角度講,各行各業都面臨著數字化的沖擊和挑戰,產業數字化特別是工業互聯網面臨一片新藍海;從社會角度看,數字技術向社會各個領域進行滲透和賦能,如數字醫療、數字教育、數字鄉村、智慧城市、數字政府等,前景廣闊;從科學研究角度看,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的內容也都可以用數字化來重寫一遍。
那么,數字經濟給我們的經濟學、管理學究竟帶來了什么挑戰?國際上有兩種極端的爭論:一種是夏皮羅和范里安所提出來的“原理沒變,只是案例變了”,另外一種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所提出來的“全部經濟學因為互聯網都要重寫”。這顯然是兩個極端,我們更多的是游走于他們之間。其實,在數字經濟時代,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管理學,基本假設、規律、方法、內容、命題等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經濟學、管理學仍然具有一般性。但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在驅動規律、關鍵生產要素、基于工業互聯網的智能制造、網絡化組織、價值最大化目標、動態競爭的屬性、指數級增長的原始積累、生態圈的產業組織等方面,都呈現出了不同于工業經濟時代企業的運行特征,這樣就局部改寫了一些經濟學、管理學的原理及其實現機制。這就要求管理學界與時俱進,搶抓研究機遇,譜寫數字經濟時代管理學的新篇章。如果我們的管理學能夠立足于數字經濟和數字企業發展,也就有可能借著這個機遇實現中國管理學的迅速趕超,有利于中國管理學贏得與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世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