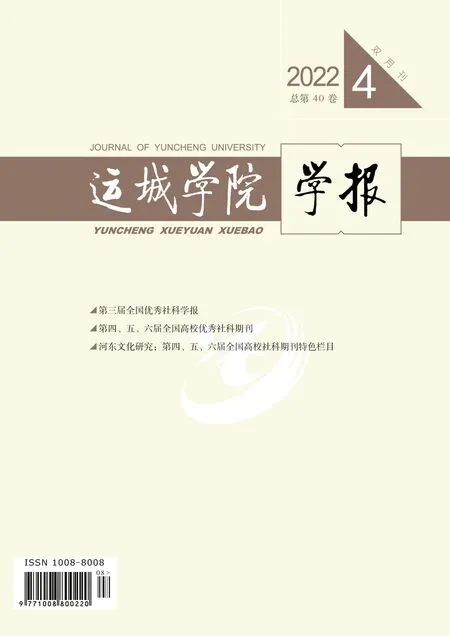郭璞奏疏文的政治思想探究
蔣 繪 燕
(西南民族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成都 274000)
郭璞(276-324),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博學有高才,但訥于言論,性情放散而不拘于禮節。東晉初,郭璞因卜筮之能被王導引薦給晉元帝,又因文筆俱佳被晉元帝提攜為佐著作郎,又遷尚書郎,后來被王敦脅迫做了記室參軍。王敦謀反時讓郭璞占卜,郭璞以卜筮不吉勸阻王敦,王敦惱羞成怒,殺害了郭璞。王敦之亂平后,郭璞被追贈為弘農太守。
郭璞現存奏疏文共五篇,分別為《省刑疏》《因天變上疏》《皇孫生請布澤疏》《平刑疏》和《彈任谷疏》。郭璞的奏疏文集中創作于佐著作郎與尚書郎任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著作郎承擔著史官的任務,規諫國君就成為郭璞義不容辭的責任。如郭璞所說:“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諫留任谷宮中疏》)郭璞奏疏文的創作目的是為了統治者鞏固王朝政權服務的,因而,其思想內涵也是圍繞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
目前學界對郭璞奏疏文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陰陽災異思想,儒道思想等方面。
高剛在《郭璞辭賦與散文研究》中指出,郭璞奏疏文中的陰陽災異思想繼承了董仲舒的思想學說,還傳承了董仲舒奏疏儒雅雍容的風格,又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郭璞能站在百姓的立場上,以他們的利益為出發點為百姓代言。與同時代的庾亮、溫嶠相比,郭璞更多的是站在老百姓立場諫言刺世,雖然官職低微,卻不懼權貴,敢于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1]趙華超的《東晉奏議文研究》同樣指出,郭璞奏疏文中充滿了陰陽災異思想,該文將郭璞奏疏文與西漢時谷永奏議文對比分析,指出二者之間的差別。谷永奏議文直言敢諫,行文一氣呵成,作者認為這源于漢代人對君主關系的客觀認識,郭璞奏疏文注重陰陽災異思想的推演,增加了論述角度,是對漢代此類奏議文的發展。[2]連鎮標的《郭璞研究》對郭璞奏疏文中的思想成分剖析透徹,深刻闡釋了奏疏文中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和道家“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3]胡中勝的《東晉愛國文學研究》主要對東晉愛國文學進行研究,認為“上念國政,下悲小己”始終是郭璞詩文創作的主旋律。以僅存一句話的《諫禁荻地疏》為例,胡中勝指出,郭璞以儒家經典為依據,闡發了儒家愛民思想,借此諫阻統治者“禁荻地”之舉措,郭璞此舉體現了儒家知識分子正道直行的處世態度。[4]
綜上,對于郭璞奏疏文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學者們往往以郭璞的具體人生經歷為底本,對其思想進行探討。本文試圖從郭璞的生活環境、社會現實和奏疏文文本出發,挖掘郭璞思想的淵源和流變,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政治和思想傾向。
一、陰陽災異思想
郭璞在面對政治問題時,往往以陰陽災異思想應對。
(一)陰陽災異說的起源與發展
陰陽災異又稱為天人感應說,這一理論正式形成是在漢代,但它的起源很早。“陰陽”“五行”觀念在《尚書·洪范》中已有表現。戰國時期,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們把五行提升為“五德終始”,并把五行與陰陽附會起來。呂不韋組織門客編撰《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在《周書》《夏小正》和鄒衍學說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以此為經,再綜合了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因素和政治行為,使萬物萬象都組合到了陰陽五行里面去,形成一種神秘的大有機體。《淮南子》把《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完全吸收進《時則訓》中,以十二紀紀首的五帝五神為《天文訓》中的五星。在漢代思想家中,受十二紀紀首影響最大的是董仲舒。董仲舒繼承了十二紀紀首的觀點,運用以類相推的方法,由人推及于天,強調“以類退之”“以合和之”,由類推以言災異,達到天人合一的狀態。繼董仲舒后,以孟喜和京房為代表的卦氣思想還在發展,孟喜易學把傳統周易的八卦與五行完全結合起來,構成天地之體和宇宙的基元。[5]292京房對孟喜的易學又有建樹性的發展,京房以陰陽為基礎,糅合了天文、律歷、人事、五行、方位、歲時、天干等,構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大統一體,鮮明地反映了漢代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思想的特點。
三國時期還有一位卜算大師叫管輅,《三國志·管輅傳》[6]675有專門介紹。管輅,字公明,平原人,精通卜筮之學,其弟管辰作《輅別傳》,使后世對管輅有所了解。《輅別傳》主要介紹了管輅關于占卜的一些奇妙故事,《管輅傳》是放置在《三國志》的《方技傳》中,因此,管輅并不被認為是一位思想家,而是一位方士。但管輅本身也是一位精通易學思想的大師,由于各種原因,他的思想被忽略,然而也不能完全被抹殺。目前關于管輅的研究很少,牟宗三的《才性與玄理》中專有一節講管輅之象數。牟宗三分析了治易的三種體系,也通過分析《輅別傳》中管輅占卜的實踐過程,解讀管輅術數學的理論和方法。他把易學研究分為三系。[7]78對于管輅的術數學,牟宗三指出,數術的根本還是陰陽感應的變化。也就是說,具體的或常或變的征象都來源于陰陽的感應。[7]83谷繼明對這些問題又做了深入探討,他在《管輅易學研究——兼論術數學的思維方式》[8]一文中指出,術數無法用現代科學去解釋,因為科學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但術數沒有規律性,因此術數要“入神”,才能實現對客觀世界的超越也就是打通人與神之間的界限,通神靈,才能準確地演繹神秘化的真意。
(二)郭璞陰陽災異思想的體現
《晉書·郭璞傳》:“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9]1900《晉書》在介紹郭璞生平時,為了凸顯他占卜的能力,把他與漢代京房、三國管輅相媲美,甚至認為超過了他們,可見郭璞攘災轉禍的能力非常突出。
按照牟宗三先生對于易學思想的劃分,再結合郭璞的人生經歷,可以做出以下論斷:
首先,郭璞在經王導推薦做官之前,一直是以占卜為生,這就屬于術數系。根據《晉書·郭璞傳》的記載,西晉后期,國家動蕩,郭璞卜筮到河東會有大亂,就帶著親戚朋友去東南避災。這一路上,為了生活,每到之處都會給那些地方官員鄉紳占卜,滿足生活需求的同時,郭璞也提高了自己的聲譽。如在將軍趙固之處,郭璞用術數使趙固的良馬死而復生,趙固給了他一筆不菲的物資。[9]1900郭璞過江后,宣城太守聽說了他的名聲,援引他為參軍,這時候郭璞的名聲在江南也漸漸建立了。郭璞此時的占卜往往是用術數解決問題,不摻加經與注的內容,因此,郭璞與管輅有相仿之處。兩者在卜筮之時,不附會經書的內容,只是方技之士。但是,方士因為未進入政治中心,就沒有很高的地位。如管輅,雖是聞名四方的占卜大師,卻被收錄在“方技”一類中。
郭璞南渡后,所攜物品數量有限,在新地方落戶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他還是攜老扶幼,很多地方需要安置,在財力上,郭璞無疑是不充足的。起初,郭璞做一些官員的參軍,提升自己的個人地位,然后又尋找機會,得到王導的青睞,王導順勢而為,再把他推薦給晉元帝。當時有一句俗語,“王與馬,共天下”。王導是晉元帝渡江后最信賴的人,元帝對他的話自然言聽計從,郭璞漸漸地進入了政府機關。郭璞自己知道占卜本身并不是一個很光鮮的職業,然而他為了生計,只能靠給人占卜賺取錢財。但郭璞并非只是一個方士,他還是一個文學家,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像司馬相如一樣,通過辭賦馳騁官場,因此他作了《江賦》。一經上呈便得到了晉元帝的贊賞,郭璞卻并未由此就受到了重用,晉元帝只給了他一個佐著作郎的官職。
其次,牟宗三先生提出,第二種是術數系附會上經注。郭璞本身是卜筮者,做著作佐郎之類的官員正是讓他承擔勸諫之類的政治任務,郭璞也全力以赴地盡到自己的職責,創作了一系列的奏疏文,如《省刑疏》《因天變上疏》《皇孫生請布澤疏》《平刑疏》等,其創作目的皆是通過陰陽災異思想勸阻皇帝減輕刑法。郭璞奏疏文所提出的政治主張承繼了董仲舒的“尚德去刑”理論,不僅理論上相同,論證上也繼承了董仲舒的方法,以陰陽災異干預政治。其中最精彩的是在《省刑疏》中對于天象人事的分析,郭璞把陰陽、四時、人事、天文、氣候、八卦、經傳等統統結合起來,綜合分析,得出自己的結論,借以引起晉元帝的警惕。郭璞的貢獻不僅是提出了問題,還在于擺明了“消復之救”。第一篇疏文上奏以后,晉元帝雖然有所警惕,但并未采取行動,郭璞又借天變再次上疏,還是接著上次卜卦的內容,郭璞一步一步地驗證自己卦象的真實性,同時也催促晉元帝盡快行動。
郭璞在他的奏疏文中引經據典,這就符合把經書內容附會到自己的卦象上,借以干預政治。如《省刑疏》中有言“謹尋案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10]46“案《洪范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于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10]46徐復觀曾指出,《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對漢代的影響很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對災異的解釋與對策;第二,是對刑賞的歸正和運用。”[11]41漢代思想家接受《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的影響,郭璞又把前代思想融通起來,用陰陽災異干預刑法,主張刑法分明。陰陽災異思想是天人感應思想在政治上的具體實踐。
通過對郭璞散文思想的研究,可以發現,天人感應思想在郭璞的散文中無處不在,不管是在其奏疏文還是圖贊文中都不可或缺,這也是郭璞作為一個占卜者的表現,正如同他在《客傲》中所說的那樣:“吾不幾韻于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10]77作為一個卜者,天人感應思想是他面對天地間問題時近乎本能的反映。
二、儒家思想
根據《晉書·郭璞傳》可知,郭璞的青年時代是在老家河東地區度過的,河東屬于黃河以北,據《唐長孺社會文化史論叢》:“三國時期的新學風興起于河南,大河以北及長江以南此時一般仍守漢人傳統,所謂南北之分乃是河南北,而非江南北……魏晉期間的江南學風是比較保守的。”[12]75又言:“在魏晉時黃河北岸的學風和江南一樣保守,因此他(葛洪)的學問純為漢人之舊。”[12]]80唐長孺明確指出,魏晉時期的黃河以北和長江以南的學風主要還是以漢代傳統思想為主。關于郭璞的身世,歷史上的記載很少,《晉書·郭璞傳》只有簡單的幾句話:“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于建平太守。”[9]1899魏晉時代,尚書都令史是尚書郎下的一個書吏,《晉書》中并未給郭瑗立傳,因而郭瑗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吏,由此也可知郭璞并非出身于胄族。郭璞并未生在世家大族,父親是從書吏一步步走到了太守的職位。因此,郭璞雖不是錦衣玉食養大的,但也出身于書香門第,自小接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在郭璞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這些思想的痕跡。在郭璞奏疏文中,儒家思想體現得尤為明顯。
(一)廣泛征引儒家典籍
郭璞在奏疏文中還廣泛征引儒家典籍,構成他的話語主題。郭璞閱讀了大量的儒家經典,并大量運用于其文章中。不僅在其奏疏文中有體現,在其他類的散文和詩賦中也有鮮明的體現。《易經》《尚書》《春秋》《左傳》《禮記》《詩經》《史記》《漢書》等都是他征引的對象。郭璞不僅征引古書,還吸收歷史上功勛卓著的政治家的主張和見解,體現了一個政治家的胸懷和涵養。以郭璞奏疏文為例,“《鴻雁》之詠不興,康哉之歌不作者……《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10]]46“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冰。”[10]]52儒家經典的運用構成了郭璞奏疏文的主要內容。郭璞本身就對儒家思想有深入研究,再加上他站在一個史官的位置上,主要任務就是規勸皇帝。因此,郭璞想要使自己的話語權更有說服力,必須大量征引儒家典籍,體現了郭璞濃厚的儒家思想。
除此以外,郭璞在其奏疏文中還多次勸誡晉元帝勤政愛民,減稅減刑等。郭璞總是條理分明地指出問題,又提出了解決方法。“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10]46郭璞認為面對國家現存的問題,晉元帝應該采取行動,發布詔書,承擔責任,把不完美不公平的現象掃除干凈,施恩布澤,讓那些含冤而去的人重獲新生,郁結之氣隨風而散。
(二)抒忠君愛國之情
忠君愛國就是心念天下蒼生百姓,盡管郭璞在《省刑疏》中運用了大量篇幅闡述他的陰陽災異說,企圖干預政治,但他的終極目的還是解決現實問題,體現了他忠君愛國的思想感情。在《省刑疏》中,郭璞主張“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10]]46在《皇孫生請布澤疏》中提到:“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10]55郭璞在這篇奏疏文中規諫晉元帝通過皇孫降生的國之喜事大赦天下,開陽布惠,充滿了對于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懷和熱忱。
《皇孫生請布澤疏》有言,“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10]56郭璞直白地表示,日蝕出現是因為國君沒有盡到責任,陰雨連綿是因為民眾心中有怨恨之氣,陰蔽陽時間長了會出現以下犯上的情況。郭璞在這句話里面不僅直白地表現了對晉元帝的不滿意,還催促元帝要盡快采取行動。其中,“陰氣積則下代上”,有一種隱約提醒晉元帝的味道。郭璞作為占卜大師,對于東晉王朝的前途肯定是提前預知到了的。因而,他不斷提醒晉元帝采取行動,否則,陰氣郁結時間長了會出現內亂。只可惜就算晉元帝會意了也試著改變現狀,然而東晉王朝本身就是建立在門閥貴族的掌握之中,晉元帝乃至整個東晉王朝都無法擺脫現狀。所以一切想法都只能是白白費力,徒勞無功。盡管如此,郭璞為官期間,還是不斷地通過奏疏形式勸誡元帝。
(三)儒家的鬼神觀
在《彈任谷疏》中,郭璞展現了自己的鬼神觀。開篇直接切入正題,任谷是妖異,晉元帝把他留在宮里是不符合禮正思想的。接著,郭璞舉出《周禮》來論證他的觀點,“奇服怪人不入宮”,把任谷留在宮里,“塵點日月,穢亂天聽”,郭璞個人感覺是不可取的。然后郭璞又提出三種可解決的方法,其一,如果把任谷奉若神明,應該敬而遠之。其二,若把任谷當作蠱惑人心的妖孽,應該把他流放到邊疆。其三,如果任谷是神祇驅使來降罪于人間,應該克己修禮,而不是讓任谷安然放肆地行事。最后郭璞提出自己的觀點,任谷是妖孽,應該把他遣出去,又申述自己因為擔任了史官一職必須正義直筆。
郭璞本身就是一位占卜大師,通神靈,但他對于鬼神之說,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癡迷,他繼承了儒家的鬼神觀念。《彈任谷疏》表明郭璞對于自稱是神靈的任谷是不相信的。他以《周禮》的“奇服怪人不入宮”為依據,批判晉元帝允許任谷入宮的行為,并且還繼承了傳統儒家對于鬼神的態度,敬鬼神而遠之,表現出一種理性的祭祀觀和認識論。
總而言之,郭璞在奏疏文中表現出了濃厚的儒家思想。在放蕩不羈、自我嘲諷的外衣下,掩蓋的是他熾熱的憂國憂民之情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但無奈世人總把他看成術士,就忽略了他的才華和胸懷,在屢次上書屢次被忽略的悲劇情況下,郭璞意識到自己不可能被重用,再加上對于自己的命數非常了解,就借母親去世丁憂回家,但回去后也免不了被殺的命運,于是安然從容地接受命運的安排。
三、法治思想
田余慶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文中對于東晉門閥制度的本質剖析得非常透徹。“王與馬的結合發展到了江左,權力結構才發生變化,門閥士族勢力得以平行于皇權或超越于皇權。皇權政治從此演化為門閥制度,竟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這是皇權政治的一種變態,是皇權政治在特殊條件下出現的變態。”[13]門閥制度是東晉王朝的根本制度,這種制度統領下的社會,必然是士族之間為了利益互相傾軋,而法律制度勢必不完善、不公平。面對“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的時代問題,郭璞奏疏文切中時弊,五篇中有四篇都涉及了刑法問題。由此可知郭璞對于法律制度的重視,也可以了解到郭璞的法治思想。
一是強調刑法制定的合理性。《皇孫生請布澤疏》:“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勛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圣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眾乖,此自然之勢也。”[10]56郭璞認為晉元帝至今還未使東晉達到中興的盛世氣象,原因之一是刑法太過繁重,因此主張適時大赦天下,讓那些本不該被關進牢獄的百姓得以重見天日,使恩澤布惠于天下蒼生,又能對之前的大興牢獄之風有所補救。由此可以看出郭璞強調法律制度要合情合理。
二是強調刑法實施的公正性。《平刑疏》:“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難,思在斷之為難。”[10]58刑法不分輕重,而在于是否公正,但公正的評判標準并非刑法本身,而在斷案的審判上。在具體審判過程中要公正嚴明,刑法審判的公正性直接影響了一個國家的穩定與長久,不公平的審判是不能使民心所向的關鍵。
三是強調法律的穩定性。《平刑疏》中“是以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系,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而主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群惑者也。”[10]58若法律制定后,又有人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為了自身利益而讓法律朝令夕改,只會造成人心惶惶、民心不穩的局勢,對于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郭璞舉子產鑄法于鼎上的故事是為了強調法律制定后的長期堅持。
由此可知,郭璞的法治思想切中時弊,是針對東晉初期法律朝令夕改的社會現狀而提出的,展現了郭璞政治手段的靈活性和變通性。
四、黃老思想
“黃老”中的“老”是指老子的《道德經》,“黃”是指“黃帝”,關于黃老思想,金春峰在《漢代思想史》中指出,黃老思想面向政治和社會,發展出一套和儒家對立的社會、政治、軍事思想。[5]18長沙馬王堆漢墓于1973年12月出土了帛書《老子》甲卷和乙卷,乙卷前有《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這四篇帛書被學界稱為《黃帝四經》。黃老思想起源于戰國,在漢惠帝至武帝在位前的七十年間成為一種政治指導思想。黃老思想表面上主張清靜無為,實質是站在法治的立場,主張法治精神。因此在無為表象下,漢初統治者遵守的是黃老思想或者法家思想的理論主張。漢初的君臣上下皆強調休息無為,以發展經濟,恢復生產力,而黃老思想正適應社會的需要,因此得到了充分的運用。
郭璞政治思想中也有典型的黃老思想,“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10]58曹參是實踐黃老思想的人,在歷史上留下了美名。當時百姓紛紛歌詠:“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凈,民以寧一。”[14]2466郭璞在《省刑疏》中舉曹參的例子是為了說明制度制定之后的實踐性和長久性,不能朝令夕改,應該如曹參一樣長久堅持。
《省刑疏》又言:“《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10]58郭璞依據《老子》立論,希望晉元帝不要繁禮縟節,任意刑罰,而倡導無為而治、不宰而宰的治世主張。由此可知,郭璞奏疏文中黃老思想體現的是堅持在法制建立之后對其兢兢業業的堅持。
總之,郭璞雖然有濃厚的儒學思想基礎,但本身就思想駁雜的他不會限定自己的思維。惺惺惜惺惺,所以,對于子產,郭璞充滿了贊賞。子產在倡導鑄法于鼎的時候,很多人都反對,連孔子也不例外。鑄法于鼎上對于孔子來說是一種術,孔子是主張道的,當然不能表示支持。但子產是一位敢于革新的政治家,主張道術兼而有之。他還曾提出政治要寬猛相濟的原則,展現了極大的靈活性。通過分析郭璞奏疏文,可以發現郭璞是一個思維非常靈活的人,不會僅限于一家思想中,而與魏晉時期的自覺意識有關,思想融通解放,政治思想也更加靈活。
結語
《晉書·郭璞傳》記載:“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橫恐不得盡,親乃憂酒色之為患乎!’”[9]1905郭璞并非一個純儒,儒家思想只是他思想體系中的一部分,他平時行為放蕩、縱酒好色,這就說明了郭璞思想的駁雜性和豐富性,這也是兩晉士人的共同特點。相比于兩漢時期思想家的純粹,魏晉時期,由于多元文化的影響,人們在思想上更加靈活多樣。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郭璞在仕宦方面一直都不顯達,是一位普通的史官,沒有實權,也沒有受到晉元帝充分的重視。因此,他一直是以術士的身份立于朝廷之上。在《客傲》中,他才會有最后一句感嘆,“吾不幾韻于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10]76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他在自嘲外表下的款款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