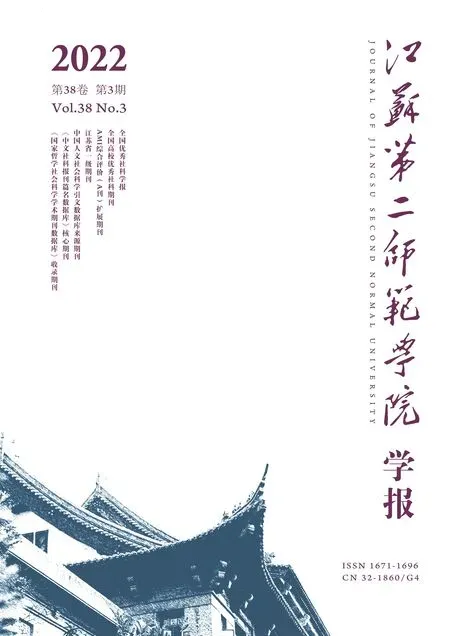劉勰三教觀研究*
謝 淵
(1.南京大學哲學系, 江蘇南京 210023;2.江蘇第二師范學院美術學院, 江蘇南京 210013)
劉勰是南北朝時期具有儒佛道兼容思想特質的典型代表,其在三教關系上的觀點是南北朝時期三教關系的重要分支,亦是該階段關于三教關系的代表性觀點。佛教進入中土后,就致力于對以儒道兩家為代表的本土文化的滲透,并積極尋找中國化的契機。歷經兩漢的主動依附謀求發展與魏晉時期的沖突、融合,發展至南北朝時期三教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為后期三教的深層次融合提供了基礎,以劉勰為代表的文人階層,對于三教觀的思考推動了三教關系及相關理論朝向更完善、科學的方向發展。
劉勰三教觀的形成與其生平及家世密切相關。其父劉尚早亡,20歲前相依為命的母親亦離開人世,遂南下定林寺,隨僧祐學習佛儒經典十余載。后得學士沈約舉薦步入仕途,曾官至六品太子府機要秘書、東宮一通事舍人。但隨著沈約與僧祐的相繼離世,仕途之夢破滅。其后奉敕回定林寺整理僧祐經藏,垂暮之年皈依佛門燔發出家,一年后黯然離世。門第觀念盛行的南朝,劉勰仕途不暢或與其家族的衰敗有直接聯系。名門貴族把持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與仕途的晉升,十分注重品階門第,寒門出身的學子面對的是難以逾越的身份鴻溝,即便才能卓越,勛勞卓著,若沒有家世背景,斷然不可能與權貴精英交游并列。另一方面來看,家世亦決定了家學的傳承,這對于個人思想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劉勰雖出身東莞劉氏,但傳承至劉勰時衰敗蕭條,幾乎于庶族無異。關于其是“士”或“庶”歷來爭論不休,筆者認為,劉勰一支雖沒落至與寒門無異,但其士族家學并未丟失,其父曾任越騎校尉,其堂叔劉岱于句容出土的墓志上記載亦可佐證,劉氏這一支至少到齊梁之際,尚能保持家風不墜。因此,單憑朝野高官斥其為寒士為依據,將其歸為庶人似有不妥。
南朝儒釋道鼎立的背景,少年時期佛學浸潤的經歷,加之士族家學的傳承,對劉勰三教觀的形成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亦決定了其儒佛道思想兼容并包的特征趨勢。
一、立足儒家、融涉佛學
永明二年(484年),劉勰因家庭變故南下定林寺,追隨名僧僧祐儒佛并學。這一階段是劉勰三教觀的形成初期,家學的熏陶讓其立足于儒學視角,身處佛門則讓其開始融涉佛學思想。因此展現出以儒涉佛的思想特征。
“齊高帝少為諸生,即位后,王儉為輔,又長于經禮,是以儒學大振。”[1]382在其后的三年之中,齊將儒學立為國學,并下詔“修建教學,精選儒官”。故在永明元年后形成了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永明文學時期”,此時的社會各基層幾乎進入了家家尋孔教、人人誦儒書的局面。此時正值劉勰邁入青年階段,人生觀思想觀樹立之際,故自幼聰慧、篤志好學的劉勰,在二十歲前學習內容以儒家思想為主是無疑的。另一方面,家風使然,也決定劉勰初期的思想必然不離儒家,這些都讓儒學之風在劉勰思想成長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從主觀方面來看,以沒落士族自居的劉勰亦不可能主動涉及佛教經論的學習,更沒有機緣接受佛學的改造。這種情況至劉勰進入定林寺后發生了改變,父母離世的變故,促使劉勰南下謀求生活,委身于受皇家認可的定林寺謀求日后發展。此時江左釋風日盛,佛教得到帝王的重視是客觀事實,佛學與佛教對于早孤而失去依靠、入仕無門的劉勰存在巨大吸引力。
“(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2]473文士蕭子良首開雞籠山是南朝學術思想領域的大事。他于建康西邸廣泛召集文人學士,名士名僧,“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眺、王融、蕭深、范云、任防、陸錘等并游焉,號日八友。”[2]473形成了“竟陵八友”。由此可見“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此言絕非虛言。在此處集道俗于一邸,如此盛況一定程度上對于佛學的盛行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彼時身為竟陵王的蕭子良,看似與佛教與儒學,并不相關。但以蕭子良的社會地位,以及基于此社會地位所接觸到廣泛的社會影響,都決定了佛風的盛行必定對自身及對他人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彼時的南朝無論統治階級還是平民百姓,可以說從文至武、從士到庶,出入佛老者甚多。而皇家寺廟定林寺更是香火鼎盛高僧輩出,佛法受到上層統治者的尊崇,達官貴人、鴻儒俊彥經常是座上賓客,文人名士趨之若鶩,在此談佛論道,宛若高級佛學沙龍。劉勰南下初入定林寺時,當時僧祐已經接下法獻衣缽,成為定林方丈,僧眾繁多,盛況空前,連貴為臨川郡王的蕭宏亦常出入其間。在這樣的皇家寺廟中寄身佛門的經歷,為劉勰從根本上認識佛學與從思想上接受佛學浸潤,提供了天然的沃土。入寺的前六七年時間中,劉勰整理定林經藏,為佛經編排目錄、撰寫序跋,并負責處理日常與僧祐往來之書信,在這些看似瑣碎與經書相伴的幾載中,令他有機會充分學習佛學理解佛經。與進入定林寺前相比,劉勰的思想從根源發生了變化,佛學已經牢牢地占據了一席之地。
南北朝時期盛行的佛學實質已經是玄學化了的佛學。此時經學的地位有所下降, 玄學的地位逐步上升,思辨的玄風盛行于南朝各個階層,佛學通過與玄學的相互吸收,進入了思想界,借由玄學來格義,利用玄風的盛行不斷發展自身。如此以玄解佛促使了玄與佛趨于合流。此時的佛學實質上已經大量地吸收了老莊的道玄思想,其本身已具足道家部分思想作為成長的細胞。在此階段的劉勰,雖然沒有直觀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但大量融涉了玄學化佛學決定了劉勰在思想上大量吸收佛學思想的同時,道玄亦在佛學思想的包裹下,滲透于劉勰的思想大廈之中。
從初上定林寺整理佛典,到隨僧祐編排目錄,都是劉勰在自身純粹的儒學血脈中不斷融釋佛學因子的過程。“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3]1859亦是劉勰從實踐中體會佛學理解佛學的經歷。無論自覺抑或非自覺,這對于劉勰三教觀的構筑起著重要作用。立足于儒家視野,廣泛接納佛教的思想改造,為其三教觀的發展與成熟提供了充足的養料,云集佛儒經藏的定林寺是劉勰的思想發展的天然溫床,也為在《滅惑論》中從義理層面調和儒佛關系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立足于儒的視野接受佛學的沐浴,這時期的劉勰已向儒佛兼用的道路踏出了堅定一步。
二、彌合佛儒,批判道教
佛教在中土站穩腳跟后,與儒道形成鼎立的態勢,這期間三教不可避免地展開了正面交鋒。劉勰于建武四年(497年)撰寫了《滅惑論》,從義理、源流、人倫等多重方面將佛與儒進行全方位的調和,把道家與道教相分的同時,將道教定義為神仙方術。定林寺長期接收到的佛學熏陶,使佛學的種子在劉勰的思想中開始生根發芽,在這一時期展現出強烈的彌合儒佛批判道教的思想傾向。《滅惑論》代表性地反映了劉勰這一階段的三教觀,展現出以儒護佛的思想特征。
儒佛并修使劉勰開始以儒學的視角理解佛理問題,在義理層面,劉勰提出佛教以二諦法讓世人辯明三空掃象破執,弘法傳道的過程本身就是教化眾生救人脫離苦海的大德大善之舉,因而“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4]則指明佛和儒兩家所說的“至道”,本質上是一樣的,“菩提,漢語曰道”,佛教里至高的菩提智慧就是漢語中所說的“道”,所以“孔釋教殊而道契”,儒、佛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同時“異經同歸,經異由權”又指出儒道和佛道是并行不悖的,只因語言各異而言論不一。
在人倫方面,他強調佛教的德行與儒家的基本原則相通,“孝理至極,道俗同貫”。出家在家僅有形式上的區別,都能闡發德行。甚至提出在家奉養雙親是一時之孝,學習佛法才能永久地讓家人脫離苦海的大愛大孝。故儒佛之間是“玄化同歸”,所追求的理想殊途同歸。關于二者誰先誰后以及夷夏之辯的爭論,劉勰指出《老子化胡經》為道教徒偽造,老子傳道西方沒有根據,且佛教本身并不是為了教化蠻夷而設立,極力證明佛教與儒家的根本一致性。
關于教化功能方面,劉勰提出“殊教合契,未始非佛”,認為受教化的不同是由眾生不同的機緣所決定。有佛緣,就接受佛教的教化,如有俗緣,那就接受帝王的教化,甚至認為世俗的教化也是佛法的體現。因而,儒佛二家在思想層面是完全可以相融合的,實質可以稱得上是殊途同歸。之所以顯示出不同,只是兩家思想在不同地域不同文明背景下生長綻放出的文化表象。
《滅惑論》是劉勰回應將佛教全盤否定的《三破論》而撰寫出的,其根本立場是為佛教辯護。《三破論》由道教提出,其對于佛教破國破家破身的指責不留余地,彼時劉勰仍寄居于寺中,依靠佛門的同時仕途上仍待機而動,如果真將佛教定義為亡國之教,豈不是前程盡毀。于定林寺十余載深諳佛理的劉勰用《滅惑論》為武器尤其是針對指責佛教的道士群體,組織起言之有據的反擊,故劉勰對其的批判上不遺余力。南北朝時期,道家作為一個學派已經失去了其獨立形態,往往與道教混合在一起。劉勰首先將道教從道家剝離,指責道教為神仙方術,道人也為愚狡方士。又從南朝佛教的真神論出發,指出道教修煉的永生追求“形器必終”,但佛教所修行的脫離苦海涅槃之境才是“神識無窮”,這就是所謂常住不滅的泥洹妙果。同時又肯定老子學說為導世良方,是“非出世之妙經”,但語下之意,仍隱有治世之道不如救人之佛的意味。
《滅惑論》中彌合儒佛關系拉攏道家排斥道教的傾向,是劉勰三教觀發展階段中對儒佛道三教關系的重新思考與定位。但劉勰對于儒佛道的三教關系的認識,略顯曖昧。雖然在儒佛關系上劉勰極力彌合,但關于出世與入世的追求二者又是必然不可調和的,劉勰本人也在數年后用行動做出了選擇,甚至對道家為未必是一味地批評。所以這一時期劉勰對于三教觀的認識,彌合佛儒批判道教的同時,實際趨于三教思想的調和與吸收。這時期的激烈思考,為其后期趨于穩定兼收并蓄的三教觀鋪平了道路。
三、兼收并蓄,三教并用
中興二年(502年)劉勰完成鴻篇巨制《文心雕龍》的撰寫,兼收并蓄的三教觀在50篇的論文中展露無遺,劉勰以三教并用的手法,高于儒釋道的角度闡發思考問題,展現出三教和合的思想特征,也標志著劉勰三教觀步入三教匯通的成熟階段。
文心雕龍序志即言,劉勰夜夢手捧紅漆禮器,隨孔子向南走,遂決定撰寫文。“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籍,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一……腳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絲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據筆和墨,乃始論文。”[3]1862劉勰夢見的是孔子而非如來,也說明其夢中所追隨的圣人,是儒家圣人,所求為孔孟之道,這也是劉勰從內而外的尊崇儒學的外化表現;同時以夢的形式展開又充滿著老莊的道玄色彩;以心為題命名是遵循佛學著作命名的慣例,單從表相來看,文心雕龍三教熔于一爐的特征顯然易見。
關于內里的融合,從《原道》篇來看,提出“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5]1強調人能立言也是順乎天道的準則。“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采; 有心之器,其無文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5]1萬事萬物于人世間都具備文采,圣人所立之言自不必說,古今先賢所留的濟世之文誠然是天地的主宰,在誦讀學習圣人之文時,對于個人心靈與社會風氣有著教化之大功效。另外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提及“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如此強調無為正是取自于老莊學說,是為老莊論道; 此后又提及“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效。”[5]1此強調神理設教正是出自《周易》的卦辭,是為易傳論道。同樣,在此《原道》篇中多次提及神理一詞,從劉勰協助僧裕所編撰的《出三藏記集》一書中來看,明確言辭表達所說的“神理”其“理契乎神”,這樣幾處很明顯指佛之理,是為佛學之神理解。全書中這樣由表及里的對于三教兼用的例證多不勝數,在這樣50篇大論文的合著中,立足于三教并蓄的視域下著述,足以說明這一時期劉勰三教觀已趨于成熟,真正達到兼收并蓄,三教并用。“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令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3]1867《文心雕龍》得到沈約的好評,為劉勰扣開了仕途之門。兼收并蓄,三教并用的三教觀經過撰寫《文心雕龍》的洗禮,已成熟穩定融匯一爐。充分吸取了三家學術之精華,從形而上之體到形而下以致用,為后期劉勰開創經藏目錄,創建名實相符的目錄學思想,形成兼顧內容形式的文體起了指引方向的作用。
四、“儒學為本”的三教觀傾向
劉勰三教觀三個向度的演變與其個人發展自洽且相適。不管是以儒涉佛、以儒護佛還是三教和合,不難看出盡管是一個動態變化逐步成熟的過程,但思想是常常隨著時代的發展、個人的遭遇而有所變化。因此,厘清其三教觀展開的根源尤為重要,直接關乎于分析劉勰看待三教問題角度,對其思考問題方式的探討及對其利用三教觀處理事物切入點的研判。
一直以來最大疑惑是,篤信佛教的劉勰為什么要堅守儒家立場呢?
首先,從動因來講,劉勰始終以儒士自居。《文心雕龍》中的《宗經篇》中充分肯定了儒家的地位。雖然自我的評定可能出現偏差,而自身的行為也可能與自我的定位產生背離,但其初心落于儒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如前文提及的其原生家庭而言,劉勰家世雖沒落,但家學傳承仍在,其祖父、堂叔以及父親都是士族出身。南北朝時期雖然儒學消沉導致佛道并興,但儒學在世家的家學傳承中仍是占據主導地位,即便是梁武帝時期佛教被推行為國教風光一時無兩之際,儒學仍不可撼動地根植于士人血脈中。從個人發展而言,父母雙親的過早離世,讓劉勰想要再度躋身士族已經相當困難,其父離世之前曾官居四品秩二千石,本身是無須納課服役的,到建康定林寺依沙門僧祐更多的可能是考慮避免四處流落寄人籬下之苦,從而安心學業。同時僧祐為其進入仕途也提供了可能性。棲身于作為南朝的皇家寺院的定林寺,亦有為日后謀求政治資本之意。于此看來,他似乎并不是純粹出于佛學的感召而拜服于高僧遁入釋門。
其次從動機來談,劉勰完成《滅惑論》的寫作后構思《文心雕龍》,也是出于在同一時代的文士之中未有鴻篇巨制的著作誕生的考量,寫曠世之作《文心雕龍》以期立言;反響未達到預期后,反思認為或是自身影響力不夠,著書不能達到廣泛認可,求見沈約后步入仕途,求功名以期立功;得沈約舉薦后更有恩師僧祐為其仕途保駕護航,胸懷“緯軍國任棟梁”之志以期立德。最終雖抱負未成,但究其動機仍不離儒家“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窮則獨善以乘文,達則奉時以騁績”是劉勰為自身設定得人生信條。后期出家為僧,是因對其有知遇之恩的沈約與仕途上為其保駕護航的恩師僧祐離世,從而政治幻想的破滅,而本身的奮斗終其一生也只得到梁武帝蕭衍對其“高級文學侍從”的評價定位,心灰意冷之下的無奈之舉。
如此對自身“樹德立言”的期許,其出家之際仍不忘上表朝廷的行為,也足以證明劉勰的思想剝去外相,本質上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筆者認為,劉勰的一生“出世”是為了“入世”,“入世”無果后才選擇了“出世”。關于劉勰在儒佛道三教中的偏向問題中,王元化先生做了簡明準確的概括:“劉勰的一生經歷正表明了一個貧寒庶族的坎坷命運。懷著緯軍國、任棟梁的入世思想,卻不得不以出家作為結局。”[6]31當然,其中關于庶族的定位仍值得商榷。但總體來說,劉勰的三教觀是一個融涉儒佛道的動態過程,雖然歷經了三個階段的動態發展,總體呈現儒佛道三家合流匯通的趨勢,但本質是以儒學為基點而展開的,其以儒為本的思想取向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