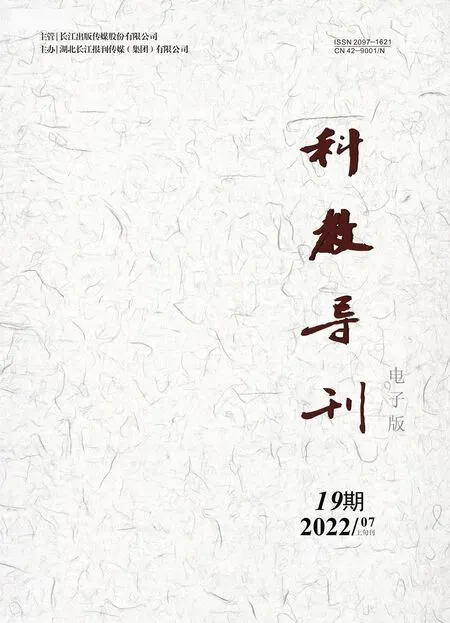大科學創新的進步模式及其啟示
趙 煦,張 琰
(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8)
目前,在自然科學領域,大科學已穩穩占據著科學研究的主導地位。但直到目前為止,對大科創新模式的研究還沒有產生一個統一的理論,還沒有系統概括出大科學創新的進步模式。因此,探究從傳統科學創新模式到大科學創新模式的演變,對我們未來的大科學的布局有著特殊的意義。
1 從物理學標準模型理論到超對稱理論
從建設到運行,共耗資500多億美元,由來自全球80多個國家的約7000名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參與,數十萬臺計算機聯結到一起,位于地下 100米深的一個全長約26.659公里長的環形隧道,經過28年的建設才投入運行。這組令人吃驚的數據是對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即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的真實描述。事實上,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是當今大科學的一個典型。“所謂大科學研究,是指規模巨大、人數眾多、投資龐大、并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的綜合性的科學研究。”[1]具體什么是大科學,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一個統一的認定標準,但有學者認為,項目總金額達到一億美元以上的涉及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就可以被稱為大科學研究。大概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大科學便開始逐漸顯現,到20世紀中葉,大科學漸趨成熟。二戰以后,大科學就迅速發展,占據了科學前沿各研究領域的核心地位。
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從設計到建設運行,一直肩負著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探尋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以驗證物理學標準模型理論的準確性。因為物理學標準模型理論是目前為微觀粒子世界作出解釋和說明的最為成功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粒子共包含18種夸克、6種輕子、12種規范玻色子,另外每一種物質粒子都有自己所對應的反粒子(其中,規范玻色子本身就是自己的反粒子),因此,物理學標準模型理論主張,構成世界的基本粒子至少有62種。不過,直到20世紀90年代,物理學標準模型所預言的所有基本粒子,只剩下1種沒有被發現,這種基本粒子就是希格斯玻色子。因此,希格斯玻色子是否存在,就成為驗證物理學標準模型理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經驗證據。正因為如此,探尋希格斯玻色子的蹤跡,就成了21世紀物理學向前推進的一個重要前沿。
雖然,經歷了諸多困難,終于在2012年7月,發現了希格斯玻色子的蹤跡,并導致了201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誕生,為物理學標準模型理論畫上一個較為圓滿的階段性的句號。不過,科學有關世界的探索不會就此停止,人類關于世界的認識永遠在路上。物理學標準模型理論在粒子物理學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卻并未能解決所有問題。
因為超對稱理論告訴我們,宇宙誕生時,“大爆炸”產生了數量相同的物質和反物質。但不知什么原因,少量物質幸存下來,形成了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而反物質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因此,探尋反物質、暗物質的存在,驗證超對稱理論正確與否,就必然下一階段物理學前沿推進必然要面對的問題。
2 傳統的科學進步模式及其問題
20世紀以后,科學知識的產生不再是緩慢的累積式的演進,而是以一種爆發式的速度在跳躍式增長,各門學科在高度綜合的同時又高度分化,呈現出整體化的特征。[2]特別是進入到大科學時代以后,科學研究活動的特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傳統的科學進步模式已經不能為科學活動中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提供合理的說明。
2.1 線性累積的邏輯分析
邏輯導向的科學進步觀認為,科學的發展是一個累積進步的過程。從科學哲學史的歷程看,邏輯導向的科學進步觀又分為實證主義進步觀和證偽主義進步觀兩個階段。雖然在邏輯導向的科學進步觀內部對科學進步也有著不同的主張,但其總體上都是認為科學理論是在不斷朝著真理,或者是在不斷逼近真理進步的。不過,科學發展如果只是科學知識的積累,而且只表現為單一的量的積累,科學研究的過程也只是簡單的經驗歸納,那就必然會忽視人類在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創造性,也就會忽視質變的作用。[3]
與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一樣,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理論及其證偽原則也同樣有著一定的片面性。波普爾認為,一個科學理論一旦被經驗或邏輯證偽,就要拋棄這個理論。同時他指出,萬事萬物的發展都經歷了從低級到高級的突變過程,進而結合他的“三個世界”理論,認為事物的發展從世界1突變到世界2,然后再突變到世界3。從表面上看,三個世界的突變過程似乎和大科學跳躍式進步是一樣的,但從本質上看,波普爾的這種理論突變在邏輯上是連續的,是朝著一個固定不變的真理目標不斷逼近的過程,而大科學發展的跳躍式進步是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目標的。因此,波普爾在本質上依然是一個邏輯主義者,他的這種線性的邏輯主義思想無法為大科學的進步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模式。
大科學項目的新目標與之前所完成的科學目標之間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邏輯演進關系,不同的階段支撐大科學項目運行的所要研究的理論對象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大科學的進步表現為:在完成一項大科學研究后,又迅速轉向另一個與它可能是毫不相干的大科學研究,在不同的理論之間實現跳躍式的發展。
2.2 庫恩的科學革命進步模式
以庫恩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對科學的進步模式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既否定了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科學理論的線性累積的進步模式,也批評了批判理性主義對科學理論簡單粗暴的否證,提出了一種動態研究科學進步的新模式。[4]庫恩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指出,科學的進步是科學新范式戰勝舊范式,新、舊范式更替的過程。他不同意波普爾的線性邏輯的科學進步模式,而是把科學發展分為幾個階段:前科學、常規科學、科學革命、新的常規科學……在進入常規科學以后,科學就不斷經歷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的交替發展的循環進步過程。
而大科學誕生以后的近百年科學史來看,大科學所開展的項目和研究并沒有經過前科學—常規科學—科學革命—新的常規科學這樣循環發展的現象,無論是大科學早期的典型代表——曼哈頓計劃、阿波羅計劃、國際空間站計劃,[5]還是今天的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實驗。在大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科學一直保持著平穩的進步,沒有產生關于大科學的科學革命,也沒有關于大科學發展的新舊范式的轉換。此外,庫恩認為,因為整個科學的發展是非連續的,因此理性不是普遍的,科學的發展沒有一定的客觀規律和進步目標指向。同時,庫恩認為,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文化擁有不同的世界觀,并且不同時代的不同世界觀反映的均是在自己的經驗范圍內所認識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庫恩進而主張,每一種世界觀都是正確的,但又都有片面性,都是相對存在的。[6]這樣一來,庫恩就陷入了非理性主義和相對主義之中。
3 大科學的跳躍式進步模式
從大科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我們可以發現用邏輯實證主義的線性積累的邏輯分析方法,還是用庫恩的科學革命的模式,都無法解釋大科學發展的進步過程。以前文所述的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在發現希格斯玻色子的前后的目標變化為例,從大型強子對撞機開始建設一直到希格斯玻色子被發現之間的這一階段,尋找希格斯玻色子,驗證物理學標準模型理論,是該大科學項目的主要目標,但希格斯玻色子一經發現,其階段性任務完成了,該大科學項目就轉向了新的目標——尋找反粒子、暗物質,驗證超對稱理論。
從大科學發展的具體過程中看,2012年希格斯玻色子的成功發現標志著一個大科學實驗的完成。此后,無論是2015年我國的世界首顆暗物質探測衛星“悟空”號,還是2016年我國“墨子”號量子衛星的發射、2017年我國貴州“天眼”望遠鏡等,與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之間都不存在必然的邏輯演進關系。上述大科學項目的開展意味著大科學的進步,并非邏輯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累積進步或逼近真理的過程。而且,上述所有大科學項目都是地位平等,平行發展的,而不是如邏輯實證主義主張的那樣,舊理論被吸納到一個具有更大范圍,內容更加豐富的后繼理論之中。同樣,大科學的進步也并非像波普爾證偽主義所主張的科學進步的過程,就是科學理論不斷被證偽的過程。
通過對比國內外開展的這些大科學工程,我們也沒有發現如庫恩所說的科學革命的發生,新舊范式的交替,甚至發現中微子具有質量是對標準模型的沉重打擊的極大危機,但是也沒有改變標準模型在粒子物理學中的地位,也并沒有發生代替標準模型的科學革命。而且從這些先后開展的大科學項目來看,大科學的進步是跳躍的,是在一個大科學項目結束后選擇另一個大科學項目,且前后兩個大科學項目可能是毫不相干的,是跳躍式的向前發展。
通過邏輯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科學進步模式與大科學所開展的一系列項目的比較研究,我們發現大科學的進步是非累積的,前后開展的大科學項目之間不存在必然的遞進關系。大科學的進步是間斷的,一項大科學項目結束后可能會轉向另一個毫不相干的大科學目標,比如說上海的同步輻射光源和量子衛星計劃之間是沒有什么相關性的。大科學的進步是跳躍式前進的,大科學項目的開展會在問題的引導下,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而進行具體選擇,大科學開展的前一個項目可能是在微觀領域的大型強子對撞機實驗,下一個項目就有可能跳躍到宇觀大尺度空間關于引力波的探測研究。此,近期我國還開始獨立開展了一批大科學計劃。研究大科學的問題,借鑒國際上大科學計劃的經驗與得失,從中尋找啟示,是我國大科學健康發展的必經之路。
4 大科學的進步模式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科技投入不斷增長,科研實力也不斷提高。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已有部分在國際領先的大科學項目嶄露頭角。目前正在建設之中的江門地下中微子實驗(JUNO)可為代表。這一實驗項目的規模將比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大100多倍,計劃運行至少20年,以揭示更多宇宙奧秘,理解微觀的粒子物理規律,也將對宇宙學、天體物理乃至地球物理做出重大貢獻。[7]此外,位于我國四川的錦屏地下實驗室從4000立方米擴容到12萬立方米。錦屏隧洞最大埋深達2400米左右,實驗室設立其中,就相當于將實驗室設在地下2400多米深的地方,超過了加拿大的巖石覆蓋厚度2000米的斯諾實驗室,能將宇宙射線通量降到地面水平的約億分之一。中國錦屏地下實驗室二期工程將包括4組共8個實驗室及其輔助設施,已于2015年年底完成土建工作,總容積將從目前的4000立方米擴容到12萬立方米,能夠容納更多的深地科學領域實驗項目同時開展,建成后將有望逐步發展成為國家級的面向世界開放的基礎研究平臺,是開展粒子物理學、天體物理學及宇宙學等領域中的暗物質探測、雙 衰變、中微子振蕩、質子衰變等重大基礎性前沿課題的重要研究場所,是巖體力學、地球結構演化、生態學等學科開展相關實驗研究所需的特殊環境,也是低放射性材料、環境核輻射污染檢測的良好環境。[8]
21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不同學科的大科學項目的先后立項開展,國與國合作的大科學項目也越來越多,大科學在科學前沿推進中的作用已成為世界共識。發現和研究大科學的進步模式與小科學科學的本質區別,對于大科學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從目前世界各國正在開展的大科學項目看,大科學的開展愈來愈需要發揮已有科學技術的橫向支持,來促進其縱深發展,同時大科學項目的正常運行需要創新組織和管理模式。這就對不同領域不同學科的科學家們提出了要求,要看到這種區別,更要用新眼光和新思維去看待大科學的變化,設計新項目,提出新概念,探索新領域。
雖然目前大科學面臨著種種問題,但正處于科技發展上升期的我國卻必須全力融入國際大科學計劃中,不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