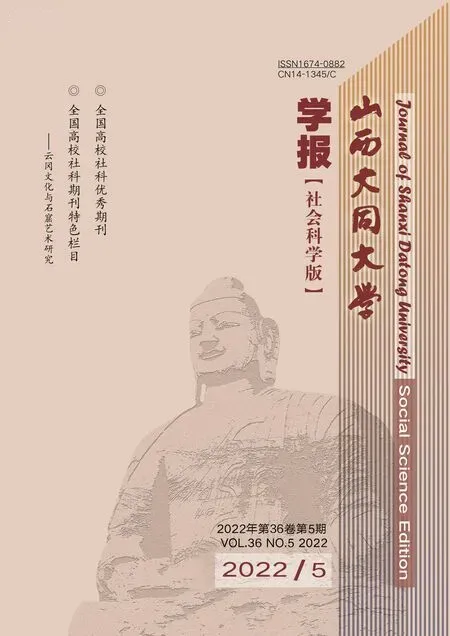“床榻”:論《海上花列傳》中的主題物與妓女書寫
馮 偉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海上花列傳》自問世以來,受到學界高度評價,并在后世文學史書寫中逐漸實現經典化,尤其妓女書寫,被歷代研究者廣泛、頻繁地納入考察視野,并獲得相當豐碩、深入的成果。就目前所見,相關研究往往聚焦于妓女形象本身。這固然是一個常規考察點,但問題在于,人物形象塑造與人物書寫的概念“區間”并不完全重合,嚴格來說,前者意在考察人物形象的呈現面貌,后者則更側重于橥析某類人物的塑造方式,尤其調動各種敘事結構為人物塑造服務的方法與路徑,而稍有不足的是,以往關于《海上花列傳》中妓女形象的考察,顯然更貼近于前者。[1]
這里,筆者借來“主題物”[2]一詞,嘗試以新的角度窺察《海上花列傳》中妓女群體的書寫方式。正如趙毓龍先生所指出的,主題物“由于經常作為一組場景的持續焦點存在,與人物的思想、行動環環相扣,主題物成為敘事文本書寫時風物情時最突出、最具線索性的道具。”[3]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進一步延展:主題物不僅可以作為“一組場景的持續焦點存在”,亦可以作為一個章節,一部文本,甚至一類作品的敘事“標本”,從而承擔重要的書寫功能。基于此,我們或可打破既往囿于人物形象本身的研究壁壘,以“主題物”為切入點,對《海上花列傳》中的妓女書寫做出新的觀照。經考察,“床榻”就是一個典型個案。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選定的研究對象,是指包括床、榻、炕等在內的廣義上的“床”,在此以“床榻”代指廣義的“床”。就筆者粗略統計,該書明確以獨立的“物”的形式(而非“鋪床”“床褥”等修飾性形式)提到“床榻”近270次,其中出現在妓女相關場景者有八成以上,在64回篇目中,僅第12回未有明確提及。當然,并非所有的“床榻”都可以作為主題物參與敘事,如:“小村冷笑不語,自去榻床躺下吸煙”,[4](P8)“那相幫早直挺挺睡在旁邊板床上”[4][P272]等,除了營造場景的真實感之外,“床榻”并未承擔重要的敘事功能。但不能否認,部分“床榻”確實是具有特定意義的主題物,且多與妓女書寫相關。而我們要做的,就是以“床榻”為先,盡可能有效、深入地將其納入時代語境與文本語境的聯系中,并以此為基礎,討論敘事者給予妓女群體的書寫匠心與藝術底色。
一、“床榻”的文學映像與空間聚焦
就形式而言,《海上花列傳》中的“床榻”主要有大床和煙榻兩類。二者既是坐具,又是臥具,皆具有日常意義上的起居功能。當然,也存在具體的差異,如前者形制更大,雕飾更為華美,主要用于睡寢,相比之下,后者則簡約得多,多用以供人吸食鴉片等。事實上,二者的差別遠不止于此,王健《中國近代床榻研究》[5]已做出較為詳細的考證。但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關注的并非“床榻”作為器物本身所承載的文化意涵,故本文更傾向于以文學本位,將其視為一種承載著重要的人物書寫功能的主題物加以闡釋。換言之,敘事者在敘事文本中對此類“床榻”做出的藝術提煉與加工,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海上花列傳》中涉及到的“床榻”的具體名類有:廣漆大床、隔板拼作的煙榻,跋步床、大理石紅木榻床,(外國)鐵床,板床,繩床,炕,胡床等9種,除胡床以外,其他床類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在與妓女相關的場景中。當然,這里僅臚列敘事者明確標明名類者,故文中俯拾即是的“床上”“榻上”等泛指暫不納入統計。不難發現,在出現近270次的“床榻”書寫中,被“點名”的僅10次,足見作者在行文敘事中對“床榻”細節的淡化處理。
盡管如此,不論形式、款式、價值、功能,現實生活中的各類“床榻”皆被敘事者大量采擷進敘事場景中。其中既有中國傳統樣式的廣漆大床、跋步床,又有時新西方款式的鐵床,亦有榻、炕等“另類”的“床”,而尤可注意的是,雖然文中“床榻”的名類不可謂不多,但作者似乎對其外觀、功能、價值等“常規要素”并不在意——全書幾乎找不到對某類床的詳細描摹。或可說明:第一,作者秉持“平淡而近自然”[6](P248)的創作原則,并未有意模糊、夸大、改變“床榻”的文本呈現方式,而是盡可能還原現實中的生活情狀,這于探察生發其中的人物形象而言,尤其重要;第二,反過來看,作者雖未將筆墨凝結于“床榻”本身,卻頻繁提到“床榻”,反復突出其存在痕跡,亦足以見“床榻”在該書敘事網絡中的重要功能。由此,我們可以做出合理推測:相比于作為一般物象存在,《海上花列傳》中的“床榻”顯然更傾向于作為一種功能性的主題物被有意凸顯。
一個看似的悖論在于:既然敘事者并未集中筆墨描寫“床榻”,主要以碎片式的呈現、泛化的言辭一筆帶過,那么他是如何突出其重要性的?當然,如前所述,出現頻率高顯然是原因之一,這勢必會在客觀上不斷強化受眾的閱讀印象。但筆者以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點,即敘事者主觀上對“床榻”的空間聚焦。
在敘事學視閾中,“聚焦”即“表現敘述情境與事件的視角”,[8](P75)也就是“敘述者或人物從什么角度觀察故事”。[8](P19)在這里,我們引入“空間聚焦”的概念,意在借用其“觀察”的含義,討論某一特定空間內“床榻”被“看到”的方式和形式,繼而發現其在文本書寫中的重要意義。我們簡單選舉幾例,臚列于下:
(1)樸齋跟小村上去看時,只有半間樓房,狹窄得很,左首橫安著一張廣漆大床,右首把擱板拼做一張煙榻,卻是向外對樓梯擺的,靠窗杉木妝臺,兩邊“川”字高椅,便是這些東西,倒鋪得花團錦簇。[4](P12)
(2)雙珠也笑著,坐在榻床前杌子上,裝好一口水煙,給善卿吸。[4](P20)
(3)張壽見那后半間只排著一張大床,連桌子都擺不下,局促極了。[4](P41)
(4)原來屠明珠寓所是五幢樓房,靠西兩間乃正房間;東首三間,當中間為客堂,右邊做了大菜間,粉壁素幃,鐵床玻鏡,像水晶宮一般。[4](P163)
(5)剛踅至樓梯半中間,從窗格眼張見帳房中樸齋與小王并頭橫在榻上吸煙,再有大姐阿巧緊靠榻前胡亂搭訕。[4](P338-339)
(6)一進房間,便見大床前梳妝臺上亮汪汪點著一對大蠟燭,怪問何事,葛仲英笑而不言。[4](P421)
從中可以看出:第一,(1)(3)(5)(6)是敘述者以人物視角投射空間布局,每一處空間的具體呈現中,“床榻”都是首先被關注的對象。第二,(2)(4)是敘事者基于“上帝視角”進行的敘事,皆表現出敘事者對“榻床”的有意曝光,尤其是(4),敘事者煞有介事地介紹了屠明珠“五幢樓房”的空間布局,僅重點呈現了“鐵床”“破鏡”兩個物象,頗具代表性。第三,更有趣的是,(2)(6)的中心物象雖然是“杌子”和“蠟燭”,但敘事者卻皆以“床榻”為參照系,而實際上這里的“床榻”并不承擔必要的敘事功能,如若刪去也不會對敘事效果產生影響,留下反而會有繁縟之嫌。由此,敘事者對“床榻”的重視不言而喻。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床榻”都會晉升為承擔重要書寫功能的主題物,它們往往只是敘事者擷取現實生活碎片進入文本的藝術投射。但敘事者總在有意無意間將“床榻”引入敘事進程,不僅體現出“床榻”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特定場景敘事的常規組成部分,且其行為本身也在客觀上強化那些具備主題功能的“床榻”的存在痕跡。受制于小說題材的指向性,這些“床榻”絕大多數都與妓女書寫有關,因此我們也可以相對容易地找到“床榻”與妓女書寫之間更為縱深的騰挪空間。
二、“床榻”:妓女形象情欲化轉型的主題物
關于近代狹邪小說的分期,學界有“三期說”和“二期說”兩種主張,無論哪種說法,都將《海上花列傳》視為狹邪小說發展中期的轉捩點。[9]揆其緣由,主要是自該書伊始,狹邪小說創作初步體現出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當然,這種轉型是多方面的,它綰結著文化、思想、題材、技法、敘事等諸多層面,其中妓女形象的轉型即是不能忽視的一點。魯迅更是直接將妓女書寫作為判斷狹邪小說分期的重要標準:“……又有《海上花列傳》出現,雖然也寫妓女,但不像《青樓夢》那樣的理想,卻以為妓女有好,有壞,較近于寫實了……這樣,作者對于妓家的寫法凡三變,先是溢美,中是近真,臨末有溢惡……”[6](P314)由此不難覘見妓女書寫之于近代狹邪小說轉型的重要意義。問題在于:學界對該問題的主要聚焦點,仍停留在魯迅所提出的妓女形象由“近真”到“溢惡”嬗變的范疇里,這當然是十分精準的考察方向,但不是唯一的。筆者以為,以《海上花列傳》為代表的中后期狹邪小說中妓女形象的轉型,還體現在妓女情欲書寫的凸顯。這里,我們以“床榻”為例,試做討論。
“床榻”作為《海上花列傳》妓女書寫去傳統化的主題物,主要體現在其作為情欲符號的象征意義。就古代文學作品的書寫傳統來看,妓女形象多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如李娃、杜十娘、玉堂春、趙盼兒、李香君等,她們或是有情有義、德才兼備的理想愛人,或是智勇雙全、大義凜然的女中豪俠,皆是文學史中膾炙人口的藝術形象。她們幾乎具備一切男性視角中屬于女性的美好品質,也被有意遮蔽、消解掉了現實中的妓女群體的原始情欲特征。出于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傳統等多方面因素“撕扯”下而形成的話語“合力”,這種刻板乃至失真的妓女書寫傳統一直被沿用至晚清前期狹邪小說的創作。而在《海上花列傳》中,作者則有意通過對“床榻”的凸顯與聚焦,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該書妓女形象的去傳統化轉型。
“床榻”作為日常生活中的臥具、坐具,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小說中妓女書寫中的常客。但需要看到,無論傳統抒情文學,還是敘事文學,無論作為意象,還是物象,抑或純粹的物,晚清以前的妓女書寫中,“床榻”的書寫程式和文學意涵都已在不同體式的作品中基本趨于穩定。盡管結合明清白話小說的書寫特質,“床榻”被普遍賦予更多象征性和敘事功能,但究其根底,小說家仍無法擺脫合德、合禮的創作旨歸。也就是說,晚清以前的妓女書寫中,“床榻”之于人物的表征和象征意義往往依附于傳統價值標桿下人物塑造理念,具體到情欲書寫,更難免多顯含蓄與隱晦。如《賣油郎獨占花魁》,秦重“看美娘時,面對里床,睡得正熟……不敢驚醒她”,又將棉被“輕輕的取下,蓋在美娘身上……脫鞋上床,捱在美娘身邊……眼也不敢閉一閉”。[10](P28)這里,“床”顯然是作者表現秦重性格特征的重要道具,但耐人尋味的是,男女共處一床,卻毫無肌膚之親,“床”反而被賦予充滿道學氣息的象征意味。相比之下,擬話本中帶有情欲意味的“床榻”絕大多數都被當作行為發生的“場所”或情節的收束點而被一筆帶過,如“服侍公子上床,解衣就寢”等。嚴格來說,這類的“床”并不具備主題物的功能。再如《花月痕》等文人化程度非常高的作品,也普遍將妓女“床榻”作為展示傳統才子佳人式溫情的道具,而刻意消解其情欲意涵。另外,還需要注意到的是,艷情小說中的妓女“床榻”經常與情欲相關聯,但問題在于:第一,艷情小說有其特殊的題材指向,是社會性文化和性風氣影響下的畸形產物,不適合被納入常規考察范疇;第二,即使在艷情小說中,“床榻”也主要被作為宣淫的場所和道具,而普遍不具備主題物功能。
《海上花列傳》中妓女的“床榻”書寫,則將這種傳統、常規的書寫程式打破了。“床榻”成為人物打破性別隔閡,沖破情欲禁錮的重要道具。如果說此前小說中的妓女書寫是有意規避男女“床事”,而著重凸顯敘事者(或人物)的道德品格與禮制觀念的話,那么《海上花列傳》則以更為獨到的眼光,將“床榻”作為突破傳統禮制規范的情欲符號。如:
(1)徐茂榮點了榻床煙燈,叫張壽吸煙。張壽叫來安去吸,自己卻撩開大床帳子,直爬上去。只聽得床上扭做一團,又大聲喊道:“啥嗄,吵勿清爽!”[4](P38)
(2)楊媛媛睡在床上,尚未起身。鶴汀過去揭開帳子,正要伸手去摸,楊媛媛已自驚醒,翻轉身來,揣住鶴汀的手。鶴汀即向床沿坐下。[4](P142)
(3)那潘三正躺在榻上吸食鴉片煙……匡二悄悄上前,也橫下身去伏在潘三身上,先親了個嘴。潘三仍置不睬。匡二乃伸手去摸,四肢百體,一一摸到。[4](P237)
這是全書頗具代表性的三例。在傳統章回小說中,閨闈空間中的床往往象征著未婚男女倫理的絕對底線,即使對妓女這種特殊群體的書寫,在文人理想的加持下,作者也大都有意規避對“床”的正面聚焦。而在這里,“床”不僅沒有被邊緣化處理,反而被有意曝光與凸顯:(1)中張壽棄“榻”而“床”,“直接爬上去”,與妓女“扭作一團”,絲毫沒有性別差異所帶來的拘束與遲疑;(2)中鶴汀在楊媛媛“尚未起身”的情況下直接進入閨房,“揭開帳子”,自然地“伸手去摸”,后又向“床沿坐下”,亦毫不關心男女有別的金科玉律;(3)中匡二更是“伏在身上”,“親了個嘴”,“四肢百體,一一摸到”。不難發現,在這三個場景的鋪排中,“床”都是聚焦中心,而作者正是借助“床”的私密性及男女對這種性質的逾越,以簡單的筆墨,彰顯男女之間溫存、曖昧甚至淫穢的情愫,從而強化妓女輕浮、放蕩的情欲特征。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此前文學作品中也會偶爾出現類似的情況,但需要明白,那些吉光片羽式的存在并不能成為一種常規書寫范式,而作為主題物充斥于《海上花列傳》字里行間的“床榻”,才是真正體現妓女形象情欲化轉型的代表。
最后,還需要看到,這種情欲的隱喻性,當然不能與艷情、色情描寫直接掛鉤。敘事者雖然始終沒有強調“床榻”本身的禮制內涵,但它卻不是模糊的,其作為“床榻”所蘊藉著的文化、倫理價值標準,始終伴隨著“床榻”被置于相關敘事場景的聚焦中心。而在敘事者以此為界,驅使人物行動在邊界內外兜轉與逾越的過程中,我們更能看到“禮”讓渡于“欲”的嬗變軌跡。可以說,在這類書寫中,“床榻”顯然已經成為承擔著重要情欲隱喻功能的主題物。
三、“床榻”:“再現”妓女生存狀態的主題物
如前所述,“床榻”是《海上花列傳》中妓女場景的常規道具。其出現一般是緣于相關敘事話語“再現”生活真實的需要。由于妓女的生活軌跡(如交際、留宿等)大多涉及“床榻”,故其在妓女相關場景中的出鏡頻率尤為密集。經過小說家的藝術闡釋,這些在文本中頻繁出現的“床榻”不僅作為器物普遍體現著特定的物質文化,更有部分脫離物的層面,上升為一個符號學意義上的主題標識,其背后更暗含著一個深刻的文學隱喻:妓女生存狀態的縮影。
首先,“床榻”是妓女名利欲望的外化。致力于晚清娼妓文化的研究者們早已指出:“社會關系的物化和對時尚物品的追求也體現在妓家的室內陳設”,[11](P62)包括妓女閨房陳設在內的多個方面早已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她們的身份、性格和生活方式,俘獲了公眾的想象力”,她們是城市潮流的風向標。[12](P23)這當然與開埠城市的繁華風尚密切相關,但更重要的是,這同樣體現出妓女群體的共同特征:崇奢,尚奇,求新,好異。[13]而若我們將所謂的“室內陳設”具體到《海上花列傳》中的“床榻”,則不難發現其已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代表妓女名利欲望的價值符號。
就器物層面本身而言,“床榻”的樣式、材質、尺寸等客觀條件將直接決定其價值,于崇奢尚異的上海妓女而言,這種價值往往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其自身的商業價值。因此,狹邪小說家往往圍繞這種文化特質,展開對妓女名利欲望的文本投射。如小說第四回敘張蕙貞跳槽事,敘事者即以善卿視角“看到”,房間里“空空落落的沒有一些東西,只剩下一張跋步床”。[4](P30)這看上去只是敘事者簡單提掇的敘事習慣,實則不然——張蕙貞隨即托蓮生向善卿說到:“我請耐來,要買兩樣物事:一只大理石紅木榻床,一堂湘妃竹翎毛燈片。”[4](P31)此番對話雖然簡短,但敘事者對前后兩處“床榻”的呼應卻頗值玩味:如前所述,該書極少有直接點明“床榻”名類的表述,而此處接連出現的“跋步床”“大理石紅木榻床”,其本身所流露出的強調意味是十分明顯的。這實際上是對張蕙貞其人而言的:“跋步床”和“大理石紅木榻床”,一個是妓女睡寢的大床,一個是供客人休憩的煙榻,二者的材質、款式、規格,將直接影響到物主自身的形象,成為妓女“臉面”的代言。當然,這種“臉面”不僅關乎自身排場,更重要的是用來招徠顧客,以獲得更豐厚的經濟回報。無獨有偶,在妓女屠明珠的寓所,我們也能看到敘事者類似的聚焦習慣——“右邊做了大菜間,粉壁素帷,鐵床玻鏡,像水晶宮一般”。[4](P163)這里的鐵床,是指時髦的西式大床。敘事者明確提示,屠明珠不惜重金也要在“水晶宮”內安置一張外國鐵床,其用心正與張蕙貞仿佛。正如陶慕寧先生所言:“官妓既革,青樓遂不再承擔為士大夫消愁遣興的義務,妓女也不再含英咀華、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妓家的一切均以迅速贏利為依歸。”[14](P215)
其次,“床”里“榻”外,是妓女真實生活場景的“再現”,是其全面而真實的生活經驗的文學映射。“榻”是客人暫坐、吸煙的場所,“床”是妓女和客人纏綿之處,二者之間,是用以擺放酒局的桌椅。“榻”“床”之間的流連與兜轉,幾乎是妓女日常活動軌跡的全部寫照,更是其真實生活的鏡像與縮影。由此生發的敘事場景,在《海上花列傳》中尤為常見:
(1)說時,大姐已點了煙燈,又把水煙筒給樸齋裝水煙。秀寶即請小村榻上用煙,小村便去躺下吸起來。[4](P16)
(2)張小村與吳松橋兩個向榻床左右對面躺著,也不吸煙,卻悄悄的說些秘密事務。陸秀林、陸秀寶姊妹并坐在大床上,指點眾人背地說笑。[4](P24)
(3)隨后湯嘯庵也踱過這邊房里來,吃得緋紅的臉,一手拿著柳條剔牙杖剔牙,隨意向榻床下首歪著,看蓮生燒煙。[4](P84)
事實上,“榻上燒煙”“床上談笑”已經成為一種近似機械性的重復敘述模式,在妓女相關場景的鋪排中,敘事者總是習慣性的遵循“榻上——酒局——床上(榻上)”的鏡頭轉換線索,并在這條固定的“墨線”中,以各類情節填補空白。
最后,“床榻”也經常作為妓女的私人道具而出現,其最為突出的功能,就是成為妓女個人財產的“貯藏所”,如:
(1)諸三姐偏死命的拖進來,要他陪伴,卻自往床背后提出一串銅錢,在手輪數。[4](P242)
(2)翠鳳自去床背后,從朱漆皮箱內捧出一只拜匣,較諸子富拜匣,色澤體制,大同小異。匣內只有一本新立帳簿,十幾篇店鋪發票。[4](P441)
(3)二寶因要兌換人參,親向洪氏床頭摸出一只小小頭面箱開視,不意箱內僅存兩塊洋錢。[4](P569)
當然,不能否認,“床榻”成為妓女私人財富的“貯藏所”,與現實生活中大床的儲物功能不無聯系,但也要看到:敘事者在強調“床榻”的貯藏功能時,很少聚焦于妓女貯藏行為的本身,而是反向再現其“拿出”的動作,并分別賦予其不同的意味。(1)中“野雞”[15](P218)諸十全給李實夫買煙,僅幾個銅錢卻“輪數在手”,其生活之窘迫、待客之生澀躍然紙上;(2)中黃翠鳳取出的拜匣,實際上是先前通過欺騙手段從客人羅子富手中得來的,而此處歸還拜匣的前提,就是借此取得了理想中同等價值的財物,其陰險狡詐的形象特點,伴隨著“拿出”的動作被最終定格;(3)中妓女趙二寶因關門謝客,一心等待史天然而將自己的生活逼入絕境,“兩塊銀錢”不僅是二寶生活山窮水盡的象征,更是其理想幻滅的昭示。可以說,在這里,作為“貯藏所”而存在的“床榻”,其不斷“充實”與“空落”的過程,也是妓女不同生活境遇的縮影。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在《海上花列傳》對妓女日常生活的“再現”過程中,“床榻”絕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普通器物。作為觀照妓女生存狀態的主題物,它既有助于敘述者完成對妓女真實生活經驗的藝術闡釋,也有助于讀者實現對妓女生活的二次重構。我們固然不能先入為主地認為這是作者有意為之的書寫手法,也不能妄圖僅憑借一個單薄的“床榻”概述甚至還原整個妓女群體的生存境況,但毫無疑問,無論如何,《海上花列傳》中的“床榻”都為我們探察妓女的一般生活狀態提供了天然且合理的可能性。
四、“床榻”:觀照妓女命運軌跡的主題物
最后,我們認為,“床榻”是觀照妓女命運的主題物。這主要緣于其在妓女生活中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它是妓女營業過程中的具有公共屬性的常規道具,承擔妓女待客交際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它是妓女非營業時間內的私密“場所”,全書中無論疾病相關的身體書寫,還是夢境相關的理想書寫,都與其息息相關。可以說,通過對這些散落在全書情節脈絡中的“床榻”的歸攏,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妓女的命運軌跡。
一方面,“床榻”是妓女發跡的起點。一般來說,客人“不能要求留宿此處(大床),只能耐心等待妓女請他留宿——通常是在他在這房間里擺了數款酒局并贈送她貴重禮物之后”。[11](P66)也就是說,妓女往往利用“床榻”的留宿功能以盡可能多得博取客人錢財,狹邪小說中圍繞于此展開的敘述情節不在少數。如《海上花列傳》敘陸秀寶與趙樸齋事時,張小村便勸樸齋道:“況且陸秀寶是清倌人,耐阿有幾百洋錢來搭俚開寶?就省點也要一百開外哚,耐也犯勿著啘。耐要白相末,還是到老老實實場花去,倒無啥。”[4](P11)與之呼應,后來秀寶不斷要求趙樸齋請酒,贈送戒指,樸齋未應,秀寶便轉而與出手闊綽的施瑞生相好。好像怕讀者不明,敘事者還委婉地點出了秀寶的“代價”:“(瑞生)我就不過一個陸秀寶,故末起初是清倌人,我一做仔就勿清哉。(第25回)”[4](P222)不難發現,在這里,“床榻”已經由一般器物晉升為一種隱喻符號,其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器具,而是妓女獲取財富的關鍵道具。
另一方面,“床榻”也是妓女理想幻滅的終點。《海上花列傳》對此最為明顯的呈現就是妓女對恩客萌生的真摯感情,其中既有雙方互相傾慕的才子佳人式愛情,也有客人始亂終棄的負心漢式愛情,但無論如何,都最終以愛情的幻滅告終。在這個過程中,“床榻”顯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如陶玉甫與李漱芳之間傳統才子佳人式的愛情,就是在漱芳臥病期間不斷發展、升華的。若我們把散落在第七至四十二回中關于二人情感的線索提出,則發現二人情感的完整線索中一直都有“床榻”的影子,如:
陶玉甫聽得李漱芳咳嗽,慌忙至大床前揭起帳子,要看漱芳面色。[4](P154)
玉甫笑而不言,仍就床沿坐下,摸摸漱芳的手心,問:“故歇阿好點?”[4](P174)
漱芳先已睡熟,玉甫覺天色很熱,想欲翻身,卻被漱芳臂膊搭在助下,不敢驚動,只輕輕探出手來,將自己這邊蓋的衣服揭去一層,隨手一甩,直甩在里床浣芳身邊。[4](P178)
玉甫本待不睡,但恐漱芳不安,只得掩上房門,躺在外床,裝做睡著的模樣;惟一聞漱芳輾轉反側,便周旋伺應,無不臻至。[4](P321)
當然,漱芳臥病,“床榻”作為主要情節、場景營構的道具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條件,但我們不能據此將其簡單理解為線索發展的客觀組成部分。需要看到:不同于全書其他部分對“床榻”的淡化處理,這條情節線索中,敘事者在有意圍繞“床榻”展開對二人情感進程的鋪敘,更重要的是,當漱芳死后,“床榻”更是這段理想、美好的感情走向縱深和高潮的主題物:
玉甫哭的喉音盡啞……跌跌撞撞進了右首房間……額角為床沿所磕,墳起一塊。[4](P374-375)
跨進門檻,四顧大驚,房間里竟搬得空落落的,一帶櫥箱都加上鎖,大床上橫堆著兩張板凳……玉甫心想:漱芳一死,如此糟蹋!不禁苦苦的又哭一場。[4](P382)
此段描寫,正與前文漱芳臥病的文字遙相呼應。而敘事者以“床榻”磕破額角,睹“床榻”思人為“靶心”連施兩筆,不僅能進一步歸攏、收束、升華二人圍繞“床榻”而建立的真摯情感,更著意通過“床榻”的“傷人”與被“糟蹋”,強調這段理想愛情的無奈與幻滅。正如學者所言:“(李、陶的愛情悲劇)昭示了海上青樓已不再有以往青樓文學作品中的真情……韓邦慶在這里使用隱喻的寫作手法,抒發自身對青樓詩意不再、真情不存、金錢當道的實際情形的不滿與嘆息。”[1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趙二寶與史天然的情感線索雖未緊貼“床榻”展開,但我們仍能從趙二寶的臥床一夢中,體會到其理想破滅的復雜心態。可見在“物象語言”的使用上,作者對李、趙二人的“床榻”進行了別樣的象征化處理,它不僅是二人文本生命結束的標志物,更是其美好、真摯的愛情理想幻滅的隱喻物。
不惟如此,我們還能從一些零散的敘述中,通過“床榻”看到妓女命運的部分“插曲”。如妓女的生意偶爾會遭受流氓的侵擾:“早闖進兩個長大漢子。一個尚是冷笑面孔;一個竟揎拳攘臂,雄糾糾的據坐榻床,掿起煙槍,把煙盤亂搠,只嚷道:“拿煙來!”[4](P122)這里,敘事者正是緊貼“床榻”來完成兩個流氓的形象塑造的。再如,敘事者也會利用一些日常場景之外的“床榻”敘寫妓女的“姘戲子”情結:“向來亭子間僅擺一張榻床,并無帷帳,一目了然。蓮生見那榻床上橫著兩人,摟在一處。一個分明是沈小紅;一個面龐亦甚廝熟,仔細一想,不是別人,乃大觀園戲班中武小生小柳兒。”。[4](P294)無論流氓,還是戲子,都難免對妓女的生意和名聲造成相當的惡劣影響。不論作者是否有意圍繞“床榻”展開敘事,但客觀來看,“床榻”與這些“小插曲”的書寫確實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系。事實上,具有類似功能的“床榻”還有很多,它們雖未成為主線情節敘事中的線索性道具,但也作為妓女命運圖景中的針腳而存在,是不能被忽略的。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海上花列傳》中的“床榻”絕非作者“再現”真實生活場景的陪襯器具。作為現實器物的文學映射,其自能體現作者的藝術呈現方式與提煉原則;作為主題物,其是我們探察妓女形象情欲化轉型的價值符號,是“再現”妓女生活狀態的隱喻符號,更是觀照妓女命運軌跡的象征符號,是表征全書妓女書寫特點的主題性道具。而類似的情況在近代狹邪小說,乃至明清世情小說中不乏其見:不僅還有大量“床榻”之外的主題物,如:水煙袋,化妝鏡,首飾等,還有更多敘事文本中的“床榻”,都具備線索性、功能性、隱喻性的書寫功能,而我們對此的關注還遠遠不夠。當然,筆者學力平平,在此僅嘗試以《海上花列傳》的女性書寫為對象,以作為主題物的“床榻”為切入點,為相關闡釋、研究提供一個可資參考的典型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