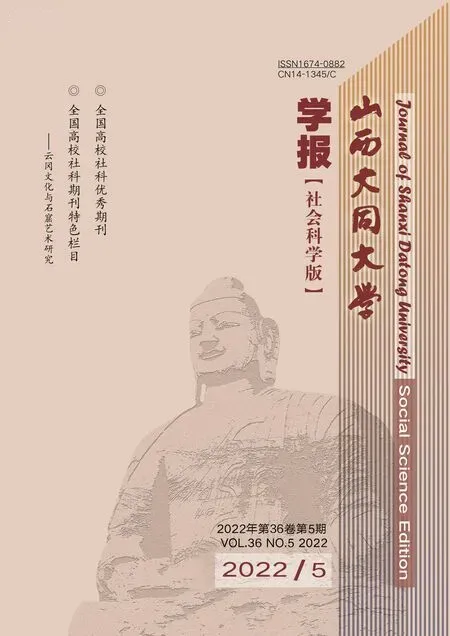論金元之際詞曲的互融與互異
——以受元好問影響的詞曲創作群體為例
姚亞男
(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詞、曲同為音樂文學,彼此聯系密切。清人劉熙載《藝概》云:“未有曲時,詞即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茍曲理未明,詞亦恐難獨善矣。”[1](P123)將詞曲二體結合研究,有助于對詞曲二體相互關系和各自的體式特征以及演變發展軌跡形成更確切、更深刻的認知。自民國以降,學人多有詞曲合并研究的倡導與實踐。王易《詞曲史》、[2]任中敏《詞曲合并研究概論》、[3]盧前《詞曲研究》、[4]龍榆生《詞曲概論》[5]等,堪為代表。其后諸多學者,如趙義山、陶然、胡元翎等,或探究詞曲體式的遞興,或揭示詞曲觀念的演變,或微觀審視某一作家詞曲兼作的具體情況,不一而足。
金元之際散曲初興之時,文人創作即出現了詞曲互融現象。選擇受元好問影響的詞曲創作群體作為研究范本,是因為該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金末元初詞曲演化階段的時代風貌,在詞曲互動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另外,就有限的成果看,專以這一角度為進路探究詞曲關系者,相對較少。而且,其研究視角多以散曲立論,分析散曲受詞的影響程度,并未明確涉及這一群體詞曲間的互動。[6]有鑒于此,筆者試圖通過對元好問及其詞曲創作群體的創作實踐及互動理念的研究,以點及面,形成對詞曲互動關系的一個較為深入的理解和認識。
一
元好問是金末元初的文壇盟主,其詞作承上啟下,代表了這一時期的最高成就;散曲創作亦領一代風氣之先。以他為中心,中原地區的士人廣泛聯系,逐漸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影響極大的北方詞曲創作群體,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詞曲演化階段的時代風貌。其中,既有詞曲兼作的作家,也有僅作詞或散曲的作家。作為個體,這些詞曲家有其相對獨特的創作題材或風格偏好,但總體上仍可看到這一群體或顯或隱的共通之處,以及對詞、曲兩類文體界限的認識。
關于元好問的交游情況,降大任在《元遺山新論》中的《元遺山交游考》[7](P167-429)一章作了詳細考證,共統計出469人與元好問有直接交往,筆者據此得出與元好問直接交游的詞人31人,以生年為序,分別是:胡祗遹(1127-1295?)、王庭筠(1151-1202)、許古(1157-1230)、趙秉文(1159-1232)、完顏璹(1172-1232)、馮延 登(1175-1232)、李 俊 民(1176-1260)、李 純 甫(1177-1223)、王渥(1186-1232)、高永(1187-1232)、楊宏道(1189-1270后)、耶律楚材(1190-1244)、趙元(1190-?)、李獻能(1192-1232)、李治(1192-1279)、楊果(1195-1269)、段克己(1196-1254)、段成己(1199-1279)、杜仁杰(約1201-1282)、劉秉忠(1216-1274)、耶律鑄(1221—1285年)、白樸(1226-約1306)、王惲(1227-1304)、魏初(1232-1292),以及生年不詳的辛愿(?-1231)、胥鼎(?-1224),生卒年不詳的白華、李天翼、曹居一、王特起、王鉉。另者,與元好問直接交游的散曲家12人,以生年為序,分別是:商衜(1194-1253)、商挺(1209-1288)、王惲(1227-1304)、白樸(1226-約1306)、魏初(1232-1292)、杜仁杰(約1201-1282)、楊果(1195-1269)、劉秉忠(1216-1274)、胡祗遹(1127-1295?)、徐琰(約1220-1301),以及生卒年不詳的石子章、張子益。其中詞曲兼作的有:王惲、白樸、魏初、楊果、杜仁杰、劉秉忠、胡祗遹。僅有散曲流傳于世的有:商衜、商挺、徐琰、石子章、張子益。該群體的成員主要是上層官吏,同時也有未出仕的社會名流。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所列為有作品存世的詞曲家,而實際上,這一群體的詞曲家數量遠不止于此。元好問《鵲橋仙》題序:“同欽叔(李獻能)欽用(李獻甫)賦梅”,[8](P93)《臨江仙》題序:“李輔之(李天翼)在齊州,予客濟源,輔之有和”,[8](P91)《《鷓鴣天》》題序:“隆德故宮,同希顏(雷淵)欽叔(李獻能)知幾(麻革)諸人賦”。[8](P94)此外,元代鐘嗣成《錄鬼簿》載元好問其師郝天挺“有樂府行于世”,[9](P317)表明李獻甫、李天翼、麻革、郝天挺皆有創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導致其詞或散曲湮滅不聞。
以元好問為中心的北方詞曲家群體,是一個以友情和學術交往為紐帶,自然而然、自發形成的文學群體。其中既有元好問本人的文學成就與聲譽威望的因素,也因為群體成員所具有的相似或共同的審美追求和風格傾向。他們相互之間志同道合,過從甚密,其交游盛況屢見于史傳、方志、詞曲家別集等各類文獻記載,此不一一展開論述。群體成員在詞曲創作上多有交流,以元好問為例,如其《水龍吟》詞序:“從商帥國器(完顏鼎)獵于南陽,同仲澤(王鉉),鼎玉(王渥)賦此。”[8](P77)辛愿曾與元好問作詞唱和,有《臨江仙·河山亭留別欽叔(李獻能)裕之(元好問)》,元好問亦有《臨江仙·西山同欽叔(李獻能)送溪南詩老辛敬之(辛愿)歸女幾》。另如李治、楊果追和元好問名篇杰作《摸魚兒》詞,詮釋了與元好問原作相似的忠貞愛情,構思命意,同一機杼,而在辭情上各具特色。此外,唐圭璋在《全金元詞·引用書目》云吳重熹石蓮庵本《遺山新樂府》有“后庭花破子兩首曲調及附楊果和后庭花破子一首”。[8](P1)詞曲家交往頻繁,創作上亦多同題或唱和之作,在思想與風格上彼此影響,逐漸形成了這一創作群體。
這一群體的詞曲作品不僅數量可觀,文學成就亦不容忽視。就詞而言,詞人的存詞數量已達到相當規模。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劉秉忠、白樸、王惲等人存詞均在六十首以上,元好問則高達三百八十余首,為金元詞人之冠。這一群體的創作成果,成就了一個體現著北方文化特色和文學傳統的北宗詞派。從散曲而論,這一群體是最早進行散曲創作嘗試的一批曲家,如王惲、白樸、胡祗遹、楊果的散曲數量較多,這一群體也具有極多成就突出、頗有造詣的散曲家。
二
通過梳理歸類這一群體的詞與散曲的題材內容,不難發現,除一部分詞曲題材完全不同外,仍有相當一部分詞曲內容難以區分,相同的題材內容共同存在于詞曲之中,出現了詞曲題材的互融現象。寫景、歸隱、離別以及青樓題材,共同出現于這一群體的詞曲創作之中。而應酬類作品,如贈答唱和之作、題友人園林之作、呈上司之作、宴飲之作等等,僅存在于這一群體的詞作中。表明在金末元初,散曲仍處于初期階段,在文體功能上還沒有像詞那樣被廣泛應用,缺乏交際功能。同時也說明,對于這一群體而言,散曲被視為較為卑下的文體,難以作為應酬之用。同樣,散曲中也存有詞中所沒有表現的題材,如展現男女幽會的具體場景,或敘述莊稼漢進城看戲的情形(杜仁杰《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較詞描繪出更為世俗、廣闊的社會內容,體現出這一群體對散曲本色、俚俗文體特征的認識。這里試圖重點闡釋和比較的是,這一群體中題材相同或相似的詞曲作品,其具體表現內容與表現深度的不同。詞曲題材互融中的這種細微差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這一詞曲群體對詞曲兩類文體界限的認識。
(一)寫景題材 寫景散曲的主導內容是描繪清新明快的景色,表達散曲家逍遙自在的心境。如劉秉忠〔雙調·蟾宮曲〕分別描繪春夏秋冬四景,其中一首詠春:
盼和風春雨如膏,花發南枝,北岸冰銷。夭桃似火,楊柳如煙,穰穰桑條。初出谷黃鶯弄巧,乍銜泥燕子尋巢。宴賞東郊,杜甫游春,散誕逍遙。[10](P14)
相似的還有白樸〔越調·天凈沙〕,同樣描繪春夏秋冬四景,色彩清新明快,雖單純寫景,但流露出作者的愉快心境。
而在這一群體的詞作中,除描繪清麗之景外,更具特點的是描繪北方雄壯之景。這一描寫內容在此前的詞作中極少出現,是這一群體對詞境的開拓,體現了典型的“北宗詞”特色。如王惲《木蘭花慢·居庸懷古》:
壯巉巉鐵峽,誰設險,劈蒼岑。擁萬里風煙,一栓橫鎖,形勝雄沉。漢王陽,憶當年、叱馭走骎骎。半夜郵亭索酒,平明燕市長吟。 追思往事不堪尋,山色古猶今。甚三十年來,青云垂翅,素發鬅鬙。投閑卻教應聘,笑委身、從事老難任。立遍西風殘照,山光翠滿疏林。[8](P665)
詞中描繪居庸關的蒼涼雄闊景象,與詞人的深沉感慨融為一體。如果與元好問名作《水調歌頭·賦三門津》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元詞中描寫黃河的磅礴氣勢與三門津的雄奇壯闊,并寄托了詞人的豪情壯志;王惲之詞,便是取法于元詞以北方雄壯之景,融胸中豪邁深沉之情的。
(二)歸隱題材 抒功名之累,發歸隱之情,是這一詞曲創作群體最具特色的題材。金元易代,家國傾覆。感慨世事難料,渴望歸隱田園,便成為這一詞曲創作群體成員的共同心聲。除詞曲中皆有的直接感嘆世事黑暗,渴望歸隱的內容外,散曲更多通過描繪閑適愉快的田園生活,表達歸隱之樂。如胡祗遹〔雙調·沉醉東風〕:
漁得魚心滿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個罷了釣竿,一個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兩個不識字漁樵士大夫,他兩個笑加加的談今論古。[10](P69)
這類散曲題材,直接由元好問隱逸散曲導引而來。詞中雖也有此類作品,但更多的是將歸隱之情置于蒼涼豪邁的心境中加以表現,如魏初《念奴嬌·為王約齊紹明壽》“離騷痛飲,問畢竟、世上功名何物。眼底誰能知許事,只有雙鳧仙客。一局殘棋,兩窗疏翠,談笑揮冰雪。”[8](P703)激越豪放而清曠超逸,體現了典型的北宗詞特色。在這一類題材中,散曲與詞同樣用以抒發文人士大夫的個人情懷,即這一群體賦予了散曲與詞相同的功能。
此外,散曲中極少關心時政之作。散曲家們多采取冷眼旁觀的態度,其重點描述的是時政混亂中的歸隱情懷,而對于戰亂的描寫、時局的描繪往往一筆帶過。而詞人常充分描繪慘烈的戰爭及動亂的現實,并在感嘆時政之外,進一步表達濟世之豪情壯志和渴望力挽狂瀾的豪情,如王渥《水龍吟》“萬里天河,更須一洗,中原兵馬”,[8](P52)王惲《水調歌頭》“丈夫出處道在,義命正需安”,[8](P650)此類描寫內容在散曲創作中是缺乏的。由此可見,在包括元好問在內的早期散曲家的創作中,根據表現內容的不同,確有詞曲分工的現象存在,前輩論家對這一點有所忽略,其實是很值得探究的。
(三)離別題材 散曲中所抒發的離愁別恨均為男女間的相思之情,或是女子埋怨男子不歸,或是男子懷念與女子的歡樂時光。如商衜〔南呂·一枝花〕《遠寄》以女子口吻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對男子的思念,又如商挺〔雙調〕《潘妃曲》中的多首小令,白樸〔中呂·陽春曲〕《題情》、〔仙呂·點絳唇〕,杜仁杰《喻情》,楊果〔仙呂·翠裙腰〕等。這一類散曲作品肆意暢情而描寫淺白,不求婉轉寄寓。詞中也有類似題材,但其中的閨情多用以寄托身世之感與亡國之恨,詞人傳達的重點是閨情之外的情思。如《蕙風詞話》卷三評價元好問所作擬宮體詞《鷓鴣天》八首及“薄命妾詞”:“蕃艷其外,醇至其內,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而其苦衷之萬不得已,大都流露于不自知。”[11](P72)以閨情言志,以宮體詞表達黍離之悲與零落棲遲之感。
此外,這一群體詞作中的離愁別恨題材多抒發對友人的懷念。不只表達思念之情,更多的或是勉勵故人,或是悲嘆有志難酬的境遇,或是表現淡泊逍遙之志。如楊果《太常引·送商參政西行》、耶律鑄《南鄉子·送人北行入燕作》、李天翼《臨江仙·和元遺山》等,皆極敘對友人的深切相思。又如辛愿《臨江仙·河山亭留別欽叔裕之》:
誰識虎頭峰下客,少年有意功名。清朝無路到公卿。蕭蕭茅屋下,白發老書生。邂逅對床逢二妙,揮毫落紙堪驚。他年聯袂上蓬瀛。春風蓮燭影,莫問此時情。[8](P51)
辛愿所留別的欽叔、裕之二人即李獻能、元好問,詞人敘寫了自己有志難酬的凄涼,并表達了對二人的鼓勵與期望。
(四)青樓題材 在以元好問為中心的散曲群體中,青樓妓女題材占據很大比重。在散曲家的筆下,出現的是形象豐富的妓女以及真實的青樓生活,富于俗趣,表現出了娛樂化的一面。其描繪分為三類:一為摹寫妓女外貌、衣飾,如杜仁杰〔雙調·雁兒落過得勝令〕《美色》、白樸〔仙呂·醉中天〕《佳人臉上黑痣》等。二為表達對妓女的同情,如商挺〔南呂·一枝花〕《嘆秀英》,以妓女口吻敘述悲慘的青樓生活。三為描繪男女幽會場景,時有格調低俗之作,如徐琰〔雙調·蟾宮曲〕《青樓十詠》。而詞中此類題材不僅數量少,在內容描寫上也遠不如散曲豐富。相較于散曲傾向于描繪妓女的外貌,詞中則多渲染妓女的風度氣質及高超的演唱技藝,描繪的是妓女形象的一個剪影。如胡祗遹的兩首詠妓詞《木蘭花慢·贈歌妓》及《點絳唇·贈妓》,第一首描摹妓女高超的說唱技藝,第二首更是極力贊賞妓藝的修養、風度,并且表達了對其凄涼身世的真摯同情。在這類青樓文學題材中,詞曲的表達或描述仍有一定的界限,詞作較為高雅,曲作富于俗趣。由此可見這一作家群體詞雅曲俗的文體觀。
通過對以上四類題材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寫景詠物題材與嘆世歸隱題材中,詞曲有一部分表現內容是重合的,體現了散曲向詞的融合以及詞對散曲的滲透。還有一部分內容僅有詞作涉及,如抒發對人民、對時政的關切以及表現作者蒼涼悲慨、懷抱高遠的心境。說明在這一群體中,詞是可以表現嚴正內容、抒發個人真實情懷志向的,而不只是像散曲一樣描寫淺近的內容與心情。在離愁別恨題材與青樓妓女題材中,詞與曲兩種文體更多體現的是相異之處。散曲在這兩類題材中抒發普通男女的離愁別恨、描寫妓女的生活場景,表現出了其通俗化、娛樂化的一面。而詞仍然是雅正的,表現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情感。由這兩類題材,可以看出詞與曲之間仍有界限,有著各自承擔的不同表現內容,保持了相對獨立性。
三
以元好問為中心的詞曲創作群體成員以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為多,均屬北方籍貫,“秉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12](P10)其主導詞風剛健清朗,質樸厚重,體現了融入北國地域文化以及北方民族文化特點的審美風格,形成了與南宋詞迥異的“北宗詞”。如耶律楚材《鷓鴣天》一詞,況周頤評價其中“不知何恨人間夢,并觸沈思到酒邊”二句“庶幾合蘇之清,辛之健而一之。”[11](P79)魏初二十五歲時師從元好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青崖詞一卷提要》評其:“詞學淵源有自也……氣剛文勁,縱橫合矩。”[11](P127)清人陳廷焯評王惲詞“骨力甚堅,仿佛孫孟文。”又評《點絳唇·楊柳青青》一詞“壯氣凌云,不作兒女語。”[13](P129)至于段克己、段成己兄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妙集提要》謂其詞“大抵骨力堅勁,意致蒼涼,值故都傾覆之余,悵懷今昔,留露于不自知。”[14](P1707)
而這一詞曲群體的散曲創作以清新明麗、閑適淡泊為其主導風格,極少豪邁之作。如商挺〔雙調·潘妃曲〕“綠柳青青和風蕩,桃李爭先放。紫燕忙,隊隊銜泥戲雕梁。”[10]P61)描寫了色彩明麗、生機盎然的春景,饒有諧趣。又如元好問〔雙調·驟雨打新荷〕:“綠葉陰濃,遍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妖艷噴香羅。老燕攜雛弄語,有高柳鳴蟬相和。”[10](P3)同樣寫景明凈,語言清新,意境雅潔。
盡管,這一群體的詞曲主導風格有前述之異,但二者在相當程度上亦呈現出趨同的樣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詞之曲化。以元好問為中心的詞曲作家群體成員的部分詞作有“俗化”或“曲化”特點,即語言俚俗活潑、意境直白淺顯,體現了與曲相類的風格情趣。甚至有些作品屬詞屬曲,已難分辨。如《全金元詞·凡例》中注意到:“金元人詞集中,往往羼入曲調,如王惲《秋澗樂府》中,竟有三十九首曲調。”[8](P3)梁啟勛《曼殊室隨筆·詞論》評李治所和元好問《雁丘詞》“已全入曲子韻味”,并云:“金在宋元之間,其中不乏文學知名,試讀元遺山、韓溫甫、李欽叔、蔡伯堅、王拙軒、李莊靖及段氏弟兄誠之、復之諸人之集,則詞曲遞嬗之消息,未嘗不可尋。”[15](P19)
雖然如此,但總體而言,這一群體的詞作雖然“俗化”,偏于散曲風格,但俗化程度遠不如散曲。如趙秉文一首成為后世散曲〔青杏兒〕標準模板的《青杏兒·風雨替花愁》詞:
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揀溪山好處追游。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8](P47)
流暢自然,明白如話,但相較于劉秉忠的〔南呂·干荷葉〕散曲小令,便可以看出詞曲俚俗程度的不同:
腳兒尖,手兒纖,云髻梳兒露半邊。臉兒甜,話兒粘。更宜煩惱更宜忺,直恁風流倩。[10](P14)
詞學蘇、辛,是這一群體的共識,蘇、辛的言志體詞得到了極度推崇。由內容而言,這一群體的詞作已經摒棄了旖旎紅軟之作,提倡描寫現實,抒發文人士大夫之志,實現了詞作內容上的“雅化”,即詞的“詩化”。而由形式而言,卻出現了通俗化、散文化的傾向。其原因不僅有金末元初時期審美風尚趨俗的影響,還有這一群體成員提倡抒發真性情的創作傾向,正如元好問所提出的“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16](P39)直抒胸懷,不拘泥于聲調格律,以散文化語言吟詠性情。此外,群體成員沿著辛棄疾“以文為詞”的道路繼續開拓,受到辛棄疾詞敘事性以及散文化語言熏染,以及其以口語、俚語入詞的特色。所有這些,對詞的俗化均產生了一定影響,造成了詞的“俗化”現象。
其次是曲之詞化。散曲本身是一種來源于民間的俚俗本色的文體。以元好問為中心的散曲創作群體成員皆為上層文人,他們秉承文人傳統觀念,以詞為曲,在散曲的俚俗本色中增添典雅之風,融入文人情懷及文人風格,使散曲具有了“詞化”傾向。這一傾向主要體現在小令及一部分套數創作中,語言典雅有致,曲風明顯傾向于詞風。如元好問〔黃鐘·人月圓〕《卜居外家東園》:
玄都觀里桃千樹,花落水空流。憑君莫問,清涇濁渭,去馬來牛。 謝公扶病,羊曇揮涕,一醉都休。古今幾度,生存華屋,零落山丘。[10](P2)
又如楊果〔越調·小桃紅〕:
滿城煙水月微茫,人倚蘭舟唱。常記相逢若耶上,隔三湘,碧云望斷空惆悵。美人笑道,蓮花相似,情短藕絲長。[10](P6)
此二首用語典雅,除“一醉都休”、“美人笑道”等略顯通俗之語外,極為類詞。
在金末元初俗文學盛行并對各體文學產生影響的環境中,在散曲本身的俚俗本色之風影響下,這一群體的散曲創作仍能夠出現雅化傾向,可以看出這一群體對散曲文體進行改造的努力,他們有著以詞繩曲的創作立場,企圖讓散曲更加靠近詞體。此外,另有徐琰與白樸,是這一群體中創作較為成熟的散曲家,他們的散曲創作能將詞的雅致與曲的本色俚俗融為一體,達到渾融境界。
但就整體而言,這一群體的散曲創作仍然顯示出本色自然、通俗流暢的曲風。不僅如楊果套數〔仙呂·賞花時〕、杜仁杰套數〔般涉調·耍孩兒〕或是商挺的言情小令等極其質樸俚俗,其他一些沾染較多詞味、較為雅化的散曲作品也常常直白顯豁,有曲之本色。這一群體的散曲既受到傳統文人詞創作手法的影響,又具有本色俚俗特色,體現著散曲產生初期受到詞體文學與民間俚曲共同熏染而形成的獨特風貌。
四
以元好問為中心的詞曲創作群體,無論題材還是風格,都既有相融又有相異之處。就題材而言,詞傾向雅化,群體成員秉承元好問所主張的“詞詩”一說,以寫詩的態度作詞,將詞體功能由應歌娛人轉向了言志抒懷。在內容上偶有俗化傾向,但其“俗”仍維持在一定程度和范圍之內,有別于曲。散曲雖也有部分言志內容,表現出向雅化方向的努力,但總體上體現的仍是娛情傾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詞的這一功能,表現出詞曲有別的文體意識。這一詞曲創作群體成員身份顯赫,雖有一定的散曲創作興致,但并沒有采取如詞一般的端嚴態度,散曲在其手中只是用以娛情遣興,思想深度不能與詞相比。正如鄭振鐸評價鐘嗣成所記“前輩名公有樂章傳于世者”時所云:“寫些歸隱、閑適、道情一類的東西,很少具有深刻的情思,只不過歌來的適耳而已。”[17](P331)并未賦予散曲深刻的社會內容和鮮明的創作個性,體現了早期曲作家詞尊曲卑的文體觀念。
由風格而言,詞以豪邁深沉為主,偏于嚴正;曲以清新愉悅為主,富于俗趣;體現了詞曲家們對于詞曲兩種不同文體的認識。此外,詞曲都有雅俗共存的特征。詞在形式上的化雅為俗,受到的是辛棄疾“以文為詞”以及當時俗文學環境的影響。曲在風格上的雅化,源于詞曲家欲以詞繩曲的創作立場,企圖讓散曲更加靠近詞體。這一詞曲風格出現雙向滲透的現象,與群體成員既尚雅致又不避俚俗的觀念是分不開的,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這一群體對詞曲存有某種共通的理解與認識。也許,在他們看來,寫作最重要的是表現真情,而非過分倚重形式。這一觀念融通了詞、曲的創作,對元代詞、曲文學的創作是具有較大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