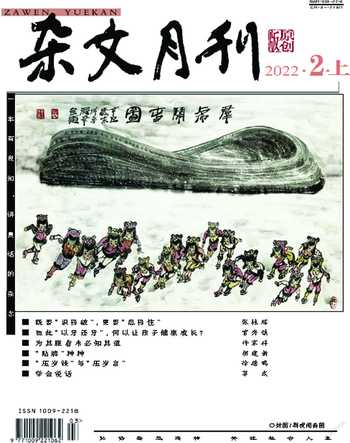“笑罵從汝”
張樹民
做到“笑罵從汝”,難,甚難。倘若是痞氣十足的官迷,則另當別論。
“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這句挺不要臉的話,是北宋官迷鄧綰面對同僚譏笑,嬉皮笑臉著說的。為能爬上高位,臉皮又價值幾何?縱觀歷史,以厚臉皮謀官而載入史冊的,鄧綰恐怕是獨一份。
鄧綰和王安石處于同時代,但當時王拗公已位高權重,而鄧綰正挖門路往上鉆。即便鄧綰腦袋再尖,倘無權貴引薦,也鉆不進堅固的朝堂,此乃大宋官場的現實狀況。鄧綰四下撒目,鎖定一個權威人物,于是,向王安石發起猛烈攻勢。《宋史·鄧綰傳》記曰:“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吹捧,歌功頌德,說王安石勝過“伊尹、呂尚”,“變法深得人心”,云云,反正變著花樣拍馬屁。別看王安石雅號“拗公”,在吹吹拍拍之下,同樣受用,且舒坦得很,便將鄧綰“薦于神宗”。
神宗召見鄧綰,問:“可認識王安石么?”鄧綰矢口否認:“不識,與其從無往來。”言之鑿鑿,以示毫無私情。而下朝見到王安石,“欣然如素交”,圍前跑后,諂笑如花,狀若搖尾之巴狗,親熱得比對親爹還親,因而得到擢拔,從寧州通判升為知州。
然,鄧綰很不滿足,伸手要“館職”,也就是“中央機構大員”。神奇得很,鄧綰跑官要官,居然如愿以償,次日就提升為“集賢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當上了諫言官,專職監察官員,后又升遷御史中丞。一個品濫德損之徒,居然監督他人,真是一出滑稽好戲。
同僚對鄧綰甚為不屑,不斷有人笑罵他,諷刺挖苦,鄧綰也不惱怒,說:“笑罵隨你們,好官還要我來做。”及至王安石丟了相位,鄧綰立馬依附宰相呂慧卿,攻訐王安石;俟王安石恢復相位,又轉回頭阿諛諂媚到極致,還出手彈劾呂慧卿。這位鄧大人,臉皮厚得堅不可摧,真個是“人笑冷齒渾不覺,升得官位是真格!”
笑讀鄧綰其人其事,我在琢磨,當時,鄧綰在官場口碑如何?從同僚笑罵來看,應該差評如潮。氣節操守,緊系人品官德,似鄧綰這等反復無常之徒,據說在民間庶民中,早當成笑料相傳,足見其口碑之差。然而,口碑似乎無關緊要,屬于“無效票”,即便是民主測評再差,只要君主和關鍵權臣看著順眼,感覺舒坦,并無丟官之虞。因此,鄧綰笑罵從汝亦安然。
鄧綰之類深諳封建官場升遷套路,兩眼緊盯著對升遷握有薦舉權、決定權的關鍵少數,功夫全下在揣摸關鍵人的喜好上,從而投其所好,百般攀附,以謀私利。鄧綰之流甚是明白,雖然“眾口可以鑠金”,但是,一旦深得關鍵人物的青睞,笑罵便化作了“小人長戚戚”,人家鄧綰笑罵從汝的“從容”,反倒成了大度能容了。在不同人眼里,有時君子和小人是可以轉換的,這便是世相百態的有趣處。當然,時間可以準確檢驗一個人的道德操守,再高明的馬屁精,也總有拍到馬蹄子上的時候,會將人猛然拍醒。正氣未泯之人一旦醒過神來,便會重新審視,君子和小人自然就歸回原位了,這個過程長短不一,但終究要回到本原。倘若同為奸佞之徒,只要事不禍己,便依舊假寐。
鄧綰為討好王安石,居然上書君主,要求錄用王安石的兒子和女婿擔任要職。神宗驚疑,認為鄧綰“佞諛太過”。馬屁拍過了頭,諂媚過了火,更嚴重的問題是主子驚疑,讓王拗公也甚覺臉上發燒,認為鄧綰“不安守本分,上書為宰相乞求恩賜,有辱國體”。于是,將鄧綰貶出朝堂。
說到底,鄧綰被貶,官場和民間的笑罵并未起任何作用。倘若鄧綰沒有踐踏君主的紅線,沒有打王拗公的老臉,恐怕“好官還要我來做”。其實,對一個官吏的考查,通過口碑可以了解到真實的另一面,有時,官吏的口碑與留給權威者的印象大相徑庭,因此,有時百姓恨得牙根疼、同僚亦不屑的人,卻屢獲升遷,就是當權者僅憑個人好惡取人造成的。
倘若用人薦舉機制不變,鄧綰之流難絕。大宋選人用人上的腐敗和不公,猶如擊潰人心的重器,污染官場生態的毒瘤,危害之烈,有目共睹。大宋官場大興吹捧浮夸攀附之風,乃其產物之一。但話又說回來,鄧綰能風生水起,在封建專制社會,并不足為怪。官場沉浮,只在關鍵少數掌權者看著是否順眼而已。
當然,倘若鄧綰之流輩出,“厚顏無恥病”流行,那一定不是什么好征兆。盡管病發于鄧綰之流身上,然而,病根卻在薦人用人導向上,所以,王拗公們著實責任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