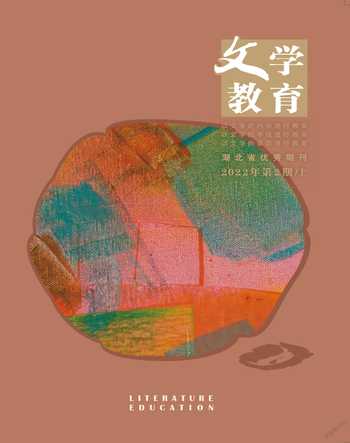一場寬闊明亮的精神性締結
鐵凝的《信使》是一個關乎“信”的故事。什么是“信”?人言為信。所謂“送信人”“報信人”,其身份就鎖定了“信”的內涵與邊界。“信”也是中國儒家文化的“五常”之一,然而,我們當下顯然是一個“信”快速崩塌的時代,不但其載體從可觸可感趨向于沒著沒落(網絡),就連內容也已經微化甚至表情包化了。
或許鐵凝正是有感于此,寫下了關于“信”的鄭重篇章。一對閨蜜陸婧與李花開的家境和際遇不同,婚戀各有曲折。陸婧愛上了從北京來的父親的同學、已婚的“肖恩叔叔”;李花開嫁給了有私房獨院、以畫彩蛋為生的遠房表哥起子。由于陸婧的戀愛頗見不得人,于是托李花開轉情書,地址就是起子的獨院。李花開要上班,所以信件往往由“永遠在家”的起子代收。這是一樁私密加親密的事,如果起子是“有信之人”,便會是兩個女人友情中的“催化劑”和“甜蜜素”。不料這是個卑鄙小人,不但無“信”,還將“信”當作了威脅陸婧的工具。每次收到信,他都會將信紙偷取出來拍照,于是“信使”成了閨蜜關系惡化的“引爆器”。
說起來,起子的目的倒也并不多么卑下,他無非是以此為要挾,讓陸婧的文教局局長父親幫他調到一個“鐵飯碗”單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通過這些不體面的信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清高的陸父聞之震怒,此事既然不成,起子便將信的照片發往陸婧和肖恩的單位,還有陸局長。陸婧被父親趕出了家門,憤怒之極的她給李花開打電話大嚷了一通,就此絕交,然后去了北京,閃婚嫁人。三十多年來,她一直以為這是李花開和起子的合謀,她的友情、愛情和親情一起被埋葬了。
故事說起來并不復雜,但鐵凝卻以巧妙的敘事將一個不復雜的故事講出了豐盈動人的韻味。在“倒敘/現實”的閃回和嵌合中,一個包裹在友情中的關于愛、信、守的故事被層層剝露開來,每一層都攜帶著強烈的沖突和戲劇性,也帶來了兩個女人關系的陡轉與突變。一場關于“信”的誤會在三十多年后才被解開。原來,起子干的事李花開一律不知曉。在得知陸婧被“出賣”后,懷有身孕的她從房頂上跳下來,只為了逼迫起子離婚。之后,她跛著一只腳回到老家生下了兒子,與初戀結婚。兒子善跑,進了國家隊。她退休后便隨兒子來到北京,開了一家體育用品商店。丈夫留在老家開發旅游業,亦有不錯的前景。
鐵凝的情感傾向和價值判斷是鮮明的。“信使”起子玷污了“信”之名,就算有私房獨院,也留不住單純美貌的妻子。與猥瑣的男人相比,兩個女人的形象格外地精彩、漂亮。這漂亮不單指外貌,更是她們的有情、有義、有堅持、有擔當。陸婧在被起子的威脅惹惱后,一把抓起燒水的鋁壺,倒入爐火正旺的爐膛,用力地摔門而出;“軸女子”李花開為了朋友而決絕地與起子離婚,為了離婚不惜命地從房頂上跳下,跛了腿也不后悔。這是何等地快意恩仇,凜然剛正!用她的口頭禪“值嗎”來說,這些又“傻”又“軸”的行為很“值”。因為人生必須得要有這么些個剛烈的時刻,才扛得住那些言而無信、背信棄義、忘恩負義帶來的致命打擊。這些看上去“無用”的抗爭成就了兩個女人,她們成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使”:一個恢復了對友愛的信念,內心重新圓滿;一個離開小人,嫁得良人,用自己的“信”掙來了后半生的安心和穩妥。
一個“信”字,讓我想起了年輕時讀過的小說《千江有水千江月》,臺灣作家蕭麗紅所作,主人公名為大信和貞觀。“女有貞,男有信,人世的貞信恒常在”,可惜一場苦戀,終因大信無“信”(信件和信諾)而結束。
我又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鑄劍》,無數人喜歡它的壯烈、奇詭、跌宕起伏、驚心動魄。我卻喜歡它傳遞出來的兩個字:一是“義”,二是“信”。黑色人幫眉間尺復仇,不為私利,只為道義;黑色人向眉間尺要他的頭和劍去復仇,說:“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眉間尺舉手抽劍,從后項窩向前一削,頭顱墜地時,他將一條冰似的青劍遞出。人間大信,莫過于此。
在當代文學中,像《信使》這樣直接以“信”為主題的故事并不多見。“信”是人對自己立下的“契約”,這看上去容易,實際上是一場艱難的跋涉和持守。鐵凝用爐火純青的技藝,舉重若輕地傳達出了這場精神性的締結。當“有信之人”被證實為是卑鄙小人、“有信之地”化為烏有時,關于“信”的信念依然是存在的,依然有人愿意為了不知能否兌現的“信”而做好了付出生命代價的準備,這是《信使》帶給我們的寬闊和明亮。
曹霞,文學博士,著名文學評論家,南開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