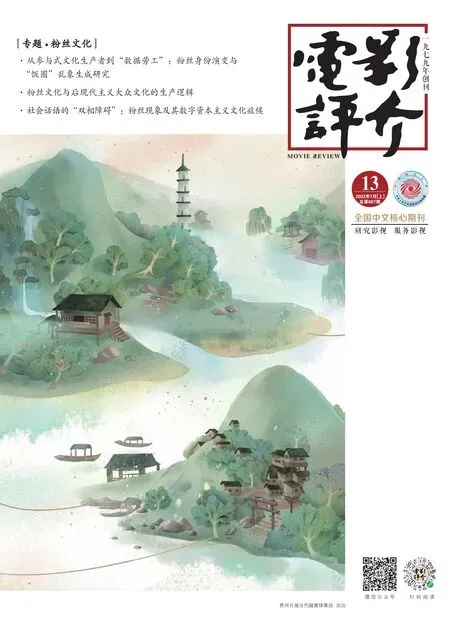《我在他鄉挺好的》的異鄉寫實、多重視角與話語空間
甘圓圓
《我在他鄉挺好的》是一部小體量、高密度的現實主義題材劇,作品通過劇場式的寫實手法,講述了四位青年女性在異鄉生活的歡笑與淚水,以此凝練出“異鄉打工人”群體性的生存形態。電視劇開播后被觀眾稱為“最人間的女性群像劇”,且豆瓣評分高達8.3分,超10萬網友為此劇打分。在現實主義題材劇日益趨同的當下,《我在他鄉挺好的》能夠在同類型電視劇中脫穎而出,一方面得益于創作者對異鄉生活的體察和感悟,使作品呈現出既“真”又“近”的藝術效果,另一方面是作品在深入觸及群體精神困境時,沒有固化地販賣公眾焦慮,而是通過更包容的話語空間帶動積極的反思和價值觀念的突破。該劇以大量真實的生活情節刻畫了都市群體生態,現實且鋒利地呈現了情感孤獨、精神抑郁、職場競爭還有虛榮消費等問題,但是作品又沒有僅僅停留在還原真實生活的層面,而是通過對庸常生活的書寫來突出生命狀態的執著。本文將從寫實生態、視角運用和話語空間拓展三個角度分析《我在他鄉挺好的》的獨特之處。
一、群體寫實生態與庸常個體面相
現實主義題材劇長于書寫千姿百態的大眾生活,基于對社會熱點議題的反映和剖析,多層次、多角度地記錄不同群體的生活圖景。《我在他鄉挺好的》以四位身處女性的成長經歷為切口,呈現了繁華帝都中北漂一族的真實生活。相較于同類型作品而言,該劇雖然以女性視角切入,但是并沒有在性別觀念的基礎上搭建空中樓閣,而是將她們看作生活中最普通的個體,言說出“我”在他鄉的真實生存狀態。
(一)全景描摹下的群體寫實
《我在他鄉挺好的》顯現出的真實感,主要得益于全景視角下的群體寫實手法。第一層是對社會百態的全景展示。劇中用了眾多遠景鏡頭呈現出繁華都市的人潮洶涌、緩慢前進的汽車長龍、早晚高峰期地鐵站外擁擠的人群、寫字樓前步履匆匆的上班族等。遠景鏡頭的使用不僅渲染出緊張、躁動的氛圍,還能襯托出在茫茫人海中個人的微不足道。同時攝像機跟隨人物在各個場景中來回穿梭,以手持肩拍的方式追求晃動、慌亂的效果,讓觀眾在視覺上感受到人物的驚惶、急躁,同時輔以主人公面無表情的臉部特寫,展現出快生活節奏下人物內心的壓抑和麻木。
第二層是對異鄉奮斗者生活狀態的全景展示。從題材類型上講,都市女性群像劇大都會以女性群體的精神困境,折射出城市化進程和消費主義潮流中的階層矛盾和價值沖突,觀眾在凝練寫實的情節中建立與主人公的情感連接,從而產生內心的共鳴、認同和投射。《我在他鄉挺好的》抓住了異鄉租房、職場內卷等具有普遍性的現實問題,作為本劇現實主義創作理念的思想底色。奮斗多年事業沒有起色的喬夕辰,工作勤懇努力卻因為沒有資源被辭退的胡晶晶,事業小有成就卻困于婚姻焦慮的紀南嘉,缺乏遠見又陷于女性消費誘惑的許言,這些人物的性格特質在一定意義上承載了都市年輕人的群體共性。在喬夕辰的公司里,市場部總監盧以寧即將臨盆仍然堅守崗位,羊水破裂后還在救護車上安排工作計劃,諷刺的是救護車剛走,接替她的新總監立即走馬上任,充滿現實感的情節正面展現了職場競爭的殘酷。
第三層是對異鄉群體選擇困境的全景展示。對于書寫“漂”群體的現實主義作品來說,關于異鄉游子失根與尋根的精神困境,一直是這類作品著重探討的話題之一。《我在他鄉挺好的》也不例外,電視劇在“歸鄉心”這一主題中,講述了三位女孩春節期間回到東北老家遭遇的窘迫問題,盡管家鄉還有牽掛的父母家人,但是那些不再熟悉的街頭,無法融入的話題,還有故鄉翻天覆地的變化,都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她們,她們在故鄉人的眼中也成為了異鄉人,一句云淡風輕的“挺好的”,背后呈現出的是失根的焦灼和尋根的迷茫。
(二)對平常個體的精心刻畫
在以女性為敘說對象的作品中,個體敘述將單一人物作為敘事中心,而集體敘述會以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女性人物為敘事中心,而且每個表現對象都有與眾不同的性格特征。“對觀眾來說,他們真正關心的是人,只有讓他們了解了沖突中的人物,關心人物的命運,才能真正地感受到沖突的尖銳程度,才能真正地感受到沖突的意義。”[1]比如說《粉紅女郎》中的結婚狂、萬人迷、男人婆、哈妹,《歡樂頌》中的安迪、樊小妹、曲妖精、小蚯蚓,還有按照女性群像題材量身定制的《三十而已》《二十不惑》。這些電視劇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具體的、個別的、獨特的,不同的人物設定不僅能展現出女性形象的多面性,還能使作品更具生活流、更具原生態感。
與熱衷于塑造“精致幻象”的都市劇不同的是,《我在他鄉挺好的》選擇了四位具有典型意義的外來打拼者作為敘事主體,并將她們的標簽定義為勤勤懇懇的普通人。其中經濟條件最好的紀南嘉,代表了最早來到北京打拼的一代人,獨立自主且有明確的事業藍圖,與其他三個女孩相比,紀南嘉的能力和情商更為出眾,但是觀眾也會看到她因為客戶的臨時要求而加班到后半夜,也會因為買房子湊不齊首付款而焦慮不堪,向客戶追要尾款時也會低聲下氣,要債未果反而被對方訛了一瓶三千多元的高端酒,等等。作為三十六歲的單身女性,婚姻焦慮無疑是紀南嘉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父母千里催婚,還數落女兒長得難看就得擺正自己的位置,還有小侄子無意間說出的“你死了,這些都是我的”。可見紀南嘉的一切努力都因為單身而變得毫無價值,且始終逃不開世俗觀念中的“被看”視角,當她鼓足勇氣去相親時,卻在婚戀市場上被人挑揀奚落,如其嘆道:“我活了三十六年好不容易活成現在這樣,兩分鐘就把我否決了。”
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喬夕辰則代表了“漂泊的大多數”,沒有美貌和身材,沒有強大的社會背景和貴人相助,只是寫字樓里最兢兢業業的打工人,每天面對的是加班的夜晚、擁擠的地鐵和精打細算的生活。早上兩個小時的通勤路,本以為可以借此機會看看書、刷刷劇,結果早高峰的地鐵擁擠到手機都拿不出來,真實的筆觸使得網友們大呼“這部劇偷窺了我的生活”。而年齡最小的許言則困于容貌焦慮和虛榮消費的牢籠,喜歡大房子、名牌包,又沉浸在愛情的世界中不想成長。
可貴的是,作品雖然真實地書寫了女性在家庭、婚姻和事業中的進退兩難,但是卻沒有屈從于現實,單一地做社會問題的“放大鏡”。電視劇以“此心安處是吾鄉”為創作主旨,通過庸常個體傳遞出立足于女性成長的全新價值觀。紀南嘉經過婚姻焦慮和住房焦慮后能夠釋然,喬夕辰經歷事業坎坷后更堅定了心之所向,而許言在感情敗北后選擇回到故鄉陪伴生病的母親。《我在他鄉挺好的》真正的動人之處在于,以幾位女性的庸常生活切實地詮釋了“我們如此努力卻依然平凡”的悲壯,但是女主人公們敢于追求不同價值向度的幸福和自由,在生活應然與實然的裂痕中活得勇敢、熱烈,也使不同年齡段、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從中找到了自身的情感投射,傳遞出具有現實導向意義的新價值觀。
二、多重視角的靈活運用與藝術內涵
藝術創作的空間視角分為仰視、平視和俯視三種,其中平視視角可以使事物呈現出本來面目,避免了表現對象的夸張變形,以平視視角表現人物和人物所處的環境,需要創作者將自己與人物置于共同的生存空間,把自己對時代生活的感知和體察移情到表現對象身上。《我在他鄉挺好的》能夠靠真實感打動人心,主要來源于兩位編劇十年北漂生涯的點滴積累。在劇中,喬夕辰早晨到達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換工作鞋,因為編劇虢爽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總結出“擠地鐵必須穿雙舒服的鞋子,要不根本就擠不進去”,而且喬夕辰被坑騙了半年房租的事情,也是編劇們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所改編。“任何作家都只能在自己經驗的范圍內和對社會問題認識的水平上進行創作。”[2]只有真正感知過人物的生活狀態,才能對異鄉人的生活痛點刻畫得既直白又精準,才能使置身于繁華都市的四位女性,既代表她們自己,也能代表千千萬萬個異鄉追夢人。
但是從某種意義來講,單一的采用平視視角,往往只能呈現出事物的表象,停留在對事物的表層認知中,無法從不同層面、不同維度反映人和事物的復雜多面。所以為了克服平視視角的局限性,創作者在某些時候需要從宏觀上透視人物的行為邏輯和情感走向,以俯視角度看到獨立事件背后錯綜復雜的成因,這樣才能使觀眾透過現象看本質,剖析社會現象與人物情緒背后的動因。對此,《我在他鄉挺好的》通過不同性格的人物透視生活的多面性,且精準地把握了人物的精神命脈和成長走向。比如該電視劇開篇便通過胡晶晶自殺設置懸念,然后以倒敘的線性敘事手法為觀眾解開謎題,失業、被分手、高利貸催債、家人的痛斥等種種負面情緒的長期積累,成為將人物推向絕望的原因。胡晶晶自殺之所以讓人心痛又不突兀,是因為觀眾在“非我”但“似我”的人物身上感知到了彼此共通的辛酸苦楚,是因為在成年人的多面人格中確實存在著“微笑抑郁”這樣的附屬面相,所以對于這樣的情節設置,觀眾在心酸之余會發出“成年人的崩潰從來不是一個瞬間”的感慨。創作者準確恰當地運用俯視視角,綜合了群體的生活共性,塑造出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形象,并通過“上帝之眼”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動,在必然性的角度上調配人物的行為軌跡和精神走向,這樣的創作方式,既能凝練人物的性格特質,也能使作品具備高度的穿透力和概括力。
在電視劇創作中,仰視視角是最不常用的一種創作方式,創作者過于虔誠的仰視角度往往會造成表現對象的夸張變形,因為將人物或者事件過于神圣化,會潛意識地創造出“似神非人”的銀幕形象。但是當創作者需要通過人物向觀眾傳遞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念時,誠懇、真摯的仰視角度,反而有利于其發掘人物身上的美德和智慧,同時也能在一定意義上拓寬作品的精神內涵。所以有評論家認為“藝術創作的最佳狀態應是仰視、平視和俯視的交叉與有機結合。”[3]《我在他鄉挺好的》就是以仰視視角發掘人物身上的人性閃光點,為苦澀的生活注入溫情,紀南嘉的擔當、喬夕辰的勤懇、許言的真誠和胡晶晶的熱情,這些平凡女性身上顯露出的高尚品質,使該劇呈現出深沉、強烈的精神感召力。作品既不回避人生道路上的坎坎坷坷,也不忽視普通人之間的溫情傳遞,這種溫情是當你一個人在醫院打針時,小女孩放在你手心里的一塊糖,是你在烈日炎炎下不知所措時,陌生人勻給你一半的遮陽傘,是你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困境中一蹶不振時,姐妹們傳遞給你的關愛與溫暖,正如喬夕辰所說的“想離開的理由有很多,但是留下來的理由一個就夠了”。
除了以不同視角、多層次地展現藝術形象之外,該劇還采用了12集,每集70分鐘,一集一話題的劇場式模式結構全篇。對于集體敘述的女性題材劇而言,這種以生活的枝節片段建構故事情節的開放式敘事結構,使作品在形式上更加大眾化和生活化,同時還能調動觀眾的積極性,喚起觀眾的參與意識。而且在劇中每個人物都有各自的沖突和獨立主題,故事情節也都按照縱線的時空軸線進行,然后將幾條平行的故事線橫向串聯,縱向時空軸線與橫向獨立主題并行,完成了一場并列式的集體敘述。比如第四集中圍繞“安居處”的標題,講述了喬夕辰因為中介、室友等問題兩度搬家,在價格、交通、戶型等方面反復權衡后,最后選擇在城市邊緣處安家。而紀南嘉租住的房屋因為年久失修問題頻現,想要重新裝修卻遭到了物業的阻撓,最后在租房和買房之間躊躇不決。從結構來看,兩件事情都有各自的緣由和沖突,在情節發展上也沒有因果聯系,但是兩個事件在整個文本中共同服務于同一主題,即對于都市異鄉人來說,安全、安心、安家的問題永遠是個無窮解。
三、話語空間的現實揭露與深度拓展
(一)重“生活”輕“藝術”
以塑造女性群像為主的藝術作品,在話題性和人物豐富性上占據明顯的優勢。在“得女性觀眾得天下”的創作環境中,自帶熱搜體質的女性群像戲為了增加話題討論度,往往會走向兩種極端:一種是利用話題熱度販賣公眾焦慮,以重“藝術”輕“生活”的手法,刻意塑造出標簽式的人物形象來增強作品的戲劇沖突,使女性形象和女性的精神成長逐漸扁平化;一種是人物困境缺乏普遍性和真實感的懸浮創作,劇情橋段缺失基本的藝術邏輯,依靠巧合統領故事、制造轉折,最后通過編劇的“金手指”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為觀眾制造廉價的興奮。從這樣的書寫方式可以看出創作者缺乏對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同時也限制了觀眾對真實生活圖景的認知。
《我在他鄉挺好的》對生活瑣事的重點關注和對情節連續性的淡化處理,反而突出了作品對生活本真的頌揚,在電視劇中沒有輕松地用幾十萬體驗生活的颯爽形象,沒有可以灑脫地用人生A計劃或者B計劃來無限試錯的她們,也沒有令人啞然又迷惑的臺詞。作品的重“生活”輕“藝術”是指劇情沒有過多依賴“金手指式”的開掛方式來化解矛盾,而是通過敘事結構的“減重”,使文本更加凝練,隱喻性更強。比如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室友,竟然不記得對方的名字,喬夕辰的獨居生活只能靠安裝假監控探頭和帶假人影的窗簾來抵御恐懼心理,在客服中心工作的許言連“感謝您的來電”都沒有說完,就被粗暴地掛斷了電話,為了湊夠房屋首付款,許言違法刷單被騙后,對方偽裝成警察再次將她剩余的積蓄榨盡,還有工作中突發急性心肌梗塞的同事,不遠千里來投奔的鄉里鄉親,等等。電視劇沒有生硬地復制輿論槽點,而是通過大量的生活閑筆展現出人物艱辛而焦慮的生存現狀,反映出人物在外部壓力與內心需求之間的失衡。
(二)灰色空間的突破呈現
《我在他鄉挺好的》突破性地呈現了世俗生活中的灰色空間和灰色精神狀態,以此來諷刺逐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淡漠。胡晶晶的經理看似高尚、實則畸形的職場邏輯堪稱現實版的人血饅頭,“你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就應該幫助其他人呀,年輕人不能太自私”,惡意辭退職員還不愿支付賠償金,以推薦信要挾員工主動離職,機關算盡和狡黠的處事方式,使電視劇呈現出更深層的現實意義。喬夕辰堅持在工作中“人總得相信點什么”,轉身便遭遇了職場中的“農夫與蛇”,只能含淚吞下因幼稚而引發的惡果。周末在電影院放松心情,被公司市場部催要產品策劃方案,還被指責道“我和同事在加班,你看電影,合適么”。病態的道德綁架逼迫著人們屈從于規則、適應規則到最后主動利用規則,在灰色精神狀態的滲透下,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該劇通過富有象征意味的生活細節,呈現出世俗生活中介于黑與白之間的灰色空間,影射商品經濟時代人們精神世界的畸變,同時也表現了創作者對女性內心世界的關懷,以期喚醒大眾對女性社會群體的關注。
結語
對于現實主義題材劇而言,《我在他鄉挺好的》以通透的眼光呈現了一群具有典型意義的異鄉群體,展現“漂”族們的集體生存困境。作品敢于打破以往職場劇的成功之道和精英定律,用回歸真實的方式,直言普通人在生活、事業、情感中的種種考驗,同時折射出社會問題的多元性,所以該電視劇開播后被觀眾稱為既“致郁”又“治愈”的生活劇。由此可見,創作者只有從生活本真出發,真正融入藝術形象的精神成長和生命軌跡,才能豐富現實主義題材劇的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