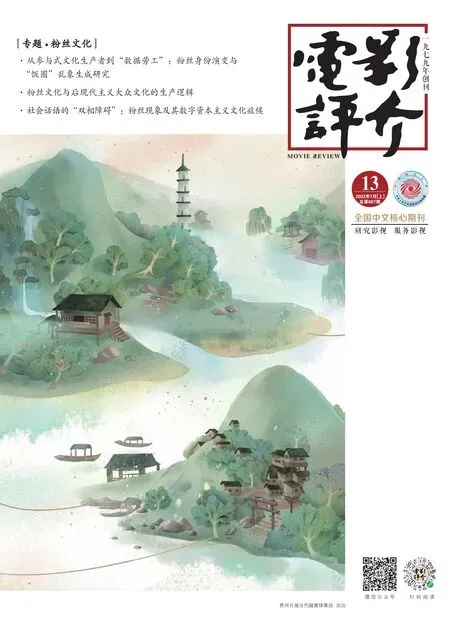《盲琴師》:存在主義的影像表征與潛敘事
徐夢晨
2021年12月10日,波蘭電影《盲琴師》(馬切伊·佩普日察,2021)登陸內地院線,最終以105.5萬元的票房成績收官。①數據來源于“貓眼票房”.《盲琴師》累計票房[DB/OL]http://pf.fe.st.maoyan.com/dashboard.從票房上看,《盲琴師》的成績并不理想,但著眼電影本身,其藝術成就卻不容置疑。實際上,該片于2019年在波蘭本土上映,并在波蘭電影節上大放異彩,在歐洲各大電影節上表現也十分亮眼。該影片改編自波蘭天才盲人鋼琴家米耶奇斯瓦夫·科什的真實人生經歷,講述了他杰出又飽含悲劇色彩的傳奇一生。在《盲琴師》中,觀眾既能看到用非線性敘事勾勒人物傳記的高超手法,又能看到盲人視角的創新鏡頭,既能感受到音樂之于電影的重要意義,更會驚異于可見影像對不可見精神、意志等內在世界的探尋和表現。聚焦意識世界的影像充滿著存在主義的特征,其不僅體現在對“意識存在”的影像外化,也通過影像構成了對“意識存在”的潛在敘事,描繪了整個生成和變化的完整進程。在《盲琴師》中,觀眾隨影像窺探盲人鋼琴家的內心,從其內心透視整個人生。影片從個體生命出發,折射出存在主義的哲學力量。
一、存在主義與波蘭藝術電影
存在主義可以說是二戰后最具影響力的思潮之一。在存在主義之前,基于邏輯性、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想在哲學體系中占據統治地位,而存在主義卻將關注中心從世界的外在理性轉移到“人”和人的精神意識世界中來。存在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經歷了海德格爾的完善和發展,最終由法國哲學家保羅·薩特將存在主義推向了高潮。從薩特開始,存在主義開始滲透到文學、戲劇等其他領域,逐漸成為一種文藝內核。薩特認為:“當代哲學在本質上是戲劇性的”,“戲劇具有哲學意味,哲學又帶有戲劇性。”[1]以存在主義思想為核心,薩特創作了一系列戲劇作品,開啟了存在主義哲理劇的先河。薩特以為劇作家的任務是在這些極限處境中,選擇那個最能表達他的關注的處境,并把它作為向某些人的自由提出的問題介紹給公眾。[2]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主人公在極端境遇下,基于人與人關系中的利弊,做出了“自由選擇”,由行動引發后果,而這些后果,往往是離別、湮滅等,這與薩特思想里所主張的個人為自我的自由選擇承擔以及他“虛無”的思想相呼應。而電影藝術本身的故事內核也是從戲劇發展而來的,可以說,薩特的戲劇創作為存在主義電影的最終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實踐基礎。
存在主義電影,泛指主題或具體議題指涉存在主義哲學命題,或故事情節、人物性格、物象形態等能引起存在主義哲學思考的電影。[3]從這個維度上來審視電影,一系列在極端矛盾下關注人的生存狀況、精神世界,探討人與世界的關系,揭示個體自由選擇及其后果的電影都可以被納入存在主義電影的體系中。縱觀世界電影的發展史,“存在主義”已然成為藝術電影發展的重要思想根基和方向。以《盲琴師》為切入點回顧波蘭存在電影的發展,其根源十分深遠——二戰后,隨著羅茲電影學院培養的安杰伊·瓦依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羅曼·波蘭斯基、安杰伊·蒙克、克日什托夫·扎努西和馬雷克·科特斯基等一批電影人進入電影業,成長為波蘭電影的大師級人物,直到20世紀50年代,波蘭電影學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波蘭電影漸漸走向存在主義電影的創作方向,影響深遠。這一時期較為著名的存在主義電影包括《繩套》(沃伊切赫·耶日·哈斯,1957)、《再見》(沃伊切赫·耶日·哈斯,1958)、《偉大戰爭的真實結局》(耶日·卡瓦萊羅維奇,1957)、《夜行列車》(耶日·卡瓦萊羅維奇,1959)和《修女喬安娜》(耶日·卡瓦萊羅維奇,1960年)、《夏天的最后一天》(塔德烏什·孔維茨基,1958年)等。20世紀70年代,戰后宏大的民族歷史主題開始消解,創作者開始將視角轉向對個體及其心理的關注。這一時期的電影人以克里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為代表,其作品《紅白藍》三部曲、《機遇之歌》(1987)《愛情短片》(1988)等無一不在探討人的存在、選擇、意識世界的掙扎與最終幻滅,煥發著存在主義的思想光芒。
近十年來,波蘭電影業人才輩出,波蘭電影也迎來新的高峰,《獵人》(馬辛·克里茲塔洛維奇,2012)、《修女艾達》(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2013)、《流浪詩行》(克日什托夫·克勞澤,2013)等藝術電影佳作享譽世界,其中存在主義的思想主題一直貫穿其中。《盲琴師》導演馬切伊·佩普日察就是波蘭存在主義電影創作浪潮中涌現出來的佼佼者。作為新世紀波蘭電影的新生力量代表,早在2013年,就以一部《生命如此美好》征戰蒙特利爾電影,并一舉拿下第37屆蒙特利爾電影屆宗教人道獎。和《盲琴師》相似,《生命如此美好》仍然基于真實事件改編,聚焦的也是“殘疾個體”的生命經歷。在《生命如此美好》中,主人公因先天殘障導致永久性肢體痙攣,并無法開口說話,疾病、殘障成為他生命的阻力,但少年不斷成長、不斷突破,最終能夠成功地進行自我表達。在這個過程中,自身的存在、個體與自身、他人,與世界的關系成為影片關注另一重點,這一存在主義視角也被延續到《盲琴師》中。
二、存在與虛無:存在主義電影潛敘事
薩特是通過“存在與虛無”的關系來說明人與世界的關系。所謂“虛無”,就是指薩特思想體系中基礎的“否定性”:一方面,他認為人的內在存在和外部世界一樣,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即“自在”和“自為”。人的自在是他現在所處的生活境況,而人的自為表現為對已有的存在境況的否定,這種否定包含著對個人存在的探索和自由選擇,以達成意識的自由,也是存在主義所談論的根本的“自由”;另一方面,他從否定上帝的角度去強調人的存在性,“上帝已死”的思想使得其與傳統的神學存在主義和宗教存在主義產生了質的分野。[4]在電影《盲琴師》中,主人公米提克從小被寄養在修道院中,他在宗教的“禁欲”教育中依然保留著作為“自我”的“人性”,他對作為女性的修女們有源自性別的本真好奇和沖動,會偷窺修女沐浴;他接受修道院的教育,卻不遵守教條化的音樂演奏風格,叛逆、自我,熱衷于被修道院所不容的“靡靡之音”。這一切無疑可以看做是對“上帝”的反叛,“童年”這一敘事副線,可以看做是米提克在生命奮進中,“自由選擇”開端。另一條重要的隱線則是米提克和父親的關系——父親因為米提克的眼疾而離棄他,這也成為他悲劇的開始,也可以說,父親的否定奠定了米提克“自我虛無”的心理基礎。他終其一生都是在否定因眼盲而“被離棄”的境遇,而這個境遇是由父親“定義的”。米提克也正是這個過程中去演奏、作曲,去完成自我探索和自我超越。
薩特在自己的著作《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闡述了關于人自身存在的觀點——“人始終處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去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既然人是這樣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這方面掌握客體,他本身就是他超越自我的中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觀性宇宙外,沒有別的宇宙。這種構成人的超越性和主觀性的關系——這就是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之所以是人道主義,因為我們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別無立法者;由于聽任他怎樣做,他就必須為自己作出決定;還有,由于我們指出人不能反求諸己,而必須始終在自身之外尋求一個解放(自己)的或者體現某種特殊(理想)的目標,人才能體現自己真正是人。”[5]在《盲琴師》中,主人公米提克因為眼疾幾近失明,經歷了被父親“謀殺”、拋棄之后,最終在修道院長大;因為鋼琴演奏的風格不斷被壓制、否定;米提克憑借其音樂天賦,開啟了自己的鋼琴家之路,卻因為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局限一路坎坷,不斷被“拋棄”;但是米提克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對音樂的追求,始終在探索更高的音樂境界,以此實現自我。如果說,因為遺傳基因而注定失明是米提克的“自身”,那么米提克學習鋼琴,精進技巧,鉆研演奏風格,作曲取得突破,在一次一次“被拋棄”的絕望中重新振作的過程就是超越“自在”而追求“存在”的過程。
同時,在米提克的奮斗歷程之外,也需要看到作為一名盲人鋼琴家,他的人生存在一種悲劇性,這可以看作是《盲琴師》傳記體系中的潛在敘事線。對于米提克來說,生理的缺陷導致了其一系列不幸的人生遭遇,一步步加深了其心理否定與懷疑,最終使他走向自盡的結局。為了構建這一潛在敘事線,影片采用非線性的剪輯方式——“現實時空”的故事從米提克回家參加母親的葬禮開始,逐步過渡到米提克前往華沙參加國際爵士音樂節,米提克憑借在此次音樂節的表現一舉成名,新的生命歷程就此展開。另一個敘事時空則是在不斷的閃回中逐漸建立,兒時的米提克原本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家庭,但隨著他的眼疾嚴重,父親選擇拋棄他,這是米提克第一次“被拋棄”;為了挽救米提克的生命,母親將其帶離家,送往修道院,對于米提克來說,母親的離去是又一次“被拋棄”;米提克在修道院中學琴的童年,雖然得到修女的照顧,但也在孤獨中靜待“失明”的到來,雖然學習了鋼琴演奏,但他喜歡的音樂風格卻被看作是“靡靡之音”,最終修女也“拋棄”了他;成名前的米提克在餐廳演奏鋼琴,但餐廳老板和飯館的客人卻對米提克看似瘋狂、自我,實則天才的演奏風格并不理解,這也代表了他被“主流”拋棄;當他被制作人發現,并在華沙嶄露頭角時,一直陪伴他的伙伴也選擇離他而去;當他找到心儀的歌手合作,并漸漸對對方暗生情愫時,女孩卻選擇終止合作,同時將這份愛情徹底扼殺;當他重新與人相愛,重新找到創作激情時,卻在重壓下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一個鋼琴家的傳奇傳記,同時也是一個個體走向毀滅、走向最終虛無的人生軌跡。薩特闡釋到:“人的實在在自身存在中是受磨難的,因為它向著一個不斷被一個它所是的而又不能是的整體不斷地糾纏的存在出現,因為它恰恰不能到達自在,如果它不像自為那樣自行消失的話。它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痛苦意識,是不可能超越的痛苦狀態。”[6]《盲琴師》中“拋棄”這一敘事線,正是薩特所說的“實在的痛苦”,而這一結局就是薩特所闡述的“虛無”的一種形式。
三、鏡頭與物象:存在主義的影像表征
作為一門以視覺為基礎的綜合藝術,電影能夠在發展中成為思想表達的載體,始終要落腳到電影創作者對電影影像的掌控和創造中去。對于存在主義電影來說也是如此,只有通過一系列屬于視聽范疇的電影元素的表征,才能精確地向觀眾傳達影片的存在主義思想。在影片《盲琴師》中,觀眾不僅能看到特殊鏡頭對人——特別是主角米提克——所屬境遇的表現、對心理狀態的隱喻;通過色彩和影調的變化,隱喻時空和人的變化;也能看到影片選取的特殊物象,揭示主人公自身存在的形成和變化;還能看到對在此傳記片中擔任重要角色的“音樂”這一元素的創新運用,最終呈現出的效果,讓觀眾領略到故事之外的人生哲思。
對于存在主義電影來說,展現一個人的“存在”,必定離不開人的主觀視角。但對于《盲琴師》來說,由于主人公存在視覺障礙的特殊性與電影的視覺性是相悖的,所以難以直接呈現出主人公米提克的主觀鏡頭,但創作者依然通過特殊鏡頭的處理,既表現了盲人的視覺特性,又展現了一種更為內心化的主觀視角。較為突出的鏡頭當屬米提克在華沙國際音樂節的舞臺演出前,尚未適應舞臺的他遲遲不能進入演奏狀態,他的慌亂、迷茫通過舞臺暴露在觀眾面前,這時小景深轉軸特寫鏡頭深入到觀眾席的內部,放大了觀眾對于米提克的質疑。這組鏡頭可以看作是米提克的心理主觀鏡頭,昏黃的燈光以及并不明朗的畫面,暗示著他因眼疾窺視到的世界樣貌:觀眾的竊竊私語、身上的配飾、包的拉鏈,無一不透露著觀眾的不耐煩、質疑甚至是嘲笑。從寫實的角度去分析,這些觀眾席上的“細枝末節”是不能被處在舞臺上并幾乎失明的米提克盡收眼底的,所以,這組鏡頭的處理更偏向于對米提克的心理活動進行展現,融合了米提克在極端環境下的心理想象。相比于對觀眾席的窺探,影片在講述米提克兒時失明的時間線時,通過“遮蔽鏡頭”表現米提克眼中的世界更為寫實。在米提克的眼睛里,世界模糊而昏暗,像是小孔中的幻象。隨著米提克的病情進一步惡化,鏡頭的遮蔽范圍進一步擴大,也傳遞出一種更深的壓抑感。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特意根據主角不同的狀態,賦予了畫面不同的色彩和影調——兒時的修道院是近乎黑白的冷色調;當米提克成名成家后,他開始活躍于聚光燈下,畫面變得明亮閃耀。
除了鏡頭上、技術上的藝術創意,《盲琴師》在鏡頭內容的選擇上也形成了一種“物象隱喻”的藝術效果。一方面體現在鏡頭對身體局部的選擇上:在影片開頭,米提克前往母親的墓地,鏡頭首先呈現了一雙在地上摸索的腳,比起開篇車窗內帶著墨鏡的米提克的正臉,這個身體局部特征的選取更能表現他作為“盲人”的生理特征;在兒時的時間線中,影片給米提克的紅腫眼睛做了大量的特寫,這樣一雙病態的眼睛一再強調著米提克的悲劇命運。另一方面,電影文本中還塑造了幾組相互呼應的物象,對米提克的悲劇命運形成一種巧妙的隱喻。其中最值得稱道的當屬“關門”這一隱喻,當米提克一再“被拋棄”時,他回想起在修道院的日子,母親關上門離開,修女也關上門離開。那扇被關上的門就是貫穿米提克人生軌跡的一個物象隱喻;米提克在家中演奏,鋼琴上的花束隨著他的演奏微微顫動,而花朵繽紛的顏色卻只出現在米提克尚未生病時,幼年時的他也曾擁有父母的疼惜,母親哼著童謠,教給他花朵的顏色,也許那就是米提克一生中最為“鮮艷”的日子,之后的苦難讓生活“褪色”;當愛情出現,花朵也再次出現,這代表著米提克對生活的熱愛、對音樂的熱情再次復蘇,但整個影調卻不如回憶中那樣鮮艷,“復蘇”是短暫的,天才也最終選擇以離開世界的方式飛向空中。
結語
電影藝術發展到今天,已經開辟出了在畫面之內、在故事以內的第三個層面。在這個層面上,電影傳達著更深層次的思想,對人和社會的過去、現在、未來提出疑問,并在電影文本中去不斷求索。對于存在主義電影而言,對存在主義思想的探究和表達無疑是創作者的核心意圖之一,透過《盲琴師》,能夠再次看見波蘭電影的內生力量,也瞥見了存在主義思想的光芒。人在影像中生存,也在影像中完成存在主義的自我表達;影像為了表現人的存在,也被賦予了超出“呈現”之外的“象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