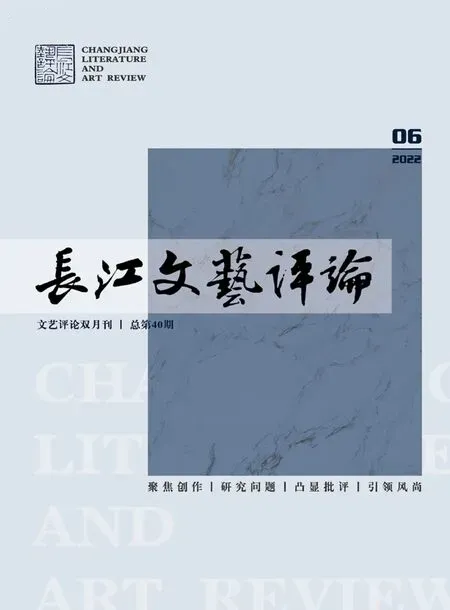《批評的返場》:重建“文學”的行動檔案
◆李 瑋
文學批評如何面向急劇變動的文學場?這是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面臨的重要問題。新世紀以來,“文學”的存在方式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是,從微信公眾號到新浪微博等自媒體文學蓬勃興起,網絡文學以及周邊衍生、劇本殺、新歌詞體等“文學”樣式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傳統文學期刊和出版也在不斷調整姿態。文學經典化問題,文學標準的問題,在層出不窮的新的文學經驗面前面臨挑戰。作為應對,把新的文學經驗鑲嵌到特定的知識裝置中,用“知網體”進行統籌和歸納,這種批評方式固然重要,但它的問題也逐漸浮現。用既有的標準和框架去衡量文學新經驗,指出它們或符合或背離的特征,是否會強化已然物質化、制度化的文學認知?將新經驗壓縮在知識裝置中,成為一種能為學院認可的衍生性概念,是否會壓抑文學新經驗的“異質性?當被規訓的“經驗”與文學現場之間產生各說各話的“區隔”時,我們不禁要思考:文學新經驗能否成為破除既有知識裝置,指認既有文學標準邊界的新的開始?文學新經驗能否成為激發文學再出發活力的契機?
何平的《批評的返場》于2021年11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與其說這是一本“靜態的”文學批評論文集,不如說這是面向和應對新世紀以來文學新經驗的文學行動檔案。該書對新媒體文學、網絡文學、少數民族文學、代際文學等諸多文學新現象及時反應,對文學內部歷史與個體、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間、城市與地方、時代和代際等重要問題結合作家作品進行新的思考,對新世紀文學現場進行“文學策展”式的概覽。該書從體例上看可謂是新世紀文學面面觀,實際上,“重建文學和大文藝,重建文學和知識界,重建文學和整個廣闊的社會之間的關聯性”是全書的核心。一方面是各種張力化的表達:文學標準的嚴正性和新經驗的逃逸性,審美的穿透力和粗糲現象中所具有的創造性……另一方面是有效對話的建立:基于抵達文學現場的田野調查和“在現場”的實踐基礎,每一篇文章都在提出問題,并進行復調式的探討。如果把文學批評作為文學“之內”而不是“之外”的一部分,如果把批評家作為特定的“文學主體”,那么《批評的返場》就是重建文學性的“文學”本身。
對話:“同時代的批評家”與變動的文學場
在《批評的返場》中,何平認為“批評家,尤其是年輕的批評家們要有理想和勇氣成為那些寫作冒犯者審美的庇護人、發現者和聲援者,做寫作者同時代的批評家。”對于“同時代的批評家”的呼喚,是出于一種對當下共同體的關切。“同時代的批評家”不會將文學現象區隔于自我的感受之外,不會將作家作品當作審視和辨別的對象,借用阿甘本的話來說,“同時代”意味著共同蘸取著時代的幽暗來寫作。何平對話題、文學空間或作家群的關注表現出一種同時代的問題意識。《返場》重點評論的五位當代作家是因為這五位作家成名于1990年代,是寬泛意義上的“同時代作家”,且有一定的代表性。當談論文學與縣城時,他關注的是同時代作家中的張楚、阿乙、黃孝陽、陳再見等,同時,“縣城”在何平的視域中并不只是一個被文學敘事的“地方”,同樣是一個被忽略的、與整個中國的發展命運與共的特殊空間,通過觀察“同時代作家”的縣城敘事和當代文學中縣城被敘述的歷史,何平指出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聚焦的“城”與“鄉”這兩極之外,“可能還隱伏著第三種文學傳統譜系”。當論述地方性敘事時,他所思考的仍是共同生活的時代:“生活在全球化時代的新境遇里,地方日日新,我們的文學已然不是在福克納、馬爾克斯的時代敘述地方。當今時代文學如何敘述地方?”
針對批評家自覺參與文學現場能力退化的問題,何平提出“文學策展”的概念,策展人是聯絡者、促成者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斷的文學布道者,由是批評家才能發現中國當代文學新的生長點。從藝術展示與活動中獲得啟發的“文學策展”概念生動體現了批評家的能動性,批評家不再僅僅是對已經發表的文學作品被動做出評價和判斷,而是以“策展人”的身份介入文學生產過程,將自己的工作前移到編輯環節。在談到“花城關注”這一欄目對自身的意義時,何平指出“它的特殊意義在于:‘主持’即批評———通過主持表達對當下中國文學的臧否,也凸顯自己作為批評家的審美判斷和文學觀”。但是,何平同樣清醒地意識到這種“介入”的限度,意識到處于“策展”過程中的批評家需要“時刻保持警惕,避免將自己的觀感和見解施加到別人身上”,“策展人就是幫助公眾走近藝術,體驗藝術的樂趣”。正是在平等的視點下,何平指出新世紀媒體新變導致傳統文學媒體形成“泛文學”“亞文學”化的“文化媒體”特征,這充分激發了散文的探索性、生長性文類潛能……當他思考網絡文學,特別是資本化的網絡文學時,他看到“‘再造網絡文學’是從資本和讀者為王的時代進階到‘大神’為王的時代。‘大神’為王不只是經濟上的‘要價’,而是‘大神’對網絡文學存有文學公益心,在和讀者的交際中兌現網絡文學的文學理想,影響讀者,‘大神’可以成為某種文學風氣、風格和風骨的被效仿者,也可以為現代文學傳統提供新的可能性。”當談及青年寫作的問題時,何平不將之簡單歸結為一個文學問題,而將之視作更深層面的“青年問題”,因此,除了考察今天青年作家的寫作,何平更看重當下青年作家的“青年狀況”,由此反思在思想和行動層面,青年作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青年思想者與思想實踐者的前鋒和先聲的可能性。他說:“青年作家不要只止步‘文學’的起點,做一個技術熟練的文學手藝人,還要回到‘青年’的地點,再造真正‘青年性’的思想和行動能力,重建文學和時代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回顧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如何敘述地方時,何平嚴苛地指出“近三十年文學地方敘述被文化、政治、歷史劫持和征用的大勢”,這由此捆縛住了當代漢語文學的手腳,而這種地方敘述的局限也是整個中國文學的局限,因為這“暴露出中國文學迄今的非自足性和想象力匱乏癥”。當學界對可能策動的新“小說革命”心懷向往時,何平一方面對“再次革命”說保持認同與向往,另一方面又敏銳地指出,類似中國現代文學發生之初斷裂式的文學革命在當下不可能發生,“‘不革命’就是今天,甚至未來文學的常態”。他冷靜分析了思想解放與文化啟蒙的現狀、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等“革命”的基礎工作,認為當下的中國文壇缺乏完成新的文學革命的基礎條件,最終做出了在“文學不革命時代”寫作的論斷……
由此,面向變動的文學場,《返場》踐行“同時代的批評家”的理念,以“策展”的理念進行平等、復調式的“對話”,一方面以專業的眼光促成新現象、新經驗成為新的文學生長點,另一方面,在新現象和新經驗中重新檢視文學的內與外、歷史的常與變。何平在該書序言中指出當下裝飾性的文學交際、文學活動、文學會議等是“假裝的對話”,并推崇“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性”。迎合和指摘都不是真正的“對話”,無意義的描述或是生硬的概念化也不是“對話”的面膜,這種文學批評對話性的重建,在本質上是共同面對“同時代”整個社會公共性、民族審美的相關問題而共同成就的“對話”。
早在1985年這一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時刻,批評家吳亮就提出了“圈子批評家”的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用以批判封閉、自守乃至充滿利益交換的批評亂象,而是指陳這樣一種文學現實與文學期待:伴隨著當代小說的多向性發展,全知全能型的批評家已在事實上迅速瓦解,“事先準備好的理論匣子”已經無法再與當時當刻的文學現場相匹配,普泛的尺度開始失效。因此,對當代文學現場的感知與闡釋亟需“圈子批評家”的出現,其理想形態就是由幾個審美意向、興趣主張相近的小說家和批評家組成一個文學圈,“這個圈子有著自身的運轉機能和協調機能,以及對外說話的多種媒介工具”,“不止于被動地作闡釋和注解,他們還將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批評尺度與模式”,“圈子批評家是圈子小說的對外發言者,他們溝通圈子和圈子的聯系,協調著相互的關系和彼此的理解程度”。站在今天的文學現場回看吳亮的這一主張,其中當然包含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文學理想主義,但更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當代小說的多元化發展面向和文學批評的話語危機,以及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之間存在的巨大裂隙,并站在批評家的立場上對當代文學何以被言說表達了自己的隱憂。
今天,伴隨著更加多元的文化沖擊以及媒介革新、資本介入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文學沒有單獨的命運”愈發成為一種共識,面臨著遠比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新潮更為復雜的文學現場,吳亮所提出的那種“圈子批評家”的建立也愈顯艱難與奢侈,并且這一概念的內涵也越發收窄與貶義化———何平自己也提到“當下中國文學界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關系過于‘甜膩’”,作家對批評家的在乎有時更體現在他們“在選本、述史、評獎和排榜等方面的權力”。出于對重建一種富有張力的對話關系的渴望,何平的文學批評在今天的中國文壇就顯得尤為重要。《批評的返場》收錄了何平從2017年至2021年在《花城》主持的“花城關注”專欄內容,在“開欄的話”中,何平以《一個報信人,來自中國文學現場》作為標題,以文學“報信人”自居,深刻體現了批評家對文學現場的感知力與敏銳度,彰顯了引入“文學新風”的擔當與勇氣,而這種“報信”,不是簡單地為新的文學現象、文學新人搖旗吶喊,更不是運用學院派的“知網體”進行知識分析,而是深入文學的“田野”,用批評家的感知力和批判力深刻剖析某種文學現象的存在之由與變遷之故,不僅嘗試發現文學的“新血”,也憑借批評家的警覺發現其中的可疑之處,從而更好地認識當下文學的肌理,以一種時刻在場的狀態面對著變動不居的文學場。“中國文學現場”所昭示的“中國性”“文學性”與“現場感”也深刻表明了作為批評家的何平介入廣闊社會生活、促使文學有效參與公共生活、發微民族審美的努力。“身體力行的行動和實踐的文學批評,它和文學現場的關系不只是抵達文學現場,而是‘在文學現場’;或者說‘作為文學現場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們參與時代文學的生產,也生產著自己的批評家形象”。“花城關注”與何平的文學批評不是對當下文學新現象的“被動接招”,而是對文學新質的主動融入,以批評家的自覺建構起自己的批評尺度與話語體系,溝通著文學現場與文學研究的聯系,協調著文學新人與學院派研究者的彼此理解,構筑起文學的對話性。何平所強調和追求的做寫作者“同時代的批評家”,其深遠意義也正在于此,而從某種層面來說,也正是何平的這種自覺與敏銳,能夠確保他的文學批評始終具有在場性、對話性與敞開性。
在2010年,作為《南方文壇》的“今日批評家”欄目推出的最后一個“60后”批評家,何平就表達了對做批評語源意義上“能批評的人”的渴望,《批評的返場》正是這些年來何平理想追求的體現,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性,這既是對批評家的鍛造,也在重拾著批評話語的尊嚴。
行動:為“文學”賦予新義
當近些年諸多論述強調作為“動詞”的文學時,《批評的返場》以對文學現場變動充分的理解,跨界、跨圈的批評視野,反思“文學性”問題,與“同時代”文學經驗參與實踐性的“文學”,為“文學”賦予新義。
除了對新媒體文學、網絡文學反應迅速,何平對各種邊緣性的、異質性的文學都予以關注,對所謂“文學”邊界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2017年和《花城》雜志合作的“花城關注”,30期欄目包括30個專題。這些專題,與其說是對所關注作家的分類,不如說是何平為“文學”進行的邊界拓殖嘗試。“導演和小說的可能性”關注電影導演萬瑪才旦和唐棣的小說創作,其用意不是對“跨界作家/導演”身份的迎合式關注,而是“用小說的尺度來衡量他們的小說給當下的中國文學帶來了什么”;“搖滾與民謠”開篇指出“一部中國現代詩歌史,也是一部歌詞的失蹤史”,通過對舌頭樂隊、萬能青年旅店、木推瓜和五條人等樂隊的分析,確認了搖滾詩歌和民謠自身的文學性,并發掘出其精神立場的質樸和天真對于今天文學匱乏的補救作用;“散文的野外作業”提出寫作者首先要是一個行動者和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何平在指出當下文學越來越“宅”的現狀與困境后,提出散文需要野外“作業”,“希望以面向、走向、扎根于‘野’,來矯正糾偏”,勇敢地對越來越規訓和拘束的當代文學說“不”;“機器制造文學”專題的兩篇小說由人和機器共同完成,在大眾對AI技術的好奇與恐懼同步增長的同時,何平通過“文學策展”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當下機器寫作的大致邊界并做出自己的判斷,從某種層面來說,這個專題亦是對大眾的一次技術啟蒙;通過聚焦“文學向其它藝術門類的擴張”,何平提出“文學擴張主義”,關注文本的可再生性以及文學參與藝術實踐的行為。何平認為文學的擴張主義“啟蒙和啟動了青年對中國當代提問和發聲的問題意識和思想能力”,指出歧異情境中的寫作實踐與藝術行動是當下青年思想與寫作值得關注的動向,并對此所可能帶來的積極影響充滿期待……這些“文學”重新定義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并反向性地修改著文學理論。比如關于文學主體,何平指出“正是網絡空間助長了‘多主語的重疊’文學時代的來臨,并使之成為現實”;通過戲仿式的“制造‘85后’”,何平試圖重現不能被連續的文學史所容納的“一個個孤獨的文學島嶼”;通過恢復曲、歌與文學之間的關系,何平不僅是要接續歌詩傳統,而且指出“搖滾詩歌和民謠,也許是雜音,甚至是噪音,但它們的現實意義不只是自身文學性的再認和辨識,更重要的是其精神立場的質樸和天真可以救濟今天文學的匱乏”;通過觀察網絡文本從“線上”到“線下”的引流,何平富有警覺性地指出冒犯的網絡寫作空間正逐步退化成大型商業網文平臺夾擊下茍延殘喘的、“小而美”的網絡文學平臺,因此“我們以為是越境,其實可能只是一次轉場”,“在網絡寫作”難以改寫和拓展中國當代文學版圖、難以成為漢語文學革命的策源地。從重申多重文學主體,到指認文學的多元存在方式,從重新勾連文學與音樂、影視的關系到重構文學和城市、鄉村、田野等空間的關系,何平重建的“文學”不是僵化的概念,死板的律令,而是一個與時代的蕪雜和豐富共生的“未完成”———“一個時代的文學是由無數不同的主語共同書寫的,參差重疊或眾聲喧嘩”,文學主體如此,文學客體也應如此,要讓所有“幽微的存在”都被照亮……
圍繞此種文學觀,對于當代五位重要作家的評論隱約滲透著重述中國當代文學的努力。通過阿來,何平關注災難在整個國家和民族精神資源和心靈史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讓災難成為關涉國家、民族和國民心理建設與生命成長的精神性事件”;通過遲子建,何平指出“小說的目的最終是不是滿足建構一種和國家宏大歷史對應的‘復線的歷史’?不是這樣的,和歷史學、社會學相比,文學更應該在重建自為和潑辣的‘日常生活’上有所作為……”;通過李洱,何平在關注當下社會主義經驗、市場化經驗、全球化經驗等疊加的“混雜現代性問題”,并且是個體內部的現代性;通過艾偉,他在思考當代中國的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纏繞問題,呈現文學領域對公共時間和個人時間、中國故事和細民日常交疊于一起的表達;通過邱華棟,何平指出“新生代”的“代”就是90年代的時代城市敘事,是個體的青春記憶于城市現代性、同質化的世界和標簽化的背景地方性之間的張力和選擇……這幾位作家的寫作都并入了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的延長線,成為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而何平對他們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新世紀延長線上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敘事。何為當代?何為文學?從來都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需要“同時代”的作家和批評家共同創造。
命名:批評實踐與語體自覺
在《批評的返場》的序言和后記中,何平都表達了對當下文學批評特別是批評語體的關注。在何平那里,文學批評不僅是一個名詞和動詞,也同樣是一個形容詞和一種表征,它區別于學術制度規約下的“學術論文”,有著自己的文本格式和修辭語體,也有著思想、思維等精神層面的特征。“應該意識到現代文學批評和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內在關系。這種內在關系達成的文學批評,最基本的起點是審美批評,而從審美批評溢出的可以達至魯迅所說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而當下的文學批評早已從文學現場向學院轉場,自覺接受了學院知識生產的改造與塑形——用何平的話說,變得不再“文學批評”。作為何平近年來的文學評論集,《批評的返場》中有何平對大量文學現象的“命名”,這種命名溢出了既有的學院批評話語體系,體現著何平的才情、勇氣與見識,也體現出何平在批評實踐中的語體自覺及其重建文學批評“批評性”的努力。
除了他首倡的“文學策展”這一概念,不妨以《批評的返場》所收錄的“花城關注”中何平對當下文學現場的最新文學現象的命名為例:“文學的逃逸術”“制造‘85 后’”“‘奇點時代’前夜的科幻和文學”“散文的野外作業”“多主語的重疊”“文學西游”“文學擴張主義”“文學轉場和越境”……這些生動的命名是何平對當下文學現場新現象的捕捉,其中蘊含了他所認為的、新的文學可能性,這些略顯異質性的審美事實上填補了傳統文學譜系中的空白,也溢出了傳統學院批評關注對象的范疇。如何描述這些文學新現象?既有的學院批評話語體系能否實現對它們的精準闡釋?何平的命名行為既是“批評即判斷”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同樣是掙脫被“規訓”的學院批評話語、重建批評話語效力的努力,這體現了何平文學批評的語體自覺。當然,誠如何平所言,這“并不是退出學院,而是在實踐學院批評和文學現場對話的可能性”,多年的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使得何平能夠敏銳發現文學新的可能性,同時能夠將這些新現象置于文學史與整個漢語文學的譜系中進行學理的分析,因此,這類命名不是語言的“炫技”,而是扎根文學現場并將之接駁入學術研究的文學批評實踐。
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何平基于自己的判斷提出了“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這一命名方式,意在接續文學與時代共同建構的整體觀文學史傳統,并探索在“中國道路”的進程中,“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如何發展、延續和深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提出“散文的野外作業”以糾偏小氣、裝飾、自戀的散文文風,倡導當代散文向“野蠻”的轉向;提出“多主語的重疊”以摒棄文學的“鄙視鏈”,呼吁在網絡時代讓寫作者“自在地開口說話”,“讓所有的‘幽微的存在’被照亮”,由此燭照當代文學新的可能性……
“來吧,讓我們一起到世界去”,“讓我們一起下山吧”,《批評的返場》中這樣的語句表達著一次次的文學突圍、破界。《批評的返場》中的“文學”不再是自我凈化的過濾器,“文學批評”成為有思想有溫度的“參與”。何平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學之所以能夠不斷向前推進,正是有一批人不滿足于既有的文學慣例、挑戰并冒犯文學慣例,不斷把自己打開,使自己變得敏銳。而他的這本《批評的返場》也正是對這一精神的實踐,是中國當代文學再出發的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