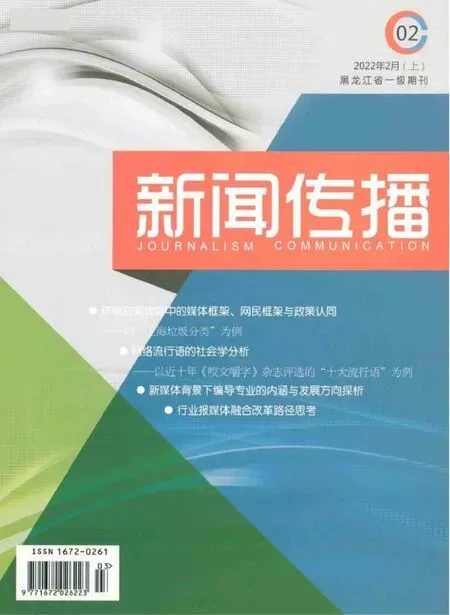淺談如何做好文化新聞
董云平
(黑龍江日報報業集團 哈爾濱 150010)
作為一名在文化戰線耕耘了十余載的新聞工作者,從最初的追求時效地程式化地采訪寫作,到如今能夠有“感”有“情”地以喜愛之情去采寫文化領域的新聞,感受很多,收獲很多。
在這里,淺談一下自己的體會和感受。對于自己比較滿意,讀者也比較認可的報道,我的體會是,能夠讓人樂意讀的作品都要有“情”有“愛”,還要好“看”。
那么如何能做到有“情”有“愛”,還要好“看”呢?
一、好的文化新聞必須有情感打底
毋庸置疑,好的作品都需要情感的注入,否則就沒有溫度,就不會打動人,更不會吸引人。
文化領域的新聞,在通常的新聞題材中,其實更有這方面先天的優勢。如果你喜歡這個領域,那么在認真的日積月累的學習中,你就會增長自己的文藝細胞,會更具文藝范兒。那種潛移默化地浸入,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偏得。但這個前提是,你喜歡它,否則就避免不了變成通稿記者,僅僅根據素材發表“相同”或“類似”的新聞。但如果你喜歡它,并每次都從中認真學習研究,你就會成長,就會發現不一樣的點,或者產生不一樣的感受,從而就會流淌出不一樣的文字。
也許是經歷了一定時間浸潤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開始對博物館里的文物,對美術館里的書畫,對音樂廳里的樂曲,對非遺技藝的傳承等等,開始產生了喜愛之情。
以往采訪,都是匆匆忙忙,如趕場一般。只要感覺新聞要素齊全,就立即離開,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件。
但是,突然有一天,感覺眼前的文物,不再是靜止的一件“古董”,而是在你眼前閃現著歷史的光芒;眼前的畫作,直擊心靈,讓你有所觸動;耳邊的樂曲,讓你不禁淚流滿面,你就會突然想用另一種筆觸去寫作。
比如說,我曾經去采訪一個名為“精神的光感——趙云龍水彩藝術展”。這個展覽規模不是很大,也沒有做很大的宣傳,但是當我走進展廳,聽著黑龍江省文聯副主席、省美協主席趙云龍的傾心講述,欣賞著一幅幅樸實而淡雅的畫作,心中就逐漸升騰起一種欣賞而喜愛的感覺。隨后,我又細細研讀了作者的作品集,深入探索研究這些作品打動人心之所在,寫出了《趙云龍:至樸至簡中書寫水彩之“靈韻”》這篇副刊作品,受到書畫界和許多讀者的好評。
我后來回憶并總結到,這篇作品之所以能夠打動人,特別受到業內人士的認可,首先是我對此傾注了自己的感情。自己對這些作品喜愛,才進一步去體會,去感受,去研究,去探索,然后在筆端自然流淌出一種最契合的表述形式,最自然的情感的表達。
再如,我曾經寫過一篇副刊作品《當新詩遇上版畫》。我以此為開篇——“一個天高云淡的秋日午后,收到剛剛獲得第28屆“金牛杯”優秀美術圖書金獎的《飛鴻踏雪——龍江新詩與版畫七十年巡禮》一書,灰色復古的封面,古版書般的線裝裝幀,似乎未做整齊切割的鋸齒書邊,一種厚重但潛藏著低調的奢華質感,讓人一時間竟舍不得打開它。”
這篇作品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和喜愛。最主要的原因,我想,也許有文筆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是自己對這本書發自內心的喜愛。無論是書的形式,還是里面的內容,都非常唯美,但又低調而不奢華。
正是因為喜愛,特別的喜愛,所以經歷了很長時間的摩挲,讀里面的詩歌,賞里面的版畫,遲遲不敢動筆,探索寫作它的方式。直到有一天,在黑龍江省博物館院里等候間,見到了一個那樣的場景,突然有了寫作的靈感和沖動。如是,我頭腦中躍出了這樣的文字:打個比方吧,讀這本書,就仿佛秋日在一個寂靜的庭院里,看秋風輕輕地掃拂著一株株黃綠相間的小樹,忽然間一只貓,跳躍而過,你的目光立時被它所吸引。也許它是一只黃白相間的小貓,與秋日下的黃綠相間的庭院相融相宜,形成一幅亦動亦靜的秋日風景圖;也許它是一只黑白相間的小貓,與眼前的風景,沒有任何的瓜葛,但是卻平添了一份靈動與突兀之美。
我想,這就是寫作中情感的力量,喜歡它,才有可能讓筆端有生機,有活力,有色彩,有溫度。
二、寫好文化新聞需要“在現場”,亦需多積累
和所有的新聞一樣,文化新聞也需要記者必須在現場。通過現場,獲得對寫作素材盡可能多的搜集,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獲得最真實的感受。雖說,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一個文化新聞來說,同樣的素材,每個人的感知是不一樣的。如果你有積累,那么你看到的就不僅僅是表象,寫出來的就不僅僅是通稿,或者是有些文采的通稿,而是活生生的或者是有味道的有新意的,或者是有深度的報道,會讓讀者享受到美,或者感悟到一定的深意。
比如說,采訪我省國家級非遺項目麥秸畫,這個題材此前已被大量采寫刊發。該從哪個角度切入?如何讓報道有新意,有可讀性?
我在采訪前做了充足的功課。但這個功課,我給自己訂下了“規則”,只對傳承人的情況、企業的情況、這個技藝的傳承過程進行了解,對以往報道的立意和主題完全摒除,不受其左右和影響。
帶著充足的準備,我走入了麥秸畫傳承基地。在現場,認真觀看傾聽傳承人的介紹,并根據所作的功課適時提出問題,在兩個多小時的采訪中,對這項技藝有了了解,并有了一定的感覺。然后又采訪了制作室,現場認真了解并感受了這項技藝的制作過程,增加了更深的認識。
采訪之后,我對此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并對這項技藝頗為驚嘆,情不自禁地產生了喜愛之情。這個時候,我大概就知道,這篇稿件基本可以動筆了,因為我找到了感覺。隨后,我又認真研讀有關麥秸畫的相關資料,進一步深化,找感覺,找角度。
最后,我沒有像以往寫非遺技藝的報道那樣,而是從《從田間廢棄物到國寶非遺且看“非遺”技藝如何點“草”成“金”?》這樣一個角度,寫了一篇有現場感又有深度的探究性報道,并配以麥秸畫代表性作品的圖片和視頻,及傳承人現場制作麥秸畫的視頻,圖文并茂,在黑龍江日報客戶端推出,收到好多好評。其中一位資深的非遺保護人士說道:“你的稿子有看頭,因為是用心做的”。話很樸實,但對我來說,是極大的鼓勵和認可。
我一直認為,現場加積累,加反復的研磨,是寫好報道的前提。這樣的稿子寫出來,會提升自己,也會讓自己感到愉快。
三、好的報道需要認真打磨,精心布局,文字上下功夫
好的作品要直擊心靈,要能產生共情。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作品不僅題材“出眾”,形式也要相得益彰。
如何做到相得益彰?每個人有自己的認識。
我認為,好的作品應當是真實的、樸實的,真誠的,在此基礎上做好謀篇布局,用好寫作技巧。
以往,我曾認為,文化報道應該文筆美。而這個文筆美,就應當用好鋪陳渲染。直到在日積月累的寫作中,特別是閱讀了大量中外優秀作家的作品及好的新聞作品后,我發現,優美的文章,令人心動的文章,經典流傳的文章,往往都沒有太多的渲染。在許多大家的作品中,就是最普通的話,最簡單的字眼,卻讓人感覺生動、準確、真實;沒有許多絢爛的形容詞,卻讓你深刻感受和領悟到了他要表達的情感。這是真正的寫作,也是最高級的文字。
所以,逐漸地,我也開始摒棄以往那些浮夸的寫作方式,不再過多使用形容詞,嘗試多用白描的寫法,盡量使用短句子,讓文章讀起來輕快,不費勁,而又力求有內容,吸引人,將自己要傳達要表述的思想融入其中。
比如,在寫《崔鐘雷:讓分級閱讀照亮孩子悅讀之旅》這篇報道時,開篇在描寫崔鐘雷這個人物時,我這樣寫道:“崔鐘雷,人如其名。說起話來,噼里啪啦蹦豆子一般;57歲,攀四層的辦公樓,小伙兒般輕盈迅捷。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急性的人,卻在過去的26年間,日復一日地如“小笨熊”般地做著一件事兒。一說起這件事兒,他就激情洋溢,成就感和自豪感也總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20多年,他專注于一件什么事兒呢?——為孩子們做圖書!從初期傾心于做原創圖書,到后來執著于做分級閱讀,20多年來,他主編出版的萬余種圖書,成為許多孩子人生中翻啟的第一本書,引領了無數孩子的“悅”讀之路。”
這樣的開篇,摒棄了對這個人物整體的外貌描寫,而是把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和要做的事兒形成了一個對比,短句子,簡潔明快;人物性格鮮明,有點小懸念,易吸引人讀下去。
再比如,在寫《李義泉:鋼筆畫中繪出別樣龍江風情》這篇稿件時,對一位執著鋼筆畫創作一生的老人,我經過認真對話交流,反復揣摩,找到了這樣一種精神的描寫:“和李義泉老人交談,很是舒暢。在他身上,仿若濾掉了世間的絢爛和喧雜,只留下如他鋼筆畫中的黑白灰三色調,簡單,干凈,淳樸。更給人以親切之感的是,他的嘴角總是漾著淡淡的笑,仿佛微風吹起的漣漪。也許是和喜歡運動有關,80歲的李義泉,神情舉止中,全然沒有一位耄耋老人的樣子。身材清瘦挺拔,動作迅捷,反應機敏,語速很快,回憶過往如在昨日。”
這樣的開篇,較為干凈利落,也符合人物性格和精神,為下文埋下了較好的伏筆。這樣的文風,也和鋼筆畫的風格極為相近,二者相得益彰。在副刊發表出來,配以鋼筆畫,使文章和畫作達到了很好地默契和呼應。
結語
文化新聞的報道,如果能夠深入其中,既有新聞記者踏實的采訪觀察,又有文化愛好者的喜愛加持,二者合力,就能讓文化新聞報道成為有著文藝味兒的、抑或有著自己品格的新聞,讓讀者喜讀,樂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