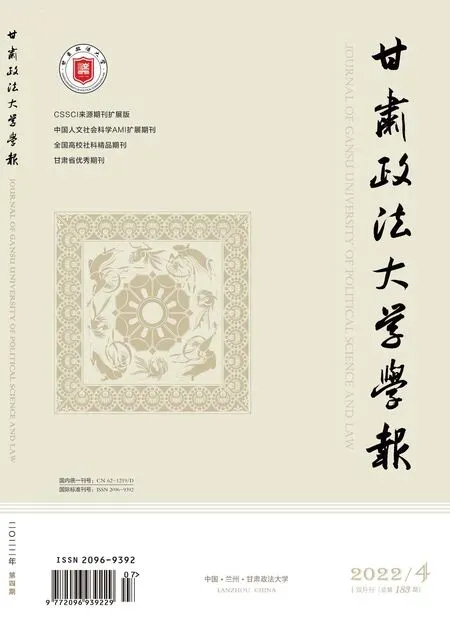醫師刑事責任的限縮:假定同意理論之提倡
徐 前
一、問題的提出
在現代醫患關系中,起源于自主決定權的知情同意原則備受重視,其核心在于確保患者獲得充分的醫療信息并理智地作出同意決定。(1)參見馬輝:《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權責任糾紛的鑒定問題研究——兼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中國衛生法制》2018年第4期。知情同意原則在醫事刑法領域的確立經歷了從“醫療父權”到“以患者為中心”的嬗變(2)即隨著作為傳統最高醫學倫理準則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確立的“一切托付于我”的醫療父權主義思想的瓦解,二戰后一系列的醫學倫理規則逐步確立了知情同意原則的思想:《紐倫堡倫理規范》(Nuremberg Code,1947)第一次在國際意義上提出了有關“知情同意”的問題;《日內瓦宣言:醫務人員誓詞》(Declaration of Geneva:A Physician’s Oath,1948)對紐倫堡審判中確立的醫學倫理進行了必要修改,但并沒有強調患者的自主決定權;《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1964)肯定了人體試驗領域關于受試者知情同意權的生成;但真正將患者自主決定權確立為最高醫學倫理準則的是《里斯本患者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Lisbon on the Rights of the Patient,1981),該宣言在患者自主決定權的基礎上引申出了知情同意權和醫師的釋明義務。由此,知情同意原則在醫學領域得以確立,并成為國際醫學倫理的最高準則。,隨著知情同意原則以及患者自主決定權的確立,患者的自我權利意識也逐漸覺醒。當醫師需要解釋說明的事項不斷泛化,以違背釋明義務為由施以醫師以罪責,極易導致刑事處罰范圍的擴張。如以下兩個案例:
案例一:“陳瑞雪訴武警醫院案”。患者陳瑞雪因左眼復發性結膜囊腫到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上海市總隊醫院(以下簡稱“武警醫院”)進行左眼脂肪瘤摘除手術。術后,陳瑞雪因感到左眼上瞼下垂再次去武警醫院就診,后實施了眼瞼下垂矯正手術。在患者去另一醫院復查時得知左眼上瞼下垂乃是脂肪瘤摘除手術時提上瞼肌損傷所致,遂以武警醫院未告知其手術風險且在手術中割斷其上瞼肌存在過錯為由提起訴訟。(3)參見胡永慶:《知情同意理論中醫生說明義務的構成》,載《法律科學》2005年第1期。陳瑞雪訴武警醫院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1)滬一中民終字第900號民事判決書。后終審法院認為,由于被告存在履行手術風險告知義務上的瑕疵,使得原告喪失了是否選擇手術的機會,由此造成的傷害后果應當由被告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事實上,這類案件若造成了嚴重后果就有了刑事歸責的可能性,在我國,之所以多以民事侵權處理,既考慮到尚未造成嚴重損害的現實情況,也是由于患者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程序獲得更多的物質賠償甚至精神損害賠償,而這些在刑事訴訟中幾乎是不可能的,況且醫方也希望可以通過賠償了事。
案例二:“子宮筋腫案”。被告醫師在對一名46歲的女性患者進行事前檢查時,發現患者子宮內有兩個拳頭大的筋腫,在獲得患者的同意后開始實施筋腫切除手術。但在手術過程中才意外發現,筋腫并非附著于子宮表面而是與子宮牢牢地長在一起,由于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切除筋腫,醫師在未取得患者同意的情況下切除了患者的子宮。(4)參見馮軍:《專斷性醫療行為的刑事處罰及其界限》,載劉明祥主編:《過失犯研究:以交通過失和醫療過失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73頁。法院認為,在是否可以為了健康而傷害身體完整性這一問題的判斷中,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患者本人的意愿。在本案中,醫師在未獲得患者有效同意的情況下實施的對患者身體造成嚴重影響的手術,即使存在醫學上的適應證,也是對患者自主決定權和身體完整性的侵害,故應當承擔身體傷害的刑事責任。
上述兩個案例都涉及刑法上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即在醫師未獲得患者的有效同意就實施手術進而導致糾紛時,如果醫師當時作了符合規定的確切說明,患者也會表示同意的情況下,醫師是否仍需要因實際上未取得患者的同意而承擔傷害罪的刑事責任?這就涉及醫師的釋明義務以及患者的假定同意問題。對于這類案件的處理,無論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務都缺乏統一的認定標準:有觀點認為該行為只是侵害了患者的自主決定權,與傷害行為無關,因而只具有民事不法,并不構成刑事犯罪;(5)參見劉明祥:《傷害罪若干問題比較研究》,載馮軍主編:《比較刑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頁。也有觀點認為,未獲得患者有效同意的醫療行為不僅具有民事違法性,也完全可能具有刑事違法性,且大多都應作為刑事案件處理;(6)參見粱根林:《醫療過失與專斷性醫療行為“斷想”》,載劉明祥主編:《過失犯研究:以交通過失和醫療過失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頁。還有學者認為,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完全可以運用推定同意理論予以解決,即通過推定患者存在同意從而排除醫師的刑事責任。但是,推定同意由于通常適用于緊急情況下無法獲得患者現實承諾的場合,因而缺乏適用推定同意處理案件的合理條件。因此,基于對上述問題的處理存在的各種爭議以及處理結論上的大相徑庭,筆者認為,根據國外刑法研究的新進展,新近出現的假定同意理論則為這一爭議問題可提供解決方案。
二、假定同意理論的興起
(一)釋明義務泛化下的醫師刑事責任擴張
在醫療實踐中,醫師對于手術風險應向患者就哪些事項作出說明,以及應當作出何種程度的說明,是醫患關系糾紛中決定醫師是否負有法律責任以及承擔何種法律責任的前提性要件。隨著醫療倫理準則由“父權主義”轉向“以患者為中心”,新的主流觀念認為,醫師的釋明義務是獲得患者有效同意的前提,不能因擔心全面履行告知義務可能影響患者治療,而將其作為豁免醫師違背釋明義務的理由。隨著對醫師釋明義務的全面肯定,醫師需要解釋說明的事項范圍不斷泛化。盡管通常將解釋說明的事項限制在“一般標準”范圍之內,即包括診斷結果、擬采取的治療措施及可能風險、結果、并發癥、副作用、替代措施、拒絕治療的后果以及治療費用等一般意義上需要解釋的事項(7)蔡桂生:《醫療過失犯罪中說明義務的性質和內容》,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8年第1期。,但具體司法實務中需要醫師解釋說明的事項遠多于此,并最終發展成一種“實質標準”——如何把握須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而定。然則這種實質標準會因患者自身變量的不穩定性以及治療過程的不確定性導致醫師釋明義務的范圍難以把握,從而使患者得以以“未充分告知”為由主張其同意無效。
在“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倫理準則下,醫師釋明義務的履行成為存在患者有效同意的前提,當未充分履行釋明義務或者存在履行缺陷時,就會導致患者同意的不存在或者同意因瑕疵而無效。在瑕疵同意的問題上,很長一段時間,傳統司法實務的立場都是即使事前取得了患者同意,但若醫師未充分履行釋明義務,患者的同意也歸于無效。詳言之,一方面,當醫師基于“善意”以其他信息欺騙患者或隱瞞了應當充分說明的事項,抑或是出于過失沒有告知足以影響患者決定的事項,若患者因此陷入錯誤認識,哪怕該錯誤僅僅是動機錯誤(8)所謂動機錯誤是指表意人在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時,錯誤地理解了對法律效果具有影響的事項的情形。如患者誤認為其截肢后仍可以安裝義肢生活而同意截肢,但其實際身體狀況卻不允許。參見徐久生、康子豪:《論被害人錯誤同意的效力——對民法中意思表示瑕疵效力之借鑒》,載《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患者的同意也歸于無效。另一方面,若患者基于自身原因而非他人失誤產生對事實情形的認識錯誤,導致其對現實和想象之間出現認識偏差,那么則應區分是醫師充分履行釋明義務之后患者仍存在認識錯誤,還是患者的認識錯誤在醫師釋明義務的范疇之外,而后再根據具體情況認定患者的同意是否有效。
可以看出,傳統司法實踐在認定醫師釋明義務的履行時通常采取一種整體考察方式,即只要存在未充分說明或部分未充分說明的情形,原則上都有可能導致在此基礎上獲得的患者同意無效,進而主張醫師承擔身體傷害罪的責任。換言之,在通常情況下,只有當醫師對治療過程及其可能出現的后果進行充分說明后才能獲得有效的患者同意。但是,隨著醫師釋明義務的不斷擴張,加之醫療活動常常伴隨著各種風險,如果要求醫師事先毫無遺漏地向患者作出說明,顯然是不可能的。當醫師無法充分履行釋明義務時,一律要求追究醫師身體傷害的責任,這無疑給醫師群體帶來很大的負擔,且極易造成刑事處罰范圍的擴張,這顯然是不利于醫師職業的發展和醫療技術的進步的。因此,如何緩解醫師的釋明負擔,限縮醫師的刑事責任,則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和研究。
(二)假定同意理論之刑法引入
隨著需要說明的事項逐漸泛化,醫師被課以沉重的釋明義務負擔,從而率先在司法實務中催生出用以限制患者追究醫師責任的假定同意理論。所謂假定同意(hypothetische Einwilligung),是指雖然醫師在實施治療行為之前沒有對手術的全部風險或應當解釋的事項向患者說明便取得了患者的同意進而實施了手術,但若患者事前知曉這些風險或其他事項,也會作出同意決定。(9)參見陳冉:《“假定同意”案件中醫療行為的正當化研究》,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可以說,這種假定同意是以當時未出現的“假設之情況”來替代“實際之進程”,以“假設之同意”來彌補現實同意之瑕疵。
假定同意理論最早起源于德國民事判例,特別適用于醫療侵權責任中,該理論旨在限縮醫師因對患者存在說明上的瑕疵而承擔過度的責任(10)參見周維明:《刑法中的假定同意之評析》,載《環球法律評論》2016年第2期。,因而被稱為一種“責任矯正”措施。其根據在于,在醫師錯過了說明時機的情況下,患者事后往往會濫用醫師未履行釋明義務這一事由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因此,為防范這種風險,當醫師未盡釋明義務時,患者應當合理證明若其事前獲得了全部的說明信息,就會作出同意治療之外的其他選擇(11)江溯:《醫師的說明義務與患者的假定同意》,載《北大法律評論》2015年第16卷·第1輯。,否則就應認定存在假定同意,排除醫師的侵權責任。
假定同意理論引入刑法并逐步成為刑法教義學上的一個新概念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20世紀90年代以前,假定同意理論在刑法領域中并未獲得認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也只是在一些判例中隱晦地提出了假定同意的思想,但醫師仍然必須對患者履行充分的說明義務,否則就以違背釋明義務為由追究醫師身體傷害的責任。這一時期,醫師說明義務的范圍仍然相當廣泛,假定同意理論也處于嚴格限制適用階段。(12)參見周維明、黃濤:《論假定同意理論在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中的發展》,載《法律適用》2018年第24期。隨后,“羅圈腿案”(13)基本案情:被告醫師在為患者實施手術治療羅圈腿前,并未對手術可能帶來的并發癥的風險向患者作特別說明,患者以為危險不大,便同意進行手術。手術后,患者右腿果然出現并發癥,便以過失傷害罪起訴。的判決標志著假定同意理論在刑事判例中獲得了初步肯定。該判決的意義在于,首先,它否認了以往司法實踐中一直堅持的若醫師未充分履行告知義務,即使醫療行為具有醫學上的正當性,也屬于侵犯患者人格尊嚴和自由的立場。其次,對于該類案件,法官在裁判時需要明確違反說明義務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這就表明,以往那種嚴苛的、不合理的釋明義務規則開始動搖,假定同意理論開始獲得認可。而假定同意這一術語及相關理論開始正式使用則要追溯到“外科手術人造骨案”(14)基本案情:被告醫師在為患者實施頸椎椎間盤切除手術時,并未使用從患者盆骨處切除一部分植入這一傳統方法,而是植入用牛骨制作的人造骨,這兩種方法各有優缺點。被告在植入人造骨前,為避免患者擔心,并未向患者說明采用該材料的優缺點以及并發癥,最后果然產生了并發癥。的判決。該判決指出,雖然缺乏患者的有效同意,但仍然存在著如果作了說明患者就會表示同意的情形,根據“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應當認為具有存在“假定同意”的可能性,因而被告不成立過失傷害罪。(15)參見周維明:《刑法中的假定同意之評析》,載《環球法律評論》2016年第2期。這一判決標志著假定同意理論的正式確立。最終將假定同意作為一項正式的法律制度確立下來的里程碑式的判例是2007年的“抽脂手術案”(16)基本案情:外科整形醫師在向患者實施抽脂手術時,事先向患者說明了全身麻醉可能帶來的風險并獲得了患者的同意,隨即在麻醉師與護士的協助下進行了手術。但在第二次手術時沒有再就全身麻醉的風險作出說明,且由于這次手術由一名沒有經驗的學生協助,導致麻醉劑過量,又因急救不得法導致患者死亡。。該判決指出,對第一次手術的全身麻醉表示同意,就表明存在對第二次手術的假定同意,因而可以將第二次手術正當化。但是,第二次手術的團隊組成與診療過程并不符合醫療標準,根據假定同意的判斷準則,無法認為存在患者的假定同意,因而應當追究醫師的責任。由于該判例首次使用了“正當化”這一術語,這表明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廢除了先前判例中所確立的假定同意具有使“違反說明義務與患者身體傷害之間缺乏因果關聯”的作用,而是將其作為排除行為違法性的正當化事由,因而具有突破性意義。至此,假定同意理論成為一種正式的教義學理論應用于醫事刑法領域。
三、假定同意理論限縮醫師刑事責任之證成
(一)對假定同意理論的批判及回應
1.假定同意不同于推定同意
在以往的學說討論中,論及較多的是現實同意和推定同意,故有觀點指出推定同意實際上包含了假定同意的含義,在已有推定同意的情況下是否有必要再行承認假定同意呢?(17)參見蔡桂生:《醫療刑法中假設的被害人承諾》,載《法律科學》2017年第4期。答案是肯定的。所謂推定同意,是指雖然行為時并不存在患者的有效同意,但可以認為若患者知曉情況當然會作出同意,從而推定其意思而實施行為。(18)參見車浩:《論推定的被害人同意》,載《法學評論》2010年第1期。推定同意僅僅適用于在緊急情況下,由于存在無法克服的障礙,事前無法獲得患者明確意思表示的場合;而在假定同意的場合,患者具有作出同意的條件和可能性,有辦法使患者在手術之前作出相應的意思表示。申言之,在推定同意的情況下,該情況具有醫療的緊急性和迫切性,若醫師不實施緊急醫療,患者可能面臨更大的危險與傷害;而在假定同意中并不存在醫療行為的緊迫性,也不存在無法獲得患者有效同意的困難與障礙。因此,在刑法上,盡管對二者的處理結果相同即都可以排除行為人的“不法”(19)林東茂:《醫療上病患同意或承諾的刑法問題》,載《中外法學》2008年第5期。,但適用情形完全不同,不能因為已有推定同意就認為沒有假定同意存在的必要。
另一方面,在推定同意的場合,其實是不存在患者同意的,或者說僅僅有一個虛擬的同意即“擬制意志”,但可以據此推定患者可能會作出同意。換言之,在推定同意中,同樣存在著假設患者會作出同意的這層含義,故推定同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假定同意,甚至超過假定同意。在推定同意的場合,患者根本無法使用其自主決定權,是根據平均理性的病人標準推導出來的同意意思,這體現出高度的父權主義和事實上無法取得患者同意時醫師的高度他決權。因此,與推定同意相比,假定同意并沒有弱化患者的自主決定權;就被害人同意理論所確立的對自主決定權加以考慮的幅度而言,假定同意也沒有超出這個幅度范圍。既如此,假定同意具有同樣合理存在的必要。
2.假定同意與自主決定權
假定同意理論在刑法領域中并沒有獲得一致性認可,反對性的觀點也有不少。其中一種批判的聲音認為,盡管假定同意以事后發生的事實主張患者本來會作出同意,但在假定同意的場合,事前沒有獲得患者的有效同意是不爭的事實,如果運用假定同意理論將這種有瑕疵的說明予以正當化,就構成了對患者自主決定權的侵害。(20)參見江溯:《醫師的說明義務與患者的假定同意》,載《北大法律評論》2015年第16卷·第1輯。
筆者認為,承認假定同意就意味著對自主決定權侵害的觀點是存在疑問的。首先,主流觀點通常將侵害身體的完整性作為身體傷害罪的保護法益,自主決定權是否是身體傷害罪獨立的保護法益尚有爭議。事實上,將他人對自己身體的傷害認為是自己是否同意他人侵害自己權利的觀點是令人費解的,在無法證立這一點時,就不能說假定同意侵害了患者的自主決定權。其次,退一步講,即使認為自主決定權是身體傷害罪獨立的保護法益,這種將假定同意視為對自主決定權侵害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自主決定權雖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自治,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個人可以毫無限制地任意決定。所謂自主決定的意思是基于一定客觀標準的主觀概念,它服從于社會一般人的共識性理解,是在恪守信賴原則的基礎上在一般人看來可以合理期待,并經過客觀判斷和準確理解后仍會同意的內容,即使在事后看來這種解釋與當時患者的內心真意相反。(21)參見[德]迪爾特·施瓦布:《民法導論》,鄭沖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頁。因此,從這一點來看,假定同意可以說是對自主決定權的一種合理限制,它要求個人行為和真實意思必須建立在社會共識性理解的基礎之上,因而無所謂侵害。
3.假定同意與事后追認
另一種對假定同意批判的觀點認為,所謂假定同意其實意味著對現實發生的結果做一種回溯性的事后考察,如果在行為時患者愿意接受這一結果就表明存在假定同意,反之,則否定假定同意的成立。因此,可以說假定同意實際上是對“患者如果知道現實結果是否還會作出同意”進行的一種事后判斷,其與事后追認并無區別,只要具有患者事后表示同意的意思即可,因而沒有必要使用假定同意的概念。
然而,假定同意所采取的事后判斷并不同于事后追認。在假定同意的場合,所要進行的是“在患者不知道現實結果的情況下,如果做了充分的說明是否會表示同意”這樣一種事后的蓋然性判斷,事后追認所要求的“現實的結果”僅僅是假定同意的一種標志而已,在行為時并不存在。而且,患者作為并不具備專業醫療知識的人,其對醫療行為正當性的判斷往往基于該行為能否治愈自己的疾病,如果將假定同意等同于事后追認,那么無論何種醫療行為,也無論其是否符合診療規范,只要從事后的結果考察治愈了患者的疾病就都能獲得患者的同意。而這與假定同意所蘊含的基本理念并不一致:在行為符合診療規范,具有醫學上的適應證,但并未充分履行告知義務的場合,即使發生的結果不符合患者的心理預期,也可能成立假定同意。但是,在醫療行為與造成的結果嚴重不符時,仍然可以否定假定同意的存在。總之,假定同意與事后追認在本質上并不相同,患者事后的意思是判斷是否存在假定同意的重要參考,事后的同意并不意味著存在假定同意,而事后的不同意也不意味著假定同意的不存在。
4.“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的適用問題
從前述判例中可以看出,在無法確定患者如果在行為前獲得了醫師的充分說明是否會作出同意之時,則根據“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開釋行為人,但這一做法遭到了許多學者的批判。如英格博格·普珀(Puppe)教授就指出,患者是否本來會作出同意這一問題本身就是無意義的。(22)參見蔡桂生:《醫療刑法中的假設被害人承諾》,載《法律科學》2017年第4期。假定同意作為一種事后的蓋然性判斷,行為時患者的自主意思是無法確定的,因為這種自主意思不受自然法則支配,是個人自治的體現。因此,無論患者作何決定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都令人懷疑且沒有意義。此外,如果將“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應用于假定同意,將無法證明患者本來不會作出同意的這一情況,從而造成對患者自主決定權的侵害。
然而,在筆者看來,上述批判可能過度夸大了“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的適用問題。在涉及假定同意的許多案件中,患者的意思表示都是可以明確且能夠得出合理結論的;判斷能否適用假定同意理論的事實情形和附隨狀況也都是可以清楚探明的。如前述“抽脂手術案”中,當醫療行為的手段和方式逾越了診療規范所規定的基本界限造成了對患者法益的侵害,患者毋庸置疑會否定假定同意的存在,“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也就沒有適用的余地。因此,事實上并不存在反對意見所說的“無法證明患者本來不會作出同意”的問題。同時,上述否認假定同意成立的判例也表明對可能存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則濫用的擔心也是多余的,這一原則在假定同意中的適用并不會導致案件結果朝著有利于醫師的方向發展,也不會造成對患者自身法益以及自主決定權的侵害。
(二)假定同意理論的法理依據
1.“軟法律父愛主義”的哲學基礎
父愛主義(Paternalism),其拉丁文詞源是pater,學界又將其譯為“家長主義”或“父權主義”,意思是“像父親那樣行為或對待他人像家長對待孩子一樣”。(23)孫笑俠、郭春鎮:《法律父愛主義在中國的適用》,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父愛主義原初僅適用于政治領域,直到18世紀才被引入法學領域,這一思想較早出現在約翰·密爾《論自由》一書中,是指為了兒童或精神錯亂者的利益,可以對其實施家長式干預。(24)參見車浩:《自我決定權與刑法家長主義》,載《中國法學》2012年第1期。后來哈特在否定 “法律道德主義”的基礎上對其展開論證,認為個人并不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從而將這一理論稱之為“法律父愛主義”。法律父愛主義旨在借助“家長往往會干涉子女的自我危害行為”這一現象來比喻國家、政府和法律在某些領域為了公民自身利益而不顧個人意志限制其自由和自治。申言之,法律父愛主義是建立在“個體有限理性”和“增進弱者利益”這兩個假設基礎之上的哲學理論,而假定同意理論的正當性之確立也同樣離不開這兩個基本假設。(25)參見姚萬勤:《法律父愛主義與專斷醫療行為的正當化》,載《比較法研究》2019年第3期。
首先,理性能力作為一種選擇自己行為的能力,個體一旦擁有便具有了自覺意識,并能夠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從而實現自治。(26)參見[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8頁。然而,社會分工的日益精細化使得各行各業都積淀了相當廣泛和深刻的專業知識,因社會個體自身能力有限性,社會個體對客觀世界認知不足,也不能全面充分掌握社會信息。當個體理性主義無法在醫療領域徹底凸顯時,社會個體面對醫學知識可能“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那些僅僅依靠日常生活經驗的普通患者就很難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醫學判斷。法律父愛主義憑借其優先認知,認為國家比社會個體在面臨抉擇時更加理性和明智,因而作出的決定也就更加符合社會和個體期待。
其次,絕對的理性主義必然走向絕對的形式主義,當社會平等意志發揮到極致勢必導致個體的有限理性與社會永恒價值的嚴重分離(27)參見[英]鮑曼:《個體化社會》,范祥濤譯,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5頁。,患者人權也就無法得到充分保障。就醫療行為而言,如果完全遵照患者的意愿行事,雖然可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患者的自主決定權,但是與醫學誕生之日起就秉持的“行善”這一基本原則的永恒價值相比,其合理性必然有所減弱。當患者的自主決定導致其自身利益的損害時,完全遵照患者的意愿行事就造成了對患者生存權這一基本人權的侵犯。因此,法律父愛主義要保護患者免于傷害,就要對可能給患者造成不良后果的自我選擇予以限制,以避免個體基于認知缺陷或信息獲取不足而作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斷。
最后,人性尊嚴作為衡量法律父愛主義的核心標準之一,在醫師的“強”與患者的“弱”這種強弱關系涇渭分明的二元模式下,對于弱勢的一方,法律發揮其慈愛般的父親形象,通過“損有余而利不足”“抑強扶弱”等這種對社會強制力量的干預進行再分配,來促進醫患關系的和諧,實現患者人性尊嚴,從而達到增進弱者利益的目的。(28)參見吳元元:《法律父愛主義與侵權法之失》,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法律父愛主義基于其強制程度的不同可以劃分為“軟法律父愛主義”和“硬法律父愛主義”。“軟法律父愛主義”所昭示的是國家并非對個體的任何待決事項都有干預權和決策權,當且僅當個體未能及時有效地作出同意時,國家立足于本人立場,從維護個體最佳利益出發作出的干預個體決策的行為,并且相信在障礙消除后個體也會認可這種干預。(29)David L.Shapiro, Court, Legislatures, and Paternalism, 74 Virginia Law Review 519,528(1988).“硬法律父愛主義”則不考慮個體是否對待決事項具有認識或同意,只要國家認為有必要保護個體利益,就可以直接作出限制個體行動的干預。(30)Anthony T. Kronman, Paternalism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 92 Yale Law Journal 763,763(1983).假定同意理論實際上可以說是這種“軟法律父愛主義”的體現。首先,在“軟法律父愛主義”看來,只有當患者的自我選擇面臨不真實或者存在障礙時,國家才可以介入和干預,這既相對尊重了患者的自主決定權,符合了當下“以患者為中心”的基本醫學理念,又在釋明義務不斷擴張導致醫師存在較高職業風險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醫師治療行為的正當性,限制了對醫師刑事責任的認定與追究。其次,假定同意理論所體現出來的這種“軟法律父愛主義”的家長式作風,即使對患者產生了不當干預,也只是一種損害較小的干預,并不會對患者造成嚴重損害,因此“即使是最狂熱的自由主義者也可以接受”(31)參見姚萬勤:《法律父愛主義與專斷醫療行為的正當化》,載《比較法研究》2019年第3期。。 最后,從醫療后果來看,在可能存在較大手術風險時,客觀上非專業的事后判斷對于事前行為的選擇并不具有指導意義(32)參見陳冉:《“假定同意”案件中醫療行為的正當化研究》,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若否定這種以“軟法律父愛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假定同意理論,強行將患者事后的自主意識凌駕于醫師的專業判斷之上,勢必迫使醫師采取更加保守的治療方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無疑會造成醫師與患者“雙輸”的局面。
2.“患者最佳利益”的考量
現代自由主義的興起引發了對法律父愛主義的批判,認為國家的干預導致了社會個體自治價值的喪失,在自主決定權與法律父愛主義的激烈沖突中,誰是患者最佳利益的維護者?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自主決定權從患者是自身疾病的感知主體以及對自身利益的維護出發,認為患者有能力作出與自身健康利益相匹配的最佳判斷,醫師則是患者決策的協助者,來促使患者最佳利益的實現。也正基于此,尊重患者自主決定權成為當代醫療領域的基本理念。而這一理念則源于密爾關于自由的論述,密爾嚴格區分了涉己和涉他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33)參見約翰·密爾:《論自由》,許寶骙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1頁。所謂涉他行為,只要存在對社會的危害性,國家就有權進行干涉和控制;而對于涉己行為,尤其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利益時,個人乃是自身利益的最高主權者,擁有絕對的自由。(34)參見劉月樹:《醫療中的善意強制及其可能——醫學父權主義的實踐合理性解析》,載《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5期。因此,個人自身的健康利益作為一種涉己行為,患者擁有普遍認可的自主醫療決定的權利,這不僅是患者個人自由的實現也符合其自身的最佳利益。
然而,尊重患者的自主決定權雖然符合當下“以患者為中心”的醫學倫理,但是在這種患者自主意識日益高漲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地強調患者的自主決定權而不加以理性限制,則百害而無一益。密爾所倡導的“涉己自由”是建立在以擁有絕對成熟理性的人對自身利益作出有利判斷為重要前提的基礎之上。而在醫療領域中,患者由于其醫學知識的匱乏、病痛的困擾、醫療費用的考量、身體素質的限制等常常處于理性不足或判斷失誤的境地,若把這種專業的判斷權全部賦予患者的話,雖然可以最大限度尊重患者的自我決定,但這種自我決定不一定是正確的、專業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醫師實施一定的干預來保證患者的利益。基于對患者最佳利益的考量,以“軟法律父愛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假定同意理論通過對患者自主決定權施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很好地填補了患者自主能力欠缺時遺留下來的主體空間,從而避免了患者的自我損害行為并提升了其健康利益。因此,即使在患者自主決定意識興盛的今天,對這一權利的主張也并不是越充分越好,如果無限放大患者的自主決定權,實際上也是對患者自身權利的一種侵害。當患者的自主決定權與法律父愛主義發生沖突時,立足于患者最佳利益的假定同意理論,將“行善”的天平向法律父愛主義一方傾斜以適度限縮患者的自主決定權而進行專業的判斷,這就極大地保證了患者最佳利益的實現。
(三)假定同意理論的判斷依據
1.假定同意理論的“折中說”
假定同意作為一種涉及行為人與被害人(醫師與患者)兩方面關系的理論,在司法實務中判斷是否存在假定同意時,為了防止判斷的恣意,則需要明確應以哪一方作為判斷標準。對此,在理論上存在著“被害人本人標準說”“理性的一般人標準說”以及“折中說”這三種觀點。
“被害人本人標準說”認為,在假定同意的場合,應當側重于被害人本人的價值觀,事后從被害人本人的立場出發來判斷行為時是否存在假定同意,至于判斷結果在一般人看來是否合理不影響假定同意的成立。“被害人本人標準說”強調重視患者本人的價值觀,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決定權,并在此基礎上判斷是否存在患者的假定同意,因此可以說是一種主觀現實的意思判斷。
“理性的一般人標準說”則側重于社會整體的價值觀,立足于社會一般人的立場強調對被害人客觀利益的保護,認為是否存在假定同意應以理性的一般人的價值觀為基準進行判斷,若處于被害人本人立場的理性的一般人在當時的場合也同樣會作出同意,那么則存在假定同意。“理性的一般人標準說”在判斷是否存在假定同意時,主張從保護患者客觀利益的角度出發站在一般人的立場上進行判斷,因而可以說是一種客觀整體的意思判斷。
無論是采取“被害人本人標準說”還是“理性的一般人標準說”都無法在具體案件中對是否存在假定同意的問題作出全面判斷,故將上述兩種視角的學說進行折中的理論就應運而生。“折中說”主張在判斷是否存在假定同意時,應同時考慮上述兩種標準,即在重視患者本人價值觀以及尊重其自主決定權的基礎上,還應當符合社會整體利益,以此作為假定同意理論的判斷標準。
本文主張“折中說”的觀點。假定同意理論適用場合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判斷主體并不是毫無獨立思想的抽象理性的“一般人”,而是具有自主判斷能力和決定權的獨立的個體。在判斷是否存在假定同意時,如果不考慮患者本人的特殊意愿,而是單純以客觀理性的一般人的價值觀為標準,這樣固然可以減輕司法機關的證明責任,但將與作為假定同意理論根基的尊重患者自主決定權以及維護患者最佳利益的理念相抵牾,同時也不利于個案正義的實現。相反,若僅立足于患者本人立場而不考慮社會整體價值觀,則極易導致判斷結果因造成對社會整體利益的損害而沒有存在的價值。因此,在具體判斷時,應以行為時患者本人的價值觀為判斷基礎,以裁判時已經查明的所有客觀事實為判斷依據,同時將社會整體利益納入考察范圍進行事后判斷,從而確定是否存在假定同意。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折中說”是對兩種不同立場和標準的學說進行綜合或折中,但通常所說的“折中說”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折中,除了少數真正能被調和的不同學說之外,大多數的“折中說”實質上都偏向于其中某一種立場,即以一種學說為主同時兼顧另一種學說的“折中”。因此,本文所主張的“折中說”是以“被害人本人標準說”為主、“理性的一般人標準說”為輔的“折中說”。
2.患者本人的價值觀與風險分配原則
以“軟法律父愛主義”為哲學基礎,同時保護患者最佳利益的假定同意理論決定了其必然充分重視患者的自主決定權以及患者本人的價值觀。因此,在某些特殊場合判斷是否存在假定同意時,必須考慮當時特定情況下患者本人的意愿。前述“被害人本人標準說”與“理性的一般人標準說”的理論分歧也正在于此:基于一般人的立場和價值觀會表示同意的場合,而被害人由于具有特殊的價值觀不會作出同意時,應當如何處理?以“病人基于宗教信仰拒絕接受輸血案”(案例三)為例,“耶和華的證人”信徒堅持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接受輸血。(35)參見夏蕓:《患者自己決定權與醫師裁量權的沖突——評“病人基于宗教信仰拒絕接受輸血案”》,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3年春季號。因此,當持有此種宗教信仰的患者由于原本會拒絕輸血,但醫師并不知曉這一情況而給患者輸血時,是否需要考慮患者個人的特殊信仰這一情況?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首先應當厘清“事前判斷”與“事后判斷”的適用場合,這也是假定同意與推定同意的區別所在。假定同意與事后判斷相對應,在假定同意的場合,行為人對于行為時所存在的各種事實情形是否全部知曉并不重要,而應以事后查明的所有事實作為判斷依據,但這些事后查明的事實也僅以行為時已經存在的情況為限。而對于事前判斷,則適用于推定同意的場合,即對于被害人所具有的但行為人在行為時并不知曉的特殊情況,不得將其作為判斷依據。就此而言,在前述患者因信仰某種宗教而拒絕接受輸血的場合,如果患者對宗教的信仰發生在手術結束之后,則這種情形不宜作為事實評判的依據。相反,若患者在手術前就已經信仰此種宗教而醫師并不知曉,在患者由于嚴重昏迷無法獲得其輸血同意的場合,則適用推定同意的法理,從行為時的客觀情況推測法益持有人的主觀意思,即不將患者的個人宗教信仰這一特殊情況作為醫師是否應當為其輸血的判斷依據,從而認定存在推定同意,阻卻醫師行為的違法性。而在患者意識清楚,醫師為挽救其生命欺騙患者或者不顧患者的反對意思堅持為其輸血的場合,患者個人宗教信仰這一特殊情況應當作為判斷依據,根據假定同意的成立條件,則應認為不存在假定同意,從而追究醫師身體傷害的責任。
從上述各種情形的分析以及相應的解決方案可以看出,處理同意錯誤的法理實際上所涉及的是風險分配的問題,即在屬于事前判斷的推定同意的場合,由于特殊狀態下無法取得患者的現實同意時,將身體傷害的風險分配給患者而不是醫師則是合理的。而在屬于事后判斷的假定同意的場合,由于本來能夠獲得患者的現實同意或不同意,但基于醫師自身的原因,(故意或過失)未充分履行告知義務從而未獲得患者同意的場合,將這種風險分配給醫師則是恰當的;但是,若醫師充分履行了告知義務,患者事前知曉了這些風險也會表示同意時,則患者的假定同意成立,醫師不承擔風險分配的責任。
四、假定同意理論的適用范圍
醫療目的的適正性、醫療行為符合診療規范以及患者的有效同意(36)參見[日]前田雅英:《刑法總論講義》(第6版),曾文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頁。,是醫療行為正當性的“三根支柱”。(37)參見邵睿:《專斷性醫療行為的刑罰界限》,載《江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缺乏患者有效同意的醫療行為通常被稱為“專斷性醫療行為”。一般意義上的專斷性醫療行為是在排除了強制醫療和緊急醫療情況之外的醫師應當且能夠獲得患者的有效同意卻不顧患者意思而擅自實施的醫療行為。(38)參見楊丹:《醫療刑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頁。關于專斷性醫療行為的正當性法理在刑法理論上存在著業務權說、目的正當說、行為正當說、緊急避險說、同意說、優越利益說以及社會相當性說等。但由于這些學說都存在著各自的刑法障礙,故不能合理地闡釋專斷性醫療行為。以“軟法律父愛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假定同意理論從維護患者最佳利益的立場出發,突破了同意表示的時間性限制,可以很好地證立專斷性醫療行為的正當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假定同意是在醫師釋明義務泛化下用以限縮對醫師刑事責任的認定與追究的理論,但并非任何缺乏患者有效同意的專斷性醫療行為的案件都可以適用假定同意作為醫師的“避風港”以規避刑事責任,這就必須明確假定同意理論的適用范圍和界限。
(一)違背患者意愿的拒不治療
所謂違背患者意愿的拒不治療,是指醫師拒不接診患者或者接診后拒不治療的行為。即在需要獲得患者同意的治療行為的場合,醫師對于患者所要求的某種治療拒不實施,不滿足患者所期待的治療意愿。該情形可以分為兩種情況:醫師未接收治療和已經接收治療。根據我國《執業醫師法》第22條第2款之規定:“醫師應當……樹立敬業精神,遵守職業道德,履行醫師職責,盡職盡責地為患者服務。”第24條規定:“……醫師應當采取救助措施進行診治,不得拒絕急救處置。”據此,無論出于何種原因不滿足患者意愿拒不接診患者或者接診后拒不治療的,都是未能履行醫師職責的失職行為。對于此種情形,由于不存在假定同意的適用余地,就其法律后果而言,應根據具體情況作不同處理:對于違背患者意愿的拒不治療的行為,若未造成嚴重后果,則應根據相關執業規定給予醫師行政處罰,而不涉及刑事責任問題;但若因此造成嚴重后果,如致使患者嚴重殘疾或死亡的,則應根據其主觀罪過,追究醫師醫療事故罪或遺棄罪等責任。
(二)超越患者同意范圍的治療行為
根據具體超越患者同意范圍的大小不同可以將其分為“未充分告知手術風險”和“擴大手術范圍未予告知”兩種情況。就前者而言,以臺灣地區曾發生的一起“處女膜撕裂傷案”(案例四)為例,一名未婚且無性經驗的女性在前往婦科處診療時,為進一步確定其病情,醫師對其進行了內診,但未向患者解釋內診實施方式和相應風險,導致其處女膜撕裂。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在醫師未告知患者內診時使用的器械存在傷及處女膜的風險時,患者同意醫師的內診行為是否有效?臺灣地區高等法院指出,醫師在進行內診時對其使用的器械以及方法不需要向患者進行詳細說明,相關風險衡量的高低,患者因此受到的傷害,醫師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39)參見王皇玉:《刑法上的生命,死亡與醫療》,臺北承法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56頁。可以看出,上述法院判決是基于“理性的一般人標準說”的觀點來說明醫師行為的正當性。而從“被害人本人標準說”的立場出發也同樣可以得出類似結論:即使在內診前醫師告知患者可能存在的風險和結果,出于內診檢查的必要,患者也會同意醫師的診療行為,因此,本案中存在患者的假定同意,故排除醫師的歸責。此外,本案的判決結果同時也暴露出具體醫療案件中“假定同意”理論適用的“細節”問題,即以司法判決的形式來限縮醫師釋明義務的范圍。類似的,前述案例一(“陳瑞雪訴武警醫院案”)也屬于此種類型,基于“折中說”的立場,在該案中,盡管手術造成了患者左眼上瞼下垂的損害,但整個治療過程符合診療規范,具有醫學上的適應證,即使醫院在手術前充分履行了告知義務,患者知曉了全部的手術結果和風險仍然會表示同意,因而存在患者的假定同意,故應排除對被告的刑事歸責,不宜追究醫院醫療事故的責任。
所謂“擴大手術范圍未予告知”,即患者對于手術本身而言是認可的,但在具體手術過程中醫師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對手術范圍進行了擴大,且并未對患者履行相應的告知義務。前述案例二即屬于此種情況。筆者認為,在該案中,基于患者最佳利益的考量,在生命權與身體完整性發生沖突時,醫師作出保全患者生命的決定并不缺乏正當性;盡管“子宮”對于每一位女性來說都具有特殊意義,但是作為一名46歲的患者,生命比子宮有更高的價值,因此,基于“折中說”的立場,應當認為即使醫師當時中止手術以尋求患者的意愿,患者也會作出同意,因而存在患者的假定同意,醫師不承擔風險分配的責任。此外,對于這種醫師在手術過程中發現的對患者身體健康造成威脅的情形,雖然可以中止手術以獲得患者的同意,但這種機械地征求患者意見、使患者再一次經受手術痛苦的做法不僅極不明智,而且也是對醫療資源的一種浪費。因此,當醫療行為符合診療規范、具有醫學上的適應證,基于手術結果,患者事后認為即使當時知曉手術的全部情況也會作出同意決定,則應當認為存在患者的假定同意,從而排除醫師的責任。
(三)因欺騙而同意的治療行為
案例五:“鉆尖案”。醫師在對患者進行接骨手術時,不慎將一個2厘米長的鉆尖留在了骨內,為了掩蓋這一失誤,醫師以出現了新癥狀為由告知患者需要進行再一次手術,在獲得患者的同意后醫師借此將鉆尖取出,后患者自第三人處得知此次手術存在失誤。(40)參見江溯:《醫師的說明義務與患者的假定同意》,載《北大法律評論》2015年第16卷·第1輯。
案例六:“腰椎間盤突出案”。一名患者被診斷患有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醫師在實施手術時誤將腰椎脊柱下節較為輕微的突出當作嚴重的那節突出切除了。在發現手術失誤后醫師向患者隱瞞了真實情況,謊稱上次手術不太成功需要再做一次手術,患者信以為真,遂同意進行再一次手術。(41)參見曹斐:《德國刑法中醫師釋明義務的歷史脈絡及新近發展》,載《北大法律評論》2016年第17卷·第1輯。
以上兩個案例均是醫師為掩蓋第一次手術的失誤而哄騙患者進行第二次手術,但醫師在進行第二次手術時,對其必要性的說明中均隱瞞了真實目的,因而屬于欺騙行為。盡管在這種情況下,患者都希望取出鉆尖或者切除嚴重的椎間盤突出,從而必然會同意醫師進行手術,但是否仍會同意由原來的醫師繼續手術是存在疑問的。且在患者受到欺騙的情況下,患者與醫師達成的手術協議實際上是不涉及取出鉆尖以及切除嚴重的椎間盤突出的,故患者對于第二次手術并不存在同意。退一步講,即使患者事前知曉了全部的情況仍然會作出同意決定,但對于手術的目的、內容以及由哪位醫師進行手術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因此,上述案件中,無論是基于患者最佳利益的考量還是“折中說”的立場,患者的同意均不滿足假定同意的成立條件,不存在假定同意的適用余地,由此造成的風險和后果也應當由醫師承擔,即醫師第一次手術的行為可能成立過失犯罪,第二次手術若造成嚴重后果則成立傷害類犯罪既遂,若并未造成嚴重后果,該行為也仍屬于傷害行為,成立傷害類犯罪未遂。
基于上述類型化的分析可知,在缺乏患者有效同意的各類專斷性醫療行為案件中,假定同意理論主要適用于超越患者同意范圍的治療行為即“未充分告知手術風險”和“擴大手術范圍未予告知”這兩種場合。從維護患者最佳利益的立場出發,以“軟法律父愛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假定同意理論很好地解決了釋明義務泛化下,醫師刑事責任的過度擴張問題,因而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需要強調的是,在判斷是否存在患者的假定同意時,必須考慮患者本人的價值觀,即患者的特殊信仰(案例三)以及于患者而言極具特殊意義的事項,如“畫家案”(42)如一位右手小臂患有骨髓癌的畫家,若不及時切除小臂,最多只有半年可活,畫家告訴醫生他需要用右手完成他一生中最值得完成的畫作,即使只能活半年也要畫完。最終醫師給他注射了一針麻醉劑,然后切除了其右手小臂。然而,盡管這位畫家又因此多活了二十多年,但痛不欲生,終日以淚洗面地注視著那幅未完成的畫作。。這兩例完全違背患者意愿的積極治療,雖然根據“理性的一般人標準說”考慮到了患者的最佳利益,但基于“被害人本人標準說”以及“折中說”的立場,這并不是患者本人所期望的,故當然不符合假定同意理論的適用條件。因此,在判斷是否成立假定同意時,必須將患者本人的價值觀納入考察范圍。
結 語
醫師的釋明義務和患者的假定同意理論實際上早已超出了純教義學的范疇,具有一定的刑事政策考量,對于促進醫患關系良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以假定同意理論來限縮醫師刑事責任的做法,既順應了現代醫療倫理所追求的尊重患者自主決定權和保障醫患之間關系平等的趨勢,又維護了傳統醫學倫理所崇尚的不傷害原則和行善原則,具有歷史與現實以及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意義。對假定同意理論的研究,實際上就是為了解決自主決定權與“法律父愛主義”發生沖突時,二者應當如何衡量的問題。假定同意理論基于其“法律父愛主義”的形象,從維護患者最佳利益的立場出發,在一定程度上限縮了醫師釋明義務擴張所帶來的醫師刑事責任擴大的問題,阻卻了不法和責任,從而較好地處理了部分專斷性醫療行為的案件,適度降低了醫師的職業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