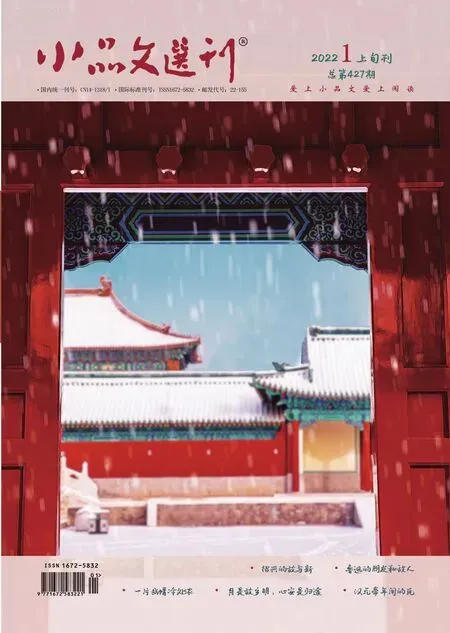紹興的故與新
李駿虎

十年頭尾兩次來到紹興,都是借魯迅先生的名義。十年前是來領取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這次是在先生誕辰140周年之際來參加紀念活動。
來紹興是要去蘭亭的,十年前也去了,不過那時只顧著玩,身著漢服附庸風雅,體驗曲水流觴的雅集與盛會。而今再來,已然“無我”,眼中所見,心里所想,都是對此地的過去與未來的遐思。蘭亭之外,紹興還有沈園;王羲之、陸游之外,紹興還有謝靈運、賀知章,更有王陽明。如今上虞白馬湖畔,留有夏丏尊先生任教春暉中學時的舊居平屋,豐子愷之小楊柳屋,朱自清亦曾客居任教于此。1928年,幾人并經亨頤、劉質平醵資在“春社”西側的半山坡為弘一法師建禪居晚晴山房,法師數次光降白馬湖小住,其風雅若此。紹興之所謂“文物之邦,魚米之鄉”,與“地上文物看山西”的“文物”不同,不指器物,而應指人物,蓋名士之鄉,風流無際。紹興的歷史人文也好,舊事物也罷,越劇、社戲、越王臺、烏篷船,一起構成傳統江南水鄉文化,幾成標本,又綿延流長。
而紹興又有魯迅。這次來紹興,終于有時間去訪百草園和三味書屋,一邊瞻仰拍照,一邊溫習先生的作品,尋找他筆下描述過的物事。“光滑的石井欄”還在,“碧綠的菜畦”里爬滿了南瓜的枝蔓,“短短的泥墻根”被各種茂密的野草覆蓋著——這個墻根對于一個頑童來說,的確有著“無限趣味”。三味書屋大概就是課文里描述過的那個樣子。這家“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在清末的紹興城內頗負盛名,匾額和抱對都是清末大書法家梁同書所題,雍容靈動而有風骨。“三味”的含義為:“讀經味如稻粱,讀史味如肴饌,讀諸子百家味如醯醢。”精神食糧的意思吧。陳列的物品中,除了魯迅在課桌上刻的那個“早”字的拓片,松鹿圖前的八仙桌上擺著當年私塾先生的相框,須發花白,面容清雋而高古,令人肅然起敬,看上去確如魯迅所描述的:“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這位先生是魯迅散文里藤野先生之外塑造的又一個知識分子形象,用的是小說手法,極為生動:“讀到這里,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著,向后拗過去,拗過去。”這是對舊文人漫畫式的批判嗎?我從前以為是。我不由得想起《故鄉》里的那幅圖畫:“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這是多么美好的畫面,描繪的是魯迅的少年朋友閏土兒時的樂園——恰如魯迅兒時的百草園。我突然醒悟,自己淺薄了,魯迅之所以為魯迅,無論他的“哀”與“怒”,都隱藏著可以稱為“愛”的濃厚的情感,他求新,而絕非完全地否定傳統,他是兼容而博大的,并且不會因為曾經的束縛、屈辱、壓抑、憤恨而變得刻薄和片面,于人于物莫不如此,所以他又是豐富而有趣的。
記起那年在浙江大學培訓,研究過馬一浮先生所作浙大校歌《大不自多》,有一句是“靡革匪因,靡故匪新”,意思是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斷革新,但革新也需要繼承傳統,因為舊事物往往蘊含著新意。魯迅先生無疑是革命的,但他絕不是簡單粗暴地割裂傳統,他推陳出新,新在精神,所以如今仍為新時代的年輕人所推崇。
不難發現,這座擁有2500年歷史的古城已經被魯迅文化所重塑。在這里,你可以找到《孔乙己》里的咸亨酒店,可以找到阿Q們戴的黑色氈帽,可以看到《故鄉》里的社戲和烏篷船,魯迅公園和魯迅故里更是游人的打卡地。紹興也是中國最具有江南水鄉特色的文化和生態旅游城市,是書法之鄉、名士之鄉、魚米之鄉。它們共同構成紹興的文化格局和精神氣象。
紹興有五百多萬常住人口,比很多省會城市規模還大,但穿行在紹興的大街小巷,還是會感覺她是一座小城,她天然地保留了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小城韻味,看到橋下的流水,無端地耳邊就會響起古琴的韻律。雖然高樓大廈林立,但是街角的小公園里、林蔭中的粉墻根、店招的字里行間都留存了濃郁的歷史文化,讓人感到無論陽光斑斕的晴天還是細雨淅瀝的雨天,這都是一座有文化的城。上虞區建設了一座瓷源小鎮,將古越窯遺址建設為文化公園,將歷代青瓷珍品陳列于越青瓷博物館。人們在遺址上、博物館中領略這項中華傳統工藝的魅力,那翠玉般溫潤的色澤、古樸而精巧的器形賞心悅目,不去旁邊的青瓷超市里帶走一套青瓷茶具,是不忍離開的——至少,要帶一個翠綠的茶杯回去,倒水喝的時候欣賞一番,也是一種享受,或者就放到博古架上。
溫故而知新,紹興的文化傳統和創新精神與魯迅先生一脈相承,更與新時代合韻合拍。
選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