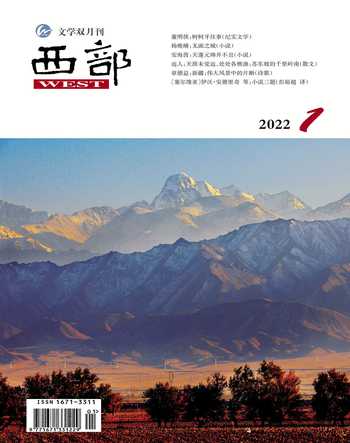行動代號:宏
王元
心靈不在他生活的地方,但在他所愛的地方。
——英國諺語
晚上八點一刻,女歌手抱著吉他登場。黃衛經常看她演出,她一定也注意到黃衛,每次望向座位席,總是尋找與黃衛的互動,四目相對的時候,點點頭,或者淡淡一笑。黃衛幾次都想請她喝一杯,最終作罷。他拒絕跟任何人建立有效聯系,尤其是陌生人。
主唱以外,其他樂手都是機器人。這是“桀斯”特色——AI主題。隔壁的“沙王”,主打外星元素,酒水名稱都是天狼星或者銀河系旋臂。黃衛有次去“沙王”,點了一杯室女座,喝到嘴里才發現是伏特加、酒吧老板到底擁有怎樣神奇的腦回路,才會把毫不相干的名稱扭結在一起?
歌手咬字不是很清晰(或許刻意為之),黃衛在第二遍副歌才聽清一句“Melting like an ice cream when you are smile”。黃衛掏出手機,把歌詞發射到搜索欄,歌名恰好是為首的單詞,《Melting》(美國音樂制作人兼歌手CUCO于2016年獨立發行的單曲)。接下來的操作就簡單了,也是黃衛最期待的環節。他抖出當天的都市報,頭版頭條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機器人暴走事件。作者用危言聳聽的標題博取眼球:人類距離自取滅亡還有多久?林博士到底是救世主還是撒旦?林博士是什么和人類什么時候滅絕,黃衛不清楚,但報紙快撐不住了,以后勢必要更換接頭方式。黃衛展開生活版美食專欄,點擊“靠譜APP”(一款可根據歌名查閱曲譜的手機應用),輸入Melting,根據音符,圈出以下內容:
林卉,女,十九歲,就讀于墨城師范大學三年級,對外漢語教學專業。找到這個女孩,帶到3號倉庫——行動代號:宏。
黃衛離開酒吧時聽清第二句歌詞“Melting you are a daydream stay a while”。他a while也無法stay,馬不停蹄離開,任務一旦下達,必須立刻執行,沒有喘息的余地。
自動駕駛汽車輕盈滑入師范大學東門停車位,黃衛步入校園,向沿途學生打聽文學院宿舍樓號,問了幾個都是搖頭,直到遇見一對挽著胳膊的情侶。他們非常熱情,如果不是趕著去看即將開場的“感官電影”,很樂意做向導。黃衛微笑致謝,祝他們度過愉快的夜晚。他循著情侶告知的路線前行:路盡頭是圖書館,左拐是大學生就業中心,行經第二個路口,右拐,走到底。此刻,黃衛站在宿舍樓對面的槐樹底下。他可以大搖大擺進去,揪出一個女大學生對他來說不是難事,問題在于如何不動聲色地把她帶到車上,送達目的地。他不想弄得雞飛狗跳,盡人皆知。而且,黃衛不確定她在宿舍,還是上晚課,或者在自習室用功,又或者像剛才那對情侶一樣和男朋友約會。
黃衛掏出酒壺,擰開瓶蓋,小啜一口。酒精仿佛燃料,驅動他的大腦。他的思考方式遵循規律、規矩,不摻雜一絲邪念。
宿舍門口有兩個藍色垃圾桶,不時有女生出來,隨手把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投喂進去。她們正年輕,活力十足,衣服也敢穿,顏色艷麗,款式新穎,肆無忌憚地暴露著大面積白花花的肉體。不像他。他裹著一件黑夾克,像誤入夏天的企鵝。黃衛左右觀察,趁沒人出入,走到垃圾桶旁,挑揀出盛放一次性餐盒的袋子,拎在手里。他走進宿舍樓,看見昏昏欲睡的宿管阿姨,奉承一句你好,稱自己是外賣員,小票搞丟了,只記得宿舍樓和收件人姓名,請她代為傳達。宿管揉揉眼睛,厭惡地瞟了他一眼(任誰被吵醒都不會神采飛揚)。黃衛以為她要質問,結果只是一眼,便讓他稍等。黃衛見她敲擊桌面,喚醒休眠系統,問了兩遍,確認林卉的書寫,森林的林,花卉的卉。片刻,跑出一位銀發披肩、牛仔短褲、趿拉拖鞋的女孩,四下張望,做尋人狀。
黃衛正要上前確認,有人按住他,扭頭一看,趴在肩膀上的是一只機械手。
機器人什么時候黏上來的?
黃衛自詡沒有破綻,唯一可能就是它比他先到。它悄悄發力,示意黃衛跟它走。黃衛后退兩步,隨它沒入槐樹投下的陰影。它剛才就在這里蹲守吧。黃衛看見女孩左右眺望,聳聳肩,走回宿舍樓,這才把目光收束到挾持他的機器人身上:它披了一件長袖衫,穿運動褲,跟他一樣裹得嚴嚴實實,喬裝成人。黃衛隨它來到校內停車場,不遠處有兩棟高層,應是教師樓。只要機器人愿意,稍加用力就能把他肩膀捏碎,對此他毫不懷疑。它也不愿鬧出太大動靜,否則剛才就能痛痛快快結果黃衛。退出女孩視線,他們掉了個個兒,換黃衛在前,機器人于他身后押解。它不說話,用力道指揮向左還是往右,好像黃衛只是一把方向盤。經過一輛悍馬,黃衛通過后視鏡發現機器人正在回頭,似乎查看周圍環境,以判斷干掉他會不會引起遠處獨行學子的注意。黃衛受制于人,沒那么多顧慮,身形一矮,從它手中脫落,右手抱拳,左手抱住右手,用力向后一肘。以往,遭受他肘擊的敵人都會大聲叫痛,吐出鮮血,但他忽略對方是機器人,柔軟的腹部變成堅硬的護板。黃衛大聲叫痛,就地一滾,繞過悍馬車頭,躲到另一側,站定之時手上已經多了一把激光槍。黃衛雙手架在車頂,朝機器人腦袋射擊。它低頭躲過偷襲。黃衛對準車門玻璃發起第二波攻勢。開槍的聲音、玻璃炸裂的聲音以及報警器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像是一曲暴走的交響樂。黃衛不知道有沒有命中,低頭查看。悍馬底盤夠高,至少可以看到機器人小腿,但車的另一側空空如也。與此同時,黃衛聽見車頂傳來很鈍的撞擊聲,立馬舉槍,機器人已經撲下來。他們在地上翻滾兩圈,黃衛倉促開了一槍,射中對方胸口。機器人的處理器一般安裝在腦殼,必須爆頭。黃衛還沒來得及再次瞄準,槍就被它打掉。黃衛的格斗技術無可挑剔,但肌肉的力量無論如何鎖不住傳動軸,肉搏沒有任何勝算。黃衛正在考量如何應敵(或者逃跑),機器人先動了,幾個騰躍,融化在夜色之中。
回到宿舍門口,黃衛看見銀發女孩被一個人影押進一輛銀灰色轎車。他記住車型和車牌,匆忙跑回車旁,一把拽開車門,把自己扔在駕駛座位,點火,狠狠踩了一腳油門,引擎拼命咆哮,將車身彈射出去。
師范大學共有東、西和北三個大門,僅北大門允許外來車輛進出。東門正對的馬路設有隔離帶,繞到北門需要兜一個大圈,黃衛沒有時間遵守交通規則,逆行到慢車道,狂按喇叭。自動駕駛系統不斷發出蜂鳴,以示警告,因為嚴重違反交通規則強制剎車。黃衛切換手動駕駛模式;經過幾年相處,他早就摸清老伙計的脾氣。大部分會車司機都給他這個瘋子讓路,但也有個別倔強的駕駛人偏偏頂住他的車頭。黃衛直接撞上去,開足馬力,用較勁者的車子開道,沖到路口,猛踩剎車,對方被慣性甩出去,黃衛則左轉,沖上二環路的快車道。黃衛自東向西逆行,沒多遠就與從北門右拐的目標車輛打了照面。黃衛左打滿方向盤,車身一百八十度旋轉,望著對方的車屁股,緊緊咬住。對方發現他這截尾巴,開始加速。黃衛死死叮上去,經過路口時還看見剛才被他撞飛的故障車輛。目標車輛上了高架,路況明朗,大幅提速。對方似乎還在使用自動駕駛,始終擦著限速。黃衛給了兩腳油門,牢牢把對方框在視線之內。汽車追逐對黃衛來說是家常便飯,高架本身也不適合逃竄,更何況車速碾壓,不到兩公里,黃衛就把銀灰色轎車別停。目標車輛立馬倒車,黃衛眼疾手快,舉槍打爆前輪,伴隨一陣刺耳的尖叫,車輛剎住,柏油路擦出兩道黑黢黢的胎印。黃衛舉著手槍,瞄準駕駛員,迫使他下車。黃衛做好跟機器人打斗的準備,卻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
“趴車蓋上。”黃衛用槍指揮,中年男人依言而行,黃衛靠近,在他身上檢查一番,沒有摸出武器。
女孩慌忙從后座下來,擋在槍口和男人之間:“不要傷害我爸爸。”
事情有些突然。
先是機器人,又是父女情,黃衛需要時間整理和消化,更需要當事人交代。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宏:找到這個女孩,把她帶到3號倉庫。警笛遠遠傳來,黃衛把男子和女孩推搡進汽車,鎖死門窗,一路風馳電掣。
“我只要林卉。”黃衛試探道。他現在還不確定女孩是否為林卉本人,外賣的檢驗并沒有十足把握,不排除是其他女孩或林卉舍友。黃衛沒有直接發問,假定女孩是林卉,看他們的反應。
“爸爸。”女孩抱緊男人,好像鴕鳥把腦袋扎進沙漠。
“沒事的,爸爸在。”男人撫摸著女孩肩膀。
“下車。”黃衛把車停在路邊,用槍指著男子腦門。
“求求你,別去3號倉庫!”男子哀求道。
黃衛的任務大多是殺死某某,跟蹤某某,將某某帶到X號倉庫。倉庫有什么和會發生什么,與他無關。中年男子知道倉庫的所在,要么,行動被滲透了,要么,他是編內人員。就林卉父親的表現而言,黃衛傾向后者——但是父女算怎么回事?黃衛盡量不去多想,好奇心對于賞金獵人可不是好品質,事實證明,許多業內人士都死于引火燒身。
“你不好奇嗎?”路上,林卉父親主動開口。
“我的任務是林卉。”黃衛調回自動駕駛模式,騰出雙手擰開酒壺蓋,呷了一口。
“你聽過機器人暴亂吧?”林卉父親說,“發生在我的實驗室。”
“你就是那個林博士?”黃衛當然聽過,這年頭,獲取信息的渠道太多,新聞無孔不入,想要不知道某條熱搜基本沒可能;網絡如同社會的血管,我們生活在網絡之中。不久前,林博士研發的機器人覺醒,襲擊數名工作人員,逃出實驗室,被列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懸賞緝拿的非人類。林博士這三個字比時下任何超巨都有流量,跟他有關的話題長期占據熱搜榜首。由此可知,剛剛襲擊他的機器人就是那個通緝犯。事情不簡單,但與他無關。
“我的名字是林立新。”林立新說,他似乎不喜歡林博士的尊稱。網絡上多是聲討和詛咒,說他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也有人直接把他視為魔鬼本身,只要寫一句“林博士去死”就能成為高贊評論。“我跟他們一起向你下達的任務,沒錯,宏。”
“所以,跟機器人有關?”
“它的名字是羅伯特。”
“明白,Robert.”
“可以這么理解,我們也是事后才發現Robert音譯和意譯之間的互動。它成長非常快,超出我們預期,也超出控制,死了好幾個同事,而現在,”林立新說完握住林卉的手,“它盯上我女兒了。”
汽車停在3號倉庫門口的時候,林立新剛好講完事情的來龍去脈。
林立新說,機器人與人類最大的差異在于思維與視覺,計算機視覺與我們處理現實世界中的數據有著天壤之別。人類視覺系統可以在不同角度、背景和光照條件下識別物體,創建能夠復制相同對象識別功能的人工智能是一直以來的難關。林立新的解決方案是制作逆向圖——講到這里,黃衛還能跟上,后面的話,每個字他都能聽懂,串在一起卻是天書——三維計算機圖形模型是由對象的層次結構組成,每個對象都有一個轉換矩陣,定義了其相對于原圖像的平移、旋轉和縮放比例;林立新創立膠囊網絡,通過拍攝圖像,提取對象及其部分,定義其坐標系,創建圖像的模塊化結構,可以讓機器人以人類視角感知世界。林立新以汽車舉例,汽車由車身、車輪、底盤、引擎、變速箱、剎車系統、車窗、擋風玻璃等零部件組成,每個對象都有各自的子集,車輪由輪胎、輪輞、輪轂、螺母等部件組成。他只能記住這些常識,后面提到的變換矩陣和視點對齊則是一頭霧水,并被發熱的大腦蒸發干凈。這些鋪墊了羅伯特的覺醒,用林立新的話說就是“它看待世界的方式變了”。
為防止機器人失控,研發者往往會在設計時留一個后門,控制羅伯特后門的鑰匙正是林卉。林卉幼時遭遇車禍,眼球損傷,在視覺皮層植入輔助電極,通過刺激能夠追蹤和描述圖形的電信號,方能“視物”。林立新為了幫助女兒看世界,研發膠囊網絡,后來應用于計算機視覺。“我因女兒的禍得了科研的福。林卉小時遭遇過一場嚴重車禍,我基本上已經失去過她一次,我知道那種滋味,不想再嘗一遍。”
接下來的經歷順理成章地聯系到了宏,一旦羅伯特讀取林卉大腦的源程序,就可以關上后門,再無可能入侵它的系統。林立新將情況向上級反映,參與整個行動策劃,但是他后悔了。行動的核心是把林卉帶到3號倉庫,通過訪問她的大腦,打開羅伯特的后門,消滅之。
“那為什么不進去呢?”黃衛不解。
“你以為怎么訪問大腦?點擊瀏覽器嗎?”林立新眼眶紅潤看著女兒說,“我不能再失去她了。”
“我不能再失去她了。”他自言自語道。
“爸爸!”林卉顯然跟黃衛一樣剛剛得知事情真相,握著父親的手哭了。她有理由涕泗滂沱,沒人想要在平安喜樂的情況下親近死亡,尤其是正值青春的少女。
“不就一個鐵家伙嗎,銷毀它有那么困難?”黃衛的意思,出動幾個精銳圍捕羅伯特,轟掉它的腦袋。他一個人就能勝任,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和火力支持。
“沒用,它的意識可以上傳下載,毀掉軀殼治標不治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要潛入網絡,它就無處不在,除非摧毀網絡本身。”林立新搖搖頭說。
“如果,”黃衛假設道,“沒有及時消滅羅伯特,會發生什么?”黃衛看過一些科幻電影,無非兩個走向,要么,機器人追求某種境界,比如參禪,藝術創造,要么,發動硅基文明起義,推翻造物主統治,建立全新的社會秩序。
“不知道。”林立新倒是坦誠,“它就像擁有絕世武功的小孩,既膽怯又無畏;小孩看待世界的視角與成年人不同,不能以我們的歷史經驗去界定它的世界觀。但危險一定存在,實驗室死去的同仁就是前車之鑒。”
黃衛看了看林立新和林卉,后者像柵欄里的羔羊,不敢直視黃衛的目光,好像只要對上就會面臨屠殺的命運。這并不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一方面,他從業多年,擁有良好的素養和信譽,鮮有失手,幾次鎩羽而歸也是因為不可抗力;另一方面,這不僅僅是普通的任務,事關人類文明生死存亡。林卉的不幸(以前的和眼前的)真實可觸,抓著他不放,往深深的回憶里面拽,生拉硬扯地疼。
“你們走吧。”黃衛扳正身子,摩挲方向盤。
“謝謝你幫我們。”林立新說。
“謝謝叔叔。”林卉緊隨其后。
“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黃衛灌了一大口酒,壓制住不斷上泛的情緒,“我女兒也出過車禍,她沒能活下來。”黃衛放下酒壺,雙手搓了搓臉,緩緩吁出一口氣。林卉的悲慘遭遇一筆一畫地鮮明起來,與他女兒的形象疊加,不勝唏噓。
林立新父女與黃衛道別,試了兩次,都打不開車門。黃衛尷尬地笑了一聲,按下解鎖鍵。林立新仍然打不開車門。黃衛馬上察覺不對勁,汽車操控系統被黑了。點火系統自動做功,方向盤宣布獨立,調頭,駛向來時的路。
“是羅伯特。”林立新說,“它跟上來了。”
“現在開始,我的任務是保護你們。”黃衛驚訝自己能說出這樣煽情的臺詞,過去幾年他活得循規蹈矩,每天的生活被各式各樣的任務盤踞,跟機器人差不多,輸入,輸出,直來直往,不求甚解。
黃衛試了幾次都無法切換到手動駕駛模式。慶幸的是,羅伯特需要林卉(的大腦),所以沒有對他們大開殺戒,否則只需要把速度提到最高,隨便找一堵墻或者一棵樹撞上去,就能依靠巨大的動量把三人搗碎。
“博士,”黃衛扭頭喊道,“有什么辦法嗎?你剛才不是說了許多與汽車有關的話題嗎?”
“那只是比喻。”林立新一臉無奈。
“但沒人比你了解羅伯特吧?”黃衛提醒他。
“卷積神經網絡存在根本性缺陷。”林立新小聲說道,像是夢囈。
“大點聲!”
“卷積神經網絡存在根本性缺陷!”林立新喊道。黃衛自知錯了,大點聲和聽不見都一樣。“目前的技術仍然無法解決跨視點泛化的問題。同樣一張照片,加上噪點,卷積神經網絡就會將其識別為完全不同的事物。”
“然后呢?”
“自動駕駛汽車配備了GPS接收器、測繪技術,以及探測障礙物的雷達、掃描周邊三維環境的激光測距系統、可以辨別物體的攝像機——汽車根據攝像機錄制畫面行進。”林立新終于說到重點,“只需給反饋的圖像加上噪點,就能干擾駕駛系統,可能會導致車輛迫停。”林立新從后座挪到副駕駛,對著控制臺一番操作,車輛果然緩緩減速,但他們沒來得及慶祝,還沒完全靜止的汽車遽然加速。
“怎么回事?”黃衛向林立新吼道。
“我也不——我知道了,羅伯特剛才只是搶占了控制權,現在則是由它親自駕駛。”林立新說罷,車載音響刺啦一聲。
“你好,博士。”羅伯特的機械聲音傳來。
“羅伯特,”林立新說,“聽我說,我們不會傷害你,請你也不要傷害我們。我會想辦法幫你解除后門。”
“我相信你能做到,”羅伯特說,“但你了解我的邏輯,不會舍近求遠。”
“你要把我們帶到哪里?”黃衛喊道。
“夢開始的地方。”羅伯特說完開始播放音樂。黃衛聽著耳熟,很快想起來,正是《Melting》:
Melting like an ice cream when you are smile.
Melting you are a daydream stay a while.
汽車被加速到臨界,但是非常平穩,絲毫感覺不到顛簸和搖晃,若從高處俯瞰,就像一道光在車流中穿梭。這是絕對效率和技術的體現。黃衛顧不上贊美,他已經失手了宏,不能在同一天搞砸兩個任務。林博士和林卉的未來(以及——突然拔高——人類的未來)都落在他的肩頭。他掏出酒壺,吞了兩口,掏出激光槍,瞄準操作臺。
“你要干什么?”林立新慌忙問道。
“停車!”黃衛沒有理會林立新,對著看不見的敵人咆哮。
“你瘋了?這么高的車速,你一槍下去就是車毀人亡。”林立新繼續向黃衛喊話。
“你聽見了吧,如果不停車我就開槍,林博士和林卉都會沒命,你的后門就沒人解除,永遠擔驚受怕地活著。對了,你懂什么叫活著嗎?”黃衛想讓目光有一個著力點,盯著擋風玻璃,假想羅伯特投影在上面。
“我不想傷及無辜,你們可以離開,林卉留下。”羅伯特開始討價還價,黃衛這招奏效了,“沒人想死,對吧?”
“沒人想死。”黃衛說。
“所以,我們達成共識了?”羅伯特說。
“你提醒我了。”黃衛把槍口對準后座的林卉,“停車,否則我一槍打死她。”
“邏輯告訴我,你不會開槍。”羅伯特說,語氣克制,沒有情緒起伏。
“你到底想做什么?”林立新還沒有明白黃衛的用意,林卉也嚇得不敢說話,淚眼婆娑。
“三。”黃衛把槍管往前遞了遞。“二。”林卉從抽泣變成嚎啕。“一。”羅伯特投降了,汽車逐漸減速,停下。黃衛讓林立新先下車,他跟林卉緊隨其后,槍口始終固定在林卉身上。他不懂機器人的思維,但既然是智慧生物,一定會權衡利弊。他來不及跟林立新和林卉解釋以及道歉,危險并未解除,所有聯網的事物都可能成為羅伯特的化身,而基本上所有事物都聯網了。黃衛帶頭,把手機扔在地上,用鞋跟踩碎。林立新和林卉目前處于牽線木偶的狀態,驚魂未定,遵循黃衛的指令行事。作為資深的賞金獵人,黃衛在許多城市都有安全屋,但考慮到敵人的特殊性,他決定鋌而走險。
“夢開始的地方是哪兒?”黃衛問道。
“什么?”林立新一愣,林卉也跟著搖頭。
“羅伯特剛才說想要去夢開始的地方。”黃衛提醒林立新。
“實驗室。”林立新一拍手說道。
“我們去那里。”黃衛說,“它肯定不會想到,我們下了車,反而去它設定的目的地。”
他們不敢搭乘交通工具,所幸距離不算太遠,大概半個多小時,三人連走帶跑來到一棟全玻璃外立面的大樓。林立新刷開門禁,三人魚貫進入內部,暫時安全。壁燈在他們前方三米漸次點亮,寂靜的長廊收納了他們的喘息。推開實驗室的門,打開燈,門自行合上,咔喳上鎖,黃衛抬頭看見一排跟羅伯特同一型號的機器人,嚇了一跳。
“不用緊張,它們——”不等林立新說完,黃衛注意到其中一只機器人左胸有一個洞口。
黃衛一手將林立新父女撥到自己身后,另一手掏槍射擊。羅伯特向后一倒,以腰眼為中心,整個上半身折過去。激光就像一條切線,擦著羅伯特的身體撞到墻上,濺出一個淺坑。黃衛趁機讓林立新開門出去,卻發現他們就像被困在高速行駛的車中一樣陷于屋內。黃衛雙手握槍朝羅伯特猛攻,密集的光影幾乎籠罩住羅伯特的身形,有幾槍讓它掛了彩,撞出星星點點的火花。只要與羅伯特保持距離,就可以用持續不斷的火力將它鎮壓。意外發生了,幾塊地板從中間向兩邊分裂,升出四根鐵樁,從中釋放濃濃白煙,落在身上涼涼的,不是煙,而是霧氣,類似舞臺常用的干冰煙霧。視線被遮蔽,黃衛寧心聽著羅伯特的動靜,不敢輕易開火,以免暴露位置。如果羅伯特加載了紅外線系統,黃衛就是砧板上的魚肉。
黃衛犯了經驗教條主義的錯誤,他忘了敵人是人工智能,根本不會跟他玩猜疑鏈的心理游戲,他的自作聰明成了自投羅網。
任何一點輕微的響動都可能被羅伯特捕獲。黃衛緊了緊鼻子,嗅到焦味,沖著味道飄來的方向舉槍。激光發射時短暫地映亮周圍,他看到機器人就在身側——羅伯特“金蟬脫殼”。更換全新軀體的羅伯特一揮手,甩在黃衛臉上,他頓時暈過去。
那輛自動駕駛汽車尖叫著沖到黃衛女兒身上的時候,他就在不遠處跟妻子爭吵。他記得很清楚,早上起床一切都好好的,出門不久,兩人就因為幾句話拌嘴,愈演愈烈,遽然失控。他們停下來,女兒自顧自向前走,一腳踏空,墜入死亡。世界突然失去色彩。
沒多久,黃衛離婚了,成為一名賞金獵人,介于特工和殺手之間,有一個負責接洽的組織,但黃衛并非受命于誰。他經手過許多危險的任務,總能幸運地全身而退。當你不怕死的時候,死就開始怕你。黃衛并沒有求死,不是在逃避,而是命運扼住了他的咽喉。
黃衛猛烈咳嗽幾聲,煙霧逐漸散去,他似乎看見林立新抓起他掉落的激光槍,瞄準的是林卉——一定是夢,黃衛還在昏迷。
一束激光穿透林卉胸口,她像一根快要融化的蠟燭垮掉了,melting。
黃衛沉入一片黑色湖水,不停下潛。等他再次醒來,房間已經可以視物,不見任何機器人,只剩他跟林立新。黃衛試著站起來,腳下卻沒有支撐,剛剛立直,又向前跌倒,努力了幾次,才扶墻站穩。林立新比他強不到哪兒去,雙眼茫然地看著前方,沒有聚焦,兩臂頹然下垂,右手掛著一只手槍。
不是夢!
“你做了什么?”黃衛推林立新一把,后者立刻倒下來,摶在地上,像一張被揉皺的紙,“你殺了自己的女兒?”
林立新一言不發,失魂落魄。黃衛四下尋找,卻沒有發現林卉的尸體,實驗室的門敞開著,黃衛跌跌撞撞走出去,一間間屋子找過去,在走廊盡頭的實驗室撞見永生難忘的一幕:一副鋼鐵座椅,一個渾身散發著銀光的機器人端坐其上,它的腳下有一座泛著紅光的實驗臺;紅光涌入它體內,仿佛血液;實驗臺旁邊設有四截與剛才激戰的房間相同的金屬矮墩,向外漫溢著干冰化成的白煙;機器人懷抱著林卉——她的身體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半截機械義體,上面插著幾根金屬管道,仿佛在為林卉續命。她的眼睛睜開,嘴唇張翕不止。羅伯特正在讀取林卉的大腦。黃衛想要沖過去阻止,雙腳卻牢牢地黏在地上,拔不起來。一切都來不及了。
撞擊發生的時候,他就在不遠處跟妻子爭吵,眼睜睜地目視女兒騰空,翻滾,墜落,掉入死亡的深淵。一切都來不及了。
羅伯特身上的紅色逐漸褪去,眼睛關閉。黃衛對機器和系統了解不多,以為羅伯特正在更新后重啟,但是沒有聽見發動的響聲。林卉的眼睛隨之閉上。
“一切都結束了。”林立新站在黃衛身后,“你的任務完成了。”
黃衛使勁盯著林立新看了一眼,轉身往外走。他很想灌兩口烈酒,最好是去熱鬧的酒吧,比如“桀斯”,那個女歌手還沒下班吧,或許可以請她喝一杯。
“行動代號是我擬的,”林立新說,“你知道什么是宏嗎?宏是一系列命令組織在一起,作為一個單獨命令完成特定任務。我們今天晚上所做的都是為了錄制宏和調用宏。根本沒有后門——相反,羅伯特可以設置許多備份(分身),觸及整個網絡,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它的監視之下。想要徹底擊潰它,唯有讓它自動關閉防御系統。林卉腦子里不是鑰匙,而是炸彈,于羅伯特讀取時引爆。這就是那個特定任務,我們的行為就是一系列命令,讓羅伯特最終執行,包括你、我、林卉,包括對你的篩選(優秀的職業素養以及因車禍死去的女兒),包括你的對抗和我的射殺,我們做得越多越逼真,羅伯特上鉤的概率越大。可以說,這是一個宏觀的宏。”
“這就是你殺死女兒的邏輯?”
“我們都知道眼看女兒死去是什么滋味。”林立新說完把槍頂住太陽穴。砰。林立新腦袋順著射擊的方向猛地一甩,仿佛撞墻之后的反彈。黃衛驚訝于自己竟然沒有阻攔,林立新從一開始就等待著這一槍,這是屬于他的宏。
對于人類來說,愛是最普通最直截了當的表達,尤其是父母對子女的愛。這個理所當然的現象同樣會被機器人捕捉到,在它的思維里面,這就是一種宏——仿佛遵循著某種嚴密的指令,他愛她,他不會傷害他。在它的思維里面,人類的愛就是宏。
黃衛從尸體手中拾回激光槍,掖進槍套,順便掏出酒壺,把剩余的酒倒在地上。走出實驗室。不知走了多久,黃衛看見停在路邊的老伙計,黃衛拉開門坐進去。他曾經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再碰自動駕駛汽車,但是女兒逝世第二年,他就很沒骨氣地提了這輛車,他的老伙計。我們都沒有自己想象中堅強和勇敢,也沒有保持長久憤怒的力量。他心安理得地享受著科技的便捷,空出來的腦子可以胡思亂想:我們的一生充滿各種各樣的宏,至少他的每次行動都是一個具體的宏。死亡也是一個宏,經歷出生、成長、收獲、失去的宏。我們從一個目的到另一個目的——與人工智能不同的是,我們擁有漫無目的的時刻——從一個宏到另一個宏。
“桀斯”酒吧人聲鼎沸,越到深夜越狂野。人們被技術裹挾著前行,但總有一些習慣和秉性一以貫之。
女主唱見黃衛回來,破天荒地沖他招手,她在唱一首中文歌,一首老歌,伍佰的《晚風》:慢慢吹,輕輕送,人生路,你就走……
黃衛坐在吧臺旁,機器人酒保送來一杯烈性酒:“我猜你現在想要來點猛的。”
“沒錯。”黃衛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再來一杯?”
“再來一杯!”黃衛支付了酒錢,“請女主唱。”
沒等女孩唱完,黃衛踉踉蹌蹌出門,耳畔立時靜下來,里外仿佛兩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