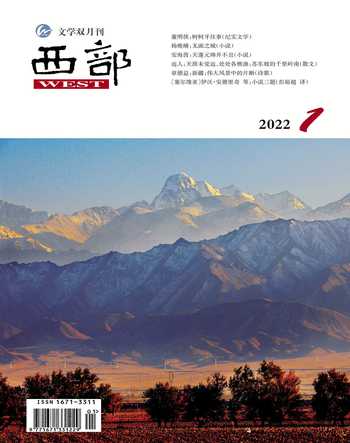雙腦筑城記
楊楓
在那場實驗開始前,老徐只是一名廢柴俱樂部的普通新會員。
眾所周知,任何優等大學都有所謂的“主旋律”:大一刷分,大二打比賽,大三混實驗室,大四實習……整條道路猶如走鋼絲,稍有不慎,便將墜入萬丈深淵,渾渾噩噩度過殘存的數年歲月,泯然眾人矣。廢柴俱樂部正是為此而生,以收容各路落難同胞,互幫互助為己任。
俱樂部的新人通常會再掙扎一陣子,但是人生啊,一旦跌倒,再爬起來可沒那么容易。大多數人最后都還是選擇與自己和解,躺平一陣,再去找別的出路。因此,當老徐在迎新會上大喊“我和你們這幫人不一樣”時,我們只當他是開玩笑,大家該吃吃,該玩玩,甚至還要他來試試《幻世-3》T大特供DLC,接進副腦,在虛擬世界當幾天學神,快樂快樂,氣得他跑到洗手間哭天抹淚,又引來一陣哄笑。
可是后來,老徐的成績竟然真的漲了。
這要多虧他在網絡中心工作的朋友老李。
彼時,拜新問世的副腦所賜,校園網的網速一直很爛。
副腦是裝在顱內的流體計算機,與大腦雙向連通,構成完備的腦機系統。用通俗但不準確的話講,就是我們可以用操作舊式電腦的方式來對大腦動手動腳了。
副腦上裝載了不少炫酷功能,從猝死預測機到數字貨幣投資專家,應有盡有。在大學里,使用頻率最高的當然是學習機制:想學什么,只要從云端下載資料到副腦,讓信息處理單元反復刺激大腦的記憶區,形成長期記憶即可。水平高的學生還會把經驗和靈感記錄成文檔,再次輸入副腦,從而形成更有效的自反饋回路。
大學生活因此天翻地覆。渴求知識的莘莘學子開始向數據中心發動一輪又一輪的DDoS攻擊,引得網管們叫苦不迭。老李那會兒剛剛加入網絡中心,急需做出業績,壓力自然更大。而在西西弗斯之路上一去不返的老徐也剛剛絕望地發現:他已經窮盡了所有手段,卻仍然無力回天。
一天,在夜宵食堂,二人歷史性地會面了。老李端著餐盤,一屁股坐到老徐面前。二人先照例就日常生活大吐苦水。等到氛圍恰到好處,老徐的怨念即將飛躍巔峰,老李便順勢問他,要不要來參加一個試驗。
“我打算搭一個小型分布式網絡。”他興沖沖地說,“我寫了一個模塊,能讓副腦開啟無線熱點。參加實驗的人互開WIFI,組成P2P網絡,把資料切塊,隨機存儲到彼此的副腦里。這樣一來,數據就分散到每個人身上了,讀寫都不用走主干網和數據中心,節省下來的帶寬就可以分配給其他服務,提升校園生活質量。”
老徐聽得一頭霧水,卻不愿在友人面前露怯。
“聽著不錯,可這跟我有啥關系?”他轉而拋出最關鍵的問題。
“噓——后面這事你可別外傳。我給你寫了個后門,能讀取加密數據塊,自動往記憶區寫。也就是說,不管你醒著睡著,只要有數據過你這兒,你都會一直在學習。這可能會讓你覺得累,但我保證,絕對不傷身體,而且大概率能迅速提升成績。”
聽到這里,老徐立刻精神了。走投無路的他幾乎立刻便接受了友人的邀請。后來的你問我答不過是走走形式。
“為什么找我?”
“隨機抽樣。”
“不可能,肯定有什么原因吧。”
“其實還有一個隱含的實驗,是我的私人課題。”
“什么實驗?”
“說細節你也不懂。我就是想看看在這樣的超載學習環境里,你這類學生能提升到什么境界。也不用你額外做什么,讓我觀察記錄你的成績和學習過程就好。”
“哼,瞧不起我是吧?等著瞧。”
“行,那你提交組網申請,回頭我給你單獨裝環境。”
事情就這樣成了。首批受試者來自各個學院,平均成績為中等偏上,湊齊了所有學科,但是后門程序唯老徐獨占。受試者組成的副腦集群采用RAID-486策略存儲數據切片,會保證所有的文件塊每周在老徐這里輪換一輪。
實驗啟動后,信息洪流日夜沖洗著老徐的大腦,把數倍于常態的資料注入海馬體。每天醒來,老徐都會去做老李準備的調查問卷。問卷上的問題五花八門,嚴重超綱,涵蓋從室女座星云到夸克世界的方方面面。可他卻漸漸喜歡起這些題目,因為每次做題,他都會發現自己學會了更多的東西,諸如一套數學理論,一組外科手術總結,或是一種新提出的計算機算法……穿插其間的優等生私藏札記則如同鋼筋梁架間的熔焊,融合知識和知識,構造出五花八門的精巧建筑。
此時我們還不知道老徐的秘密。當他在俱樂部的派對上表演手工求解高維旅行商問題,使出五花八門的奇技淫巧時,我們只是覺得不可思議。這家伙大概只是一時水土不服,才會淪落到此處,真正屬于他的,應該是特等獎學金聯盟吧。
不出所料,期末考試,老徐拿了大滿貫,順理成章地拿到了特學聯的入場券。接受校報采訪時,他再次引述了那句關于成功、天賦和汗水的破爛名言。他的黑眼圈則成了名言的確鑿證據,一層一層掛在眼袋周邊。
他感謝他的朋友老李(但巧妙回避了真相),表達了對尖子生的崇拜,卻唯獨沒有提到俱樂部。盡管當他家中遭遇飛來橫禍,經濟包袱死死咬住他時,是我們拿倒賣VR游戲外掛的錢幫他擺脫了困境。
那是他入學以來最大的危機:他家單親,農村戶口,入學第一年,母親出了車禍。拿到我們的援助款時,他沒有感謝我們,只是吞咽著眼淚,不停地說自己是個廢物。我們倒也沒什么怨言,反而特理解他。他討厭自己,迫切想要翻身。多積極啊。為了家人而力爭上游,俱樂部的成員們又何嘗不想如此呢?如果有可能,誰又會真的接受混吃等死的狀態呢?
大三開學,分布式網絡實驗宣告成功。系統正式上線,老李當選模范員工。擺脫了重壓的數據中心也終于能讓人舒心選課了。
選課結束后,老徐來辦退會。我們發現他的黑眼圈更重了,讓他注意身體。
“沒事,習慣了。”他擺擺手,辦好手續,搖搖晃晃地走了。
那時我們仍然對他的顱腔一無所知,遑論他所承擔的重負。在漫天飛舞的八卦中,我們只知道他要去綜合科學研究院的王牌教授手下實習。選實驗室那陣子,邀請雪片般飛進他的郵箱。而按照社員的說法……媽的,他挑選offer的樣子,活像翻閱情書的校花校草。
他如愿以償地進了最好的實驗室,開始做課題。
接著,他又挨罵了。
更好的環境自然要求更高。后門程序只給了他敲門磚,而且出于安全考慮,大幅限制了讀寫模組的吞吐量,還過濾掉了很多冗雜數據,從而限制了他的飛升高度。
他去找老李解除限制。老李打量著他的倦容,搖了搖頭,沒有同意,送了他兩張溫泉酒店的券,要他去放松放松,還跟他說,他已經今非昔比,不需要后門也能應付得來。實驗還是要慢慢來,急不得,急不得。
面對友人的關懷,老徐無言以對,但教授幾近人格否定的責備卻同樣刻骨銘心。于是,利用過去攢下的學識,他完成了以往做不到的事:他從機器碼層面破解了后門程序,重寫了一版,放開了諸多限制,還新增了完善的交互界面,以便微調。
深夜,他啟動新版后門,先沿用舊配置,然后慢慢提升強度。過了一會,后腦疼了起來,像是在被針扎。他這才緩慢降低洗腦規模,待刺痛鈍化,才去休息。他自知背叛了友人,但第二天,當他完美地回答了教授的問題,還拋出了全新的扎實假設,令教授刮目相看時,愧疚感便隨之煙消云散了。
他的第一篇論文發表在《Cell》,第二篇,NIPS,接著是《Science》《柳葉刀》。有社論宣稱百科全書學派即將迎來文藝復興,附錄是他和各界名流的合影、合作者的稱贊和報菜名般的學術成果,卻無一字提到他是如何忍耐頭痛,不斷接受日益升級的折磨的。
他們也沒提到當老李猜到了原委,去找他對峙時的場面。
“停手吧。不然我只能公開這一切了。”
“公開吧,但是要記住,是你把我卷進來的。而且不要忘了后來那些我幫你做,掛你的名,幫你刷獎學金的項目。”
“我是在關心你!”
“我知道。所以,就當無事發生,好嗎?”
老李張嘴,閉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他出局了。老徐接手了他拖拖拉拉的實驗,繼續挑戰自我,直到程序的資源消耗抵達硬件極限。
從此,二人的友誼便只剩下室友關系了。
有老徐這種超人在,校園學術圈的氛圍勢必會發生改變。
越來越多的人視他為領路人,嗷嗷待哺,靜候他輸出新的靈感,供他們延拓細枝末節,賺取履歷上的點數。
半年后,就連我也繞不開這座大山了。我那時正在帶領俱樂部給海洋塑料清污項目設計微機器人集群,其中,預測洋流運動的模型用到了老徐設計的算子。算子很難懂,我寫郵件問他,他沒回,我又換了幾種渠道,去信也都石沉大海。
后來有一天,凌晨兩點,我去社團活動室通宵,發現他獨自一人蜷在沙發上。我沒撤銷他的門禁,所以他能進來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會來。我裝作若無其事,坐到他對面,卻發現他雙目無神,正在哭泣。
“怎么了?”
“沒事。”
“你看著可不像沒事。”
我盯著他,遞過紙巾。他避過我的目光,兩眼血絲密布。
片刻寂靜,然后他問我怎么看現在的學術環境。
“為什么問這個?”
他伸出兩根手指,在看不見的系統設置面板上開啟了應用共享。一瞬間,璀璨的星群點燃了整個房間。他坐在星河中央,告訴我,每一顆星星代表一封求助郵件。
群星間還交織著猩紅色的河流,它們是向他的大腦發起的攻擊記錄。
“成天到晚應付這些東西,我快不行了。”
“不回不就好了?大不了弄幾個小號,或者寫一套代理人系統幫你處理唄。”
他搖搖頭,抽出吸管,攪動著手邊的星星,說這些就是經紀人系統的分析結果。它們雖然保護他,卻也剝奪了他的生活,甚至像家長一樣指揮著他的一舉一動。
“所以,現在你出名了,但你還是不開心。”
他沒說話。他沉默了很久。
“我覺得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過了一會,他又說。
“一開始家里窮,我以為是要回報父母,可是財富自由了,反倒沒感覺了。”
“你的量化投資模型賺了?”
“賺翻了,下個月要跟塞拉證券談收購合同。”他點點頭,“說回來,當初我還覺得追求的是成績、排名、點數,但這些……感覺就像毒品,越升越沒成就感,就要去挑戰更大的問題。”
“那就繼續做更大的問題,繼續深挖。做學術本來就要掀開世界的面紗,探索本質……”說到這,我反倒覺得我像個班門弄斧的小丑。我甚至意識到,在特學聯的迎新面試上,我也跟他說過類似的話。
“探索本質……也對吧,我也是這么想的。”
接著,他跟我說,他正在嘗試解決千禧年難題。
“那你之前的研究呢?”我提起要問他的算子。來之前我已經大致弄懂了,還找到了改進的空間。“我隱約覺得它能解決材料力學領域的幾個關鍵問題,還能開辟幾個新的研究方向。”
“送你了。”
我愣住了,過了一會,才反應過來。
“哦,所以你并不在乎探索與發現,你只是把科研當成打怪升級。”
“可能吧。”他垂下頭,避讓開我的叱問。
“我知道這可能是死胡同,也試過去改變生活,去旅行,去運動,去種些花花草草,擺弄些瓶瓶罐罐,認識一些人,出去喝酒唱歌看電影逛街,或者上云端干同樣的事情,甚至還申請過私人云空間,在里面創造世界。但你能想象那種沉悶嗎?太簡單了,做什么都太簡單了。人們也都頭腦簡單,說出來的話全是錯誤和偏見,煩。”
“所以,最后我發現,還是得回到這里。”他指了指半空中浮動的問題描述。
“那你哭什么?”
“因為我解了好久也解不出來,正好你來了,就跟你發發牢騷。”
“……祝你好運。”我想走了。簡直是自取其辱。我不知道老徐為什么要和我說這些。此時,有關水論文之風的批判尚未成為主潮,我依舊無從知曉它對老徐的智慧造成的巨大打擊,無從知曉他之所以難以破關,正是因為作為他靈感源泉的T大科研社群正在成群結隊地收受他的施舍,淪為他的附庸,而非他的助力。
也許他想坦白一切,卻舉棋不定?又或者他在轉彎抹角中完成了自我說服?無論如何,這些后知后覺的反省都已經于事無補。那時,我只是熄了火,疲憊地站起身,打消了通宵達旦的念頭。而他也只是抿著嘴唇,低下頭,展開一張張虛擬草紙,繼續他的闖關大業。
我走出俱樂部,群星謙遜地為我讓開道路。星光在虛構的氣流下翻滾,飛騰,繞著老徐旋轉,猶如籠罩周身的圣光。
可我只覺得他可悲。和那些黯然退場的俱樂部會員相比,他只不過走得更遠些罷了。
老徐的真正對手出現在2036年的首屆雙星交叉科學技術大會上。
收到邀請函時,他剛剛通關了PhD,正要從地火行星際飛船發動機的設計工作中脫身,留下海量的重要成果。同期,他還遺棄了很多項目,看得出來,他累了。
新生的盛會邀請他去當特邀嘉賓。這與其說是他的榮譽,倒不如說是組委會的。唯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開幕式上,還將有另一人與他一道登場。
一個此前名不見經傳的新手,有趣。
他漫不經心地翻閱會議議程,從開幕式往后順著看,第一眼就看到了新手的論文題目。
《黎曼猜想的兩種證明方法》
樸實無華,但擲地有聲。他頭皮發麻,眼淚一下就涌了出來。這不是他正在攻略的題目么?
身份反轉,新手驟變強敵。論文題目的后面跟著“已經同行評議確認”的粗體注記,次序緊跟在開幕式之后,顯然意在為大會造勢。他喚醒信息流模組。果然,關于此事的話題熱度正在飆升。而更令他感到眩暈的,是他的對手雖然執意要在開幕前保守秘密,卻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了一件事:他的研究受到了老徐的啟發,他為此感謝他。
收到致謝,老徐只感到頭皮發麻。有人在他撐起的科學天空上戳了個洞,飛出去了。為什么自己沒有想到解法呢?是什么啟發了面前這位比他還要年輕的新手?他一遍又一遍地掃描著自己的心智倉庫,變換著檢索算法,一直到視野中彈出顱溫警告,依然一無所獲。
他寫郵件給那位年輕學者,言辭盡可能禮貌。對方回復得很快,提到了一個簡單的定理,出自一篇早被他拋到腦后的論文的中間步驟。他得到了終點和一個起點,中間的路徑卻依然云霧繚繞。含糊其詞的回應令他勃然大怒,他開始盤算自己的未來,想要從計劃中擠壓出足以與對方抗衡的新發現、新創造。
他不斷逼問自己,逼問后門程序。空閑資源很快就不夠了。于是,他開始手動干預資源分配。
腦殼之下的數字生態系統中,供他娛樂的程序率先死去,接著是侍奉他日常起居的輔助組件,最后是用于人格修補(用來彌補洗腦造成的損害)的那些。他小心翼翼地拆解自己,將其獻祭給大腦深處的學術熔爐,煉不出寶藏,也要硬煉。帶寬不夠用了,就切斷所有無關鏈路,中斷與外界的聯系;存儲不夠用了,就刪除應用、音視頻和日常照片……可他仍然一無所獲——或者說,面對一道千禧年難題的解法,那些收獲全都一文不值。
大會正在按部就班向他走來。他先是詛咒自己,接著詛咒T大的無能,詛咒全校師生的笨拙和懶惰,最后詛咒后門程序,氣急敗壞地做了一個假設:在來自數據中心的知識之外,數十萬T大人一定在各自的私人空間中存放了更多的智慧,而這些要么是被他們偷偷藏起來了,要么就是被過濾器濾掉了。
對此,他做了兩手準備。他先帶頭發起了一場跨校運動,鼓勵大家共享知識片段,在開源協議的約束下互幫互助,以改良學術氛圍。可是這一活動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收獲什么啟示,反而讓他又倒貼了不少思想結晶。到了這時,時間也不夠了。于是,他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取消一切過濾條件,讓副腦徹底暴露在數據流中,全盤通吃。
限制解除的瞬間,他暈了過去。
數據塊在看不見的空間里飛來飛去,他將一切盡收腦中。這之中不僅包括他夢寐以求的知識大廈,還包括辦公材料和社會新聞,包括虛擬樹洞里寫給老師的問候,情人間的分手信和海誓山盟,甚至包括廢柴俱樂部采購游戲的賬單和收藏小電影的番號……
山呼海嘯的信息垃圾洶涌而來。他的大腦超載了,但程序卻沒有終止,仍在持續不斷地灌注資料。
瑣碎的信息構成了人們生活的點點滴滴,進而參與人格的塑造。在固化了太多碎片以后,老徐的大腦逐漸變成了人格的游樂場,你的人格,我的人格,他的人格,她的人格……T大全體師生的隱私數據匯成了人格的海洋,造成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精神分裂。老徐的意識被困在洶涌的波濤中,在外人看不見的汪洋里,發出A的聲音,揮舞著B的雙手,踢蹬著C的腿腳,水中倒映出D的臉龐,而這張臉,也是由成千上萬的大頭照拼成的。
一切都結束了。等到老李回寢室,發現老徐時,他正躺在地上抽搐,口吐白沫,說著十余種語言串聯而成的胡話。
老李慌忙給醫院打電話,接著眨眨眼睛,關閉了給自己用的后門程序副本。結束進程,打開控制面板,卸載程序,一氣呵成,毫不猶豫。
卸載完程序,他又去卸老徐的。可老徐卻漸漸安靜了下來,胡言亂語也慢慢變成了低沉的嘟囔。
老李湊近去聽,發現老徐說中文了。話語中,八卦似乎越來越少,科學規律則越來越多。
接著,老徐睜開眼睛,環顧四周,伸手擦凈嘴角的白沫,然后坐起身。
“副腦的容量不夠開新程序了,共享你的白板過來。”
老李照做了。二人的視野中隨之浮現出一張懸空畫布。
老徐的眼睛轉了轉,在虛擬畫布上寫下一個希臘字母。他開始移動頭部,一邊轉頭,眼珠一邊滾來滾去,寫下更多的公式,更多的證明。
“老徐,你沒事吧?”
“老徐,誰是老徐?”
他面無表情,繼續搖頭晃腦。畫布的左上角有一行小字:“關于P≠NP的證明”。
相關調查啟動后,俱樂部來了一位意料之外的客人,帶了一份意料之外的禮物。
“這個給你們。”活動室里,老李把一張存儲卡放在茶幾上,放在棋牌和骰子中間。我們遞給他一聽冰鎮可樂,他扯下拉環,喝了一口,看著易拉罐里的泡沫,若有所思。
他又猛灌了幾口,才開始講述真相,揭露老徐頭顱中的秘密。我們看完了老徐被送醫前提交的數學證明,又回顧了近日的報道。最后,老李告訴我們:老徐忘記了關于自己的一切。他的腦內似乎形成了一種自衛機制,清除了所有的冗余信息,只保留對他最重要的部分,讓他能夠繼續活著,繼續鉆研知識。
昔日的老徐,如今成了T大的化身。他得到了最好的磁盤清理程序。只不過,他自己的人格,也被劃進了垃圾堆里。
“人腦是最高明的騙子,你永遠想不到為了自保,它會做出什么事。”
最后,老李擦擦額頭上的汗,感慨道。
“說真的,雖然我知道他渴求知識,但一直理解不了為什么他要那么偏執。上大學之前他就這樣,最愛給人講題,給全班所有人講,還開直播。有人會了他不會的,他就氣得不行……可能是家教如此吧,獨生子,從小到大都被期待,就容易這樣。”說到這里,他嘆了口氣,“沒他,我上不了T大。找他測試,也是看他那樣,想反過來做點好事。沒想到弄成這樣。”
我們依然什么都沒說。
靠著后臺日志,老李得到了老徐的完整學習路徑,還過濾了其中的污染。把路徑圖譜導入副腦,按圖索驥,將知識輸入大腦,就可以迅速領悟人類知識的全景,而不必遭受信息過載之苦。
“這個應該對你們有用。”老李拾起芯片,示意我們誰試一試。
有些人看看我,我依然沒有表示,于是也沒人應他。他自己也覺得討了個沒趣,又閑聊了幾句,便告辭了。
事后,在法庭上,他想借芯片來爭取寬大處理,失敗了。芯片確實幫助到了一些會員,甚至還幫我重新規劃了俱樂部的培訓計劃。但一碼事歸一碼事。
老徐則全程沉默,直到法官宣讀審判結果。法警帶他離庭時,面對山呼海嘯的閃光燈和質問,他說:“歌德-巴赫猜想解決了。”
竊聽校園網的計劃解體了,吸食副腦集群的老大哥也消失了。
二人都離開了學校。老李坐了牢,老徐進了精神病院。沒過多久,一家赫赫有名的科研機構保釋、聘用了他們,在機構內組建起強化版的腦聯網,把后門程序寫進了所有科研人員的腦袋里。機構的學術影響力從此扶搖直上九萬里,四百余名研究員,個個堪比門薩俱樂部的秘密大師。
或許,對他們來說,只要能攀登科學高峰,其他怎么樣都無所謂吧。
老徐自己自然是無所謂的。只要應激性過濾機制不被打破,他便能一直鉆研學術,代價不過是人格缺失。這是他的追求,他成功了。
很難說他留下的足跡就是最好的——他后來獨立解出了那位新晉天才挑戰的問題,但手法笨拙乏味。而我也從圖譜中找到了很多迂回、冗余和重復。
但他至少守住了自己的陣地。
老李離開之后,我拿起卡片。
“主席?”
“你們誰想試試,就拿去吧。”我說,“東西挺貴重的。記得備份,別弄丟、弄壞了。”
“主席呢?”
我搖搖頭。當社長要保證成績在年級前10%,我也很享受親自探索未知的樂趣。像這樣坐享其成,我不甘心。
但我知道不該歧視知識。我知道有人需要它,還有很多人和老徐一樣。
而我不想他們變得和老徐一樣。
于是我拿起卡片,和幾位干事一起,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各自存了檔,最后交給剛剛問我主意的社員。
“拿去用吧。”
他點點頭,我也點點頭。
俱樂部又熱鬧起來。我繼續埋頭備課,同時盤算著論文怎么寫,晚飯吃什么,該把女朋友的名字賜給哪顆星星,作為她的生日禮物。房間里,全人類的智慧沉睡在十五克的芯片里,從一個人手中傳遞到另一個人手中,沾了些微汗水,在昏暗的燈光下閃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