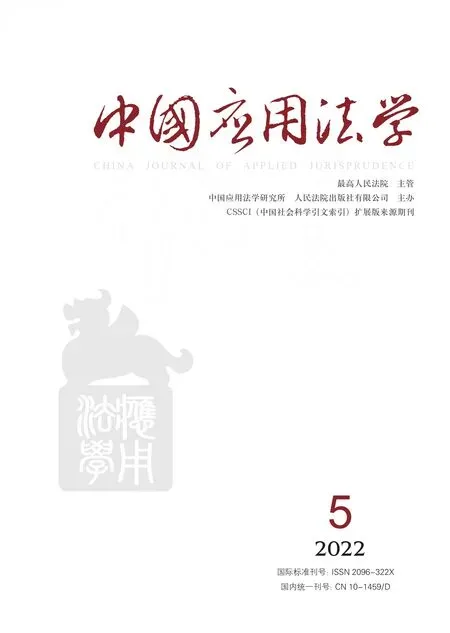保險合同中受益人雙重指定糾紛的解決
——姓名與身份關系之間的選擇
梁 鵬
一、受益人雙重指定引發的問題
本文所謂“受益人雙重指定”,乃指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中指定受益人時,既載明了受益人的真實姓名,又載明了自己與受益人之間身份關系的情形。通常,保險合同載明的受益人姓名與身份關系指向同一人,保險事故發生后,領取保險金之人為同一主體,故雙重指定并不會引發糾紛。不過,在偶然情況下,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姓名與載明的身份關系并非同一主體,可能出現兩個主體同時向保險公司索賠的情形,于是產生保險金給予何人的糾紛。下述案件正是實務中發生的真實案例。
2018年3月,李某與王某結婚后,在某人壽保險公司為自己投保了一份人壽保險,保險合同約定,在被保險人李某死亡時,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60萬元。在指定保單受益人時,李某在受益人一欄寫道:我的配偶:張某,同時注明了張某的身份證號碼。2020年12月,被保險人李某因車禍死亡,受益人張某持保險合同要求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60萬元。與此同時,李某的真實配偶王某也向保險公司提出給付保險金的請求,保險公司核賠查明:被保險人李某的真實配偶為王某,張某并非李某的真實配偶,但是,保險合同中李某寫明的受益人身份證號碼卻是張某的真實身份證號碼。保險金究竟應當賠付給被保險人李某的真實配偶王某,還是保險合同明確寫明姓名的張某,保險公司頗為為難。
在處理這一案件時,保險公司的法務部門對這一問題形成兩種意見:一種觀點認為,保險合同中載明了受益人的姓名和身份關系,但身份關系有誤,應當視為未指定受益人,保險金應當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處理,由被保險人的繼承人享有。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當尊重被保險人的真實意思,將保險金給付于保險合同明確寫明的受益人張某。兩種意見爭持不下。
此類受益人雙重指定之糾紛如何解決,還需仔細研究。本文首先對上述第一種觀點予以反駁,進而對第二種觀點區分評析,得出不同情形應以何者為受益人的結論,最后討論存在同居關系的特殊雙重指定的問題,希冀對此類糾紛的解決有所助益。
二、“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的懷疑
(一)“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之理由
第一種觀點認為,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其提出的理由有理論和立法兩個方面。
理論上,這一觀點認為,雙重指定導致受益人的指定不明確,不明確的受益人應當視為未指定。由于雙重指定導致保險合同中出現了兩個受益人,究竟以何者作為受益人并不明確。既然受益人不明確,便不應隨意以其中一種指定方式確定受益人身份,以免對另一種指定方式確定的受益人有所不公,同時,以其中一種指定方式確定受益人,也可能造成對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真意的不尊重。〔1〕杜萬華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理解適用與實務指導》,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262頁。有鑒于此,不如將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在此種情形下,保險金給予被保險人的繼承人,大致不會違背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本意。因為繼承人是被保險人的直系近親屬,被保險人通常并不反對將保險金給予自己的直系近親屬。〔2〕筆者就這一問題訪談了一些法官和律師,過半數的受訪人士認為,將保險金給予繼承人不會違背被保險人的本意。
在立法上,這一觀點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以下簡稱《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的有關規定可以適用于雙重指定的情形。《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2款第(三)項規定:“約定的受益人包括姓名和身份關系,保險事故發生時身份關系發生變化的,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這一規定調整的正是雙重指定的情形,可資適用于本案所述情形,其適用結果便是“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
(二)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理由之檢討
關于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理論上的理由,筆者認為,受益人指定的不明確,并非受益人不能確定,倘若能夠通過其他方法確定受益人,則不宜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第42條規定,在“受益人指定不明無法確定的”情況下,將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處理,亦即,此種情形應視為未指定受益人。值得注意的是,依照該條之規定,此處的“受益人指定不明”須在“無法確定”的情況下方可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這意味著,在受益人指定不明時,需要審查相關事實和材料,探求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真意,用以確定受益人。〔3〕樊啟榮:《保險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頁。如果受益人指定雖然不明確,但是能夠通過其他方法,如通過法律解釋的方法將受益人確定下來,便不宜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而正如下文所論,雙重指定的情形,通常可以通過解釋確定受益人,故不應將其直接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
此外,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極有可能違背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本意。由于被保險人是受益人指定的實質權利主體,〔4〕梁鵬:《論保險受益人指定權》,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受益人之指定真意便是確定受益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實務界有觀點認為,將雙重指定作為未指定受益人,保險金歸于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大致不會違背被保險人之本意。但是,通常來說,在雙重指定情形下,被保險人指定的受益人,要么是依照姓名確定的主體,要么是依照身份確定的主體,無論如何,不應將被保險人之繼承人作為受益人,倘若被保險人意欲將其繼承人作為受益人,毋寧依照慣例,在“受益人”一欄填寫“法定”,或者將此欄空白。被保險人填寫此欄之目的,恰恰在于不欲將其繼承人作為受益人。將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導致被保險人之繼承人成為受益人,可能正好違背了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本意。
關于雙重指定適用《保險法司法解釋三》規定之理由,我們認為,《保險法司法解釋三》之規范的適用范圍與本案所涉之雙重指定的情形并不相符。《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2款第(三)項規范的當然是雙重指定問題,但是,其規定的雙重指定附有條件,這個條件即該規定中寫明的“保險事故發生時身份關系發生變化的”,也就是說,與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之時相比,倘若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受益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身份關系有所變化,例如,于指定受益人之時,被保險人與受益人系夫妻關系,于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已經離婚,則身份關系出現變化,此時可以推定為未指定受益人。(關于此點,下文另有論述)在本案所涉雙重指定的情形下,身份關系為“配偶”,就保單中指定的張某而言,其與李某自始至終不是法律上的配偶關系,身份關系并未變更;就保單中“身份關系”指向真實“配偶”王某而言,直至保險事故發生之時,其與李某并未離婚,身份關系未變更。因此,保險合同涉及的可能受益人與被保險人之身份關系均未變更,不符合《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2款第(三)項規定之“身份關系發生變化”的條件,當然不能適用該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雙重指定并非絕對不能視為未指定受益人,在某些特殊情形下,窮盡解釋方法也可能無法確定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本意,〔5〕譬如下文所論,當保單上的輔助資料顯示應將身份關系作為受益人,但該身份關系在保險事故發生前已經變動,則可將此種情形視為未指定受益人。此時將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在保險法上具有充分的理由。當然,此種情形的出現并不多見。
綜上,“雙重指定視為未指定受益人”的觀點未能對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之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斷然將其視為未指定受益人,可能恰恰違背了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本意。該觀點將《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2款第(三)項作為立法上的依據,忽略了該項中設置的“保險事故發生時身份關系發生變化的”這一條件,導致其適用出現偏差。因此,這一觀點可能是錯誤的。
三、“以姓名確定受益人”觀點之區分
國內有學者認為,在身份與姓名雙重指定的情況下,應以姓名來確定受益人。〔6〕樊啟榮、張曉萌:《論保險受益人指定不明之解釋》,載《保險研究》2016年第6期。這種以“姓名確定受益人”的處理方法針對的是所有雙重指定的情形,未對雙重指定的情形作出區分,似可再予細化。
雙重指定可以分為指向同一主體的雙重指定和指向不同主體的雙重指定兩種情形。指向同一主體的雙重指定,是指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之時,姓名指向的主體與身份指向的主體乃是同一主體。指向不同主體的雙重指定,是指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之時,姓名指向的主體與身份關系指向的主體乃是兩個不同的主體。
對雙重指定的上述兩種情形,又可以根據指定之后身份關系是否變動各作兩種劃分。在雙重指定之后,受益人姓名通常不會發生變動,〔7〕除非被保險人主動變更受益人的姓名,否則受益人姓名不會發生變化。即便被保險人主動變更受益人姓名,變更后的糾紛亦適用下文所論規則。但身份關系卻可能發生變化,〔8〕從是否可能發生變動來看,身份關系可以分為可變動的身份關系和不可變動的身份關系。在民事法律上,身份關系通常可以分為:以血親為基礎的身份關系和以姻親關系為基礎的身份關系。其中,前者又可分為基于自然血親產生的身份關系和基于擬制血親產生的身份關系,譬如,親生父母子女關系,兄弟姐妹關系等屬于基于自然血親產生的身份關系,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系則屬于基于擬制血親而產生的身份關系。后者基于婚姻關系而產生,主要表現形式是夫妻關系。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身份關系又可以分為不能變動的身份關系和可以變動的身份關系。整體上來說,基于自然血親產生的身份關系不能變動,這種身份關系基于自然血緣產生,是一種不能變動的事實存在。基于擬制血親產生的身份關系卻可能發生變動,最典型的例子是,基于收養關系形成的父母子女關系可以通過合法辦理手續而解除。基于姻親產生的身份關系亦可變動,最典型的表現便是夫妻離婚。依身份關系是否發生變化為標準,雙重指定指向同一主體的情形可以劃分為:指定后身份關系未作變動的情形和指定后身份關系發生變動的情形;雙重指定指向不同主體亦可作同樣的劃分。
下文依上述兩種劃分方法,對雙重指定情形下,應當將何者作為真正受益人進行分析。
(一)指向同一主體的雙重指定
雙重指定指向同一主體,若身份關系未發生變化,通常不會發生糾紛,不須加以研究。此種情形,姓名與身份關系指向同一主體,且身份關系自始未變,可能提出保險金請求的只有一個人,故不會發生糾紛。
雙重指定指向同一主體,若身份關系發生變更,多數情形應當視為未指定受益人。與雙重指定相關的身份關系變動主要是,〔9〕另一種可能存在的變動是: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時,其與所指定的受益人并無保單中載明的身份關系,但嗣后身份關系發生變動,被保險人與所指定的受益人之間形成保單載明的身份關系。此種情形的雙重指定變動,因保單中的姓名與身份關系指向的對象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是同一個人,實務中不會產生糾紛,本文不予討論。在受益人指定之時,被保險人指定之姓名與其載明之身份關系為同一主體,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之后,由于時變境遷,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身份關系發生變更,多數情形下,這種變更表現為夫妻離婚。此時,受益人應視為未指定,這也是《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的觀點,其中原因,有論者解釋道:指定姓名附加身份的方式,應當理解為既有姓名又有身份關系的約定,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原合同約定姓名與身份所對應的人已非同一主體,此時被保險人又已身故,無論直接確定其中哪一個人為受益人都難以說是對被保險人真意的完全尊重。故司法解釋決定將此種情形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10〕杜萬華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頁。這一理由固然有其道理,但筆者以為,將此種情形視為未指定受益人,更深層的考慮乃在于對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真意的推定,即身份關系的變動,多因關系惡化所致,例如,因夫妻關系惡化而離婚,在關系惡化之前,被保險人將某種身份關系作為受益人尚可理解,在關系惡化之后,被保險人愿意將其作為受益人者少之又少,譬如夫妻離婚,雖有古之“孔雀東南飛”之特例,但多數情況已屬夫妻感情破裂,被保險人自然不愿將其保險金歸于原指定之受益人。由于此種情形下,姓名與身份關系所指向之對象在最初指定時為同一主體,被保險人不愿將保險金歸于身份關系指向之人,即不愿將保險金歸于其指定之姓名,從而可以推論,保單上載明之受益人,在身份關系發生變化之后,均非被保險人意欲賦予保險金之人。然則,此時被保險人意欲將保險金給付何人?立法者依一個理性之普通人的考慮進行推斷,認為被保險人愿將保險金給予其法定繼承人,此點當能為公眾所接受。而在目前法律規定之下,唯有將保單受益人視為未指定,才能將保險金歸于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故而,司法解釋將該種情形視為未指定受益人。〔11〕不過嚴格地說,此種情形應將法定繼承人視為保單受益人, 《保險法司法解釋三》作“未指定受益人”之規定,在目前法律體系下,雖可取得與“將法定繼承人視為受益人”同樣的結果,但與《保險法》之原理尚有出入。參見梁鵬:《受益人缺失與保險人賠付之處理——以〈保險法〉第42條第1款為中心》,載賈林青主編:《海商法保險法評論(第七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213頁。
當然,即使身份發生變更,但保單上指定之受益人能夠證明被保險人并無變更受益人之意向者,該受益人仍可領取保險金。如上所言,現實生活中存在夫妻雖在法律上離婚,但其離婚乃是出于某種特殊原因,例如為了能夠符合購買二套房的優惠政策,夫妻假意離婚,此種情形,雙方并無真實離婚意愿,被保險人亦無變更受益人之意圖,因此,只要原受益人愿意承擔舉證責任,能夠證明被保險人并無變更受益人之意向,即應認定原受益人之指定有效。〔12〕更有甚者,實務中出現了夫妻雙方為了符合購房政策,已經辦理離婚手續,但在其后購買保險時,一方仍將另外一方指定為受益人,這種指定符合被保險人的本意,雖然受益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與被保險人并非法律上的“配偶關系”,但是,本著尊重被保險人真意的原則,被保險人指定的受益人仍然有效。參見林剛:《對人身保險身故保險金受益人指定的思考——兼談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3款的法律適用》,載《上海保險》2018年第1期。從這個意義上說,《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2款第(三)項之規定仍有瑕疵,其未考慮到上述少數情形。筆者以為,該項應當增加但書規定:“但原受益人能夠證明被保險人并無變更受益人意向的除外。”
(二)指向不同主體的雙重指定
第一種情形是:雙重指定指向不同主體,而身份關系始終未發生變動。
此種情形,將何者確定為真正受益人,需對被保險人之指定真意進行解釋。此種解釋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其一:被保險人在指定受益人時僅寫明了姓名和身份關系,未記載其他確認事項。此時,將姓名作為受益人略占優勢,其理由是:
一方面,從姓名與身份關系的地位來看,姓名在指定受益人過程中應當居于主導地位,而身份關系處于輔助地位。自投保人指定受益人的行為觀之,絕大多數被保險人在指定受益人時均會記載受益人姓名,但記載身份關系并非常態。自保險公司的實踐觀之,“受益人姓名”一欄為所有人身保險合同的必設欄目,但是,并非所有人身保險合同均設有“與被保險人關系”欄目,即便保險合同設有該欄,實務中,保險公司亦不強調該欄的填寫,其強調的是姓名和身份證號的填寫。自理論研究觀之,已有學者提出:被保險人既將受益人之姓名明確記載于保險合同中,縱使又載明身份關系,但這一身份關系并非強制填寫事項,是否填寫身份關系往往取決于保單欄目的設計,此種指定方式所注重的,乃是姓名,而非身份關系。〔13〕林群弼:《“保險法”論》,我國臺灣地區三民書局2006年版,第578頁。更有論者明示:雙重記載應采受益人姓名欄為主,與被保險人關系欄為輔的記載方法,而記載身份關系僅在于加強說明。〔14〕陳猷龍:《“保險法”論》,我國臺灣地區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81頁。由此可見,姓名在受益人指定的實踐中處于主導地位,身份關系處于輔助地位。〔15〕前引〔6〕,樊啟榮、張曉萌文。
另一方面,從法律規定來看,各國保險法強調對受益人姓名的記載,但對身份關系的記載并不重視。我國《保險法》第18條規定,保險合同應當記載“受益人的姓名或者名稱、住所”,《韓國商法》第729條規定,人身保險單需要確定保險受益人的,應當記載其“住所、姓名及出生日期”。盡管這些規定并非強制性規定,但從中可以看出立法在受益人指定上的態度,即更加強調受益人姓名的記載,而不是身份關系的記載。《日本保險法》第40條規定,生命保險應當記載“保險金受領人的姓名或名稱以及其他用以確定保險金受領人的必要事項”,對該規定進行文義解釋可得,姓名處于必填事項地位,確定受益人的其他內容,包括身份關系、身份證號碼等,均屬于“其他用以確定保險金受領人”的輔助地位。
上述解釋著眼于被保險人、保險公司的實踐行為以及法律的示范性規定,雖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顯示被保險人指定何者為受益人的本意,而被保險人究竟意欲以何者為受益人,最重要的是推定其本來意圖,故而,以姓名為受益人,〔16〕此種情形,不宜認為保單未指定受益人,因為被保險人的指定行為雖指向不同主體,但畢竟有所指向,將該保單認定為未指定受益人,即否定了被保險人的指向,不符合被保險人的本意,故而,在雙重指定中選擇一種,優于將其認定為未指定。雖有理論與實踐的優勢,但優勢微弱。
其二,被保險人在載明姓名與身份關系之外,尚載明了其他幫助確定受益人的事項。
此種情況下,可以根據記載的不同情況推定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意愿,其結果是,既可能將姓名作為受益人,亦可能將身份關系作為受益人。在我國,幫助確定受益人的記載通常是身份證號碼,利用身份證號碼,基本可以確定被保險人意欲指定的對象:當身份證號碼與被保險人指定之姓名相一致時,姓名應作為受益人;當身份證號碼與身份關系所指對象相一致時,身份關系指向的對象應作為受益人。此間的推定邏輯大致是:被保險人將身份關系和姓名同時記載于保險合同中,其中必有一項是錯誤記載,而身份證號碼恰好可以用來甄別究竟哪個記載是錯誤記載。此外,在姓名與身份關系記載的證明力不相上下之時,身份證號碼的出現立刻補強了其中一方的證明力,使得此方成為證據的絕對優勢方,法律上應當推定此方作為受益人。當然,除了身份證號碼之外,其他與受益人相關的記載事項,例如,性別、年齡、出生日期等亦能夠起到與身份證號碼類似的作用,其證明作用雖不似身份證號碼一樣直接,但亦能加強某方作為受益人的證明力。
第二種情況是:雙重指定指向不同主體,并且在指定之后身份關系發生了變動。又可分為兩種情形討論。
其一,身份關系發生變化,但仍應將受益人確定為姓名指向之人。即身份關系發生變化對受益人的確定沒有影響。詳言之,倘若保單在雙重指定之外,另有信息顯示應將姓名作為受益人,例如,保單中記載的身份證號碼與姓名一致,或者,在姓名與身份關系之外別無其他信息幫助確定受益人,則依上述規則,此時應以姓名所指之人作為受益人。因為身份關系指向之人既然不能作為受益人,無論其如何變化,均不會影響受益人的認定。
其二,身份關系出現變化,除身份關系指向之人能夠證明被保險人無意變更受益人之外,應視為未指定受益人。此種情形出現的前提如上所述,即被保險人進行了雙重指定,但在姓名和身份關系之外,尚有其他信息證明被保險人意欲將身份關系確定為受益人,例如,保單載明的身份證號碼與身份關系所指之人一致,此時,按照上述規則,推定被保險人不欲將以姓名所指之人作為受益人,而意欲以身份關系所指之人作為受益人。然而,被保險人指定之后,身份關系發生變動,這通常意味著,被保險人與身份關系所指之人的關系惡化,在關系惡化的情況下,法律宜推定被保險人最終不欲將身份關系所指之人作為受益人,除非身份關系所指之人能夠證明被保險人沒有變更受益人的意圖。由此可知,若非存在被保險人不欲變更受益人的證據,便應推定被保險人不欲將姓名和身份關系作為受益人,此種情形,自然符合《保險法》第42條第1款“受益人指定不明無法確定”的情形,宜推定該保單未指定受益人,由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領取保險金。
綜上,在受益人雙重指定的情況下,應當將保單中的姓名還是身份關系視為受益人,需分兩種情況討論:第一,雙重指定指向同一主體。此種情形又宜有所區分:若身份關系未發生變動,因不會出現糾紛無需討論;若身份關系發生變動,則除非身份關系所指之人能夠證明被保險人并無變更受益人的意向,否則應視為保單上未指定受益人,而以被保險人之繼承人作為保單受益人。第二,雙重指定指向不同主體。此種情形亦宜區分:若身份關系未發生變動,應當借助保單上載明的,能夠幫助確定受益人的其他信息(譬如身份證號碼)確定受益人。在沒有其他信息可資幫助的情況下,應將保單中載明的姓名確定為受益人。在身份關系發生變動的情況下,如果能夠借助其他信息將姓名確定為受益人,或者除姓名和身份關系之外別無其他信息,則應將姓名確定為受益人;如果其他信息更傾向于將身份關系作為受益人,則除非身份關系所指之人能夠證明被保險人并無變更受益人的意向,否則應視為保單上未指定受益人。
四、雙重指定的特別情況:同居情形的處理
(一)雙重指定的特殊情況:因同居而指定受益人
此處所言雙重指定的特殊情況,乃指前述案例情形下的一種特例:被保險人與姓名所指之人存在同居或其他不道德關系。譬如,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時,在保單中填寫某甲的姓名,并注明某甲的身份證號,同時,保單中載明的身份關系為 “配偶”,但事實表明,某甲與被保險人并無法律上的 “配偶”關系,被保險人將某甲指定為“配偶”關系,是因為其與某甲長期同居,自認為關系已屬“配偶”,但事實上,被保險人與其法律上的“配偶”尚未離婚,其法律上的“配偶”仍然存在,因此出現法律上之“配偶”與保單載明的“姓名”之間的保險金歸屬爭議。
此種特殊情形之所以應被討論,是因為在此種情形下,本文第三部分所確定的處理規則可能遭遇挑戰。依照前述關于雙重指定的受益人確定規則,某甲應當被認定為受益人并最終領取保險金,然而,將保險金給予同居之人,往往會遭到普通道德觀念的質疑:部分民眾會認為,將保險金給予同居之人,有違社會公共道德。同時,亦有一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這一處理辦法違背了法律上的公序良俗原則。那么,在這種特殊的雙重指定之下,誰應當被認定為真正的受益人?保險金應當歸于何者?
(二)公序良俗的判斷對象:指定受益人行為
在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間存在同居關系時,指定受益人涉及兩個行為:同居行為和指定受益人行為。
盡管同居行為違反公序良俗原則,但與保險金的歸屬并無必然聯系。在民法學理論上,一派學者認為,民法之公序良俗乃私法自治的前提,公序良俗本身便是對私法自治的限制。〔17〕謝瀟:《公序良俗與私法自治:原則沖突與位階的妥當性安置》,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5年第6期。如果違背公序良俗,則該行為應當受到否定性的評價。依此理論,被保險人與配偶之外的他人同居,無論出于何種原因,皆不能為社會公眾所接受,同居行為應當受到否定性的評價。筆者以為,對同居行為的否定性評價不能殃及對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否定性評價。同居行為并不能直接導致保險金歸于同居者,在同居行為與保險金歸于同居者的事實之間,尚存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如無這一行為,保險金不會歸屬于同居者。雙重指定糾紛的焦點仍是保險金歸屬的問題,故僅僅對同居行為進行考察,不能回答保險金應當歸于何者的問題,對問題的解決并無實益。
真正需要考察的是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行為,考察該行為是否違背了公序良俗原則。這是因為,指定受益人的行為直接決定保險金的歸屬,考察被保險人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是否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即成為問題之關鍵,倘若該行為違反公序良俗原則,則該指定行為無效,同居之人不能獲得保險金;倘若該行為并不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則該指定行為有效,同居之人可以獲得保險金。德國法院曾判決了一起類似案件,該案中,被繼承人將其財產遺贈給同居情人,在被繼承人死亡之后,其同居情人與法律上的配偶爭奪遺產。法院認為,該案的考察重點并非被保險人的同居行為,而是被保險人的遺贈行為是否違背了公序良俗原則。〔18〕于飛:《公序良俗原則研究——以基本原則的具體化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頁。德國學者對此指出:“在判斷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善良風俗時,人們倘使不以法律行為為準而是以行為人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可歸責性作為判斷的基礎,是十分危險的。”〔19〕[德] 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 遲穎譯、米健校,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頁。同時,在我國理論界,也出現了公序良俗原則的考察對象僅限于法律行為的觀點,〔20〕易軍:《民法上公序良俗條款的政治哲學思考——以私人自治的維護為中心》,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依照這一觀點,接受公序良俗原則考察的應當是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這一法律行為,而非同居行為。
(三)指定受益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的判斷:被保險人動機之探究
由上可知,我們需要判斷被保險人將同居者指定為受益人的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然而,在作此判斷時,裁判者需要一定的標準,如此,我們必須為判斷尋找標準。
研究公序良俗原則的學者認為,判斷一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原則,主要從行為內容、行為動機兩個方面著手。〔21〕前引〔18〕,于飛書,第109-114頁。考察行為內容,即考察法律行為的權利義務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原則,例如,交易毒品的行為,其內容為交易雙方對毒品的權利和義務,該內容必然違反公序良俗。考察行為的動機,即考察行為人作出該行為的間接原因,例如,行為人購買房屋,如果其動機乃是用于開設賭場,則該動機必然違反公序良俗原則。〔22〕值得注意的是,動機與目的有所不同,一般認為,動機是法律行為的間接原因,目的則是法律行為的直接原因。參見鄭玉波:《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頁。在上述購買房屋的行為中,行為人的目的是獲得房屋,動機則是開設賭場,其目的并不違反公序良俗,動機則違反公序良俗。不過,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嚴格區分動機與目的。
從行為內容考察,并不能得出被保險人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的行為違反公序良俗原則的結論。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行為,屬于處分行為,其內容是將被保險人自己的財產給予受益人,在道德上,這種轉移財產的行為本身是中立的、符合法律規定的,很難說其違反了公序良俗原則。因此,僅從行為內容考察,不能認為被保險人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的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原則。該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原則,尚需從該行為的動機考察。
從行為動機考察,被保險人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原則,需區別對待:當被保險人之動機在于將保險金作為不合法性關系的交易籌碼時,指定受益人之行為違背公序良俗原則;當被保險人之動機并非將保險金作為不合法性關系的交易籌碼時,指定受益人的行為并不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其中原理是,被保險人通過指定受益人將保險金給予不合法性交易的對方,其指定受益人的行為乃是不合法性交易的支付價款行為,屬于不合法性交易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合法性交易既違反法律,又違反公序良俗,指定受益人的行為作為其有機組成部分,自然也違背公序良俗。然而,倘若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并非出于為不合法性交易支付對價的動機,而是出于某種中立甚至善良的動機,例如,為同居者的日后生活考慮,則指定受益人之行為并不是為不合法性關系支付對價,亦非不合法性交易的組成部分,盡管不合法性關系本身違背公序良俗,但不能籍此證明指定受益人之行為違背公序良俗。對此,德國學者茨威格特和克茨指出:“一個已婚的男子如果給他的情人作出贈與或者供養其生活的許諾,或者將其作為人壽保險的受益人,或者將其作為遺囑繼承人時,這種協議一般是有效的。這種行為只有在如下情況下才是無效的:即該女性的目的就是以固定的方式、持續性地從這種關系中不道德地獲得報酬作為產業性的利益。但是,如果該男子具有某種值得尊重的動機,或者是在一段長期的共同關系之后為了保障該女子日后的生活,或者是為了感謝她給予自己的支持、照料生活以及扶養等,從而給予該女子物質性的報酬,則這種行為總是有效的。”〔23〕[德]康·茨威格特、海·克茨:《違背法律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后果比較》,孫憲忠譯,載《環球法律評論》2003年第4期。
基于上述論證,發生特殊的雙重指定糾紛時,絕大多數情況下,應視同居之人為真正受益人。這是因為,基于“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訴訟原則,糾紛當事人(非同居之人)若想成為受益人,必須舉證證明被保險人與同居之人之間存在不合法的性交易關系,〔24〕同居關系并非性交易關系,許多情況下,同居并不存在交易。且被保險人指定同居之人作為受益人乃是為了支付性交易的對價,而證明這一點非常困難。〔25〕倘若當事人能夠證明被保險人以指定受益人作為性交易的對價,保單真正的受益人應當為誰?是被保險人法律上的配偶?還是被保險人所有的法定繼承人?這一問題頗為復雜。筆者認為,既然通過解釋的方法能夠確定同居之人乃是被保險人意向的受益人(此受益人指定僅因違背公序良俗原則而無效),說明保單上載明的“配偶”并非被保險人意向之受益人,盡管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因違背公序良俗原則而無效,并不能證明保單上載明的“配偶”應當作為真正受益人,此種情形下,從被保險人的指定意圖推定,應將受益人推定為被保險人的所有法定繼承人。由于證明被保險人以指定受益人作為性交易的對價幾無可能,對這一問題,筆者不打算展開討論。正是因為證明上的困難,此類案件在德國的審判結果通常是同居之人勝訴,對此,德國學者梅迪庫斯指出:“今天,司法判例也不再推定性關系是行為人給予對方財產的主導性原因。而由于財產給予人的真實動機往往是無法證明的,因此在今天,幾乎所有的財產給予行為,其動機是否與性有關,都屬有效。”〔26〕[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頁。
(四)公序良俗原則的謙抑:原則向規則的退讓
上述論證乃是基于對同居之人可否作為受益人的微觀技術性論證,自宏觀方面來看,同居之人可以成為受益人亦可獲得證成。
同居之人可否作為受益人在宏觀上的爭點,可以看作《保險法》規則與公序良俗原則之爭:這里的規則,即《保險法》上公認的規則——被保險人有權自由指定受益人,無論該受益人身份如何,均有權獲得保險金。這里的原則,即公序良俗原則。《保險法》之規則與公序良俗原則在被保險人能否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這一問題上發生沖突。沖突之解決,通常的處理辦法是,“窮盡法律規則,方得適用法律原則”,〔27〕馮玉軍:《法律基礎》,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若無更強理由,不適用法律原則”。〔28〕舒國瀅:《法律原則適用中的難題何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如果存在法律規則,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則原則之適用一般應當退讓于規則之適用。有學者進一步對此詳釋:“在具體個案中,若規則與原則相沖突,在例外情形下也可適用,但須承擔例外情形下的論證義務。”〔29〕林來梵、張卓明:《論法律原則的司法適用——從規范性法學方法論角度的一個分析》,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2期。正如上文所論,由于同居行為與指定受益人的行為應當分離,對同居行為的譴責不能直接殃及指定受益人的行為,故而,論證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行為應當例外地適用公序良俗原則并不容易,因此,在這一角度,適用公序良俗原則否定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之行為,很難服眾。
我國法院曾出現過以公序良俗原則否定現行法律規則的案件,但是,這一案件的判決遭致理論界的廣泛批評。此即“中國公序良俗第一案”(瀘州遺贈案),案件中,黃某與蔣某于1963年結婚,但夫妻關系不睦,1994年,黃某認識了張姓女子,并與其長期同居,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2001年,黃某被診斷患有肝癌,在患病期間,張某以妻子的身份守在病床前照顧。黃某于是立下遺囑,將自己的財產遺贈給張某。黃某去世后,張某依照遺囑向黃某法律上的妻子蔣某索要遺贈財物,被蔣某拒絕,遂訴至法院。一審法院認為,黃某的行為違反公序良俗原則,拒絕支持其訴訟請求。〔30〕參見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2001〕納溪民初字第561號民事判決書。二審法院同樣以黃某的遺贈行為違背公序良俗原則為由判決張某敗訴。〔31〕參見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1〕瀘民一終字第621號民事判決書。這一案件在法學界引起巨大反響,除個別學者支持本案判決外,〔32〕范愉:《瀘州遺贈案評析——一個法社會學的分析》,載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編輯部主辦:《判解研究》2002年第2輯,第49頁。大多數學者對公序良俗原則在本案中的適用持懷疑態度。〔33〕黃偉文:《法律與道德之爭:瀘州遺贈案的司法裁判研究》,載《湖北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朱慶育:《民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頁;許明月、曹明睿:《瀘州遺贈案的另一種解讀》,載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編輯部主辦:《判解研究》2002年第2輯,第81-82頁。有學者提出,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法官適用該原則應當慎之又慎。〔34〕前引〔20〕,易軍文。更有學者認為,公序良俗原則只能以補充與解釋原則的身份留存于民法體系中,而不能獲得民法基本原則之神圣至尊地位,當行為人的自由處分行為與公序良俗相違背時,自由處分行為優于公序良俗原則適用。〔35〕前引〔17〕,謝瀟文。與被繼承人將自己的遺產遺贈于同居之人類似,被保險人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亦屬于自由處分行為,由于存在《保險法》上的具體處理規則,公序良俗原則應當謙抑地適用。
總之,在被保險人以姓名的方式在保險合同中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同時又將受益人的身份關系載明為“配偶”或“夫妻”這種特殊情況下,判斷同居之人是否可以成為受益人并領取保險金時,主要涉及的問題是被保險人將同居之人指定為受益人的行為是否違背了公序良俗原則,而判斷該指定是否違背公序良俗原則的標準主要是指定行為的內容以及被保險人指定的動機,從指定行為內容看,該行為并不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從被保險人指定之動機看,倘若被保險人將該行為作為性關系的交易籌碼,則該行為違背公序良俗原則。除此之外,該指定行為并不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即便受益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存在不道德的同居關系,該同居之人依然有權作為受益人領取保險金。
結 語
最高人民法院在《保險法司法解釋三》第9條第2款第(三)項中對雙重指定的情形作了規定,然而,該規定針對的問題主要是雙重指定中最常見的情形,即姓名與身份關系指向同一主體,且身份關系隨后發生變動的情形。在該種情形下,司法解釋將保單視為未指定受益人具有合理性,畢竟,身份關系的變動通常是因被保險人與其所指定的受益人關系惡化所致,既然被保險人與其所指定的受益人關系惡化,大致可以推定被保險人不欲將保險金給予所指定的受益人,又由于保單上不存在其他受益人,故而毋寧推定該保單未指定受益人,從而由被保險人的法定繼承人領取保險金。但是,該規定可能忽略的問題是,因身份關系的變動在少數情形下并非雙方關系惡化所致,在這種情形下,推定保單未指定受益人正好違背了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本意,以保單所載受益人作為真正受益人乃是合理的選擇,不過,保單所載受益人需舉證證明被保險人并無變更受益人的意向。司法解釋應對此加以完善。
姓名與身份關系并非指向同一主體的情形,司法解釋未作處理,在這種情形下,倘若保單中除了姓名和身份關系,尚有其他信息能夠幫助確定被保險人想要指定的受益人(例如身份證號碼),則應以該輔助信息指向的主體作為真正受益人。即便沒有其他輔助信息,鑒于實務中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時以姓名為主,身份關系為輔的常態,結合法律對指定受益人的宣示性規定,似將姓名認定為受益人更為適當。
難以處理的是存在同居關系的特殊雙重指定。被保險人一方面將同居之人的姓名記載為受益人,這涉嫌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另一方面又記載了“配偶”的身份關系,而同居之人顯然不是法律上的配偶,這將導致保單上出現兩個相互矛盾的受益人。在此情形下,究竟以何者作為受益人,應當審查的是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行為是否違背公序良俗原則,而非同居行為是否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對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行為進行審查,主要審查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的動機,倘若被保險人指定同居之人作為受益人的動機是將保險金作為不合法性關系的交易籌碼,則指定行為因違背公序良俗原則而無效,同居之人不得領取保險金。除此之外,同居關系不影響該同居人作為受益人,保險金應歸同居之人所有。
——兼評《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42條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