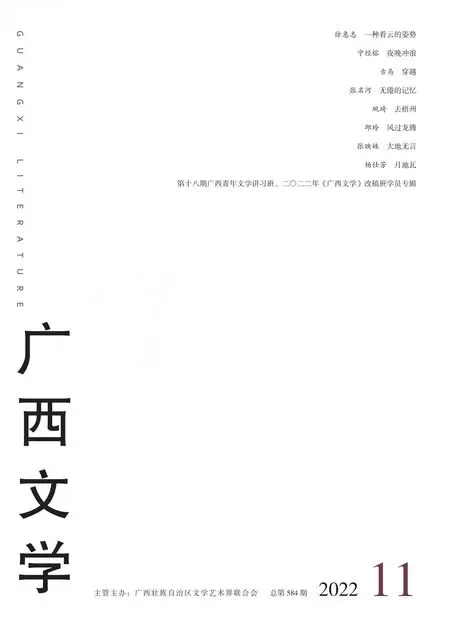歷史的召喚與秩序的重建
——錦璐小說近作讀札
曾 攀
小說是否能夠有效地召喚與征用歷史,以審視和改造現實的境況,蘊蓄并創生未來的鏡像,往往取決于寫作者或敘事者是否具備真正的歷史意識,這一方面再往大里說,在我們談論歷史的時候,便意味著以當下之處境、觀念、立場重新審度之,即便是回到當時的語境,同樣難以擺脫主體性與主觀性的參與,這是海登·懷特意義上的史與詩兼具的審美結構;進一步說,敘述主體以及人物主體內在的價值話語,同樣需要借助于小說的想象性序列,重新理解歷史這一重要參數,紊亂則重整,坍塌便再造,以探詢靈魂之畛域,摹畫主體的精神圖譜,重建內外之秩序。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所有的現實都是從歷史走來,未知的與未竟的構筑,同樣需要在此基礎上加以衡量。對于小說而言,召喚歷史以重建秩序的過程,常常摻雜著不可估量的現實變量,這是虛構性敘事最具難度的部分,同時也是主體命運歸入自身序列抑或走向背反的潛在可能。錦璐近期的小說便試圖處理這樣的命題,其所透露出來的,是在既往歷史與現存秩序的鴻溝中,嘗試修補、填充,循此開掘隱秘而幽深的靈魂,并洞悉精神困境中的人性微光。
《復調喀秋莎》是典型的懷舊敘事,故人重逢,聊話家常,平淡的敘述中,涌動著過往的波瀾。小說寫歷史的再現與重演,儼然已不是新鮮的題材,無論是時代的還是主體的歷史,總是以某種異質性的光譜,折射進當下的現實,又不斷地被現實的情緒、境況所分解、重塑。小說中,原本其樂融融的懷舊氣氛,被張司令的到來所打破,聚會的KTV包廂作為他們重逢的場域,彼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些傷疤和創痛開始不斷水落石出。不得不說,真相總是經不住細細地琢磨,人心之幽深有時候也常常顯得淺顯,喜怒哀怨、愛恨情仇,到底使人入魔著困,萬難消歇。時間故而常常可以開出玫瑰,但也時時面臨枯萎敗落。艾四萍、呂心韻她們之間的往事如煙,彌漫心間,友朋間的敘舊甚至營造出了一種意識流的氛圍:“喬老爺和綠眉毛頭對頭咬耳朵,女進修生托著下巴啃手指,張司令吭哧吭哧喘粗氣,呂心韻眼里冒著光。他們藏在旋轉光的光影里,一會兒浮出,一會兒隱沒。很多種顏色交替出現,檸檬黃色、荼蘼紅色、橄欖綠色、紫羅蘭色,有一種接近腐敗的氣息。某個旋律兀自單循環,形成一坨黏黏糊糊的液體,仿佛達利那幅名畫《永恒的記憶》里扭曲變形的軟塌塌的時鐘,給人一種壓抑痛苦卻又無法聲張的感覺。”小說最后,說到動情之處,艾四萍拖著因年邁而受難的膝蓋,闖進一間又一間包廂,用一種匪夷所思的執拗打斷唱歌的人們,要他們查找俄語版《喀秋莎》。這是一代人的精神印記,也是他們的情感紐帶,阿霞、安德留沙、阿杰莉娜,一個個名字,成了彼此熠熠生輝的勛章,因為這背后的記憶和創傷,為他們抵御著時間的風暴,“看吶,她多么像一位穿越了炮火穿越了時空帶著勝利歸來的老年喀秋莎,灰白的童花頭發絲紛飛,疲憊又堅強。她沉著地低聲起調門,雙手做鏗鏘的指揮,舌頭打卷,彈出一連串堅定的跳躍的飽滿的富有彈性的俄語單詞”。與此同時,呂心韻也引吭高歌,勇毅奔襲,亦如一個戰士。這便是“復調”的喀秋莎,跳躍在不同的時間褶皺,也流播于不同個體的精神巖層,歷史的神采于焉若隱若現。
小說《女人邊鋒》盡管在題名中突出的是作為女性的邊鋒,然而在小說中,卻不斷掩蓋她作為女性的性征,無論是邊鋒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還是醉心體育不讓須眉,又或是性情耿直風風火火,小說意欲塑造的是一個顯明的中性主體,甚至以此抵抗時代的偏見與人事的繁雜。有意思的是,“她的行動、做派都有些男性化的成分存在,但由于容貌、體態的峭拔,反倒使她擁有了別具一格的氣度”,如她的名字邊鋒所彰顯的,其性情往往偏于凌厲而棱角畢現。“誰也沒想到哪天會見到邊鋒,我們已經十五年沒有聽到她的音信了”,小說同時通過邊鋒的回憶性與現實性的敘寫,不斷提出自身的性別議題,特別是在當下女性(包括男性本身)都被符號化、系統化與智能化所取代,性別時而僅成為系統中勾選的選項;又或在世俗生活中不斷被異化,在種種的妥協、獻祭與自我的衰亡中,抹除內在的性別指向。因此小說通過“少女邊鋒”,實際上是試圖將性別模糊化,并重新完成主體自我的評估再塑。小說最驚心動魄的,是曾經作為標槍運動員的邊鋒,向體育場的主席臺投擲標槍,那意味著她對男性及其權力,包括她對過往情感的憤懣的反叛、反抗以至反擊,“透過云層的陽光將一條條壯麗的光線斜插大地。這種學名‘云隙光’的自然現象,又被稱為‘耶穌光’。這束光與斜插遠處的那桿標槍呈‘X’交叉,仿佛一個巨大的未知數自從天降”。然而我的疑問是,在這樣激烈對抗之后,是否能形成某種情感的、倫理的與體系性的機制,邊鋒的遭遇以及她所代表的女性訴求和命運,是否足以建構有效的路徑,以通達女性的所欲、所求及所往。否則,小說里丑陋骯臟、低俗無趣的趙一寧之流還是會層出不窮,且占據歷史的中央。或許這也是小說的尖銳之處。因此,我更愿意看到的,不是邊鋒手持標槍的孤注一擲,而是可以復刻的反抗后的重塑,借此可以扭轉情勢,啟示總體性的精神序列和想象空間。
在《喬丹的祝福》里,準退休人員高遠重返故地S城,踏上單位安排的退休旅行。在那里,他重訪故友,往事并不如煙,重拾往事的經過,同時也是再思生命的起錨地。站在時間的彼岸,現實的此岸竟如此黯淡,高遠需要重新尋覓生命的出口。除了那些世俗世界里的男性同學,高遠此行的重要目的,還有一個她。他對她情意悠長,也幽深。一雙故意剜爛的耐克鞋,放在陽臺,成為庇護她的舉動。但是話說回來,我倒覺得這樣的做法更多只是象征性的意義,于她的生活幾乎不會產生太大影響。但悲哀的是,他也唯有如此,只能如此。每個人對于自己向往和期待的所在,能夠傾盡努力的時候不多,回首往事,很多事情不過只是盡一點心力罷了,更多的是無力和無助。說到底,高遠也只有對著遠方的陳亞軍,一筆一畫寫下一句:祝你平安。召喚并重塑歷史的嘗試同樣如此,千頭萬緒中的千思萬慮,到底收效甚微,但怪就怪在,即便“無可奈何花落去”,我們還是不甘心,還是想試一試,“此情可待成追憶”,時間可以開出鮮花,更多的時候是枯枝和敗葉。對于高遠而言,重返S城是一場尋根之旅,在那里,暴露了他的一段情感歷史,但也照亮了往事的塵埃,盡管這樣的時刻大部分是灰暗無光的,但已足夠令其感念。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在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而歷史的光束,再如何微弱,打在人的身上,足可周身通透。
《我是金銀珠》講的是老人臨終關懷的事,小金是陶叔的保姆,陷入了倫理旋渦,小金一片真誠,被陶叔子女誤解其是想侵吞家財。但小金敬重陶叔是高級工程師,清清白白的知識分子。兩人的確也有著非同一般的感情。然而波折在于,小金的生活另有難處,她名義上的丈夫不斷給她施壓想要謀取錢財。小說最后,臨終前的陶叔執意要和小金結婚,同時丈夫也步步緊逼。作為再普通不過的女性形象,小金最終卻完成了對二者的超克。一個卑微的底層女工,卻有一身正氣,對人俠肝義膽。她對陶叔自有情意,卻不相虧欠,終而復得自然。小說特別有意思的一個地方,是小金最后登機前,不斷聽到廣播傳來催促自己的聲音,“金銀珠、金銀珠……”,這是自我確認,也是內在的建構,她做出了艱難的抉擇,這是一個現代女性的重要標識,無關乎地位和金錢,那種不慕虛榮、不貪錢財、不畏脅迫的人格,一身清白、無懼無畏。現實世界里,這樣的人不多,但很珍貴,是可以撬動乃至重塑整個社會風氣與文化革新的關鍵。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樣的主體存在,歷史將如何推動向前。
最后重點談一談中篇小說《不忘》。女主人公金燕是公司的財務高管,帶著患上阿爾茨海默癥的母親梅楠出游,“從朝天門碼頭登上從重慶開往宜昌的黃金六號游輪。這或許是母女倆最后一次同行出游。回來之后,梅楠有可能被送去養老院”。梅楠是一個醫生,“她并沒喪失全部能力,但腦回路里的‘線路’經常斷掉,或者搭錯,同時喪失了時間感和方位感,需要人照料”。對于一個人來說,縱向看是失去了記憶和歷史,橫向說來又沒有了方向感,不僅多有人身危險,而且空余嘆息與悲觀。這讓我想起鐘求是的《父親的長河》,同樣寫老年癡呆癥的父親,其大部分的記憶已經喪失,父子故地重游,父親最后不忘駕駛自己兒時碼頭上的船只,劃向記憶的長河,也隱喻著遠去生命的渺無蹤跡。而《不忘》則更傾向于世俗的理解,“她余生所有的時間,就是消磨。與時間一同被消磨的,還有她無可挽回的記憶,以及親人必將被消耗殆盡的耐心”。現實秩序的紊亂、生活邏輯的喪失,使得主體性產生萎縮,由是面臨著被現世拋擲的危機。質言之,年邁的孤獨疊加疾病的棄置,母親梅楠的處境可想而知。在病中,“慢性的大腦退行性疾病,記憶顛倒錯亂,只記得以前的事,不記得眼前的事”。不僅如此,對于金燕而言,也有過難以忍受的記憶,她“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兩段不堪回首的情人經歷,一場烈火烹油般的姐弟戀,還曾被PUA,財色兩空差點崩潰”。她與現任丈夫林遠高的關系也是岌岌可危,直至最后才略顯亮色。
小說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船上參加完一個舞會回來,母親突然對金燕說,她看到了金燕的父親陳志凡。原來是她將同行的老先生,誤認為是自己的丈夫。如此一來,她和他的往事一下被激活了。自此,每個人事實上都背負著歷史與現實的巨石,有時候壓得喘不過氣來,更多時候是以自嘲相撫慰。這么似乎又說得太晦暗了,姑且將之視為小說對人物的一種賦形吧,就像小說最后,令人駭異的一幕發生了,“老先生脖子上用絲巾圍住的地方,有一個傷口。那是一個留置管,用于深靜脈輸液,得了癌癥的病人才這么搞,針頭置留在血管里不取出來”。也許,只有疾病的折磨與死亡的脅迫,最可觸動人心。衰落與死亡,又恰是人之常態。而唯有“不忘”,方有救贖可能。
讀到這個小說的最后,尤其是金燕為母親洗澡的那一段,不禁想起我的外婆。外公去世得早,外婆獨自生活在一個小屋子里,那是她和外公的臥房。十余年幾乎足不出戶,我一直很詫異,是什么信念支撐著她堅持了那么久?如今她已經九十高齡。后來我得知,外婆始終“不忘”外公,甚至認為他沒有離她而去,一邁腳、一抬頭,依然在她身邊,她不愿乃至不覺得外公已離她遠去,倆人還擠在那個略顯雜亂的并不光明通透的房子里;第二個是她忘不了也放不下子女們,想經常見見他們,哪怕她已經認不全了,忘了他們的名字和形貌,又或有時對兒女、孫輩滿懷抱怨,但她很愿意看到他們在她身邊,給她做一頓飯、洗一次澡、說一次笑,這是她的精神支柱,也是靈魂倚靠。所以我常常在想,人生活于此一世間,總有一定的極細微又極宏大的信念撐持著,比如親情,比如愛,又或是怨念與欲望,也就是人類文明長期建構起來的人之為人,同時又使人超越自身的價值范疇,即便這樣的道德倫理遭受厄運,也必將通過所有的方式加以重建。
總而言之,對于錦璐而言,經由近期的小說創作,重拾寫作之技藝,從實有的經驗再次回過頭來訴諸虛構之力,這又何嘗不代表著一種歷史的召喚與秩序的重建。這些小說有時顯得偏于溫情而冷峻不足,結構上過于尋求完整的背后,是否還可以存在宕開一處的可能,結構的殘缺乃至斷裂,有時或能呈現悠長、致遠的意味。就像她的小說《不忘》里面,人們在郵輪上觀望星象,北斗七星由是進入大家的眼界,“一年四季,它基本都是在正北方不動的。在野外迷了路,看到北極星就能判斷方向了”,這似乎有一種隱喻在,對于人而言,或病痛,或惶惑,或迷亂,時而“迷了路”,但只要念念“不忘”,也許可以于再造中加以超克。因為在小說里,充溢著對溫情與敬愛的倚重,以及對良善和守持的秉有,那里樹立著一重對照與反思的鏡像,那是現代主體得以實現內部自循環的憑借,是依此建構種種可能的要素,迷失得再遠,好的文學到底是生命的“北極星”,辨明方向,解析價值,這個過程自然充滿曲折,卻始終鮮活、靈動、開闊,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