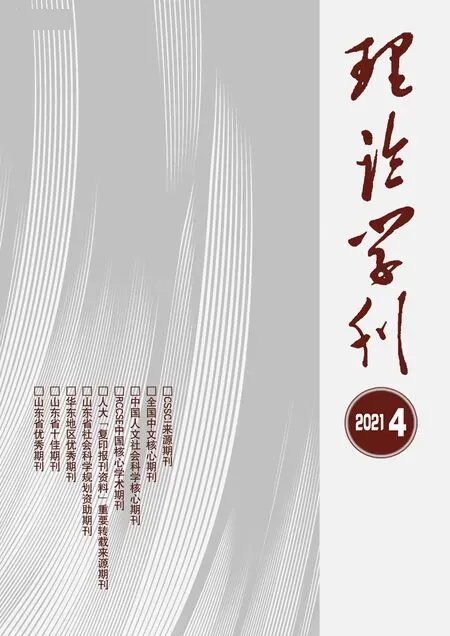調(diào)查與革命:社會改造追求下的李大釗
黃道炫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 100871)
社會調(diào)查興盛于近代中國,并受到中國共產(chǎn)黨的高度關(guān)注,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共產(chǎn)黨調(diào)查研究傳統(tǒng)的形成,同李大釗關(guān)系至大。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李大釗憑著對社會改造的關(guān)懷及學者的訓練,已經(jīng)對社會調(diào)查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依據(j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改造要求和實踐傳統(tǒng),自覺地通過社會調(diào)查了解中國實際。李大釗的改造社會要求使他能夠很快接納近代興起的社會調(diào)查,而社會調(diào)查的結(jié)果又導致他更加堅定自己的社會改造立場,加速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zhuǎn)變。
一、人力車夫和自殺者
近代中國的社會調(diào)查肇始于晚清,據(jù)統(tǒng)計,《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中計有調(diào)查消息和案例1489個,其中中國人自己做的國內(nèi)調(diào)查有957個(1)參見李章鵬:《清末中國現(xiàn)代社會調(diào)查肇興芻論》,《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當然,這時候的調(diào)查多數(shù)都比較粗淺,比如《浙江潮》1903年刊登的《處州青田縣調(diào)查稿》,涉及青田縣的官場、書院義塾、學生、歷史人物、田產(chǎn)交易、土產(chǎn)、風俗、煙館、妓院等,均只有寥寥數(shù)語(2)《處州青田縣調(diào)查稿》,《浙江潮》1903年第6期。。較具學術(shù)自覺的調(diào)查一般認為是1914—1915年北京社會實進會做的《洋車夫生活狀況的調(diào)查》。該調(diào)查得到美國傳教士約翰·步濟時的幫助,共調(diào)查了302個洋車夫的生活情況。此后,社會調(diào)查在中國廣泛開展,成為20世紀中國一個經(jīng)久不衰的現(xiàn)象。
社會調(diào)查的興盛有多方面的原因,同近代中國的大變局息息相關(guān)。面對列強的沖擊,晚清中國自覺意識不斷強化,在和西方世界的比照中,既猛醒自身之不足,大力學習西方科學;也在碰撞中區(qū)分自我,產(chǎn)生更加濃厚的自我認知要求。社會調(diào)查兼具這兩個因素,既有科學精神的滲入,也代表著中國人自我觀照的努力。體現(xiàn)近代社會的目光向下要求,這樣的觀照又具有明顯的底層特征,調(diào)查對象主要是城市或農(nóng)村的中下層民眾。正如北京社會實進會在《新社會》創(chuàng)刊號發(fā)刊詞中所說:“我們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數(shù)中下級的平民生活、思想、習俗改造起來;是漸進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運動;是切實的——一邊啟發(fā)他們的解放心理,一邊增加他們的知識,以提高他們的道德觀念。”其中社會學的研究態(tài)度是社會改造的重要方法,要“實地調(diào)查一切社會上情況,不憑虛發(fā)論,不無的放矢”(3)《發(fā)刊詞》,《新社會》第1號(1919年11月1日)。。
社會調(diào)查在馬克思主義中更是備受推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社會調(diào)查都極為重視。恩格斯在談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寫作時說:“我非常認真地研究過你們的狀況,研究過我能弄到的各種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為滿足。我尋求的并不僅僅是和這個題目有關(guān)的抽象的知識,我愿意在你們的住宅中看到你們,觀察你們的日常生活,親眼看看你們?yōu)榉纯鼓銈兊膲浩日叩纳鐣驼蔚慕y(tǒng)治而進行的斗爭。”(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3頁。1889年至1893年,在薩馬拉期間,列寧經(jīng)常到農(nóng)民中作調(diào)查。他于1893年寫成的第一部著作《農(nóng)民生活中的新的經(jīng)濟變動》,就是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產(chǎn)物。正因如此,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有著社會調(diào)查的雙重資源,他們從新文化中吸取科學精神,又從馬克思主義中獲得實踐態(tài)度,社會調(diào)查幾乎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必修課,即如毛澤東所說:“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身,作了許多調(diào)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chǎn)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diào)查”;“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diào)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xiàn)在及將來)”(5)《毛澤東農(nóng)村調(diào)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頁。。
作為中國接受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先驅(qū),李大釗可謂中國社會調(diào)查的先行者。同為北京共產(chǎn)黨組織發(fā)起人的張國燾曾評判說,李大釗“很注重實際的資料和比較研究”(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現(xiàn)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80頁。,這應(yīng)為中肯之言。縱觀李大釗的求學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他和19世紀末興起的社會學有不解之緣。1907年,李大釗入天津法政學堂,清末以降,一些法政學堂已將社會學列入教材(7)《法政學堂教科書一覽表》(下),《東方雜志》第7卷第11號(1910年12月26日)。。1913年,李大釗赴日,次年進入早稻田大學修習政治經(jīng)濟學。在早稻田大學的第二學年,李大釗有16門必修課、6門選修課,必修課包括財政學、貨幣與信用論、工業(yè)政策、農(nóng)業(yè)政策、社會政策、經(jīng)濟史、文明史、統(tǒng)計學、格廷庫斯社會學基礎(chǔ)等,選修課包括都市問題、保險政策等(8)參見韓一德:《李大釗留學日本時期的史實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這些都和社會學有著相當?shù)年P(guān)聯(lián)。當時,社會學剛剛興起,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根據(jù)當年日本大學的慣例,把社會學放在哲學課內(nèi),規(guī)定第二學年修習(9)《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國留學生章程紀要》,《東方雜志》第2卷第4號(1905年5月28日)。。李大釗必修課里的社會學,就是基于這一學術(shù)背景。
社會學的修習經(jīng)歷,對李大釗有著相當深刻的影響,后來,李大釗一直對社會學有濃厚的興趣,其寫于1919年的名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從社會學的角度闡釋歷史唯物主義,指出:“于社會學上的進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貢獻。他能造出一種有一定排列的組織,能把那從前各自發(fā)展不相為謀的三個學科,就是經(jīng)濟、法律、歷史,聯(lián)為一體,使他現(xiàn)在真值得起那社會學的名稱。”(10)《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頁。應(yīng)該說明的是,此時關(guān)于社會學的概念還不嚴密,當李大釗講社會學的時候,可能是指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學,也可能是指社會科學。20世紀20年代中葉,他對維柯、孟德斯鳩、孔多塞、圣西門的討論,既是歷史哲學的討論,也是社會學的討論,如其所言:“社會學得到這樣一個重要的法則,使研究斯學的人有所依據(jù),俾得循此以考察復雜變動的社會現(xiàn)象,而易得比較真實的效果。這是唯物史觀對于社會學上的絕大貢獻,全與對于史學上的貢獻一樣偉大。”(11)《李大釗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0頁。
社會學的修習和改造社會的愿望相互作用,讓李大釗對中國政治和社會保持密切關(guān)注,并使他和社會調(diào)查結(jié)下了緣分。從日本回國后不久,他和一班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的學生一起成立中國財政經(jīng)濟學會,宣稱:“本會以研究經(jīng)濟學理及調(diào)查事實,以期適用于中國為宗旨。”(12)《京師警察廳抄報李大釗等組織中國經(jīng)濟財政學會致內(nèi)務(wù)部備案呈》(1917年4月21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文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頁。該會會員分甲乙兩種,其中甲種為承擔學會義務(wù)和經(jīng)費的基本會員,1916年有甲種會員11人。李大釗作為發(fā)起者之一,是當然的甲種會員。該會確定的主要職責,就是開展研究調(diào)查。
同中國最早具有學術(shù)自覺的社會調(diào)查選擇了以人力車夫為對象一樣,李大釗最初的社會觀察目光指向的也是人力車夫。1917年2月10日,李大釗發(fā)表《可憐之人力車夫》一文,描述了他眼中的人力車夫:“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車夫為最可憐。終日窮手足之力,以供社會之犧牲。始贏得數(shù)十枚之銅元,一家老弱之生命盡在是矣。”李大釗發(fā)現(xiàn):“北京濁塵漫天,馬渤〔勃〕牛溲都含其中,車馬雜踏之通衢,飛騰四起,車夫哮喘以行其間,最易吸入肺中。茍有精確之觀查,年中車夫之殟〔殭〕而死者,必以患肺病者居多。”(13)《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頁。1870年,日本人高山幸助首先造出人力車,法國人梅納爾很快引入中國作為新興的交通工具,由此而催生出人力車夫群體。李大釗對人力車夫的感受和北京實進會的調(diào)查是相通的,該會的調(diào)查結(jié)論是:人力車夫勞動極為費力且不經(jīng)濟;工作不合衛(wèi)生,佝僂身軀奔跑,阻礙胸部發(fā)展,呼吸急促,吸入街上污濁的灰塵,影響肺部健康;付出的體力與得到的報酬不相稱。人力車夫的問題不僅為個人或國民經(jīng)濟之問題,實為極重要之社會問題(14)參見陶孟和:《北京人力車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版,第120—121頁。。李大釗則進一步強調(diào),這些人力車夫背后面對的是“工廠不興,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歸于此途”(15)《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頁。。正因如此,人力車夫當年引起了知識界的廣泛注意,繼李大釗之后,胡適、陳獨秀、魯迅、沈尹默、葉圣陶、劉半農(nóng)、郁達夫等都寫過以人力車夫為題材的文章、小說或詩歌,至于老舍的小說《駱駝祥子》,也是以人力車夫為主角。新一代知識人對人力車夫的持續(xù)關(guān)注,寄托的是對普通民眾的深刻同情,李大釗可謂開風氣之先者。
五四運動后,改造社會的呼聲日漸強烈,社會調(diào)查成為知識青年的普遍自覺。1919年7月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秉持“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的中國”的目標,在其創(chuàng)辦的《少年世界》中明確標示了刊物宗旨:“注重:(一)實際調(diào)查,(二)敘述事實,(三)應(yīng)用科學。”(16)參見舒新城:《我和教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頁。1919年12月4日,李大釗主持的《晨報》副刊發(fā)表了王光祈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主張過工讀的生活,“每日作工六小時,讀書三小時,其余時間作為娛樂及自修之用”,要求擬加入者“代調(diào)查手工藝種類,并說明需要資本若干”(17)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晨報》(北京)1919年12月4日。。調(diào)查成為這一時代年輕人進入社會的通行方式。
1920年1月,李大釗主持的《晨報》副刊發(fā)表了《北京貧民的悲慘生活》,這是一群受李大釗影響的青年人到人力車夫聚居區(qū)域所作調(diào)查的記錄,內(nèi)稱:“先索得該區(qū)警署所存的極貧居戶冊子,里面開列貧民姓名門牌,共計百五十余家,所以調(diào)查時比較的容易著手。我們一共十人分五組,每組擔任30戶。”調(diào)查呈現(xiàn)了驚人的貧困:“他們的衣服除小孩了〔子〕大多穿著破棉外,大人有穿夾襖的下面大都穿著單褲――以婦女為最多。……土炕上有許多是沒有被窩的,有的是攤著爛穿了的,或東一塊西一塊的什么東西。一家五六口的,也只有一個土坑,甚至有兩三家拼住一間小屋的。屋里的黑暗污穢不通氣,無異舊式的牢監(jiān)。”這篇社會調(diào)查最后寫道:“這些貧民,并不是懶惰不愿做工,實由社會組織不良,叫他們無路可走。”(18)光舞:《北京貧民的悲慘生活》,《晨報》(北京)1920年1月26日。
無論是李大釗,還是其他調(diào)查者,都特別關(guān)注艱難生活的人群,以此自殺者順理成章地進入了李大釗的視野。通過自己的觀察及利用相關(guān)調(diào)查材料,李大釗接連發(fā)表了一系列關(guān)于自殺問題的討論文章。1913年的《原殺(暗殺與自殺)》首度涉及自殺問題;1915—1919年的《厭世心與自覺心》《北京的“華嚴”》《新自殺季節(jié)》《一個自殺的青年》等文,繼續(xù)對自殺問題有所申論。1919年底、1922年分別寫成的《青年厭世自殺問題》和《論自殺》,則運用調(diào)查材料,更為深入地探討了青年自殺問題。
今人說到自殺問題的研究,很容易想到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出版于19世紀末期的社會學名著《自殺論》,李大釗的《青年厭世自殺問題》和《論自殺》采用了大量《自殺論》的數(shù)據(jù),不過他所參考的并非前者,而是意大利精神分析專家恩里科·莫爾塞利的《自殺論》。
19世紀意大利的精神病學研究居于世界領(lǐng)先地位,莫爾塞利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有學者指出:“熱那亞的莫爾塞利(E.Morselli,1852—1929)是《科學心理學評論》雜志的創(chuàng)辦人,他寫過一本精神病手冊(1885—1894)和一部詳細的人類學通論(1899)。他創(chuàng)建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在這里,他對人的臨床心理特性及瘋?cè)说膫€性做了很有價值的研究。”(19)[意]阿爾圖羅·卡斯蒂廖尼:《醫(yī)學史》(中),程之范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59頁。莫爾塞利的《自殺論》出版于1879年,是涂爾干寫作《自殺論》的重要參考書,其中的調(diào)查材料也是李大釗討論自殺問題的重要數(shù)據(jù)來源。
目前尚不清楚李大釗究竟是如何讀到莫爾塞利的《自殺論》的,推測應(yīng)該是從日文翻譯中獲得,不過可以確信的是,他引證的莫爾塞利書中的數(shù)據(jù)并不是轉(zhuǎn)自涂爾干的《自殺論》。李大釗文中利用莫爾塞利的數(shù)據(jù)證明知識精英自殺率最高,曾提及“自殺最多者為從事科學文學的人,百萬人中有六百十四人,其次就是從事國防的四百零四人,從事教育的三百五十五人,從事行政的三百二十四人,商人二百七十七人,司法官二百十八人,醫(yī)師二百零一人,從事工業(yè)的八十人,從事原料制造的二十五人”(20)《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頁。,而在涂爾干的書中,這些數(shù)據(jù)被作了大幅度簡化:“在意大利,莫塞利可以把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職業(yè)分出來,并發(fā)現(xiàn)從事這些職業(yè)的人中自殺的人數(shù)大大超過所有其他職業(yè)。他估計,在1868—1876年,每百萬從事這些職業(yè)的人中有482.6名自殺者;其次是軍隊,有404.1人。”(21)[法]埃米爾·迪爾凱姆:《自殺論》,馮韻文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6年版,第161頁。從李大釗引用的數(shù)據(jù)遠比涂爾干完整可以證實,涂爾干不大可能是李大釗和莫爾塞利之間的橋梁。
相比后來中國知識界關(guān)于自殺問題的連篇累牘的討論,李大釗的上述文章很難說有什么特別的觀點,給人印象深刻的毋寧說是李大釗在討論中對數(shù)據(jù)的重視——文中除了有從莫爾塞利等西方作者借用的數(shù)據(jù)外,還有來自日本和中國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比如日本警視廳及中國內(nèi)務(wù)部和京師警察廳的統(tǒng)計材料,以調(diào)查材料展開論證而不是單純的邏輯推論,顯示了李大釗的社會學素養(yǎng),引領(lǐng)了當年中國關(guān)于自殺問題討論的風向。關(guān)于自殺問題的討論體現(xiàn)了李大釗作為學者的一面,這使之成為以深厚理論功底結(jié)合現(xiàn)實關(guān)懷的馬克思主義者,并在相當程度上形塑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
二、工人調(diào)查
李大釗是河北樂亭人,這里距中國最早使用機器開采的唐山開灤煤礦只有百里之遙。當年,唐山擁有中國其他地區(qū)不多見的大比例產(chǎn)業(yè)工人,如后來張?zhí)自诠伯a(chǎn)國際匯報時所說:“黨特別重視唐山地區(qū),因為它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工業(yè)中心。這里有:(1)二千五百工人的京奉鐵路修理廠;(2)兩千工人的啟新洋灰公司;(3)一萬四千工人的開灤礦務(wù)總局。我黨在這個地區(qū)正竭力通過開辦工人學校、工人俱樂部以及建立各產(chǎn)業(yè)工會發(fā)起小組的辦法來鞏固自己。我們在這里除了共產(chǎn)主義組織外,還有兩個小組,一個是五金工人小組,另一個是鐵路員工小組。在它們周圍,我們團結(jié)了一批相應(yīng)的工會。”(22)張?zhí)祝骸吨袊墓伯a(chǎn)主義運動》(1921年6月10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頁。
早在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就開始關(guān)注家鄉(xiāng)唐山工人階級的狀況。1919年3月9日,他在《每周評論》發(fā)表《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一文,這可以說是中國相當早的關(guān)于工人生活的調(diào)查文章。該文采用間接調(diào)查方式,通過詢問唐山煤廠來的朋友,了解那里工人的生活狀況。雖然以現(xiàn)代眼光來看,該調(diào)查不能算十分的專業(yè),但是調(diào)查的一些要素已基本具備。李大釗最關(guān)心的是工人的生活,文中寫道:“他們每日工作八小時,工銀才有二角,飲膳還要自備。他們……常常把兩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來作。在這星期中,無晝無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他注意到了唐山煤廠的包工制度,寫道:“資本家對于工人不生直接的關(guān)系,那包工的人對于工人,就算立在資本家的地位。也有許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該令他們作的工,那種情景,更是可憐。”懷著改造社會的心理,李大釗特別關(guān)注工人的組織狀況,發(fā)現(xiàn)擁有八九千人工人的唐山煤廠,“竟沒有一個工人組織的團體”(23)《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436頁。。作為弱勢一方的工人,他們要想把握自己的命運,只有利用數(shù)量上的優(yōu)勢,組織起來才有可能。李大釗此時雖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已經(jīng)憑著自己對社會的了解,初步窺到了這一癥結(jié)。
五四運動后,1919年7月下旬至9月初,李大釗又親身到唐山開展社會調(diào)查。其間,他訪問唐山工業(yè)專門學校,調(diào)查開灤林西礦,以了解工人的勞動和生活狀況。同時,李大釗還指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到工人中去。1920年初,為更加深入地了解工人情況,李大釗安排北京大學的羅章龍、新潮社成員羅家倫等到唐山,在唐山京奉鐵路制造廠、啟新洋灰公司、開灤礦務(wù)局展開勞動狀況調(diào)查,所寫調(diào)查報告發(fā)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6號上,即署名“無我”的《唐山勞動狀況》(一)和署名許元啟的《唐山勞動狀況》(二)(24)許元啟當時為唐山工業(yè)專門學校的學生,參與了羅章龍等組織的相關(guān)調(diào)查。。
兩篇調(diào)查報告詳細記述了唐山三大企業(yè)的情況。從調(diào)查看,三廠工人處境不完全一致。唐山京奉鐵路制造廠技術(shù)含量高一些,工人知識水準較高:“工人大都居唐山鄉(xiāng)間,知識程度比他種工人為高。廠中每年每人有一次來往京奉路三等旅行券,每年有外加一月(依星期計算,一月扣除三日)無工資名為獎勵金。廠中有工課夜課社使工人補習。”(25)許元啟:《唐山勞動狀況》(二),《唐山工運史資料匯輯》第1輯,唐山:唐山市總工會辦公室工運史研究組,1985年版,第16、22頁。正因如此,這里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錯:“常見有每月賺四五十元錢的工人,他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冬天就穿上皮襖,其余就可想而知。小工們賺錢不多,自然是不能闊綽,然尚不至十分狼狽。”(26)無我:《唐山勞動狀況》(一),《唐山工運史資料匯輯》第1輯,唐山:唐山市總工會辦公室工運史研究組,1985年版,第11—12頁。啟新洋灰公司實行按日計薪制,工人做工時間通常為十小時,“廠里全是包活,工人做的快,工價自然賺得多,跟制造廠的辦法相同。其生活狀況,也跟制造廠的工人相仿。惟裝洋灰的小工,因洋灰末一經(jīng)啟動,彌散到空氣里,吸入鼻管喉嚨里,就干的難過;吸進肺里去,若日久天長,大有生命危險”(27)無我:《唐山勞動狀況》(一),《唐山工運史資料匯輯》第1輯,唐山:唐山市總工會辦公室工運史研究組,1985年版,第11—12頁。。勞動量最重、生活最艱難的是開灤煤礦的工人。調(diào)查報告詳細記載了開灤煤礦工人的勞動、生活狀況:他們的勞動時間很長,工資卻非常低,工人“每日分三班,每班工作八小時”,很多礦工一天上兩班,做十六個小時的工作,而“每日所做的工一吊六只夠他一人生活,要贍若家室非做雙工不可。工人的工錢連‘五銅子’想儲蓄都不能”。他們的住屋叫“鳥窩”,“‘鳥窩’里……一盞燈油,睡的地方也沒設(shè)備,只有一只空炕,無數(shù)的工人枕著磚瓦而睡”(28)許元啟:《唐山勞動狀況》(二),《唐山工運史資料匯輯》第1輯,唐山:唐山市總工會辦公室工運史研究組,1985年版,第16、22頁。。
當年的技術(shù)條件及工人本身的無力,導致工人的生產(chǎn)環(huán)境異常惡劣。調(diào)查報告寫道:“我們親自去調(diào)查的是第七層和第八層。大路闊十一尺高十尺,途中昏黑沒燈火及種種設(shè)備,非常泥濘,路旁有水溝,水深過膝。路中設(shè)軌,用騾車運煤,闊只七尺,高只四尺半。走時須俯伏行走。……空氣里夾著煤氣、水汽、硫磺氣和種種重濁的臭氣。氣溫高至攝氏三十八度。”生產(chǎn)安全幾乎無從談起,工人死傷率很高:“每月因傷死于礦內(nèi)者平均四人,多的時候十幾人,幾十人不等(病死者不計)。大半因不通風的悶死和中毒死,傷的人數(shù)比死的多兩倍。”(29)許元啟:《唐山勞動狀況》(二),《唐山工運史資料匯輯》第1輯,唐山:唐山市總工會辦公室工運史研究組,1985年版,第22—23、25頁。
和李大釗的《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一樣,調(diào)查報告也引人注目地提到了工人組織。辛亥革命后,唐山工人一度建立了自己的政黨,可惜在1914年“二次革命”后消亡。五四之后,又有同人聯(lián)合會成立。調(diào)查報告認為:“在救國的題目下,這種組織不是純粹工人的組織,所以不能發(fā)揚工人的精神,更不能專做謀工人幸福事業(yè)。現(xiàn)在也有不少人覺悟到此,想另組勞工團體,他們成功的快慢,就要看工人要求的決心。”(30)許元啟:《唐山勞動狀況》(二),《唐山工運史資料匯輯》第1輯,唐山:唐山市總工會辦公室工運史研究組,1985年版,第22—23、25頁。工人組織問題的反復提出,如果和此時馬克思主義者的建黨準備及走向工人的要求聯(lián)系在一起,可以見出在李大釗指導下,北京年輕的共產(chǎn)主義者們逐步具有了開展工人運動的理論自覺。
由于李大釗等的提倡,20世紀20年代初,關(guān)于工人、工廠的調(diào)查蔚成風氣。1921年4月,李大釗出席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決定“調(diào)查北京之平民學校及平民講演所,并設(shè)法使變?yōu)樯鐣髁x化”(31)《關(guān)謙關(guān)于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備“五一”活動等事項報告》(1921年4月8日),《北京青年運動史料(1919—1927)》,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508頁。。《新青年》雜志設(shè)計了一個社會調(diào)查表,提出展開工農(nóng)調(diào)查的詳細項目。該刊第7卷第6號系“勞動節(jié)紀念號”,登載了12篇中國各地勞動狀況的調(diào)查,涉及南京、唐山、江都、長沙、蕪湖、無錫、北京、上海、天津等11個地區(qū)。《勞動界》等雜志也發(fā)表了大量關(guān)于工人的調(diào)查文字(32)參見熊秋良:《“尋找無產(chǎn)者”:五四知識分子的一項社會調(diào)查》,《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鄧中夏在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創(chuàng)辦的《勞動音》發(fā)刊詞中發(fā)出號召:“我們更希望國內(nèi)的勞動同胞與我們攜手,時常將其所在的工廠制造場和一切生產(chǎn)機關(guān)的內(nèi)容組織,現(xiàn)在辦理情形,所出產(chǎn)的物品概況,工人的數(shù)目種類——如男女老幼,待遇的情形,工錢的制度,做工的時間,工場的規(guī)則等,和工人自己個人的生活情形,感想的意見,對于家庭的關(guān)系等一切情形,隨時詳詳細細的告訴給我們。”(33)《鄧中夏全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9頁。
關(guān)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將視線下移到底層,目的在于改變現(xiàn)狀。1924年,李大釗訪蘇期間,“目睹工人兒童的幸福,娛樂,教育,不禁想起這一班淪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萬多的幼年群眾”,遂寫下《上海的童工問題》一文,表達了對上海童工的關(guān)切。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會的調(diào)查材料說:“上海市分為十區(qū),共得雇傭童工的大小工廠二百七十五個。童工總數(shù)有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人。”這些“童工被傭于家內(nèi)鋪店、小工廠、家庭工業(yè)、洗衣房、并建筑業(yè)及大工廠等。女童工間有淪落而為娼為婢者。……很多的不過六歲的童工,在大工廠里作工。十二小時內(nèi),僅給他們一小時的工夫去吃飯。他們大都是站立著作工。分日夜兩班換班,直到一星期終了的時候,才停一班”。絲廠的童工多是女性:“小女孩子們在那里作些刷繭、去障礙、剖出絲纖的工作,為機工作預(yù)備工夫。此苦工作,須臨于盛著沸水的盤盆前邊,他們的小手,須和沸水相接,以致手受痛傷,顯出粗丑的樣子”。李大釗痛切地希望:“留心社會的青年同志們,看一看你們的小朋友們的生活狀況,是如何的悲慘,如何的痛苦,而設(shè)法以改進之。”(34)《李大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4頁。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無疑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中掌握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先驅(qū),但他關(guān)于工人的社會調(diào)查常常更多訴諸情感。無論社會調(diào)查還是政治革命,都不離開情感的關(guān)懷,這是這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明顯的特點。
三、農(nóng)村與農(nóng)民調(diào)查
李大釗出身農(nóng)村,對中國農(nóng)村問題有著深切的認知。雖然根據(jù)共產(chǎn)主義革命的理念,工人問題更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其對農(nóng)民問題卻也從未忽視。1918年3月,李大釗去清華學校參觀后,盛贊該校學生:“于課余之暇,尚在校外附近鄉(xiāng)村中為各種改良社會之活動,已在附近二三里許之某村設(shè)一職工學校,上午授課,下午工作,以收附近村中之貧兒,聞成績頗著。”(35)《李大釗先生來函》(續(xù)),《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3月20日。次年2、3月間,他撰文呼吁青年人面向農(nóng)村,了解農(nóng)村:“中國農(nóng)村的黑暗,算是達于極點。那些贓官、污吏、惡紳、劣董,專靠差役、土棍,作他們的爪牙,去魚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謀自衛(wèi)的方法,結(jié)互助的團體。”(36)《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439—440頁。他要求青年人“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脫他們的苦痛,應(yīng)該用什么方法”,“大家一齊消滅這痛苦的原因”(37)《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439—440頁。。
隨著中國革命不斷走向深入,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問題的重要性日漸凸顯,革命者越來越多地關(guān)注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問題,共產(chǎn)國際和蘇俄也給予了有益的指導。1920年10月,中國共產(chǎn)黨還在醞釀階段,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致電維經(jīng)斯基(吳廷康)時要求:“必須立即通過電報傳送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問題的材料:第一,哪種土地所有制最有代表性——是大土地占有制還是小土地占有制?第二,怎樣按擁有土地的多少把農(nóng)民分類,例如什么叫大土地所有者或中農(nóng)?第三,農(nóng)村有沒有無產(chǎn)階級,有多少人?第四,因農(nóng)村人口的減少,城市居民增長的幅度有多大?第五,有多少人兼營副業(yè)?第六,人均占地是多少?第七,有多少人租種土地?請?zhí)峁┯嘘P(guān)這個問題的材料。”(38)《阿勃拉姆松和勃隆施泰恩致吳廷康的電報》(1920年10月底),《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頁。可見,面對農(nóng)村人口占據(jù)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問題一開始就已在國內(nèi)外的革命者眼中聚焦。正如鄧中夏1923年所言:“中國不革命則已,欲革命我們不教育,煽動,領(lǐng)導這占人口大多數(shù)之農(nóng)民積極的參加,那有希望?”(39)《鄧中夏全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頁。
秉持著這樣的觀念,農(nóng)村調(diào)查備受中國共產(chǎn)黨人重視。曾受中共北京黨組織指導的賀昌撰文提供了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調(diào)查大綱,包括地理上的大概情勢、農(nóng)民的種類及其生活狀況、生產(chǎn)的種類、農(nóng)村的副產(chǎn)、生產(chǎn)的方法、農(nóng)民的組織、農(nóng)民的教育、農(nóng)村的風俗習慣、普通農(nóng)民生活最低限度的標準、農(nóng)民一般的負擔、災(zāi)荒情形、農(nóng)民破產(chǎn)情形、農(nóng)民的心理和要求、農(nóng)民運動的狀況等(40)《賀昌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8頁。。賀昌的調(diào)查大綱比之上述俄共提出的調(diào)查計劃,明顯更為完整細致,這表明,中共黨內(nèi)的調(diào)查研究方法日趨成熟。
1925年,中共北方區(qū)委開辦了中共第一個區(qū)委黨校。李大釗給學員講授了土地與農(nóng)民問題的課程,訓練農(nóng)民運動骨干。時任中共北京西郊區(qū)委書記的樂天宇回憶道:“在共青團支部時,劉伯莊同志(地委書記)曾向他們傳達過李大釗同志的指示:要求他們支部的團員每天都要找一位農(nóng)民談話,并作談話記錄。支委則每天至少找一位農(nóng)民談話,并且把談話記錄向支部匯報。”(41)《樂天宇同志的回憶》,《文史資料選編》第9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頁。李大釗深知,“在經(jīng)濟落后淪為半殖民的中國,農(nóng)民約占總?cè)丝诎俜种呤陨希谌丝谥姓贾饕奈恢茫r(nóng)業(yè)尚為其國民經(jīng)濟之基礎(chǔ)。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nóng)民是其重要的成分”(42)《李大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就是說,要深入推進中國革命,就不能不去了解農(nóng)民。
1925年冬,李大釗到河南鄭州一帶走訪農(nóng)村,撰成《土地與農(nóng)民》一文。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論述中國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問題的重要文獻之一。該文指出,秦漢以后的土地制度分為兩類:一類欲行公有,一類欲借土地增加稅源,后一類是歷史上的主流。由于政權(quán)以土地為逐利工具,造成豪強兼并、土地不均,不斷發(fā)生的平均地權(quán)運動即成為農(nóng)民與土地關(guān)系一個不絕的旋律。土地是農(nóng)民的命脈,中國革命不能不面對農(nóng)民和土地問題。李大釗強調(diào):“中國今日的土地問題,實遠承累代歷史上農(nóng)民革命運動的軌轍,近循太平、辛亥諸革命進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國現(xiàn)代廣大的工農(nóng)階級依革命的力量以為之完成。”如何完成這個任務(wù)?首要的是真正了解鄉(xiāng)村的現(xiàn)實狀況。李大釗認為,中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以自耕農(nóng)、佃戶及自耕兼佃為最多,“此等小農(nóng)因受外貨侵入軍閥橫行的影響,生活日感苦痛,農(nóng)村雖顯出不安的現(xiàn)象,壯丁相率棄去其田里而流為兵匪,故農(nóng)戶日漸減少,耕田日漸荒蕪”。李大釗使用數(shù)個調(diào)查材料以證明這一趨勢,包括民國七年農(nóng)商部統(tǒng)計全國農(nóng)家戶數(shù)表,民國九年、十年河南、山西、江蘇等六省區(qū)合計農(nóng)田畝數(shù)統(tǒng)計比較表,京兆、直隸、吉林等省區(qū)合計農(nóng)家戶數(shù)耕田多寡累年比較表,等等。
在李大釗看來,要解決農(nóng)民尤其是自耕農(nóng)和佃農(nóng)的破產(chǎn)問題,必須讓農(nóng)民真正擁有土地。他使用蕪湖102個農(nóng)家社會經(jīng)濟調(diào)查及鄭州附近的河南滎陽五村、密縣二村、汲縣一村農(nóng)民生活要項調(diào)查,通過數(shù)據(jù)的分析、比對,證明道:“農(nóng)民之需要土地,需要較大的農(nóng)場,為最迫切,因為農(nóng)具設(shè)備效率增大的結(jié)果,可以增大場主的利益,可以稍舒此級農(nóng)民的痛苦”。因此,國民革命應(yīng)該切實推行土地改革:“國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茍能按耕地農(nóng)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nóng)民,……則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歷史上久久待決的農(nóng)民冋題,當能謀一解決”。解決農(nóng)民問題,除了革命政權(quán)的努力而外,還要有效組織農(nóng)民。李大釗認為:“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權(quán)與節(jié)制資本,惜其所擬的平均地權(quán)辦法,未能及身而見其實行!”看得出來,李大釗對孫中山之后的國民黨能否切實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并不樂觀,前文中的“茍能”一詞,很能代表李大釗內(nèi)心的真實判斷。因此,由中國共產(chǎn)黨來發(fā)動農(nóng)民、組織農(nóng)民,領(lǐng)導農(nóng)民形成自己的土地改革推動力量,就成為李大釗思考的方向:“鄉(xiāng)村中舊有的農(nóng)民團體,多為鄉(xiāng)村資產(chǎn)階級的貴族政治,全為一鄉(xiāng)紳董所操縱,僅為鄉(xiāng)村資產(chǎn)階級所依為保障其階級的利益的工具,……若想提高貧農(nóng)的地位,非由貧農(nóng)、佃農(nóng)及雇工自己組織農(nóng)民協(xié)會不可。只有農(nóng)民自己組織的農(nóng)民協(xié)會才能保障其階級的利益。”更能體現(xiàn)李大釗發(fā)動農(nóng)民參加革命思路的,是他提到的農(nóng)民武裝組織問題:“哥老會、紅槍會等皆為舊時農(nóng)民的自衛(wèi)的組織,革命的青年同志們,應(yīng)該結(jié)合起來,到鄉(xiāng)村去幫助這一般農(nóng)民改善他們的組織,反抗他們所受的壓迫”,“中國的浩大的農(nóng)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43)《李大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107頁。。李大釗對紅槍會這樣的農(nóng)民武裝組織抱有高度期待,可以說,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李大釗是最早注目于此的革命領(lǐng)袖之一。
紅槍會作為農(nóng)民自保組織,成型于20世紀20年代前后。民國初年,政治控制力式微,戰(zhàn)爭頻仍、盜匪蜂起,地方由實力人士領(lǐng)頭,組成村或村落間的防衛(wèi)組織。紅槍會目標在于自保,并無抗御官府的主觀意圖,但由于代表本村利益,一旦壯大,必將抵制官府苛剝,甚至拒絕官府的正常稅賦要求。李大釗對紅槍會的組織力量印象深刻。1925年,當皖西大刀會占領(lǐng)縣城、組織農(nóng)民政府的消息傳出后,中共北方區(qū)委立即派樂天宇以應(yīng)聘安徽第三農(nóng)校教員名義,到蘇家埠、麻埠、金家寨等地訪問,寫成調(diào)查報告轉(zhuǎn)報李大釗(44)《皖西革命史(1919—194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頁。。李大釗多次向中共中央提交關(guān)于紅槍會的報告。1926年7月,中共四屆三次中央執(zhí)委擴大會議召開,在李大釗等的堅持下,會議通過了《對于紅槍會運動議決案》,強調(diào):“紅槍會是軍閥政治下的產(chǎn)物,是一般中小農(nóng)民不堪貪官污吏之搜括,苛捐苛稅之剝削,軍閥戰(zhàn)爭之破壞,土匪潰兵之騷擾,以及受帝國主義經(jīng)濟侵略之破產(chǎn),土豪劣紳之魚肉,才發(fā)生這種農(nóng)民原始自衛(wèi)的組織。……應(yīng)注意使農(nóng)會成為整個的農(nóng)民組織,紅槍會成為農(nóng)民武裝組織。”(4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頁。8月,李大釗又依據(jù)對北方紅槍會的調(diào)查和分析,寫成《魯豫陜等省的紅槍會》一文,繼續(xù)闡發(fā)改造紅槍會為農(nóng)民武裝的設(shè)想,即“變舊式的紅槍會而為堂堂正正的現(xiàn)代的武裝農(nóng)民自衛(wèi)團,變舊式的鄉(xiāng)村的貴族的青苗會而為新式的鄉(xiāng)村的民主的農(nóng)民協(xié)會”,以“達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稅,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紳土豪的目的”(46)《李大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頁。。通過武裝的農(nóng)民建立農(nóng)民自己的武裝,是李大釗經(jīng)由調(diào)查得出的結(jié)論,盡管文中或有高估紅槍會組織之嫌,也未能指出“沒有革命政黨和軍隊的指導幫助”,像紅槍會這樣的農(nóng)民武裝很可能“化為土匪、教匪,或者受軍閥土豪所收買利用,反而變成壓迫農(nóng)民的武裝勢力”(4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但他建立農(nóng)民武裝的呼吁,對此后中國共產(chǎn)黨人到農(nóng)村開展武裝斗爭,還是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實際上,在后來的革命實踐中,李大釗已在努力探索組織和領(lǐng)導農(nóng)民武裝的途徑。1927年3月,經(jīng)由中共北方區(qū)委聯(lián)絡(luò),河南召開各地紅槍會代表集會。“各代表在會議席上之主張甚為熱烈,表示愿受派遣在各地方組織勞工中央部(機關(guān))聯(lián)合,并堅固各地方紅槍會之組織,然后創(chuàng)建聯(lián)合機關(guān)”。雖然該次會議“實際上所代表之地方甚少,不能有良好之活動”(48)《關(guān)于河南組織紅槍會聯(lián)合行動及黨員服務(wù)情形工作地點等項之報告》(192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區(qū)委時期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頁。,但會上呈現(xiàn)的組織化趨勢,尤其是中共黨組織參與其中,已經(jīng)顯示了黨獨立領(lǐng)導農(nóng)民武裝的努力和可能。
李大釗一生注意扎根現(xiàn)實社會,特別強調(diào)個人人格的樹立及社會改造的必要。他在談?wù)摻逃龝r曾批評道:“教育只是偏重知識,而忽視使用知識之人格,知識也不過是作惡的材料。”(49)《記者與李大釗氏之談話》,《教育與人生》第1期(1923年10月15日)。李大釗不希望知識人只是在書齋中求取知識,而主張走進社會、調(diào)查社會、了解社會,找到改造社會的路子,從而既健全個人的人格,又使社會得以進步。他對社會問題的敏銳,對工人、農(nóng)民問題的充分了解和重視,都和注重調(diào)查有著不可分離的關(guān)系,可以說既出自他的社會學訓練,也來自改造社會的愿景,還和健全人格的要求及腳踏實地的思想風格無法分開。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憑著自己的認識和良知接受馬克思主義,投身共產(chǎn)主義運動,他們是極具個性和情懷的一代。具體就李大釗而言,他既是一個學者,又走入社會成為倡導政治和社會改造的革命者,社會調(diào)查隱隱然成為居于其間的兩種氣質(zhì)的結(jié)合點。事實上,在后來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這也被打造成知識者了解革命、投身革命、融入革命的一條有效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