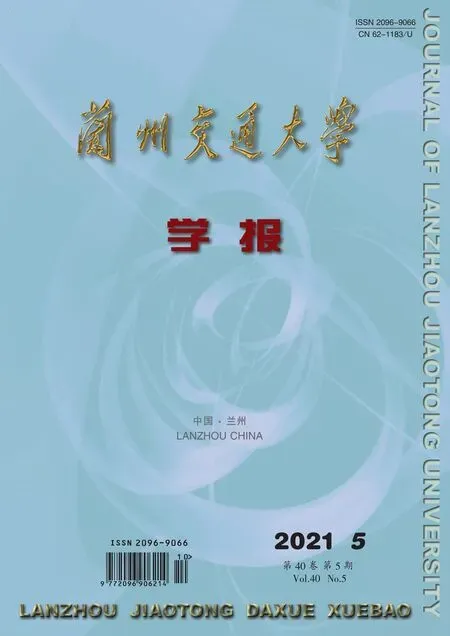超脫的傾情書寫
——論民間審美視野下的《生死場》
榮斯柔,潘黎勇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33)
《生死場》是蕭紅創作初期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作品,完成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由魯迅為之作《序言》,胡風為之作《讀后記》,并且與葉紫的《豐收》及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作為《奴隸叢書》系列而一同出版,問世于上海這個現代化的大都市文壇。
蕭紅是沿著魯迅的創作之路前行的,雖說她堅持站在啟蒙的立場上去揭露民間生活的愚昧、落后和野蠻,然而展示出的卻是透露著原始之氣的生命。所以,馮驥才說:“生命之美是民間審美的第一要素。”民間審美是建立在民間文化這個“源”的基礎之上,具有自發性,這種“自發”直接來自生命本身,具有生命的本質。民間文化有自己獨特的審美體系,包括審美語言、審美方式與審美習慣。民間審美視野作為一種視域角度,從審美視角出發突出表現民間特色。而文學理論中的“現實主義”風格是指文學流派和文藝思潮,與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等相區分。審美視野中的民間特色和文學中的現實性可以等同,二者都是對某一特定場域中特色的強調。所以在這種獨特的民間審美視角下審視蕭紅的《生死場》,生命一方面展現的是鮮活的、激情的、生動的,是充滿著原始之氣的,另一方面更獨特地展現了生命的本真。亦即陳思和所言:“《生死場》寫得很殘酷,都是帶血帶毛的東西,是一個年輕的生命在沖撞、在呼喊。我覺得這樣的東西才真是珍品!她的生命力是在一種壓不住的情況下迸發出來的,就像尼采說的‘血寫的文學’”。
一、生的艱辛與掙扎
人之所以得以存在的意義就在于保持著生命的活力。《生死場》中寫到:在鄉村生活的人們永遠不知道,永遠無法體驗靈魂,他們只是用現實中存在的物質來充實他們。第十三章寫到了二里半,人們因為抗日要殺二里半的羊來進行宣誓,可是二里半卻舍不得,最終找了一只雞來代替這只羊。我們可以想到這只羊對于這些人而言只是一只普通的羊,但對于二里半而言,卻是他的“靈魂伴侶”,是他情感的依托。所以他才找了一只公雞代替山羊,隨后他牽著自己的山羊回家去了。可以說這是一幕對于生存之道非常細膩的描寫,其間充斥著人和動物的特殊感情。在鄉村的民間社會中,勞動人民所看重、所在意的僅僅是自己能否生存下去,這個是居于第一位的。或許我們因此會自然而然的認為這是一種國民落后性的深刻展現,但是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是不是一種樸實真誠的實用主義的獨特展示呢?他們關注的首先是自己的生存空間,聯系到的是自己的實際生存之道。同樣的對于二里半來說,他關心的是自己能否在這個動亂不堪的時代中生存下去,在他的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生存。這種念頭就是民間的生存法則,因為只有人能夠活著,有生命力,才會有力量去實現別的東西。可以說在民間生活著的人們,他們所關心的是如何生存,也可以說他們把自己的生存看的比其他都重要。
在第二章《菜圃》中寫到:發育完全的青年漢子,帶著姑娘,像獵犬帶著捕捉到的獵物似的,走下高粱地去……這是對月英和成業第一次結合的描寫。這些原始而放肆優美的習俗在這里持續著,又在這里一圈又一圈輪回著。在后面作者又寫到:“我知道給男人做老婆是壞事,可是你叔叔,他從河沿把我拉到馬房去,在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在其間他們或許會想到道德的束縛,但是在生存之道的選擇之下,道德似乎已經不再是約束人行為的繩索。他們用最原始的方式訴說著生的艱辛。生之所以為生,就是要為生命不斷注入鮮活的生命力,來維持生命的基本特征。這種場景我們依稀可以在《詩經》中找到相似之處,很早之前的先民們也在用相似的方式做著類似的事。他們用最原始的方式訴說生的本能,這或許已經變成這個古老民族的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在這種充滿原始之氣的生命歷程中,展示的是他們充滿了粗獷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盡情釋放著生命的能量。無論是受古老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還是作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展現出的都是一種自然的美。這種古老而優美傳統一直在輪回著,輪回著生,輪回著死,輪回著獨特的結合。這是一種放肆而狂蕩的原始生命之美,這更是一種生命充沛之美的象征,這是一種在原始力量涌動中的一種動態之美。
第三章《老馬走進屠場》中又寫到:王婆回過頭來,馬走在后面;馬什么也不知道,仍想回家。這是一個充滿感情的場面描寫,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王婆對于他所愛的馬有太多的不舍。因為她和馬已經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可以說她此時此刻對于馬的關系已經超越了普通的人與馬的關系,而是給它賦予了人的些許性格,將其人格化、人物化、感情化。而這種感情是基于馬陪著她走過了無數個春秋,可是她為了能夠生存,不得不忍痛割愛把它賣掉。我們可以看到,在《生死場》中蕭紅把自身童年時代的生活體驗和對大自然特殊生命力的獨特感悟融入到個人創作之中,通過動植物的一些特征來展示人身上類似特征,或是通過它來表現人的生存際遇。這種人與動物間深沉的感情,是來自于生命的本原,是穿透種種文明的遮蔽,拋開貧窮、卑瑣、愚昧的人生不堪。人跟土地、跟生命的原始狀態,是一種原始生命活力勃然噴發,是人不同于動物的豐厚、細膩的情感流淌。這種“愛”更是一種單純而無私的美,是一種源于自然的對一切生命的坦誠相待。在這個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的村子里卻出現了一種淳樸而真誠的愛,一種展示人和動物之間戀戀不舍的真情之美。
我們可以看到,在蕭紅的筆下,農民首先是對于土地、對于動物的熱愛之情。我們可以看到二里半為了找羊變得如同發瘋一樣。我們也能看到王婆牽馬上屠宰場那種依依不舍的沉重復雜之情。這所展現的并非簡單的人與動物的感情,更是農民對于土地的熱愛。因為土地養育了他們,他們把土地作為自己的對于動物的一種特殊的感情,這是一種超越生命本質的一種原始的發自本能的熱情。我們或許可以說,在那個年代,人與動物、人與植物相似性體現出一種很原始的生存狀態,看似無能為力,卻也包含著對人生和命運的反思與抗爭。生活永遠都是這樣,貫穿著一個無法改變的選擇,那就是弱肉強食。盡管有著再多的不舍與愛,那也是徒勞的,在一個基本物質生活都得不到滿足的時代,不可能要人放棄物質上的需要而去追求精神上的滿足。
孔穎達在研究《詩經·七月》曾說:“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人的生存之道高于一切,也許這便是蕭紅寫這篇作品的主旨吧!
二、活的自然與和諧
和諧是一種生活的最自然狀態,這種自然狀態表現在人與人、人與群體間的社會關系之中,而且展現在人與物之間的無限親近上。《生死場》是一個“藏污納垢”的民間世界,展現的卻是一幅富有詩意的田園生活圖景。在小說的開頭,蕭紅便寫到:山羊在大道邊嚙嚼樹根。用一種很自然的狀態開始寫生命的自然之美,有孩子在捉蝴蝶,有太陽普照大地,有高藍的天空,有碧綠的菜田。這可以說是一幅濃縮了的鄉村農家自然生活景致,我們在此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和物都在最自然的狀態下鎮定自若的生活場景。《禮記·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者謂之和。”我國古代的傳統認為人是天地的主宰,人的情感如果都能夠得到恰當的控制,世間的萬事萬物的秩序也能因此得到保證。這反映在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上,呈現出的是一種和諧之美。《論語·八佾》說:“《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孔子看來,文學藝術中表現的感情要受到理性的制約,追求理性與感性的融合,講究中庸、適度、平和的原則,不能過于泛濫,這表達的正是中國傳統美學的中和之美。而蕭紅究其一生是顛沛流離的,在經歷了早年失家、病痛折磨與愛情創傷之后,她開始對人生世相呈現出了一種消極悲觀的認識,幽深孤獨的內心世界使她的文字抒寫整體上呈現出一種蒼涼孤寂的格調,寫人運的不幸與生存的艱辛。但是她也并不總是竭力暴露痛苦,而是以一種平靜淡泊的筆調,舒緩自如的節奏,在文字間呈現出一種“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
《生死場》不僅僅讓我們一飽眼福人與動物的和諧,同時也展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在《生死場》第一節《麥場》和第二節《菜圃》中,就生動展示了農業在鄉村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作者的筆下蔬菜和谷子在鄉村人的生活中占有主導地位,它是生活在下層的勞動者的生命之本。在這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離開了土地與農業,那也就如同離開了賴以生存的法則,因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文中麻面婆把麥粒看得比孩子還重要,金枝的娘把菜棵看得比女兒還重要。第三章《老馬走進屠場》、第五章《羊群》所著力描寫的都是老馬和羊群,它們都是作為鄉民們生活的必須品,而鄉民將其視作命根子一樣看待。蕭紅對于這樣的生活是非常了解的。她在這部小說中沒有將人物作為故事的中心,因為在蕭紅看來,這塊土地上生存的不僅僅只有人類,人物并非占據主導地位,而且人物是做不了主人的。《生死場》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個由自然主宰的自然王國,在蕭紅的小說中,我們看到只有月份,卻沒有年份。如果說年份僅僅是指向人文的,那么月份則是指向自然的。對于那些生活在鄉下的村民而言,他們是無法聽見歷史前進的腳步聲的。他們所看見的只是季節的輪回和轉換,他們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停滯的,十年如一日,甚至千百年也沒有多大變化。我們可以在《生死場》中看到的他們,與《詩經·七月》中表現的農村生活,似乎沒有什么大的區別。
三、死的從容與淡定
《生死場》中,作者描寫了大量的富有哲學色彩的死亡。死亡是一種歸宿,一切事物都是從生開始,然后漸漸走向死亡,死亡的存在說明了生命存在的彌足珍貴。小說中描寫的村里最美姑娘月英的死,就訴說著一種死的恐怖與淡然。月英患了癱病,在十二月的寒冬,夜夜聽見她那歇斯底里的吶喊。三天以后,人們把她葬在了荒山腳下。《罪惡的五月節》一章中寫老王婆的服毒自殺,可怕的死亡之氣緊逼著王婆,人們把棺材準備好并且掘坑的鏟子也不再翻揚,當一切準備就緒時王婆卻大吼了兩聲從嘴角吐出了一些黑血,在人們不知所措地喊著死尸還魂的同時,他的丈夫趙三用自己手中的扁擔刀一般地切在王婆腰間,弄了一身血。王婆被視為死尸般地被最親近的人蹂躪著如蟲蟻,如草芥,即將被拋入另一個冰冷的世界。大家都覺得她必死無疑了,然而就在快要釘棺材蓋的時候,她說了句“我要喝水”,又活過來了。或許讀者可以理解為趙三用扁擔壓王婆的時候把肚子里的毒素清除了,但對于垂死掙扎中的人來說,顯現的是頑強而堅忍的生命力,在生與死的較量中勃然噴發,生命最本質的一股力量顯露出來,震撼著人的心靈。當王婆的女兒馮丫頭因為當胡子的哥哥死了,生活無所著落而回來投奔父母,看到垂死的母親時,“一陣清脆的泰裂的聲浪嘶叫開來。”這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靈魂的吶喊,是一種原始生命本能的母女之情的迸發,這種哭喊帶著一種埋藏于心靈深處的力量穿透了大地與山林。這種哭與女性常有的哀哭是絕然不同的,她展示給人的更多的是一種生命吶喊的力量。
“死人死了!活人算計著怎樣活下去。在這里,冬季的女人們準備夏季的衣裳,男人們考慮明年的耕種”。盡管這里充滿了死亡的氣息,他們依然在死亡的氣息中度過了一年又一年。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人的眼里,死亡似乎變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在他們的眼中生是一種從容的姿態,死又何嘗不是呢?《罪惡的五月節》一章中寫到,這里時刻都充斥著死亡的氣息,這種死亡的氣息讓人覺得可怕,讓人覺得悲涼,更讓人覺得淡定。這正如胡風在《生死場·讀后記》中所說到的一樣:“蟻子似地生活著,糊糊涂涂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種出了糧食,養出了畜類,勤勤苦苦地蠕動在自然的暴君和兩只腳的暴君的威力下面。”在這種獨特的生存環境中,人們世世代代繁衍著,在痛苦的生命面紗之下卻涌動著原始生命的活力。死亡是每個人都必須要去面對的一件事情,自古以來,生存與死亡總是相伴而行的。我們可以看到在作者筆下的鄉村,人和動物們一起忙著生,忙著死;死亡是無可逃避的,但對于死亡的態度展現的卻是對待生命的尊重與敬仰。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到處都彌漫著一種死亡的氣息,雖然說這種氣息有點壓抑,但是這種死亡之氣所展示的卻是一種近似從容的、淡定的、泰然自若的、毫不吝惜的一種狀態。蕭紅筆下這些在鄉間生活的鄉民們更多的是保留了自然的原始特性,而這種自然原始特性更多的表現在鄉民們對待生與死的冷漠與漠視。在他們的眼中,死亡并沒有什么可怕之處,死亡就如同出生一樣,是一種對于大自然的自然回歸。
整部《生死場》似乎給我們所呈現的只有生與死,而且生與死似乎都在一直輪回著,都在循環往復。也許人們大都會覺得死亡是最無意義的,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而且它吞噬掉了人之所以得以生存的根本意義。但是,在鄉間生活的人們始終明白一個道理,人之生必然相伴于死,每個人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便開始步入了走向死亡的旅途,從生到死僅僅只是一個過程而已。所以他們在生的過程中體驗著死亡,沉思著死亡。可見在他們這里“死”的存在并不會使“生”毫無意義,而是更凸顯出了“生”的意義與價值。只有對于“死”有更深入的探索,才會懂得“生”的獨特意義與價值。蕭紅對于人生的理解與探索,更多地集中在她對農民命運以及他們生存方式的深切關注之中。她對于鄉間生存的人們,給予的不是只看到他們的愚昧與落后,而是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與同情,這或許源于她對于鄉間民眾的特殊之情吧!
四、結語
通過對蕭紅作品的民間視野之下審美意蘊的發掘,讓我們得以深入地挖掘出蕭紅作品民間視野之下的審美特質,也讓我們不得不欣羨這位天才女作家感受美與抒寫美的創作才能,指引著我們在理解美與感受美的路途中找尋到藝術的魅力。從作品的內涵角度來說,其作品中積淀的民間視野之下的審美意蘊,是她面對生命的苦難亦或是面對生活的苦難,并沒有沉浸于生活的“苦汁”中而就此沉淪,而是審視、領悟、感受人性中光輝的一面。她的一生雖然遭際坎坷,但她卻始終能以一種審美化的人生態度看待生活。她終其一生追尋著屬于女性的自由天空,始終堅持獨立寫作,為弱者發聲,追求文學超越階級性的美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