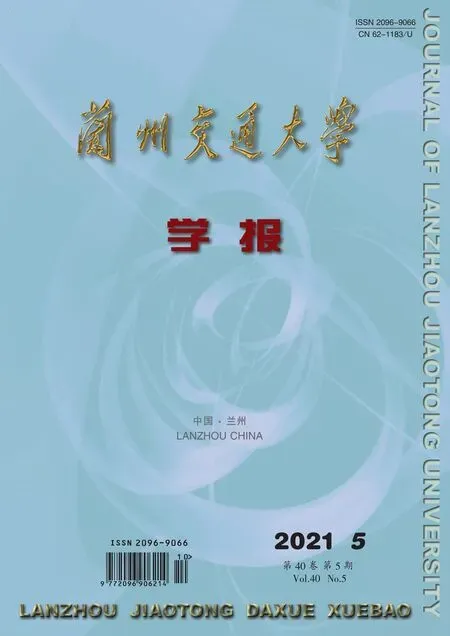抗戰時期的《現代評壇》與“西北詩運”
唐翰存
(蘭州交通大學 文學與國際漢學院,蘭州 730070)
筆者在《抗戰時期“西北詩運”考述》(發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1期)一文中,曾以《甘肅民國日報》和《西北日報》為中心,發掘民國年間“西北詩運”這一抗戰文藝的殊象,盡管論文也提到《現代評壇》,但由于手頭資料的缺乏,沒能對《現代評壇》上的有關文學活動展開論述。后來,筆者在圖書館的西北地方期刊報紙閱覽室,終于查閱到當年的《現代評壇》雜志,得窺其中內容,遂寫此文,算是補遺。
《現代評壇》于1935年9月創刊于北平,是一個綜合性的文藝刊物,抗戰爆發后與《現實生活》合并。因戰亂,1937年10月遷往西安。1938年8月遷往蘭州,由趙西主編,當時被譽為“西北唯一的大型文學刊物”,也是西北地區唯一公開發行的非官辦雜志。筆者看到的《現代評壇》,即是遷往蘭州后的《現代評壇》(戰時半月刊),刊物標注的編輯兼發行者為“蘭州現代評壇社”,社址為“蘭州北門街六六號”,代售處為“蘭州各大書店”,印刷處為“國民印刷局”、“俊華印書館”。可惜的是,現在館藏中只剩第四、五、六卷,每卷20多期,時間從1939年至1941年。其中,第四卷第11期整理發表茅盾在蘭州的演講《抗戰與文藝》,第五卷第20、21期合刊推出“七七抗戰建國三周年紀念特輯”,第六卷第1、2合期推出“通俗文藝專號”,第六卷第12-17合刊推出“五四青年節專號”。
一、“青年詩歌專號”對詩運的首倡與“街頭詩運動”
《現代評壇》第六卷第18-24期合刊發了一則《本刊重要啟事》:“本刊因印刷困難,決定自第七卷第一期起改為月刊,于每月中旬出版發行一次,內容及頁數均稍有增加,敬希讀者注意為荷!”另有一則《本刊改訂定價啟事》:“本刊自第七卷第一期起改出月刊,同時改訂定價如下:(一)全年十冊定價國幣四元;(二)半年五冊定價國幣二元;(三)零售每冊國幣四角。外埠酌加郵費,如蒙函購郵票十足通用。”①而在前一年即1940年,刊物定價為“全年二十四冊一元”、“半年十二冊六角”、“三月六冊三角”,可見在戰時環境里,由于印刷及經費等原因,《現代評壇》跟那時許多刊物一樣,辦刊愈來愈困難,甚至難以為繼了。
盡管如此,這三卷本的《現代評壇》舊雜志里,卻隱藏著“西北詩運”的端倪。此前,筆者閱覽《甘肅民國日報》的縮微膠卷,至1940年10月,“草原”詩歌專欄創刊,馮振乾發表創刊詞《詩運展開在西北吧》,其中特別提到《現代評壇》:“抗戰詩歌不但沒有為炮火所摧毀,并且在各地蓬勃的展開,由集中而分散,由大都市而小城鎮,由后方而戰地,它是在烽火彌漫的各個角落擔負起英勇斗爭的任務。然而慚愧得很,西北的詩運正和西北的文壇一樣失敗,廣大的西北竟沒有一份詩歌刊物,在蘭州除了《現代評壇》曾出了一期詩歌專號之外,其余則一直沉默著,這不能不歸咎于我們詩歌工作者的努力還太不夠,本身的陣容太弱,又沒有□□。”②正是順著這一線索,筆者幾經周折,查詢到《現代評壇》的“詩歌專號”的實物文獻。
《現代評壇》的“詩歌專號”,全稱叫“青年詩歌專號”,正好刊載于第5卷第17、18合期,出版日期是1940年5月20日。
這一期的《現代評壇》,刊頭紅底白字,現出四個考究大氣的美術字,下面“青年詩歌專號”黑底白字,大字豎排,兩邊是“本期目次”。按順序,發表的詩文分別是:趙西的《詩歌專號前言》、穆天的《詩人阿寧沙的故事》、安汭的《由詩歌藝術大眾化說到街頭詩運動》、馮振乾的《對街頭詩的幾點意見》、夏濱的《詩歌朗誦和通俗化》、風吹干的《洞庭湖畔》、唐那的《邊塞詩抄》、韓揚的《鴨綠江上》、禾豐的《論情感的說服》、普庚的《雜談詩歌的寫作和詩人的修養》、伯峰《談談洮岷的“花兒”》、蕭離的《華家嶺上的路工》、建宇的《這是什么年代》(報告詩)、爽頻的《微神》、坦克的《憶》、劍生的《午夜》、蒲之津的《反抗的鐵流(中條山來的故事)》、史成漢的《北中國歌》。
別小覷這期“青年詩歌專號”,它是抗戰以來,西北文藝刊物的第一個“詩歌專號”,由此拉開了“西北詩運”的序幕。
趙西的《詩歌專號前言》,因透露的信息重要,茲全錄如下:
在本刊第五卷里已出過兩個專號,即“青年讀書專號”與“青年生活專號”。這一期的“青年詩歌專號”是本刊今年度的第三個專號了。不過這一次專號的產生,和前兩次情形略有不同。從前出專號,是先決定題目,再向讀者征文然后出版,但這一次的專號,事前并沒有敢作怎樣的計劃,原因是本刊是一種綜合性的刊物,出文藝性質的專號,好像不是分內應辦的事情;其次稿件也恐怕發生問題。然而結果,詩歌專號居然產生出來了,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意外的收獲。本刊被物質的困苦和經濟的貧乏所迫害,不能夠正常的按期出版,在百無辦法中,只好將刊物實行合期,數月來就是這種茍延殘喘的辦法來維持本刊的生命,然而愛護本刊的人,并不因此減少,而投稿者來信鼓勵者,反而日漸增多,我們就從不斷的來稿里,發現了不少關于詩歌論文和優秀的創作,于是決定出這一次專號,以酬答投稿者愛護本刊的熱忱,同時,也是對西北的詩歌運動作一番提倡。
詩歌在國內各地,都是隨著抗戰的形勢而有蓬勃的發展,尤其在桂林昆明等地,詩歌的運動幾乎形成全國詩歌發展的中心。就刊物說,桂林出版有《詩文學》《頂點》,及昆明救亡詩歌會編行的《戰歌》等。專集則有鄒荻帆的《他們將為那些受難的人們去斗爭》,和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重慶方面的詩歌發展,似乎不及華南,然而在全文協的推動之下,詩歌運動也表現著不壞的成績,如《抗戰詩歌》《詩時代》,都是在困難環境里開出的花朵。朗誦詩,街頭詩,在中國另一個地方形成一種普遍而廣大的運動。然而西北,尤其是蘭州,詩歌的運動始終是寂寞無聞。在本市的幾種刊物和報紙副刊上,雖然也有詩歌的刊登,但只是一種點綴或應時的性質,不能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文藝的作品,一登在報紙的副看上便被一般人認為是報屁孔的東西,不值得重視,而詩歌似乎更被編者和讀者所輕看,于是使蘭州的文藝運動遠落于全國的文藝運動之后,而詩歌,更其落后于文藝。這種原因,固然由于文藝及詩歌工作者本身努力的不夠,另一方面也是刊物報紙,不能作一種提倡和鼓勵工作,據個人所知道的就有一部分熱心文藝工作青年,想借報紙地盤出一種文藝刊物,而達不到目的,也有許多優秀的詩歌作品,被編者們以限于篇幅退回或投入字紙簍里,不予刊載,這些事實,直接間接都足以影響到詩歌運動的不能開展。
把詩歌寫成標語式的狂呼亂喊,這確實是目前寫詩的人們容易犯的毛病,但我們絕不應該因此就將詩歌一筆抹殺,而否定了它發展的前途。在西北的青年里,誰能說沒有人寫出堅實而有力的作品呢,如本期里的《詩人阿寧沙的故事》《洞庭湖畔》《邊塞詩抄》《微神》等幾篇創作,誰能說是標語式的沒有情感的狂呼亂喊。西北青年的詩歌作者,一方面是作品無處發表,另一方面又被人責備著拿不出貨色。這種矛盾的事實,不僅造成青年人的苦悶,而且使青年感到絕大的失望;西北的青年并不是完全拿不出貨色,而最大問題是在沒有陳列貨色的地盤。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來注意。
因此,我們希望這個專號,能引起西北各刊物報紙對詩歌的重視,共同來提倡,使西北詩歌,配合全國詩歌運動而蓬勃的發展起來。③
這篇前言,情懷深厚,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十分豐富。概而言之,其一,《現代評壇》借著自由來稿,要提倡西北的詩歌運動;其二,詩歌運動在桂林、昆明、重慶等地已蓬勃發展,形成全國影響,而蘭州仍然“寂寞無聞”,落后于全國文藝運動;其三,究其因,是詩歌被刊物輕看,認為是“報屁孔”的東西,不受重視;其四,“標語式的狂呼亂喊”,是抗戰時期詩歌創作的一個通病,然而西北的青年卻也能拿出貨色,寫出“堅實而有力”的作品;其五,呼吁西北各刊物報紙重視詩歌,共同提倡西北詩歌運動。
趙西主編的這期“青年詩歌專號”,連同他撰寫的這個《前言》,在當時產生不小的影響力和帶動力,時隔半年后,《甘肅民國日報》率先響應,開辟“草原”專欄,由馮振乾主編,開始大張旗鼓地發表詩歌,推進詩歌運動。
本期《現代評壇》在詩論方面的一個話題,是“街頭詩”運動。
安汭在《由詩歌藝術大眾化說到街頭詩運動》中認為,詩是語言的藝術,在中華民族解放斗爭階段的詩,是要用大眾的語言來訴說大眾的生活和情感。大眾的語言,并不是每一句都是詩,而是進步了的大眾語。詩人們應該下一番刻苦的功夫,去從大眾的語言中采取寶貴的成分而加以鍛煉。大眾化的方法,最容易做到的要算街頭詩運動。街頭詩并不是一種詩的類型,而是使詩歌趨向于大眾化的運動方法。“街頭詩,在今日印刷非常困難的時期,為了滿足群眾愛好詩歌的人們(無力購買書籍的),這是如何有價值的事哩。這種運動,并不限于城市地方,我們應該把它開展到各鄉村地方。至少這種運動可以消滅或代表了往昔的街壁琳瑯的那些濫調的標語。”“在文藝新聞上我們看到,田間從山西來信說晉南的街頭詩運動非常普遍的開展推進著。前方這種運動是需要的;而后方應該嘗試著使這種運動普遍的實行。”③文中提到的詩人田間,即是“街頭詩”運動的發起人。從1938年開始,田間在晉察冀邊區從事抗戰文藝宣傳,將“街頭詩”的大眾化、戰斗性風格發揮到極處,創作出《給戰斗者》《假如我們不去打仗》等流傳千家萬戶的作品,“由于田間的推動,街頭詩形成了風靡一時的詩歌運動,與傳單詩、朗誦詩等成為抗戰初期解放區乃至國統區最具有現實性和時代特色的詩歌形式。”④
馮振乾《對街頭詩的幾點意見》一文,則從文藝所具有的教育大眾的性能以及激發大眾“高度的抗戰情緒”出發,認為街頭詩是詩歌大眾化最活潑最好運用最易迎合時機的新形式之一,但街頭詩必須具備它應有的條件,然后才能發揮其最高的性能與影響。(一)內容要力求通俗。街頭詩一定要明確易懂(最忌使用典故、生詞及很抽象的詞句),要口語化,要滲進歌謠的語句的氣氛,而使大眾能看能讀愛讀,還有一點重要的便是“音樂成分的滲入”,“由此我們可以說通俗化,是指我們的作品一定要識字的人能看得懂,即使不識字的人也能聽得懂,喜歡聽,并且大眾要歡喜唱,老是唱,讀給別人聽,唱給別人聽,那么無形中他們便做了街頭詩連環的分派員,我們的街頭詩便像投入深潭的一顆石頭一樣深入擴蕩于大眾群中。”(二)要簡短。街頭詩最忌冗長(我們認為相當短的詩,在大眾看來就成了冗長的了),尤其在初創的現階段,因為拖拖拉拉的一大片,在興趣孱弱、知識低落的大眾看來,劈頭就給他一個“雞刀不能宰牛”的感覺,或者他們看著眼前一片烏鴉,未免有些頭痛,或者根本就不去讀,即使能讀也未見得能領會其內容,“所以我們對街頭詩應力求簡短,不但華詞浮句不要,同時還要額外減縮詩材的長度,要短至不能再短,抓到精華有力的警句,做最有力的表現,倒比起那冗長的吞不下吃不消的東西要好得多。”然而簡短不等于口號,街頭詩應避免死板的口號化,“雖是很短的幾句,應比口號要具體,要豐富,要復雜要有生命,要活潑生動,才能表現其最大的力量。”(三)抓住情感的焦點。就是要用情感的合力線,用真實的內容表現出來,以期發揮高度的教育大眾的意義,要用有血有肉的具體的真實材料,充分的潑辣的戰斗性,以“挑起大眾的同感”。③馮振乾對“街頭詩”的提倡,以及他認為“街頭詩”具備的特點,確實符合戰時文藝在鼓動宣傳方面的需要,也符合文藝大眾化的需要。
二、“青年詩歌專號”作品賞析
除了詩論,這次專號,一共推出10首詩歌作品。
穆天的長篇敘事詩《詩人阿寧沙的故事》,寫阿寧沙投筆從戎,在草原上戰斗、生活、與女戰友玉娜產生戀情,乃至失去唯一的愛伴,用“淚水洗不清的仇恨”,寫他“血涂的詩”。與那些“標語式的狂呼亂喊”的詩歌不同,穆天的這首敘事詩情景交融,自然和生活氣息濃厚,很有感染力。寫詩人的思想轉變,“詩人要用粗壯的音調/符合大眾底腳步/大眾底呼喊”、“他不因‘詩人’/而有言語的傲慢/要像一杯水/溶在溫樸斗士們心間”。寫戰斗生活的過程:“白天的戰爭里/用勇敢打擊敵人/吃著玉蜀小米紅高粱/沖鋒時,踏著腳步/失去溫柔的天真/夜晚別人休憩戰斗的疲倦/伙伴們發出興奮的鼾聲/聽他們夢囈/高呼殺敵/他揣了欣喜的心情/在狹小的茅房/依著暗淡的光/他,執著筆/用興奮在寫血的詩篇”,這樣的描寫,給人的在場感和體驗感很強,顯得真實而有力。蒲之津的《反抗的鐵流(中條山來的故事)》也是表現戰爭題材的作品,將自然與戰爭融為一體,有一定的控訴力量。風吹干的《洞庭湖畔》,先寫洞庭湖寧靜美麗的風光,以及人們祥和的生活,“綠竹掩著茅屋,/門前的菜園緊靠著荷塘;/那白云下/白云山腳有這些村莊;/村莊外就是無垠的湖田,/有戴著斗笠的小伙子/牽起水牛在耕著早晌”,然而,侵略者的炮聲和“汽艇子”來了,“湖水激蕩了,/湖水發出了怒響,/多少兵船呀開向前方,/兵船拽過雄壯的戰歌,/兵船載過去刀槍。”“我們有刀槍,我們有力量,我們要把大湖當一個戰場,當一個戰場!”這種鮮明的對比,令人不由的產生保家衛國的慷慨沖動。韓揚的《鴨綠江上》同樣寫江海,卻已經不是自然的江海,而是一個抗敵的戰場:“八年以前了!/一個長的時間/——從三月到六月,/我們年青的一群,/走上了鴨綠江上。/從長白山腳,/伴著江水,/朝著西南的方向,/盡情的流浪,飄蕩。/不,/我們是為了戰斗,/才跑到了這個戰場。”詩歌中表現出濃重的“淪亡”情緒和悲愴的戰斗決心。建宇的《這是什么年代》,寫新年伊始,一個村莊被侵略者殘害的過程,“這是什么年代/人要受野獸的災害/早上陪著黃牛出去/晚上淌著汗珠回來”,詩中充滿令人咬牙切齒的細節描寫。
到了劍生的《午夜》,那種苦大仇深的描寫少了,詩歌主要表現人的“內情緒”,有一種比較深沉的力量。“午夜里,/人靜了,/悄悄的流著人們給予的血淚,/偷偷的踱著流浪的步子,/祖國的大地上一地角里,/有一個孤獨的殘影!/‘流浪的人生!/是無家園之念了嗎?’/追隨著我的足跡,/是討債者的鐵拳,/亦是創痕血影結晶的鞭子?/深深的知道,/知道創痕的心田上,/都刻印著家鄉淪亡的日子!”這是在午夜,人靜下來,慘徹心扉的一種反思,不僅“家鄉淪亡”,還有“討債者的鐵拳”,雙重的迫害,豈能不“創痕血影”?“這一顆逃亡的心!/滴滴流浪的淚,/一個殘痕的影,/和一筆筆的血債,/是不能淡淡的消失了,/朋友:知道吧?/滿腔的熱血,/周身的斑點,/是在追尋祖國的黎明。”后面幾句,有了鏗鏘的力量,而不是一味絕望,因為過了午夜,還有黎明,是可追尋的黎明,祖國的黎明。
本期“青年詩歌專號”里,最具藝術魅力、最值得欣賞的詩歌,還是史成漢的《北中國歌》和唐那的《邊塞詩抄》。
史成漢是詩人牛漢的原名(其時他還沒有筆名),發表這首詩歌時,牛漢已舉家從山西遷往甘肅,在天水中學上學,當時年僅17歲。《北中國歌》是牛漢漫長詩歌生涯中發表的第一首作品,算他的處女作。然而從這首作品里可以看出牛漢的詩歌創作潛力與才華。“塞北,那遙遠的地方,/像古騎士泛著斗爭的微笑,/兀立在祖國龐大的畫面。/在那里——/有海樣大的沙漠,/有森林般的草莽,/遍野的牧歌云外飛草莽里飄,/聲聲茄音撩人心悸,/駝頸下縈回著徐緩的鐸聲……/還有幕慕神秘的故事——/青塚交響著昭君的長嘆;/群羊里浮動著蘇武孤影。/蘇武須影里流出無盡的悲憤惆悵……/皺面昭君無力的奏著古曲。/大青山像白蛇樣的亮灼灼;/——披著白雪要踱過熱夏,/暖暖山村隱約在遠方,/莜麥地里飄拂著彩花頭巾,/田壟旁卷著炊煙;/‘簞食瓢飲’里泛著愜意的心波。/然二年前她遭受了可憎的命運,/曠野里吼著東來的狂飆,/人們的心,/像秋崗上枯紅的梨葉,/被吹飄的紛紛下落。/斑斑的血染紅了野莽,/那沙海染成了血紅,/黃河湍流迸滾著血球,/墓地面容皺著臨死的悲紋。/但,那新塞北的嬰兒,/在血泊里戰斗里,/成長著,健壯著,/抗戰的烽火映紅了草原漠地;/斗爭的呼嘯像駝頸下的鐸聲,/響遍整個塞地。/大青山旁,黃河畔,/印鐫著勝利的光芒,/在包頭,在五原,/掘下了敵人的墓場,/黃河唱著凱歌,/大青山巔泛著勝利的微笑,/呵!新塞北在血泊里戰斗里,/成長著健壯著。/——作于天水,五、三”。③這首詩,是牛漢人生里的一次“不悔少作”,一次才情的初展。雖然從詩歌取意上來看,并沒有多少“擺落一切,冥心獨造”的東西,仍然是抗戰文學的一般立意模式,但作者的描寫抒發能力,以及語言的表現力,讓人另眼相看。那種詩語的漫卷,深沉,及物性,以及舒張的節奏感,展現了一個少年作者的大器。多年后,牛漢在回憶錄中談起此事,仍滿懷深情:“從甘谷到天水,升入國立五中高中部后,開始向天水的《隴南日報》文藝副刊等文藝報刊投稿,多為散文,筆名為牧童、谷風等。《現代評壇》(蘭州)發了我一首短詩《北中國歌》。我還多次向蘭州的《民國日報》文藝副刊《草原》(沙蕾、陳敬容主編)投稿,刊發了幾首短詩。”⑤
唐那的《邊塞詩抄》,更顯示出某種難得的藝術自覺和成熟的風格。唐那即唐祈,九葉派著名詩人,后長期在甘肅高校工作。發表這首詩時,唐祈年僅20歲,正在西北聯大歷史系上學。除《邊塞詩抄》,唐祈在《現代評壇》多次發詩,包括《我們的七月》、《九行詩二章》、《送征吟》、《逝水草》、《短歌二章》、《冰原的故事》等。
《邊塞詩抄》共二首,其中一首是《河邊——邊塞十四行詩之七》:
河邊吹起了清脆的號角,
集合了許多的牧羊人,
沒有駝鈴和純白的羊群,
符號卻告訴你是一個兵丁。
沙原的草還很嫩綠。
岸邊的蹄印里仍積結著薄冰,
是要拋開這寂寞的歲月了,
用歡喜來聽取入伍的命令。”
羊皮襖上肩一支馬槍,
那根牧鞭已交給自己的女人,
知道這是防備的時候了,
否則,黑色的強盜會闖過來。
河上都吹響亮亮的號角,
牧羊人的隊伍走過了山坡……③
唐祈在西北聯大學習期間,作為校園詩人群的一員,耳濡目染,深受歐洲文學的影響。他用這種詩體寫中國之詩、抗戰之詩,顯得自然精到,很是從容。詩的意境開闊遼遠,空間感很大,同時又很具象,有可感的細節。抒情含蓄,給人回味的余地。語言的控制力極好,不羅嗦不重綴,簡練而有力。
另一首《蒙海——邊塞十四行詩之八》,如下:
蒙海,一個蒙古女人,
四十歲了,還像少女的年青。
她說一串難懂的言語,
告訴我來自遼遠的沙布尼林。
她穿著舊日的馬靴和羊皮衣,
頭套上的珠子夸著貴族的富麗,
她唱一支牧羊女的謠曲:
說是成吉思汗英雄的后裔。
如今,她走得過遠了,像白云
卻掛住了以往的回憶。
她愛那沙漠的金色的土地呢;
時刻想回到沙上的帳幕里。
蒙海是個被迫的漂泊者,
蒙海的影子是悲哀的。③
這首《蒙海》,后來成為唐祈的代表作。同樣的意境遼遠,同樣的具象可感,同樣好的語言控制力。抗戰題材的詩歌寫到這個程度,足以證明“沒有感情的標語式的狂呼亂喊”,只是當時的一部分現象,優秀的青年詩人還是能夠拿出陳列的“貨色”,創造雋永含蓄之美。
三、“五四青年節專號”與“西北詩歌選輯”
《現代評壇》在推出專號之余,也發不少詩歌,如第4卷發表離浮的《時代青年曲》、喬之的《送別音弟》、禾子的《我們是游擊隊》、更狄的《警報》,還有唐那的《我們的七月》《九行詩二章》,第5卷發表安汭《流亡小唱》《音訊》《劫》《血淚交織著的遺音》《夏日詩篇》、穆天的《新詩二章》《用溢滿的聲音》、張天授的《敵機去后》、唐那的《送征吟》《逝水草》、易寒的《你問我何處去》,第6卷發表陳敬容的《寄玲》、沙蕾的《石像的笑》、唐那《冰原的故事》、穆天的《路工》、馮振乾的《黃馬的綠孩子》《塞上初冬》、谷滹的《禾場》、青萍的《祁連峰》等。這些詩歌因人而異,水準不一,但總歸其中有好詩,甚至有十分優秀的作品。
《現代評壇》第6卷第12-17合刊,推出“五四青年節專號”。
刊物在《編輯后記》中說:“本期的難產,真正‘難于上青天’。征集稿件,倒還好辦,只有印刷,編者不惜流汗吵嘴,碰釘子,跑了好幾家,也就是把蘭州市的機關要跑遍了,在無法之中,仍然找到國民印刷局,到今日才出版了。”可見當時印刷的困難,所以從第7卷第1期開始,刊物由半月刊改為月刊了。在時局如此艱難的狀況下,編輯辦刊仍然毫不含糊,因此,“這一期算然是幾期合刊,但在內容上,我們覺得相當滿意。”⑥本期推介的文章,主要是短評《在青年節致西北青年》、張聿飛的《五四運動的偉大啟示——為五四紀念二十三周年作》、李安宅的《給青年一面鏡子》(本刊特稿)等。
《現代評壇》以編輯部的名義發《在青年節致敬西北青年》一文,其中滿含熱情地說:“于此將近四年的偉大抗戰中,不用說,大西北的青年群眾是進步了。這成千成萬的西北青年,在態度上,在言語上,在文字表現上,雖然不像全國幾個大都市的青年那樣活潑,那樣靈巧,那樣質量都豐富的表現,然而在他們和她們的內心里,卻時刻都在鼓勵著,都在民族國家的本位上下工夫。”⑥編輯部呼吁社會人士一致的贊助青年,同時也對西北青年提出幾點意見:第一,大西北的青年要與進步的力量團結,和現代社會集體生存的原則相適應,不要孤獨的行進。第二,大西北的青年要擴大學習范圍,吸收現代智識,和抗建工作相配合,不要專門埋首于故紙堆中,或者尋章摘句的上面。第三,大西北的青年要認定應走的路線,堅決信仰,統一行動,不要亂抓亂碰,徒耗心身。第四,大西北的青年要勇敢的積極的工作和學習,開拓地接受科學智識,蔚成大器,不要妄自菲薄,態度局促。最后說:“以上四點,是我們對大西北青年群眾知心的共勉,共同的目標。因為我們曉得無論就世界大勢或中國大勢說,是時候了,大西北的青年群眾們起來。”
“作為本刊對讀者的一個小小貢獻”,本期“特選”了五首詩。從內容上來看,這五首詩像是對青年節專號的一個配合,因為它們正是“大西北青年要與進步的力量團結,和社會集體生存的原則相適應,不要孤獨的行進”的一種體現,也是“和抗建工作相配合”的一個體現。
常波的《洮萊河——塞上草之九》,1940年元月寫于酒泉政校,作品透出一種剛健的西部美學:“草原上,/我將躍馬歸去的時候,/塞風飄送著鈴鐸的聲響。/我望著那些送別的弟弟妹妹和姊姊們,/也望著西方的天壁上,/抹過斜陽。/我沒有閑情投給友人以溫慰,/但愿我鋼強的歌喉響!/譜一支凄切的歌子,/馬蹄在彈奏著石子的清響,/我頰上是汗?是淚?/潛潛地流下胸膛。”寫朔方將士的躍馬別離,“迎接祖國勝利的消息”,卻也兒女情長,回味起塞外江南的生活,洮萊河因此承載了自然之思。紅薇的《我歌唱烏拉特部》,詩末標記1941年3月寫于蘭垣,歌頌綏西一個蒙古部落,成吉思汗的英雄后裔,“我歌唱戰斗的烏拉特部,/我贊揚英勇的札薩克戰士,/烏拉特部是我們的土地,/烏拉特部是我們祖先的家鄉。”在1938年冬季,雪原上的烏拉特部,又是怎樣“陷在敵人的馬蹄”,進行了怎樣的浴血抗爭。安汭的《伐木篇》,寫于古成紀,作者對于“被伐者”和“伐者”,抱有雙重的同情,“風/刷掠過林梢/它們/為砍滅了的同伴/詠出一支/不知名的祈禱的歌”、“整天/汗水滌洗著你/深紅的面孔/……你甚至/把它也砍倒了/那生長在深澗邊的/從童年時份起/伴同你年歲的/常綠的鐵羅漢樹/于是冷血的‘超人’們/說你是殘酷的(然而生活呢)”。石夫的《啊!他們來自遠方》,作于蘭州,是一首為西北的戰士聲訴的作品,當“他們”抗戰勝利歸來,“渾身的戎裝,/變成破爛,精光,/大時代的行列里,/敵人使得他們這樣:/不久的以前,/昏暗的燈光下,/——那顆殺敵的面孔,/忽然出現在后方的都市上;/一副副的風霜容貌,/都成了消瘦的模樣。/是的,/他們來自遙遠的西北方。”在陌生化的都市,衣衫的襤褸,“丘八生活”帶來的不適應,觀眾的白眼,讓英雄們的流血付出蒙上一層悲哀,作者聲訴的正是這種悲哀,表達的是內心的不平。谷風(牛漢)的《西中國的長劍》,作于天水,是對回民抗戰精神的謳歌,“他們/活在西中國的回民/多少年代/希望像纏頭的彩巾/隨著死亡葬沒在沙漠/在寒瘦的地帶/燃起疲憊的生命之星火”、“然而/西中國的長劍/那上帝的睽亮的眼眸/永遠踒藏在戰斗的血流星/不會銹爛/或遣沒在沉寂的沙漠/他們不會忘記/他們是愛武的民族”,抗戰是全民族的,回蒙藏漢都有“血流星”,也都有長劍的事跡。
總之,五位青年詩人在西北本土,寫出了西北抗建的詩篇,這大概也是《現代評壇》從詩歌來稿中,選編這一期“西北詩歌選輯”的一個緣由。
注釋:
① 《現代評壇》,第六卷第18-24期合刊.
② 《甘肅民國日報》,1940年10月15日,第4版,“生路”副刊.
③ 《現代評壇》第5卷第17、18合期.
④ 洪子誠主編《百年中國新詩史略——<中國新詩總系>導言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124-125頁.
⑤ 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7月第1版,第56頁.
⑥ 《現代評壇》,第6卷第12-17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