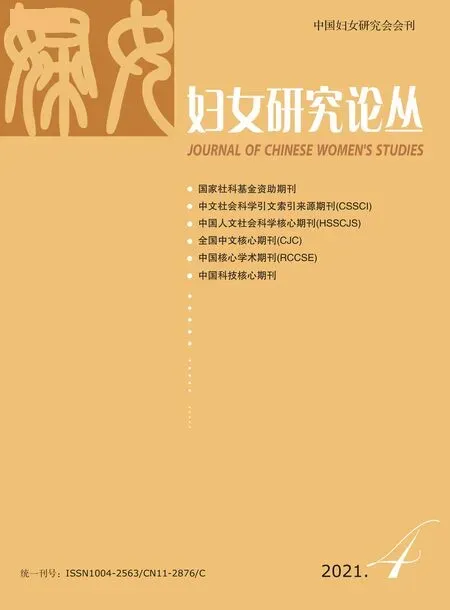性別、民族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五朵金花》中的旅途敘事與公路形態
張 泠
(紐約州立大學珀契斯分校 電影與媒體研究系,美國 紐約 10577)
電影《五朵金花》(王家乙,1959)呈現了某種關于尋找的旅途經驗,在當時的中國與海外都廣受歡迎。它曾在46個國家放映,對中國電影史與大眾文化記憶影響深遠(1)《五朵金花》在1960年于開羅舉行的第二屆亞非電影節上獲得最佳電影“銀鷹獎”(王家乙)與“最佳女演員獎”(楊麗坤)。見李奕明:《十七年少數民族電影的文化視點與主題》,《電影創作》1997年第1期,第69頁。。影片中,白族男青年阿鵬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蒼山公社尋找他心愛的金花——阿鵬與金花在前一年的“三月街”節相遇相愛,約定今年再見。金花為了考驗阿鵬的誠心,并未留下具體地址,而“金花”又是白族女孩常用的名字,于是阿鵬一路上遇見了幾位同名卻并非他意中人的金花,她們都是各行各業的模范,有積肥能手、畜牧員、煉鐵工人和拖拉機手。在經歷誤會、錯過、延遲與失望之后,阿鵬終于見到了“真正”的金花——蒼山公社的副社長(2)這種男主人公在去見愛人/對象的路上因不斷幫助別人而延遲約會、但因他的美德而引向美好結局的敘事,也出現在比《五朵金花》早一年上映的喜劇電影《今天我休息》中。。他們在初會的蝴蝶泉邊再次對歌,在群眾的圍擁祝福中,影片結束。《五朵金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獻禮片,贊頌社會主義建設、農業集體化、民族團結及婦女通過參加生產勞動而獲得解放。
若以“電影類型”的框架來討論《五朵金花》,它通常被視為有少數民族文化色彩的喜劇與風光音樂片,即“成功的歌舞喜劇,以描繪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面貌和采用豐富多彩的民歌和舞蹈而受到觀眾熱烈的歡迎”[1](P 25)。20世紀60年代的相關討論將喜劇電影分為兩大類,即諷刺性(暴露性)喜劇和歌頌性喜劇。《五朵金花》與《今天我休息》(魯韌,1958)常被視為歌頌性喜劇的代表作、凝結著社會主義喜劇因素的新樣式。在當時的評論者看來,《五朵金花》被列為歌頌性喜劇主要由于其“更多運用了幽默、詼諧、風趣,恰當地運用了誤會巧合等手法,別具一格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豐富美好的生活面貌,獨特地處理了喜劇矛盾”[2](P 13)。影片生動展現了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載歌載舞的日常生活畫面,也呈現了云南的明山秀水以及勞動于其間的社會主義新人。
呈現出某些“公路敘事”特征的《五朵金花》公映于美國作家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在路上》(1957)出版兩年后,這當然只是冷戰世界兩端歷史的巧合。《在路上》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文化標志,也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公路電影與亞文化運動的先聲。盡管這種并置看起來有些荒誕,但我認為《五朵金花》可被作為“社會主義公路電影”來分析研究。正如美國學者尼爾·阿切爾(Neil Archer)所言,我們通常“后見之明”地辨析某些影片的“公路電影”特征,而這些特征對當時的觀眾來說并非最重要的因素[3](P 5)。因此,我將《五朵金花》作為“社會主義公路電影”,置于全球冷戰背景下,探究與挑戰英文學界中電影與媒體研究領域界定的以歐美為中心的“公路電影”主題與風格界限的可能性(3)關于“公路電影”的英文著述,見Timothy Corrigan,A Cinema without Walls:Movies and Culture after Vietnam,New Brunswick,New Yor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Cohan,S.and Ina Rae Hark(eds.),The Road Movie Book,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David Laderman,Driving Visions:Exploring the Road Movi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Devin Orgeron,“Revising the Postmodern American Road Movie:David Lynch’s The Straight Story”,Journal and Film and Video,2002,54(4),PP.31-46;Katie Mills,The Road Story and the Rebel: Moving through Film,Fiction,and Televisi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6;Mazierska,E.and Laura Rascaroli(eds.),Crossing New Europe:Postmodern Travel and the European Road Movie,London and New York:Wallflower Press,2006。。如果說美國公路文學與電影是一種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現代現象,是個人流動與自由及反社會主流的縮影,那么《五朵金花》則暗示了一種社會主義現代性——囊括民族團結、性別平等、農業集體化與社會建設,以及文藝的大眾化實踐——位于社會的主流。
實際上,當代“公路電影”研究已經超越美國中心的思路,有更多研究關注其他地區如拉丁美洲與歐洲的公路電影,介入社會、文化與政治議題,如后殖民創傷、身份探尋與跨國遷移等(4)相關英文研究見Michael Gott and Thibaut Schilt,eds.,Open Roads,Closed Borders:The Contemporary French-Language Road Movie,Intellect,2013;Veronica Garibotto and Jorge Peérez,eds.,The Latin American Road Movie,Palgrave Macmillan,2016;Nadia Lie,The Latin American(Counter-)Road Movie and Ambivalent Modernity,Pickle Parnters Publishing,2017;José Duarte and Timothy Corrigan,eds.,The Global Road Movie:Alternative Journeys around the World,Intellect,2018。。建構20世紀50年代中國電影《五朵金花》與“公路電影”分析框架的對話,不僅能夠為社會主義文化生產與交流提供一種新的視角,而且將復雜化“公路電影”類型的地理政治學與歷史維度。此外,該框架有助于提出一些重要的觀念性問題:《五朵金花》中深具社會主義意味的性別與民族呈現如何不同于其他“典型”的西式公路電影?影片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如何與其主題和風格互動從而創造出一種非常特殊然而極具表現力的公路電影形態?自然、勞動與音樂如何在影片中被編織進與公路敘事相關的社會主義現代性?
典型的歐美公路電影范例如1965年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的《狂人皮埃羅》與1969年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的《逍遙騎士》的出現,基于歐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公路基礎設施的修建、私人汽車的逐漸流行及公路旅行作為中產階級(尤其年輕白人男性)游弋于主流社會空間邊緣的象征。一方面,可以說是個人主義關于“自由”與自我發現的表達;另一方面,也暗示著資本主義在特定階段對人心理造成的危機。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五朵金花》中,阿鵬與兩位來自長春電影制片廠的繪畫與音樂工作者輾轉于蒼山洱海間,前者尋找金花與后二者民間“采風”(收集少數民族圖案與民歌)交織,構成旅行的敘事根由與動力。但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西南地區由于地勢險峻、資源不足,基礎設施仍在修建之中。影片中沒有現代交通設施如高速公路,或交通工具如汽車與摩托車,影片中的旅行都是通過前工業形態的交通方式進行,如搭乘人工劃的小船、坐馬車、騎馬、步行等。除了縱馬飛馳的時刻,這些交通工具的遲緩速度一方面構成徐緩橫搖鏡頭中的田園詩意,另一方面暗示出社會主義工農業建設的緊迫性,與影片背景中主張加速工農業建設的“大躍進”構成復雜的張力。
相對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公路電影中盛行的男性危機、逃避型幻想、反叛的欲望與對速度的迷戀,《五朵金花》強調堅強開朗的社會主義新女性如何參與勞動及投身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性別敘事與多數歐美公路電影有著顯著不同:前者折射出保守的消費主義的男權中心體系(5)也有學者探討過一些公路電影敘事中的女權主義因素與潛能,如法國女導演阿涅斯·瓦爾達(Agnes Varda,1928-2019)的《流浪女》(1985)與《拾穗者》(2000)。見“From Flanerie to Glanerie:The Possibilities of a ‘Feminine Road Movie’”,in Neil Archer,The French Road Movie:Space,Mobility,Identity,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3。,而后者致力于打破這種商業電影模式與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呈現出更具性別、民族、階級平等性的樂觀愿景。如在西式旅行/公路敘事(甚至從古希臘史詩《奧德賽》始)框架中,通常男性出門旅行而女性在家中等待;當前者不斷探索新的時空彰顯其主體性時,后者則被動處于靜態時空。《五朵金花》中,盡管實施旅行與尋找的是三位男性人物,但并非意味著女性處于靜止被動狀態,如前所述,除了副社長金花忙于處理公社事務如水庫建設、煉鐵狀況、社員結婚、“三月街”貨物運輸甚至社員工作與感情矛盾等外,其他四位金花都是各自領域的勞動模范,通過積極參與公共領域的生產勞動、社會建設體現出她們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自主性、能動性和領導力。
在公路電影中,公路通常也作為隱喻出現:進步、向前的線性邏輯。在很多美國公路電影中,一方面,公路可能暗示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與冷戰時期的焦慮與恐懼,也給這些影片帶來“一種獨特的存在主義氣質”(6)見Devin Orgeron,Road Movies:From Muybridge and Melies to Lynch and Kiarostami,New York:Palgrave,2008,PP.10-30;Timothy Corrigan,A Cinema without Walls:Movies and Culture after Vietnam,New Brunswick,New Yor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P.144。;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美國高速公路的發展與延伸、公路電影中驅車飛馳成為視覺與感官奇觀,也強化了一種美國國族身份[4](PP 39-41)。如果說多數美國公路電影中的時間維度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懸置”,在《五朵金花》中則是可期的未來,而這個未來根植于當時充滿干勁與樂觀色彩的社會環境。探究《五朵金花》中性別與民族的主題如何被編織進公路敘事,會豐富我們對于公路電影的理解,并揭示位于電影核心的、隱喻性的“社會主義道路”輪廓:在勞動人民的推動下,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駛向一個明朗的社會主義未來。《五朵金花》中這種“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隱喻,也可參照1959年1月1日《云南日報》社論中所言:“經過一年的艱苦奮戰,我們已經開始改變我們國家農業生產的面貌,已經找到一條發展農業生產的高速道路。”[5](P 71)
《五朵金花》中的尋人與采風之旅,宣揚和鞏固了一種多民族的無產階級國族身份,這一點與典型公路電影中文化身份鑄造的形態彼此映照但截然不同。這部電影結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風格,技巧上突出流暢的攝影機運動以及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尚顯新潮的彩色攝影,并雜糅音樂片、喜劇與公路敘事的樣態,這些都使其成為一種社會主義的公路經驗——樂觀主義的旅途,穿行于壯美的山水、民間文化與社會主義公民之間。本文分為三個部分,將在三個層面展開討論:首先,《五朵金花》所構建的多民族影像與社會主義公路敘事如何呼應了當時的民族政策及面向少數民族地區的公路運輸等社會主義基礎設施建設;其次,《五朵金花》中通過“公路敘事”結構統攝、民歌串起的旅途如何在呈現人與自然、勞動的關系中凸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最后,《五朵金花》這部在不同維度顛覆傳統西式“公路片”的社會主義公路/路途電影如何不僅在民族關系而且在性別結構中體現出基于民族、性別、階級平等與解放的社會主義現代性及隱喻性的樂觀的“社會主義道路”。
一、多民族影像與社會主義公路敘事
極具觀賞性甚至輕松愉快的《五朵金花》在1959年被規劃、創作出來有其特別的背景。那一年,中國的電影工作者拍攝了約十八部電影作為建國十周年“獻禮片”(7)包括湯曉丹的《鋼鐵世家》(1959)與沈浮的《萬紫千紅總是春》(1959)等。。周恩來總理認為這些電影在宣傳社會主義政策與文化方面有教育意義,但對當時電影界缺少優美動人、寓教于樂影片的狀況很不滿意。周恩來向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1900-1995)表達了意見,建議拍攝一部關于云南少數民族生活的載歌載舞、基調歡快的喜劇。夏衍將任務交給了作家趙季康(1931-)。趙季康在云南居住了十年,熟悉少數民族生活,也有類似創作經驗(8)接受這個任務之前,趙季康與王公浦擔任背景為西南邊陲的反特片《兩個巡邏兵》(方徨,1958)的編劇,片中涉及漢族與傣族人民的互動。《五朵金花》后,趙季康與王公浦合作編劇了關于傣族女性的電影《摩雅傣》(徐韜,1961)。。據另一位編劇王公浦回憶,夏衍曾于1959年1月造訪大理,對白族人民的生活與文化非常感興趣,決定將白族人作為電影的主要角色[6](PP 23-27)。因此,《五朵金花》可以說是政治任務、機構運作與地方創作彼此協調的結果。
以社會主義建設中民族多元與團結為主旨,《五朵金花》的制作無疑也有國際想象存在。夏衍指定長春電影制片廠的王家乙(1919-1988)擔任此片導演。王家乙曾在法國短暫學過電影,并與法國導演羅杰·比果(Roger Pigaut,1919-1989)合導了中法合拍片《風箏》(1958)(9)羅杰·比果,法國演員、導演,曾與荷蘭紀錄片導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拍攝旅行紀錄片,如《瓦爾帕萊索》(1964)與《海岸之風》(1965)。。《風箏》也是關于“旅行”的影片:兩個巴黎小朋友乘“魔床”飛到北京尋找一位寄送了“孫悟空”風箏去巴黎的中國男孩。影片贊揚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兒童間的國際主義友誼。《風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部合拍劇情片,也是中國第一部彩色兒童電影,曾在一些歐美國家上映,包括法國、美國和英國。在冷戰時期中國基本與美國、西歐等國家官方交流隔絕的情形下,《風箏》成為一個重要媒介,呈現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就與人民的日常生活。《五朵金花》也預期要在資本主義國家放映,但那些國家對社會主義訊息與文化傳播管控嚴苛,因此影片中并未直接出現政治口號標語贊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是“寓黨于人物形象之中”(10)王家乙寫道:“影片(《五朵金花》)在印度放映,尼赫魯(1889-1964)首相看了之后就說:‘這影片是說中國的三面紅旗好的!’(三面紅旗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他全看明白了。”王家乙:《王家乙導演談影片〈五朵金花〉創作》,《電影文學》2010年第1期,第146頁。。這一點與王家乙拍攝時目標觀眾不僅在中國相關,也延續了他創作“旅途電影”的興趣。王家乙也因為拍攝《風箏》的經驗,對電影彩色技術有一定心得,而彩色電影當時在中國能夠吸引大批觀眾(1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部彩色片為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桑弧、黃沙,1954),在當時廣受歡迎。。得益于拍攝《五朵金花》積累的經驗,王家乙后來拍攝了更多少數民族題材電影(12)王家乙此后拍攝了四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包括關于朝鮮族女性革命者的《金玉姬》(1959)、關于彝族人民的《達吉和她的父親》(1961)、關于景頗族婦女的《景頗姑娘》(1965),以及關于傣族人民的《相約在鳳尾竹下》(1984)。。
《五朵金花》中的社會主義公路敘事暗示了一個面向未來的多民族國家建設的樂觀圖景。這部影片也可被視為1949年以后拍攝的數百部“少數民族題材”劇情電影類型與主題的先行者。1949年以前關于少數民族人民的劇情片較為少見,其中之一是《瑤山艷史》(楊小仲,1933),被左翼知識分子(包括魯迅)批評為“低俗”及漢族沙文主義。應云衛的《塞上風云》(1940)在抗戰背景下鼓舞漢族與蒙古族人民團結抗擊日本侵略。柳城指出,1949-1989年,中國拍攝了130部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約占總數(約1800部)的7%,涉及23個少數民族。1949-1966年,拍攝了47部少數民族題材劇情長片,涉及18個少數民族的生活(13)余紀:《從“雙百方針”到“新僑會議”——論新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黃金時期》,《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第104頁。見柳城:《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漫評》,《電影通訊》1989年第8期,第7頁。。這些影片的主要角色大都是少數民族中具有無產階級美德——勤勞、勇敢、誠懇、智慧、無私、樂于助人——的人物(14)有些海外批評者認為,在這些影片中中國共產黨與漢族導演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少數民族民眾,將前者描述為后者的救星,這種看法多有不確,因為這其實是基于階級的敘事來合法化革命目標與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時期文藝作品對漢族女性受害者的描述也是采用類似方式,如《白毛女》(王濱、水華,1950)與《紅色娘子軍》(謝晉,1961)。。《五朵金花》中的主要少數民族角色如金花們與阿鵬也是這些進步品德的化身,他們是新型社會主義社會中理想化的新公民。這些影片的敘事通常講述漢族與少數民族人民共同經歷的歷史:階級壓迫與剝削帶來的苦難與激發的反抗,外國勢力侵略與殖民。因此,這些影片呈現的是超越民族差別與民族間等級制度的新型民族關系:以被壓迫大眾的階級認同與解放的意義代替民族差別與等級。
這種具有包容性的多民族文化作品背后是中國政府推行的少數民族政策。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六章“民族政策”中第五十條規定:“中國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7](PP 1-2)民族政策支持各民族權利平等及鼓勵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如上文第五十三條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應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7](P 3)在“十七年”(1949-1966)期間,少數民族人物及文化形象在文學、繪畫、電影、音樂、舞蹈及其他視聽與表演藝術中都呈現出欣欣向榮之勢(15)各少數民族自治區與地方也建立起各種少數民族表演團體,延續本民族文化傳統。在《五朵金花》中扮演副社長金花的楊麗坤是一個來自當地歌舞團的彝族演員。關于這方面的英文研究見Chen,J.,Nation,Ethnicity,and Cultural Strategies:Three Waves of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Post-1949 China,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2008,P.53;Elena Barabantseva,Overseas Chinese,Ethnic Minorities,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P.49。。響應官方政策,各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都弘揚民族平等與團結,在銀幕上構建出一種新的“多民族大家庭”內部的民族關系。通過電影與其他大眾媒介,這種新中國的多民族影像被迅捷地傳達到大眾心中,激發鼓舞了他們對新型民族關系的理解與實踐。
《五朵金花》拍攝時的社會歷史背景,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自然山水的現代化改造格局,以及公路等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工農業發展與改善(尤其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生活。1957年的報道稱:“公路建設方面,七年來修建公路新增里程86775余公里……這些工程艱巨的公路的建成,溝通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這是黨的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8](P 2)公路建設也成為當時文藝創作的題材。據藝術史學者吳雪杉的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全國美展中,公路成為廣受藝術家青睞的畫題,如關山月的《新開發的公路》等[9](PP 71-82)。1954年9月27日《人民日報》用整版篇幅,從鐵路、水運、航空、郵電等方面報道“發展交通運輸業,為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服務”。公路運輸工會主席安力夫的文章《公路運輸的面貌在改變著》回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公路建設的巨大成就:到1953年,公路通車里程比1950年增加了33%。新建公路的共同點為“多在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岳地帶。這些地方過去很多都是人煙絕跡的原始森林和邊沿地域,工程異常艱巨。筑路的軍工、民工和廣大群眾,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克服種種困難,和大自然進行搏斗……這種高度愛國主義的勞動熱情和頑強的斗爭意志,使我國公路建設迅速推進到新的地區”[10]。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公路建設才是真正為了人民群眾,使得“廣大群眾從自己的生活實踐中認識了今天的公路是促進物質交流,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工具,與反動統治時期有著本質上的差別,都自動地參加了公路的整修工作”[11](P 10)。
安力夫的文章認為,公路運輸事業的發展,對沿線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公路建設,促進了各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事業的發展。例如,歷來無法外運的土產品逐漸可以運到外地,從來少見的工業品在這些少數民族地區出現且不斷增多。這些生動的事實,使少數民族人民深切體會到民族政策的偉大,感受到祖國民族大家庭的溫暖。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支援公路建設[10]。1951年10月23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報告中指出:“國營貿易機關正以各種努力向少數民族地區推進工作,凡力所能及的地區,均以等價交換甚至實行補貼的辦法來組織物品交流,因此土產價格一般提高三倍或者四倍,多至十數倍。”[7](P 51)這令我們聯想到《五朵金花》開篇與結尾場景的“三月街”盛會中,“各族人民齊歡唱,賽馬唱歌做買賣”,各族人民售賣本地土特產及購買外地生產的生活用品,貿易呈蓬勃之勢。交通運輸發展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使得物品交流通暢且摒棄剝削色彩,盡管由于技術資源條件的限制,當時還不是柏油或水泥路面,而是泥結碎石及在蘇聯專家指導下修建的級配路面,馬車為主要交通工具[9](P 76),如《五朵金花》中所呈現的那樣。
相較之下,資本主義體系之下產生的公路電影質疑國家與社會機構的合法性,憎惡資本主義、消費主義與其他社會問題,浪漫化自身的邊緣位置、個人主義,甚至享樂主義[12](PP 38-40)。在多為白人男性中心的敘事中,也時見種族主義與男性沙文主義的態度,如尼爾·阿切爾指出“厭女”傾向及對“他者”(尤其是對少數族裔)的恐懼在美國公路電影中并不少見,公路電影本身在政治上并不一定進步[13](P 5)。在完全不同的社會與政治背景下,中國社會主義公路電影如《五朵金花》擔負著對國內觀眾的政治教化、審美愉悅功能及對海外觀眾的怡情與宣傳意義,如強調社會主義政權、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及如今頗有爭議的“大躍進”的合法性(16)關于“大躍進”的英文論述,見Meisner,M.,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6;程郁儒:《論新中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話語本質及其功能》,《思想戰線》2009年第5期,第59頁。。學者柏佑銘(Yomi Braester)指出,這些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時期文學和電影樣式有一種映照關系:面對同樣的群眾,帶有同樣的目標,因此,“形式與意識形態交融在一起創造出一種與某些政治運動相關的特色”[14](PP 119-140)。
《五朵金花》的拍攝只用了四個月,質量卻絲毫未打折扣。它的敘事是在“大躍進”背景下宣傳加快社會主義工農業發展步伐的一種激進的理想主義,集體性水利建設與“大煉鋼鐵”都得到了體現。例如,阿鵬尋找的蒼山公社副社長金花在繁忙的工地參與及指揮水庫建設;另一位金花與愛人在煉鐵廠,經過“祖傳三代是鐵匠”的阿鵬幫助解決了技術難題,終于成功煉出鐵。影片中集體勞動與參與建設的社群感及性別平等密切相關,也映照著歷史現實。在全國范圍內,始于1957年秋冬的興修農田水利運動帶來了大規模協作勞動,如朱羽所言:“興修水利等需要大量勞動力集體參與、互相協作的項目極大地改變了原有小生產者的勞動狀態,從而帶來了走出家庭、建構集體生活甚或軍事化組織勞動的可能。”[15](P 193)當然,片中關于“大躍進”的訊息比較隱晦,如前文所述,部分原因是該片預計在國外放映,為了不在其他國家引起審查麻煩,以及不疏離對社會主義缺乏理解的外國觀眾、傳達新社會的美好,這也就解釋了夏衍為何對王家乙說:“不要搞政治口號,要表現出山河美、人情美,這部片子的主題就是社會主義好!”[16](P 30)[17](P 34)
在贊揚《五朵金花》以歡樂喜悅為基調透露出對新生活的謳歌真誠可信的同時,評論者柳城指出,盡管多數少數民族題材影片對少數民族人物有比較豐富的表現,強化了觀眾在心理、意識與美學體驗上的認同,增強了漢族與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但這些影片也有其歷史局限性,“一些影片僅僅停留在風俗、服飾、語言表達等表面層次的表現上,沒能真正進入到對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層思考和探索上”[18](PP 7-9)。也有一些批評涉及這些影片中的主體性問題,因為除了演員外,絕大多數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由漢族電影工作者編劇和導演。客觀原因在于,與都市相比,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地理環境隔絕及歷史上經濟發展相對不平衡,多數少數民族民眾在1949年以前很少有機會看到電影,識字率(無論是本民族文字還是漢文)較低,接受電影訓練、進行電影實踐的機會非常有限。隨著1949年以后16毫米電影放映隊深入到廣大農村地區,以及各少數民族自治區都建立了自己的電影制片廠,培養人才,拍攝影片,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情況才有所改進(17)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民族電影人才不多。至70年代,才有了更多訓練有素的少數民族電影工作者,新疆、內蒙古、廣西、云南等地也陸續建立起自己的制片廠。少數民族導演如錫伯族的廣春蘭和白德彰,維吾爾族的吐依貢·阿合買德,蒙古族的云文耀、塞夫、麥麗絲、珠蘭琪琪柯(1930-2011),等等。人類學者貝絲·諾塔(Beth Notar)的研究表明,1951年時,云南省只有1/10人口一年能看到一部電影,但到了1959年,因為有近四百個流動放映隊,云南省平均每人每年能看到至少三到四部電影。見Chen,J.,Nation,Ethnicity,and Cultural Strategies:Three Waves of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Post-1949 China,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2008,P.79;柳城:《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創作漫評》,《電影通訊》1989年第8期,第7頁;Beth Notar,Displacing Desire:Travel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51。。
如果說《五朵金花》通過公路敘事呈現的多民族影像呼應著當時的民族政策與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社會歷史現實,其公路旅途的意義又如何被影片的視聽風格尤其是攝影與音樂所強調?片中出現的少數民族歌舞,尤其經過再創作的白族民歌,都為阿鵬與李同志、孟同志沿途所聞,不僅串聯起公路敘事,更體現出一種少數民族的、地方性的民間文化如何成為國族性的民族形式,且與當時文藝作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與政治意義密切相關。這些問題會在下一部分展開討論。
二、民間音樂文化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道路
在世界各國的公路電影中,聲音/音樂扮演了重要角色:映照人物情緒,強化變幻風景的壯麗,或與車速及影片視聽蒙太奇構成的速度和節奏感共呼吸。這樣的音樂有時作為敘事空間內的音樂(diegetic music)自車上的廣播或其他設備播放,有時作為敘事空間之外的配樂(extra-diegetic music)。在學者大衛·拉德曼(David Laderman)看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搖滾與流行音樂的盛行與叛逆性的青年文化密切相關,也為美國公路電影中常見的開車場景提供了敘事的便利與配樂的來源[4]。在其他一些非美國的公路電影中,混雜各大洲不同風格的配樂質疑一種歐洲中心的文化身份觀[19](P 34)。在《五朵金花》這部社會主義公路電影中,音樂的呈現是滿族作曲家雷振邦(18)雷振邦(1916-1997)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的作曲家,創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電影歌曲。其中很多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中的主題歌與插曲,如《五朵金花》中白族風格的《蝴蝶泉邊》、《冰山上的來客》(趙心水,1963)中塔吉克風格的《花兒為什么這樣紅》、《蘆笙戀歌》(于彥夫,1957)中拉祜族風格的《婚誓》、《劉三姐》(蘇里,1960)中壯族風格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等。他是滿族人,在日本學過音樂,常到各地區收集民歌。《蝴蝶泉邊》這首歌,雷振邦結合了劍川(阿鵬家鄉)的白族曲調與大理(金花家鄉)的“西山調”風格(李二仕:《〈五朵金花〉的“今點”意義》,《當代電影》2005年第2期)。影片勘景時,編劇趙季康與雷振邦決定將部分場景的對白改成對歌,這也是白族的風俗習慣,尤其便于青年男女表達愛慕之情。雷振邦將白族民歌非常高亢尖利(因在野外傳播)的曲調調整得柔和了一些,以便于大眾欣賞與傳唱。所收集及改編后的白族民歌,因民間音樂傳統而傳達出一種歡快生動情緒及擁抱社會主義集體生活的通俗感染力。影片內(音樂家李同志)外(雷振邦)的音樂“采風”涉及旅途,也涉及創造性勞動:奔走四方收集民間音樂進行再加工和創作。因為基于社會主義體系內產權和生產方式的公有制特征,盡管影片作曲署名“雷振邦”,這些音樂并不具有可牟利的私有“知識產權”,而是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資源。因此,來自少數民族的、民間的、地方的音樂,可以成為國家的、民族團結與平等的非物質象征。這種融合不同民族形式的多元一體的國族想象,經由民歌與電影呈現的愿景強化而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主流,并浸淫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以積極、明朗、樂觀的態度呈現理想化的社會主義新人與新型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關系。
與多數公路電影不同,《五朵金花》中的插曲并非只出現在無聲源的聽覺領域,所有歌曲承擔敘事功能且發生在敘事空間內,更像歌舞片中的歌唱段落。片中除了配樂外,還出現了幾首在影片上映后膾炙人口的插曲,如影片開始各族人民在“三月街”盛會齊唱的《繞山林》(白族稱為“繞三靈”)、在洱海撈海肥的姑娘們所唱的漁歌、副社長金花的爺爺山上采藥時所唱的《采藥山歌》、阿鵬隔窗對畜牧場金花所唱的《唱個山歌扔過墻》、副社長金花想念阿鵬時所唱的《繡圍裙》、歌唱家黃虹在鄰近結尾“三月街”盛會所唱的民歌等。片中出現的插曲鑲嵌于片頭、片尾兩次出現的主題歌《蝴蝶泉邊》之間(19)《蝴蝶泉邊》隨著影片的大受歡迎而被廣為傳唱,女聲部分由白族女高音歌唱家趙履珠演唱。她的演唱發音不是非常“標準”的普通話,帶有一點本地口音及鼻音,使得她的風格聽起來親切與“本土”。。這些歌唱段落有獨唱、對唱、合唱,有時還伴有精心設計的群舞。片中歌舞場景的呈現也對應著社會現實——歌唱是白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他們表達與交流(如對歌)的重要方式。片頭慶祝白族傳統節日“三月街”的集體歌舞段落呈現出一定的劇場風格(集市忽而成為群眾歌舞表演的舞臺),同時又有極具戲劇性的貨品交易與賽馬活動。在片頭的愛情場景里,四處尋找金花的阿鵬是通過跨越空間距離的她的歌聲而找到她的。這對情侶在對唱中交換信物,信物都是自己的勞動成果:金花繡的荷包,阿鵬鍛制的鋼刀。前者象征著金花的美麗、靈巧、勤勞,后者象征著阿鵬對愛情的堅貞。若說荷包與鋼刀是物質形態的信物,《蝴蝶泉邊》則成為金花與阿鵬非物質形態的愛情信物。
《蝴蝶泉邊》歌聲的兩度出現,不僅標志著影片敘事開端至結尾的變奏、阿鵬尋找金花旅途的終點,也開拓了一種電影聲音空間。聲音的多向發散性使得片中聲音空間不僅超越線性的道路,也順暢地聯結了實景與攝影棚內拍攝之間的空間與認知的縫隙。沿著蝴蝶泉邊平滑橫移的攝影機強化了布景的超凡脫俗的魅力及華美的人工性。盡管幾乎所有公路電影都是實景拍攝,有些具有紀錄片式的粗糙質感,但《五朵金花》中的多數內景(包括部分外景如“蝴蝶泉”)都是在長春電影制片廠的攝影棚里拍攝的。這種視覺上明顯的人工性與影片的后期配音實踐彼此呼應:片中所有歌曲由專業歌唱演員配唱,副社長金花扮演者楊麗坤的聲音也是由聲音演員后期配音的(20)這是因為楊麗坤無法講標準普通話。有報道說周恩來總理兩次帶楊麗坤出國訪問,勉勵她早日學好普通話。劉連:《〈五朵金花〉幕后悲喜人生》,《人民文摘》2009年第6期,第11頁。。此外,所有白族人物都講標準的普通話而非白族話,語言的縫隙也被彌合。在這樣的聲音實踐中,電影容易被大多數其他民族觀眾所理解,也暗示多民族統一的國族性比地方文化的本真性呈現顯得更為重要。
這種電影聽覺空間與地理政治空間緊密交織。如果說在很多公路電影中,“公路”成為一種另類空間,“與主流的隔絕使得個人轉變的經驗成為可能”[20](P 5),這種方向和動力感可被描述為“離心的”,在《五朵金花》中,空間方向卻是“向心的”:阿鵬路遇長春電影制片廠來的兩位漢族文化工作者——畫家孟同志與音樂家李同志——結伴穿行于蒼山公社。他們穿過的是社會主義空間的政治想象,關乎公社作為集體與社會主義建設作為意義。在蒼山公社的曲線旅途通過阿鵬不斷尋找金花而連接起不同地點——洱海、社管會、畜牧場、煉鐵廠、拖拉機站等,這些旅途場景與地點不但被流動的配樂“縫合”,也由現代通訊與交流工具——電話——而連成一個閉合的線路(盡管金花與阿鵬一次重要的電話通話因馬車拉斷電話線而斷掉線索,導致敘事中更多的誤會與延遲)。前文提到的片中歌曲中,每一首都與某個地點相關(無論內景還是外景),如“三月街”、“蝴蝶泉”、山間、畜牧場與金花的房間等。若我們將“繞山林”視為“引子”、兩度出現的《蝴蝶泉邊》為阿鵬與金花的重頭戲,與洱海相伴的漁歌、山間的《采藥山歌》及畜牧場的《唱個山歌扔過墻》則串聯起阿鵬等三人的旅途,通過他們的“聽聞”、他們在場的主觀性中介而傳達給觀眾。金花在房中所唱的《繡圍裙》則沒有其他人物在場,暗示出一定的私密性和個人情感維度,以歌唱吐露心聲成為與觀眾的直接交流,從而強化觀眾對這一人物心理狀態的認同。靜止的歌唱場景與流動的旅途交叉輪替,創造出一種張力,如歌舞片中敘事與歌舞場景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歌舞片與公路電影在敘事結構上有相近之處:結構于一路向前的運動與偶爾停下的場景,也如交通工具在公路上飛馳或停在某個休息區[21](P 94)。
雜糅喜劇、音樂片與公路電影的《五朵金花》中,兩位來采風且幫阿鵬尋找金花的漢族文化工作者,一胖一瘦,一莊一諧,他們與當地人的互動,有著歷史與政治寓意。他們被當地人尊為“專家”,但作為文化的外來者,他們驚嘆于當地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之豐富。當他們一片好意要幫忙時,常因不太熟悉體力勞動而容易弄巧成拙,造成麻煩、延遲與誤解。例如,他們因為不會趕馬車,馬拉斷了電話線,導致阿鵬與金花的通話中斷[22](P 40)。這兩個人物創造了一種自嘲的喜劇效果。導演王家乙后來檢討說:“最大的缺憾是對兩位藝術家的處理……在國外放映時,有外國評論說,中國內地輕視知識分子……沒想到政治與政策性問題,當做笑料來寫,這樣的塑造是失敗的、錯誤的。”[23](P 146)當然,拍攝時攝制組并未將兩位喜劇人物設定為音樂家和畫家,是擔心音協與美協問罪,作曲家雷振邦與美術師盧淦說戲里人物就是他們二人,因此加上“長影來的客人”臺詞[22](P 40)。與片中的李同志一樣,雷振邦到全國各地去采集民歌,有時會興奮地聽老鄉們為他整夜唱歌,記下歌譜[23](P 145)。
協助阿鵬尋找金花同時,兩位文化工作者的“采風”活動也是有目的的旅途——這是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眾,收集素材進行再創作,轉化為文化動員力量的過程與實踐。討論到社會主義思想實踐與性別話語時,美國學者白露(Tani Barlow)認為即使對于20世紀40年代的社會主義思考者來說,文化是動員大眾能量進行國家建設的媒介,傳統、通俗的“民族形式”被用來啟蒙大眾并服務于無產階級革命。在這種情形下,文化工作者如黏合劑,一種將不同社會因素聯合在一起建設國家的社會凝聚力[24](PP 211-212)。類似地,在《五朵金花》中,改編后的膾炙人口的白族民歌與作曲家們(雷振邦與片中的李同志)作為文化工作者為影片的文化實踐添加了一種獨特的民族元素。
除了兩位文化工作者收集民間文藝形式的任務為載歌載舞的視聽奇觀及公路旅途提供了敘事上的便利外,《五朵金花》也承載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與政治特色,這一點與絕大多數美國和歐洲公路電影不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延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精神,文藝工作者要“為工農兵服務”。他們也要通過向無產階級學習來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與工農大眾互幫互學。這在《五朵金花》中體現為下鄉采風的文藝工作者“意識到他們既是人民的老師,也是他們的學生”[25](P 289)。因此在影片敘事過程中,畫家與音樂家不斷向他們一路上遇見的人們學習且成功地轉變了:他們可以自如地進行體力勞動,如將公社的貨物裝上馬車,且跟阿鵬學會了如何嫻熟地趕馬車。在學者朱羽看來,這種“工農群眾知識化和知識分子勞動化”的流動過程旨在消除勞動群眾“臣屬性”問題,“構造新的習慣和生活方式,也可以說是‘生產’新的內在自然、新的心理機制、新的‘人性’,而非對于‘等級關系’的簡單顛倒”[15](P 186)。而金花、阿鵬、采藥老爺爺等勞動群眾克服了對自然的恐懼而獲得“主人”意識,克服了對“知識”的恐懼、破除了對專家、知識分子的迷信而獲得對勞動—知識主體的全新設想[15](P 187)。
《五朵金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典范,頌揚堅韌的少數民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也呈現了“人物的升華”[26](P 69)與優美風景,以及在勞動中收獲的愛情及同志情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政治與美學概念,盡管在蘇聯提出與發展,對社會主義中國文藝有深刻影響,但中國根據本國文化資源發展出自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路徑。它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藝創作中一個重要的準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并非單一的概念與實踐,其影響也延展到藝術創作領域且在不同歷史時段經歷過變化與轉折(21)“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自1932年在蘇聯被提出后成為蘇聯文學創作的重要方法(Katerina Clark,“Socialist Realism with Shores:The Conventions for The Positive Hero”,Thomas Lahusen and Evgeny Dobrenko,eds.,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27)。奧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1904-1936)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與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ev,1901-1956)的《青年近衛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經典作品且在中國有著廣泛的影響。見Regine Robin,Socialist Realism:An Impossible Aestheti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Thomas Lahusen and Evgeny Dobrenko eds.,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它也并非照搬現實,而是要在發展的活力中表現一個“更真實、歷史而具體的現實描述”;它是一個歷史階段社會關系的總和[27](P 4)[28](P 57)。因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預設藝術的社會介入與樂觀意義,追求創造一種理想化的世界,以簡單、明晰、易懂的方式與大眾溝通[26](PP 53-69)。就《五朵金花》的電影風格手法而言,它顯得中規中矩,攝影、場面調度、剪接等樸實流暢,為敘事、塑造人物、表達主題服務,力求視聽語言不對觀眾構成挑戰或引起格外注意。從這一點而言,與好萊塢主流電影中視聽風格服務于敘事并無二致,當然后者更多為了掩蓋電影制作過程的勞動及將更多觀眾吸引進敘事幻覺而實現利益最大化,前者則以通過電影方式為大眾提供教育普及、審美怡情文藝作品為目的。這一點也與20世紀中后期歐美“作者”/藝術電影中不時出現的先鋒實驗、意識流等現代主義電影手法迥然不同。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中,勞動對社會主義公民而言是一種道德與美學愉悅的源泉。它通常與田園抒情的美好、詩意以及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模范人物如在大家庭的人情之美密切相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通常被稱為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有機結合,因為浪漫主義被視為真正的現實主義及社會主義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26](P 67),如周恩來總理贊揚《五朵金花》,“我們的電影已經開始創作一種能反映偉大時代的新風格,一種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新風格”[29](PP 52-53)。《五朵金花》創造的是比生活本身更美好的理想化世界,在順暢的攝影機運動與充滿抒情色彩的音樂之中得到強調。秀美的蒼山洱海風光在緩緩橫移的攝影機運動中呈現出卷軸山水畫般的意境,點綴以五顏六色的繁茂花朵,這既是現實,又是被電影語言與彩色電影技術強化了的、充滿詩意樂觀色彩的理想化空間。
《五朵金花》中被“路途/公路敘事”結構統攝在內的“自然”,不僅事關影片中主要人物為少數民族的設定(相對于城市漢族居民,他們與“自然”更接近)、呈現的自然山水(與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的地理位置有關),還有其他層次:在民歌中被寄托了人們情感而吟唱的自然,以及作為社會生產實踐與作為生產資料與空間配置的自然,在這里形成一種和諧的政治“生態”(22)關于這幾點,感謝朱羽在閱讀本文文稿時提出的問題與建議。。這里的自然山水之美,可以被外來的文化工作者如李同志、孟同志代表攝影機的視角隔開距離進行審美性的觀照,更重要的是,它在這一社會結構下人類勞動活動的介入中與當地人形成更親密的關系,因擬人化的“為社會主義服務”而被勞動者歌唱:金花與伙伴們在洱海撈海肥時齊唱著“勞動號子”般的漁歌;副社長金花的爺爺在山上采草藥,唱著“采藥山歌”:“采得山藥除百病,人人樂呵呵”……被畫家孟同志問道:“您老這么大年紀了,怎么還上這么高的山啊?”他說:“這是個寶山哪,到處是藥材,能讓它呆在山上,不為社會主義服務嗎?”在另一場景中,煉鐵廠金花與姐妹們到山上找礦石,盡管遇到黑熊只能躲在山洞里過夜,但終究找到了高質量的鐵礦石。生產積極性高漲的新型社會主義勞動者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以及對后者的改造利用(但非涸澤而漁的剝削)中,主體性得以彰顯。他們也通過歌唱這種勞動的藝術表達獲得了“一種主體的尊嚴感,甚至帶來超越此刻體力勞動的解放感”[15](P 202)。
關于烏托邦與公路敘事,學者也曾論及美國公路電影中將社會批判編織進一種略帶游戲色彩的烏托邦主義,構建汽車旅行帶來的流動性、速度、自由與自我發現。這種公路電影敘事或呈現“一種同質性與國族凝聚力的烏托邦幻想”,或是“社會矛盾與反動政治的反烏托邦噩夢”[20](P 3)。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的“黑色電影”(films noir)中充斥著反烏托邦視角下的公路旅程,后來的美國公路電影則展示出一個主流公共想象中更加樂觀與烏托邦的版本(23)Katie Mills,The Road Story and the Rebel: Moving through Film,Fiction,and Televisi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6,P.38;Neil Archer,The French Road Movie:Space,Mobility,Identity,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3,P.6;David Laderman,Driving Visions:Exploring the Road Movi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P.37.。顯然,美國公路電影中個人主義的、特立獨行的叛逆型烏托邦精神與《五朵金花》中的截然不同,后者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公路敘事的隱喻性化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朝向未來,本質上進步與樂觀,結合與改造了民間與傳統文化資源;它雜糅地方文化形式并賦予其新的政治力量與社會功能:動員大眾。在學者托馬斯·拉胡森(Thomas Lahusen)看來,所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主要情節”走向是一種目的論的“完成任務”,而“主要結局”會告訴大家這個暫時任務完成后,還要面對未來的任務(24)Thomas Lahusen and Evgeny Dobrenko(eds.),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9;Régine Robin,Socialist Realism:An Impossible Aesthetic,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42-63;Xudong Zhang,“The Power of Rewriting:Post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n Chinese Socialist Realism”,in Thomas Lahusen and Evgeny Dobrenko(eds.),Socialist Realism without Shore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304;Ban Wang,eds.,Words and Their Stories: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Leiden,Boston:Brill,2011,PP.101-114.。
這一走向在《五朵金花》結尾場景中也顯而易見:阿鵬與金花終于重聚,對唱《蝴蝶泉邊》。另外四位金花與她們的伴侶及其他人物在花叢中出現,合唱一曲,祝福他們“白頭到老同甘苦,地久天長永相愛”。這首朝向未來的歌,不僅頌揚持久不渝的愛情是社會主義國家中一種積極的情感,也將戀人的私會變成一種在社群人們親切注視下的公共性情感,因此將個人的情感生活結合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集體訴求中。多數西式公路電影傾向于維護特立獨行的反叛精神,抗拒傳統家庭價值與新教工作倫理(25)David Laderman,Driving Visions:Exploring the Road Movi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P.10。也有一些特例,如大衛·林奇(David Lynch)的電影《史崔特先生的故事》(1999)。德文·奧格隆(Devin Orgeron)認為在這部電影里,公路作為離開與回到結構的方式,是社群建設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處的道路是重聚而非反抗的空間;一個合群與溝通而非隔絕與沉默的空間。此處傳統的家庭被高度贊揚且比六七十年代公路電影中對自我發現的強調更為重要。見Devin Orgeron,Road Movies:From Muybridge and Melies to Lynch and Kiarostami,New York:Palgrave,2008,P.34。,中國社會主義官方邏輯則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以確保社會穩定性與生產力。因此,在《五朵金花》中,五位金花都有愛人,拖拉機手金花的婚禮也是影片的重頭戲:因其地方習俗的奇觀性及引起阿鵬對金花誤解的戲劇性。金花與阿鵬的愛情故事富于浪漫色彩地暗示了一種社會主義家庭與未來添丁的圖景,在這種呈現里,這些社會主義新女性形象的塑造與基于性別和民族平等的社會主義現代性及一種隱喻的持續性的“社會主義道路”設想密不可分。
三、體制化的性別話語與社會主義道路
公路電影通常被視為“男性的類型”,因其男性中心的敘事與意識形態邏輯,甚至常有“厭女”傾向。這或許在意料之中,因為性別這個社會構建通常關聯著等級森嚴的空間與行為的政治、歷史實踐與認知,如“史詩”敘事中通常男性在外游歷而女性在家等待。流動性常被視為主體性與自由的象征,美國公路電影中男性角色通常享有更多特權,他們驅車自由穿行,獨自或與男性伙伴體驗自我轉變或救贖的歷程,而女性人物通常只是被動的乘客或他們的欲望客體(26)Timothy Corrigan.A Cinema without Walls:Movies and Culture after Vietnam,New Brunswick,New Yor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PP.143-144;Neil Archer.The French Road Movie:Space,Mobility,Identity,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3,P.121;David Laderman,Driving Visions:Exploring the Road Movi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P.20.。用學者蒂莫西·科里根(Timothy Corrigan)的話說,公路電影類型傳統上專門聚焦于男性,女性則是缺席的[30](P 143)。然而,社會主義公路電影如《五朵金花》中的性別結構截然不同。盡管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如五位金花與她們的社員姐妹們)并非積極的旅行者,但她們代表著具有主體性的新型社會主義公民,積極參與生產勞動,發展婦女主體性,同時為社會主義發展貢獻力量。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電影中少數民族女性的解放與獨立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義(27)20世紀五六十年代,電影工作者拍攝了多部關于少數民族女性自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影片,如《邊寨烽火》(林農,1957)、《摩雅傣》(徐韜,1961)、《阿娜爾罕》(李恩杰,1962)、《景頗姑娘》(王家乙,1965)等。,回應著推動性別與民族平等的官方政策。金花作為少數民族女性干部,也是官方政策的一種折射,如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李維漢于1951年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報告大綱中就強調,“普遍大量地培養同人民有聯系的民族干部,是圓滿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政策,以及發展各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建設事業的關鍵”[7](P 83)。學者王玲珍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國內多稱作“婦女解放”“性別平等”)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階級斗爭、民族革命與經濟發展等議題齊頭并進[31](PP 595-608)。1949年后,它成為官方支持的主流意識形態與體制化的充滿活力的實踐,與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等核心政治議題息息相關。這一點不同于第一世界資本主義框架下的女權主義實踐:基于個人主義與爭取政治權利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間雜被邊緣化的左翼知識分子的聲音。
討論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如何組織婦女勞動力時,白露指出,女性在公共領域和集體生活中付出勞動動員了一種根植于共同工作的大眾主體性[24](PP 211-218)。在鼓勵女性參與集體勞動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打破傳統男權結構下的勞動性別分工(如“男主外,女主內”等),使得性別解放與其他政治與社會訴求如女性的階級與經濟解放密切相關。這種性別政策也令人想起恩格斯的理論:“只要她還被排斥在社會生產勞動之外,被局限在私人領域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婦女讓其與男性平等就不可能。”[32](P 184)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大眾文化的蓬勃發展在改變性別角色和推動一種新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女性主體(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至關重要。另一電影案例中突出的女性形象是《李雙雙》(魯韌,1962)中的進步婦女李雙雙,與其保守落后的丈夫相比,她政治覺悟更高,對公共事務更熱心也更有能力。在關乎婦女的敘事中,健壯剛毅的社會主義女工形象在這一時期的視覺媒介中頗為普遍,對廣大婦女起到鼓舞作用,《五朵金花》也不例外。《五朵金花》中,女性角色沒有像美國公路電影的男主角那樣開汽車或騎摩托車旅行(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中,這些都與男性與技術關聯),但她們是出色的積肥能手、畜牧能手、拖拉機手和煉鐵組長。和重工業或技術要求較高的工作打交道,傳統上被視為男性專利,但她們信心十足地挑戰這種勞動分工——盡管女性與重體力勞動的關系在片中的確被浪漫化了(28)紀錄片《女拖拉機手》(沙丹,1950)與劇情片《女司機》(冼群,1951)、《馬蘭花開》(李恩杰,1956)、《笑逐顏開》(于彥夫,1959)中的女性都是經過刻苦努力,克服多種困難,最終勝任了傳統的“男性職業”,如拖拉機手、火車司機、鏟運機司機、建筑工人等。。雖然“大躍進”如今被很多歷史學者認為是激進的、頗有爭議的運動,但奧地利學者金伯利·曼寧(Kimberley Ens Manning)的田野調查研究表明,很多中國婦女認為這是婦女解放的高峰時期,因為“大躍進”為動員婦女的社會參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33](PP 138-156)。
自1958年起,中國政府號召農村婦女更大程度參與工農業生產。一些家務勞動被社會化(如成立集體食堂、托兒所及洗衣、縫紉小組等),婦女被部分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參與有償勞動而獲得經濟獨立,“同工同酬”也被提上日程。這使得她們獲得前所未有的社會尊重,在工作中培養彼此支持的社群,也拓展了社會空間,使得她們可以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甚至成為領導者(小說和電影《李雙雙》是呈現這些面向的典范之作)。同時,婦女也通過意識覺悟、文化知識、勞動技能的提升為國民發展做出貢獻。在將政治道德化的趨勢中,這些具有先進意識的模范女性勞動者是新型公民社會主義理想的化身,銀幕上下皆如此。如《五朵金花》中,五位金花都是各行各業的模范,在社會主義意識與職業技能方面都非常出色。阿鵬的愛人金花更是蒼山公社的副社長,她高效無私地處理社里的各種事務。女性人物金花們被影片著重描寫,她們的愛人退居次要位置。金花們被呈現為潑辣爽朗、勤勞能干、無所畏懼、勇于且善于表達想法,女性勞動主體的自信溢于言表。
《五朵金花》中積極樂觀、自信能干、大公無私、富有健康美的少數民族勞動女性形象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性別與民族話語與政治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人類學學者梅根·布萊森(Megan Bryson)的研究表明,“五朵金花”形象為白族婦女提供了不同的榜樣:一種現代社會主義的白族女性性征,取代類似忠貞、賢妻良母等傳統女性“美德”[34](PP 147-148)。金花這些女性模范也影響了幾代中國勞動女性。女性社會地位與自我預期的提高對整個社會對女性的認知有著長期的重要作用[33](PP 138-156)。社會主義女性既是《五朵金花》的核心人物,也是目標觀眾——它曾在“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放映[35](P 6)。《五朵金花》也成為動員大眾的有效方式。20世紀50年代,大理白族地區與其他漢族地區都出現了無數以“金花/銀花”為名的勞動競賽。例如,陜西省的“銀花賽”即是為《五朵金花》所鼓舞,宣傳在棉花種植方面的當地婦女勞動模范。那里的婦女傳統上只做家務,被局限在家庭空間,在農村的性別與階級層級關系中被邊緣化。《五朵金花》甚至激發越南人民開展類似競賽以提高生產力。這一時期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也受到列寧與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影響(29)Gao Xiaoxian,“‘The Silver Flower Contest’:Rural Women in 1950s China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in Zheng Wang and Dorothy Ko,eds.,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Oxford:Blackwell,2007,PP.164-182;秦家華:《社會主義新生活的贊歌——重評〈五朵金花〉》,《思想戰線》1977年第6期,第88頁;李二仕:《〈五朵金花〉的“今點”意義》,《當代電影》2005年第2期,第93頁。。性別平等的話語因此成為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重要象征。
四、結語
《五朵金花》在地方、國家與國際層面都有豐富延展的生命。它在1959年首映與1978年重映時,都曾引發云南當地與全國觀眾的熱烈反響。白族觀眾尹明舉寫道,1959年《五朵金花》在昆明上映時,24小時不間斷滾動放映仍滿足不了觀眾要求,作者看的是凌晨五點場。1978年《五朵金花》重映時,“每個電影場、院都像趕三月街一樣熱鬧。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只要有盛大節會就少不了放映這部電影,歌曲則每天都響徹大理城鄉”[36](PP 26-27)。1960年東北三省舉行長春電影制片廠1959年新片展覽周時,《五朵金花》等影片上座率達100%或95%以上。觀眾的熱烈要求使沈陽、哈爾濱兩地影院不得不增加放映場次。春節期間,竟至通宵達旦地放映,仍不能滿足觀眾要求[37](P 9)。一位白族觀眾贊揚人物樂觀熱情地投入生活與勞動,“勞動帶來愛情和幸福,把一窮二白的大理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幸福的樂園”[38](P 41)。少數民族民眾對《五朵金花》這樣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接受部分成為他們對自身文化身份想象與重構,以及他們生活與文化經驗的一部分,加強了他們的自豪與尊嚴感。白族觀眾尹明舉回憶看完《五朵金花》后余興未盡的交談,同學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便是:“你們白族真好!”他寫道:“從那時開始,‘金花’便成了白族的一張最醒目的名片,無論在國內國外,任何一個白族人只要說:我是從‘五朵金花’的故鄉來的,人們就明白這是什么樣的一個民族了。可以說是這部影片在世界范圍第一次給白族樹起了一個藝術形象,給了白族一個叫得響的名字:金花”(30)例如,景頗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結婚時,會放映《景頗姑娘》來招待親戚和客人。見李二仕:《十七年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15頁;尹明舉:《第一次讓全世界都認識白族》,《大理文化》2009年第1期,第26-27頁。。人類學學者貝絲·諾塔注意到如今大理很多年長的村民還會自豪地看《五朵金花》,因為他們的家鄉出現在這部著名電影里。他們從未對白族文化在影片中的表現有什么批評[5](P 79)。《五朵金花》的文化遺產也被大理政府用以吸引游客發展旅游業,大理有家名為“五朵金花”的電影院,每天為游客放映這部電影,并催生一部自稱“《五朵金花》續集”的電影《五朵金花的兒女》(郝曉源、張進戰,1990)[39](P 98)——片中的公路旅途與半個世紀后的旅游在此聯結——副社長金花的女兒在片中是一位導游。
正視“公路電影”的國際性與跨國性而非一個本質上“美國”的電影類型有助于提供一個有效的概念框架來重新思考電影史上的另類公路電影以及當代公路電影中觸及的新的主題與面向,如遷徙與身份、移民與離散、音樂與記憶等。旅行、運動與跨界是自電影史早期就備受關注的議題。一種充滿活力的形式感與多數公路電影密切相關,如片中呈現的高速運行的交通工具帶來的運動性、速度快感、不斷變換的視野以及快速蒙太奇段落。然而,正是現代交通技術的缺席與非機械化的(或說更自然有機的)旅行方式使《五朵金花》顯得獨特:平滑、優美、緩緩橫向運動的攝影鏡頭強化了蒼山洱海的全景繪畫感。影片描繪了一種更為傳統的交通方式與不同于“垮掉的一代”的“青年文化”:浪漫愛情在此作為一條線索,編織進影片的訊息,即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及未來道路的崇高目標。《五朵金花》中,交通工具(如馬車)并非私有而是公社的公有財產,兩位長影來的客人可以隨意使用。當這一時期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嘆息機器如何異化了人與時間和空間的關系,及機械化的流動性帶來的身體與社會的代價[40](P 9),《五朵金花》中的中國描畫了一幅朝向工業化與現代化的熱忱樂觀的道路。因為中國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及美國通俗文化的影響,當代中國主流商業類型電影中也出現了更多公路敘事(31)如《站臺》(賈樟柯,2000)、《走到底》(施潤玖,2001)、《尋槍》(陸川,2002)、《旅程》(楊超,2004)、《在路上》(張菁,2004)、《千里走單騎》(張藝謀,2005)、《芳香之旅》(章家瑞,2006)、《練習曲》(陳懷恩,2006)、《男人上路》(劉小寧,2006)、《賴小子》(韓杰,2006)、《尋找智美更登》(萬瑪才旦,2007)、《紅色康拜因》(蔡尚君,2007)、《落葉歸根》(張楊,2007)、《香巴拉信使》(俞鐘,2007)、《尋找阿依闊勒》(侯克明,2009)、《西風烈》(高群書,2010)、《人在囧途》(葉偉民,2010)、《太陽總在左邊》(松太加,2011)、《轉山》(杜家毅,2011)、《飛越老人院》(張楊,2012)、《后會無期》(韓寒,2014)、《心花路放》(寧浩,2014)、《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李睿珺,2014)、《路邊野餐》(畢贛,2015)、《岡仁波齊》(張楊,2015)、《詩人出差了》(雎安奇,2015)、《失孤》(彭三源,2015)、《皮繩上的魂》(張楊,2016)、《冥王星時刻》(章明,2018)、《撞死了一只羊》(萬瑪才旦,2018)、《阿拉姜色》(松太加,2018)、《過韶關》(霍猛,2018)。跨國公路電影有在意大利和中國拍攝的《消逝的星星》(Gianni Amelio,2006)。,不過已與《五朵金花》截然不同。
電影是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媒介與文化形式,可以超越其地理空間與歷史背景做“長途旅行”。《五朵金花》曾在“冷戰”時期“旅行”到46個國家,在“文化外交”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王家乙之前拍攝的《風箏》一樣,傳播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正面影像,加強了國際主義團結。20世紀60-70年代,《五朵金花》與長影出品的另一部關于少數民族女性的歌唱風光電影《劉三姐》(蘇里,1960)在港澳及東南亞上映,因其美好的山水、民歌與人物引發當地華人的強烈反響,成為“冷戰”時期中國大陸爭取南洋華人支持的重要文化媒介。1960年,《五朵金花》與其他一些中國電影在倫敦上映,評論者贊揚它給觀眾帶來“意外的愉悅”,是“抒情性與現實主義的重新結合”[41](PP 84-86)。《五朵金花》中暗含的國際視野與想象使得其對國內外觀眾都有巨大吸引力——它展示了這個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美好的風景、公民與人情,王家乙回憶說,《五朵金花》的最高目標是讓中國和外國觀眾“愛他們,愛他們生活的社會,愛這些熱愛勞動的人”!周恩來總理也贊揚此片“歌頌了我們美好的國家、美好的人,歌頌了我們人與人之間的美好關系”[23](P 145)。為漢族與少數民族及國際觀眾創造一個國家影像,是社會主義中國自我宣傳的方式,是在充滿冷戰政治敵意的世界獲得國際認可的努力[42](PP 74-84)。各國人民與文化團結的意識象征著社會主義作為一個世界范圍的、本質上國際主義的現象[43](P 106)。《五朵金花》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公路電影的國際主義元素相遇與重疊,創造出一種旅行世界的多層次流動。在“冷戰”的全球框架下重新解讀以《五朵金花》為例的社會主義文藝的呈現形態及其獨特的政治與美學意義,在“后/再—文化冷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更為復雜的今日尤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