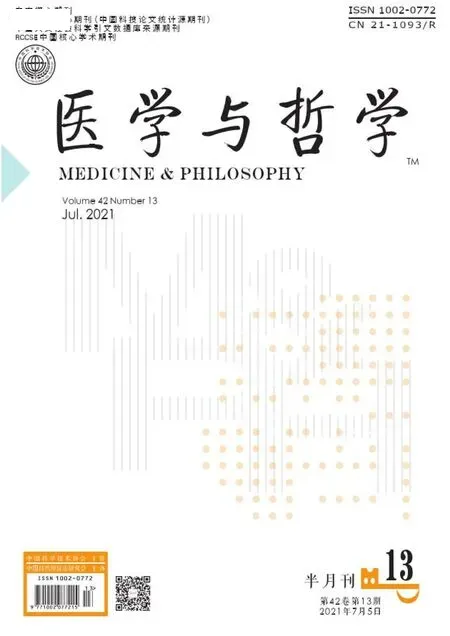極高齡女性供卵助孕存在的風險及倫理思考*
楊德輝 郭翠翠
目前,國際上對于高齡的界定尚無統一標準,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學會、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專家將高齡 (advanced maternal age) 界定為年齡≥35 歲[1-2],即35歲是女性生殖高齡的分界線,其中年齡≥45歲為極高齡女性[3]。高齡不孕女性常規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妊娠結局差,供卵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IVF-ET)成為高齡不孕女性獲得妊娠的有效方法[4-6]。卵子捐贈技術(oocyte donation)是IVF-ET的衍生技術。本文借助各方網絡媒體報道的多例極高齡女性通過“供卵試管嬰兒”成功產子的案例,探討極高齡女性助孕存在的問題以及助孕易于引發的倫理問題,為今后工作中遇到類似患者提供應對策略。
1 案例資料
多家網絡媒體報道。
2010年,安徽失獨家庭盛女士60歲時通過供卵試管嬰兒產下雙胞胎女兒,9年后表示“如果再有一次機會,我會考慮得很慎重”。
2012年,失獨家庭文姨50歲、劉叔55歲在廣東省婦幼保健院的集愛遺傳與不育診療中心通過贈卵試管嬰兒生下一對龍鳳雙胞胎,10年后他們自殺了,生前曾說“很后悔生了這對孩子,其實自己是在害他們”。
2016年,浙江1位61歲老年女性于境外實施供卵助孕產下嬰兒;同年,上海1位極高齡女性亦于境外接受供卵助孕,在當地醫院分娩后死亡;同年12月,吉林1位64歲失獨老年女性借助供卵助孕產下1名男嬰。
這些報道使眾多極高齡不孕女性看到了再生育的曙光,她們忽略了高齡產子的負面影響,紛紛到各大生殖中心咨詢,希望可以借助ART實現其再生育的愿望。
2 極高齡女性的生育現狀
正常情況下,隨著年齡的增長,女性生育力逐漸下降,卵巢儲備功能下降,即卵巢中卵泡數量減少,同時伴隨卵子質量的下降,這是導致高齡不孕女性行常規ART助孕妊娠結局差的主要原因。極高齡女性的卵巢功能更是急劇下降,她們幾乎沒有質量好的卵子,葛明曉等[7]報道高齡女性行自卵IVF-ET的妊娠率低而流產率高,≥45歲女性幾乎無妊娠發生。自1984年Lutien等[8]利用供卵的方法成功地解決了卵巢早衰的患者的受孕問題以來,供卵IVF-ET成為高齡不孕女性獲得妊娠的有效方法[4-6]。2008年~2010年美國一項納入27 959個供卵周期的回顧性研究中,根據年齡分為五組:≤34歲、35歲~39歲、40歲~44歲、45歲~49歲、≥50歲,比較各組的妊娠結局。研究結果顯示,<45歲的3組中胚胎種植率、臨床妊娠率、活產率穩定,無統計學差異,而≥45 歲的2組中各項指標均顯著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研究人員進一步比較分析了45歲~49歲組中5個年齡段,即45歲、46歲、47歲、48歲、49歲的妊娠結局,發現≥48歲的胚胎種植率、活產率均顯著降低,研究結果顯示年齡≥48歲的高齡受卵者妊娠結局極差[9]。
3 極高齡女性助孕存在的風險
3.1 對自身的風險
3.1.1 身體方面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各項機能逐漸下降,基礎疾病的發生率逐漸上升,多數極高齡女性可能已經合并心血管系統(如高血壓)、消化系統(如病毒性肝炎、消化性潰瘍、膽囊炎、膽囊結石)、內分泌系統(如糖尿病、甲亢/甲減)、呼吸系統(如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血液系統(如貧血)、泌尿系統(如慢性腎炎、腎結石)和免疫系統(如系統性紅斑狼瘡、抗磷脂綜合征、干燥綜合征、類風濕)等內科疾病,以及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病、宮頸病變、卵巢腫瘤等婦科疾病,這些疾病不利于妊娠,對母嬰均可產生不良影響。或者即便孕前身體尚健康,若能成功妊娠,也更易并發一系列的病理妊娠(如流產、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妊娠期糖尿病、貧血、前置胎盤、胎盤早剝、早產等),增加了圍產期并發癥(如先兆子癇/子癇、產后出血、高剖宮產率等)及母嬰風險(母體:心、肺功能衰竭,深靜脈血栓形成,腎功能衰竭等致孕產婦死亡率顯著增加;胎兒:死胎、死產、早產、發育遲緩、低出生體重等發生率顯著上升),上述并發癥/風險隨孕婦年齡增大而升高,嚴重危害母嬰健康[10]。
3.1.2 精神方面
極高齡女性患者大都處于圍絕經期,特殊的生理狀況決定了其實施 ART治療時更大的精神心理壓力,焦慮、抑郁發生率較高,尤其對于失獨的極高齡女性患者,失去子女已造成毀滅性的重創,若經歷多次助孕仍不能獲得妊娠,每一次助孕的失敗都可能會加劇心理創傷,負性心理反應和助孕不良結局之間相互影響,容易形成惡性循環。
3.2 對子代的風險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青少年更希望自己出生時父母親年齡不要超過35歲。如果年齡過大,自身精力、體力、經濟及社會能力下降,其撫養后代的能力必然下降,甚至部分子代尚未成年,高齡父母即面臨生病、死亡,部分/完全喪失撫養后代的能力;且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完善,不能很好地覆蓋高齡父母的子代,因此高齡助孕的后代在成長過程中易受到身體和社會心理傷害,從而導致子代易患精神分裂癥、情感障礙及自閉癥等精神疾病[11]。鑒于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中對贈卵的規定,獲卵數20枚以上者多為多囊卵巢綜合征(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PCOS)患者,PCOS自身存在遺傳風險,卵母細胞潛在的質量問題令人擔憂,且高齡產婦子代更易合并早產、低出生體重、發育遲緩,出生后易出現喂養困難,母子年齡差距過大易導致教育及溝通障礙等問題,均不利于子代身心健康。
我國贈卵/受卵專家共識中建議贈卵者年齡在20歲~35歲以保障卵子的質量,但極高齡受卵者配偶的年齡往往亦屬高齡,隨著年齡的增加,高齡男性精子基因突變概率增加,發生遺傳性疾病的風險增加,子代出生缺陷(如唇腭裂、先天性心臟病等)的風險升高,且精子表觀遺傳學的異常改變可能導致子代易患精神分裂癥、兒童孤獨癥,甚至惡性腫瘤等疾病[12]。伴隨年齡相關改變,若男方為嚴重少/弱精子癥,尚須行卵胞漿內單精子顯微注射技術(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授精,ICSI可能增加子代認知能力障礙的風險。
4 倫理原則與監管
2018年,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發布的《卵子捐贈與供/受卵相關問題的中國專家共識》指出,受卵者胚胎移植時年齡不應超過52歲,不建議已自然絕經女性接受供卵助孕[13]。這個年齡的限定是基于受者至少需健康存活至70歲,即可以陪伴孩子出生后成長至18歲成年的考慮。但極高齡夫婦助孕易引發諸多倫理問題[14-15],因此在給極高齡女性患者助孕前應嚴格遵循以下倫理原則。
4.1 患者有利
人類生育權是一項基本人格權,是指合法夫婦享有決定是否生育、何時生育和生育子女數量的權利[16]。因此極高齡女性享有生育權,不能剝奪,但其自身面臨的身體健康問題、心理狀態不可忽視,建議極高齡夫婦在計劃再生育前應首先進行孕前咨詢(包括遺傳學咨詢)及相關醫學檢查,充分了解母體自身及助孕產生的子代可能存在的健康風險。在為此類患者實施助孕前,應同時評估其配偶的年齡和健康狀況,組織生殖醫學、高危產科學、內科學、心理學、男科學、遺傳學等多學科綜合評估。從身體角度評估,近期:有無ART助孕禁忌證,是否有指征對其施行ART助孕;中期:高齡母體是否能耐受妊娠、生產過程;遠期:能否陪伴子代至成年(除意外)。從經濟角度評估,排除養老生活、一般疾病所需的費用,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支持ART、高危妊娠過程以及撫養子代、教育子代的開銷。若綜合評估結果弊大于利,基于安全及長遠的考慮,倫理上是允許拒絕為極高齡女性尤其是已自然絕經的女性提供助孕。
4.2 知情同意
應充分告知目前醫療技術條件有限,卵源稀缺、等待期長,極高齡女性助孕妊娠率低、流產率高、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多、妊娠結局差、生產風險大,可能經過多周期助孕仍無法獲得妊娠或有幸妊娠卻不能最終抱孩回家,不僅消耗大量財力,還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心理壓力;高齡男性精子質量下降對胚胎及子代可能產生不良影響;極高齡父母缺乏足夠的體力、精力和智慧來撫養、教育孩子,容易產生交流障礙;若子代未成年即喪失父母就迫使子代過早負擔家庭責任容易引發社會問題等風險。知情同意不是簡單的對或錯的判斷題,而是體現患者對于其臨床診療的一種決策能力[17],尤其不孕不育癥并非真正意義的疾病,患者的認知主觀且比較片面,醫務人員僅僅提供與醫學相關的咨詢,并不能代替患者做出是否需要進行醫療行為的決定,這就需要患者的共同參與——醫患共同決策模式[18]顯得尤為重要,醫患雙方共同探討臨床決策,以期達到認知相同或相近的效果,減少醫患沖突,為患者提供相對適宜的醫療方案。最終由極高齡夫婦患者根據自身條件慎重、理智地做出合理選擇。
4.3 保護后代
除了卵源、精子可能存在的遺傳風險和ART對子代安全性潛在的風險,極高齡夫婦需持續付出財力以撫養孩子,以及子代在成長過程中缺乏父母參與的親子活動,年齡差距過大,容易產生代溝,引起交流障礙,導致親子關系日漸疏遠。且父母生育時年齡過大存在孩子成年前父母一方或雙方去世的可能,這將對子代造成致命的打擊。因此,在助孕前應囑其慎重考慮其社會經濟狀況是否足以負擔后代的成長與教育需要,是否有持續的時間、精力投入到子代的撫養過程中,若子代成長及受教育的基本權益難以保證,應該拒絕為極高齡患者提供助孕治療。
4.4 社會公益
隨著社會生育觀念的轉變,不孕患者對于供卵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其中多數是高齡婦女。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規定“贈卵者僅限于接受人類輔助生殖治療周期中取卵的婦女”,即供卵助孕周期的卵子必須來自接受ART治療周期中婦女的無償捐贈,捐卵者須年齡≤35歲、身體健康、獲卵數≥20枚的成熟卵母細胞且至少保留15枚自用的前提下自愿將多余的卵子進行捐贈。因此卵子來源有限。且目前隨著ART日趨成熟,越來越多的生殖專家開始倡導獲卵數在滿足助孕周期使用的前提下盡量減少促排卵藥物的使用,以減少醫源性損傷,降低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OHSS)的發生率,同時也減少ART周期中過多胚胎凍存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獲卵數的減少,能夠滿足卵子捐贈條件者隨之減少,卵源愈加稀缺,加劇了供需矛盾。正所謂物盡其用,有限的資源應該用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筆者認為稀缺的卵源更應在有穩定妊娠率的人群身上發揮其最大作用,減少資源浪費。
極高齡女性往往需要多個周期助孕才有可能妊娠或仍無法獲得妊娠,消耗大量的醫療資源(尤其是卵源);高齡生育導致危重孕產婦增多,占用大量醫療資源;極高齡父母精力、體力、財力有限,疏于對子代管教,加大了社會監管責任,若子代成年以前失去雙親成為孤兒勢必增加社會監管責任和經濟負擔。這些有悖于社會公益原則。
4.5 嚴防商業化
我國衛生部門明確禁止任何形式的買賣精子、卵子和胚胎,嚴禁代孕。但是由于卵源的稀缺,在經濟利益驅使下,黑色利益鏈條非法買賣卵子猖獗。違法分子以各種手段誘騙年輕女孩出賣卵子,其中不乏名牌大學的高材生,違法分子給卵子貼上“高學歷、高顏值、名人”等標簽供“顧客”挑選。這些女孩為了與之付出并不匹配的“高”經濟利益出賣卵子或非法代孕,不惜損害自己的身體。很多人在出現了感染、腹腔內大量出血、OHSS等并發癥到醫院就診時才知道自己的賣卵行為導致了嚴重的后果,因為事先她們根本不了解促排、取卵的過程以及取卵手術中及遠期可能伴隨的風險(盆腔炎性后遺癥、不孕癥等,甚至危及生命)。這些非法獲取的卵子可能提供給多名受者,增加了后代近親婚配的風險等。要斬斷這些黑色利益鏈條,除了公安機關等相關部門的嚴厲打擊,呼吁受卵者不要只為自己“有后”而不擇手段,“杜絕非法買賣卵子、非法代孕外,生殖機構亦不能為了“挑戰女性生育年齡極限”或為了科室收益把大部分卵源消耗在極高齡人群上。
4.6 嚴格保密
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規定,機構和醫務人員對使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所有參與者(如卵子捐贈者和受者)有實行匿名和保密的義務[19]。凡使用供卵/供精實施的ART治療周期,供方與受方夫婦、與實施ART的醫務人員、與后代之間均保持互盲狀態。本文列舉的案例經媒體報道后,子代的隱私蕩然無存,若喪失父母,他們便成了人們口中的“野孩子”,可能流落街頭,引發諸多社會問題,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成長。因此,不僅在輔助生殖過程中要嚴格遵循互盲原則,更要保護受者及其子代隱私。
匿名和保密原則雖然保護了供方與受方的隱私,且《卵子捐贈與供/受卵相關問題的中國專家共識》中建議受卵者接受贈卵數目也僅為3枚~5枚,但卻無法完全避免子代近親婚配的小概率事件的發生。
4.7 倫理監督
為極高齡夫婦實施助孕必須全程接受倫理委員會監督。不僅要保障其生育權,實施助孕前須就“該夫婦是否可以接受助孕治療”提交生殖醫學倫理委員會討論。生殖醫學倫理委員會應依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倫理原則對該夫婦充分發揮其倫理監督指導的作用,基于對父母及其子代身心健康、利益的考慮,倫理委員會有權決定“是否給予極高齡者助孕”,嚴防技術濫用。
綜上所述,隨著人們生育觀念的改變,越來越多的極高齡不孕患者有再生育需求。對于極高齡受卵助孕患者,嚴格把握供卵助孕的適應證和禁忌證。醫務人員既要尊重極高齡女性的生育權,更要從有利于患者、有利于后代、有利于社會公益等角度出發,加強知情同意及心理疏導,充分告知極高齡女性生育給自身及后代帶來的風險,盡量勸導極高齡女性放棄助孕治療,若勸導無效由倫理委員會最終決定是否給予極高齡者助孕,嚴防技術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