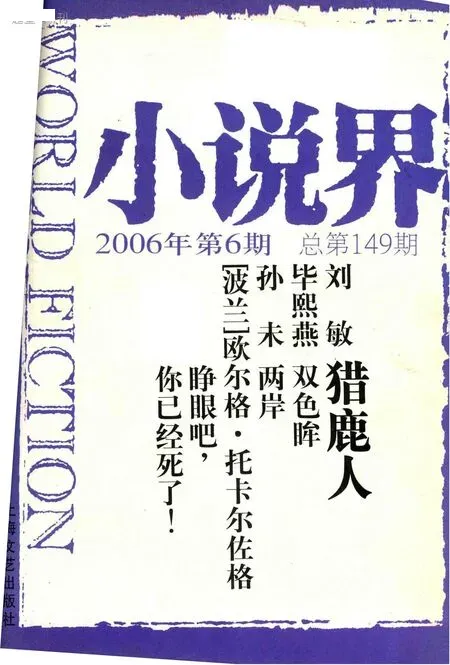遺珠
2021-12-04 20:40:29張彬
小說界 2021年6期
張彬
第一天,他捕獲他的時候,只記得慌亂且痛。那天風很大,浪潮推著他撞到尖石,蚌殼都被沖破。就這樣,那個他,小小的晶石住了進來,裹進他腹肚,留在身體里,本是為了愈合傷口,又好像是陪伴。
他和他濡濡地講話,也骨碌碌打滾兒玩。游蕩在身體中,日夜波漾。那個他變成圓潤的珠子,長出和自己的手心一樣的光彩,有時看著像岸邊的月光。
蚌殼越長越厚,珠子也越來越大,守在他的心臟旁,小聲說話。有時生氣,也會倔強地滑到手的邊緣,拉扯他,讓他再次感到疼痛。好像一種甜蜜的負擔。
歲月如流,他逐漸奄奄一息。我們要分開了,他想。像那天一樣的浪潮把他推到沙灘。
拾貝人發現了他,也發現了里面瑩彩華美的珍珠。他被鑲嵌到一頂玉冠上。
王侯眉目,灼灼生輝。帷幕野苑中,一只小鹿遠遠看到玉冠上的他,這時候的他像太陽。小鹿呦呦叫喊:“是我呀,是我啊。”羽箭帶著生冷利風,直射而來。
過了一百年,冥蟲淺唱,幽夜無光。他沉睡于地下,而他跟隨其他鳥群在朝暮世界劃線投影,從清晨初啼,到黃昏斂翅,到處找不到他。
再百年過去,考古界的大發現,玉冠出土了。在人頭攢動的博物館,終于又看到他。“哎,這顆冠頂珍珠好漂亮,兩百多年了竟然還這么有光彩。”旁邊參觀的姑娘小聲說。
在射燈照耀下,在玻璃隔絕外。他站在前面,時光縮短,神思相對,卻再也無法觸碰。
身外之物,我們只是滄海遺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