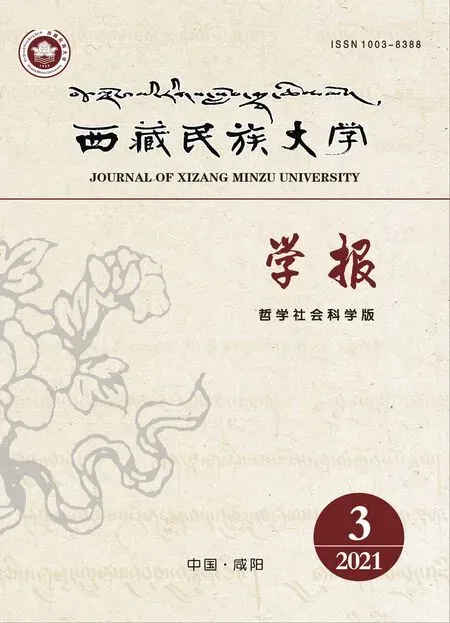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奴”等群體社會地位考述
冉永忠,李博
(1.西藏民族大學研究生院 陜西 咸陽 712082;2.陜西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陜西 咸陽 712046)
關于敦煌陷蕃之后的社會變化,目前有不少學者從社會組織結構、民族成分結構、政權組織結構、土地分配政策等多個方面展開研究,筆者以為探討敦煌陷蕃之后社會的深刻變化還應考慮當地居民變成吐蕃屬民以后的身份地位是否有根本性變化,尤其是是否轉變為社會地位較低的“奴”等群體①,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既可以厘清吐蕃在敦煌地區的施政措施,也可以由此管窺吐蕃本土的相關社會制度。
一、吐蕃占領敦煌之后的人口擄掠現象
781年,吐蕃占領敦煌,敦煌進入吐蕃統治時期②。一般認為吐蕃統治下的敦煌地區漢人地位是低下的、悲慘的,其主要證據在于《全唐文》的記載:“臣嘗仕于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以東,神鳥、敦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1](P7851)這段記載成了人們界定吐蕃占領下敦煌百姓地位的有力證據,但需要注意的是,沈下賢的記述不一定完全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他作為唐朝的一名知識分子,比一般人擁有更強烈的榮辱感,所以當一直處于唐朝統治下的敦煌突然被稱之為蠻夷的吐蕃所占領,這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來是不能接受的,甚至是屈辱的,其所記載的相關歷史必然會充滿個人感情,損貶“攻陷者”和夸大吐蕃統治下敦煌地區人民的悲慘生活也是難以避免的。
吐蕃在進攻河西、隴右和攻陷敦煌的戰爭中,確實俘掠過一些唐朝士兵和百姓,用來為吐蕃統治者服務。如787年,吐蕃攻汧陽、華亭(今甘肅華亭一帶),“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眾慟哭,投塹谷死者千數。”[2](P6097)可見,當時擄掠漢人的規模不小。直到吐蕃占領敦煌以后,他們仍從其統治下的敦煌地區抄掠漢人。S.3287《吐蕃子年(九世紀前半)五月沙州左二將百姓氾履倩等戶口狀上》(以下簡稱《氾卷》)記:“戶(氾國珎)死。妻(張念念)在。男(住住)在。男(不採)在。小婦(寵寵)出度。奴(緊子)論悉□夕將去。奴(金 剛)□。婢(落娘)已上並論悉□息將去□。”[3](P377)P.T.1083《禁止抄掠漢戶沙州女子牒》載:“往昔,吐蕃、孫波與尚論牙牙長官衙署等,每以配婚為借口,前來抄掠漢地沙州女子。其實,乃傭之為奴。”[4](P52)可見,這一時期的搶掠現象仍有發生。但需要注意一些細節問題,如從S.3287《氾卷》所記的五戶百姓來看,被吐蕃官吏抄掠的只有氾國珎一戶,而且被掠之人也只是其家庭成員中原本就屬于奴或婢身份的人。
二、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奴”等群體考析
(一)“奴”等群體的相關記載
在關于吐蕃占領敦煌時期的文獻中,經常出現“奴”“婢”“奴仆”“奴戶”“奴隸”等詞,這些稱謂無疑表明了這部分群體在當時社會中較低的身份地位。但他們的地位低到何種程度?群體規模有多大?是否是當時社會中的主要生產形式?對此需要加以認真考證和分析。這是判斷當時敦煌地區社會形態的依據。
“奴”。P.T.1071號文書《狩獵傷人賠償律》中,有大量關于“奴”[4](P9-30)的記述。P.T.1080號文書《比丘尼為養女事訴狀》:“你比丘尼如能收養,視若女兒亦可,傭為女奴亦可。”[4](P48)P.T.1083號文書《據唐人部落稟帖批復的告牒:禁止抄掠漢戶沙州女子》載:“……其實,乃傭之為奴。”[4](P52)S.3287《氾卷》載:“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戶(氾國珎)死。妻(張念念)在。……奴(緊子)。奴(金剛)□。……[]部落已后新新舊生口、(定國)妻(王)死……奴(定奴)奴(弁奴)”[3](P377-378)等。
“婢”。S.3287《氾卷》記載“戶(索憲忠)妻(陰)……婢(目目)……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戶(氾國珎)死。妻(張念念)在。……婢(落娘)已上並論悉□息將去。□婢(善娘)婢(□□)……[]部落已后新新舊生口、(定國)妻(王)死……婢(宜娘)(榮娘)婢(星星)”[3](P376-378)。由此可見,婢作為索憲忠和氾國珎的家庭成員與其妻子兒女同樣登記于戶冊之上。
“奴仆”。P.T.1081號《關于吐谷渾莫賀延部落奴隸李央貝事訴狀》文書載:“張紀新稟:辰年,我從吐谷渾莫賀延部落之綺立當羅索(人名)處以五兩銀子買了名喚李央貝的男性奴仆。”[4](P49)《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記載:“南面直達卡果江多邦(Khar-go-ca(ng)-do-spong)之奴仆的耕地,兩地間有手砌圓石堆作地界標記。”[5](P316-317)“由此向前,沿著水渠直達以陡峭山石分開的吉笑加卡水渠的山谷,又有一個手砌的圓石堆為標志,穿過沙漠沙地,進入東南線上,直達達熱·席義奴仆的耕種地。”[5](P318)“十八個人一伙,有母親、父親、孩子、主人和奴仆,都生了病,或許他們因此身死,他們要求人們離開(dgol)(或譯:他們恭敬地要求人們與他們隔離)。”[5](P324)《吐蕃簡犢綜錄》中記載了“論努羅之奴仆已在……冬季田租之對半分成于兔年。”[6](P37)
“奴戶”。P.T.1071號文書中,有大量關于“奴戶”[4](P9-30)的表述。《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中載:“及至狗年(玄宗天寶五年,丙戌,公元746年)……征四茹牧場之“大料集”,收集已攤派之一切奴戶之賦稅,明令獎諭論·結桑達囊。是為一年。”[7](P118)
“奴隸”。《古藏文文獻中關于新疆的資料》中有:“在大斗軍(Dang-to-kun),墀扎、窮空、桑空三人已經分到了奴隸(Brang)”[5](P40)和“沙州比丘尼瓜氏吉玲之女奴瓜氏丹丹;比丘尼通吉”[5](P64)的記載。
(二)吐蕃社會“奴隸”相關問題的探討
關于吐蕃社會的“奴隸”問題探討,事關對吐蕃社會基本形態的認知,也關系著對吐蕃占領敦煌地區后社會性質變化的研究。
1、吐蕃社會的奴隸來源
奴隸通常指失去人身自由并被奴隸主任意驅使的人,其來源主要是戰俘、罪犯、破產平民、奴隸的后代等,他們在成為勞動工具的同時也被當成一種有價值的貨物進行贈賜與交易。關于吐蕃奴隸的文獻記載不在少數,但多在于統治階級向下屬賞賜的名錄,關于奴隸來源的直接記載幾乎很難見到,僅在敦煌出土的一些文書中能見到零星記載。
在關于吐蕃時期的文獻記載中,戰俘成為奴隸的記載并不多見。吐蕃政權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先后征服了青藏高原上的許多部族,如蘇毗、象雄、吐谷渾、黨項等,但并沒有將被征服的民眾變為各貴族的奴隸,而是保留其原有治理模式,對地方首領進行任命。如吐蕃征服蘇毗、象雄后,僅按茹、千戶進行重新編制,使其與吐蕃五茹的體制相類似,而且蘇毗還保留了小王。吐谷渾被吐蕃攻滅后,吐谷渾被編為萬戶部落,受吐蕃調遣,吐谷渾小王還成為吐蕃的高級官員。可見,大規模將戰俘變為奴隸的現象較少發生,而是派官員或者委托原來的統治者對征服地的居民進行管理。姜伯勤指出“官配手力一般由戰俘或罪人充當,其地位略近唐代的雜戶”[8](P17),也可以理解為戰俘和罪人一般都變成了身份類似于唐代雜戶的群體。如此,吐蕃社會鮮有戰俘變為奴隸現象的原因也就更加明朗了。
關于吐蕃社會文獻中零星出現的奴隸來源記載主要有以下幾種:
附作奴③。據P.3774《丑年(821年)十二月沙洲僧龍藏牒——為遺產分割糾紛》(以下簡稱P.3774號文書)載:“大兄初番和之日,齊周附父腳下,附作奴。”[9](P284)該文獻中明確交代了“奴”的一種來源,即“附作奴”。此處主動“附作奴”的可能性比較大,但在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里,是沒人愿意當奴隸的,更無人自愿變身為奴隸,故此處的“奴”應該比奴隸的地位要高。從其后文“便有差稅身役”的說法來看,這種“附作奴”的“奴”應該是不用承擔差稅身役的。所以,逃避差稅身役應是他附作奴的主要動機。
將收養子傭為奴。P.T.1080號文書載:“你比丘尼如能收養,視若女兒亦可,傭為女奴亦可。”[4](P48)此處記載了一貧人將無力撫養的女嬰送于一位比丘尼,至于送給比丘尼以后女嬰的身份地位,將由比丘尼來決定。通過后文“彼女亦不似以往賣力干活”[4](P48)的記載來看,該女名為收養子實則為奴仆,但此處又隱隱透露了該奴的特殊身份地位,即主人對已傭為奴的女子另謀出路而不賣力干活這一情況采取了上訴,而不能直接行使主人的生殺大權。官府最后的判詞“按照收養律令,不得自尋主人,仍照原有條例役使”[4](P48)也再次證明了她被役使的奴仆身份。
賣身為奴④。P.T.1081號文書載:“李央貝自證:我當初屬莫賀延部落,賣身契為幼年九歲時所立,名叫李央貝。”[4](P49)該文書較為詳細地記載了李央貝賣身為奴的時間(九歲時)和方法(立賣身契)。針對這一訴狀,最后的判詞為“嚴格按照賣身契所書內容處理。”[4](P50)足見這種賣身為奴的行為是受統治階層認可的,也是受當時法律保護的。而這種保護從另一方面說明,若某人想要賣身為奴,是需要嚴格按照一定程序來完成的,并不能隨意而為。
將抄掠的漢戶傭為奴。P.T.1083號文書載:“……每以婚配為借口,前來抄掠漢地沙州女子。其實,乃傭之為奴。”[4](P52)該文書記載了吐蕃、孫波與某些尚論長官衙署等將抄掠來的漢戶女子傭為奴的事件。從這一記載來看,將抄掠對象傭為奴的數量應該不少,但統治集團對此類現象進行了禁止,并強調說“不準如此搶劫已屬贊普之臣民”[4](P52),不能搶掠已屬于吐蕃占領地方的臣民為奴。
總體來看,以上幾種來源的奴隸數量都非常有限,而且有些來源途徑還受到當時統治階層的嚴格限制甚至禁止。
2、吐蕃社會奴隸身份的解除
通常,奴隸可以通過逃亡、贖身、立功等行為重新成為自由人,但這種機會一般都比較少。在吐蕃社會的文獻記載中,關于奴隸重新成為自由人的現象大致有以下幾類。
自由選擇。從文獻記載來看,吐蕃社會中的某些情況下,奴是可以自由選擇其歸屬的,如P.T.1071號文書中多處記載:“在放箭殺人者被處死后,另一半奴戶,愿為何人之奴,何人之民,可聽其自愿。”[4](P11)文書中交代了在有限的情況下,即在放箭殺人者被處死之后,奴戶可以自由選擇為何人之奴,何人之民,獲得更為自由的身份。而在P.T.1080號文書的判詞中,特別強調“不得自尋主人”[4](P48),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自尋主人的情形是存在的。這與奴隸制社會的殘酷統治是不符的。
析出為戶。P.3774號文書載:“大兄初番和之日,齊周附父腳下,附作奴。后至僉牟使上析出為戶,便有差稅身役,直至于今。”[9](P284)這里交代了“奴”的一種解除,即“析出為戶”。從文獻的敘述來看,析出為戶的目的在于攤派差稅身役以增加統治階級的收入。毫無疑問,這表明統治階級已經不需要依靠嚴酷的奴隸制勞作來實現剝削,而是變為更加隱秘的剝削方式,如此一來,奴隸也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社會大環境。
3、吐蕃社會被稱為“奴”等群體的權益
擁有土地。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建立在土地資料占有制基礎上的勞動關系直接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性質。吐蕃社會,被稱為奴的群體很多都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如前文所述的“奴仆”條中出現了奴仆擁有土地的現象,還指明了所擁有土地的類型即耕種地。
從敦煌文書的記載來看,吐蕃占領敦煌以后,大量漢族百姓不僅沒有被遷往他處,或者變成統治階層的奴隸,反而通過一些政令確保他們擁有住房和土地等,保持其小生產者的地位,如S.5812《丑年令狐大娘訴狀》載:“論悉諾息來日,百姓論宅舍不定,遂留方印,已后見住為主,不許再論者。又論莽羅新將方印來,于亭子處分百姓田園宅舍,亦不許侵奪論理。”[10](P116)這表明,在吐蕃占領敦煌初期,當地百姓因房屋和土地產權等問題發生過一些糾紛,吐蕃也曾派員進行處理。從文中也可以看出,處理糾紛的原則為“見住為主”,即基本上維持現狀,這是有利于實際居住者的,也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
在S.9156號文書《吐蕃年次未詳(九世紀前半)沙州諸戶口數地畝計簿》中[3](P417-418),因有大量百姓擁有土地的具體記載,一些學者將這份文書定性為寫于吐蕃占領時期的田冊殘卷,主要記錄了元琮、武朝副等21戶敦煌百姓的占田數。此外,S.4491號文書《吐蕃年次未詳(九世紀前半)沙州諸戶口數地畝計簿》[3](P418-420)也登錄了至少26戶⑤人家的田畝數。這些文獻中均記載的是某一戶百姓的占地情況,而不是某一奴隸主的占地面積。可見,以每戶人口為單位的土地分配是當時敦煌地區土地分配的主要形式。
擁有勞動工具。吐蕃社會的“奴仆”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的這些土地一般不會由別人來耕種,只能靠自己。如此,擁有耕種所必需的勞動工具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雖然這種情況還尚未在文獻記載中發現相關記載,但卻是可以肯定的。
擁有剩余的生活資料。吐蕃社會的“奴仆”既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也擁有相應的勞動工具開展自由勞作,那么他們在勞作后就會有產出,就能生產出些許剩余農產品,這可以從他們要承擔田租和賦稅的記載中得以證實,如“論努羅之奴仆已在……冬季田租之對半分成于兔年。”[6](P37)和“狗年……收集已派之一切奴戶之賦稅。”[11](P24-25)這兩個記載表明,“奴仆”“奴戶”是有能力靠自己的勞作生產一定數量農產品的,并且在完成田租和賦稅后還有部分產出以滿足自己的生存生活需要,否則他們根本不可能完成田租和賦稅這類任務,也不可能滿足上一階層的剝削,上一個階層更不可能將土地租給或分給他們耕種。當然,若沒有多余的產出,他們自己也無法繼續生存下去。
擁有家庭。“在大斗軍(Dang-to-kun),墀扎、窮空、桑空三人已經分到了奴隸(Brang),并為他們領取的奴隸及其家庭,登記了各自的名字,以及如何納稅(或受懲罰,或強制服役),均寫于一份共同的契約中……”[5](P40)從該文獻中“奴隸們”的表述來看,它記載了墀扎、穹恭、桑恭3人均分得了一定數量的奴隸,具體數量雖無從考證,但至少說明這批稱之為“奴隸”的人是不少的,而且他們還有家庭,更為關鍵的在于奴隸們的家庭是被統治階層認可的,否則沒必要對其進行登記。另外,在P.T.1071號文書《狩獵傷人賠償律》中,有大量關于“奴戶”的稱呼,這表明“奴隸”擁有家庭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馬克思認為:“在古代世界,城市連同屬于它的土地是一個經濟整體;而在日耳曼世界,單獨的住宅所在地就是一個經濟整體,這種住宅所在地本身僅僅在屬于它的土地上占據一個點;這并不是許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為獨立單位的家庭。”[12](P481)由此可見,這種擁有家庭的“奴隸”是一種擁有較大勞作自由的勞動者。S.5812《丑年令狐大娘訴狀》也明確記載了吐蕃占領敦煌以后為保障仍居住在敦煌地區居民住房的具體做法,即“見住為主”。可見,吐蕃占領敦煌以后,并不是將大量漢族百姓變成統治階層的奴隸或者遷往他處,而是通過政令確保其擁有安身之處,維持社會生產的穩定。
受到法律保護。《西藏通史》記載:“……后來,子松那布之妻巴曹氏對娘氏奴戶驕蠻橫暴,威嚇時加,恣意侮辱,且以婦女陰部辱咒之。娘·曾古心中不服,來到森波杰赤邦松面前,含冤負屈而訴苦,道:‘我實不愿為念氏之奴’”[13](P39)。從此處可見,吐蕃的“奴”是具有申訴權的。P.T.1071號《狩獵傷人賠償律》文書中載:“另一半奴戶,愿為誰之民,誰之奴可聽其自擇。”[4](P21)該文書是吐蕃時期的法律文書,其表述具有普遍的社會認可性,在對被處死者的奴戶進行處理時,允許其自由選擇為何人之奴,何人之民,說明在當時的法律規定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定的自由選擇權,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奴隸所不能享有的權利。敦煌吐蕃文書中關于此類現象的記載不在少數,說明其覆蓋的群體范圍是相當寬泛的。P.T.1083號《據唐人部落稟帖批復的告牒:禁止抄掠漢戶沙州女子》文書中載:“……每以婚配為借口,前來抄掠漢地沙州女子。其實,乃傭之為奴。為此,故向上峰陳報,不準如此搶劫已屬贊普之臣民。”[4](P52)可見,政府明確規定不允許吐蕃統治者抄掠被征服地方的居民作為奴隸,而要將其當作贊普的臣民一致看待。
4、吐蕃社會被稱為“奴”等群體的義務
繳納賦稅。吐蕃本部很早就建立起了基于牲畜和土地的賦稅征收體系,最具代表性的稅種為牛腿稅、田地貢賦和關卡稅,如“及至牛年(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贊普駐于輾噶爾,大論東贊于‘祜’定牛腿稅,(肉類賦稅)。達延莽布支征收農田貢賦。”[7](P101)“及至龍年(高宗顯慶元年,丙辰,公元656年),贊普駐于美爾蓋,大論東贊于‘仄木’之瑪爾地方,征收牛腿稅。”[7](P102)“及至蛇年(高宗總章二年,己巳,公元669年),贊普駐于悉立之都那,吐谷渾諸部前來致禮,征其入貢賦稅。”[7](P103)“及至龍年(中宗嗣圣九年,太后長壽元年,壬辰,公元692年),多思麻之冬會于甲木細噶爾舉行,收‘蘇毗部’(孫波)之關卡稅。”[7](P107)
吐蕃社會的納稅主體較為明確,一般以戶為納稅單位,主要為牧戶和奴戶。如“及至雞年(中宗景龍三年,己酉,公元709年),贊普駐于泥婆羅。……征調腰茹牧戶大料集。”[7](P110)“及至狗年(玄宗天寶五年,丙戌,公元746年),……征四茹牧場之‘大料集’,收集已攤派之一切奴戶之賦稅,明令獎諭論·結桑達囊。”[7](P118)當然,還有其他的土地租佃戶類,如“及至馬年(玄宗開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冬,贊普駐于札瑪牙帳。征三茹之王田全部地畝賦稅、草稅。”[7](P112)“及至羊年(玄宗開元七年,己未,公元719年),征集“羊同”與“瑪爾”之青壯兵丁,埃·芒夏木達則布征集大藏之王田土地貢賦。”[7](P112-113)以上記載中沒有明確納稅主體的戶類,但明確交代了他們耕種的是王田,而且需要納稅,這肯定不同于牧戶和奴戶。另一材料中還提到“宮廷直屬戶”,“及至虎年(玄宗開元十三年,丙寅,公元726年),春,大論芒夏木于島兒集會議盟,訂立岸本之職權,征宮廷直屬戶稅賦。”[7](P114)雖然此處的“宮廷直屬戶”具體范圍不得而知,但肯定有別于牧戶和奴戶。千佛洞的材料中有“并為他們領取的奴隸及其家庭,登記了各自的名字,以及如何納稅(或受懲罰,或強制服役),均寫于一份共同的契約中……”[5](P40)的記載。可見,除了普通百姓需要承擔貢賦外,奴戶也要承擔相應的賦稅,并且以契約為憑,這一點從他們擁有土地的事實可以肯定。因為“除去戶稅外,吐蕃統治下的敦煌官府又向部落民戶征收‘地子’……這時的‘地子’實際上就是土地稅。”[14](P180-181)。
吐蕃在賦稅征收方面有一套較為成熟的流程,即先確定貢賦,然后再行征收,如“及至狗年(中宗嗣圣三年,太后垂拱二年,丙戌,公元686年),……冬,于查瑪塘集會議盟。定襄·蒙恰德田地之貢賦。”[7](P105-106)“及至豬年(中宗嗣圣四年,太后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冬,定大藏之地畝稅賦。”[7](P106)“及至虎年(中宗嗣圣七年,太后天授元年,庚寅,公元690年),……噶爾·沒陵贊藏頓與巴曹·野贊通保二人征收腰茹之地畝賦稅。”[7](P106)隨著賦稅承載主體的不斷變化,賦稅征收一段時間以后,政府還會對賦稅情況進行清查,“及至兔年……清理土地賦稅并統計絕戶數字。”[7](P106)從“及至狗年……嚴切詔告,減輕庶民黔首之賦稅”[7](P118)可見,吐蕃統治階層為了緩和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曾采取過減稅的措施,這對維持以稅賦為基礎的剝削方式是極其重要的。
以戶為單位支差。文獻記載中出勤、應征戶、戶差等詞匯清晰地表明了當時一種以戶為單位的剝削方式,如“一頭空(stong,不能馱)的懷孕驢折銀四兩,一頭公驢銀三兩,一頭小驢銀二兩。雇費從出勤之日起,每天(per diem)糧一藏升(bre),如不付糧,也可折作應征戶的戶差。姜孜(rgyangrtse)處的公牛和驢子(已死),賠償價如上述。支付雇費糧半馱。”[5](P326)這種以戶為單位的剝削方式有助于理解吐蕃文獻中為何會有相當數量關于奴戶的記載。
三、吐蕃對敦煌的人口管理
吐蕃政權在敦煌確立統治地位以后,不久便開始清查戶口和統計人口,并編訂名簿,敦煌遂出現不少關于戶籍的名簿,如官府役人名簿和寺院僧尼名簿等。這表明,吐蕃政府在敦煌地區的人口管理政策是比較嚴格和完善的。
清查戶口。P.3774號文書載:“大兄初番和之日,齊周附父腳下,附作奴。后至僉牟使上析出為戶,便有差稅身役,直至于今。”[9](P284)“番和之日”,即“丙寅年”,即786年[3](P398)。文中所言“僉牟使”,即吐蕃清查戶籍的官員,齊周也因吐蕃官員開展戶口清查而析出為戶,開始承擔差稅身役,其具體時間可據S.2729號《吐蕃辰年(788)三月沙洲僧尼部落米浄詟牒》(筭使勘牌子⑥歷)所載“辰年三月五日,算使論悉諾羅接謨勘牌子歷”[3](P358)做出初步判斷。陳國燦指出,“此勘牌子的‘接謨’,實即‘僉牟’,……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即780)至貞元十五年(己卯即799)間,唯有一個辰年——戊辰,即公元788年。”[14](P6)故而,齊周析出為戶,開始承擔賦稅身役的時間應該為公元788年。這說明吐蕃在這一年開展了對敦煌居民戶籍的清查工作。
編籍造冊。S.2729號文書中詳細記載了僧尼名、僧尼數、僧人總數、尼姑總數及所屬寺名和部分死亡僧尼的死亡時間[3](P358-362),這是吐蕃占領敦煌之后,進行僧尼統計和造冊的記錄,是較早的戶口勘查原始檔案。由此看來,吐蕃占領敦煌后還是高度重視對當地人口管理的,尤其是從一開始就對敦煌居民的戶口進行清查和造冊。
后來,吐蕃在敦煌的戶籍制度隨著鄉里制度的廢除和部落制度的確立而有所改變,即戶籍制度按照“部落的體制編制”。《氾卷》對此進行了記載,并以午年為界線,將在籍人口分為新、舊口,如“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生口”[3](P376)、“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3](P377)等。說明午年曾針對擘三部落的居民編制“牌子”,即敦煌陷蕃初期擘三部落的戶籍。金瀅坤認為S.3287《氾卷》是一件擘三部落左二將五戶百姓的戶口狀,明細各戶主對戶口變動情況的申報,相當于唐代的手實[15](P120)。關于《氾卷》記載內容的時間問題,藤枝晃認為《氾卷》寫于公元832年[3](P378)。文書題目中“子年”和內容中“午年”所對應的具體時間,楊銘認為“午年”為790年,“子年”則以808(戊子)年為妥。”[16](P64)可見,此時關于戶籍中的內容更為豐富和詳細,管理也日趨完善。
在戶口清查和編籍造冊的基礎上,為了保證戶籍冊中人口的穩定,吐蕃當局在處理敦煌居民住房和土地糾紛方面采取了有利于居民穩定生活的做法,即S.5812(G.7371)號文書⑦中記載的宅舍以見住為主和田園宅舍不許侵奪論理[10](P116)。這一方面使易主后的敦煌社會糾紛解決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也保障敦煌居民能在一定范圍內穩定生活。
對P.3774、S.2729和S.3287號文書所載內容的分析,可見吐蕃在占領敦煌以后近30年的時間里,先后開展了清查戶口工作、將吐蕃本部的戶籍制度和敦煌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建立了適應“部落——將”的編戶制度,進而對居民進行分部落編籍造冊,內容大致包含居民現在的將籍、戶主姓名、新舊口之別、新增或減少人口及其原因、戶內成員關系等;另外,在開展戶口清查統計時,要求居民必須如實申報,不得隱漏,而且還要作保證,足見吐蕃當局在敦煌地區的戶籍制度之完善。通過加強對敦煌居民的戶籍管理,吐蕃當局有效地控制了敦煌地區的居民,進而為其征發賦稅、派遣勞役提供了基礎支撐,也為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吐蕃政權對寺院屬戶進行編戶,推行寺戶制度,使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寺院經濟得到了穩固發展,從而也有效地把敦煌佛教納入其統治體系之中。
結語
吐蕃占領敦煌這一歷史事件,在沈下賢等一些以中原王朝為正統的文人看來,情感上是難以接受的。他們認為吐蕃在其占領下的敦煌必定推行野蠻的奴隸制度,但是通過多方面分析發現,事實并非如此。一方面,從吐蕃本土社會來看,吐蕃在征戰過程中并未出現大規模的戰俘奴隸;勞作過程中也并非主要役使奴隸,剝削形式主要是建立在財產基礎上的賦稅征收。關于“奴”等群體,非但在文獻記載中未找到有力的證據說明他們就是嚴格意義上會說話的工具,且發現他們有家庭、有財產,還要承擔賦稅,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時法律的保護。另一方面,從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社會狀況來看,吐蕃占領敦煌初期就非常重視人口管理,開展戶口清查,編制戶籍,調解財產糾紛,并用法令的形式將處理糾紛的原則固定下來,確保當地居民的穩定;針對部分吐蕃貴族抄掠敦煌原住民的現象,吐蕃統治階層還以政令的形式嚴格限制甚至禁止抄掠被占領地方的居民為奴,并強調他們“已屬贊普之臣民。”[4](P52)故而才有“流沙僧俗,敢荷殊恩,百姓得入行人部落,標其籍信,皆因為申贊普,所以綸旨垂邊”⑧的贊語。誠如陳慶英所言,“蓋因此處唐人所謂‘奴婢’,乃是指被占之地的唐人在異族統治下被奴役的地位而言,并不能與科學意義上的‘奴隸’畫等號。”[17](P106-107)盡管當時的唐朝臣民從情感上不接受吐蕃占領敦煌地區這一事實,對此有所貶損,但畢竟事實勝于雄辯,吐蕃在占領敦煌以后,并未在當地實行踐踏之能事的政策——將原住居民變身為奴,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敦煌地區進行有效管理,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注 釋]
①此處僅指被稱為“奴”“婢”“奴仆”“奴戶”“奴隸”的群體。
②有關敦煌何時陷于吐蕃,歷來有多種說法,而學術界采用較多的有兩種,即:戴密微的787年“陷蕃”說和藤枝晃等認為的“建中二年(781)陷于西蕃”說。筆者在參考各家之說的基礎上,對部分事例進行分析后認為吐蕃于781年攻陷敦煌較為合理。
③筆者理解為依附于某戶或某人的“奴”。
④筆者理解為通過某種官方認可的程序將某人賣身為奴。
⑤此處26戶包含能明確戶主名字的22戶,22戶中又有3個戶主下被標為“兩戶”,前半部文獻不全的按1戶統計。
⑥史書中將這種記載詳盡的戶籍稱之為“牌子”。
⑦關于S.5812號文書的年代問題,藤枝晃認為文書所落丑年是指公元833年,筆者結合文書中“今經一十八年”的表述,大致判斷論悉諾息和論莽羅新兩位官員解決宅舍、田園糾紛的時間為公元815年左右。
⑧P.2449號卷子背面錄釋子文。《敦煌遺書總目錄索引》錄其正面,題作《元始應變歷化經》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