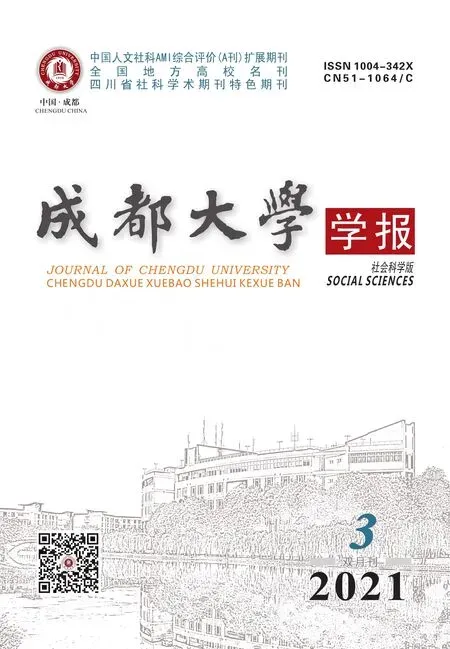舊體紀行詩和新型國際團結
——淺談郭沫若20世紀60年代文化政治實踐的一側面
王 璞
(美國布蘭代斯大學 德語、俄語和亞洲語言文學系,美國 馬薩諸塞州 諸波士頓 MA02090)
一、一組問題的提出
1964年7月15日,郭沫若(1892-1978)“率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和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代表團”飛抵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首都河內,參加日內瓦協議簽訂十周年紀念活動。在北越南訪問期間,郭沫若屢屢成詩。其中,《穆穆篇》記述在主席府拜訪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以“五言古”出之。在游覽風景名勝區下龍灣時,“應船員索求”[1]2004,作《舟游下龍灣》,這是一首詩行整齊的押韻白話新詩。7月21日至23日,又連作八首近體七律,是為《下龍灣》組詩。7月24日結束訪問回國后,訪越詩篇相繼發表(有些即興之題則始終未正式發表),以上提到的幾種后收入1977年出版的《沫若詩詞選》。這樣一批紀行詩,我們今天如何解讀?在本文中,筆者想聚焦郭沫若晚年在反帝、反殖的國際交往活動和革命團結運動中所形成的紀行詩寫作(尤其是其中的舊體因素),提出關于20世紀60年代文化政治實踐的一組互相糾纏的問題。
首先,還是從研究郭沫若在新中國成立后作品的難題性說起吧。筆者關于郭沫若著譯的英文專著(2018年出版)曾試圖貫通“新文學三十年”(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十年)的郭沫若和晚期(包括“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郭沫若,但仍遇到些許困難[2]。本來,在中國革命及文化的進程中,這兩個“三十年”的既矛盾又連環的關系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理論闡發,形成了一個整體歷史視野,不過在郭沫若這一貫穿性人物的個案上,新中國成立后作品的相關研究仍相對單薄。尤為關鍵的是,我們能否針對這一批富有爭議性的文本,找到更有效的解讀角度和方法?
眾所周知,在上面提到的這兩個“三十年”的歷程中,不僅中國革命的文化態勢始終處于激烈流動之中,而且郭沫若在其中的占位和身份也有多次轉化。從20世紀40年代他被中國共產黨確立為“新文化的旗手”開始,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他在中國文化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處的位置,他的實踐活動的樣態乃至性質,都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在今天的輿論場中,卻常有這樣的聲音,即把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的身份聯想為“御用文人”,把他的大量詩詞比附為“館閣之體”,或者把他的官方角色形容為“文化屏風”。這樣的說法未必能真正觸及這批作品的歷史性。另有學者——比如美國的文棣(Wendy Larson)教授則曾指出郭沫若在革命新政權內部所代理的“紀念性”文化功能[3]152。目前研究難點或許在于,如何從“應時”“應景”“應邀”的一面出發,進入文本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的文本構造。而同樣眾所周知的是,作為新中國文化界領袖的郭沫若的“紀念性”寫作常以舊體詩詞形式出之(一部分收入《沫若詩詞選》等集,散佚作品也不在少數)。這種對舊體詩詞的借重,至少可追溯到抗戰時期國統區政治中的“聲韻共同體”[4],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又深深聯系到郭沫若對毛澤東詩詞的解讀以及和毛澤東的詩詞唱和,以至于成為社會主義“文化革命”中的“民族形式”乃至象征性話語行動。正如拙著中所論及,郭沫若作為“開一代詩風”的白話新詩奠基人之一,后來成為舊體詩詞“革命化”的高產作者,這一看似悖論的發展本身就表征了革命文化的復雜路徑,更確立了一種社會主義文化人的特殊歷史存在模式。所謂舊形式,反而意味著新的文化政治實踐,我們還必須透過“內容的形式”探討“形式的內容”[5]。在這里,新和舊,社會主義和詩教遺產,官方紀念功能和革命話語生產,政治身份和文人修養,高級文化交往和“喜聞樂見”的普及性,乃至于國內政治和國際形勢,等等,一系列問題已然彼此交織。
在拙著(及相關中文論文)中,筆者只以郭—毛唱和為線索,對郭沫若晚年舊體詩詞寫作略做梳理[2]271-296。此后,筆者也有意轉向英文專著寫作中“掛一漏萬”、沒有充分涉及的郭沫若作品,再做專題研究。出于對旅行書寫的持續關注,筆者發表了討論郭沫若1945年訪蘇日記的文章——《旅行書寫與社會主義想象——以郭沫若〈蘇聯紀行〉為中心》[6]。一方面是革命時代的旅行文學,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文化政治,在這兩個線索的交點上,郭沫若新中國成立后的紀行詩——尤其是舊體紀行詩——作為一個有待解讀的現象就凸顯出來了。本來,紀游詩在古今中外都是常見的文類,新文化中對異地、異國、異文化的文學處理也蔚為大觀,但即便學界如今對中國文學現代性中的舊體詩問題進行了越來越多的討論,晚期郭沫若的紀行詩仍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對象。這不僅因為其中的新舊體并置(乃至雜糅),更是緣于它超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般意義生成和交流機制,而深度介入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交往——尤其是文化外交——乃至全球革命團結的政治建構。
自從1949年當選文聯主席起,郭沫若長期以進步文化界領袖的形象出現,但如果細察,我們就會發覺,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壇激烈的斗爭和接二連三的運動、辯論之中,這位領袖并非總是處于這一重要而敏感的場域的中心。相反,翻檢《郭沫若年譜長編》便知,同一時期,郭沫若(先后)以中國科學院院長、國(政)務院副總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等身份,承擔著豐富的國際交往任務,所從事的外交活動相當繁忙,這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尤其明顯,簡直是他工作的主要部分。他不僅參與了反帝、反殖的革命外交路線的展開和變動的全過程,而且更可以說,他所代表的文化外交形成了新中國國際交往的一大特色。反過來,脫離了這樣一種新中國所力圖形塑的國際革命政治,作為外交活動一部分的紀行詩也就無法得到有效理解。
這也要求我們越出當代文學史的“國內”框架而更加重視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的國際性。越來越多的學者重新認識到,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文學也是深刻地參與到一種(遠不同于今日全球想象的)“世界文化”的生產和構建之中。這其中不僅包括中國和蘇聯、東歐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多元交往,還包括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內部的泛左翼文學的譯介和關注,而且突出體現于亞非拉的新興文化政治交流,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反帝反殖運動所形成的“第三世界”的團結中,中國更扮演著極為重要但又變動乃至矛盾的角色。中國和亞非拉世界的文化外交,也產生了豐富的旅行書寫,比如,艾青20世紀50年代訪問拉美(為智利大詩人聶魯達祝壽)留下的杰出新詩作品;而郭沫若的紀行詩則是其中又一例,卻體現出舊體詩傾向。這些作品都需要從社會主義文化機制、革命地緣和國際團結等多重角度來解讀和分析。此外,我們后面的梳理將表明,郭沫若外交實踐和紀游寫作見證了社會主義中國對反帝、反殖乃至于“反修”的國際政治的探尋,而且在60年代愈發轉向“亞非團結”主題,標記出中國在“全球六十年代”中獨特而能動的態勢。所謂“全球60年代”,是近年來國際學界所常用的文化分期概念,強調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政治變革具有全球聯動的特征。弗雷德里克·杰姆遜(Fredric Jameson)在“斷代”說中很早就點明,20世紀60年代的全球文化政治是以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崛起為基本驅動的[7]。而越南戰爭就是這一全球聯動的中心節點。郭沫若訪越期間的詩作,在形式、內容和文化政治動向上都是一次集中體現。社會主義文化中的舊詩體、旅行書寫中的新型國際團結、革命外交和“六十年代”的世界建構——這便是本文所要提出的一組問題和所要追求的視角轉變。
二、外交紀行:從“國際精神”到“五洲震蕩”
旅行意味著自我和遠方遠人的相遇,旅行書寫是這一相遇的文本性“產出和記錄”[8]10。1945年6月,郭沫若作為當時的中蘇文化協會研究委員會主任和中國進步文化的代表人物,受蘇聯科學院邀請,出訪剛剛戰勝納粹德國而尚未對日宣戰的蘇聯。他是在游蘇期間,迎來了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6]。回國后他發表了《蘇聯紀行》(1946年,再版改題為《蘇聯五十天》)。這可以說是郭沫若文化外交及其紀游文本實踐的一段前史。新中國成立未久,毛主席經過艱難談判,于1950年2月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開啟了外交上“一邊倒”的階段。而就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次日,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告成立,郭沫若隨即當選為其全國委員會主席。從那時起,他開始在中蘇結盟的外交格局下全力參與維護世界和平、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國際運動(這一運動當時確定以蘇聯為主導)。1951年10月底,郭沫若率代表團經莫斯科赴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二屆會議,11月2日擔任會議執行主席。在維也納時,曾作白話新詩《多謝》,而在歸途中,和越南代表黎廷探博士同車,奉酬而作七律四首《西伯利亞車中》——“和平奔走幸同車,國際精神四海家”[9]62。這樣的政治紀程可以說是郭沫若外交紀行詩的端倪。
同年底,郭沫若獲得“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獎。在20世紀50年代,郭沫若所謂的“國際精神”,有兩個重要維度。其一,郭沫若強調,中蘇的聯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毛澤東初次訪蘇并和斯大林會談時,郭沫若頌之為“一個東方又加上一個東方”的“史無前例的大事”:
四萬萬七千余萬同兩萬萬,
全人類三分之一結成了聯盟,
由兩只最有力的慈祥的巨手,
緊握在歐亞大陸的中心。[9]12-13
到了1957年,他又這樣書寫中蘇團結:“八億人同甘共苦,/使和平壓倒戰魔”[9]182。
但如果說蘇聯是冷戰意義上的“東方”,那么中國作為“東方”還代表著亞細亞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反抗殖民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的新興力量。所以,和黎廷探同車穿過蘇聯,探討朝鮮、越南革命形勢,強調以斗爭求和平,并酬唱成篇,這樣的紀行場景本身就展示出一種亞洲團結的視野。這是“國際精神”所蘊含的另一維度,而且這一維度將越來越重要。郭沫若有詩作記述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于1952年在北京籌備和召開。而第一次亞非會議(萬隆)在1955年的舉行,又產生了以和平共處為原則的“萬隆精神”(“種族反歧視,萬隆又一章”[9]231)。萬隆產生的亞非作家會議成為一個新平臺。1958年初,郭沫若率團出席在埃及舉行的亞非團結大會,同一年,茅盾率團參加了在蘇聯塔什干舉行的亞非作家會議。
這兩個維度在50年代的交織決定了郭沫若當時的國際活動軌跡和紀行詩寫作。一方面,在為中蘇友好、世界和平奔走的過程中,郭沫若訪問過蘇聯、中歐、東歐、北歐,留下了不少詩篇,如果說在政治抒情時還常用白話新詩體,那么游歷即筆時,舊體詩的傾向越來越顯著。1955年7月郭沫若在芬蘭赫爾辛基主持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曾作五律《赫爾辛基》,記述在北歐千湖國度過了“約翰節”:“中夏逢佳節,和平發浩歌。”[10]661959年出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順訪丹麥、蘇聯,郭沫若自稱“八日三都”,在律詩《游北歐詩四首》中記述下泛舟海上與丹麥使館人員暢談蔡文姬的大好情致:“汽艇豪游海上馳,負暄暢話蔡文姬。”[10]57而這類舊體紀行作品中,最有名的或許還是《游里加湖》組詩。1954年5月,參加完在(東)柏林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之后,郭沫若于6月初訪問莫斯科,由于6月下旬還要去斯德哥爾摩參加會議,所以“接受蘇聯和平大會招待,往格魯吉亞旅行”[1]1490。在格魯吉亞避暑期間,郭沫若于12日游覽里加湖。里加湖,通譯“里察湖”,為格魯吉亞境內高加索山脈群峰峽谷中的天然湖泊,“群峭削如壁,藍池百米深”[10]69,為風景勝地,離黑海避暑地加格拉亦不遠。里加湖“風景清奇”[1]1491,顯然激發了郭沫若的游興,給他留下了極美好印象,五絕組詩《游里加湖》先錄入散文游記,共計二十首。其中第六首為:“愛山還愛海?山海皆愛之。山體森嚴律,海是自由詩。”[10]72從對高加索山和黑海的兼愛,論到對格律詩和自由詩的兼收,這其實和郭沫若早期“一元多體”的泛神論詩歌觀一脈相承[11],也是對自己晚期新舊詩體并蓄的一種內嵌式說明,更重要的是,還流露出一種如山海般廣闊的世界情懷。
另一方面,在反帝、反殖的世界新興力量團結這一維度上,我們可以讀到《游埃及雜吟十二首》中的亞非新誼:“兄弟亞非國,受災歷有年。求同情不異,反帝志彌堅。”[9]231在1957年底郭沫若參加在開羅舉行的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時,埃及納賽爾政府剛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取得對英法老牌殖民主義大國的局部勝利,中國代表團不僅大受歡迎,還參加了塞得港的“勝利節”,夜游尼羅河,體驗著“上下六千年”的古史和新變。《訪問古巴》五首把外交視野從亞非引申到了拉丁美洲。在古巴革命和古巴導彈危機后訪問這一加勒比海島國,這是郭沫若一生中唯一一次西半球旅程:“景物新奇愛古巴,蔗田標穗似蘆花。”[10]242新奇之中,他發現古巴松樹河谷如同桂林風景——“陽朔風光照眼臨”[10]242——并思考著帝國主義的歷史。他見證了古巴和美國正式斷交:“使館高樓深鎖定,女兵圍裹抱沖鋒。”[10]244又在歸途飛渡大西洋,體驗了“游仙”般的世界旅程:“朝別古巴含可可,夕臨瑞士看《康康》。前人幻擬游仙夢,今日游仙事等常。”[10]244這是又一種世界感。
不過,也就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這兩條原本合一的路線正發生劇烈的變化。中蘇之間的分歧漸次浮現,1958年,郭沫若為中蘇北京會談公報歡呼,繼續強調中蘇友誼是世界和平的核心,但同時在紀念《莫斯科宣言》一周年時,卻已經提出要警惕猶大式的“修正主義”[9]398。這是因為,中國所倡導的世界和平,是東風壓倒西風的和平,是以反帝斗爭為原則的和平,是以亞非拉革命為前提的和平:“亞洲人民站起來了!/非洲人民站起來了!/拉丁美洲人民站起來了!”[10]373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反帝斗爭起著“連鎖反應”,世界進入“五洲震蕩風雷激”的60年代。60年代初的國際孤立中,毛澤東堅持中國獨立自主,“天垮下來擎得起”,便是“滄海橫流”時顯出的“英雄本色”,而中蘇論戰則是“堅持原則”[10]119,“爭正誼”“明真相”[12]16。郭沫若的任務隨之轉變,而有意思的是,在表達“反修正,斥新殖”[12]14這一對不可分割的主題時,他在60年代的詩作愈發傾向舊體。“太陽出,冰山滴。真金在,豈銷鑠”[10]119——郭沫若的《一九六三元旦抒懷》引起毛澤東和詩,也正因為它標記出社會主義的中國走出了一個國內和國際的困難期,繼續探尋革命新路。“天難撓,人難枉;帝難鎖,修難謗”[12]30-31。反帝、反殖、反修合為一體,作為中國對亞非團結的新定義、新訴求,可以說是“全球六十年代”最富爭議性的動向之一。在這樣一個“五洲震蕩”的“連鎖”[10]373之上,越南顯然是重要關節:第一,它是前殖民地反帝斗爭的新中心,是最強大帝國主義美國傾力投入的新戰場,是全世界進步力量矚目所在,雖遠卻近;第二,它緊鄰著新中國的南大門,戰爭并不遙遠;第三,領導民族和人民解放事業的越南共產黨和中蘇都有良好關系。郭沫若外交活動和紀行寫作從新中國成立到60年代初所形成的軌跡,為我們理解他60年代文化政治實踐提供了富有縱深感的背景,也引導我們聚焦到1964年的訪越作品上來。
三、訪越作品和“全球六十年代”的革命團結
1964年,郭沫若已經72歲。這一年對中國和世界都是不平凡的一年。新中國和西方大國法國建交,又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還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越南戰爭也在這一年全面升級。在肯尼迪遇刺后接任美國總統的約翰遜本已擴大美國對越戰的參與,試圖助南越軍事獨裁政府扼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裝力量,而七八月間的東京灣事件,更是整個戰爭的分水嶺之一,事態陡然升級,美國確定了直接介入、冒險豪賭的方針。到1965年初,美國已完成從“特種作戰”到“地面作戰”的轉變和大部署,而在空中和海上,對北越的殘暴地毯式轟炸也“滾雷”般開始,戰火燒到中國邊境和海疆。也是在1964年,全球范圍內的反戰運動和支援越南人民的行動已經興起。越南問題構成了當時郭沫若外交活動的一個重大方面。
郭沫若率團訪問越南,是在東京灣事件之前不久。《穆穆篇》這首五言古詩,記錄了訪問主席府、拜會胡志明的難忘經過。河內巴亭廣場的主席府,是殖民地時代建筑,而富有平民精神和苦行品格的領袖胡志明,卻拒絕住進這豪華的歐式宮廷,只以它作官方接待活動之用,自己安居在后花園的棚屋。《穆穆篇》雖記異國風致和外交活動,但充滿了親切感,這當然是因為胡志明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老朋友,和許多中國革命領袖有深交,并有很高的中國文化修養;雖然郭沫若是第一次到訪河內,但和胡志明早有北京交往之誼。《穆穆篇》所寫出的賓主交流,處處體現出親切與新奇的美好融合。
首先,雖是外交場合,但“胡老信步來”[12]45,直接把郭老引入了自己所住的后花園。好奇的郭沫若先是被林間孔雀所吸引,后來和胡老相擁,一同觀賞、喂食池塘中魚,這先入庭院的一幕幕,既有越南風情,又充盈著跨國深誼,甚至還透出兩國文化人所共享的“園林雅趣”。庭院之樂稍罷,胡志明才請郭沫若參觀其居室:“邀我至其居,其居如珈藍。胡老自設計,仿照舊時庵。舊庵乃竹制,革命時所潛。今雖易以木,未改村舍觀。下有無壁殿,四面皆垂簾。中橫長案一,賓主坐寒暄。”[12]46胡志明居室是樸素甚至有些簡陋的,這段描寫正從側面成功塑造了他艱苦奮斗、貼近勞苦大眾的人民領袖形象。以“珈藍”“舊庵”為比附,在中文語境中都有寡欲、苦行的寓意,而詩人對越式室內布置的觀察,也可謂認真細致。詩行展開至此,我們也可以感到詩人和領袖之間關系進一步拉近,革命情誼也被比附為這樸實無華的居室——“無文至斑斕”。詩人又“脫靴上樓軒”,走入“東寢”“西齋”。“入齋盤膝坐,坐亦無蒲團。回欄繞四周,素樸非雕鐫。清風欣然來,好鳥奏笙弦。”[12]46-47如果說以“無文”為至色,已有以道家為喻的端倪,那么,這里就幾乎是用一種返璞歸真的清靜美學來渲染革命風范。接下來,詩人和胡志明回憶兩年前的交往:“胡老至北京,同觀《武則天》。”眾所周知,《武則天》是郭沫若在新中國成立后創作的重要歷史劇。而胡志明仍留著當時郭沫若夫人所贈之扇,而且上面還有郭沫若手書毛澤東詞《沁園春·雪》:“上題沁園春,詠雪之名篇。”[12]47兩人的情誼有了更多的交織,也形成了兩國團結革命的一個文化共通體。
至此,郭沫若才轉向主席府的主體宮室:“正廳西式樓,遙看頗莊嚴。昔為殖民宮,今操專政權。”[12]47-48這樣的歷史鼎革、政治翻轉,又立刻融入了胡志明的悠閑幽默和革命樂觀精神:“胡老指顧告,意態何悠閑:在此曾判罪,梟首當懸竿。不意此頭顱,至今尚安全。”[12]48胡志明帶著中國友人從后花園來到正廳,是因為招待晚宴要在這從前的“殖民宮”、現在的主席府舉行。全詩以暢寫盛筵上的熱烈氣氛作結。在筆者看來,《穆穆篇》有一點遠勝過我們上面提到的外訪其他國家的紀行詩,那就是,它一方面遠比其他作品顯得親切、不拘束、放松,革命情誼真實可感;另一方面,對異國文化風情的見聞、對異國革命精神的體察又不失新奇、細致、豐富。親切感和新鮮感的辯證統一,也可以說是旅行書寫所企及的革命團結新境界,或許也只在中越兩國歷史、文化、革命的特殊關系情境中才成為可能吧。
值得一提的還有據《郭沫若年譜長編》,郭沫若在訪問主席府時,有白話詩《孔雀》《魚和鳥》二首[1]2002,似為即興、即景而作,而《穆穆篇》稍后作。相比較可知,兩首從未發表的白話新詩,在詩意詩情上,可謂是后來成篇的五言古詩的原始質料。這樣白話新詩先作而為后作舊體詩提供準備的“作詩法”,我們在郭沫若關于下龍灣的紀行詩中也將看到。
在河內參加完紀念日內瓦協議簽訂十周年的系列集會之后,郭沫若有了游覽下龍灣的機會。下龍灣在越南東北部,為東京灣一部分,島嶼星羅,如“萬朵花”[12]50,是越南風景勝地,今已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和在格魯吉亞里加湖時一樣,郭沫若顯然為這里的奇異美景所折服并驚喜。在《下龍灣(七律八首)》中,一方面,就像他在里加湖看到了“陽朔風光”一樣,詩人也發現了越南奇境和桂林的相似:“誰移桂林來海上?”[12]50通過這樣的比附,越南風光得到了中國式的辨認,甚至“中國化”了,畢竟只有通過自身的語言文化才能認識異域。但另一方面,八首中又充滿了“驚奇”“驚異”:“人驚北越繡天涯”“下龍灣景一奇詩”“倍覺下龍風物奇”[12]50-51。親切和奇異的辯證法,匯入對異域美景的欣賞角度。詩人把下龍灣比作一首詩,他又聯想到了“黃山云海”,而中國的“天池”也成了“硯池”[12]50,一幅中越自然風情的比較、互美的壯闊圖景由此展開,更蘊含中越團結的地緣政治美學。
詩人享受著沁人肺腑的“習習熏風”,“飽吃鮮龍眼”,同時也學習考察著下龍灣的歷史和現實。在這八首律詩中,詩人講到蒙元征越的海軍在下龍灣覆滅,日寇在下龍灣沉船,把越南人民抗擊外敵的歷史往事當作“殷鑒”,聯系到越南戰爭的現實:“泰萊今日烏馬爾,美帝當年蒙古王。”[12]52烏馬爾為元軍統帥,而泰萊系美國駐南越大使。在下龍灣,詩人也和越南民眾一起慶祝南方戰場上的新戰果,而且認為下龍灣多變的天氣也在和人間通感,將毛澤東詞的修辭信手拈來,化用在郭沫若的自己的詩作中:“北地歡騰新生里,南中掃蕩偽軍營。想是下龍同感奮,灣頭一出淚盆傾。”[12]52
在這種反帝、反殖、團結抗爭的革命抒寫中,又加入了新的內容:“反修正主義”。在越南所舉辦的國際活動中,當時已經事實上決裂的中蘇兩國不可能不同臺。如前述,胡志明所領導的越南和中蘇兩大黨都保持著友好關系,甚至對中蘇論戰采取調停態度。游覽下龍灣的客人中,也有蘇聯代表。律詩之四,郭沫若寫灣上諸峰——“仙女三千盡害羞,銀紗罩面怕凝眸”——頗得雨霧中朦朧綽約之美,并在頷聯用唐詩之典:“懶卷珠簾上玉鉤”。頸聯寫天色放晴,日照當頭,卻提到所謂“兩全人”。參詩人自注可知,“兩全”指“全民國家和全民黨”[12]53,兩全人即“蘇修人士”。也就是說,等到“蘇修人士”掃興離開,天立刻放晴,“仙女三千”才愿展露真容:“原來回避非無故,只見英雄不見修。”[12]51英雄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指。越南仙女認得出誰是真英雄、誰是“修正主義”——在理解越南立場的同時,郭沫若要為中越團結主題賦予時代的新指向。
《下龍灣》組詩以“骨連血肉山連水,五角星旗萬古紅”[12]53作結,強調的不僅是一種鄰邦友好,更是新型的革命團結。同樣,白話新詩體的《舟游下龍灣》作于七律組詩之前,即興詠題,在意象、詩情、典故、修辭、政治內容上都可以看作是《下龍灣》八首的準備性“詩料”。把訪越作品概括起來看,或許可以說,在20世紀60年代,舊體作為郭沫若的紀行書寫的一種形式,為詩人自己所愈發倚重,也的確成就了相對更完整、更充實、更凝練的詩篇。《穆穆篇》《下龍灣》應運而生,結合時勢、地緣、自然、文化、交往、人事等方方面面;而舊形式之新應用本身,在革命外交旅程中延續了“詩可以觀”“詩可以興”“詩可以群”,乃至于“詩可以黨”[4]155-182的左翼民族文化抒發及交流模式,寓跨國革命情誼的親切感(“群”)、異國特色的欣賞學習(“觀”)和革命新斗爭(由“興”而“黨”)于聲韻律動,更應視為社會主義中國構建反帝、反殖乃至反修的新型團結的努力的特殊一部分。筆者認為,在郭沫若紀行詩中,這兩部作品風格突出而內容豐富,還代表了中國文化政治在“全球六十年代”的特殊展開和表現。
四、尾聲或余論:亞非作家緊急會議
郭沫若7月底離開越南回國后不久,東京灣事件爆發。為應對越南戰爭的空前升級,周恩來在8月6日作出指示稱,援助越南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頭等大事。8月7日,郭沫若發表《警告侵略者》:“你侵犯越南便是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1]2005聲援越南人民反帝斗爭成為亞非團結事業的主軸。郭沫若在相關國際場合多次談亞非拉的“進一步團結”,同美帝國主義斗爭,更多次參加中國人民支援越南、反對美帝、慶祝勝利的大型集會。1965至1966年,周恩來代表中方多次警告美國,休想擴大戰爭,明確了不會坐視不管的堅決態度。而1966年春夏,“文化大革命”爆發,也就在這時,中國在北京主辦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郭沫若是中方代表團團長。這次會議的“緊急”緣由,也正在于越南戰爭的升級,亞非進步作家必須以新的國際團結做出反應。
如前述,亞非作家會議本是萬隆會議的重要成果,茅盾曾率團參加在蘇聯塔什干舉行的1958年亞非作家會議。據考證,那次會上,中方邀請美國黑人知識分子杜波依斯(W.E.B.Du Bois)博士訪華,于是才有了1959年杜波依斯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場景。但是隨著中蘇分裂,亞非作家會議這一交往平臺也遭遇危機。在20世紀60年代初,社會主義中國不僅沒有得到西方的外交承認,而且還受到各國共產黨的半公開的批評,有些亞非人士甚至誤解中國背叛了萬隆精神。但中國不僅更加獨立自主地面對世界,而且比其他任何進步力量都更強勢地表態支持越南,全力援助,甚至不排除與美國直接開戰的可能,并由此尋求反帝反殖反修的第三世界新團結。原本1965年要舉行的亞非作家會議,因為中蘇分歧和阿爾及利亞政變而取消。1966年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以中國為東道主,也遭到了親蘇勢力的反對[13]。
1966年6月27日,郭沫若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開幕式,講話直指援越抗美的新國際團結主題:“亞非各國人民和作家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斗爭決心,是任何力量都阻撓不了,是任何人都破壞不了的……為了支持和聲援英雄的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為了進一步加強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國際統一戰線,為了我們亞非各國發展反帝的民族的新文化,我們要進一步團結起來……”[1]20816月30日,會議通過了《堅決支援越南人民斗爭的緊急呼吁書》。7月4日,郭沫若又作《亞非作家團結反帝的歷史使命》的長篇發言。7月9日,會議閉幕。7月10日,他又主持了首都各界人民為聲討美帝轟炸河內、海防和擴大侵越戰爭的罪行而舉行的集會。然后,他率領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各國部分代表轉至武漢。在武漢,大約160名亞非作家有幸見證了7月16日毛澤東暢游長江。郭沫若以《看武漢第十一屆橫渡長江比賽·水調歌頭》記此盛事:“迎接亞非戰友,筆陣縱橫掃敵,勝利在前程。……橫渡長江畢,皎日笑容生。”[12]108-109由“皎日”可想見,彼時彼地,盛夏氣氛,江上陽光燦爛,詩人當然也是“借喻毛主席”[14]675。次日,郭沫若又帶著亞非戰友們晉見毛澤東并合影,留下毛澤東和第三世界團結的重要影像。回到北京后郭沫若又參加聲援越南的集會。8月初,他在上海歡送亞非作家代表,再次重申“亞非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勝利道路”和“亞非反帝革命的、人民大眾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文藝的方向”[1]2084。7月12日,在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的招待會上,他又講道:“世界人民必勝,分裂主義必敗。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一定會不斷擴大和鞏固……”[1]2086
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問題,顯然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域。但作為郭沫若訪越作品和中國亞非團結工作的延續,它同樣讓筆者想到:如何從文化政治實踐中理解中國在“全球六十年代”的特殊位置以及新型國際團結的構建?但郭沫若的外交紀行詩和“全球六十年代”的反帝團結卻已經因為歷史的疾速變化、反復變化而成為模糊的片段[14],需要我們鉤沉、挖掘、辨認并重新展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