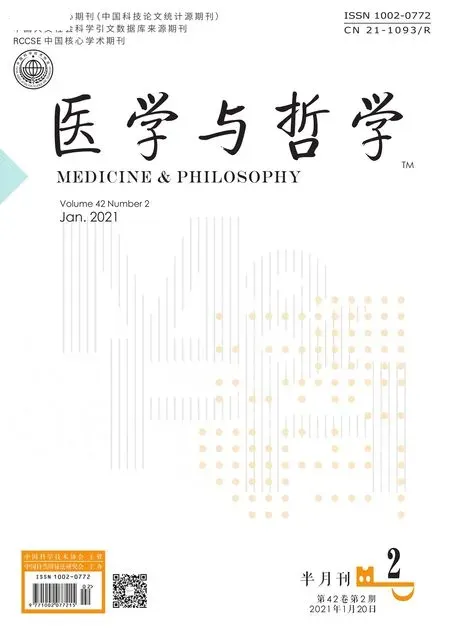甲狀腺癌、乳腺癌臨床指南與實踐碰撞的哲學解析*
張超杰 喻 潔
百年前有醫學教育學家指出,醫學實踐的弊端在于“歷史洞察的貧乏,科學與人文的斷裂,技術進步與人道主義的疏離”。時至今日,這一弊端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現乳腺及甲狀腺疾病發病率逐年升高,惡性腫瘤發病率快速增長并且趨于年輕化,但其生存情況,特別是乳腺癌,較以前顯著提升,這得益于循證醫學模式在我國得到廣泛推廣,極大減少了診療措施的盲目性與隨意性,對推動我國醫療的規范化起到了積極作用。乳腺、甲狀腺相關疾病的診治由經驗治療到循證醫學再到現在的個體化精準治療,步步為營,迅速發展。學科高速的發展帶動了共識、指南及規范的高產,盲目跟從歐美指南的“教條主義”以及“大躍進”式的迸發是否足夠地貼合臨床真實世界,值得深思。本文通過對甲狀腺微小乳頭狀癌(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PTMC)和乳腺癌的診療爭論進行討論。
1 需遵循不傷害、有利原則的PTMC診治
醫學倫理學的基本原則為不傷害、有利、尊重、公正。不傷害指的是在診療過程中不讓患者的身心受到傷害。有利指的是醫務工作者診療的動機及效果均應對患者有利。對于國內現階段PTMC診療的混亂,就是診斷治療的自我矛盾,理論教條與具體實踐的不符,技術進步與醫學人文的沖突,值得我們深思。
1.1 技術與人文割裂,過度診治低危腫瘤
近年來全球甲狀腺癌的發病率迅速增長,甲狀腺癌的暴發增長極有可能歸因于過度的醫療監視,自從超聲檢查開始大范圍應用于癌癥的普查,甲狀腺癌成為女性最常見的癌癥,以韓國為甚,過度診斷的比例達到了90%[1]。有人認為,近年來體檢計劃中將甲狀腺B超納入基本體檢,可能是導致我國甲狀腺癌檢出率顯著提高的原因,這也許正是重蹈韓國過度醫療的覆轍。根據2015年國家癌癥中心統計數據顯示,甲狀腺癌現已成為我國30歲以下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2]。1988年,世界衛生組織將癌灶最大直徑≤1cm且無論是否有淋巴結轉移的甲狀腺乳頭狀癌定義為PTMC[3]。而現在PTMC為近年來增長最為迅速的甲狀腺癌,其發病率占新發甲狀腺癌的50%以上,所以對于PTMC的過度診斷及過度治療成為爭論的焦點,對于它規范的治療及管理也成了熱點問題。Leboulleux等[4]的研究證實PTMC死亡率為0~0.3%,復發率為0.9%~4.2%,由此可見PTMC預后優良。美國甲狀腺學會(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ATA)2015年更新后的“甲狀腺結節和分化型甲狀腺癌診治指南”推薦[5],對于PTMC仍以手術為主導,但對于低危PTMC,可考慮通過進行嚴密觀察代替手術治療。這個觀點是根據日本Kuma醫院對于低危PTMC進行的前瞻性積極監測研究[6-7]而提出,他們通過隨訪觀察發現低危PTMC的預后良好,5年及10年腫瘤增大(>3mm)的比例僅分別為4.9%和8.0%,淋巴結轉移的比例也僅有1.7%和3.8%,可見對于低危PTMC的患者后續腫瘤再次出現進展及淋巴結轉移率較低。而日本在2010年10月發布第一版“甲狀腺腫瘤診療指南”之后,在2018年12月正式發布了舊版指南的修訂版[8],區別于舊版將PTMC分為低危、中危和高危三組,而修訂版指南將舊版指南的低危組進一步劃分為超低危組和低危組;其實對于低危的PTMC 2015版ATA指南并未明確指出,通過閱讀Kuma醫院的這一系列研究[6-7],他們認為排除以下危險因素后即可判定為低危PTMC:(1)臨床淋巴結轉移或遠處轉移;(2)腫瘤毗鄰氣管或喉返神經;(3)細針抽吸活檢(fine needle aspiration biopsy,FNAB)提示侵襲性亞型;(4)隨訪期間進展(結節增大≥3mm)和(或)新發淋巴結轉移。而根據中國抗癌協會甲狀腺癌專業委員會(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yroid Oncology,CATO)出版的“甲狀腺微小乳頭狀癌診斷與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16 版)”(以下簡稱“中國診療共識”)指出[9],需要同時滿足如下6個條件才可判定為低危PTMC:(1)非病理學高危亞型;(2)腫瘤直徑≤5mm;(3)腫瘤位于腺體內且無被膜及周圍組織侵犯;(4)無淋巴結或遠處轉移;(5)無甲狀腺癌家族史;(6)無青少年或童年時期頸部放射暴露史。對比日本標準,“中國診療共識”增加了頸部放射暴露史及家族史,可見我國對于其判定更為嚴格,也是由我國國情所決定的。其實早在舊版的指南里日本學者就已經提出對于低危的PTMC在患者知情且配合的情況下進行嚴密監測是可以選擇的治療方案,而在修正版的日本指南里將T1aN0M0的患者列入超低危組,并將密切觀察作為這類患者的治療方案可供選擇。“中國診療共識”指出對于符合全部預定條件的患者可考慮進行觀察,初始觀察周期可設為3個月~6個月,后根據病情進行調整,如病情穩定可適當延長,患者應簽署知情同意書并最好有統一規范的觀察記錄。根據錢凱等[10]通過分析來自復旦腫瘤醫院778例通過手術治療的PTMC且均符合日本Kuma醫院隨訪標準及“中國診療共識”隨訪標準的患者,回顧性比較各組患者的病理特征及預后差異,他們發現無論是符合“中國診療共識”,還是符合日本Kuma醫院隨訪標準的低危組患者的生存時間、中央區淋巴結轉移、腺外侵犯等情況均優于高危組,并且具有統計學差異,且符合“中國診療共識”的這部分低危患者臨床病理危險因素更少,預后更好。
我們的臨床工作需與指南的更新相契合,也應質疑現階段對于PTMC患者的手術策略是否需要優化、是否真的能讓每一位患者受益。面對甲狀腺癌術后難免出現的喉返神經損傷、甲狀旁腺功能減退等并發癥,對于那些穩定的PTMC選擇嚴密觀察的這種治療方式是不是可以提升方案選擇的優先度。其實中國現在的醫療環境、醫患關系,迫使醫師出于自我保護而采取過度醫療。面對談癌色變的國人,對于穿刺確診為乳頭狀癌且根據臨床證據指向為低危PTMC的這部分患者,在告知其疾病進展慢,不危及生命,手術可導致諸多并發癥和高額醫療費用,以此降低患者對于癌癥的恐懼水平,并配合醫生的嚴密監測,選擇觀察可能仍有一段路程要走。希望有更多的前瞻性、多中心的研究進一步來評估PTMC患者采取觀察隨訪的合理性,探索出更適合我國國情的方案。
筆者認為,針對彩超顯示可能的低危PTMC患者,就沒有必要進行穿刺診斷,此時的穿刺診斷就是過度診斷。穿刺診斷PTMC后,再建議患者密切觀察不符合惡性腫瘤“三早原則”,屬于自相矛盾,且加重患者及家屬心理負擔,是醫學技術與人文割裂的表現。
1.2 醫學技術濫用,盲目擴大甲狀腺消融技術的應用
近年來,以射頻消融、微波消融和激光消融為代表的熱消融技術伴隨著微創技術的風潮迅速發展,海嘯般席卷甲狀腺領域,超聲引導下的消融技術(ultrasound-guided ablation therapy)成為甲狀腺微創治療領域的研究熱點。熱消融技術主要是在超聲的引導下,將消融針置入病灶內,產生熱能,殺死組織細胞,達到消融病灶的目的。其靶點僅覆蓋腫瘤及周邊 0.5cm~1.0cm范圍的正常組織,所以其創傷小、并發癥少、恢復快,已被廣泛應用于多種腫瘤的治療,如肝癌、腎癌等。最早甲狀腺的消融技術僅用于手術風險高或者拒絕再次手術的甲狀腺癌復發患者,目前仍然是ATA、意大利甲狀腺專家共識[11]、韓國放射協會[12]的主要推薦,但并未作為可以手術的PTMC的初始治療方案。在2011年,意大利學者Papini等[13],對于一名81歲的PTMC患者在B超引導下進行了激光消融,在24個月后進行隨訪發現原發腫瘤由之前的8mm變為了4mm,且再次進行細針穿刺未見惡性證據。但選擇該患者是考慮到患者對于手術耐受差,因為其合并多個器官功能障礙(腎衰竭、肝硬化失代償)。然而,國內很多學者以此為說辭,盲目擴大熱消融技術的指征,片面地強調其微創的治療效果,甚至有中心將其用于可手術的PTMC的初始治療。筆者通過回顧國內外文獻,發現用于PTMC的初始治療的報道主要在國內。且一致性認為熱消融技術方便、快捷、患者恢復快。但是該治療方式在PTMC中的應用缺乏長期且有效的經驗,更缺乏循證醫學證據。通過閱讀韓國共識[12],針對于PTMC高發的韓國對于熱消融技術應用于PTMC的初始治療尤為謹慎,他們規定患者至少通過兩次及以上的FANB或粗針穿刺活檢明確為良性方建議進行。對于即使多次穿刺確診為良性,但在超聲影像下有惡性征象的結節仍推薦謹慎采用。筆者推測這樣做的緣由就是為了捍衛可手術的PTMC初始治療的大門。同時意大利甲狀腺專家共識也做出了同樣的推薦。2013年意大利學者[14]在取得患者知情同意后,對3名PTMC患者在全麻下行激光消融后隨即行甲狀腺全切術,術畢的病理證實其腫瘤組織已完全碳化,但是其中1例患者發現合并中央區淋巴結轉移,由此可見PTMC雖小但不一定“早期”。為了規范熱消融技術,我國于2018年發布了“甲狀腺良性結節、微小癌及頸部轉移性淋巴結熱消融治療專家共識(2018 版)”(以下簡稱“2018熱消融共識”)[15]。筆者多次主刀PTMC合并喉返神經侵犯、側頸區淋巴結轉移、及熱消融治療后再行手術治療的患者,術中見嚴重的局部粘連和水腫,層次紊亂,分離難度極大,加大再次手術風險。雖然“2018熱消融共識”指出對于熱消融治療后仍然需要行根治手術治療的患者,建議以3個月為時間節點,避免出現粘連加大手術難度。但是根據筆者經驗,雖然3個月后粘連可逐步減輕,但是消融后再手術難度仍然較大,出現手術并發癥風險仍高,建議患者選擇有豐富手術經驗的中心進行手術治療,降低相關并發癥風險。國內也有專家和筆者有相似觀點,劉新承等[16]對11例甲狀腺乳頭狀癌熱消融治療后再手術的患者進行分析,發現中央區淋巴結轉移 8例 (72.73%),消融側甲狀腺組織有殘留癌灶2例 (18.18%)。所以對于可手術的PTMC不可以“一消了之”,熱消融技術不能達到腫瘤根治的要求,無法保證徹底性,所以筆者所在中心對熱消融技術作為PTMC治療的初始選擇持反對態度。至于為何國內相關專業人員對于熱消融技術如此推崇,筆者考慮可能與以下幾點相關:第一,微創技術的發展訴求,該技術簡單,機器成本低,學習曲線較傳統手術短;第二,利益問題;第三,技術受眾廣,PTMC患者群體大,迎合了患者微創、美觀、恢復快的心理。
為醫者必須明確,我們給予患者的不僅僅是技術,更要有關懷,同樣需要我們在治病的基礎上辯證地分析,審慎地做出最適合患者本人的處理方案,客觀對待,合理引導。
2 深陷“唯數字”論、“唯技術”論的乳腺癌診療問題
關于乳腺癌治療的相關循證醫學證據已經遍地開花,不可否認正是因為其進步才推動了乳腺癌相關診療的大步向前。而現在很多乳腺專科醫師過分依賴循證醫學,尋求各種證據,脫離臨床實踐。孔子說“君子不器”,我們臨床醫師應該“君子用器,而非器也”,我們不應拘泥于各種循證醫學證據,禁錮于“圍城”,需緊貼臨床,了解患者需求。臨床實踐中,遵循指南規范,卻不拘泥指南規范,診療康復方案的制定,顧及人文關懷,不能以疾病為中心,而是以人為中心,如此方可真正造福更多患者[17]。這樣才是醫學理論與臨床實踐的辯證統一。
2.1 曲解的乳腺癌鉬靶篩查
乳腺癌是威脅女性健康的“殺手”,根據2018 年全球癌癥統計數據顯示[18],全球新發的女性乳腺癌患者達到201萬左右,發病率約占所有類型腫瘤的16%,死亡率位居女性惡性腫瘤的榜首。根據我國2015年發布的癌癥統計數據顯示[19],2014年我國乳腺癌新發病例數約為27.89萬人次,占女性所有惡性腫瘤發病的16.51%。另一組數據顯示在城市乳腺癌新發病例數約 18.46萬,為城市地區女性惡性腫瘤的首位,而在農村地區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數約9.43萬例,為農村地區女性惡性腫瘤發病的第2位。另外,區別于國外乳腺癌高發年齡為55歲~64歲,我國存在兩個發病年齡高峰,分別為40歲~49歲以及60歲以上。并且我國乳腺癌確診時分期較國外晚,所以落實乳腺癌的三級預防尤為關鍵,由于乳腺癌的病因不明確,缺乏一級預防方式,而乳腺癌篩查作為其二級預防的主要方式地位穩固。乳腺鉬靶健康保險計劃(health insurance plan,HIP) 試驗,是全球范圍內對乳腺癌進行鉬靶檢查的第一項隨機對照試驗,該研究發現進行鉬靶篩查的患者乳腺癌死亡風險下降了22%,奠定了鉬靶在乳腺癌篩查中的重要地位。鉬靶攝片作為乳腺癌的篩查在國外已廣泛開展十余年,也成為了很多歐美國家的首選方式。美國“國家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乳腺癌臨床實踐指南(2018.V3)”[20]推薦25歲≤年齡<40歲的女性每1年~3年接受一次乳腺體檢,年齡≥40歲的女性每年接受一次鉬靶檢查,以及必要時可接受數字乳腺斷層攝影。而對于具有高危因素的女性,指南推薦每6個月~12個月接受一次乳腺體檢,30歲后應盡早進行每年一次的鉬靶篩查以及25歲以后盡早進行乳腺磁共振篩查,必要時可進行數字乳腺斷層攝影。對比美國推薦,“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癌診治指南與規范(2017年版)”[21]推薦女性開始接受機會性篩查的年齡為40歲,而具有高危因素的女性可于40歲前接受篩查。對于40歲~69歲的女性,推薦每1年~2年一次的鉬靶篩查。對于70歲以上的女性,指南推薦每2年一次鉬靶篩查。同時,指南不建議對20歲~39歲無明顯高危因素以及查體正常的女性進行篩查。對比美國推薦,我國的推薦更為接近亞裔女性乳腺癌的發病特點及亞裔乳腺腺體較為致密的生理結構。從上述情況來看,鉬靶篩查在乳腺癌早診早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否廣泛的群體篩查真的能提高人群的總體獲益,這個值得深思。筆者認為,我國與歐美發達國家經濟水平、醫療資源差距仍然較大,且我國乳腺癌的發病特點也明顯區別于歐美國家,不能盲目依賴國外研究的數據指導我國實踐。其實通過閱讀相關癌癥篩查的Meta分析[22],將近有1/3的研究發現進行癌癥篩查只是減少了疾病特異性死亡率,而沒有明顯降低人群總死亡率。這一發現引起了業界的嘩然,大家對于癌癥的篩查進行了再次的思考,他們分析得出此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進行癌癥篩查的覆蓋率仍然較低,可能最直接的獲益并不能在死亡率上得到體現。仔細思考這個分析結果,雖然他們是對多種惡性腫瘤綜合分析得出的結果,但是筆者大膽認為該結果極其符合我國乳腺癌篩查現狀。中國人口基數大,衛生資源配置差異大,人民群眾主動參與篩查以及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識不到位等,這才是我國現階段的狀態。一項針對上海市1 502名女性對于乳腺癌及早期篩查的認知調查顯示[23],40歲以上中年女性中僅有284名(占25.8%)每年參與乳腺鉬靶篩查。林波等[24]對我國高校的女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大多數女生對乳腺癌存在恐懼心理,并且未意識到乳腺癌的高發性,未進行規律自查自檢,所以提高乳腺癌的篩查不僅僅單純依靠鉬靶,目前當務之急進行全面的科普宣教、提高女性的防癌意識、提升女性的自動篩查的意愿等可能更符合我國國情。另外,我國進行乳腺癌篩查的模式主要依托于社區,社區負責動員人員進行篩查,而參與篩查診斷的人員水平良莠不齊,筆者常在門診見到對18歲~30歲年齡段女性進行鉬靶篩查的診斷報告。在今后的篩查過程中人員的規范化、專業化有待提高,這對篩查的長效機制尤為重要。除此之外,乳腺癌鉬靶篩查的負面作用也不得不面對。首先,進行大規模篩查必須面對的是過度診斷的問題,進行篩查必然出現假陽性,極有可能導致過度診斷,而隨之將出現過度治療的問題。De Gelder等[25]通過分析1990年~2006年荷蘭乳腺癌鉬靶篩查結果,發現其過度診斷率高達11%~12%,而乳腺導管原位癌的程度要明顯高于浸潤性癌,這個結果與美國得出的數據相當吻合。美國學者發現,導管原位癌的新發病例占乳腺鉬靶確診乳腺癌的17%左右。眾所周知,乳腺導管原位癌預后良好,但他們發現幾乎所有的被診斷為導管原位癌的患者進行了手術治療,甚至放療,并有患者因此行全乳切除。筆者推測這部分患者被迫接受了這些治療的相關副作用,但并沒有獲得預期篩查所致的預防性的獲益。另外,面對篩查的假陽性結果,大部分患者表示其誘發了嚴重的焦慮及精神壓力。其次,篩查所致的經濟學效益也是需要面對的。對于大范圍的篩查,“陪跑族”肯定是存在的,就個體而言,發現了早期癌癥,獲得了更好的治療,生命至上、生命無價。但就社會而言造成了較大的人力物力損失,成本和獲益無法對等。所以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篩查方法及模式更為重要[26]。
2.2 舍近求遠的乳腺癌多基因檢測
近十年來乳腺癌的診療模式飛速發展,得益于相關臨床診療研究及循證醫學證據的提出及發布,讓乳腺癌的治療跨入新時代。診療理念的變化來自于2003年圣安東尼奧論壇上意大利專家Veronisi提出:乳腺癌的治療策略已經從“最大耐受性根治治療”轉變為“最小的有效治療”,而隨后十余年的大量臨床實踐已證實該言論的正確,引領了乳腺癌的理論創新。伴隨“最小的有效治療”的理論指導理念的更迭、新的循證醫學證據的拓展,再次引領乳腺癌診療進入精準診療、個體化治療的全新時代。已有研究證實治療方案與患者治療獲益密切相關。如果為患者制定相應的個性化治療方案必定將使更多的乳腺癌患者獲益。而多基因檢測(multi-gene assay,MGA)的發展為乳腺癌個體化治療的重要進程。MGA是在分子分型的基礎上,整合乳腺癌分子生物學信息,從而達到區分同一亞型,特別是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ER)陽性乳腺癌的不同預后,指導治療決策。MGA基本思路是,在腫瘤組織標本中檢測與腫瘤細胞抗凋亡、增殖、轉移等相關的信號通路中若干代表基因的表達水平,量化后建立數學模型,預測患者預后,給患者帶來最大獲益。目前,對于早期乳腺癌主要MGA方式有Oncotype DX、MammaPrint、EndoPredict、BCI(breast cancer index)、Prosigna。2008年NCCN指南就已把21基因Oncotype DX列為乳腺癌輔助治療臨床決策的重要依據。多項歐美研究已證實,21基因檢測已顯著降低ER陽性乳腺癌患者的化療率約26%,改變了31.4%患者的治療抉擇。2019年“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乳腺癌診療指南”[27]也同樣推薦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 Oncotype DX 和 MammaPrint 檢測,著力推進實踐個體化治療。指南的推薦,加深了大家對基因檢測的熱情,不可否認的是MGA是未來的研究方向。筆者認為,盡管在國內獲批的僅為對于淋巴結陰性或1枚~3枚陽性的ER陽性、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基因陰性患者的“70基因”MammaPrint檢測,但是我們不能完全性甚至“武斷”地依賴MGA,其實MGA只是一個工具,并不能完全獨立于相關臨床指標而存在。MGA更多是反映腫瘤本身內在的特征與預后的關系,但是影響預后的因素繁雜,很難單純通過腫瘤自身的生物學形狀與預后完全相關聯。雖然有一項針對中國人群的研究表明[28],進行21基因檢測可以提升醫生對治療方案的信心,并且可以減少輔助化療的使用。但是進行MGA檢測費用昂貴,在我國廣泛應用將面臨障礙。另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是,MGA建立的檢測模式是依據西方人群的基因表達特點所設計的,但是我國乳腺癌基因表達和突變位點與其相比存在著差異,且現在還沒有我國獨立自主知識產權或自主研發的MGA的報道,并且缺少相應的共識及規范,所以我國患者中直接應用該工具設定的分層標準是否合適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江澤飛等[29]認為,“單獨根據多基因分析進行輔助化療需要慎重,同時由于目前基于華裔人群的多基因分析相關研究仍然較少,缺乏相應的行業標準與共識! 國內開展的基因檢測技術有待驗證,結果尚不可靠,因此國內專家并不相信基因檢測的結果。希望國內能有更多可信度高的基因檢測公司的出現”。
在已十分強大的醫學技術面前,很多人愈發追求“科學技術的滿足”而忽視“患者的滿足”。從盲目的基因檢測中,我們需要反思醫學的人文精神及醫學的價值所在。醫學講究規律,而科學注重結果及精確性,但是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醫學研究所必備的,并且有時科學能提供的幫助不一定是患者所真正需求的,所以我們更加需要理性面對,不能舍近求遠、舍本逐末。
3 結語
當今醫學發展日新月異,理論到臨床實踐的路程已經大大縮短,作為當代醫生應該大膽擁抱、大膽嘗試新的理念和新的技術,但是也需要在熱潮中冷靜分析、善于思考,結合患者的實際情況,了解患者的訴求,加強多學科的交叉融合,體現精準治療的理念,真正實現個體化治療的目的。現階段數字醫療、人工智能等高速發展,盡管為疾病的治療提供了全新的治療技術、方法、理念,但是盲目地追求證據、尋求轉化,甚至脫離人文,這是將醫學帶入“流水線”“工坊”,而患者只是線上作業的“部件”,將醫學人文“降溫”,這讓我們憂心忡忡。我國古代就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之說,這一古老的智慧,在今日看來更是散發歷久彌新的洞見,激勵我們為醫者應富蘊人文思想,建樹哲學理念,技術與人文是醫學的兩翼,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