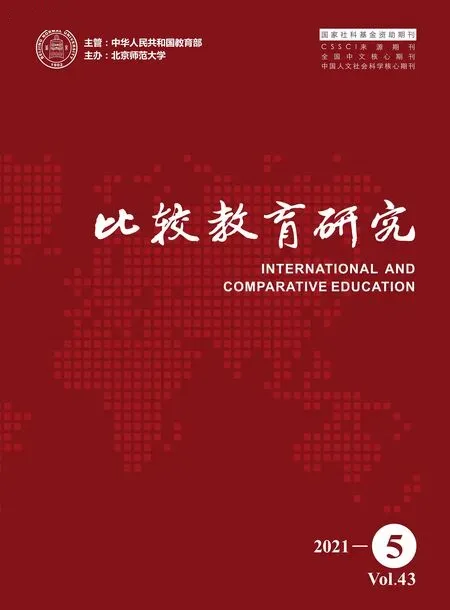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爭議與規范
郝志斌
(重慶大學法學院,重慶 400044)
“為效果付費”(Pay For Success)改革是21世紀以來美國教育改革的新探索。2013年9月,美國猶他州鹽湖縣(Salt Lake County,UT)實施了第一個低收入家庭兒童早期教育的“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2014年10月,芝加哥市(City of Chicago)也實施了兒童早期教育領域的“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所謂“為效果付費”的教育改革,是指政府通過契約合同吸引私人投資者為公立學校教育服務供給項目提供前期資金,而后根據私營機構供給公立學校教育服務的效果決定是否償還投資者本息。[1]為了規范其有效實施,美國2015年《每個學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 Act)規定了“為效果付費”改革的相關要求,為美國“為效果付費”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2]本文以芝加哥公立學校(Chicago Public Schools,CPS)“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為代表性案例,就其實施背景、舉措、存在的爭議和未來強化“為效果付費”改革的規范展開介紹與分析。[3]
一、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的背景
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是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創新之舉。為了繼續推動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2004 年6 月時任芝加哥市市長戴利(Richard J. Daley)宣布了一項振興芝加哥公立學校的“2010年文藝復興”(Chicago’s Renaissance 2010)計劃。戴利市長指出,“2010年文藝復興”計劃的根本目標是在未來6 年內新建100 所學校,為教育服務欠缺的社區提供新的選擇,同時緩解人數快速增長而出現的學校擁擠狀況。[4]芝加哥商業俱樂部(Commercial Club of Chicago)為該計劃籌集了5000萬美元資金,同時成立了一個籌款和監督機構,即芝加哥新學校(New Schools for Chicago,NSC)。該機構由商業代表、芝加哥教育委員會主席和芝加哥公立學校首席執行官等成員組成。2004年9月,芝加哥教育委員會(Chicago Board of Education)通過了“2010 年文藝復興”計劃,擬定開設100 所新學校,其中1/3 為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1/3為契約學校(contract schools),1/3為績效學校(performance schools,為“2010年文藝復興”計劃資助和政策約束的公立學校)。所有新學校都將與政府簽訂為期5年的績效合約,但作為交換,學區承諾在課程、教學和學校組織方面給予這些新學校更大的靈活性。[5]但“2010年文藝復興”計劃引起了多方抵制,反對派建立了反“2010年文藝復興”聯盟,說服了50 名市議會成員中的40 人支持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6]戴利市長的改革造成了公立學校財政危機的進一步加劇。2010年,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在競選芝加哥市長時,又提出了一個“基礎設施信托”(Infrastructure Trust)計劃,旨在將私人資本引入公共領域,例如機場擴建、水利改善以及通勤鐵路網的擴展等,伊曼紐爾稱其為“建設新芝加哥”(Building a New Chicago)計劃。[7]同樣,他在教育領域也承諾將致力于新自由主義的私營化,包括繼續進行公立學校私營化改革,如關閉公立學校和增加特許學校等。[8]2011年,伊曼紐爾上任時聲稱,將通過“為效果付費”改革來解決芝加哥公立學校的資金危機,以提供更好的兒童早期教育服務。
二、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的實踐
2014 年芝加哥公立學校開始“為效果付費”改革,通過芝加哥親子中心項目(Chicago Child Parent Center)為2600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高質量的兒童早期教育服務。芝加哥親子中心項目是美國早期教育干預項目的優質項目,主要致力于為處境不利家庭及其3~9歲兒童提供教育服務,于1967年開始實施。[9]芝加哥親子中心項目過去完全由聯邦和州政府資助,但政府資助模式出現效率低下、資金緊張等問題。在此背景下,芝加哥公立學校通過“為效果付費”改革引入市場機制提高芝加哥親子中心項目的實施效率,緩解直接撥款模式下的資金壓力。2014年,伊曼紐爾市長向市議會提出了一項法令,允許教育委員會通過“為效果付費”改革實施高質量的兒童早期教育計劃。根據該法令,芝加哥市簽署了貸款協議(The City of Chicago Loan Agreement)、“為效果付費”協議(Pay-For-Success Contract)等以提供高質量的兒童早期教育服務。[10]在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中,投資者通過中介機構向服務提供者提供資金,如果項目經由獨立評估機構評估后認為達到預定目標,則政府將償還投資者的預定本息。“為效果付費”改革按以下步驟加以推行。
首先,伊利諾伊州設施基金會(Illinois Facilities Fund,IFF)作為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的中介機構,負責從投資者處籌集資金。芝加哥公立學校近1700萬美元的“為效果付費”改革資金由高盛社會影響基金(Goldman Sachs Social Impact Fund)和北方信托(Northern trust)作為優先級投資者,普利茲克家族基金會(The J.B. and M.K. Pritzker Family Foundation)作為次級投資者共同籌集。優先級投資者具有資金優先受償權,但和次級投資者一樣均需在學生取得積極學業成績時才能得到償還,投資者的收益是通過項目所節省的費用來支付的。中介機構除籌資外,還需要根據評估協議聘用獨立評估機構并監督其服務、協調協議項下的資金往來以及根據協議提供項目信息共享服務等。
其次,伊利諾伊州設施基金會完成籌資后將資金撥付給項目服務提供者用以實施具體任務。芝加哥公立學校利用私人資本將高質量的親子中心項目(Chicago Child Parent Center)擴展到為低收入社區提供高質量的兒童早期教育服務。大都會家庭服務機構(Metropolitan Family Services,MFS)為父母參與提供指導支持,如協助家庭需求評估和計劃數據分析等。此外,該項目還建立了一個交互式在線數據庫,以實現信息共享等。
然后,在服務提供者完成項目任務后,斯坦福國際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SRI International)將對其進行獨立評估。該項目評估獲得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社會效益債券技術援助實驗室(Social Impact Bond Technical Assistance Lab at Harvard's Kennedy School)的支持,[11]同時芬尼根家庭基金會(Finnegan Family Foundation)將在頭兩年資助該計劃的評估費用。斯坦福國際研究所在哈佛大學社會效益債券技術援助實驗室編寫的設計草案基礎上開發了新的評估方法。除了評估“為效果付費”的確定指標外,斯坦福國際研究所還進行某些定性研究,以幫助提高項目績效。
最后,政府機構將根據斯坦福國際研究所的評估結果決定是否“為效果付費”。在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中,芝加哥市政府與芝加哥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City of Chicago)是項目付費機構。付費取決于學生的成績變化,衡量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特殊教育服務需求的減少、接受兒童早期教育服務后達到的幼兒園教育準備水平與三年級閱讀水平的提高。其中,每減少1名特殊教育服務需求學生,政府將支付9100美元;參加兒童早期教育項目后,學生幼兒園教育準備水平每提高1名,政府將支付2900美元;三年級學生閱讀水平每提高1名,政府將支付750美元。[12]該項目投資者將根據該項目是否達到其預定目標獲得回報。如果未達目標,那么投資者可能會損失全部投資。
三、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的爭議
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是一項創新的私營化探索,支持者宣稱其能夠提高效率、促進公平和削減成本,但反對者認為“為效果付費”改革實質是私人資本掠奪公共資源,還將這種掠奪偽裝成慈善和責任。其中,主要的爭議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否能提高芝加哥公立學校改革效率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政府績效實驗室(Harvard Kennedy Schoo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Lab,GPL)的利伯曼(Jeffrey Liebman)教授是“為效果付費”改革的主要支持者。他認為,在“為效果付費”改革的市場機制之下,政府項目的低效及資金浪費等問題將不復存在。“為效果付費”改革涉及合約多層嵌套,其基礎是政府與私人部門達成的協議,即僅當某一特定的公共服務供給結果得到改善時,政府才為其支付資金。[13]“為效果付費”改革使相關各方都能做自己最擅長的事,私人部門可以創新,政府可以擴大項目規模。“為效果付費”改革是目前填補芝加哥公立學校改革中空狀態的最佳選擇。“為效果付費”改革強調“低效的公共部門”需要“市場規范”來節約成本,增強問責和降低風險。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of American Progress)、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政府績效實驗室等,都是“為效果付費”的積極支持者。
但是,反對者認為“為效果付費”改革使政府須為教育服務支付額外費用(即利息),同時還失去了對該教育服務的民主治理控制權。“為效果付費”改革使芝加哥公立學校改革的重點“不再是教育內容和成就,而是簡單的數字”。[14]為什么市政府不直接資助該項目,而要依賴復雜的貸款結構,而且“為效果付費”改革中政府須提前預留需要支付給投資者的費用,這意味著政府并不能因此實現資金使用的靈活性。[15]支持者主張的私營化理論認為獨立的競爭力量,即“市場紀律”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提供動力的唯一力量,但這一論點似乎并沒有多大說服力,私人部門也可能像政府機構一樣僵化,同時市場力量在阻止這種僵化方面的效果并不明顯。市場力量通常只會在私人部門不再盈利的情況下發揮作用,如果公司盈利,市場則通常會放任不管,不會管公司的效率有多低,或者離理論上的最佳狀態有多遠。畢竟,利潤,僅僅是利潤,而不是效率,才是市場的全部。[16]
此外,要使“為效果付費”改革具有投資吸引力并發揮作用,就必須有收益的可能性。然而,“為效果付費”改革中經濟利益貨幣化所需的時間較長,需要私人投資者提供更多的預先資本來支持提供這些服務。資金越多,期限越長,意味著投資者必須承擔更高的風險。實際上,芝加哥公立學校短期內無法向投資者證實這些服務是否能夠按照預期的方式運作。同時,“為效果付費”的資金節約需要用可量化的數字來證明,問題是誰來測量?基準如何確定?項目成功與否完全由獨立評估確定,在這種模式下欺騙造假等行為將不可避免。實際上,在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中,這種急功近利和腐敗問題屢見不鮮。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前校長、學校董事會成員亨利·比能(Henry Bienen)就反對該提議,質疑其功能和高效率。
(二)是否能促進芝加哥公立學校教育公平
一般而言,教育公平包括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與條件、教育成功機會和教育效果的相對均等,即每個學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達到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包括學生的學業成績上的實質性公平、教育質量公平及目標層面上的平等。就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與條件而言,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體現了一種市場管理邏輯,與“新市場官僚主義”(New Market Bureaucracy)相一致,與其類似的新自由主義的私營化舉措還有特許狀、代金券、獎學金稅收抵免等。[17]但私營化舉措使教育資源差距不斷擴大,某些學校獲得了最先進的設施、設備和用品,而為低收入有色人種學生服務的社區學校卻變得越來越隔離且資源不足。[18]此外,在芝加哥貧困地區的公立學校關閉的比例過高,無論貧困地區是根據種族、收入還是地理位置來定義,這個結論都是如此的。[19]由此可見,“為效果付費”改革等私營化探索并不能有效促進芝加哥公立學校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與條件。
就教育成功機會和教育效果的相對均等而言,“為效果付費”結果導向的經濟激勵會導致多主體關注多項任務中最容易實現結果的方面,實際上這類問題早已存在。美國布什總統簽署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開創了教育問責制的新時代,這種問責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激勵,以提高學生學習成績。批評者認為當前的問責政策導致教師將資源投入具有明顯效果的科目,同時忽視邊緣學生,忽視學習中不能明確測試結果的關鍵方面。[20]與此同時,“確保地方政府的服務目標得到正確的體現,要比實際改善這些服務付出更多的努力”,這種優先次序的逆轉可以毫不夸張地描述為“市場斯大林主義”(Market Stalinism)。令老師沮喪的是,他們的工作似乎越來越旨在給“大人物”留下深刻印象。[21]然而,諸如人文學科就不太可能實現量化衡量,那么“為效果付費”改革可能僅會追隨那些可以量化的學科。[22]由此,“為效果付費”改革無疑會造成芝加哥公立學校教育成功機會和教育效果的不均等。
(三)是否能節約芝加哥公立學校改革成本
“為效果付費”改革支持者的一個中心論點是通過僅為結果付費來節省資金。然而,如果“為效果付費”評估不獨立或者“腐敗壓力”導致所謂的“市場紀律”失靈,無疑會使得這種成本節約成為空談。而且,實踐表明“為效果付費”改革會增加成本,而非節約成本。例如,“為效果付費”協議需花費高額費用來處理大量法律服務,而且這個周期一般需要很長時間。同時,如果“為效果付費”協議不能通用,則每個項目協議都必須重新協商起草,且所有新項目都不能以現有項目為模型。因而,研究者認為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并不能夠節約公立學校改革成本。[23]公立學校很難依靠項目成本節約來支付“為效果付費”改革的報酬。
“為效果付費”改革的另一個成本問題是私人部門參與其中,市場利率往往會高于政府債券的利率。研究者指出,政府的資本成本往往低于市場成本,如果真有更好的方法,這些方法應該由政府直接提供資金,而不是通過“為效果付費”改革等模式間接提供資金。[24]例如,眾議院撥款委員會(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委員羅斯·亨特(Ross Hunter)阻止了一項聯邦“為效果付費”法案。他說:“作為一個私人投資者,你會要求什么樣的利率?11% ? 9% ? 相比之下,政府收益債券的利率可能低至4%。”[25]此外,研究者還擔心“為效果付費”改革會出現將慈善資金用于彌補公共支出的風險,將慈善資金鎖定在收益上。戴維·麥克唐納(David Macdonald)甚至明確指出,“為效果付費”改革并非慈善事業,相反,是“反慈善”的,是偽裝成慈善事業的逐利活動。[26]換言之,對投資者最具吸引力的項目是那些看起來更有可能產生可靠且優厚回報的項目,而非風險更大的“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27]像高盛這樣的銀行永遠不會冒著50%的損失風險投資500萬美元,即使高盛要承擔風險且評估結果對其不利,政府也不可能拒絕償還高盛全部的500萬美元。[28]同時,如果政府因項目成本大于收益而被迫在“為效果付費”實施過程中重新談判協議條款,還可能會面臨私人投資者鎖定交易的風險,例如提高收益率或要求以部分擔保的形式提供信用增級等。實際上,在大多數“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中,慈善基金會或政府都為投資者提供了某種形式的擔保。[29]總之,“為效果付費”改革中政府將稅款支付給銀行等私人部門并不能有效節約成本[30],反而可能會損害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目標群體的利益及其附隨的公共利益。[31]
四、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的規范
“為效果付費”改革實際上仍需“政府買單”,因此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需要進行完備的規范建設,以防范可能造成的資金損失。[32]已有研究指出,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的規范程度并不高,相關規范處于缺位狀態。“為效果付費”改革在現有法律框架下能否有序實施?能否與傳統模式實現契合?“為效果付費”改革中,政府如何知道預期目標是否實現?誰來評估服務提供者的績效——發行人、政府、投資者,還是其他人?誰負責評估獨立評估機構?對于未能按預期執行的困境應如何處理?如果“為效果付費”項目中政府、投資者等資不抵債該怎么辦?以上諸多問題暫未有明確答案。[33]對此,密歇根大學法學院(Law School,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布蘭德(Deborah Burand)教授認為,“為效果付費”改革要有序實施就需有效管控“為效果付費”的多層合約嵌套、績效評估以及不確定性風險。[34]
針對“為效果付費”改革的風險和效率問題,2016年,美國教育部(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撥款支持“為效果付費”改革可行性研究;2018年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社會影響伙伴關系成果支付法》(Social Impact Partnerships to Pay for Results Act,SIPPRA),旨在提高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的效率。國會撥款1億美元用于實施“社會影響伙伴關系示范項目”,并為這些項目提供可行性研究。在此基礎上,一些已有研究也為未來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的規范提供了方向:一是,規范“為效果付費”改革的信息共享。依據良好的商業慣例和有關法律的規定,“為效果付費”協議各方披露關鍵信息和數據。[35]二是,制定有關影響力投資的標準,以便于項目主體理解、衡量最重要的影響因素;[36]三是,定期召開相關會議,建立對話渠道,促進政府和市場主體之間的信息共享,確定可以采取的具體措施等。[37]四是,規范評估制度。根據美國財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發布的《資金可用性通知》(Notice of Funding Availability,NOFA),財政部預計將撥付大約994萬美元用于支付獨立評估機構的費用。[38]在該通知下,“為效果付費”改革項目中需要為獨立評估機構支付的費用將與項目結果脫鉤,以此來保證獨立評估機構的獨立性。
綜上所述,與任何一種創新無異,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的復雜性同樣帶來了諸多問題,可能造成芝加哥公立學校的公共使命遷移,因而研究者對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是否能提高芝加哥公立學校改革效率,是否能促進芝加哥公立學校教育公平,是否能節約芝加哥公立學校改革成本等存在較大爭議。在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中,私人部門成為重要力量,政府僅“為效果付費”,這種新型治理力量帶來的新權利訴求、新利益關系、新責任配置方式,滋生了諸多風險和矛盾,產生了許多不可預見的新的破壞力,例如“新市場官僚主義”,即代價高昂、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中,私人部門分享治理權或自我賦權的趨勢,可能形成私人部門壟斷芝加哥公立學校資源的局面。同時,私人部門還很容易被經濟理性所激勵的利益集團所俘獲,最終損及公立學校附隨的公共利益。質言之,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多重合約嵌套結構和多元主體的特質,帶來了法律治理的諸多挑戰,不斷挑戰有關利益歸屬的傳統規則和公平正義的價值體系。因此,未來芝加哥公立學校“為效果付費”改革需要加強規范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