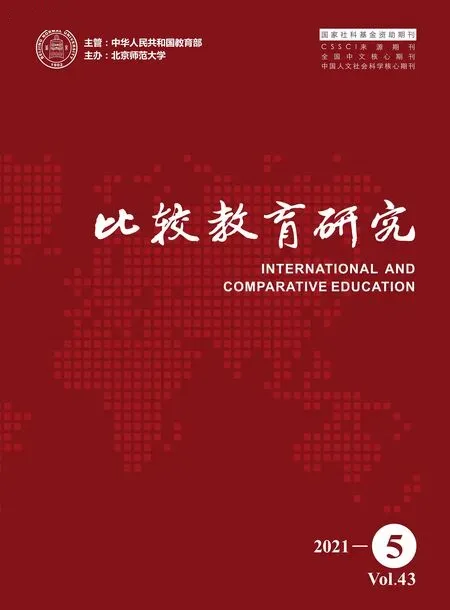重構(gòu)學(xué)術(shù)共同體:建設(shè)世界一流大學(xué)的治理制度和組織文化
王英杰
(北京師范大學(xué)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問題提出
大學(xué)在走入21世紀(jì)第三個十年之際,治理制度和組織文化面對極為復(fù)雜的社會環(huán)境和極嚴峻的挑戰(zhàn)。
首先,高等教育大眾化極大地改變了大學(xué)的圖景和性質(zhì),大學(xué)規(guī)模動輒數(shù)萬人,使大學(xué)不再是培養(yǎng)社會精英的精英機構(gòu)。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學(xué)促進社會流動本應(yīng)是高等教育的題中之義,但是大學(xué)作為社會向上移動的階梯作用卻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開始減弱,大學(xué)學(xué)位不再是獲得進入社會上層的入門券,獲得學(xué)位只是進入一個前途不那么明確的職業(yè)的必要一步。在規(guī)模宏大的大學(xué)中,學(xué)生很難獲得個別化的人文關(guān)懷,他們都成為數(shù)萬“號碼”中的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大學(xué)增加了管理層次和管理人員,強化了管理文化和行政權(quán)力,教師在大學(xué)管理中不斷被邊緣化。高等教育大眾化持續(xù)不斷地使大學(xué)治理更偏向于科層治理模式。
其次,市場正在深刻地改變大學(xué),大學(xué)的公共物品性質(zhì)正在變得愈來愈模糊。學(xué)費不斷上漲,公眾和學(xué)生日益把高等教育視作有價商品,甚至在大學(xué)內(nèi)部也開始把學(xué)生視作消費者,把學(xué)生的滿意度視作評價教師教學(xué)的唯一指標(biāo),使教育成為教師打包遞送的產(chǎn)品,消費者的滿意度成為教師攀登學(xué)術(shù)階梯的必要條件。大學(xué)把教師等同于企業(yè)的雇員,特定期限合同正在取代長聘約定,合同成為大學(xué)行政管制教師的利器,從而嚴重地改變了大學(xué)的本質(zhì)特征。大學(xué)在適應(yīng)市場需求和應(yīng)對政府問責(zé)的雙重壓力下,專業(yè)行政人員不斷增多,行政權(quán)力不斷膨脹,決策層級不斷上移,大學(xué)校長的價值觀和決策行為越來越像企業(yè)的CEO,而院系基層學(xué)術(shù)單位正在被改造成知識生產(chǎn)車間、知識傳播演播室和政府機構(gòu)的服務(wù)站。
最后,信息化與市場化糾纏在一起相互強化,正在改變著知識生產(chǎn)和傳播的過程與方式。持續(xù)的信息技術(shù)創(chuàng)新對大學(xué)教學(xué)和科研等核心活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信息技術(shù)和市場成為大學(xué)實現(xiàn)對教師的支配、控制和剝奪的有力工具。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使用極大地改變了大學(xué)教師的勞動過程。馬克思認為勞動過程包括三個要素:“有意義的活動,即勞動本身”“勞動對象” 和“勞動工具”。在數(shù)字化的知識生產(chǎn)環(huán)境中,知識生產(chǎn)的周期大大縮短,大學(xué)有意義的活動(教學(xué)與科研)不斷加速,大學(xué)教師感受到知識創(chuàng)造的難度加大,知識創(chuàng)造的緊迫感增強,大學(xué)教師被知識創(chuàng)造的時限所裹挾,無暇思考知識創(chuàng)造的社會意義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價值和倫理意義,或者說無暇思考“有意義活動”的意義在哪里。“勞動對象”被異化,從重知識創(chuàng)造轉(zhuǎn)向以發(fā)表為第一要義,創(chuàng)作論文和著作成為學(xué)者的主要關(guān)注,為了獲得和維系學(xué)術(shù)聲譽就要不間斷地發(fā)表,同時還要在社交媒體中管理自己的聲譽。數(shù)字技術(shù)不斷強化了大學(xué)對教師勞動的監(jiān)管,發(fā)表的數(shù)量與被引用次數(shù)成為大學(xué)評價教師的最直接和最簡單易行的工具。在教學(xué)方面,學(xué)生與教師的關(guān)系也日益受到數(shù)字技術(shù)的影響,教師被期望時刻在微信中可及,智能手機幾乎成為增加學(xué)術(shù)勞動壓力的最有效工具,講課可能隨時被錄像,講課截圖可能隨時被發(fā)布在網(wǎng)上,教師在課堂上的一舉一動和一言一行都在數(shù)字工具的監(jiān)控之中,這對教師構(gòu)成無形的壓力。勞動過程的第三個要素“勞動工具”正在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大學(xué)教師埋頭于故紙堆中“爬格子”的形象已經(jīng)一去不復(fù)返,大學(xué)教師現(xiàn)在一整套的勞動技能包括線上搜索、上收費的數(shù)據(jù)庫搜尋、保存在線資源、構(gòu)建數(shù)字分析模型等。這就使學(xué)術(shù)勞動的資源與大學(xué)的地理存在脫鉤,大學(xué)變得更像一個平臺,大學(xué)教師的勞動更多地是與大學(xué)的數(shù)字資源相連,如電子郵箱和企業(yè)微信等。這種人際間的疏離造成教師與教師、教師與管理者、教師與學(xué)生之間關(guān)系的不穩(wěn)定性,而這種不穩(wěn)定性又帶來了心理上的焦慮。“勞動工具”的變化會引起社會質(zhì)疑大學(xué)實體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嗎?
大學(xué)治理制度和組織文化面對如此尖銳的挑戰(zhàn),卻對此反應(yīng)并不敏銳。在大學(xué)內(nèi)部,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與行政權(quán)力對峙嚴重;在大學(xué)外部,公眾和政府對大學(xué)不能全面滿足他們的期望而深感不滿。在自媒體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時代,大學(xué)的問題和“丑聞”被無限放大,大學(xué)被公眾的批評和政府的指令所裹挾,正在失去引領(lǐng)社會進步的功能,因此必須改革大學(xué)的治理制度,重構(gòu)大學(xué)的組織文化。
二、三個發(fā)達國家的大學(xué)治理改革:經(jīng)驗與教訓(xùn)
在歷史上,大學(xué)是由它們的學(xué)術(shù)共同體運轉(zhuǎn)和治理的,但是在當(dāng)代一些國家的政府不斷施壓大學(xué)改革其治理結(jié)構(gòu)和治理制度。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全世界大學(xué)治理結(jié)構(gòu)和制度正在發(fā)生史無前例的變化,隨著這些變化的加劇,大學(xué)的性質(zhì)正在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當(dāng)然國際共同的改革趨勢在各國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和形式是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大學(xué)組織的國家傳統(tǒng)在決定各國的大學(xué)治理制度形態(tài)方面繼續(xù)起著重要作用。
(一)三個發(fā)達國家的大學(xué)治理改革
1.英國大學(xué)的治理改革
1979年撒切爾當(dāng)選英國首相,開始嚴格審查所有公共支出,1981 年高等教育經(jīng)費被大幅削減,這標(biāo)志著英國大學(xué)獨立時代的終結(jié)。1985年《加拉特報告》(Jarrat Report)的指導(dǎo)思想是,大學(xué)應(yīng)該像私企一樣,相互競爭資源,學(xué)生應(yīng)被視作顧客。[1]該報告還建議大學(xué)采用中央集權(quán)的領(lǐng)導(dǎo)方式,減少教師的決策參與,制定更正式的長遠發(fā)展規(guī)劃,建立更系統(tǒng)的定量績效指標(biāo)。[2]大學(xué)校長委員會接受了這份報告的建議,采取的第一步行動就是建議取消大學(xué)教師的終身聘用制,這就破壞了大學(xué)教師的職業(yè)安全,使學(xué)者難以發(fā)出與大學(xué)行政不同的聲音。英國政府也根據(jù)該報告采取了新機制監(jiān)管大學(xué),1986年制定了“科研水平評估作業(yè)”(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對高等教育機構(gòu)的科研進行排名,并根據(jù)排名結(jié)果確定高等教育機構(gòu)的科研撥款,即根據(jù)“科研質(zhì)量”有選擇地撥款,這導(dǎo)致了大學(xué)科研的管理和目標(biāo)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1988年政府進一步通過立法撤銷了存在70年、曾被國際高等教育界視為維護大學(xué)自治典范的大學(xué)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因其被指責(zé)對大學(xué)太過“軟弱”,而被更“強硬”的高等教育經(jīng)費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HEFC)所取代。這項法令還終結(jié)了大學(xué)與多科技術(shù)學(xué)院的雙軌制高等教育,將后者升格為大學(xué),這樣許多大學(xué)成為教學(xué)大學(xué),不再踐行洪堡教學(xué)與科研相結(jié)合的原則,這使大學(xué)教授的聲音在大學(xué)內(nèi)部進一步被削弱。
1997年的《迪林報告》(Dearing Report)的出臺又一次對高等教育產(chǎn)生巨大沖擊。該報告要求學(xué)生負擔(dān)學(xué)費,這就沖擊了福利社會的基本理念,使高等教育不再是公共物品,而是學(xué)生要購買的商品,學(xué)生在理論和實踐上成為大學(xué)的顧客。該報告還提出,大學(xué)最重要的任務(wù)是為提高英國在知識經(jīng)濟中的競爭力作出貢獻,這推動了大學(xué)科研與經(jīng)濟更密切的聯(lián)系,促使科研與教學(xué)的進一步疏離,并且強化了教師在為經(jīng)濟服務(wù)中的工具屬性,從而使教師更偏離大學(xué)決策的中心。[3]
在英國這一系列的激進改革中,應(yīng)該說受到?jīng)_擊相對較小的還是牛津大學(xué)和劍橋大學(xué),這兩所大學(xué)是自我規(guī)訓(xùn)的學(xué)者共同體,教師與學(xué)生在大學(xué)的學(xué)院里生活和交往,學(xué)院既附屬于大學(xué)又是獨立的實體,在學(xué)院里以教養(yǎng)為教育的指導(dǎo)原則,教育被視作成人的復(fù)雜過程,不僅僅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鼓勵批判性地思考和運用知識。如紐曼(John Henry Newman)所說:“在這里探究受到鼓勵,發(fā)現(xiàn)得到至善和證實,魯莽并非有意冒犯,錯誤被揭示,其途徑是心靈的碰撞,知識的碰撞。”[4]我們可以說,這兩所大學(xué)的學(xué)院仍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典型。
2.瑞典大學(xué)的治理制度改革
瑞典大學(xué)傳統(tǒng)上是由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的機構(gòu),大學(xué)的決策機構(gòu)是教授會議(konsistorium),會議由正教授組成,后經(jīng)多次改革,最終被類似企業(yè)董事會的決策機構(gòu)——大學(xué)理事會所取代,該理事會由校外代表出任主席,并且很大一部分成員來自校外。《2011年大學(xué)改革法令》進一步解構(gòu)了大學(xué)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基礎(chǔ)結(jié)構(gòu),該法令首先指向了大學(xué)教師理事會。此前的法令規(guī)定所有大學(xué)都要設(shè)置教師理事會,由教師和學(xué)生代表組成,負責(zé)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決策。而2011年法令沒有對大學(xué)內(nèi)部的組織結(jié)構(gòu)作出規(guī)定,只是一般性地要求科學(xué)性的問題應(yīng)由科學(xué)上勝任的教師處理,這幾乎導(dǎo)致所有的大學(xué)和大學(xué)學(xué)院都撤銷了教師理事會或?qū)⑵鋸臎Q策機構(gòu)轉(zhuǎn)變成咨詢機構(gòu),僅有兩所最古老的世界一流大學(xué)(烏普薩拉大學(xué)和隆德大學(xué))仍將教師理事會作為決策機構(gòu)保留。
其次,2011年法令指向了大學(xué)領(lǐng)導(dǎo)的選聘及其職能。傳統(tǒng)上瑞典的大學(xué)領(lǐng)導(dǎo)一般由校內(nèi)教授產(chǎn)生,得到同事支持和信任就會被選為領(lǐng)導(dǎo),學(xué)術(shù)領(lǐng)導(dǎo)被視作非永久性的、非全日制的工作,當(dāng)選領(lǐng)導(dǎo)不過是為學(xué)術(shù)共同體服務(wù)一個任期。在20世紀(jì)80年代以前,瑞典大學(xué)領(lǐng)導(dǎo)由教師選舉提名,由政府任命;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學(xué)生和職員代表也參加了選舉。2011年法令要求大學(xué)理事會就大學(xué)領(lǐng)導(dǎo)人選咨詢教師、職員和學(xué)生,但是如何咨詢由大學(xué)理事會決定,結(jié)果只有少數(shù)歷史較悠久的大學(xué)保留了選舉的形式,現(xiàn)在多數(shù)瑞典大學(xué)使用校外咨詢?nèi)藛T來招聘和審核候選人,最后由大學(xué)理事會將候選人名單報送政府有關(guān)部門,由政府任命。今天多數(shù)瑞典大學(xué)校長都是從校外聘任的,一般來說學(xué)術(shù)資格不高(2011年法令規(guī)定的最低門檻是大學(xué)講師),但多數(shù)都有長期學(xué)術(shù)領(lǐng)導(dǎo)的經(jīng)驗,有在若干所大學(xué)任職的經(jīng)歷,這表明學(xué)術(shù)領(lǐng)導(dǎo)已經(jīng)成為一種職業(yè),不再被看作為學(xué)術(shù)共同體服務(wù)的臨時性工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學(xué)術(shù)共同體制度讓位于科層制度,“賢能”價值被行政經(jīng)驗價值取代了。
最后,該法令指向的是職稱晉升和研究經(jīng)費的評審程序。在傳統(tǒng)上大學(xué)請校外的同行進行評審,因為相信校外的評審者較少偏見,更注重質(zhì)量。而2011年法令頒布后,校外評審變成整個評審過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他們只負責(zé)審查是否合格,最后的決定權(quán)仍在校內(nèi)。這種改變的依據(jù)是新的崗位和科研經(jīng)費應(yīng)該給那些適應(yīng)大學(xué)發(fā)展戰(zhàn)略與科研環(huán)境的人,這表明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讓位于大學(xué)內(nèi)部的組織戰(zhàn)略了。[5]
3.澳大利亞大學(xué)的治理制度改革
自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澳大利亞掀起了四次高等教育改革浪潮。20世紀(jì)70年代的第一次改革取消了大學(xué)生的學(xué)費,高等教育的財政職責(zé)從州政府轉(zhuǎn)到了聯(lián)邦政府,高等教育成為真正的公共物品。
20 世紀(jì)70 年代的改革導(dǎo)致政府高等教育經(jīng)費大增,于是在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了第二次改革浪潮。這次改革是以政府為主導(dǎo)、自上而下推動的,對高等教育機構(gòu)設(shè)置、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等諸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市場化改革。1988年《道金斯白皮書》(Dawkins White Paper)全面闡述了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和措施。第一是重新要求大學(xué)生負擔(dān)部分學(xué)費。第二是大學(xué)開始招收付全額學(xué)費的國際學(xué)生和研究生。這樣澳大利亞大學(xué)開發(fā)了巨大的高等教育國際市場,到2008年教育成為澳大利亞第三大出口業(yè),僅排在煤和鐵礦石之后,大學(xué)成為具有企業(yè)精神和市場導(dǎo)向的“企業(yè)”大學(xué)。第三是重組高等教育機構(gòu)。將繼續(xù)教育學(xué)院合并到大學(xué),變澳大利亞傳統(tǒng)的雙軌制高等教育為單軌制,從而改變了大學(xué)傳統(tǒng)的精英性質(zhì)。第四是對大學(xué)的管理和組織結(jié)構(gòu)進行審查。建議在大學(xué)建立與企業(yè)相類似、規(guī)模較小的治理董事會,以保證大學(xué)有適當(dāng)?shù)呢?zé)任制度、高效的決策程序和績效測量措施。第五是給大學(xué)在教學(xué)、科研以及資源使用方面更大的自主權(quán)。這次改革浪潮建立了政府治理大學(xué)的新模式,強調(diào)政府政策的主導(dǎo)作用,強調(diào)在大學(xué)內(nèi)部加強管理層的權(quán)力。這次改革標(biāo)志著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制度與經(jīng)濟發(fā)展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將“為提高澳大利亞國際經(jīng)濟競爭力服務(wù)”作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biāo)。[6]大學(xué)間的競爭成為科研撥款制度的基礎(chǔ),建立科研撥款競爭機制的目標(biāo)是“最大限度地挖掘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制度的科研潛力,實現(xiàn)與更廣闊的國家目標(biāo)更密切地結(jié)合”[7]。
20 世紀(jì)90 年代初開始的第三次改革浪潮的方向是強化大學(xué)間的競爭,加強對大學(xué)的問責(zé)。1995 年成立了高等教育管理評審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Review,又稱豪爾評審委員會),其職責(zé)是對大學(xué)的治理、組織效益、財務(wù)管理和責(zé)任制進行評審。在評審之后,該委員會建議大學(xué)采用現(xiàn)代治理制度和管理措施以回應(yīng)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期望。[8]強調(diào)將大學(xué)科研納入澳大利亞“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大學(xué)科研要成為創(chuàng)新型經(jīng)濟增長的基礎(chǔ),從而提高澳大利亞企業(yè)的國際經(jīng)濟競爭力。為此政府將科研經(jīng)費與科研成果更密切地掛鉤,借鑒英國“研究水平評估作業(yè)”(RAE)制定了“研究質(zhì)量框架”(Research Quality Framework,RQF),對大學(xué)科研成果進行評審,并根據(jù)大學(xué)科研成果的質(zhì)量分配政府科研經(jīng)費,這促使大學(xué)采用績效管理制度來推進大學(xué)內(nèi)部治理制度改革。[9]
2003 年以來的第四次改革浪潮的方向是政府不再對大學(xué)實施具體的程序性管理,而是以遠程導(dǎo)向(steering at a distance)來加強國家對大學(xué)質(zhì)量的監(jiān)管,以“澳大利亞科研卓越評價”(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ERA)取代了“研究質(zhì)量框架”,進一步強化了以科研產(chǎn)出的質(zhì)量和學(xué)生的質(zhì)量為基礎(chǔ)來分配經(jīng)費;要求大學(xué)成為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中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為提高澳大利亞全球經(jīng)濟競爭力服務(wù);要求大學(xué)學(xué)習(xí)企業(yè)的治理模式,提高大學(xué)的管理效率,加速大學(xué)治理企業(yè)化的過程,學(xué)術(shù)的聲音開始被排除在決策之外。[10]
(二)當(dāng)代世界大學(xué)治理改革的趨勢與問題分析
1.基本趨勢
以上三國大學(xué)治理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過去幾十年世界大學(xué)治理改革的基本走勢。
第一,改革基本上都是由中央政府發(fā)起、自上而下推動的,強制大學(xué)改革內(nèi)部治理制度以適應(yīng)外部社會的重大變化。第二,在政府的推動下,大學(xué)治理企業(yè)化了,建立起類似企業(yè)的大學(xué)治理董事會,大學(xué)領(lǐng)導(dǎo)的行為和價值更像企業(yè)的CEO,大學(xué)在外部通過野心勃勃的營銷,與其他大學(xué)開展激烈競爭,擴大生源,爭取更多的中央政府科研經(jīng)費,在內(nèi)部通過績效測評分配資源,不斷擠壓教師的學(xué)術(shù)權(quán)力,擴大行政權(quán)力。第三,學(xué)生被視作高等教育的消費者,保護消費者權(quán)益成為大學(xué)治理中的新詞匯,對學(xué)生評價教師結(jié)果的不當(dāng)使用影響了教師士氣和教育質(zhì)量。第四,由于大學(xué)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中最古老和最穩(wěn)定的社會機構(gòu),雖然政府強勢推動了改革,但在大學(xué)特別是歷史悠久的一流大學(xué)中,依然保留了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的影響,尤其是在學(xué)院層面,教授依然是決策的主體。因此在大學(xué)中幾種治理模式并存,相互博弈,相互制約,未來大學(xué)治理將走向何處依然是一個常研究常新的問題。
2.凸顯的問題
過去幾十年高等教育的變革,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是成功的。高等教育規(guī)模明顯擴大了,辦學(xué)效率提高了,如澳大利亞在1996—2005年間,大學(xué)生數(shù)量增加了51%,國際學(xué)生數(shù)量增加了350%,與此同時教師數(shù)量卻減少了1.3%。[11]這使澳大利亞高等教育不僅滿足了國內(nèi)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國內(nèi)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而且占領(lǐng)了國際高等教育市場的很大份額。但是這些改革也帶來了一些負效應(yīng)。
第一,大學(xué)規(guī)模不斷擴大,推動了大學(xué)內(nèi)行政人員的增多和機構(gòu)層次的增加,這就導(dǎo)致了學(xué)術(shù)人員和學(xué)生與大學(xué)的疏離。第二,高等教育過度的市場化使大學(xué)內(nèi)學(xué)科間的平衡被打破,管理和商業(yè)等學(xué)科發(fā)展不受控,而不盈利的學(xué)科被邊緣化。第三,由于政府對大學(xué)連續(xù)實施評價,如英國的“科研水平評估作業(yè)”和“澳大利亞科研卓越評價”,導(dǎo)致大學(xué)在校內(nèi)過度倚重“績效評價”,對教師制定了過多的規(guī)定,使教師不得不順從新的游戲規(guī)則,從而抑制了他們的創(chuàng)新力。第四,由于政府將大學(xué)的科研績效與經(jīng)費分配直接掛鉤,大學(xué)在內(nèi)部資源分配上也與各種績效評價直接掛鉤,導(dǎo)致基層學(xué)術(shù)組織與教師利用這種制度來擴大組織和個人的利益,攫取名聲,從而扭曲了大學(xué)的價值觀,引起了大學(xué)內(nèi)部的價值紛爭,削弱了學(xué)術(shù)共同體。第五,“審計文化”的發(fā)展促使學(xué)術(shù)事務(wù)的權(quán)力從學(xué)者手中轉(zhuǎn)到了行政人員手中。第六,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不斷增大,工資水平?jīng)]有顯著增長,甚至有所下降,臨時聘任的教師數(shù)量大增,這一切導(dǎo)致教師對管理層失去信任。第七,由于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大學(xué)缺少長遠和戰(zhàn)略性的財政基礎(chǔ),大學(xué)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第八,企業(yè)化改革促進了學(xué)術(shù)消費主義,大學(xué)教育越來越“昂貴”,學(xué)生通過支付學(xué)費成為高等教育的消費者,獲得了評價教師和學(xué)院的權(quán)利。許多學(xué)者認為,學(xué)生評價導(dǎo)致“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和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的式微”。[12]對于大學(xué)治理改革所帶來的以上問題,許多高等教育研究學(xué)者和大學(xué)教師都有痛徹心扉的認識,他們開始研究并倡導(dǎo)重構(gòu)學(xué)術(shù)共同體。
三、回歸傳統(tǒng),重構(gòu)學(xué)術(shù)共同體
如果將過去幾十年企業(yè)和其他社會機構(gòu)的改革與大學(xué)的改革進行比較研究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大學(xué)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更趨同于私企,變得更集權(quán)化,更科層化,教師不斷被排除出大學(xué)決策過程。但是企業(yè)的管理制度卻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變化,傳統(tǒng)指令/控制型的管理、由上自下驅(qū)動型的管理正在讓位給較少科層、較扁平和更靈活的管理,企業(yè)正在更多地賦權(quán)給員工,使員工有更多的機會和權(quán)利參與管理。此外,大學(xué)的管理改革似乎與20世紀(jì)80年代出現(xiàn)的“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并不完全一致,“新公共管理”所倡導(dǎo)的是通過公共服務(wù)瘦身,更注重市場導(dǎo)向,使管理更扁平,也更注重分權(quán),從而降低成本。顯然大學(xué)采納了“新公共管理”市場化的原則,卻與“新公共管理”分權(quán)/參與原則背道而馳。
另一個令人深思的現(xiàn)象是,政府要求大學(xué)把學(xué)生置于高等教育的中心(英國《2001白皮書》),同時大學(xué)卻把教師逐漸排擠出決策的中心。在教師參與決策方面,大學(xué)似乎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共同體制度下教師的完全參與,過渡到新公共管理制度下教師被盡量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加拿大高等教育學(xué)者奈特(Peter. T. Knight)等人對英國和加拿大大學(xué)學(xué)術(shù)共同體制度進行了研究,他們發(fā)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共同體制度衰退的大學(xué),教師間的交往減少,教師用在大學(xué)之外的精力和時間增加,大學(xué)對教師福利的關(guān)心減少,而對教師的索取增多,他們把這樣的大學(xué)稱為“貪婪的機構(gòu)”。[13]因此我們有必要回歸大學(xué)的傳統(tǒng),重構(gòu)學(xué)術(shù)共同體,制衡政府推動大學(xué)市場化和科層化的沖動,遏制大學(xué)內(nèi)部專業(yè)管理者對權(quán)力的貪婪吞噬。
(一)學(xué)術(shù)共同體——大學(xué)的遺傳特征
從“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視角審視現(xiàn)代大學(xué)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出現(xiàn)代大學(xué)有以下六個重要傳統(tǒng)。第一個是學(xué)科中心,大學(xué)的基礎(chǔ)組織結(jié)構(gòu)以學(xué)科為基礎(chǔ)。在大學(xué),院系的數(shù)量是有限的和可控的。在科學(xué)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的今天,新的知識不斷產(chǎn)生,但是能不能成為一門學(xué)科,要經(jīng)過相當(dāng)長時間的檢驗,能夠沉淀下來,才能成為一門新的學(xué)科,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形成建立新的院與系的基礎(chǔ)。所以,院系是相當(dāng)穩(wěn)定的,不會輕易建立,也不會輕易地被撤銷或合并。既然院系是一種長期穩(wěn)定的存在,這就形成了現(xiàn)代大學(xué)制度的第二個重要傳統(tǒng),即學(xué)院的自治。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學(xué)、牛津大學(xué)與劍橋大學(xué)。哈佛大學(xué)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就是“每個澡盆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基礎(chǔ)上”,所謂“每個澡盆”就是每個學(xué)院,這些學(xué)院都有自己的管理理事會、監(jiān)事會,自己籌款,在錄取、課程和畢業(yè)標(biāo)準(zhǔn)以及教師的選聘與晉升等重大方面都有相當(dāng)大的自主權(quán)。牛津大學(xué)和劍橋大學(xué)的學(xué)院,雖然與美國大學(xué)的學(xué)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自治,大學(xué)僅僅是院與系的獨聯(lián)體。第三個傳統(tǒng)就是教授治校。巴黎大學(xué)是學(xué)者、教授、教師的行會。現(xiàn)代大學(xué)成立近千年,利益群體不斷多元,但是教授始終處于中心地位,在歐洲大陸,尤其是以德國為代表,大學(xué)是以講座教授為中心組成的,講座教授在本學(xué)科專業(yè)中具有絕對的權(quán)威。盡管美國大學(xué)更具民主和平等的傳統(tǒng),但仍然是以教授(含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為中心,實行教授治校,大學(xué)制定了完善的制度,保證教授在大學(xué)一切重大制度和政策制定中的參與權(quán)利。第四個傳統(tǒng)是民主管理。院系管理的基礎(chǔ)原則是民主而非效率,這是與當(dāng)代管理理念所不同之處。大學(xué)的管理,特別是院系的管理是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礎(chǔ)上,其核心理念是通過形成一致的意見來實現(xiàn)管理,院系自治就保障了民主平等這一基本原則的實施。第五個傳統(tǒng)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文化。學(xué)院或系是一個學(xué)術(shù)共同體,在其中形成了大家一致認可的行為準(zhǔn)則,即共享平等的權(quán)利,具有共同的責(zé)任,通過一致意見的達成作出決定,尊重個人的思想權(quán)利,構(gòu)建和諧的氛圍,這幾乎成了共同體成員的信仰。在這種學(xué)術(shù)共同體里拂去世俗的紛擾,靜下心來從事自己所喜愛的對真理的探索工作,對于大學(xué)教師的生存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成為吸引大學(xué)教師留在學(xué)院或系安身立命的最重要因素。第六個傳統(tǒng)是學(xué)術(shù)自由。學(xué)術(shù)共同體與學(xué)術(shù)自由是共生的,兩者相互依存,教師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主體,學(xué)術(shù)共同體是學(xué)術(shù)自由的組織保障,學(xué)術(shù)自由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存在的靈魂。
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歷史可以上溯到中世紀(jì)現(xiàn)代大學(xué)的成立,雖然近幾十年來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大學(xué)治理改革,不斷強化了大學(xué)行政權(quán)力,但是這并不能完全改造大學(xué)的遺傳基因。大學(xué)與企業(yè)和政府機構(gòu)不同,不是單一權(quán)威指揮運行的機構(gòu),大學(xué)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雖然不斷受到擠壓,但仍然頑強地存在著,可以說沒有了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就改變了大學(xué)的本質(zhì)屬性,大學(xué)也就非大學(xué)了。“學(xué)者及其工作的性質(zhì)決定了很難像管理公仆那樣管理他們。”[14]“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在大學(xué)中特別成問題,因為在大學(xué)中專業(yè)權(quán)威制度限制了行政權(quán)威。”“學(xué)者是自我規(guī)制的手工藝者,他們不承認任何老板,對于更廣義的制度不感興趣。”“他們的工作是個體化和智力型的,從外部很難控制他們的工作,使學(xué)者們‘就像貓一樣難以放牧’。”學(xué)者對外部的審計不滿,認為耽誤他們的工作,貶低他們個別化工作的價值,也貶低他們追求卓越的價值。[15]
(二)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界定
在大學(xué)的各種治理模式中,應(yīng)該說“學(xué)術(shù)共同體”是最古老的,從大學(xué)的起源來看,它也是最自然天成的,長期為大學(xué)所奉行,為教師所認同,只是在過去幾十年開始被質(zhì)疑、被挑戰(zhàn)。但是許多高等教育研究者在經(jīng)歷過這幾十年的大學(xué)治理改革后,開始重新研究這一傳統(tǒng)的治理模式,努力定義“學(xué)術(shù)共同體”,從而改變傳統(tǒng)上“學(xué)術(shù)共同體”只被意會而沒有被精確定義的狀況。
2001 年著名高等教育學(xué)家伯頓·克拉克(Burton Clark)認為:“所謂‘學(xué)術(shù)共同體’最經(jīng)常的是指學(xué)術(shù)人員之間的相互尊重,或者是指一組專業(yè)人員的自我治理。學(xué)術(shù)共同體作為一種治理形式,倡導(dǎo)一種‘我們’意識,我們對于我們自己的選擇負責(zé)。”[16]1988年里弗斯(M. Reeves)曾將學(xué)術(shù)共同體定義為:“對價值規(guī)范具有共同認知”的教師共同體,這種共同認知使他們能夠抵抗過度的外界壓力以及缺少責(zé)任心的個人主義。[17]也就是說,學(xué)者要有維系和培植他們專業(yè)價值觀的責(zé)任,從而保護自己不受內(nèi)外勢力的擠壓。羅伯特·伯恩鮑姆(Robert Birnbaum)視“學(xué)術(shù)共同體”為終身聘用軌教師的共同體。他認為這些學(xué)者間的互動大量的是非正式的,學(xué)者間是平等的,決策是民主的,強調(diào)深思熟慮和協(xié)商一致的決策。管理者要“服從學(xué)者共同體,落實學(xué)者共同體的意愿”,管理者是“業(yè)余的”,而非“專業(yè)的”,領(lǐng)導(dǎo)是選舉而非任命產(chǎn)生的,他們被同事挑選出來是因為同事相信他們是踐行共同體規(guī)范的典范,領(lǐng)導(dǎo)不是老板,而是“平等首位者”。在學(xué)者共同體中,學(xué)者的行為主要受非正式規(guī)范控制,因為非正式規(guī)范要比正式的、書面的規(guī)定更為有力。[18]西普利安諾(R. E. Cipriano)和布勒(J. L. Buller)認為學(xué)術(shù)共同體成員的行為有六個特點:樂于與其他教師和行政人員合作;需要時會“站出來”服務(wù)于公眾利益;對工作負責(zé);尊重學(xué)校的決策程序;尊重他人;樂于支持和幫助他人。[19]艾倫·布里曼(Alan Bryman)認為,學(xué)術(shù)共同體主要是指由共同一致意見作出決策的治理制度,或者是指成員之間的相互支持。[20]2009年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因創(chuàng)建性地提出“公地治理模型”而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xué)獎,她在獲獎演講中認為,市場力量與國家規(guī)章都不是治理、管理和提供復(fù)雜的公共物品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21]她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中將“公地治理模型”明確無誤地用于大學(xué),她認為最好把大學(xué)看作人性建構(gòu)的自我組織的“知識共同體”。[22]奧斯特羅姆強調(diào),從長遠來講,面對面的溝通是增加必要的合作與協(xié)調(diào)的最有效途徑。
從以上我們列舉出的諸多學(xué)術(shù)共同體定義來看,學(xué)術(shù)共同體首先是一種大學(xué)治理制度。作為一種治理制度,學(xué)術(shù)共同體首要關(guān)注的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領(lǐng)導(dǎo)的產(chǎn)生。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領(lǐng)導(dǎo)必須由共同體全體成員民主選舉產(chǎn)生,經(jīng)選舉產(chǎn)生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導(dǎo)只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中的“平等首位者”。學(xué)術(shù)領(lǐng)導(dǎo)崗位是一個非永久性的、非全日制的職位,這就意味著學(xué)術(shù)領(lǐng)導(dǎo)只是一個時間段的領(lǐng)導(dǎo),在任期結(jié)束后就回到他從前的學(xué)術(shù)崗位,再次成為共同體中的一般成員。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制度的最高原則是協(xié)商一致作出決策,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決策必須以知識為基礎(chǔ)。討論、批評、篩選論據(jù)和得出結(jié)論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制度的核心特征。領(lǐng)導(dǎo)作為“平等首位者”主持這種決策討論,領(lǐng)導(dǎo)個人的意見和舉措也要在討論中被質(zhì)疑和檢討,領(lǐng)導(dǎo)只有傾聽同仁專家的意見才能保持其地位的合法性,因為他的權(quán)威是經(jīng)同仁選舉而被授予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領(lǐng)導(dǎo)與他的同事共享權(quán)威。也就是說,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制度的基本出發(fā)點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通過科學(xué)論證協(xié)商一致作出決策比任何個人的決策更明智,只有通過同事間的討論、辯論、協(xié)商,才能實現(xiàn)思想的分享,才能在同事間共同分擔(dān)責(zé)任,從而使決策和決策的實施具有更高的效力。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制度是一種限制領(lǐng)導(dǎo)個人權(quán)力的治理制度,是一種賢能治理制度,是一種不以個人利益為轉(zhuǎn)移的治理制度,是一種知識永遠優(yōu)先于利益的治理制度,因此也是最適合大學(xué)內(nèi)基礎(chǔ)學(xué)術(shù)單位的治理制度。學(xué)術(shù)共同體既是傳統(tǒng)的也是現(xiàn)代的,既是民主的也是有效的,既是理想的也是實用的治理制度。
學(xué)術(shù)共同體是一種文化。學(xué)術(shù)共同體文化反映大學(xué)的基本文化——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的自由、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的至高無上、行政權(quán)威的寬容、管理上的民主協(xié)商。學(xué)術(shù)共同體也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念,一種隱性的行為規(guī)范,是大學(xué)教師的一種生存環(huán)境和生存方式,教師在選擇這一職業(yè)的同時,實際上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與一種文化環(huán)境。學(xué)術(shù)共同體文化主要的表現(xiàn)是,有效地與他人一道工作,平等待人,在學(xué)院和大學(xué)的共同管理中發(fā)揮積極的建設(shè)性作用,尊重他人的思想和主張(盡管不一定同意),相互信任,共享思想與知識,在一種開放交流的環(huán)境中共建集體責(zé)任意識,共同解決和處理不同意見,協(xié)商一致達成決策。
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治理基礎(chǔ)是學(xué)者個人對專業(yè)工作和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忠誠,而學(xué)者的忠誠來自他們對真理的追求和他們所持“大學(xué)是追求真理的最佳場所”的信念。特別是在學(xué)術(shù)共同體中出現(xiàn)不同意見的沖突時,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制度給教師以充分發(fā)聲的機會,讓教師可以毫無顧忌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在爭辯中尋求真理,在討論中形成決策,這樣就避免了教師因被管理者禁聲而選擇退出,即選擇另一所大學(xué)或者選擇內(nèi)部流放,消極順從,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從而使學(xué)術(shù)共同體失去教師的忠誠而走向瓦解。
社會學(xué)家海奇(J.Hage)認為,教師要就專業(yè)工作進行溝通,這種溝通不是垂直的與管理者的溝通,而是水平的與受尊重的同仁進行口頭的、面對面的、持續(xù)的交流與溝通。[23]麥爾斯(M.P. Miles)認為,相互尊重和信任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文化的倫理基礎(chǔ),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成員社會化的指導(dǎo)原則。[24]
綜上所述,學(xué)術(shù)共同體是大學(xué)的基礎(chǔ)治理制度,是大學(xué)的核心文化,也是大學(xué)教師的隱性行為規(guī)范,還是規(guī)定大學(xué)不同群體間關(guān)系的準(zhǔn)則。
(三)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構(gòu)建
哈佛大學(xué)教育研究生院曾經(jīng)就教師對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看法對美國51 所院校的4500 名終身聘用軌教師做過調(diào)查,他們發(fā)現(xiàn)教師們對所在院系的氛圍、文化和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關(guān)注遠要高于對工作量、終身聘用制度和報酬的關(guān)注,對問卷的回答進行的回歸分析表明,對于預(yù)測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性來說,氛圍指標(biāo)比報酬指標(biāo)重要五倍。[25]
而當(dāng)前大學(xué)的各級領(lǐng)導(dǎo)更關(guān)注的是合同、目標(biāo)、標(biāo)準(zhǔn)和指標(biāo)而非人,他們的這種價值取向?qū)е聦W(xué)術(shù)環(huán)境不斷惡化,學(xué)術(shù)共同體不斷被解構(gòu),大學(xué)中管理者和學(xué)術(shù)人員之間的相互信任不斷被削弱。因此大學(xué)當(dāng)前緊迫的任務(wù)是重構(gòu)學(xué)術(shù)共同體,承認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存在及其在大學(xué)中的核心位置。
我們要構(gòu)建一種平等對話的、和諧的學(xué)術(shù)共同體文化,這是建設(shè)世界一流大學(xué)的基本保障。我們要促進在教師與教師之間、教師與行政人員之間搭建重要的交流平臺,大學(xué)文化與企業(yè)及政府文化顯著的不同就在于大學(xué)的決策形成于廣泛的、永無止境的交流與溝通之中。這樣的決策方式可能會慢一些,也可能出錯,但是很少會有未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政策出臺,因為大學(xué)教師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思考、質(zhì)疑和批評。
我們要以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制度的建設(shè),制約不斷膨脹的行政權(quán)力。這在當(dāng)前大學(xué)官僚化和商業(yè)化勢不可擋的潮流中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是解決校園腐敗的一劑良方,因為它搭建了限制行政絕對權(quán)力的制度框架。
我們要在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制度與科層治理制度之間保持平衡,以制度和組織的形式保證教師參與大學(xué)一切重大事務(wù)決策的權(quán)利,同時保證政府通過大學(xué)行政所提出的社會需求與期望在大學(xué)的重大決策中得到體現(xiàn)。因此,我們要建立學(xué)術(shù)評議會(或稱教授委員會)。學(xué)術(shù)評議會是大學(xué)治理中各方應(yīng)該予以支持和尊重的核心機構(gòu),是代表全校教師參與大學(xué)治理的實體機構(gòu)。正如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歷史學(xué)講座教授基恩·布魯克(Gene Brucker)所說:“……學(xué)術(shù)評議會創(chuàng)建了一種大學(xué)行政和教師共同治理理念的制度模式。這種責(zé)任分擔(dān)在其他院校尚未廣泛實施,因為這要求行政有分權(quán)的意愿,教師有投入時間和精力使這一制度運轉(zhuǎn)的意愿。在我看來,這是保持伯克利世界一流大學(xué)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26]校長既應(yīng)該是大學(xué)的最高行政負責(zé)人,也應(yīng)該是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代表。他的責(zé)任是促進教授和行政人員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相互尊重,共同協(xié)商與共同決策。1953 年羅伯特·斯普羅爾(Robert Gordon Sproul)總結(jié)其任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校長23年的經(jīng)驗時寫道:“大學(xué)校長最重要的職能莫過于與教師保持密切的關(guān)系”,沒有教師的信息、意見和建議,“組織名義上的首腦時常會患上缺氧癥,其典型的癥狀是視力喪失,步履蹣跚遲緩,左右搖擺,止步不前。”[27]
特別是在學(xué)院(學(xué)部)一級,“院長們可能認為,教師不搞事、不質(zhì)疑行政就是好同事……然而教師們對一名好同事的描述是善于合作,對有利于學(xué)生、院系和其他同事的活動作出積極貢獻的同事”[28]。院長和教師之間的認識差別導(dǎo)致學(xué)院成為教師和行政沖突的場所,院長現(xiàn)在成為大學(xué)科層治理的一個重要級別,由大學(xué)層面任命產(chǎn)生,院長成為首先對校領(lǐng)導(dǎo)負責(zé)的官僚,這使學(xué)院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受到極大的破壞。因此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重構(gòu)應(yīng)該始于學(xué)院,學(xué)術(shù)共同體治理制度應(yīng)該成為學(xué)院治理的根本制度,院長應(yīng)由教師選舉產(chǎn)生,學(xué)院內(nèi)教授委員會、學(xué)術(shù)委員會和學(xué)位委員會等教師委員會應(yīng)該成為學(xué)院的政策制定機構(gòu),院長的主要職責(zé)是落實各相關(guān)委員會制定的政策,同時在大學(xué)層面的政策指令與學(xué)院各委員會制定的政策之間進行協(xié)調(diào),使兩者融合一致。學(xué)院層面的學(xué)術(shù)共同體建好了,大學(xué)的文化和治理的基礎(chǔ)就打牢靠了。
四、結(jié)語
學(xué)術(shù)共同體促進大學(xué)人才輩出,保證大學(xué)不斷產(chǎn)生原創(chuàng)性研究成果。學(xué)術(shù)共同體可以使教師成為有勇氣、有士氣、有追求、正直的大學(xué)主人,從而使教師煥發(fā)創(chuàng)造的潛能,投身于教育這一崇高的事業(yè)。同樣,在學(xué)術(shù)共同體文化和制度的建設(shè)過程中,大學(xué)各層領(lǐng)導(dǎo)在與教師碰撞的張力中,可能學(xué)會理解大學(xué)的本質(zhì)特征,學(xué)會尊重大學(xué)教師這一特殊的群體,讀懂他們的特殊氣質(zhì)和思維特點,認識到教師是大學(xué)的心臟,將他們棄之不用、貶損和羞辱終會使大學(xué)乃至其自身付出重大代價。教師與領(lǐng)導(dǎo)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營建和諧的大學(xué)文化,通過制度保證相互間的持續(xù)溝通,共同作出學(xué)校重大決策,這是現(xiàn)代大學(xué)制度的根本,也是世界一流大學(xué)建設(shè)的重要文化基礎(chǔ)和制度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