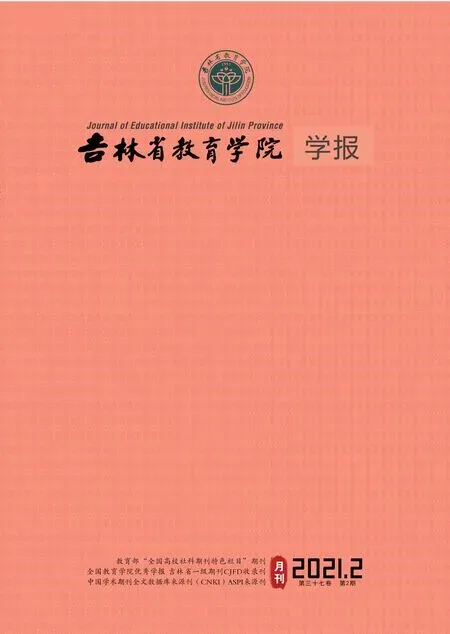《后花園》:蕭紅對生命價值的終極追問
劉愛華
(吉林省教育學院,吉林長春130022)
1933年,22 歲的蕭紅發表了處女作《棄兒》,1934年完成中篇小說《生死場》的寫作,1935年在魯迅的幫助下得以出版,以“鋼戟向晴空一揮似的筆觸,發著顫響,飄著光帶”[1]“給上海文壇一個不少的新奇與驚動”[2],從此成為文壇一顆耀眼的新星,蕭紅也以此邁入全國著名作家之林。此后蕭紅便筆耕不輟,出版了記錄她與蕭軍在哈爾濱期間困苦生活的散文集《商市街》、小說、散文集《橋》、短篇小說集《牛車上》。1937年,蕭紅從上海輾轉奔波于武漢、山西臨汾、西安、重慶、四川江津等地,過著漂泊不定的逃難生活,期間經歷了與蕭軍的分手、與端木蕻良的結合以及懷孕產子,但即便如此,蕭紅也從未停筆,創作了小說《汾河的圓月》《朦朧的期待》《逃難》《黃河》《曠野的呼喊》《蓮花池》等,還有很多散文、魯迅先生回憶錄、劇本等等,直至1940年來到香港,蕭紅有了一年多安靜的時間,終于完成了長篇小說《呼蘭河傳》《馬伯樂》的創作,同時創作并發表了小說《后花園》《小城三月》《北中國》,不幸的是,蕭紅此時疾病纏身,又恰逢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轟炸香港,蕭紅在戰火驚恐中不停地遷移顛簸,病情越發嚴重,終于在1942年1月22日結束了痛苦掙扎的一生,年僅31歲。
《呼蘭河傳》可以說是蕭紅創作走向成熟的巔峰之作,于1940年9月1日至12月27日連載于香港《星島日報》。《呼蘭河傳》延續并更加突出強化了蕭紅“作家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3]的創作取向,充分展現了呼蘭城人們習以為常、司空見慣的生活惰性和精神痼疾,其間彌漫著揮之不去的思鄉情結。小說的最后一章寫了磨倌馮歪嘴子在“自然的暴君”和“兩只腳的暴君”[1]的施虐下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和堅韌的耐力,而頗為耐人尋味的是,在《呼蘭河傳》發表之前的4月10日至25日蕭紅在《大公報》上先期連載了一部短篇小說《后花園》。讀過兩部作品會發現它們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都講述了后花園旁邊的磨房里一個磨倌的故事,《呼蘭河傳》里的磨倌叫馮歪嘴子,《后花園》里磨倌的名字是馮二成子,雖然寫的也是磨倌,但整個故事內容有了變化,人物性格也迥然不同,蕭紅通過小說所要表達的理念也有區別。據說,當時的實際生活中確有其人,是個長工,長年在磨房拉磨[4],同一個人物出現在兩部作品中的還有有二伯,在《呼蘭河傳》中蕭紅用不少筆墨寫了有二伯,其中第六章專門講述了有二伯的故事,而在更早之前的1936年9月4日蕭紅在東京完成的短篇小說《家族以外的人》,同樣充滿溫情地講述了有二伯的故事,應該說,除了祖父,有二伯就是蕭紅童年生活中的另一抹溫暖。而與有二伯不同,馮磨倌是個更加邊緣化的人物,在蕭紅的兒時記憶里也只是片斷性的若有若無的存在,但也因此給了蕭紅更多創造和想象的空間,給蕭紅提供了更多形而上思考的選擇可能。
一
從發表時間來看,《后花園》比《呼蘭河傳》稍早四個多月,《呼蘭河傳》大概有10 多萬字,由于顛沛流離的生活,蕭紅從醞釀到寫作再到發表歷時3年之久,據好友錫金回憶,1937年9月底蕭紅與蕭軍寄居于他位于武昌小金龍巷的寓所,并在1939年12月開始動筆寫作《呼蘭河傳》并完成了第一章,第二章還沒寫完就去了山西臨汾[5],之后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斷斷續續地繼續寫作,直到1940年1月來到香港,生活稍有穩定,終于完成《呼蘭河傳》的寫作。小說的第七章即最后一章,寫了馮磨倌的故事,大概1 萬余字,應該是在寫作整部小說的最后階段完成,而發表早于《呼蘭河傳》4 個多月的《后花園》的寫作時間應該與《呼蘭河傳》第七章的寫作時間前后相差不會太多,那么為什么蕭紅在幾乎同一時間對馮磨倌這一人物進行二度創造呢?
與《家族以外的人》《呼蘭河傳》第六章對有二伯的兩度創作不同,有二伯的故事實在太多,充滿蕭紅記憶的每個角落,可以信手拈來寫進作品,讓我們看到更加鮮活的有二伯,而《后花園》與《呼蘭河傳》對馮磨倌的描寫與敘述卻不僅僅是將人物更加豐盈和鮮活,其實還有更深層的意蘊和不同的創作指向。《呼蘭河傳》自始至終探討的是國民團體盲目、愚昧、麻木、殘忍等等劣根性,深刻地揭示了國民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的本質,在東北大地上這些“蚊子似的生活著,糊糊涂涂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1]的愚夫愚婦們自己已經生活在社會階層的最底端,但他們卻還像阿Q欺負尼姑、小D一樣欺負更加無助弱小的小團圓媳婦,而可悲的是他們殺人于無形之中卻不自知。小團圓媳婦就因為在他們眼里不像個小團圓媳婦,所以才要“好心”地施用各種家法,直到把小團圓媳婦折磨至死,可以說小團圓媳婦就是在這樣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的共謀下失去生命的。到了馮磨倌這里,左鄰右舍的“善人”們又故伎重施,連有二伯都加入了那些善男信女們的行列,對喜歡上馮磨倌并跟他生了孩子的王大姑娘極盡鄙視詆毀之能,而當王大姑娘拋下兩個孩子死去之后,人們非但不同情馮歪嘴子,還津津有味地看著熱鬧并造謠生事,仿佛他的兩個孩子沒有死掉、他也沒有崩潰是很令人失望的事,在此蕭紅不僅滿懷悲傷地揭示了家鄉愚民麻木、愚昧甚至殘忍的病態靈魂,更滿懷希望地寫了馮歪嘴子百折不撓的頑強生命力,而且是“原始性的頑強”,[6]馮歪嘴子在與“自然的暴君”和“兩只腳的暴君”[1]的博弈中沒有像小團圓媳婦那樣被摧毀,而是“照常地活在世界上”“照常地負著他那份責任”:“喂著小的,帶著大的,他該擔水,擔水,該拉磨,拉磨”[7],他懷著“這孩子眼看著就大了”[7]的喜悅在周圍人們“驚奇”和“恐懼”的目光下帶著兩個孩子“很有把握”地活著。
蕭紅在《呼蘭河傳》里對馮歪嘴子故事的敘述一方面延續了剖析國民不自知的無知和愚昧的悲劇主題,另一方面寫出了馮歪嘴子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對抗這麻木病態社會的“原始性的頑強”[6],在此消彼長中不被絕望擊垮,“他覺得在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長得牢牢的”[7]。馮歪嘴子作為一個渺小的小人物在聲勢浩大的傳統習俗和民眾歷來如此的慣性思維的重壓下沒有表現出激烈的抗爭,而是平靜地默默地忍受一切困苦和不幸,小草一般頑強而堅韌地活著。如果說《呼蘭河傳》里的民眾讓蕭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那么馮歪嘴子帶來的就是無聲的抗爭和絕處求生的韌性和耐力。
《后花園》里的馮二成子與《呼蘭河傳》里的馮歪嘴子一樣,都是住在后花園旁邊磨房里的磨倌,他們做著同樣的工作:打梆子、看小驢拉磨、打篩羅、搖風車……他們都結了婚生了孩子,他們的老婆都死掉了,馮二成子和馮歪嘴子住在同一個磨房里,做著同樣的工作,都曾娶妻生子,但他們的感情經歷和人生感悟卻是迥然不同的,《呼蘭河傳》里的馮歪嘴子生活在熱鬧嘈雜閑言碎語的人間煙火里,這部小說重點寫了馮歪嘴子與王大姑娘不為傳統觀念束縛,沒有“父母之命”,也無“媒妁之言”就同居在一起并且在簡陋寒冷的磨房里生了孩子,而這種行為在旁觀者的眼里是骯臟不堪、厚顏無恥的,自然就在街坊四鄰這個小社會環境里激起驚天波瀾。曾經一起幫助老胡家婆婆“規矩”小團圓媳婦的周三奶奶、楊老太太、老廚子甚至有二伯又不謀而合地聚在一起對王大姑娘進行評頭品足、造謠誹謗、惡意攻擊,而馮歪嘴子和王大姑娘不畏各種惡言惡語、譏諷嘲笑,共同抵擋著東北寒冷的冬天和周圍鄰舍們的流言蜚語,表現出他們彼此的恩愛、體貼和溫馨,這樣的場景在蕭紅小說中是極為罕見的,甚至是絕無僅有的,可能也寄托著蕭紅對理想婚姻的美好向往和希望吧。馮歪嘴子的故事作為《呼蘭河傳》的一部分與其他章節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蕭紅幼年記憶里的呼蘭河這座小城。
而獨立成篇的《后花園》不同于《呼蘭河傳》的第七章,著重描述了馮二成子千篇一律毫無變化的日常生活,馮二成子才三十多歲,頭發就白了許多,牙齒也脫落了好幾個,“看起來是個青年的老頭”。[8]他活著,但卻沒有任何感知,“陰天下雨,他不曉得;春夏秋冬,在他都是一樣”,“他什么都忘了,他什么都不記得,因為他覺得沒有一件事情是新鮮的”,說他是個活死人也毫不為過。他跟磨房里的小驢一樣知道,“一上了磨道就該開始轉了,所以走起來一聲不響”[8],毫無生氣。可是忽然有一天,馮二成子聽到隔壁趙老太太女兒的笑聲,從此心情不平靜起來,深深地被女孩吸引而不能自拔。然后他的記憶復活了,他想起了母親來探望他、回到鄉下不久就死了,也想起小時候“在沙灘上煎著小魚,在河里脫光了衣裳洗澡;冬天堆了雪人,用綠豆給雪人做了眼睛,用紅豆做了嘴唇;下雨的天氣,媽媽打來了,就往水洼中跑……媽媽因此而打不著他”[8]。鄰家女兒喚醒了一直沉睡的馮二成子,他開始失眠,想到母親說過的“成親”兩個字居然“臉紅了一陣”,“他的眼睛充滿了亮晶晶的眼淚,他的心中起了一陣莫名其妙的悲哀”,此時馮二成子是一個活生生地活著的人了。不過他的暗戀沒過多久,鄰家女兒就出嫁了,他的戀愛還沒開始就結束了。值得欣慰的是,女兒出嫁了,馮二成子便常常和趙老太太攀談,把她當作一位近親來看待,生活有了煙火味。遺憾的是,沒多久,趙老太太也要搬到女兒家去了,他幫著趙老太太收拾東西,最后送了一程又一程,轉身返回的時候,馮二成子的腳沉重起來,心也越來越空虛,“越走越往遠處飛”,他的生命意識忽然復活了一般,他放眼望去,“他望到的,都是在勞動著的,都是在活著的,趕車的趕車,拉馬的拉馬,割高粱的人,滿頭流著大汗。還有的手被高粱稈扎破了,或是腳被扎破了,還浸浸地沁著血,而仍是不停地在割。他看了一看,他不能明白,這都是在做什么;他不明白,這都是為著什么。他想:你們那些手拿著的,腳踏著的,到了終了,你們是什么也沒有的。你們沒有了母親,你們的父親早早死了,你們該娶的時候,娶不到你們所想的;你們到老的時候,看不到你們的子女承認,你們就先累死了”[8]。馮二成子完全陷入了迷惘狀態,“路上他遇上一些推手車的,挑擔的,他都用了奇怪的眼光看了他們一下:你們是什么也不知道,你們只知道為你們的老婆孩子當一輩子牛馬,你們都白活了,你們自己還不知道。你們要吃的吃不到嘴,要穿的穿不上身,你們為了什么活著,活得那么起勁”[8]。馮二成子一路上所看到的幾乎完全是這一類人,“他用各種眼光批評了他們”。他回想起鄰家女兒的種種美好,但一切都晚了,“永久不會重來了”,他失魂落魄,他不明白“是誰讓人如此,把人生下來,并不領給他一條路子,就不管他了”[8]。他回到磨房,發現一切都沒有變動,磨盤、羅架、小驢、耗子、鄰居都跟往常一樣,“昨天和今天是一點也沒有變”“什么也沒有變”,他想跟往常一樣把小驢架到磨上,打起梆子,但他沒能做到,“他好像丟了什么似的,好像是被人家搶去了什么似的”,周遭的一切依舊如常,但馮二成子已經不是昨天那個馮二成子了。他開始有了思維,有了意識,對人生有了質疑,對他所見的那些埋頭忙碌的人在心里進行了批評,他在街上閑蕩了半夜,經過靠縫衣服過活的王寡婦的家時走了進去,在這里,馮二成子和王寡婦聊得頗為投機,王寡婦不僅理解他的心情,所發的議論也跟馮二成子相契合:“人活著就是這么的,有孩子的為孩子忙,有老婆的為老婆忙,反正做一輩子牛馬。”[8]王寡婦盡管也才三十多歲,但跟馮二成子一樣,頭發也白了一半,她感嘆:“年輕的時候,誰還不是像一棵小樹似的,盼著自己往大了長,好像有多少黃金在前邊等著。可是沒有幾年,體力也消耗完了,頭發黑的黑,白的白……”馮二成子聽了王寡婦的話心里平靜了許多,兩人百感交集,“彼此哭了一遍”,沒有像別人那樣敲鑼打鼓,但很莊嚴地結了婚。后來,在磨房里他們的孩子出生了,過了兩年,孩子的媽媽死了,不久孩子也死了,馮二成子又回到了從前,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他“伏在梆子上,每每要打瞌睡”,從此便昏昏庸庸地“在那磨房里平平靜靜地活著”,繼續“打他的篩羅”“搖他的風車”[8]。馮二成子仿佛參透了人生的意義,活著或者死去已經不是一個難題,在他看來,一些終將歸于虛無,所以對他來說,經冬復歷春,人同后花園里的植物一樣隨季節不斷地輪回,周而復始,生死更迭。
二
1942年1月,蕭紅被醫生誤診做了手術,又恰逢日軍占領香港,接管了醫院,蕭紅無院可住,無藥可用,導致病情惡化,不到十天就離開人世,年僅31歲。在蕭紅離世前的一個多月里,同樣是東北作家的駱賓基應端木蕻良的懇求留在香港幫助照顧和陪伴蕭紅,在炮火的轟擊下,在停電停水、逃得空無一人的大樓里,在短暫安寧的間隙,病榻上的蕭紅與駱賓基像姐弟一樣無話不談,蕭紅不僅向駱賓基講述了自己的坎坷經歷,還跟他講述了一篇關于萬花筒的小說的構思,后來駱賓基把它整理記錄下來,以《紅玻璃的故事》為題,發表在1943年1月15日出版的《人世間》第一卷第三期上,此時蕭紅已經去世一年了。這篇小說講述的是樂觀開朗愛說愛笑的王大媽去女兒家給過七歲生日的外孫女送雞蛋,看到外孫女正在玩一個紅玻璃萬花筒,忽然失神落魄,想起自己童年時曾玩過這紅玻璃的花筒,她女兒也曾玩過,現在外孫女還在玩,一代又一代,循環往復,無休無止。王大媽忽然“對命運有所悟”,她丈夫十幾年前去黑河挖金子至今音信皆無,女婿五年前去黑河挖金子至今也不知是死是活,難道她們祖孫三代都逃不掉這樣可怕的命運嗎?男人們一去不回,女人們成了活寡婦,她和她的女兒如此,她的外孫女的命運也會如何嗎?她忽然覺得自己是“這樣孤獨,她過的生活是這樣可怕”,從女兒家回來的王大媽從此變了,“她已經窺破了命運的奧秘,感覺到窮苦、孤獨,而且生活可怕”。她似乎參透了命運的玄機,識破了人生的結局,對生沒有歡樂,對死沒有悲傷,生死輪回已變得毫無意義,一切皆無意義。從前那個“最愉快““又愛說話,又愛笑”“有著一雙充滿生命力的眼睛”“生就一身結實的筋肉”“腰粗,臂膀壯”“胃口也健旺”“活像一個跑關東的漢子”的王大媽不見了,從女兒家回來的路上,她看到屯口那座新墳的時候不像往常那樣“贊美那墓石和香案的講究”,而是想:“這里是埋葬著一個什么樣的人呢!也許他生前是個闊財主,也許遺留在世上一些叔伯、子孫和親族,而他自己是解脫了……”王大媽回到屯子后,屯子的人“聽不見她的話聲了,再也望不見她那充滿生命力的眼睛和笑容了”,不久王大媽就病倒了,臨死前對兒子說:“到黑河挖金子去吧!”王大媽死后,她的兒子就背著小包袱也去黑河挖金子去了。最終男人們逃不掉外出淘金的命運,女人們也逃不掉孤獨終老的命運。
《紅玻璃的故事》很容易讓人想起《后花園》,從女兒家回來的王大媽在路上的所見所想與《后花園》里送完趙老太太回來的路上馮二成子的所見所想何其相似,如果假以時日,蕭紅能親自動筆來寫這部小說,估計會寫得更細致更豐富更深入,畢竟駱賓基是聽蕭紅口述并在一年后憑借記憶記錄下來的,呈現出來的可能只是一個大致輪廓,但即便如此,也能從中明顯看出蕭紅當時的一些感悟和情緒狀態。
在《紅玻璃的故事》里,萬花筒更是一個象征符號,從萬花筒看進去是變化莫測和絢爛多彩的圖景,是令人眼暈目眩的美麗世界,人們往往為它的繽紛絢爛所吸引而陶醉其中、不能自拔,就像未來的人生,我們永遠對它的美好抱有期待,滿懷希望。而人一旦長大,就會知道萬花筒呈現出來的只是一個虛幻的世界,就像一場美夢,夢醒了,一切都破碎了。當王大媽拿過外孫女的紅玻璃花筒“閉一只眼向里觀望時”,她看到了她自己的童年,她女兒的童年,現在是她外孫女的童年,三代人的童年就在這神奇的紅玻璃花筒面前重疊了,再現了,她“想起她自己的童年時代,也曾玩過這紅玻璃的花筒。那時她是真純的一個愉快而幸福的孩子;想起小達兒她娘的孩子時代,同樣曾玩兒過這紅玻璃花筒,同樣走上她做母親的寂寞而無歡樂的道路。現在小達兒是第三代了,又是玩兒著紅玻璃花筒”,難道外孫女將來的命運也是“出嫁,丈夫到黑河去挖金子,留下她來過這孤獨的一生?誰知道,什么時候,丈夫挖到金子,誰知道什么時候做老婆的能不守空房”?以前王大媽從來沒有仔細想過這些事情,現在想起來,“她奇怪自己終究怎么度過這許多年月的呢!而沒有為了柴米愁死,沒有為了孤獨憂郁死”。猶如馮二成子眼看著喜歡的鄰家女兒出嫁又送別了趙老太太后產生的困惑:“人活著為什么要分別?既然永遠分別,當初又何必認識!人與人之間又是誰給造了這個機會?既然造了機會,又是誰把機會給取消了”?[8]他看到那些趕車的、拉馬的、挑擔的、割高粱的、賣豆腐的在忙忙碌碌,他在想:“你們是什么也不知道,你們只知道為你們的老婆孩子當一輩子牛馬,你們都白活了,你們自己都不知道。你們要吃的吃不到嘴,要穿的穿不上身,你們為了什么活著,活得那么起勁!”[8]與王大媽頓悟了人生、萬念俱灰,最后失去活著的動力不同,馮二成子在悟到了似乎是人生的真相之后沒有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反倒一切歸于平靜,剛剛送走趙老太太的那回事“似乎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他的心境自由得多了,也寬舒得多了”,最后他順從了命運的擺布,同其他被他批評過的人一樣結婚、生子,只是沒了生的歡喜,也沒了死的悲痛,老婆死了,孩子死了,對他都不再產生什么沖擊,人的生與死猶如花的開與謝,任憑命運的發落,他活著,但靈魂死了。而《紅玻璃的故事》里的王大媽一旦參透了命運,就同《小城三月》里的翠姨一樣走向自我毀滅。
三
蕭紅短暫生命的最后兩年是在香港度過的,在香港的兩年里,她完成了《呼蘭河傳》《小城三月》《后花園》《馬伯樂》等小說的創作,這幾部小說無論在深層內蘊上還是藝術表達上都日臻成熟,堪稱蕭紅的巔峰之作。《馬伯樂》依舊延續了蕭紅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集中刻畫了一個極端自私、毫無責任感、妄自尊大、崇洋媚外、虛偽滑稽、膽小懦弱的小人物形象。在娓娓道來的淡定敘述中處處透出毫不留情的辛辣。遺憾的是,蕭紅的身體每況愈下,小說最終沒有完結。縱觀蕭紅的小說創作,我們發現,蕭紅離家越遠,她的思鄉情結越濃郁,時間和空間距離的拉長和加大越來越讓她的內心與家鄉和童年交融在一起,久遠的過去一幕幕地閃現在她的眼前,流淌到她的筆下,于是我們看到了《后花園》《小城三月》《北中國》等小說,跟著她的回憶一起踏上回家的路,走進她的童年。1941年7月,蕭紅的身體日漸衰弱,經常頭痛、咳嗽、心悸、氣促、失眠,終于住進了醫院,也由于體力不支,無法繼續創作,《馬伯樂》連載完第九章時不得不停下,最終蕭紅也未能完成這部小說。而令人感到欣慰和心痛的是,蕭紅重病期間還是伏在病床上用了兩夜的時間耗盡了心力完成了短篇小說《小城三月》的寫作,這是蕭紅創作的最后一篇小說,也成為她短暫生命的絕唱。小說同樣是以女孩“我”的視角寫了美麗善良的年輕女子翠姨對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但最終不能得償所愿而自我毀滅的故事。同《后花園》里的馮二成子喜歡上了鄰家女兒卻不敢開口表白一樣,翠姨也喜歡上了“我”在哈爾濱讀書的堂兄,但礙于自己是“出了嫁的寡婦的女兒”的身份,覺得自己配不上堂兄,正像馮二成子愛上了鄰家女兒,但“怕自己的身份太低,怕毀壞了她”。自從聽到鄰家女兒的笑聲,馮二成子好像重新活了過來,而以前“好像他沒有活過的一樣”,如今他變得“慌張”“心里好不平靜”“無緣無故地心跳”“在夢中羞怯怯地紅了好幾次臉”,“他的感情軟弱得像要癱了的蠟燭似的”“茶也不想吃,飯也咽不下,他一心一意地想著那鄰家的姑娘”,但鄰家女兒出嫁了,他的心事“鄰家女兒根本不曉得有這么回事”。《小城三月》中翠姨死后,堂兄“不知翠姨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納悶”[9]。同馮二成子一樣,翠姨也一直把心事藏在心里,“她的戀愛的秘密就是這樣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帶到墳墓里去,一直不要說出口,好像天底下沒有一個人值得聽她的告訴……”《紅玻璃的故事》里的王大媽悟出了她們祖孫三代命運的真相,看破了生活的殘酷事實,從此萬念俱灰,自動放棄自己的生命。對《小城三月》里的翠姨來說,愛情和婚姻就是王大媽眼中命運的真相,翠姨買不到自己喜歡的鞋子時就說過:“我的命,不會好的。”在喜歡的人面前,她同樣放棄了獲得幸福的努力,既然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么就連生命都一起放棄。其實,翠姨是可以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的,“我”的繼母、她的姐姐曾說:“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們當我說。”可惜翠姨和堂兄都缺乏足夠的勇氣,在命運面前,他們繳械投降了。翠姨與王大媽一樣,不愿意在歷史和社會的巨大惰性和持久慣力的命運輪回中毫無意義地活著,因此她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自我毀滅。
蕭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時間里當然還跟之前一樣執著于對傳統文化積淀于世俗生活和國民性格深處的種種病態心理和病態現實進行剖析和批判,但同時蕭紅也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在作品中發出了形而上的哲學思考,對人生、對生活、對生命、對生存進行了靈魂拷問,而且這種對生命價值的終極追問赤裸裸地以大段的旁白表現出來。《后花園》和《紅玻璃的故事》表現得尤為明顯和突出。在《后花園》里,馮二成子送走趙老太太回來的路上,對人生產生了質疑和困惑:“他往四方左右望一望,他望到的,都是在勞動著的,都是在活著的,趕車的趕車,拉馬的拉馬,割高粱的人,滿頭流著大汗。還有的手被高粱稈扎破了,或是腳被扎破了,還浸浸地沁著血,而仍是不停地在割。他看了一看,他不能明白,這都是在做什么;他不明白,這都是為著什么。他想:你們那些手拿著的,腳踏著的,到了終歸,你們是什么也沒有的。”他看見賣豆腐腦的與吃豆腐腦的人在為一點醬油而爭吵,“他用斜眼看了那賣豆腐腦的:你這個小氣人,你為什么那么苛刻?你都是為了老婆孩子!你要白白活這一輩子,你省吃儉用,到頭你還不是個窮鬼!”他回想著鄰家女兒那向日葵般的大眼睛,想著她一去不再復返時,他發出這樣的疑問:“這樣廣茫茫的人間,讓他走到哪方面去呢?是誰讓人如此,把人生下來,并不領給他一條路子,就不管他了。”[8]王寡婦為他解疑答惑,讓他豁然開朗:“人活著就是這么的,有孩子的為孩子忙,有老婆的為老婆忙,反正做一輩子牛馬。”之后馮二成子有了老婆,有了孩子,為老婆忙,為孩子忙,而當老婆孩子都死掉后他伏在梆子上“每每要打瞌睡”,瞌睡醒來時“昏昏庸庸的他看見眼前跳躍著無數條光線”,“原來是房頂露了天了”。但無論發生什么,對他都不會產生任何波動和影響了,“不知多少年,他仍舊在那磨房里平平靜靜地活著”。
在茅盾看來,蕭紅的“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在他看來,即便在重病之際,“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對于她的最大威脅”[6]。對當時的很多人來說,他們不能理解蕭紅“這樣對于人生有理想,對于黑暗勢力做過斗爭的人”為什么會悄然“蟄居”在香港,有人分析說,蕭紅由于“感情上的一再受傷”而將自己拘禁在“自己的狹小的私生活的圈子”,而“把廣闊的進行著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給掩隔起來了”,認為蕭紅一方面“不滿于她這階層的知識分子們的各種活動”,另一方面“卻又不能投身到工農勞苦大眾的群中,把生活徹底改變一下”[6],因此才會“苦悶而寂寞”。事實上,蕭紅的確是寂寞的,但她的寂寞和苦悶不僅僅在于她的感情生活,還與朋友們對她的非議、指責、疏離有關。一方面,蕭紅承受著與蕭軍分手即如同與蕭軍陣營割袍斷義的被孤立,同時選擇與端木蕻良生活在一起的決定也不被朋友們支持,另一方面她的“作家不是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的寫作的出發點是向著人類的愚昧”[3]的創作主張在當時如火如荼的“一切為了抗戰”的主流文學主題面前顯得有點不合時宜,這種超越自己時代的文學觀念當然不被大多數人理解和接受,自然對她產生一些成見甚至偏見。而蕭紅選擇去香港也正是因為想有個安靜安寧的環境進行創作,由于時間緊迫,不辭而別,引起許多朋友的誤解和不滿。[10]再加上熟悉的朋友都在內地,蕭紅確實感到孤獨寂寞。而在生活和情感上經受多重打擊,又在顛沛流離中經歷了兩次懷孕生子,在精神和肉體上一直飽受折磨,但相對安定的生活畢竟給蕭紅提供了創作的環境,這也成了她創作生涯的高產豐收期。“由1940年到1941年6月,她正以驚人的速度,完成她一生創作歷程的重要階段,仿佛早已預知時日無多,要拼盡全力,發出最后又是最燦爛的光芒”[11]。
蕭紅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也是孤獨的,她離家鄉越遠就越想念家鄉,想念家鄉的那個后花園,想念那里的紅花綠草、蝶飛蜂舞,想念小黃瓜、大倭瓜、紅辣椒、紫茄子,還有爬山虎、胭粉豆、馬蛇菜、大菽茨、金荷葉……當然還有祖父、有二伯、小團圓媳婦、馮磨倌……也想念那久已逝去的童年……異地他鄉的漂泊者最思鄉,最寂寥,最傷懷,蕭紅的最后幾部作品無不浸潤彌漫著不招而來揮之不去的思鄉之情,也正因“疾病困之,憂患中之”[12],蕭紅才對人生發出靈魂的拷問:“為了什么活著?”“人活著為什么要分別?”“廣茫茫的人間,讓他走到哪方面去呢?”對生命價值的這些形而上思考在《后花園》里得到充分而全面的表現,也正因此,蕭紅的筆下才會兩次寫了馮磨倌,或者說由于表達意向的不同,蕭紅寫了命運完全不同的馮磨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