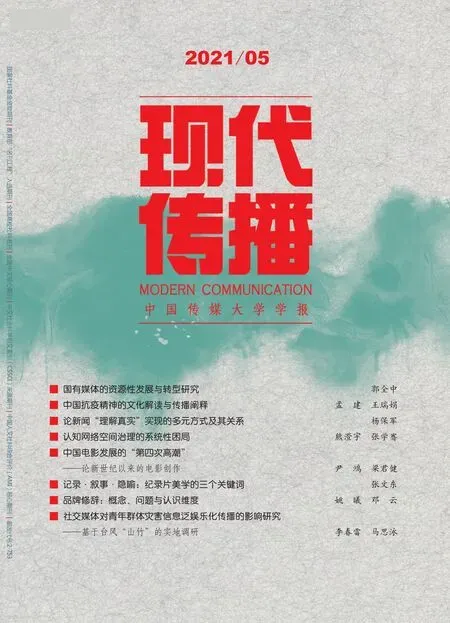美國“公共外交”及若干相關概念辨析
■ 仇朝兵
1965年,美國前外事官員、時任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院長的埃德蒙·格利恩(Edmund Gillion)在建立愛德華·R·默羅(Edward R.Murrow)公共外交中心時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這一概念。自從“公共外交”這一概念問世以來,人們對其界定一直存在著分歧。同一個概念,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其內涵和外延往往會有所不同;即便在相同時空背景下,由于各自經歷不同,人們對其內涵和外延的理解往往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對于相同或類似的事物,人們也常常會用不同概念進行表述。人們對“公共外交”這一概念及其內涵和外延的理解,也存在類似情況。
近年來,“公共外交”受到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學術界對“公共外交”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快發展,政策界、輿論界相關討論越來越多;一些致力于研究“公共外交”的機構或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許多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把“公共外交”作為學位論文選題。與這些進展相伴隨的是,國內學術界、政策界和輿論界對“公共外交”的理解和界定也存在著很大差異;“公共外交”與“文化外交”“民間外交”“公民外交”等經常被混為一談;各種新概念,如“城市外交”“公司外交”“高鐵外交”等不斷涌現,并納入“公共外交”范疇之中。于是,“公共外交”成了無所不包的東西。這種現象,無助于深化“公共外交”研究,也不利于“公共外交”作為一個學科的發展。
研究“公共外交”首先需要弄清楚人們對“公共外交”的各種不同界定;同時還必須比較、厘清“公共外交”與其他相關及類似概念,如“傳統外交”“文化外交”“公民外交”“公共事務”“宣傳”“心理戰”“政治戰”“國際政治傳播”以及“戰略交流”等的區別與聯系等,從而形成對“公共外交”的一種相對明確的界定。明確“公共外交”與這些相關概念在內涵與外延方面的異同,有助于大致確定“公共外交”研究的邊界,有助于更加平衡和全面地審視前人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深化“公共外交”研究。
一、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
愛德華·R·默羅在被任命為美國新聞署署長時曾這樣界定“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不同于傳統外交,它不但包括與政府間的互動,而且包括主要是與非政府的個人和組織之間的互動。另外,除政府部門的觀點外,公共外交活動經常會提供許多代表美國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的不同看法。與默羅的界定不同,多數人把“公共外交”看作一個國家針對其他國家民眾開展的旨在推動相互理解與合作的信息、文化交流等活動,而把不同國家政府間的互動歸于“傳統外交”。曾長期在“美國之音”(VOA)任職的漢斯·N·塔奇(Hans N.Tuch)指出,不同于傳統外交,公共外交包括國家間通過政府、外交部門的互動開展的關系。“傳統外交經常是——必須是——一種要求保密和隱私的過程(外交中的機密性決不意味著締結秘密條約或盟約。其意思僅僅是,為達成協議,其過程是秘密的)。相反,公共外交幾乎經常是一個公開的過程。公開性(publicity)是其內在的目的;直接訴諸于公眾:我們希望人民知道和理解。”①
就具體內容和活動方式而言,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有明顯不同,但其基本目標可能是相同的或互為補充的。從事傳統外交的外交官通過與外國政府代表接觸,以促進自己政府的國際事務戰略目標中闡明的國家利益。而公共外交則通過政府與外國公眾,特別是與經過細心選定的部分外國公眾進行溝通,讓他們理解這個國家的觀念與理想、制度與文化以及其國家目標和當前政策,以促進他們對這個國家歷史、文化、價值觀、制度和政策等的理解或認同,從而形成對其戰略目標的支持,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沃倫·克里斯托夫(Warren Christopher)在任副國務卿時曾表示,通過尋求與其他國家的人民之間的溝通,公共外交補充并加強了傳統外交。他認為,公共外交有四個目標:第一,確保其他國家更準確地理解美國及其價值觀、制度和政策;第二,確保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理解及對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關系的理解是全面的和準確的;第三,確保這種相互理解在不同文化間得到合作性的個人和組織關系的支持;第四,確保美國政府在制定國際政策時,充分考慮外國公眾的價值觀、利益和首要關注。②美國公共外交咨詢委員會(U.S.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在1985年的報告中也表示:“通過向外國公眾解釋美國的政策、向他們提供關于美國社會和文化的信息、讓很多人親身感受我們國家的多樣性,以及通過評估外國公眾對美國大使及美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看法,公共外交補充和強化了傳統外交……公共外交不是傳統外交的替代物,它是承認思想和觀念在塑造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忠誠和政治理解方面的重要作用。”③美國前駐敘利亞和阿爾及利亞大使克里斯托夫·羅斯(Christopher Ross)把公共外交視為傳統外交的公開面貌。傳統外交通過與外國政府的秘密交換來促進美國的利益。公共外交,除接觸政府官員外,還通過接觸政府外的民眾,包括大眾和精英,支持傳統外交。它與傳統的外交活動是相協調和平行的。④
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尼古拉斯·J.卡爾(Nicholas J.Cull)教授這樣區分“傳統外交”和“公共外交”:如果外交是一個國際行為體通過與其他國際行為體的接觸實施其外交政策的活動(傳統上的政府與政府的聯系),那么,公共外交就是一個國際行為體通過接觸外國民眾來實施其外交政策的活動。它由五個核心組成部分:傾聽、支持(advocacy)、文化外交、交流外交(exchange diplomacy)和國際廣播。⑤美國國會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外交政策分析家肯儂·H.中村(Kennon H.Nakamura)和馬修·C.韋德(Matthew C.Weed)也做了類似區分:公共外交是對由職業外交官之間進行的官方互動主導的、傳統的政府間外交的一種對外政策補充。美國公共外交指的是與另外一個國家的公民、社區和公民領袖、記者及其他意見領袖等的直接互動的活動。公共外交試圖影響其他社會的態度和行動,以支持美國的政策和國家利益。公共外交要求通過人民和思想的交流,建立長期關系并形成對美國及其文化、價值觀和政策的理解。傳統外交,包括強有力地向外國政府闡述美國的政策,分析和報告外國政府的影響美國利益的行動、態度和趨勢等。⑥
從美國公共外交的歷史發展來看,“公共外交”始終是服務于美國的傳統外交政策的,著眼點同樣是美國現實的國家利益。傳統外交,指的是政府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非公開性;公共外交,指的是一國政府對其他國家民眾開展的活動,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公開性。說“公共外交”服務于政府間傳統外交,是傳統外交的重要補充,并不是說它的重要性低于傳統外交。事實上,在美國的社會制度背景下,公共外交在其國家整體外交中的重要性、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實現與維護所發揮的作用,可能絲毫都不亞于其傳統外交。
二、公共外交與宣傳
“宣傳”一詞源于17世紀羅馬教皇為傳播天主教信仰而建立的羅馬天主教樞機主教委員會,它在現代的同義詞是“謊言”“欺騙”和“洗腦”等。出于天主教對新教傳播的擔心,教皇格利高里十五世(Pope Gregory XV)在1622年發明了“宣傳”這個詞,建立了信仰宣傳辦公室(Offic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以監督教廷在新世界的傳教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英國和美國把對敵國的溝通和說服策略稱為“宣傳”,于是“宣傳”就成了一個貶義詞。美國南加州大學安能伯格傳播與新聞學院教授尼古拉斯·J·卡爾(Nicholas J.Cull)等主編的《宣傳與大眾勸說:1500年以來的歷史百科全書》一書中這樣解釋了“宣傳”:“進行宣傳活動必須是有意識的、故意的。宣傳的‘目標’是關鍵。沒有目標,宣傳就沒有目的和方向……宣傳就是為了一個特定目標,故意通過觀念和價值觀的傳播,而非通過暴力和賄賂,來影響公眾輿論。”現代政治宣傳是有意識用來直接或間接地服務于宣傳家及其政治強人的。宣傳的目的是說服其對象,只有一種正確的觀點,排除所有其他選擇。⑦在美國的政治和社會話語中,“宣傳”在很多情況下都被視為一種負面的東西,甚至被等同于“謊言”“欺騙”等。因此,美國人更愿意把自己國家的對外信息活動叫做“公共外交”,而非“宣傳”。克里斯托夫·羅斯說:“很多宣傳包含著謊言,而且不會回避謊言。在公共外交活動中,我們不故意去傳播不真實的東西。我們可能會以某種方式表達它們,但我們討論的是事實。”⑧在20世紀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宣傳與政府對關于其國家和社會的錯誤信息的傳播經常是被聯系在一起的,公共輿論傾向于把“宣傳”視為欺騙和危險的行為。
美國一直標榜自己對外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是在向世界傳播關于美國的真實信息。信息的真實性被視為美國公共外交的生命,也被視為提高美國的可信度或信譽的最佳途徑。美國還經常攻擊前蘇聯、中國等國的宣傳活動。但從美國開展的某些公共外交活動的具體內容及其形式來看,把它稱之為美國人所理解的意義上的“宣傳”也不為過。這里討論的“宣傳”,嚴格說來,指的是“對外宣傳”。公共外交和宣傳的效果和界定,經常是難以分開的。實際上,在美國學界和政界也經常出現“公共外交”和“宣傳”相互替換使用的情況。美國國內對政府資助的信息活動到底是經過巧妙處理的“宣傳”,還是正當的“公共外交”,也時常有著爭論。甚至在反恐戰爭時期,“宣傳”和“公共外交”也被認為是可以互相替換的,而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戰略性說服手段。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南希·斯諾(Nancy Snow)教授評論道:“公共外交的定義在任何時候都是與民族國家政府的官方目標有明顯的聯系的,這傾向于意味著一種與宣傳后果相聯系的更負面的解釋。于是,或對或錯,公共外交被視為一系列主要大眾傳播技巧,利用超越理性事實的情感訴求以改變態度,隱匿對信息發出者不利的信息,以及傳播促進諸如一國社會、經濟或軍事目標等特定意識形態的信息。”⑩當人們如此看待美國的公共外交時,它與“宣傳”之間的界限也就蕩然無存了。也有人用“文化宣傳”(Cultural Propaganda)來指代美國的“公共外交”。
既然人們對“公共外交”和“宣傳”都沒有統一的界定,這就給論者各取所需提供了便利。若深入考察美國的公共外交活動,應該可以看出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就是宣傳;而且,無論從形式還是從內容或效果看,這個概念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宣傳”。只是美國希望避免用“宣傳”描述美國新聞署和“美國之音”的活動的負面含意。英國萊斯特大學教授G.R.貝里奇(G.R.Berridge)等編著的《外交辭典》中把“公共外交”直接視為描述“20世紀后期外交官進行的宣傳活動的一個術語”。
但無論如何,“公共外交”和“宣傳”在采用的手段、追求的效果、產生作用的機制等方面,都有許多相似或相通之處。美國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杰弗里·艾倫·皮格曼(Geoffrey Allen Pigman)教授評論道,“公共外交”和“宣傳”有許多相同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影響公眾態度”或“影響人民的看法”。傳統的外交學者曾試圖為“宣傳”規范地劃出邊界,防止在公共外交實踐中使用它。不過,盡管“宣傳”可能有負面意涵,但對于在特定有限條件下實現特定目標,它的使用可能是有效的。在分析和評估當代公共外交的效果時,反饋環節至關重要。而區分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動與無效的公共外交活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信任。從這些意義上看,“公共外交”和“宣傳”區別,僅僅在于人們對它們形成的情緒或心理上的反應,特定的歷史和特定的社會文化氛圍賦予了“宣傳”一詞負面的意涵。如果拋開情緒性的反應,更中性地理解“宣傳”,“宣傳”與“公共外交”的某些內容之間的界限也就消失了。
三、公共外交與心理戰
“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不是一個新鮮的詞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就曾針對敵對國家開展心理戰。所謂“心理戰”,指的是在戰爭時期針對敵國有計劃地運用宣傳手段,傳播某些觀念和信息,以影響敵國軍民的心理、情緒和行為,目的是瓦解其士氣和斗爭意志。“心理戰”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對外宣傳,它的對象是敵國而非中立國家或友好國家的人民。由于國家間沖突或戰爭的多樣性,“心理戰”也被逐漸廣泛應用于戰略和政治層面,而不再局限于正式的戰爭形勢下,因而也更多使用“心理行動”(psyops)一詞了。心理戰既廣泛用于各種戰爭和沖突之中,也被用于和平時期的意識形態斗爭之中。
從其手段來看,“心理戰”和“宣傳”以及“公共外交”中的廣播電視活動等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宣傳”和“公共外交”的范圍更加廣泛,它們的對象及其所傳遞的具體信息和內容有很大差別。“心理戰”主要運用于戰爭中的國家之間或具有重大戰略沖突的國家之間,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對德國等敵對國家的心理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對法西斯國家的心理戰,以及冷戰時期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宣傳活動等。
美國為實現其自身的戰略利益和對外政策目標,往往把公共外交活動和心理戰行動糅合在一起,二者的部分行動是重合的。這樣,也就很難用“心理戰”或者“公共外交”來劃分美國的很多行動了。從冷戰時期美國對其他國家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來看,特別是從其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開展的公共外交來看,很難把“公共外交”與“心理戰”清晰地區分開來。美國對一個國家采取何種性質的公共外交,取決于美國公共外交對象國的不同以及美國與這些國家關系的性質和狀態等因素。
也有人把公共外交視為心理戰略(psychological strategy)的基本組成部分。因為,“第一,全球范圍內大量公眾能夠獲得的信息量的增加,直接影響了公眾的看法和態度,反過來又影響了政府的行為和決策。第二,認知(perceptions)和現實(reality)一樣重要。看上去是真實的就會被認為是真實的,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更是如此。”這種理解只是非常狹隘地理解了“公共外交”,或者說只是把“公共外交”的一部分當成了“公共外交”的全部內容。但毫無疑問,公共外交的某些形式或內容,也可能被運用于心理戰的實施。
四、公共外交與政治戰
在國際政治競爭或爭奪的背景中,“政治戰”(political warfare)是一個國家為實現其在世界上的政治規劃而使用的工具,但它又不是一系列工具或手段的總和。在波士頓大學安吉洛·M.科迪維拉(Angelo M.Codevilla)教授看來,“政治戰”指的是在戰爭中或像戰爭一樣嚴重的不流血沖突中,為贏得勝利而動員人們進行支持或反對,是在特定沖突中,一個國家對其正在從事的事情或采取的政策的強有力的政治表達。科迪維拉認為,要想在政治戰中取得成功,就必須引導對象國人民把他們自己的生活、財富和榮譽與進行宣傳的一方所做的事情聯系在一起,使他們理解后者所做的事情。發動或實施“政治戰”的一方,既可能采取公開的行動,也可能采取秘密的行動,但它都必須向外國人提供他們應該站在“我們一邊”考慮問題的真實、具體的理由,并為其提供具體誘因以大大提高站在“我們一邊”的機會。
就其應有的環境而言,“政治戰”與“心理戰”類似,二者都是主要用于戰爭中或者類似于冷戰這樣的沖突中。而“公共外交”應有的范圍則要寬泛得多,它既被廣泛應用于和平時期,也被用于戰爭和沖突時期。公共外交所追求的目標,也比“政治戰”更加寬泛:“政治戰”追求的是在沖突中取得勝利;“公共外交”在特定的情境下當然也有此類目標,但它還包括促進國家間、民族間或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和溝通等。二者的另一差別是:“政治戰”采取的行動,既包括公開的,也包括不公開的;而“公共外交”活動是公開的。不過,在特定國家和特定時期,針對特定事件或問題,也很難在“政治戰”和“公共外交”之間劃出清晰的界限。歸根到底,二者都服務于特定國家的利益,都是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或工具。
五、公共外交與國際政治傳播
“國際政治傳播”(IPC)通過報紙、廣播、電源、人員交流、文化交流及國際傳播的其他手段,以實現某種政治效果。“國際政治傳播”是一種比較中性的、沒有感情或意識形態色彩的表達,它囊括了“公共外交”“宣傳”“心理戰”“政治戰”等這幾個概念所包含的全部內容。國際政治傳播可以分為四類:官方的、意在影響外國公眾的傳播;官方但非意在影響外國公眾的傳播;意在從政治上影響外國公眾的私人傳播;以及沒有政治目標的私人傳播。
“國際政治傳播”中第一類也就是所謂的“公共外交”。幾乎每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都會資助和開展這些國際政治傳播活動。研究美國的“公共外交”,需要越來越多地增加對美國私人傳播之海外影響的關注。美國私人傳播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它所產生的效果可能比“公共外交”的影響要大得多。因此,近年來美國政府在對外推行公共外交時,也越來越強調和發揮美國的個人、公司或其他非政府組織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從政策措施與行動效果之間的復雜關系來看,想把“公共外交”與“國際政治傳播”截然分開恐怕是不可能的。各種因素在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共同決定了“公共外交”或“國際政治傳播”活動的效果。有的政策及其實施可能會產生預期效果,有的可能不會;而有的政策和行動可能產生了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無意中產生的效果有時候可能比刻意造成的效果更加深刻。
因此,在公共外交研究中,特別是在評估公共外交之效果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區分“公共外交活動”和“能夠產生公共外交活動之效果的活動”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公共外交不是在獨立的空間中開展并產生影響的,許多本不屬于公共外交范疇的活動,能夠對公共外交活動的效果產生影響。對于這類活動,在對公共外交活動的效果進行評價時是不能忽視的。“國際政治傳播”的外延遠比“公共外交”廣泛。研究公共外交時,需要適當觀照“國際政治傳播”領域大量能夠影響“公共外交”之效果的活動或內容。
六、公共外交與公共事務、公共關系
在美國,公共外交主要是對外的,是針對外國公眾開展的信息、交流等活動,是美國與世界的對話;而公共事務針對的是國內民眾,目的是向國內媒體和民眾提供信息并影響他們,促進國內公眾對政府政策、活動的理解和支持。公共事務項目處理的主要是媒體事務,本質上是反應性的,主要是對一個事件或新聞故事做出反應,或者阻止媒體的行動,公共事務時限通常是由數分鐘到數天來衡量的,它要求盡可能及時地做出反應;而公共外交是積極主動的,它應對和處理的問題也寬泛得多,除應對媒體外,它還要應對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向對象國民眾提供信息,也包括建立各種關系等,公共外交尋求的是改變目標對象的態度,并說服他們,為實現成功,公共外交的時限可以用數月、年甚至十年來衡量。
美國國務院曾這樣區分“公共事務”和“公共外交”:“公共事務指的是向公眾、媒體及其他組織提供關于美國政府的目標、政策及活動的信息的活動。公共事務主要是向國內公眾提供信息……而公共外交則試圖通過理解外國公眾、向他們提供信息并影響他們,來推動美國的國家利益。”公共外交不是海外版的公共事務,前者比后者涵蓋的內容更加廣泛,形式更加多樣,手段更加復雜。
在1999年美國行政部門機構改革之前,美國負責公共外交事務的是相對獨立的美國新聞署。之后美國國務院設立統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的副國務卿,承擔對內和對外的雙重使命。盡管負責“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的機構是一體的,而且“公共事務”方面的某些活動確實可能也會對“公共外交”產生某種影響,但在公共外交研究中,仍需注意二者的區別,大致劃清二者的邊界。
另外,各國,特別是美國在開展公共外交時,越來越重視發揮各種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私營部門的作用。美國學術界近年來開始把某些非政府行為體的活動也視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這就導致公共關系活動與公共外交活動的趨同現象。皮格曼教授評論道,傳統上,公共關系和公共事務被認為是不同于公共外交的,公共事務涉及的是政府與其國內民眾的溝通,公共關系涉及的是私人行為體與其受眾及支持者之間的溝通。但實踐中,這些邊界越來越模糊了。這種邊界的模糊,對于公共外交研究形成了更大挑戰,但也為公共外交研究邊界的明確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讓模糊地帶更加清晰,才有助于推進和深化公共外交的研究。
在中國,也經常面臨公共外交研究邊界被不斷放大的情況。比如,把中國外交部對國內民眾開展的“公眾開放日”活動也視為“公共外交”活動;把“公司外交”“城市外交”等等也納入公共外交研究的范疇,這種做法,使“公共外交”的內涵和外延無限擴大,表面上呈現出“公共外交”研究的繁榮局面,實際上卻忽視或沖淡了對傳統公共外交活動及其歷史的研究,也不利于“公共外交”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在中國的發展。
七、公共外交與公民外交
“公共外交”這個概念突出的是外交活動的性質,“公民外交”突出的則是開展外交活動的主體。在美國,“公民外交”指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公民個人有權利甚至責任去幫助塑造美國的對外關系。公民外交官是非官方的大使,他們或者參加海外交流項目,或者招待在美國的國際交換項目參與者,并與之互動。有些公民外交的參與者是有薪水的,而大多數公民外交官是志愿者,他們提供時間、領導技巧、專業知識及其自己的金錢和其他資源,以維持構成美國公民外交基礎的地方非政府組織。公民外交活動中一些交流項目的資金至少有部分是美國政府提供的,因而,公民外交也構成了美國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公共外交”最有效、最深刻的部分是不同國家公民之間直接的思想和文化交流活動。作為個體的不同國家公民間的交流有助于建立持久的友誼和關系,也應該更有助于促進國家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美國政府資助和支持的交流項目也依賴私營部門合作者和公民外交官,一方面可以提高這些項目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開支。由于美國有大量參與到公民外交活動中的非政府組織和個人,他們對美國外交及美國公共外交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他們為美國外交和公共外交動員了大量的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對政府的力量發揮了“放大器”的作用。因此,公民個體或公民組織如何參與并影響美國公共外交活動,也是研究美國公共外交時不容忽視的問題。
八、公共外交與文化外交
貝里奇等編著的《外交辭典》中把“文化外交”界定為“把一個國家的文化成就推向國外的活動”。與文化外交相比較,“公共外交”這一概念強調的更多是活動的對象和形式,“文化外交”強調的更是活動的內容和性質。從形式上看,“公共外交”強調的是一國政府針對其他他國的民眾,開展的各種形式信息傳播和交流活動,重點在對象和形式;“文化外交”則不局限于此,它不但包括一國政府對他國民眾開展的文化交流活動,還包括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文化關系和文化交流活動。從內容上看,“文化外交”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政府把其國家的文化傳播給其他國家的民眾,以推動對其國家理想和制度的理解,進而爭取對其政治和經濟目標的支持的活動,其內容強調的是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而“公共外交”的內容更廣泛,并不局限于文化傳播,它既包括文化傳播,也包含內外政策的解釋說明等。二者的共同之處在于都高度重視文化在國家間關系中的作用,都強調和推動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對話。
正是基于文化在公共外交中的核心地位,美國文化外交咨詢委員會的報告認為“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關鍵”。“因為只有在文化活動中,一個國家自己的思想才能更好地展現出來。外交能夠以非常巧妙、廣泛和可持續的方式促進我們的國家安全……對于塑造我們的世界領袖地位,包括反恐戰爭,美國的文化財富所發揮的作用絕不會比軍事行動的作用更小。植根于我們的藝術和知識傳統中的價值觀,構成了一種抵抗黑暗力量的堡壘……文化外交,顯示著一個國家的精神,可以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解釋其復雜的歷史:當我們的國家處于戰爭之中,外交工具包中的任何一種工具都得以使用,包括推進文化活動。”文化和文化外交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文化實際上就是權力……文化交流是一種學與教、出口與進口、劣勢與優勢、謙恭與自信之間復雜和平衡的公平交換”。
在研究美國公共外交,特別是涉及文化外交時,需要準確把握“文化外交”和“文化政策”在美國社會文化氛圍中的意涵。文化外交是服務于美國利益,特別是其長期利益的,如維護和平、擴展民主及促進經濟合作等。美國在其國內社會政治生活中往往避免推行“文化政策”,但在國外,“它意味著一種有規劃的方法,以實現美國在教育和智力領域廣泛利益的最大化……美國在外國的文化政策目的是培育、糾正、加強以及必要時建立與美國的文化和教育聯系。”也就是說,在研究美國公共外交時,有必要深入考察美國的對外文化政策,這有助于從更深刻的層面上理解美國的公共外交。
九、公共外交與戰略交流
“戰略交流”(strategic communication)是美國軍方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美國軍方把“戰略交流”界定為:操控信息戰場,塑造信息以擊敗敵人的一種手段。而美國的公共外交活動,主要著眼于關系的建立,如增進信任、創造關系網絡、建立信譽等。美國國務院用“公共外交”描述的是與外國民眾進行了交流,“戰略交流”涵蓋的是國防部與外國公眾、軍事對手、伙伴國和非伙伴國政府、其他美國政府部門以及美國人民之間的互動及對他們的影響。
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Defense Science Board)在2004年《戰略交流:國防科學委員會報告》中指出,戰略交流包括四種核心工具:公共外交、公共事務、國際廣播活動和信息活動(IO)。在這里,公共外交被視為“戰略交流”的核心工具。奧巴馬總統根據美國《2009財年國防授權法》之要求在2010年3月16日向國會相關委員會提交的關于公共外交和戰略交流的全面、跨部門戰略報告《國家戰略交流框架》(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把“戰略交流”界定為:(1)言與行的同步,以及所選擇的聽(觀)眾如何認識這些言行;(2)旨在與目標受眾進行溝通和接觸的項目和活動,包括由公共事務、公共外交和信息活動專業人士實施的那些項目和活動。在這里,公共外交也被視為戰略交流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在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看來,戰略交流只是公共外交的一個方面。奈認為,公共外交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個也是最直接的方面是日常交流,包括解釋國內和外交政策決策的環境,以及應對危機和反對攻擊的準備;第二個方面是戰略交流,包括開展一些簡單的、類似于政治運動中出現的項目;第三個方面是通過獎學金、交流、培訓、研討班、會議等途徑,在多年內與關鍵的個人發展持久關系。這里需要特別注意,奈雖使用了“戰略交流”一詞,但他所謂的“戰略交流”遠不及以上所述的“戰略交流”所指代的內容那樣廣泛。奈在其著作中也未對“戰略交流”作更深入的論述。
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戰略交流”視為加強美國國家能力的重要手段。該報告指出:“有效的戰略交流對于維持全球合法性和支持我們的政策目標是必不可少的。協調我們的言與行,是整個政府的溝通文化必須培育的一種共同責任。在我們審慎的交流和接觸中,我們必須做得更加有效,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國人民——而不僅僅是精英的態度、看法、不滿和關注。這使我們能夠表達可信、一貫的信息,制定有效的計劃,同時更好地理解我們的行動被如何認知。我們還必須運用各種交流方法,包括新媒體,與外國公眾交流。”從該報告對“戰略交流”的目標、手段等的分析來看,它與“公共外交”也有許多相同和相通之處。
公共外交屬于傳統國際關系研究中被關注較少的領域。隨著全球化的突飛猛進,國家間的交流變得日益緊密,國家間的關系也日益復雜,公共外交在國家間關系中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公共外交研究已開始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學術增長點。公共外交與上述其它概念所指代的都是信息傳播活動,它們的手段和方式也高度相似,其區別在于活動的對象、具體目標、性質、涵蓋的內容以及適用的時空背景等有所不同。但若把它們放在一國整體戰略的框架下,或放在其對外交往的歷史中來審視,可以看出其總體目的和性質又是相同的,都是服務于其國家戰略和國家利益的。梳理、對比和分析公共外交與其他相關概念的差異,有助于更準確地理解公共外交的內涵和外延,從而有助于為公共外交研究確立大致明確的邊界,為公共外交及相關問題研究和討論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基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概念的泛化、誤用和濫用,進一步推動公共外交研究走向深入。
注釋:
① Hans N.Tuch.CommunicatingwiththeWorld:U.S.PublicDiplomacyOversea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pp.3-4.
② Allen C.Hansen.USIA:PublicDiplomacyintheComputerAge.New York:Praeger.1984.p.3.
③UnitedStatesAdvisoryCommissiononPublicDiplomacy.1985 Report.inside cover.1985.p.2.available at:https://www.state.gov/1985-advisory-commission-annual-report/.
④ Stephen Hess & Marvin Kalb ed.TheMediaandtheWaronTerroris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p.224-225.
⑤ Nicholas J.Cull.TheColdWarandtheUnitedStatesInformationAgency:AmericanPropagandaandPublicDiplomacy,1945—1989.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XV.
⑥ Kennon H.Nakamura & Matthew C.Weed.U.S.PublicDiplomacy:BackgroundandCurrentIssues,in Matthew B.Morrison ed.U.S.PublicDiplomacy:BackgroundandIssues.New York:Nova.2010.p.2.
⑦ David Welch.“DefinitionsofPropaganda,”in Nicholas J.Cull,David Culbert & David Welch eds.PropagandaandMassPersuasion:AHistoricalEncyclopedia,1500tothePresent.Oxford,England:ABC-CLIO,Inc.2003.pp.317-319.
⑧ Stephen Hess & Marvin Kalb ed.TheMediaandtheWaronTerrorism.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p.224-225.
⑨ R.S.Zaharna.FromPropagandatoPublicDiplomacyintheInformationAge,in Yahya R.Kamalipour & Nancy Snow ed.War,Media,andPropaganda:AGlobalPerspective.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4.p.219.
⑩ Nancy Snow.U.S.PublicDiplomacy:ItsHistory,Problems,andPromise,in Garth S.and Vicoria O’Donnell ed.ReadingsinPropagandaandPersuasion:NewandClassicEssay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p.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