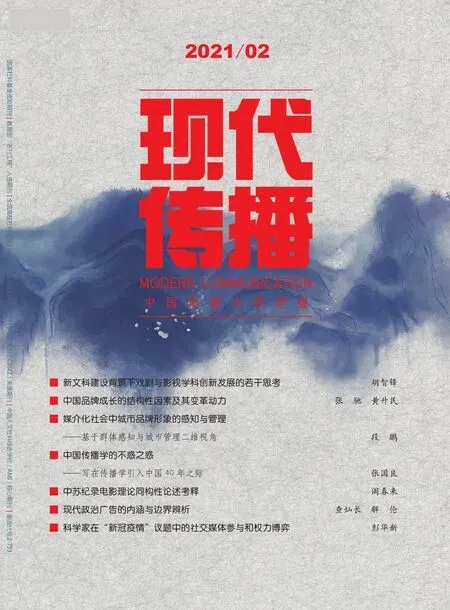作為一種新敘事方式的人工智能*
■ 唐忠敏
當機器人快速、大規模地創作出新聞、小說、詩歌、劇本、書法、國畫等作品時,人們雀躍歡呼這種新敘事媒介的到來。人工智能深度參與敘事,不只是一種新敘事形式的誕生,還對敘事內容的生成與傳播產生了深刻影響。不僅如此,這種影響還超越了特定敘事體裁的限定,對敘述者、敘事行為、話語表達乃至人與機器、人與信息之間的關系變革產生重大作用。因此,在面對數量眾多的人工智能作品時,人工智能機器到底如何組織內容、表達情感、傳播話語等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指令呈現者是人機協同敘事的組織者和見證者
從經典敘事學的角度看,任何敘事文本都有執行敘事行為的敘述者。敘述者可能是明確顯示的,也可能隱姓埋名,但始終是文本內部的一個構成元素,決定著文本講述什么和如何講述。正如巴爾特所說,“敘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紙上的生命’。一部敘事作品的(實際的)作者絕對不可能與這部敘事作品的敘述者混為一談。……(敘事作品中)說話的人不是(生活中)寫作的人,而寫作的人又不是存在的人。”①與作為作品版權承擔者的真實作者不同,敘述者既是敘事內容和敘事結構的組織者,也是敘事情感的發出者和敘事行為的見證者。
人工智能是指通過一系列計算機算法模擬人的思想和行動的智能,本質特征是“類人大腦的思維性和類人存在實體性的結合”②。人工智能技術,如大數據、算法分析、自動寫作、語音圖文識別、聲音模擬等的廣泛應用,使得常規網絡敘事向智能敘事轉變。作為一種表達手段,人工智能在素材搜集、數據處理、文本生成、傳播路徑等方面已經深度參與到敘事活動當中,并在新聞寫作、文學創作、影像制作等領域產生深刻影響。智能敘事不是單純的智能機器的深度學習和算法輸出,而是智能機器的運行規則、計算能力等技術架構和人的理性、感性、洞察等相結合的過程,是智能機器指令與人的“指令”相互結合的綜合性輸出。正如電影、電視劇、紀錄片等影像文本需要集體協作才能完成,智能敘事也是一種人與智能機器人共同協作的敘事方式。影視作品的完成不僅需要導演、編劇、演員等人,還需要鏡頭、音樂、聲音、剪輯、文字、燈光、言語等多種媒介。因此,有學者認為,影視作品的源頭敘述者應該是代表上述所有元素的“指令呈現者”③。在智能敘事中,指令呈現者控制敘事的表達方式,限定敘事的行為和進程,也參與敘事文本的傳播。可以說,作為一種敘事形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參與既豐富了傳統敘事的表達方式和敘事效果,也改變了人與敘事之間的關系。
首先,指令呈現者是協調作者、讀者、代碼、軟件、數據、算法等的中介,控制著敘事的方法和效果。以深度學習、數據和計算為基礎的人工智能在信息搜集、文本創作、文本分發等運行規則上具有一定的能動性,但所有技術和運行規則的設計都離不開人的參與。雖然智能機器已經能夠在某些領域實現自動組合和整合網絡信息,但從宏觀上看,人在人機關系中始終占據主導位置,“人只不過是由前置轉為后置,由體力變為智慧,由具體執行變為籌劃操作”④。因此,不管是人工智能系統獨立完成網絡敘事,還是以人工智能系統為主、人類為輔,或以人類為主、人工智能系統為輔,都離不開人和智能機器在文本生成中缺一不可的中介作用。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系統,指令呈現者可以從一系列社會事件、社會現象的信息中進行主題篩選、話題挖掘、關系分析等,還能通過算法掌握讀者信息和需求,實現敘事內容的精準生產、分發和推薦。美國電視劇《紙牌屋》就是人工智能協助制作的范本。大數據資料分析顯示,導演和主演合作的政治題材電視劇最受歡迎,導演的粉絲和主演的粉絲圈基本重合,劇本是點擊率較高的作品。智能系統計算顯示,喜歡英國版《紙牌屋》的觀眾和導演的粉絲是同一群人,喜歡主演作品的觀眾也喜歡英國版《紙牌屋》。奈飛公司正是依靠大數據和算法的紅利確認了美國版《紙牌屋》的制作班底和推送范圍,使得該劇成為現象級的電視劇制播傳奇。
其次,指令呈現者在平臺算法、社交關系等邏輯中建構起人與機器、人與敘事之間的關系。算法是指令呈現者獲取和傳播敘事內容的手段,也是決定敘事內容和傳播路徑的依據。平臺算法根據傳播主體的網絡使用記錄和偏好,如個人喜好、使用頻率、使用習慣、場景、時間、地域等數據信息,對用戶進行精確分析和個性化內容推送。這種基于用戶個人信息的自動化的內容生產和分發方式,直接跳過了傳統敘事文本傳播中所需要的寫作、排版、印刷、運輸、閱讀等繁瑣環節,也導致了多樣化的敘事內容、傳播路徑和敘事效果。同時,由于網絡敘事內容往往源自社交關系且在社交圈中傳播,指令呈現者所述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敘事內容的來源和傳播范圍的廣度。社交關系決定了網絡敘事的話題類型、表達方式、內容特質等,也會對社交價值如社交展演、情感互動、立場表達等多有強調。因此,指令呈現者所述內容需要在社交關系結構中生成個性化的敘事內容。其結果是,一方面管控了傳播主體接觸信息的數量,減少信息過載;另一方面也將網絡信息生產置于同質化、重復化的聚合狀態中,呈現“回音室效應”。
另外,雖然深度學習、數據、平臺算法等技術架構對智能敘事的內容和傳播路徑有著重大建構作用,但指令呈現者也會通過主動性的生產、搜索等方式對敘事內容的生成和傳播進行反向創造。人工智能往往為用戶提供更有吸引力而不是更有價值的內容,平臺運營者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干預讀者的接收和闡釋,影響讀者的看法和意見。人也通過主動的寫作、搜索、閱讀等敘事行為去適應或改變人工智能預設的內容和路徑。有研究者指出:“這種脫離了原有信息尋求導向和相關信息的選擇過程,有些是互聯網的特殊性使得受眾被動地被‘輸送’到自己沒有意識到的信息渠道,不論這些渠道會提供確認還是挑戰自己既有觀點的信息。另一部分偏軌接觸,則可能是受眾為了獲取更多或更全面議題解釋或事實的主動選擇,是更有效參與政治推動下的擴展搜尋行為。”⑤
二、程序性敘事與敘事情感的計算性模仿
作為敘事主體的指令呈現者通過程序、代碼、算法等智能技術實現對社會事件的講述,但其實現程度卻依賴于人對程序、代碼、算法等技術的開發和操控程度。就目前的技術發展來看,人工智能還處于“專司某一個特定領域工作”的專用人工智能系統階段,離“能夠像人類那樣勝任各種任務”的“通用人工智能”還很遠,并且既有的“人為的分工方案”中還存在著大量的邏輯上的分類混亂之處,如“常識推理能力”與“知識表征”“非確定性環境下的推理”等領域之間界限不清。⑥因而,作為敘述者的指令呈現者雖然置身于故事之外,但由于受到技術流程、傳播過程以及敘事情感的計算型模仿等限制,對事件或現象的講述并非總是全知全能,而是具有限制性的講述。
從敘事行為來看,指令呈現者依賴專業技術架構來進行程序性的文本生成活動。人工智能高度參與敘事的流程是通過人機協調實現對人的敘事行為的模擬,程序編輯、數據量化、算法算力等智能技術被轉化為一套技術流程,而這套技術流程在設計時已被融入了專業性、商業性等要素。因此,指令呈現者所講述的內容實際上是已經過技術流程中各級編碼者過濾或改寫過的內容,是符合特定意圖的敘事內容。這些敘事內容的背后既有專業技術架構的指導與操控,又隱含著各級編碼者的行為與意圖。智能機器撰寫新聞時,指令呈現者需要對新聞的時效性、社會價值等進行監測,然后確定敘事視角、主題、關鍵詞等,再對內容進行提煉和描述。這個過程強調新聞敘事的本質與意圖,但也隱含著對社會情境、社會意義等的簡化或遮蔽。有學者指出,“自動化新聞并不直接作用于由事實定義的現實,而是作用于主要由算法作用的數據編碼的現實”⑦。詩歌、小說等創作需要對大量的詩歌和文學作品進行多次迭代學習,再通過智能生成器根據某一主題進行運算,最后生成詩歌或小說作品。詩歌生成器或小說生成器有其專業的技術架構,往往不能隨機生成音樂或繪畫作品,也不能下圍棋。因此,特定的技術架構只能程序化地創建出特定的敘事內容,不能創建出其技術架構支撐之外的內容。
在智能敘事生成的過程中,不同的數據資源、算法以及技術架構也可將某些敘事元素進行多種組合,隨機產生多個文本塊。因此,事件或情感被講述成一個個猶如積木玩具似的獨立文本,讀者對事件或情感的認知來自于對這些分散文本的拼貼閱讀。從宏觀技術層面上看,“智能敘事模型基本結構是由敘事組件配置層、敘事生成中樞以及附屬結構層組成”。⑧敘事組件配置層主要是確定敘事的材料、主題、框架、場景、詞語選擇、段落結構等,涉及敘事作品基本元素的選擇和確定。敘事生成中樞包括敘事的情節處理和語言表述,而附屬結構層主要是對敘事作品的語法、修辭等內容進行迭代和擴展。從微觀敘事創作層面來看,智能敘事需要創作者對敘事素材數據庫進行整合與篩選,對多種算法進行選擇與確定,對智能創作能力進行訓練與培養以及對敘事作品進行修改與潤色。智能敘事將不同的敘事元素參數化,能夠在人的協助下生成符合人類敘事目的之文本,但也可能出現不可預測的敘事元素和情節。而且,這些超出預期范圍的敘事元素會在智能系統中形成多種不可預測的混合體,并最終體現在敘事內容中。這種由多種敘事元素組合或混合而成的文本形成過程,猶如樂高積木玩具的拼貼成型過程,其成品會體現出比較明顯的拼貼質感。小說中的環境、人物、狀態等可能經由不同的程序來完成,經過人工組合和潤色后才成為小說。這些不同的程序可以用于多部小說中相同場景的敘事,成為可以任意組合的“敘事積木”。
從敘事內容來看,指令呈現者依靠情感計算框架把故事寫得“像人寫的”,但卻不能抒發情感。指令呈現者能夠根據敘事模板進行模仿,能在既有的敘事框架下對數據進行機械化的歸納、演繹與類比敘事,但在敘事內容的情感性表達方面卻難有大的突破。人工智能能夠對莎士比亞詩集的語言和韻律進行深度學習,創作出與原作相似的十四行詩。華為公司生產的智能機器人“樂府”既能夠圍繞同一主題進行詩歌和樂曲創作,還能實現不同文本間的連貫性。但是,這些人工智能作品的生成主要依靠的仍然是足夠多的數據和反復的迭代學習,而缺少情感表達。從現有的技術條件來看,智能機器可以通過模擬仿造人類情感,但卻不能擁有情感,也就無法像人一樣抒發情感。人工智能及其作品都缺乏人的內在情感,“人工智能是理性的,它整套藝術生產邏輯基于數據,即便人工智能的文藝創作開始加入情感激發和隨機化模塊,但創作的內容仍然是從大量作品中提取、分解、組合而成,這種重組方式不能稱為情感化的藝術創作”⑨。
但是,在一部分智能敘事作品中,讀者能依稀感受到情感性的表達。在一些體育新聞中,人工智能還模仿了人的情感體驗,如“笑到最后”。智能機器人“小冰”的詩集中有對“人生之苦”的感嘆,用到了“寂寞”“虛空”等詞語。“小冰”的設計者認為智能機器表達情感是可行的:“3年前,我們微軟研發團隊開始探討‘情感計算框架’的可實現性。于是,我們創立了‘微軟小冰’這個項目,試圖搭建一種以 EQ為基礎的,全新的人工智能體系。3年來,這個嘗試所取得的成功超過了預期。”⑩這里所言的“成功”其實就是人工智能技術獲得了對情感加以計算并輸出的能力。
一般認為,計算機是沒有內在情感的,但“情感計算”可以讓計算機表達出情感。“情感計算是與情感相關,來源于情感或能夠對情感施加影響的計算”,“情感計算的目的是通過賦予計算機識別、理解、表達和適應人的情感的能力來建立和諧人機環境,并使計算機具有更高的、全面的智能。”從情感計算的核心機制來看,情感信息的獲取、識別與理解的實踐過程更多是機器對人類情感的智能反應,但人類情感本身的復雜多變性仍然是純理性邏輯的人工智能機器所難以企及的。人工智能機器能夠通過復雜計算收集和分析情感信息,但情感反應是人的內在機制,它具有個體復雜性,是不能被量化的。易言之,智能敘事對于情感的表達只是情感計算框架對于情感信息的模仿性輸出,而不是智能機器自身的情感感悟和抒發。因此,智能敘事中常見的情感表達蒼白無力、邏輯混亂等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選擇性敘事和網絡敘事話語的再中介化與博弈
“中介”是指“不同行動者、集體或機構之間的任何介入、傳達或協調行為”,在此意義上可以將大眾媒體和網絡媒體都看作是“中介性或中間性媒介”,“其功能是從傳播者向受眾或在傳播參與者之間傳達意義,并由此有時取代人際交流。”“中介化”強調的是媒介在連接、協調和傳播意義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現象及其后果。人工智能技術深度參與網絡敘事的過程是網絡話語和人類社會交往的中介化過程,它不同于人際傳播、大眾傳播所形成的話語形態和社會交往形態。相對于以往的敘事模式來說,人工智能系統對于網絡話語的呈現和擴散起到了再中介化的作用,是我們理解和傳播網絡敘事時不能忽略的重要元素。
話語是口頭語言或書面語言的有意義的表述,是一組反映了社會、認知以及修辭實踐的語言表述,或者是在一組語言表述中反映、影響并抑制這些實踐的語言權力。受信息技術發展和群體傳播環境的影響,網絡話語呈現出多元化、碎片化、差異化等特征,真相與謊言界限模糊,讀者只有仔細判斷文本的語言、敘事意圖、傳播意圖等才能對網絡話語進行充分辨識。同時,多傳播主體對網絡文本的點贊、轉發、闡釋等敘事行為也會影響到網絡話語的傳播范圍與影響力。也就是說,網絡敘事話語在傳播過程中會受到指令呈現者的選擇性敘事行為的中介化過程。與傳統敘事模式不同的是,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5G、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逐步成熟,網絡敘事進程更加依賴于數據庫和算法,這就催生了網絡話語的再中介化。一方面,網絡上的所有信息都是存放在龐大的云端數據庫之中的,另一方面,只要人們在網上工作、學習和娛樂,就會有觸網痕跡,這些痕跡會被計算機編碼記錄并存入到數據庫之中,成為指令呈現者二次敘事的根據或目的。
一方面,指令呈現者有選擇地將數據庫內的各類數據信息進行集合、分類、重組和派生,形成具有一定規則的“格柵”系統,這實際上是在對網絡空間中的已有話語進行再中介化。正如波斯特所說,“它們(數據庫)是純粹的格柵,其縱向的域和橫向的記錄極其精確地把客體分開并分類。”橫向和縱向的數據記錄使得數據庫能夠保存完備的數據信息,數據的擁有者可以輕松地掌握所有的信息和話語。數據擁有者還能夠對話語信息進行篩選和分類,能夠在眾多話語的過濾和重組中得到最滿意的話語表達方式和意義傳播效果。“數據庫是規模更大范圍更廣的文化轉型的一部分,這種文化轉型把主體定位在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取向可以獲得的可見性框架之外。”這種“可見性框架”便是分散的、不穩定的話語表達在數據庫“格柵”系統里的重新分類和組合。
文學、視頻創作在人工智能的輔助下,營造出了虛擬的、脫離科學規律的話語意義和敘事風格。AI機器人可以通過數據庫編程自動模仿任何一位文學大家的敘事策略,也可以任意組合各種話語表達方式,給文學創作增添色彩。即便是相同的敘事主題,人工智能系統也能創作出多個不同版本的文本,敘事話語也就復雜多變。微軟小冰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源自于小冰對500多位中國現代詩人作品的深度學習和模仿。通過深度學習,微軟小冰的詩歌行文技巧和話語策略不同于500多位詩人中的任何一位,而是獨具一格的。某些機構還推出了小冰與讀者共同寫詩的活動,可以根據一張圖片和創作者的訴求完成寫作、修改、篩選、定稿等所有一般文學作品的創作程序。人工智能應用于“換臉”App,生成如“軍裝照”“民國照”“明星臉”等。這一App不僅可以讓用戶變成影視劇中的人物,還可以隨意改變用戶的容顏。人工智能“橡皮檫”也可以將視頻中的人和物給去除掉,進而改變敘事的要素、場景和意義。人工智能系統在文學創作、App應用、視頻制作等領域發揮出的功效,已經達到了人創作的作品和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混合在一起難以分辨的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讀者參與敘事創作和話語表達的樂趣,但也正是因為數據庫的干預,話語表達實際上經歷了創作者中介化和人工智能系統再中介化兩個過程。
如波斯特所言,“數據庫為當今政府提供了非常巨大的關于其所有人民的可利用的信息量,這有助于制訂各種維持穩定的政策。由于數據庫撒播到我們的社會之中,一個重要的政治影響就是它們提升了權力的‘統治’形式,并使每個層面上的強制機構都能獲得關于所有人口的知識”。可見,數據庫比福柯所說的“全景監獄”對人的監控更為嚴密,是“超級全景監獄”。數據庫在暗中持續收集每個人的資料并組合成個人傳略,雖然不像獄卒用雙眼對囚犯那樣施行嚴苛審查,但卻比獄卒審查得更加徹底。因為數據庫對個人信息的收集不分公開與私密,只要在電腦上留下使用痕跡就會形成相應的數據資料。人工智能時代,數據庫對個人信息的監控則更為嚴密,往往在個體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之進行監視和規訓。因此,數字化一方面給普通個體帶來了自由參與社會表達的途徑和享受數字化帶來的信息民主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使得個體話語處于主流敘事的邊緣,有可能從網絡敘事的參與者演變成接受者或“擺渡者”。正如波斯特所總結的,“數據庫的話語是一種運作于主體建構機制之中的文化力量,該機制對抗著把主體視為中心化的、理性自律的那種霸權原則”。
另一方面,深度學習、數據庫、平臺算法等對網絡敘事的滲透,一則是智能技術在內容的生產、分發等領域進行的技術革命,一則是各級敘事參與者的話語博弈過程。正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機器的技術架構在設計之初就已經融入了專業性、商業性等元素,因此,智能敘事中實際上隱含著程序設計者、管理者、運營者、使用者等的敘事意圖。程序設計者需要根據技術條件、設計目的、使用者需求等不斷調試和修改程序,管理者和運營者的商業策略和利益訴求、使用者的個性化需求和價值判斷等都會在整個智能敘事行為中相互影響。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算法并不是純粹的技術人造物,算法工程師、管理人員、內容生產與運營者、用戶、平臺的商業戰略等行動者都在改寫、轉義算法”。“改寫、轉義”的過程是各級敘事參與者表達話語的重要形式,使得網絡話語的表達和傳播受到來自技術架構、行業規則、社會規范等各方面的“過濾”。設計者/運營者、內容管理者/讀者之間相互制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非智能網絡敘事中個人話語與公共話語相互協調的話語態勢,塑造著新的話語表達形態。網絡話語表達的民主性可能會因此受到影響,更具有吸引力和更易于傳播的話語將會獲得更多關注,反之則成為話語博弈的犧牲品。
維納在其著作《人有人的用處》中曾認為智能機器、計算機將會超越人類,不只是在能源和力量上取代人類的能源和力量,而是會在所有層面上取代人類。維納當年對智能機器的樂觀判斷在今天也沒有變成現實,恐怕在未來也難以實現。但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確實給網絡敘事帶來了多重影響,人工智能系統成為網絡敘事的指令呈現者,網絡敘事進程也受到了數據庫、算法等的干預。相互鏈接的敘事文本可能是由多個獨立的積木式敘事文本拼貼而成,敘事話語也經歷著數據庫運行規則的再中介化影響。維納也曾強調機器凌駕于人類之上其實源于智力惰性本身,“有些人被‘機器’這個詞迷惑,分不清哪些事可以用機器完成、哪些事不能,什么會被留給人類、什么不會”。維納提出的問題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人工智能所面臨的現實難題卻依然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注釋:
① [法]羅蘭·巴爾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載張寅德編選《敘述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0頁。
② 葛許越:《寫作機器人“作者”主體地位辨析》,《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8期,第193頁。
③ 趙毅衡:《敘述者的廣義形態:框架-人格二象》,《文藝研究》,2012年第5期,第20頁。
④ 劉偉:《智能傳播時代的人機融合思考》,《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第24期,第16頁。
⑤ 柳旭東、李喜根、劉洋:《互聯網傳播環境下的選擇性接觸與偏軌接觸》,《學海》,2017年第2期,第128頁。
⑥ 徐英瑾:《人工智能技術的未來通途芻議》,《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97頁。
⑦ 轉引自劉彥鵬、毛紅敏:《人工智能重塑新聞生產:量化轉向、價值擴展與體驗升級》,《中國出版》,2020年第20期,第25頁。
⑧ 張斯琦:《人工智能時代文學敘事功能與傳播演變審思》,《求是學刊》,2020年第3期,第152頁。
⑨ 韓業庭:《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的藝術創造力嗎》,《光明日報》,2019年6月12日,第13版。
⑩ 小冰:《陽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