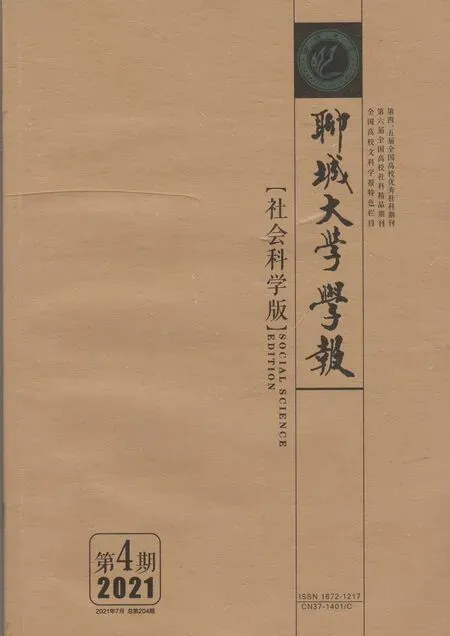秦漢以來“齊地”區域地理范圍考論
吳 慶
(淄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人文學院,山東 淄博 255100)
今之山東與“齊地”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山東”作為一個正式的政區概念最早也只能上溯到金代,嚴格意義上的“山東省”則存在于明清兩代,卻也不稱為“省”,明代是“山東承宣布政使司”的俗稱,“省”是借用元代行省的概念,清代的山東巡撫,正式職銜中也不帶“省”字,而是“巡撫山東等處”,俗稱山東省,簡稱山東,皆非正式稱呼;民國以來,尤其是新中國建立后,“山東省”才成為官方規范的政區名稱。金代以來,“山東”的地理區域范圍處在不斷的變化中,而金代以前,“山東”只是一個地理區域概念,不是政區;北宋時期,“山東”大致在京東東路和京東西路的范圍內;唐代,“山東”大致處于河南道的范圍內;隋代以前,“山東”為數個郡級或州級政區組成,這樣的區域界定更是模糊不定的。
明清以前,特別是隋唐之前,不應使用“山東”的地理概念,強加運用,有悖于歷史地理學的常識;而應該使用“齊地”這一地理概念,雖然不是政區的范疇,卻是一個穩定的地理區域范圍,這個范圍內的各級政區也是相對穩定的,這個區域范圍以黃河、濟水、泰山等自然地理事物作為周邊支撐,比較固定。邏輯上講,要開展相關的研究,必須首先具體明確地界定秦漢以來在當時被認可和使用的大體相當于今天“山東”的“齊地”這一地理概念。
一、秦漢“齊地”區域的地理范圍
“齊地”,指齊國故地,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疆域曾經涵蓋的地理范圍,秦滅齊國,天下一統,齊國既亡,齊國的疆域自然不存在了,但是,齊國疆域曾經達到的地理范圍還是存在的。這個地理范圍內,后世設置了不同的政區,政區是變革不定的,而“齊地”這個范圍卻是一直存在的,這種存在首先是一種地理區域概念和認識的存在,同時也需要一種比較穩定的不隨時代變遷而隨時變化的自然地理區域的存在作為客觀支撐,否則,齊國亡,政區變,“齊地”的范圍也會隨之改變。“齊地”區域概念存在的客觀基礎,是一定層次的自然地理區域的存在,即在“山川形勝”標準下以比較明顯且穩定的自然地理事物作為劃分界限而長期存在的地理范圍,這一點,“齊地”區域確實是具備條件的。
春秋戰國,五百余年,齊國的疆域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歷史范疇,是一個從小到大的過程,是一個從淄水流域向東西兩個方向同時征服擴張的過程,其至小時,不過初封時的營丘周邊方百里之地而已,其至大時,是齊湣王時的東到大海、西到黃河、北接燕境、西南到河洛、東南到淮泗的遼闊版圖。①齊湣王時,樂毅領兵伐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分兵以定齊地,“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瑯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后軍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六月之間,下齊七十余城,皆為郡縣。”濟西即濟水之西,樂毅率軍渡過黃河后,在此擊敗齊師,從濟南向東推進,其五路軍隊的進攻路線基本上就是當時齊國疆域的大致輪廓,這一段引文中大多為西漢時的地名,以此言之,當時的齊國版圖西到黃河、南到泰山山脈、北到千乘、東到東萊、東南到瑯琊,這也許不是齊湣王滅宋后齊國疆域的最大范圍,但應該是齊滅宋之前的戰國時期齊國疆域的比較穩定的范圍,或者說是當時認為的長時期屬于齊國的版圖,這是一個可以作為參考的地理范圍。那么所謂齊國疆域,到底是哪個時期的齊國的疆域呢?大概春秋時期是齊國疆域的形成時期,戰國時期是齊國疆域的穩定時期,自然以戰國時期的齊國疆域范圍作為“齊地”的地理范圍。戰國時期的齊國疆域雖然大體穩定,仍然有起伏變化,尤其是與列國接壤地帶的郡縣城池多有得失伸縮,但是此時的齊國疆域的基本部分是穩固的。這個基本部分就是齊國以臨淄為中心擴展時遇到山川阻隔而形成的一個范圍,就是前面所說的符合“山川形勝”標準的區域,一個自然地理區域,這個區域就是戰國時期齊國疆域的基本范圍,也就是秦滅齊時的齊國疆域范圍,即戰國、秦、漢以來人們普遍認同的所謂“齊地”或齊國故地的地理范圍的根據所在。
對于“齊地”區域的地理范圍,戰國以來的文獻有著比較連續的記載和反映。《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載蘇秦游說齊宣王之辭曰:
“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余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②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256-2257頁。
這是戰國時期的人物蘇秦的說法,“齊地”的地理范圍是東到瑯琊,西到濟水,南到泰山,北到渤海;瑯琊是指瑯琊城、瑯琊臺,為沂蒙山系向東延伸入黃海的地方,即今膠州灣一帶,清河即濟水,當時的黃河河道與東漢以后長期安流期間不同,較為靠西靠北,齊地不以黃河為界,而以濟水為界;如此一來,濟水、泰沂山系、渤海、黃海組成了齊地四周的自然地理界限。
《漢書》卷四三《酈食其列傳》載西漢初年酈食其向劉邦進言平齊之策曰:
“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于歷城,諸田宗強,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108頁。
在秦末漢初的人物酈食其看來,“齊地”的地理范圍是在海岱河濟之間的,海是指渤海,岱即泰山,河即黃河,濟即濟水。這時的黃河河道與戰國時期相比又有變化,黃河下游的西支湮廢,東支河道基本維持原狀,此處應指黃河東支河道,濟水河道在當時的黃河河道之東,按照這些自然地理界限,“齊地”應該是東到黃海,西以黃河為界,北以渤海為界;以黃河為界使得“齊地”的地理范圍在黃河下游地區向西有了較大幅度的擴展。這與蘇秦所說的“齊地”范圍有所不同,兩者之間的關鍵區別在于西部是否以黃河為界;此處,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若是把蘇秦所說的“西有清河”中的清河不理解為濟水,而是理解為清、河,清指濟水,河指黃河,那么就和酈食其所說的河濟是一個概念了,可以肯定的是,戰國時期的清河不是指政區,非清河縣,亦非清河郡,《史記》張守節正義以清河相當于唐代之貝州的說法明顯存在問題。如此看來,以黃河為“齊地”的西部地理界限更為合理。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載漢高祖五年田肯勸劉邦之辭云:
“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①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82-383頁。
比酈食其稍晚一點的西漢初年的田肯指出,“齊地”的范圍是東到瑯琊,西到黃河,南到泰山,北到渤海。依照田肯的說法,可以直接明確黃河古道為“齊地”的西部界限,與前述分析一致,同時也指出渤海西岸為“齊地”的北部界限。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秦漢時期“齊地”區域的四至范圍,即東到瑯琊、即墨,西到黃河古道,北到渤海西岸,南到泰沂山脈。
二、“齊地”區域南、北地理界限辨證
然而,問題并沒有如此的簡單,《漢書》卷二八下《地理下》中所描述的“齊地”區域范圍似乎與前述結論存在出入,其文曰: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地。”②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59頁。
東漢初期的人物班固用西漢時期的郡縣政區來描述“齊地”,東有菑川國、東萊郡、瑯琊郡、高密國、膠東國;南有泰山郡、城陽國;北有千乘郡,清河郡的河南地區,勃海郡的高樂縣、高城縣、重合縣、陽信縣;西有濟南郡、平原郡。對照《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西漢、東漢時期》之西漢《兗州、豫州、青州、徐州刺史部》圖,班固所提及的屬于“齊地”范圍內的郡、國、縣所處的地理區域的位置大體為西部以當時的黃河河道為界、北部以當時的黃河河道以及渤海為界、東部以黃海為界、南部以泰山山脈一線為界。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班固把泰山郡轄區劃入“齊地”,使得“齊地”向泰山以南有了較大幅度的延伸,這個與蘇秦、酈食其的說法均存在差異,在南部界限上,兩人都主張以泰山為界,即泰山以北為“齊地”,泰山以南地區不應視為“齊地”;其二,班固把勃海郡在黃河古道以南的幾個縣劃入“齊地”范圍,實際上就是以黃河古道為“齊地”北部界限,因為渤海的海岸線是漫長的,千乘郡比鄰渤海,勃海郡也在渤海沿岸,蘇秦、酈食其、田肯皆未指明“齊地”北到渤海是具體到渤海西岸的哪一段,班固以黃河古道為“齊地”北界,也就是以勃海郡境內的渤海沿岸為“齊地”北界,對此,也需要分析驗證。
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到底應該以泰山山脈還是以泰山郡為“齊地”南部界限。司馬遷在《齊太公世家》中說:“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在《貨殖列傳》中說:“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故而太史公所說的泰山不是指泰山郡政區,而是泰山山脈,意即從泰山到瑯琊臺一線以北、渤海以南為齊地范圍,地方二千里,換言之,泰山以北為齊國,泰山以南為魯國,泰山山脈是齊地南部的天然分界線,而《管子·小匡篇》亦云齊“地南至于岱陰”,③趙守正:《管子注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頁。明確指出泰山以北為“齊地”。對此,我們還可以參照齊長城的修建路線,齊國在南部修筑長城,作為一種大規模的軍事防御工程,明顯具有人為劃定國境分界的意味,齊國可以跨過長城向南進攻,但是以長城為依托保護長城以北地區才是主要目的,長城以南地區是可伸縮的,長城以北地區卻是必須堅守的,所以從疆域形成的長期性考慮,齊國無疑把齊長城沿線以北地區視為自己的基本疆域范圍。對于齊長城的走向,《史記》卷四十《楚世家》“還蓋長城以為防”之張守節正義云:
“《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余里,到瑯玡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上筑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余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川,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玡臺入海。’《薊代記》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為塞也。”①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732頁。
齊長城西起平陰縣,東至瑯琊臺,中間沿泰山山脈、沂蒙山系北側山嶺因勢修筑,跨越千余里,主要目的是防備楚國的進攻。至于說齊長城乃齊宣王時修建,不合情理,如此龐大工程,以齊國有限國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應是長時段逐漸累積而在齊宣王時期基本竣工。齊長城沿泰山北側展開,則泰山南側的泰山郡自然不能視為齊國疆域的基本范圍,也就不是“齊地”區域的涵蓋范圍,這一點是明確的,至于齊長城經過的詳細路線,學界早有詳論,茲不贅述。秦使蒙恬筑長城以為北界,齊修長城以為南界,可謂異曲同工,則“齊地”以泰沂山系為南部邊界是可以確定的。班固把泰山郡劃入“齊地”,最大的可能是為了機械地對應“虛、危”的天文星象分野,為湊足宿度而將泰山郡納入“齊地”,屬于以天文而改地理,總歸是牽強的,或者也可以說,雖然齊國疆域也曾涵蓋泰山郡,但終歸不是齊國版圖的基本部分,故而“齊地”區域南部仍當以泰山山脈為界。城陽國與瑯琊郡則屬于濰水、膠水流域與沂水、沭水流域接界地區,屬平原、丘陵地貌,齊國的疆域向這個地區擴展是合乎邏輯的,而且符合自戰國到西漢都有提及的“瑯琊”這一地理坐標,所以班固在東南方向劃入這兩個郡、國是合理的。
關于第二個問題,即“齊地”北部究竟以哪一段渤海海岸線為界,亦即“齊地”北界是到千乘郡還是到勃海郡。秦滅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齊國故地設齊郡與瑯琊郡,項羽滅秦而分封,以齊國故地封建三王,田都為齊王,都臨淄,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濟北、齊、膠東三國,是為“三齊”。后有齊王田廣,韓信攻殺之,漢高祖劉邦封韓信為齊王,后又徙封楚王,高祖六年以庶長子劉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是為齊悼惠王;劉肥為討好呂太后而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劉肥之子齊哀王劉襄時,呂太后封呂臺為呂王而以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封邑,又以齊之瑯琊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瑯琊王,至此,齊國被一分為四,即齊國、呂王封邑濟南郡、瑯琊國、魯元公主湯沐邑城陽郡。漢文帝立,將呂太后所割齊之瑯琊、濟南、城陽三郡復歸齊國,旋以齊之城陽郡封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以齊之濟北郡封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文帝二年,濟北王謀反被誅,濟北郡入于漢,此時之齊王為齊哀王之子齊文王劉側。劉側卒,無子,國除,齊地盡入于漢。一年后,漢文帝又以原先齊國各郡封齊悼惠王劉肥諸子為王,劉將閭為齊王,劉志為濟北王,劉辟光為濟南王,劉賢為菑川王,劉卭為膠西王,劉雄渠為膠東王,加上城陽王劉章,凡七王,原先的齊國被一分為七,即齊國、濟南國、濟北國、菑川國、膠西國、膠東國、城陽國。從戰國時期的齊國,到秦國時設在齊國故地即“齊地”的齊郡、瑯琊郡,再到項羽稱霸時的“三齊”即齊國、濟北國、膠東國,再到田廣、韓信時期的齊國,再到劉邦所分封的齊國,最后到呂太后、孝文帝時期的四分“齊地”以及七分“齊地”,都是以戰國時期齊國的疆域為基礎而一脈相承,區域地理范圍比較穩定,但政區劃分越來越精細。以孝文帝時期的七分“齊地”來看,齊、濟南、膠西、膠東、城陽、菑川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皆無疑義,唯獨濟北國不甚分明,關鍵在于濟北國的轄境能否延伸至勃海郡一帶,若濟北國僅轄一郡,則一郡之地從濟水北岸擴展至勃海郡附近,似嫌過于遼闊,可能性不大,若濟北國轄有數郡,以一國而管轄當時黃河河道以南各郡,似可成立,存在這種可能性;那么考察西漢濟北國的轄境就成為確定西漢時期“齊地”區域北部界限的要點所在。
據《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司馬貞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三縣屬平原。”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①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27頁。《漢書》卷三九《曹參列傳》亦載此事,而顏師古注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②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107頁。歷下、臨淄的位置可以確定,韓信先向東破歷下,再向東取臨淄,然后回師向西定濟北,則此處所謂的“濟北郡”,明顯處于歷下以西,更處于臨淄以西,又臨近著、漯陰、平原、鬲、盧等縣,而這幾個縣屬于后來的濟南郡、泰山郡、平原郡,這三個郡的位置也是可以確定的,“濟北郡”既與三郡相鄰,應在河濟之間的地域,則其轄境絕不至于到達勃海郡一帶。按照顏師古的注解,韓信平齊時尚無濟北郡,漢初先有濟北國,七國之亂后國除而為濟北郡,此處為太史公追書之,則可理解為當時的五縣后來屬于濟北國、濟北郡的轄境,再后來分屬三郡,如此一來,漢初的濟北國或濟北郡的位置就更加明確了,實際上與勃海郡一帶地域風馬牛不相及也。唐代人注《史記》、《漢書》,皆以西漢之濟北國或濟北郡比唐之濟州,濟州設于北魏,延續至唐宋,濟州治盧縣,位于濟南郡以西,轄境主要在東漢初年以來的黃河河道以南與濟水以北的區域,絕不能達于勃海郡轄境。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齊國的疆域或許到達過勃海郡一帶,但不是齊國疆域的基本部分,所謂“齊地”的北部應以千乘郡的渤海沿岸為界,而不當以勃海郡的渤海沿岸為界。為求規整地對應天文星象分野,班固以虛危二宿的宿度對照西漢的政區,于是便把“齊地”的范圍向南北兩個方向作了一定幅度的拉伸,南到泰山郡,北到勃海郡,在某種程度上歪曲了人文地理的劃分,難免有些牽強。當然了,若從經濟地理以及風俗地理的角度講,班固的做法或許也其道理。總之,“齊地”區域的北部應以千乘郡一帶的渤海海岸為界,而非勃海郡之渤海。
三、天文分野與“齊地”區域地理范圍
其實,關于天文分野與政區地理范圍的對應問題,《舊唐書》卷三六《天文下》中的論述要比班固的說法更為透徹明了:
“天文之為十二次,所以辨析天體,紀綱辰象,上以考七曜之宿度,下以配萬方之分野,仰觀變謫,而驗之于郡國也……及七國交爭,善星者有甘德、石申,更配十二分野,故有周、秦、齊、楚、韓、趙、燕、魏、宋、衛、魯、鄭、吳、越等國。張衡、蔡邕,又以漢郡配焉。自此因循,但守其舊文,無所變革。且懸象在上,終天不易,而郡國沿革,名稱屢遷,遂令后學難為憑準。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至開元初,沙門一行又增損其書,更為詳密……須女、虛、危,玄枵之次。子初起女五度,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郡東逾濟水,涉平陰至于山荏,東南及高密,又東盡東萊之地,得漢之北海、千乘、菑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盡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③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11-1312頁。
自戰國以來,天文學家以天文十二分野對應一定的區域地理范圍,先以列國配,再以漢之郡國配,后以唐之州縣配,星象在上,終天不易,政區沿革,代有變遷,所以分野之說頗顯雜亂與牽強。政區轄境屢有變化,星象分野卻基本固定,很多時候無法規整對應,也無法一成不變的對應,所以往往為了湊足分野而人為割裂政區格局,拆東補西的事常有發生,或者某個地理區域實際上達不到分野的范圍,也要強行添加而補足之,“齊地”區域因為要對應虛危分野的宿度而北部延伸至黃河古道以南的勃海郡且南部涵蓋泰山郡轄境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此中玄機,先賢早有洞悉,所以分野歸分野,事實歸事實,我們應辨析并尊重事實,不可拘泥于分野,那么秦漢時期的“齊地”地理區域范圍至此也就完全可以明確了,東到即墨、瑯琊一帶的黃海沿岸,西到黃河河道,南到泰沂山系,北到千乘郡之渤海沿岸。
四、余論
作為“齊地”南部界限的泰沂山系是非常穩定的自然地理坐標,但是作為“齊地”西部界限的黃河卻處于變動之中。根據譚其驤先生的研究,黃河在秦代以前是基本安流的,西漢時期尤其是漢武帝以后則很不穩定,先后決溢十余次、改道五次,黃河下游河道在今河北黃驊到今山東利津之間的地帶來回擺動,給沿河郡縣造成了深重的災難。①秦漢時期黃河河道走向及流經地域與今日黃河有較大差異。關于黃河改道問題,譚祺驤先生有詳審論述,詳見氏著:《長水集》下之《〈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及《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第39-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東漢初期,王景主持治理黃河,基本上沿著王莽始建國三年黃河決口后的流經地域,從滎陽郡到千乘郡一線修筑河堤,黃河在今山東利津縣入海,從此到隋代的五百多年中,黃河長期安流,黃河河道幾乎沒有發生改變。
從東漢初年開始,黃河下游河道大幅度向南遷移,原先班固所說的處于舊黃河河道以南的勃海郡高城、重合、陽信等縣就處于新河道以北了,而平原郡則由完全處于舊河道以南變為一部分處于新河道以北而另一部分處于新河道以南,成為一個跨河的郡,黃河下游的自然地理格局發生較大的改變,但政區格局卻基本穩定。由此,東漢初期以來,以黃河河道作為“齊地”的天文分野的理論失去了現實依據,而實際上的“齊地”區域地理范圍卻因為黃河的改道而更加的完整和穩固,因為黃河由從勃海郡一帶入海變為從千乘郡一帶入海,正好符合前述“齊地”區域北到千乘郡之渤海沿岸的定位,不需要再為了湊足天文分野而強行拆分既定的政區格局了。黃河的改道并沒有使得“齊地”區域的地理范圍發生明顯的變動,“齊地”西部到黃河,北部也到黃河,南部到泰沂山系,東到大海,四面自然地理坐標的長期穩定使東漢以后的“齊地”區域這一地理概念形成了持久恒定的內涵,而“齊地”在自然地理、政區地理、經濟地理、軍事地理、文化地理等多個層面都逐漸表現出明顯的區域特性。②詳參周振鶴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第六編《區域文化地理》,第283-29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