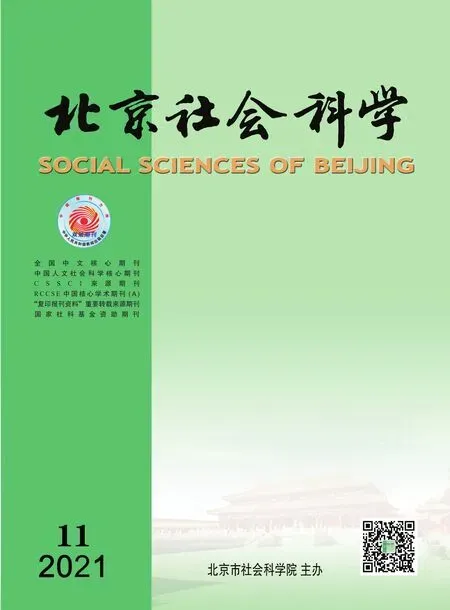南望眼:明人出使越南專集
馮小祿
在歷史上的亞洲周邊國家中,位于中國東南靠南海一隅的近鄰越南(宋代獨立后常稱“安南”),與位于東北渤海灣一角的朝鮮和東向越海而居的日本、琉球一樣,都處于以中國為中心的漢字和儒家文化圈中,它們與中國歷代王朝有著深淺不一的以朝貢冊封為標志、以互派使節為主要形式的宗藩關系往來,由此涌現和留存了大量互使史料和使行專集。其中,朝鮮、越南向元明清出使的漢文“燕行錄”“朝天錄”“使華錄”和明朝出使朝鮮的系列《皇華集》,因為近來甚為熱門的域外漢籍和“從周邊看中國”眼光的緣故,得到了亞洲文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和整理、研究。然而,當初至少有過21種、現存也有15種的明人出使越南的系列專集,卻遺憾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和研究。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值得集中和重新打量的文學類型,在使越和使外專集上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它既是明代文學的重要構成,也是中國文學向嶺南和越南外延的重要構成,可以運用跨文化旅行書寫理念來重構跨國使行文學中“異地”嶺南鏡像的推進,明人特殊的安南情結及其展開,以及與安南的宗藩交流實質等。這在重視嶺南與東南亞的地緣關系和環太平洋經濟圈的今天,立足于中國文集和中國立場的向外研究,自有其不容輕忽的意義。
一、南望眼:明人使越專集的內容及特征
所謂使越專集,是指從古代越南獨立于中國直接轄制的北宋算起,宋、元、明、清四朝曾編集或刻行的以四朝使臣出使越南之行為名的專集,不包括單篇的賦和詔敕。它可以是使臣自編,也可以是后人所編。在兩宋,目前僅知有過一次并未完成的編集,即北宋李度的《奉使南游集》[1]。到元代,張秀民考得7種,[2]然原書或主體現存的僅3種。到明代,使越專集的編刻已蔚為風氣,以至有天順六年錢溥使越,“與其國相等倡和,明日即印成詩集,此活字板也”的即時板刻異國的現象,[3]對此,劉玉珺考得13種,[4]筆者則新考得8種,共計21種。至清代則下滑,僅7人10種。由此可見,明人使越專集的數量不僅前超宋、元,后亦邁清。
明人使越專集原書現存的有劉夏《奉使交趾贈送詩》、黃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記》、王縝《交南遺稿》、張弘至《使交錄》和徐孚遠《交行摘稿》等5種,劉夏、王縝2種為筆者考得。原書雖佚但主體內容尚分體散存于明使文集或其他文獻的有10種,分別是張以寧《使安南稿》、林弼《使安南集》、任亨泰《使交稿》、黃福《使交文集》、錢溥《使交紀行志》、錢溥《使交錄》、魯鐸《使交稿》、孫承恩《使交紀行稿》、湛若水《湛子使南集》(見潘希曾《南封錄》),其中,黃福《使交文集》、錢溥《使交紀行志》、湛若水《湛子使南集》、潘希曾《南封錄》等4種為筆者考得。僅存少量使越詩的有3種,分別是吳伯宗《使交集》、嚴震直《南游集》和許天錫《交南詩》,嚴震直、許天錫2集為筆者考得。至于王廉《南征錄》、黃諫《使南稿》和呂獻《使交稿》等3種,則不僅原集已佚,即所作使越詩文亦未見,而僅見國內贈行詩文。另外,宣德六年(1431)、九年(1434)兩度奉使的章敞《質庵集》至少有44題48首詩為使越之作,也值得重視。
從出使任務看,明人使越以冊封安南國王和宣頒明朝皇帝即位詔書為主,各有10人和3人,其他則是吊祭、諭討、借道等。從作者科第看,除劉夏、王廉、嚴震直、黃福等明初官員外,都是進士出身,其中張以寧、林弼是元末進士,吳伯宗、任亨泰是明朝狀元,并稱“吳任”,黃諫是探花,魯鐸是會元。再從作者出使時的官職看,都是中央文官,而以翰林院和科道官員為主,分別有7人和5人,其他則為尚賓館副使、吏部主事、禮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和都御史等,其中任亨泰為禮部尚書,官職最高。可見這是一個以和平宣詔、冊封為主的使行活動,詩文有較為顯著的中央臺閣風格。
從現存專集和相關序言看,明人使越專集的內容和編纂方式在繼承漢晉以來外交行記、語錄、宋代使遼金集和元朝使越專集等寫作傳統的同時,又有發展和新變,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專收明人使越往返途中所作詩歌或安南所贈詩歌,記載“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5],體現專集歌詠沿途風物和感懷、唱酬的特征,可稱為“使越詩集”。該類最多,有劉夏、王廉、林弼、任亨泰、王縝、魯鐸、張弘至、孫承恩、徐孚遠等10種。
第二類所收作品除明使自作詩外,還有文類、作者不一的文,可稱為“使越合集”,體現專集的使還報告和宗藩交流性質,又可析分為三小類:所錄內容包含奉使的敕旨、與安南國的往復書信和自作紀行詩,如嚴震直《南游集》[6];所錄內容以在安南所賦詩和回京奏疏為主,附錄安南國王詩、書信和陪臣詩,如潘希曾《南封錄》[7];“多載贈答詩文”[8]和前述文體、內容的十卷以上本詩文合集,如黃福《使交文集》十七卷、錢溥《使交錄》十八卷、湛若水《湛子使南集》十二卷等3種。
第三類為使越日記,如黃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記》、錢溥《使交紀行志》。
其中,元朝專集中無劉夏、王縝類小集和十卷以上本詩文合集。
明人使越專集是明朝使臣從首都出發,一路向南,經過中國南方、嶺南出使到越南首府,進行跨國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專門載體,具有穿越不同文化類型,進行嶺南民族邊地和安南異國形塑以及宗藩交流的旅行書寫特征,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南望眼”。在明使眼里,嶺南與安南差不多都同處于中原華夏觀念里的地理、種族和文化邊緣,都是“欠發達和欠文明的空間”,而嶺南與安南又地緣緊鄰,在歷史上有多重分合關系,聯系特別緊密。由此,我們下文重點探討明人使越專集對于嶺南鏡像的推進、安南情結的展現和宗藩交流的文學演繹。
二、從“瘴鄉”到“桃源”:“異地”嶺南鏡像的推進
嶺南在古代文獻中又稱“嶺表”“嶺外”,既是一個指涉五嶺之南廣大地區的地理概念,又是一個“北方中國人”觀察和走出嶺外的文化概念[9]。其具體地理范圍和行政區劃在歷史上曾有伸縮和分異,以北宋越南獨立為界,之前的嶺南包含今廣東、廣西、海南和越南北部等環南海的廣大區域,以今越南范圍內的交州和中國范圍內的兩廣分合為標志,在漢唐時期,它們又曾共享“南越”“嶺南道”“安南都護府”等名稱;之后的嶺南則變成一個僅包括兩廣和海南的中國華南地區。然無論分合,在中越人眼里,越南與嶺南總有著極為密切的地緣和文化關系。因此,中國出使越南的作品定會涉及嶺南,而有關嶺南的作品多會延及越南。
明代之前的嶺南,常被“異化”為瘴癘之鄉和蠻夷之地,被流放和貶謫而來的中原文人視為畏途和“魑魅之鄉”,有著極為強烈的異域和邊緣色彩,“到明代其文化地位才明顯上升”[10]。而明代使臣對于嶺南的深度書寫,則在“瘴鄉”和民族邊地特色的歷史基礎上,又發展出嶄新的美好“桃源”形象。下面即依外來人與異地的接觸認識進程[11]來看明人使越紀行詩中對嶺南形象的承續和掘進。這里以洪武三年(1370)、十年(1377)兩度使越的林弼和嘉靖元年奉使的孫承恩紀行詩為主,而兼及其他明代使臣詩以作對比和豐富。
(一)“萬里瘴鄉,山川險惡”[12]:遙遠、驚怖的異域初印象
從南京特別是北京一路水陸行來,嶺南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僻遠”或“險遠”:“我行持使節,道路絕阻蹇。頗聞北來士,游宦愁僻遠。”[13]“梅嶺不見梅,翻訝傳載誤。……平生說茲山,險遠驚寐寤。”[14]其次是山川險惡,“山徑一何惡,一嶺復一溪。初言舟行苦,陸走更險巇”[15],“陸行多豺虎,水行多蛟鱷。慘慘客子情,觸目風景惡”[15]。當然,最讓人一言即心生恐懼者,則莫過于自古以來即傳說要人命的瘴氣:“其山溪之險惡,竹樹之蔽翳,一遇炎暑,則毒蛇猛獸之氣,蒸而出林莽,流而出澗谷,雖水泉蔬茹皆不可食。及再至之日,即不能食。及道左江,復染嵐暑,轉為傷寒,既泄且痢。”[16]孫承恩也在嶺南紀行詩中四言平浦驛、蒼梧、相思洲、鐙勒驛的“瘴癘”,“所喜瘴癘息,寧計水澀乾(自注:自南雄無水)”[14],“夕霧兼晨霏,瘴癘方侵淫”[17],“況茲饒瘴癘,云水昏漫漫”[18],“瘴癘日慘毒,鬼妖日睢盱”[15],加深了嶺南的歷史刻板印象。
而瘴氣,加上更為形象直觀的比人都還長的蝮蛇,比蝘蜓還毒的蜮蟲,以及“蝑蚿點醯醬,紅宿不敢飯”[13]的當地斑斕生態飯食,就成了嶺南給人的四大恐怖初印象,集中體現了帝國使者來到邊地嶺南的驚怖感和緊張感。而這也是很多中原人如非貶謫不愿來此為官的原因:“十人九物故,嵐瘴嗟滿眼。”[13]于是,嶺南僻遠、蠻荒、恐怖的異域化鏡像,也就在唐宋元以來的歷史敘述和文學書寫中繼續深化,成為嶺南初印象的刻板表達。
(二)“風氣各有限”、“土風固云惡”[13]:新奇而需警惕的多民族雜居生態
嶺南少數民族眾多,或棲山林為瑤、僮、獠,或住水邊為蜑民。其生產方式、民族性情、語言、房屋、服飾、物產、飲食、趕集、娛樂等都與內地有很大不同。其生產方式是較為原始的“畬耕與野蠶”[13],需要通過打獵、捕魚等方式補充生活資料:“獵野撚花箭,涉川刳木船”,“負弩常從犬,扳罾或得鳊。”[19]據孫承恩觀察,這種與中原不同的民俗是從廣東韶州即開始的:“凌江一超忽,日覺眼界新。莽蒼村落稀,青山多白云。行行過韶陽,蠻語漸不真。衣服中土異,竹幘革可紉(自注:始見戴竹帽皮帽者)。暄然秋冬交,氣候如深春。”[14]嶺南山地民族的房屋也很奇特,往往是竹木深處,倚山傍巖,搭一像亭子的小茅屋,分上下欄,是現在稱為“干欄式”的原始“巢居”狀態:“架巖鑿壁作巢居,隱約晴云碧樹疏。水枧枝枝橫檻似,禾囷箇箇小亭如。”[20]其發型和服裝也怪奇,男女都梳高髻,纏紅線,穿白纻衫、青布裙,遠方來的旅人甚至分不清男女:“峒丁峒婦皆高髻,白紵裁衫青布裙。客至柴門共深揖,一時男女竟難分。”[20]且出門趕集的是穿著粗短衣裙的女性,他們稱為“趁墟”。對此,孫承恩《太平(府)》亦言:“椎髻女歸丑,短衽赤雙腳(自注:自此以南,女婦衣飾盡然)。扶攜趁朝墟,白發裹青箬。”[15]
其物產因為地理和氣候差異,也與北方和江南大不同:“沙姜長豎指,泥蕨細鉤拳”,“夔羵為伴侶,麋鹿當牲牷”,[19]“山蕉木柰野葡萄,佛指香圓人面桃。更有波羅甜似蜜,冰盤初薦尺馀高”[20]。還有“盤遮蕉葉攜殽至,甕貯筠籠送酒來”[20],“趁墟野婦酤甜酒,候館溪童進辣茶”[20]等土特產。真是“天地共一域,風氣各有限。朔南殊俗習,川陸異物產”[13]。其歌舞娛樂則是全民狂歡,不分男女老幼:“蠻鬼歌堂賽,狡童舞袖翩。溪翁醉皆倒,野婦喜如顛。”[19]迥異于內地的謹守秩序,不茍言笑。
不過與此同時,針對嶺南迥異于內地的多民族雜居生態,林弼又十分“警惕”地提醒漢族官吏要秉持“寬簡”政策來“撫循”人民,否則即可能給朝廷添亂。[13]對此,明宣德六年和九年兩度使越的章敞,也提到了廣西橫州少數民族搶劫財物和攻擊官府的情形:“況有蠻人多出沒,不問黃昏并白日。前年驛吏已經傷,近日巡司新被劫。”[21]到正德元年(1506),正副使魯鐸、張弘至在府江到陽朔的舟行途中,也曾擔憂當地瑤族阻江劫奪:“府江憂賊復驚灘,十日真成行路難。”[22]直至嘉靖元年(1522)的孫承恩,也多次寫到經行嶺南麻墟水、鐵爐頂、白沙等地時的民族搶劫與暴動:“疊嶂千萬重,賊穴難比數。西或連閩蜀,東應接吳楚。居民與商舶,劫掠莫敢御。無人向誰何,況敢索征賦。”[17]“頗聞舟人言,日者屢傳警。潛過崖壑下,仆從面目冷。畏途真險艱,嘿坐心怲怲。”[17]“為言盜賊繁,干戈日騷屑。……哀哉此生民,川谷日流血。”[15]由此可見,嶺南的民族管理和社會生態確實是延綿整個古代中國的大問題。
(三)“流水桃花今有路,何須更覓武陵山”[20]:理想化的世外桃源
在經歷了對嶺南的恐怖化和新奇化階段后,明朝使臣逐漸冷靜下來,開始發現這個中原人眼中的嶺南民族邊地其實是一個有著悠遠的民族血脈和獨特生活智慧的民族世界,自成一體,取法自然,因地制宜,充滿了古樸的睿智魅力。比如他們依山傍巖的干欄式“巢居”房屋,即有深意,或是為了防衛猛獸:“考其所以然,蓋地多虎狼,不如是則人畜皆不得安,無乃上古巢居之意歟?”[23]或是為了預防瘴氣:“俗多架木為巢,以避瘴氣,所居謂之柵。”[24]此外,用竹木引水入屋的簡易工具“水枧”,以及就地取材做成的佳肴美酒和具有濃郁民族風情的歌舞、習俗等,都讓人意識到,它其實是一個立體而有趣的社會組織。一句話總結,就是“孰云殊土俗,自是一山川”[19]。
其次,當生病死亡的恐怖想象被解除,當艱辛的水陸使程暫停,接受當地漢官和土官的招待,進入比較閑暇的觀賞狀態時,明朝使臣又像當初被貶黃州的蘇軾一般,發現了該地好處多多,表現在美食上,就是山中佳果眾多,江中魚產豐富:“山果紅堪羞,江魚白堪饌。閑來惟酒桮,醉后即茗椀。”[13]表現在美景上,則是“白沙青石小溪清,魚入疏罾艇子輕。謾說南方風景異,此時真似剡中行”[20]。一種不輸于山陰道上看美景的親和感油然而生。——這又是將嶺南江南化了。
最后,在上述兩種認識和體驗基礎上,更進一步升華為理想化的世外桃源形象:“龍州溪洞極南邊,雞犬桑麻自一天。流水桃花今有路,何須更覓武陵山。”[20]現實中的桃花源不在文人筆下和傳說中的武陵山下,而就在眼前的“極南邊”地。值得說明的是,這也并非林弼一人有此想像,而是很多明使在行經嶺南時都會有的體驗和看法。比如錢溥使團在行到廣西南寧府附近一個名“凌灣”的村莊時,就覺得該村很像桃花源,而在其《使交紀行志》中寫道:“(天順六年八月)丙子,過一近村名凌灣,居民數百家,雞犬相聞,牛羊遍丘隴,男婦隱隱竹樹中,打木績麻,聚首相觀。有夫充役者,攜餉出榼于船傍。儼一武陵桃源也。地平曠,賊罕到。間有來者,人眾有備,亦難入。若使他郡皆然,豈有民不安生者哉!”[25]
三、安南情結:歷史記憶與現實關懷
在中國周邊的同文國家中,自宋代獨立后的安南國可謂是明王朝既想占據但又怕燙手、既輕蔑又覺得有些親切的復雜對象,具有“自我”與“他者”綜糅紐結的特征,可謂明朝的安南情結。與朝鮮、日本、琉球不同,安南在宋代之前一直都屬中國內地,是直接管轄的最南疆域。但五代十國的紛亂和宋代的羸弱,讓安南掙脫了秦漢唐時期的郡縣管制,成為一個雖向中國王朝進貢、接受中國王朝冊封,但實際在各方面皆獨立自主的南方帝國。即使是橫掃歐亞大陸如卷席的大元王朝,也未能通過兩次大規模的深入作戰讓其重回中國懷抱,最終仍是用傳統的封貢方式維持兩國的宗藩交往。而這一切到了明代,展現出的歷史畫卷卻讓人驚嘆其多樣性和詭譎。
其一,永樂五年(1407),明朝通過戰爭,實現了中斷400多年的中國郡縣安南的夢想,重回漢唐故事,但21年后的宣德二年(1427)冬十月,為屢仆屢起的安南叛亂頭疼不已的明宣宗朱瞻基,以安南黎利上表找到陳氏后裔愿奉為國王的偽言為藉口,終于不恤“論者”“人言”反對,在臺閣重臣“二楊”(楊榮、楊士奇)的支持下,以朱元璋祖訓“不征占安南”為托辭,就坡下驢,決定甩掉安南這個燙手的山芋,“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將安南還給安南,不再郡縣統治,“其與之”。[26]之后兩國重回封貢體制,讓懷揣安南夢的明人飲恨惆悵,是謂“宣德遺恨”。其二,嘉靖十九年(1540),乘安南國內黎莫紛爭,明朝重兵壓境,脅降莫登庸,降其國為安南都統使司,降其統治者為從二品都統使,由此在規格和形式上將安南土司化(正是如此,明朝此后再不派遣使節出關冊封,而只是讓其到鎮南關自領誥命,并進行應有的朝貢和請封),但又讓其在國內“帝制自若”[27],似乎滿足了明人對安南的圓滿處置——貶損它但又不占領它,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明末。其三,其時天崩地裂,明朝覆亡,茍延殘喘的南明小朝廷又將如何面對這時要求“漲價”甚至反攻倒算的安南國呢?這些有關明朝安南情結的歷史記憶和現實關懷,都可以在明人使越專集里得到集中演出和詮釋。
(一)安南的內地化稱名
就地理位置而言,安南在嶺南之南,是“嶺南南又海南邊”[28]和“南天南”[29]。就歷史和文化關系而言,安南在宋代之前長期是中國的聲教范圍和統治區域:“交州古號越裳國”[30],“萬里龍編舊板圖”[31],出使安南的明使和贈行的明人每每都用來自先秦的越裳國入貢和秦漢唐的郡縣統治,來稱說古代越南地區的中國內地歷史和文化聯絡。其中出使南越(趙佗)、橐載而歸的陸賈和出兵安南的馬援銅柱、薏苡、跕鳶等漢代典故出現得最為頻繁,成為事涉安南的漢化歷史和使者品格、功業的熟典。命名尤其國名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強烈體現,用中國對安南的歷史命名而不用獨立之后的安南的自我稱名(如大虞、大越等國名盡管也中國化,但中國王朝還是會斥為“僭”和“偽”),即典型體現了古人尤其是明人對于安南的內地郡縣情結。
在眾多關于古代越南的漢文稱名中,最為古老和持久的又當數“交趾”(或亦寫作交址、交阯)和交州。當作為“南蠻”之一的“交趾”與紋額的“雕題”相結合,[32]即體現了中原文明對古代越南部族由身體而風俗的最初想象,也是蠻荒而遙遠的想象:“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并立,指則相交。”[33]“其俗男女同川,故曰交阯。”[34]據《史記》,早在上古傳說時代,帝顓頊高陽氏的聲教區域即曾“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35],帝堯時亦曾“申命羲叔,居南交”[36],帝舜亦曾“南撫交阯”[37],由是交趾早早地就成為一個表征華夏文明向南擴散的固定符號,是中國文化的“南極”。到明朝永樂再度將安南郡縣化后,崇尚復古和華夷之辨的明朝也仍然選擇了“交趾”這個古老命名,稱為交趾都布按三司。
(二)宣德遺恨的出使表達
永樂五年,明王朝以泰山壓頂之勢消滅了獨立的安南王國,將其重新納入直接統治的范疇。但20余年后,宣德皇帝即不得不割棄安南,讓其重新獨立。自此之后,安南再不屬中華。對此,嘉靖年間再一次面臨郡縣安南良機的李文鳳《越嶠書》直言是“千載之恨”,“使(明朝)死者之仇不復,國恥不雪”。[38]而身逢萬歷后期抗倭援朝氛圍的茅元儀,則與很多清算的明人一樣都對安南的“既得復失”感到“遺憾”,認為是棄守的決策錯誤,應該讓英國公張輔留鎮交趾。[39]在不能指責皇帝的語境下,批判者又多將怒火燒向了支持宣德皇帝的楊士奇、楊榮,斥二人為“陋儒”,乃“太宗皇帝的罪人”。[40]而其他人即使在總的方針上贊成割棄安南,但要么在具體處理策略上仍不滿意:“惜乎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為稍靡耳。”[41]認為當初沒能保住明朝作為宗主國的威嚴和體面。要么以儒家文化理想的普世化眼光,反過來為再度被遺棄而淪入黑暗幽谷的安南人民大鳴不幸,如丘濬《大學衍義補》之言:“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竝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42]與這些或激烈、或婉曲的遺恨心態相比,冷靜認為應該棄守,肯定“二楊”對于皇帝的支持乃是“老成之長慮”的“謀國者”的辯護和體貼不是沒有[43],但顯得殊為寥寥。由此可見明人對于宣德棄守安南的遺恨情結。
這一情結在宣德割棄后出使安南的使節詩文中有明確表露,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正德七年(1512)奉使安南的副使潘希曾。他有一首關于安南總印象的長篇紀行詩《南交紀事》,在詩中他多次隨文出注,指出安南黎利在宣德初年復國后,即又回到了之前的野蠻狀態——斷發、黑牙、赤腳、席地盤膝、操舟裸身等蠻夷風俗和沿海商業,這是安南人不懂感恩、自甘墮落、不思進化的結果,與丘濬“既得見天日,而又淪于幽谷”為安南人民“重不幸”的感慨,正是一體兩面。他希望安南重回華夏文明的仁厚懷抱,凸顯的正是中國中心情結和宣德割棄的不甘心理。[44]除此之外,潘希曾還多次在其他安南紀行詩中用自注等方式揭露安南的小國心態和文明落后的表現。其《卜鄰驛》詩題自注“交地褊小,往往迂其路以示遠”,正文亦言:“我嘗御風遍八垠,徒步北斗趨紫宸,回顧一瞬隘九真。蹊徑詰曲難具陳,華風漸染何時醇?”[45]《回渡富良江二首》詩題自注“江本不闊,而操舟者循岸沿洄以示險”,正文亦言:“富良江頭風日晴,王子乘春送客行。一棹中流歌未畢,隔江花柳已相迎。”[46]均揭露了安南外強中干、國土狹小的本質,有明顯的嘲諷之意,這也正是使臣偵察其國山川險要和虛實的“覘國”表現。
(三)晚明的安南形象顛覆
此時明朝國力足夠強大,安南雖內心和行動都可能不夠恭順和乖巧,但表面的宗藩禮儀總還小心翼翼地侍奉明朝為宗主國,尚不至于讓明朝天使有其他更多的不滿。然而到了南明永歷之際,其時由福建經廣東海路借道安南欲到南明行都昆明卻被安南軟禁的徐孚遠等人,就只有苦苦哀求“披發夷人”發放脫歸的份兒了。盡管如此,他還是固執地用“交州”這個強烈內地化的地名來稱呼這個讓他感到屈辱的安南,以表達今昔之間兩國地位仍未顛覆的情感訴求。
“南來虛負一帆風,王會猶然苦未同。披發夷人何意氣,擔簦客子甚怔忡。四分州土非全國,三統雄獅有上公。休恃文佳嘗反側,獻俘終獻大明宮。”[47]僻居福建海隅的南明使者,卻因為此時不愿行跪拜禮而被安南軟禁三個月。此時的安南自然是坐井觀天、狂妄自大的蠻夷:“井蛙有國堪尊大,不異當年笑子陽。”[48]在徐孚遠不多的“交行詩”里,卻充滿了“蠻人”“夷人”“夷服夷言”“夷釀”“蠻方”“蠻鄉”等諸多鄙夷字眼,可見對安南的“他者”感受。滄海桑田,世易時移,原先的宗主國和藩屬國似乎調換了位置,乘機要價的安南反要求明使的跪拜,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南明的節節敗退和勢力微弱:“天威未振小夷驕”,“千行涕淚王威弱,三月拘留臣節艱。”[48]安南形象的“自我”與“他者”的變異體現了明安實力的消漲和使臣親身體驗的差異,也說明了明人安南情結的多個層面。
四、和平下的交鋒:宗藩文學的底蘊
明人使越專集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值得正面探討,即封貢體制下的中越兩國文學交流,也即差序格局下的宗藩文學。鑒于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呈現兩國宗藩往來和詩歌唱酬中的和平美好一面,此處將重點放置在宗藩詩歌唱酬中的宗藩關系確認,并借助中越其他文獻,揭示明安宗藩關系在實際運轉過程中的禮儀交鋒和政治交鋒。
關于明代中越雙方對宗藩關系的認識和各自角色的體認,可用“事大”和“字小”各極其誠這一相互聯系的聲明來說明。天順六年(1462),奉使安南的錢溥即在與安南國王交涉迎接詔書和天使的儀注書信中概括說明了兩國的關系,云:“況我朝之于安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49]“事大惟誠”是明朝作為宗主國對安南的總體要求,希望安南對待明朝要做到真心的誠意和真實的恭順,表里如一,主要體現在宗藩禮儀的遵從和兩國邊疆關系的和睦上。這是越南作為藩屬國必須和應該完成的職責和角色,否則即會被明朝挑剔指責。“字小”則是作為宗主國的明朝要愛護體諒藩屬國安南,不僅體現在“厚往薄來”的貢物回饋上,也體現在“仁德懷柔”的文明感召之道上,即使兩國出現較為嚴重的政治和軍事裂縫,用武之威也總是后于用仁之德,要以宗主國的包荒之量和以觀后效之度來盡量容受。
當然,最能生動地說明兩國“事大字小”這一宗藩關系和角色確認的詩歌酬唱,還是正德八年(1513)奉旨冊封安南的湛若水、潘希曾與受封為國王的黎晭(越史稱襄翼帝,本名黎瀠,中國名黎晭)之間的唱和。這些唱和詩既見載于兩人的出使專集,也見載于《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五“癸酉洪順五年,明正德八年(公元一五一三)”條,文長不錄。此處不計中越文本的字句差異,而只論宗藩關系下的明安兩國交往實情。作為長期的地緣和文化上的強大近鄰,安南對待處于其北方的明王朝總有如下一體兩面的表現:一方面十分強調在宗藩關系上歸附明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是由兩國的實力對比決定的。說到底,“事大惟恭”是明安兩國基于自身國家實力和利益而合作采取的一種國家相處戰略,“在中國方面主要是需要越南方面表現‘恭敬’,即政治上的服從”,在安南方面,則需要得到中國方面的認可,如此方能有效地實現對于安南國內的政治控制權。[50]因此,安南需要對對明王朝表示必要的卑下恭順。正是有此一面的政治依附需求,《大越史記全書》在記載明安關系時,才會特意記載作為安南國王的黎晭與作為天朝上國使臣的湛若水、潘希曾的詩歌唱酬,來表現這種屬國和宗主國的政治關系確認。可以看到,黎晭詩主要是歌頌明朝的禮樂文明和明朝天子的仁義恩惠,贊美明朝天使的雍容文雅和未來的必將大用,表達作為屬國的“越甸”“南邦”會永遠追隨明朝所代表的“文軌車書”和“威儀禮樂”;而湛、潘詩則主要表現為居高臨下式的諄諄告誡,要求安南謹守“南服”屬國的“職方”“藩垣”本分,“畏天事大”,[51]自覺維護兩國的邊境和平,成為中國邊防在南的外藩和中國文明在南的外延。這是關于有差序的宗藩關系的典型聲明和角色扮演,詩歌唱和成了其間的政治默契表達。
另一方面則是,武裝脫離了明王朝實質管轄的黎利之后的安南又十分強調國家的獨立自主、自尊甚至自強,在以五嶺為界南北分治的前提下,極力堅持安南國的領土利益和安南國王的獨立尊嚴,此即安南史官吳士連所言:“大越居五嶺之南,乃天限南北也。其始祖出于神農氏之后,乃天啟真主也,所以能與北朝各帝一方焉。”[52]職是之故,安南在與明朝發生有關迎接詔敕的宗藩禮儀、邊境紛擾和其他沖突時,又不會完全甘于聽從明朝的安排和指示,而是可能“據理力爭”,往復論辯,以至國書往來,讓明朝留下“我聞交人最狂悖,解偵中原圖向背”[53]的不乖順印象。其中,在迎接詔書和天使等禮儀上,張以寧、錢溥、黃諫等使臣都曾與安南發生爭執,結果多是明使取得了勝利,安南屈服。但是在明朝與安南發生邊界劃分和邊疆紛擾時,洪武二十九年(1396)奉使的陳誠、呂讓和正統三年(1438)奉使的湯鼎、高寅等都曾作書多封與安南國王交涉,卻多是安南反復辯解,并不妥協,結果不了了之。由此可見,安南在事關本國自尊的面子和實際的重大利益時,會與明朝發生強弱不等的禮儀和政治交鋒。尤其到明朝滅亡的南明之時,兩國的實力徹底反轉,南明使臣反被要求在安南國王和權臣面前下跪,即更能說明宗藩文學的唱酬是一種以兩國實力為后盾的話語默契。
如果說從古代越南的史料和立場出發的越中宗藩文學的精神實質是“文化中國,政治越南”,即越南使臣在與中國進行宗藩文學交流時,希望越南在文化上可以追慕作為母國的中國,但在政治上卻要求適當的獨立和拒斥[54];則從明人出使越南專集出發的中越宗藩文學的精神實質,即該用“文化中國,政治中國”來概括,也即中國使臣在與越南進行宗藩文學交流時,不僅要求越南在文化立場上中國化,而且要求越南在政治立場上也恭敬乖順、“事大惟誠”,不搞表里不一的狡猾和欺詐,諸如“內帝外臣”[55]、國王一人兩名[56]和侵擾中國及他國邊境等。這說明中越兩國之間的宗藩文學在表達脈脈含情的宗藩封貢體制的和平美好之外,也會有來自文化和政治的沖突,特別是當兩國出現嚴重的政治裂縫(如黎利率領越南脫離明朝宣德的統治而獨立建國)和邊境沖突(如黎灝于天順至弘治間的崛起擴張)之時,明朝使臣和贈行的明朝大臣就會時不時在宗藩禮儀和安南的不遜動作上進行挑剔和責難。這說明宗藩封貢體制下的兩國關系確實并不平等,文化方面是一種以中國為主導、越南為配合的差序格局下的宗藩文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