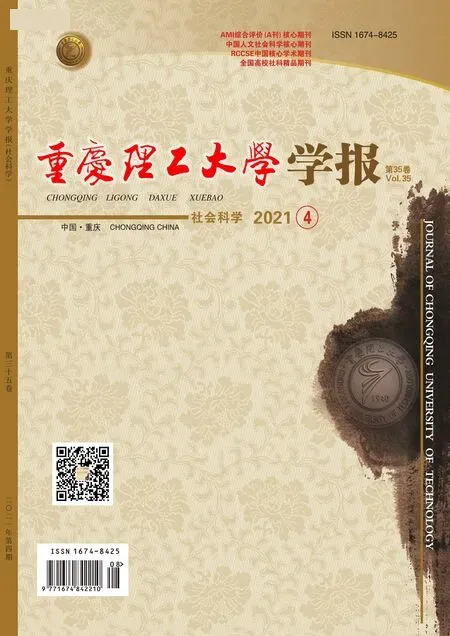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對懲罰性賠償的揚棄分析
胡海容,石冰琪
(重慶理工大學 重慶知識產權學院, 重慶 400054)
近年來,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不斷增強,要求提高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數額、遏制知識產權侵權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此背景下,可以實現賠償數額翻倍的懲罰性賠償很快成為了關注的焦點,仿佛一經引入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的現有問題全將迎刃而解。進行國際比較可以發現,懲罰性賠償并非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規則,特別是在大陸法系國家中幾乎難覓蹤跡。其間的原因及其影響令人深思。基于此,本文選取德國這一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進行分析,以期對我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構建提供更全面的視角。
一、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對懲罰性賠償的揚棄
(一)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的基本框架
在德國,知識產權這一概念是否存在一直備受爭議,其通常被稱為 “工業產權和著作權”。工業產權法包括專利法、實用新型法、外觀設計法及商標法等。考慮到我國的用語習慣,本文仍沿用知識產權一詞。德國自1871年統一以來,先后頒布了《德國著作權法》《德國商標保護法》和《德國專利法》,現行有效的前述法律均在2017年進行了最新修訂。德國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規則散見于各單行法中,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規則:
1.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是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主要的救濟方式。例如,《德國著作權法》第97條第2款規定:“故意或有過失地實施該行為的,負向受害人賠償因此而發生的損害的義務。在計算損害賠償時,也可以考慮侵害人通過權利侵害所獲得的利潤。損害賠償請求權也可以以假設侵害人獲得使用被侵害的權利的授予而需要支付的合理的報酬的金額為基礎計算。作者、科學版本的整理者、拍攝者及表演者也可以因非財產損害而請求金錢賠償,但以符合公平原則為限。”[1]134《德國專利法》第139條第2款和《德國商標法》第14條第6款具有類似的規定。概括可知,德國采用的損害賠償方法主要包括三種:權利人的損失、侵害人的利潤和合理的許可費。這與多數國家知識產權侵權賠償的做法基本一致。
2.不作為請求權
《德國商標法》第14條第5款、《德國著作權法》第97條、《德國專利法》第139條第(1)款均規定:“在有重復危險時受害人可以請求不作為。在首次存在違法行為的危險之虞,也存在該請求權。”[2]224這一請求權針對的是即將可能發生的侵權行為,對于及時制止侵權、防止損害后果擴大具有重要作用。這與法國的緊急措施和我國的停止侵權有相似之處。
3.銷毀、召回與讓與
《德國商標法》第18條規定:“商標或商業名稱的所有人在第14條、第15條、第17條的情形中可以請求侵害人銷毀為侵害人占有或所有的違法標示的商品。”[3]12《德國著作權法》第98條除了規定銷毀和召回外,還新增了“讓與”條款作為銷毀條款的替代,即“代替第1款規定的措施,受害人可以請求以不超過制作成本的合理價格將侵害人所有的復制件讓與給他”[1]136。這一救濟方式針對的是侵權產品,權利人可以選擇要求侵權人銷毀、召回或者轉讓給自己。這對于防止侵權人因侵權而獲利以及節約社會成本具有價值。
4.信息提供、出示與檢查
《德國著作權法》《德國商標法》《德國專利法》均規定,侵害人有義務及時提供涉嫌侵權的產品的來源信息,出示證書或檢查處于其有處分權的物。因未出示文件導致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實現有障礙時,可以要求侵害人出示處于其處分范圍內的銀行、金融或者商業文件。這一措施能夠有效降低權利人舉示證據的難度。
5.訴前侵權警告
《德國著作權法》第97條規定:“受害人在啟動法院程序之前應該警告侵害人,并給予其機會,通過作出以合理的違約金作保證的承擔不作為義務的承諾來解決爭議。只要警告是合法的,可以請求賠償必要的費用。”[1]135-136在德國,訴前侵權警告程序是啟動訴訟程序的前提條件,且在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是否存在懲罰性賠償的爭論
從德國現行立法的條文來看,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并無懲罰性賠償的身影,但學術界和司法界對于侵權獲利以及合理許可費是否具有懲罰性賠償的性質存在爭議。
德國法中的侵權獲利和合理許可費這兩種方法是由德國法院在審理著作權侵權和專利侵權案件中逐漸發展起來,隨后獲得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可并進而演變成德國成文法的內容的。“一是許可類比,即根據假定的許可損害來進行類比;二是返還違法所得。未經許可而使用他人受保護的權利的侵權人不應該比購買了授權許可并支付許可費的合法被許可人處于更好的境地。加害人也不能以這樣的詭辯來自我開脫,即欲獨占市場的權利人是不會將許可授予他人的。經2008年7月7日法律(BGBI I.S.1191)轉化的歐盟2004/48/EG號《知識產權實施指令》著重指出了損害賠償法上的特征。”[4]227
對于違法所得的性質,有觀點認為,“知識產權立法以過錯的程度不同為依據才產生了第三種損害計算方式。而在因過錯侵權的知識產權案件中,法院只根據權利人遭受的損失和被告的獲利兩種方式來計算賠償金。因此,這種根據被告過錯程度的不同而給予的賠償已經超過了傳統的賠償方法”[5]。通常認為,德國知識產權救濟中的侵權獲利源自德國發達的不當得利理論以及由此形成的《德國民法典》第812條的規定[6]313-314。“由于侵害的不法性,侵權人所獲得的,既無合法原因,也造成了權利所有人的損失。后者源自專利被賦予的法定內容,其將保護的發明排他性地分配給專利權人,保留給他以法定的形式獨自實施專利。它不需要專利權人的權利被剝奪以及財產減少。就此僅要求侵權人所獲得的是專利權人本應獲得的;并不要求它是專利權人已經獲得的財產。”[7]1053換言之,以專利侵權為例,侵權人侵犯的是專利權人享有的獨占實施權,這屬于沒有約定或者法定的原因不正當地獲得了利益,但是獨占實施權本身無法返還,因此需要將由此而產生的利益作為賠償金額返還給專利權人。由此可知,侵權獲利仍是權利人損失的組成部分。因此,侵權獲利被視為損害賠償的計算方式之一更為合理。
合理許可費則依據這樣的假設,即將侵權人視為被許可人的地位,一旦侵權人實施了侵權行為則意味著權利人喪失了許可費,因此將合理的許可費支付給權利人后則視其損失已得到了彌補。對此,學術界認為,這種計算方式不能為專利權提供有效的保護,因為侵害人所承受的風險非常小:如果侵害行為未被發現,侵害人可以從中獲利;一旦被發現,侵害人也只需要支付即使是守法的被許可人也需要支付的許可費,因而其處境不會比守法的被許可人差。從法律政策的角度而言,只有懲罰侵害人,才能達到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目的,從而有效地實現專利權的保護[2]130。雖然學者們在隨后的立法中曾建議規定懲罰性賠償,但是截至目前“在法律中設置一個雙倍于合理使用費數額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也沒有任何成果”[7]1048。政府堅信(也是正確地)按照許可費倍數的金額來支付損害賠償會造成某種形式的懲罰性賠償,與德國民法原則是不相符的[8]323。
此外,還有觀點認為,《德國著作權法》第97條第2款規定,作者、科學版本的整理者、拍攝者及表演者也可以因非財產損害而請求金錢賠償,這種“所謂的精神賠償的目的在于對精神利益的損耗給予充分的補償(在德語中為Genugtuung,即足額賠償,在英語中則為punitive damage,即懲罰性賠償)”[9]582。實際上,《德國民法典》第253條規定了兩種非物質損害也可以獲得金錢賠償的情形:一是法律的規定;二是因侵害身體、健康、自由或性的自主決定。顯然,《德國著作權法》第97條第2款的規定屬于第一種情形。可見,德國民法中早已承認包括精神損害在內的非物質損害,但是鮮有文章論及這屬于類似英美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實際上,即便是在英美法系中,早期設立懲罰性賠償的目的雖是為了彌補對精神損害救濟的不足,但是近代以來英美法也已承認了精神損害可以作為一種獨立的請求[10],而懲罰性賠償早已不再扮演這一角色。因此,德國著作權法似乎并無理由在21世紀的立法中還堅持英美法早在19世紀便放棄的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觀點。可見,將德國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對于精神損害賠償的金錢賠償理解為類似英美法上的懲罰性賠償并不妥當。
綜上可知,德國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體系,但是并無懲罰性賠償的相關規定。雖然學術界有關于侵權獲利和合理許可費具有懲罰性質的分歧,但是通說仍傾向于認為這兩種救濟方式只是損害賠償的計算方式而已。
二、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揚棄懲罰性賠償的原因分析
在德國,雖然存在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單行法,但是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仍然與傳統的民事侵權救濟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客觀來講,正是懲罰性賠償與德國民法中的全面賠償格格不入,導致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難覓懲罰性賠償的蹤跡。
(一)懲罰性賠償與德國民法理論不符
在羅馬法時期,具有懲罰性質的法律責任比比皆是。比如在《十二銅表法》第八表中記載:“實施非現行盜竊者,加倍賠償損失。……對于寄托案件,授予雙倍之訴。……如果諸監護人偷了被監護人的物,授予雙倍之訴對抗他們。”[11]羅馬法上關于私犯的損害賠償,并不限于賠償實際損失,賠償額可以相當于損失額的1~4倍。羅馬法學家解釋:“稱其中的1份是賠償私犯造成的損失,其余的部分則是屬于罰金性質,仍保留著舊時贖罪金的痕跡。”[12]857歐洲的所有民族幾乎都在中世紀受到作為古代文化一部分的羅馬法律的影響。德國相對來說較晚,早不過15世紀中葉,才與羅馬法有了這種基礎;然而其后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羅馬法繼受”,卻遠遠勝于法國[13]253。然而,德國在繼受羅馬法的過程中卻將具有懲罰性因素的法律責任逐漸從德國民法中分離出去了。
從中世紀到1871年德國統一之前,德意志呈現邦國林立的分裂狀態。在連形式意義上的政治中心都沒有的德意志當然也很難產生出統一的法律以及法律階層。但是有意思的是,在19世紀德國學者也曾經就是否在特定的情形下適用懲罰性賠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當時對于非填補性賠償,特別是懲罰性賠償而言,學者們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在德國,懲罰性賠償雖然并非隨處可見,但是在德國的部分州中也是十分常見的。比如,普魯士民法典規定,在特定的情形下,考量侵權人的過錯程度后法院可以允許原告獲得超過自己損失部分的賠償。而在另一方面,巴伐利亞民法典認為這些侵權應通過刑法來處罰,因此并不存在雙倍及四倍的訴訟[14]。在《德國民法典》于新世紀的頭一天付諸實施時,人們認為它代表了德國法學的勝利[15]55。《德國民法典》終結了這場爭論,但是對待懲罰性賠償的方法卻與英美法系截然不同。“在起草德國民法典的過程中,之前法典中能夠找到的懲罰性賠償的所有痕跡都被抹去了。”[5]這是因為德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特別是走向統一的過程中,“以私人作為檢察官,或由私人獲取多倍賠償,無非剝奪國家權力與攫取國家獲取罰金的利益。因而德意志普通法固然具有與羅馬法類似的多倍賠償民事制度,但該制度在現代國家制度形成過程中,不利于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因而德國雖然繼受羅馬法,但并未繼受多倍賠償的民事制度”[16]201。
在德國民法典制定過程中,特別是損害賠償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德國近現代損害賠償法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弗里德里希·蒙森(Friedrich Mommsen)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通過定義損害的概念總結和簡化了龐雜的中世紀損害賠償法,創立了聞名于世的“利益說”。計算損害之時,人們要假設,如果致損事實沒有發生的話,受害人現在的財產總額會是多少,然后將這個假設總額減去受害人現有的財產總額,所得出的差額就是損害。根據德國通說,德國民法典第249條第1款確立了全面賠償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損害賠償義務的范圍一般與損害產生的原因、侵害的情節和侵害人的主觀惡意等因素無關,而只與損害本身的程度有關。簡言之,有多大的損害,就有多大的損害賠償義務,既不能多賠,也不能少賠。這樣一來,德國民法不僅僅將損害本身的程度與損害發生的原因分開來考慮,而且將賠多少的問題與賠與不賠的問題分開來考慮[17]。
(二)德國法院拒絕適用懲罰性賠償
德國法院對懲罰性賠償的拒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國內法層面,德國法院一直嚴格遵守《德國民法典》的規定,否認賠償金具有懲罰或遏制的作用;二是在國際私法層面,德國法院一直拒絕執行包含有懲罰性賠償金的外國裁決。
在國內法層面,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經常強調賠償是損害賠償法的唯一基礎。這種強調逐漸演變成一種普遍遵守的原則,并在整個20世紀不斷被重復。在卡羅琳案(1)參見Judgment of November 15,1994,BGHZ 128,1。中,德國法院對于人身權案件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在該案中,一家德國小報發表了一篇聲稱是對摩納哥公主卡羅琳的獨家采訪,并附上了公主及其家人的照片。但這篇專訪實際上是子虛烏有的。最后,德國漢堡上訴法院判決給予原告180 000馬克的賠償金。這是德國法院針對侵犯人格權給予的最高額賠償。德國學者將本案與同時期發生在美國的Cher v.Forum International,Ltd.案(2)參見Cher v.Forum Int’l Ltd.,692 F.2d 634 (9th Cir.1982)。對比后認為,“雖然采用了一種不同于損失賠償金的方法,但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采用相同的論證達到了美國法院判決的懲罰性賠償金的效果。……德國法院對于侵權賠償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過去,侵權案件關注的重點是原告,即滿足原告的需求。現在,侵權案件關注的重點轉向被告,即遏制侵權人不再實施類似行為或防止將來發生類似行為。因此,這不再是傳統觀念中的賠償和滿足,而是更符合懲罰性賠償的理念”[5]。但是,多數學者仍然認為懲罰性賠償的懲罰目的與德國法中的填補性賠償性質不同,基于公共政策的原因不應被執行。即使是要執行包含有懲罰性賠償金的判決,也“限于該賠償金系為賠償當事人之精神上損害,且該賠償金數額非不適當者為限”[16]197。
在國際私法層面,1992年發生的一個案件具有里程碑意義。一名14歲的美國女性在美國加州對一名德國被告提起了性虐待之訴。美國加州法院裁決給予原告400 000美元的賠償金,其中包含懲罰性賠償。原告申請執行時發現被告已從加州遷居德國,并且在美國沒有留下任何財產,于是便向德國法院申請執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后認為,對該份判決中的醫療費、續醫費、因焦慮和傷痛等產生的損失部分均可以執行,但是對于其中的懲罰性賠償不予執行。理由在于該份判決中的懲罰性賠償與德國法中只賠償原告遭受的損失的基本原則相違背,同時這也與德國法的公共政策相違背(3)參見Judgment of June 4,1992,BGHZ 118,312,translated in 32 I.L.M.1320 (1993)。。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拒絕執行包含有懲罰性賠償金的外國裁決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在民事訴訟中承認和執行這類裁決會違反德國基本法中的憲法性權利,因為懲罰性賠償處以的是刑事處罰,但是卻沒有給被告提供刑法上的程序性保護[18];二是,適用懲罰性賠償會違背德國侵權法填補性損害賠償的傳統;三是,懲罰性賠償金在本質上是懲罰性和報復性的,這會違反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28條第4款中公共政策條款的規定[5]。從德國國際私法的規定來看,司法保護的對象并不限于德國人,但是法院不會裁決給予實質上會超過損失的賠償額。這也就意味著禁止給予懲罰性賠償。在討論《歐共體規則》第24條時,有學者便提出“如果立法設立非賠償性條款,比如懲罰性賠償,這會與歐共體的公共政策相違背”[19]。最后實施的《歐共體規則》第24條宣布非賠償性的條款與公共政策相違背。
三、揚棄懲罰性賠償的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效果分析
從德國現有知識產權的立法以及司法實踐來看,德國并無在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設立懲罰性賠償的打算,甚至更準確地來說,德國已有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規則使得懲罰性賠償適用的空間十分有限。盡管沒有懲罰性賠償,德國現行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體系仍然運行良好。
(一)合理許可費成為德國主要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
從實體規則來看,脫胎于《德國民法典》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規則一方面堅持了《德國民法典》中關于全部賠償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結合知識產權自身的特殊性在司法實踐中形成了侵權獲利和合理許可費這兩種計算方式,并最后成為《德國專利法》第139條的一部分。在實踐中,由于比另外兩種方式更加簡單,合理的許可費屬于主要的也是受害人最通常選擇的損害計算方式[2,7]。有研究表明:“95%的專利權人會請求許可費賠償”[20]108。對于侵害人的獲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未產生重要意義,因為往往所計算出來的利潤偏少,后來隨著“直接成本”原則的使用,權利人可以要求返還更多的利潤,因此在2001年以后這種計算方法才更多地被采用[2]130-131。此外,關于銷毀、召回與讓與請求權的規定的主要作用在于恢復原狀,這一規則與損害賠償規則一起共同貫徹了《德國民法典》確立的讓權利人恢復到權利未被侵害之前狀態的思想。
與此同時,從程序規則來看,信息提供、出示與檢查規則不僅能夠降低權利人舉證的難度,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解決糾紛的成本,共同為知識產權侵權救濟提供了較為全面的保障。
(二)訴前侵權警告和分訴制度在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訴前侵權警告是德國專利和著作權侵權救濟中的一項特殊規則。雖然多數國家也允許權利人在訴前進行侵權警告,但是類似德國這樣作為必要程序的卻不多見。更為重要的是,德國法律要求收到訴前侵權警告的當事人應當積極應對,一旦置之不理且又在隨后的侵權訴訟中敗訴,那么權利人由此產生的包括律師費在內的訴訟費用均要由侵權人來承擔。考慮到德國的律師費用較為高昂,因此收到訴前侵權警告的當事人通常都會積極與權利人進行溝通或協商。這樣一來,訴前侵權警告規則便在預防侵權損失的擴大方面以及糾紛化解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在德國專利訴訟中有一項特殊的“分訴制度”,即將專利侵權訴訟與專利侵權賠償訴訟相分離。質言之,法院會先對是否構成侵權進行判決,隨后再對專利侵權賠償進行判決。由此產生的直接后果是“粗略地看,德國每年90%的專利侵權案件就損害賠償問題達成了和解”[21]。這也是德國絕大多數的專利侵權案件最后均是以合理的許可費結案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德國通過《德國民法典》《德國專利法》《德國商標法》《德國著作權法》建立起來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規則有效保證了權利人即使在面臨侵權時也能獲得全部賠償,這對于遏制知識產權侵權案的多發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同時,德國專利法和著作權法存在的訴前侵權警告和分訴制度在預防侵權損失擴大以及糾紛化解方面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因此,揚棄懲罰性賠償對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的影響十分有限。“多數在國際上比較活躍的公司都會將德國作為專利訴訟的首選,這已不再是個秘密。如前所述,歐洲有一半以上的專利訴訟是由德國法院審理的,這種傾向性還在增強。這一現象的原因通常被解釋為效率、相對較低的成本及判決質量這三者的結合。”[22]32
四、啟示:足額賠償是影響知識產權侵權救濟效果的關鍵因素
筆者在進行國際比較時發現,如果說懲罰性賠償在懲罰和威懾知識產權侵權方面功不可沒,那么沒有懲罰性賠償的德國是否出現了知識產權侵權案頻發的結果?客觀來講,這一結果并未出現。相反,普遍認為,德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體系乃至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還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實際上,世界上多數國家并未在知識產權侵權救濟中建立懲罰性賠償。究其原因,筆者認為,知識產權侵權救濟是否有效的關鍵可能并非在于是否設立了懲罰性賠償,而是在于是否實現了足額賠償。
損害賠償金的計算是影響足額賠償的主要因素,這也是各國知識產權侵權救濟面臨的共同難題。背后的原因也是大致相同的:一是因為缺少證據;二是因為缺少計算規則。為了解決證據問題,德國規定了十分細致的信息提供、出示與檢查規則。對于計算規則問題,德國建立的損害賠償計算方法與其他國家并無明顯差異,但是德國借助訴前侵權警告和分訴制度使得合理許可費成為絕大多數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計算方式。的確,沒人能比權利人和侵權人更知曉該項知識產權的真正價值了。可見,德國雖然揚棄了懲罰性賠償,但是用適應德國國情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框架實現了足額賠償的目的。
目前,全社會普遍對設立懲罰性賠償以便解決損害賠償難以計算及偏低的問題寄予厚望。從表面來看,懲罰性賠償的確能夠直接增加權利人所能獲得的賠償金額,但是要真正發揮懲罰性賠償背后所蘊含的足額賠償或者遏制侵權功能卻還任重而道遠。以商標侵權為例,我國自2014年5月1日以來適用懲罰性賠償,但是七年以來,懲罰性賠償對于提高賠償數額而言的作用微乎其微,因為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比例幾乎可以忽略。這一現狀產生的原因則在于“99.6%的商標案件”適用的是法定賠償[23],而法定賠償不能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的計算基數。進一步深究可以發現,法定賠償適用畸高的原因則在于可以作為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的原告的損失、被告的獲利以及許可費本身無法計算出來。可見,在現行知識產權侵權救濟框架下,我國的懲罰性賠償與原告的損失、被告的獲利、許可費以及法定賠償之間正陷于邏輯怪圈而無法自拔。因此,我國雖然建立了世界上種類最多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也建立了與知識產權發達國家大致相同的知識產權侵權救濟體系,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如何計算損害賠償這一核心問題。
基于此,筆者認為,德國的實踐證明,足額賠償權利人是知識產權侵權救濟最核心的任務。無論是原告的實際損失、被告的獲利、合理許可費還是懲罰性賠償,均是實現這一核心任務的方式而已。因此,如果不能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提供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國方案,只是簡單引入懲罰性賠償可能很難發揮預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