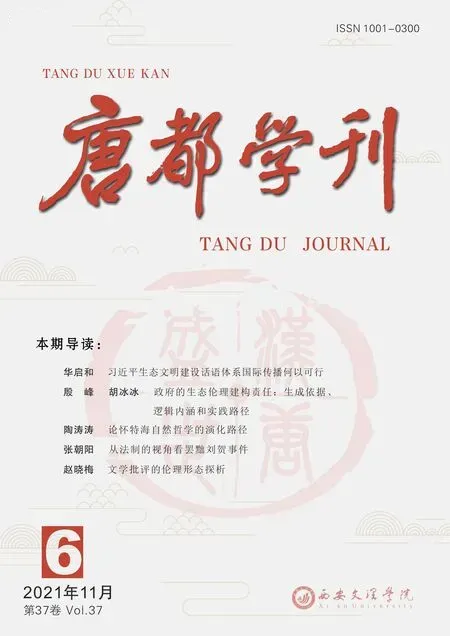阿拔斯王朝翻譯運動的歷史意義探究
黃知韻,張 敏
(西北大學 外國語學院,西安 710127)
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揭開了伊斯蘭文化創造的序幕,以翻譯方式繼承了東西方古代文明,被譽為“東方智慧的第三次浪潮”。這一時期的翻譯運動始于倭馬亞王朝,由少數通曉多種語言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將希臘醫學、哲學、自然科學等著作譯為阿拉伯語。然而,阿拔斯王朝建立前的翻譯活動還處于萌芽階段,只能歸為學術活動,并未構成完整的學術體系。阿拔斯王朝在承襲前朝豐富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吸收阿拉伯半島文化及同時期外來文化,將翻譯運動推向高潮,其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目前,學界關于阿拉伯翻譯運動的研究集中于對完整翻譯運動史實的論述或成因分析,蔡偉良在《中世紀阿拉伯翻譯運動與新文化的崛起》一文中梳理了阿拉伯翻譯運動的起始期、鼎盛期以及積極影響;丁瑞忠的《試論阿拉伯帝國的翻譯運動》在概括這一歷史事件的基礎上,分析了阿拉伯帝國翻譯事業興起和發展的原因及成果;楊文炯、張嶸的《伊斯蘭教與中世紀阿拉伯翻譯運動的興起》側重于闡述伊斯蘭教精神對阿拉伯翻譯運動的影響。國外相關研究則將目光聚焦于阿拉伯帝國的宗教、醫學著作及對外關系。本文結合阿拔斯王朝的歷史語境,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社會歷史框架下,探究阿拉伯翻譯運動興盛于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多維因素,探尋其對阿拉伯世界乃至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貢獻、歷史意義及對當今翻譯人才培養及跨文化交流的啟示價值。
一、阿拔斯王朝翻譯運動興盛的多維因素
在倭馬亞王朝時期,阿拉伯穆斯林已充分意識到吸收外民族高度發展的精神文化的重要性,為適應社會實際需要,哈里發哈立德·本·耶齊德組織起一批精通古敘利亞語、希臘語或波斯語的學者,專注于醫學以及藥理化學方面的古籍翻譯,并進行了更廣闊學術領域的翻譯探索,多重因素相互疊加,促成了阿拔斯翻譯運動黃金時代的到來。
(一)地緣政治因素
自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發曼蘇爾在巴格達建都,作為王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巴格達的重要地位就已經凸顯出來。巴格達位于西亞兩河流域,地處東西方交通要道,縱觀世界文明史,河流與文明相伴相生,優越的地理位置為文化交流創造了良好條件,加速了各國典籍流轉,為大規模翻譯活動提供了豐富的源文本。
前倭馬亞王朝首都大馬士革經歷數次政權易手后交由穆斯林統治,在此之前,大馬士革曾是重要的希臘羅馬文化中心,以希臘語作為官方語言,而阿拔斯朝新都巴格達則靠近波斯薩珊王朝故都泰西封(Ctesiphon),在伊斯蘭文化統治前曾受波斯文化影響,所以在當時的翻譯運動中,有相當一部分波斯譯者參與譯著,大量波斯典籍被譯為阿拉伯語保留下來。“波斯的影響,挫折了阿拉比亞人原始生活的鋒芒,而為一個以發展科學和學術研究為特點的新紀元鋪平了道路。”[1]通過翻譯他族經典著作,實現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互通,翻譯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同時,波斯貴族曾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政權中頗具影響力,哈里發也急需得到這一力量的支持,以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與身份認同。因此,地緣政治因素無疑是阿拔斯王朝翻譯運動蓬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二)宗教文化因素
在倭馬亞王朝初期,國內政局基本穩定,但依然存在部分政治反對派及對統治不滿的宗教學者,基督教影響尚存,伊斯蘭教作為一個較為年輕的信仰,在不同宗教文化的沖擊下努力站穩根基。在伊斯蘭教興起初期,傳播教義只能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且學術闡釋主要圍繞《古蘭經》展開。除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以外,早期穆斯林未能給征服地區輸入先進文化或科學技術,僅著眼于鞏固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地區的統治。早期翻譯活動的目的局限于推動伊斯蘭文化傳播,出于宗教目的,在翻譯過程中對宗教相關著作的原意改動較大。該做法雖能起到一定的傳教作用,但卻違背了翻譯的基本原則,未能準確傳遞原文信息,失去了對原作的承襲意義。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帝國的伊斯蘭化進一步加深,同時注入了一批新鮮宗教文化血液。《古蘭經》對于猶太教、基督教等外教派態度較為寬容,尤其對于基督教徒,《古蘭經》稱其為“與穆斯林最親近的人”[2]146。在該教義指導下,“阿拔斯帝國已經成為伊斯蘭帝國,而不再是倭馬亞式的‘阿拉伯帝國’”[3],大批異教徒與穆斯林通婚,縮小了各民族間的意識形態差距,譯者群體的宗教結構大幅調整。經過伊斯蘭意識形態過濾后的皈依者帶來了活躍的學術氛圍及非伊斯蘭神學觀念,語言學、文學、法律、哲學、數學等多學科體系逐漸形成。
伊斯蘭文化在阿拔斯王朝進一步豐富,崇知尚學精神成為這一時期翻譯運動興盛的精神淵藪,愈加多樣化的內在宗教精神外化為翻譯運動的源動力,推動了不同宗教譯者群體的翻譯行為,多元信仰相互碰撞,翻譯規模不斷擴大,譯著類別、內容也因包容的宗教文化態度而更加豐富。翻譯運動的興盛由多方因素促成,在宗教文化層面,對于各種宗教信仰的接納是翻譯運動得以蓬勃發展的前提。若穆斯林完全排斥異教,迫使他教教徒皈依伊斯蘭教,則會大大減少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在翻譯活動中的參與度,打擊譯者群體多樣性,翻譯研究視閾也勢必受到影響。
(三)科學技術因素
科學技術方面,兩點因素共同推動了翻譯事業的發展,一是早期文獻譯本基礎,二是造紙術的傳入。
先知穆罕默德有言:“學問分兩類:宗教的學問和身體的學問(醫學)。”[2]28倭馬亞王朝的翻譯家們遵循這一訓言,對醫學、哲學和化學等學科著作進行了零星翻譯,為后朝翻譯運動黃金時代的出現做了鋪墊。“至于伊斯蘭民族的醫學、邏輯學、數學等自然科學,從一開始就是系統的。因為對其局部的研究,早就在希臘、印度和波斯等國家里開展過了,已進入了整理、記載和分析階段了。到了阿拔斯時代,這些學科都完整的譯成了阿拉伯文,無須從頭做起。也許,轉述學科的著述者們看到自然科學嚴密的體系時,照搬了它們的做法,增加了一些他們認為好的體例。”[4]早期伊斯蘭教已有的科學探究及著作譯本為翻譯運動的繁榮提供了便利,阿拔斯朝的翻譯家們只需在整理好的文獻基礎上進行審校或重譯,這就大大提高了翻譯的準確性。
新興技術發展在阿拉伯翻譯運動中的地位不可否認,但技術發展對于早期文明傳播同樣重要,并不屬于阿拔斯王朝所獨有,因此不能作為阿拔斯王朝大規模翻譯活動出現的特有動因。但造紙術的傳入確為帝國的文化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帝國的第一家造紙廠位于中亞絲綢之路的撒馬爾罕市。在被伊斯蘭征服之前的幾個世紀,這座城市已經是波斯帝國最繁華的城市之一,一直到中世紀都是波斯的學術中心。東方商道的暢通為穆斯林國家帶來造紙技術,造紙術的傳入對翻譯運動的影響顯而易見,阿拉伯人用價格相對低廉的紙張代替了昂貴的羊皮紙,使得文字記錄和書籍流通更加便利,擴大了人們對學術著作的需求,從而推動了翻譯運動的大規模出現。
(四)譯者素質得到了提高
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發麥蒙在曼蘇爾皇家圖書館的基礎上建立了“智慧宮”,網羅各界學術精英進行翻譯工作。史學家亞庫比曾描述過巴格達的學術之風:“巴格達的學者教育水平更高,那里的專家在傳統方面更有見識,文法家在句法上更為可靠……邏輯學家思維更為清晰,傳教士也更有口才。”[5]雖然這一時期的譯者不是真正的翻譯家,但都曾受過嚴格的哲學及邏輯訓練。其中部分敘利亞基督徒,為提升語言能力,特地返回希臘學習,他們以母語敘利亞語作為翻譯中介,在翻譯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阿拔斯時期的翻譯者們以其出眾的專業能力、認真的翻譯態度以及對科學的無限熱情搭建起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橋梁,成為推動翻譯運動蓬勃發展的又一重要動力。
隨著學術知識普及和各類書籍傳播,譯者群體的科學文化素養也得到了全面提高,在天文、醫學、哲學等方面知識儲備的增加,使翻譯活動不僅僅停留在機械的語碼轉換層面,而是建立在理解甚至精通文意的基礎上,從翻譯質量和翻譯速度等多方面提高了翻譯水平。
二、阿拔斯王朝翻譯運動的歷史貢獻
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翻譯運動的黃金時代,在翻譯基礎上開展的學術研究及文化活動,徹底改變了阿拉伯民族早期物質上、精神上的匱乏,推動了中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孕育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
(一)推動自然科學發展
在阿拔斯王朝這一翻譯運動的黃金時代,大量波斯、希臘的自然科學及醫學著作被譯為阿拉伯語。翻譯家在翻譯過程中學習天文地理,將源語文本消化后進行創造性翻譯,用阿拉伯語為原著語義不明或晦澀難懂之處做批注和解釋,再用便于穆斯林接受的目的語輸出,增強了文本的普適性,促進了穆斯林科學文化的普及。“在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的八十年中,上述民族的文化精華都被用阿拉伯文記錄了下來。原來對算術、幾何、醫學等術語一無所知,對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和哲學根本沒聽說過的阿拉伯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用阿拉伯語來表達歐幾里得的最精細的理論,表達印度數學中的正弦定理,表達亞里士多德的唯物論、托勒密的天文學原理,以及蓋倫的醫學、比茲萊吉姆海爾的格言和波斯國王的政治了。”[6]通過學習譯著,阿拉伯人在本土醫學的基礎上構建了伊斯蘭醫學體系,從理論到臨床,修正并彌補了阿拔斯王朝以前的醫學空白,阿拔斯時期醫學成就碩果累累,舉世矚目。與此同時,藥物學、植物學、數學、物理學等領域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多部權威性著作問世,對中國、阿拉伯世界、歐洲現代科學的勃興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無論是出于哈里發個人喜好抑或服務于宗教儀式,對于占星術和天文學著作的翻譯都推動了阿拉伯近代科技的發展。部分翻譯家通過翻譯典籍成為天文學家或科學家,實現了身份的轉變。不少阿拉伯人在閱讀翻譯作品之后,對天文學和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繼續進行翻譯,歐幾里得、托勒密的主要著作也在這一時期譯為阿拉伯文。典籍翻譯與科學發展相互促進,一時間學術之氣蔚然成風。
(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形成
在自然科學蓬勃發展的同時,從思想文化層面分析,翻譯運動孕育了阿拉伯—伊斯蘭的文化。隨著阿拔斯帝國的擴張,伊斯蘭文明也被帶到了廣大被征服地區。倭馬亞時期的伊斯蘭教在被征服地區只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存在,基督教在當地依舊影響深遠,居民信仰未有太大改變。隨著通婚、政治依附等各方面因素影響,阿拉伯帝國的伊斯蘭化在統治地區逐步推進,與當地文化融合成燦爛而復雜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7世紀后伊斯蘭文化上升為地中海的主流文化,阿拉伯帝國成為當時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中心,并強烈地向外輻射。”[7]
語言的統一有利于化解意識形態矛盾,促進民族文化認同。在翻譯運動過程中,進一步普及推廣的阿拉伯語成為帝國的官方語言,周邊國家文明漸衰,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地位逐漸成形。沒有阿拔斯翻譯運動的繁榮,就沒有伊斯蘭文明新的文化構建。此后,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西班牙大放異彩,在阿拉伯人統治伊比利亞半島時期,對西班牙民族文化及語言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在歐洲文明形成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阿拉伯烙印。盡管阿拉伯帝國因宗教和政治斗爭分崩離析,但翻譯運動留下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依然熠熠生輝。
三、阿拔斯王朝翻譯運動的歷史意義
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國的第二個世襲王朝,前后延續五百余年。這一時代興盛的翻譯運動在多重合力之下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推向巔峰。盡管9世紀后半葉的阿拉伯帝國勢力日衰,哈里發大權旁落,但其文化的影響從未減弱。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翻譯學科已不僅僅局限于語言領域,跨學科翻譯已成未來趨勢,這是一種新挑戰。目前高校翻譯人才的培養主要側重于人文社會科學方向,而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方向文本專業性較強,翻譯難度較大,缺乏相關領域的翻譯人才,語言能力與專業能力不對等的問題普遍存在。在阿拔斯翻譯運動時期,哈里發麥蒙對占星術情有獨鐘,曾召集一批學者進行占星術著作翻譯及研究。智慧宮中的某些譯者同時也是杰出的天文學家,在翻譯的同時還需進行精確的天體測量及計算,在這一過程中,翻譯作為獲取知識的工具為自然科學發展提供了便利。就譯者而言,翻譯活動具有復雜性,若要完成翻譯任務,數學、天文學以及語言學知識缺一不可,對于翻譯家的綜合素質要求極高。某些印度科學著作,為了便于記憶,均用詩歌文體呈現,給當時譯者的理解和翻譯造成了極大困難。早期翻譯家需要從梵文詩歌中解讀源文本內涵,再根據譯文內容理清所講算法步驟。阿拔斯時期的翻譯家無疑是跨學科人才的杰出代表,面對日益提高的跨學科需求,當代譯者也能夠從中借鑒一二。翻譯活動并非孤立的毫無靈魂的符碼轉換,而是以一種或多種語言為媒介的信息傳遞行為,其最終目的在于滿足人類文明及不同社會文化的信息傳遞需要,僅將目光局限于語言本身是遠遠不夠的。當代翻譯研究應實現多學科深度融合,打破“語言中心主義”的藩籬,推動跨學科發展,努力構建全新的學科共同體。翻譯人才應積極尋找新的學術增長點,著眼于不同領域,進行多維度翻譯研究,將翻譯與具體學科實踐相結合,整合跨學科翻譯研究成果,增強翻譯人才核心競爭力。
其次,良好的學術環境是推動知識進步、實現學術創新的前提。阿拔斯王朝時期,翻譯活動在國家的號召下有組織、大規模地開展,注重并獎掖學術活動,設立學術機構,整個巴格達城的學術氛圍濃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得到了長足發展。這為其他國家學術環境的進一步營造提供了借鑒。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國際間學術交流日益密切,“智慧宮”的建立使翻譯運動進入高潮,不同學派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學術爭鳴與自由討論之風盛行,這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高校學風建設帶來了有益啟迪。高等院校作為科研風向標,肩負著為社會培養和輸送科研人才的重任。大學生作為高校教育的主體,可塑性較強,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提高學生跨學科綜合能力是高校教學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優良學風是治學之本,良好的科研風氣能夠育人于無形,對學生的創新意識及創新能力培養發揮著啟蒙與推動作用。學術發展與學術環境密不可分,營造優良的學術氛圍為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提供保障條件,進一步推動科技創新發展。
再次,科技發展將世界各國緊密連結,多元文化碰撞成為當今世界文明發展的主題。在上文中筆者著重分析了阿拔斯王朝緣何成為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的黃金時代,其中穆斯林對待其他宗教及異族文化的包容態度至關重要。歷任哈里發從波斯、印度搜集古籍,嘔心瀝血地組織基督教或猶太教徒合力翻譯,拋開宗教排異性,用開放的眼光對待各民族文化。這正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百年間就吸收了古希臘羅馬千年文明精華的主要原因。翻譯的目的在于文化交流與傳播,這也啟示中國翻譯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客觀審視、批判吸收外來文化,合理運用翻譯這座橋梁,在浩如煙海的世界文化中展示中華民族文化之精粹。
綜上所述,阿拔斯王朝對待學術活動的開放包容態度,引領阿拉伯翻譯運動步入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翻譯運動的蓬勃發展,推動了阿拉伯帝國自然科學的進步,為早期科學與文化傳承以及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夯實了學術基礎。盡管阿拉伯帝國式微,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特質會以新的方式延續。尤其在“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推進的背景下,阿拔斯王朝翻譯運動提供給世人更加深刻的歷史視角,為沿線國家翻譯人才培養及中外文化往來相長提供了有益借鑒。